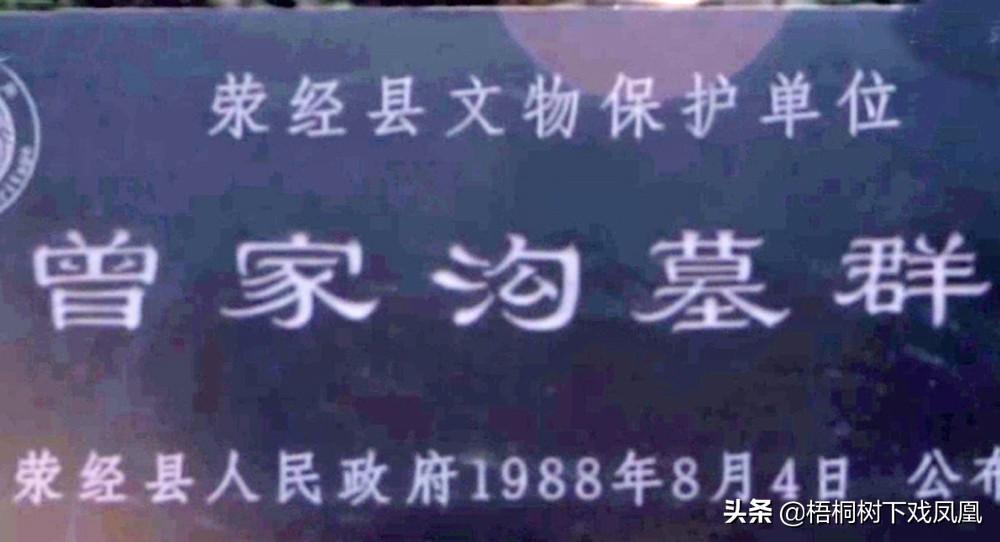遗珠:段晴老师三十年前旧作一篇
我生于1953年,如今,已进入不惑之年。与我同龄的女性,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人。我也不例外,每天穿梭在教学、科研、家庭和第二职业之间。一天到晚,有做不完的事。虽然十分忙,忙得很少回想自己走过的路,但我只要回首往事,最愿意回味的,要算是在北京大学度过的那些年代。
与我同龄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坎坷的经历。正当我们应该受中学教育的年龄,就陷入了那场铺天盖地的灾难之中。我是我的同龄人中的幸运儿,当我到了该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龄时,就十分幸运地跨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但是当时的我不知道何谓知识,何谓科学,当我万幸进入北大时,简直就是个“白丁儿”。那时候,工、军宣队还在北大,一名军官派我和其他十几个和我一样的“白丁儿”去学习德语,我那时竟然不知道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伟大的马克思就是德国人。在那个时代,正是“学而无用论”统治青少年的时代。我的同学们来自内蒙、黑龙江两大生产建设兵团,我们虽然都是科学的“白丁儿”,但却负有“上、管、改”的使命。教我们的老师刚刚从农场劳动改造归来,一个个都还是心有余悸。记得我第一次接触到一位赫赫有名的德语教授时,他向我这样介绍自己:“文革前我执行了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是资产阶级的教授。”当时我们正在校园内挖防空壕,把那漫山遍野的秀色挖得遍体鳞伤。我被名教授的对人性、对人性尊严的自我贬低惊得目瞪口呆。那时候,北京大学图书馆尽管藏书万卷,却处于封存状态,特别是西方文学作品被视为洪水猛兽不对学生开放。学生是“白丁儿”,老师不敢教,图书不开放,现在回想起来,在那时的环境中上大学,就好像在大海边的荒滩上漫步,有可能发现大海,但也有可能一直在荒滩上漫游下去,发现不了大海。
 (左二为段晴老师)
(左二为段晴老师)
我那时很用功,尽管不知道学习好一门外国语有什么窍门儿。我用的是最笨的办法,背课文。一早爬起来就背课文,新的课文还没有教,就已经会背诵了。课文背完了,就背德语的毛选“老三篇”,背完毛选,又去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至今还记得其中的几段。我对教过我的老师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面对社会的风浪.他们虽然心怀余悸,他们虽然和我们这群“白丁儿”极少有沟通的基础,但他们面对好学的学生有着极强的传授知识的责任感。有的老师知道课堂上的知识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就暗地里把自己的私人藏书借给我,有时还风趣地加上一句:“你要批判地阅读喔!”当图书可以凭借老师的条子外借时,教我的老师不怕承担责任,开条子给我。后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被指责为走白专道路,一些老师也因此受到指责。用功读书,何罪之有。尽管如此,我终于还是发现了大海。那知识的海洋中有那么多人类智慧的瑰宝,它们震撼我的心灵,我的思想,强烈地吸引着我。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读书。
大学时代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一家出版社工作,任编辑。在这个时期,不论是下工厂实习,还是去农村锻炼,我都没有间断过学习。我自学英文、法文。为补足文科基础的久缺,我自习古代汉语,广泛阅读中国历史、文学作品。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全国高校恢复研究生招生的第一年,即1978年,我通过了硕士研究生考试,再一次跨入北京大学的校门,并且非常幸运地做了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的弟子。
研究生时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代。在这个时期,我结识了一些性格开朗、才华横溢、且多才多艺的同学,他们至今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们那时都还处在青春妙龄,虽然体内也有青春的骚动,也都渴望花前月下,但大家更加珍惜学习的时光。我们这些文革后的第一批研究生,如久旱的大地逢上甘露,我们终于可以正大光明地读书了。那时候,研究生阅览室坐无虚席。我们每天的课外时间都是在这儿渡过的。
在这个时期我也有新的困惑。我被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个问题是:什么是科学,怎样才能走上科学研究的路呢?人文科学不同于理科,人文科学更多地受到了文革的冲击。文革结束后的一个时期,文科中浮夸之风甚盛。
我在这个时期偏爱学习语言,因为我感到语言是实实在在的。我学习了梵文。梵文是一门比较难的语言,与拉丁文一样已不是流行语言。梵文词的变化很复杂,名词有单、双、复数,八格,动词的变化比孙悟空的变化还多。掌握一门语言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窍门儿,只能下功夫。利用清晨、傍晚背变格、变位表,平时多读梵文原著。我还学习了俄语,前后不到一年时间,我就通过了研究生俄语免修考试。有的同学劝我别学那么多语言,说语言只是工具,还是应该多读些理论书籍。说句实话.理论性书籍我也没有少读,凡是图书馆借得到的印度历史、文学方面的书籍,我都读过。但这些理论书籍并没有为我指出研究科学的道路。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有名师的指导。现在想来,研究生时期打下的两项基本功使我终身受益。一是自学的基本功。季羡林先生指导学生有一个原则,他认为学习如同学习游泳,办法是把学生推到池子里去,绝大多数学生过一个时期就学会了,学不会的是少数。季先生总是鼓励我自学,自己去找科学的途径。二是实事求是的治学基本功。季先生对学术上的浮夸之风深恶痛绝。记得我的硕士论文第一稿交到季先生手中后,他把我论文中一切与论述本身无关的词藻统统删去。他告诉我说写科学的论文不比写散文、小说,要实事求是,用最简洁的语言,排列你的论据,不要废话。还有,引文一定要注明出处,从他人借鉴的观点要注明,等等。这些都是人文科学的基本功。
 (段晴老师陪同季羡林先生访问德国,左一为段晴老师)
(段晴老师陪同季羡林先生访问德国,左一为段晴老师)
研究生一毕业,我就得到了当时西德诺曼基金会的资助,只身去德国留学了。我选中了汉堡大学,原因有二,一是我对古代语言有浓厚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学习过梵文,另外,我国新疆地区曾经通行过几种语言,比如于阗文、粟特文、吐火罗文等。至今还有文物出土,但国内能释读这些文字的人绝无仅有。我当时立志要攻下一门死掉的语言,掌握释读的技巧。汉堡大学的埃墨利克教授是研究于阗语的第一人,我就慕名去了汉堡大学。
我的导师埃墨利克教授是位非常严格的老师。他曾是澳大利亚的神童,十八岁时被送往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攻读博士学位。他用三年时间读完博士课程,并写出非常出色的博士论文,他的各门成绩都是一类(First class)。他的导师贝利先生是语言学界的大师,因学术研究成果卓著而被授予爵士称号。埃墨利克教授很骄傲,他看不起没有才华的学生。
在埃墨利克教授身旁读书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第一次和埃墨利克教授谈话,他问我:“你是准备读博士学位呢?还是要求一般的进修?”我根本不知道这学问的深浅,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读博士。”“那么好!”埃墨利克教授说,“于阗文属于伊朗语系。你既然要成为伊朗语言方面的博士,必须了解它的整个体系。你必须掌握至少一门伊朗古代语言,阿维斯塔文就是必修课。于阗语是一门中古伊朗语,除了这门语言外,你还必须掌握另外一门中古伊朗语,比如巴利维文,也是你的必修课,粟特文也应该了解一些。现代伊朗语也是你的必修课,你是伊朗语言博士,如果不学习波斯文,以后别人会笑你,除波斯文外,奥塞梯语也是你的专修课。以上是你的主科的必修课目。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你还必须修两门副科,你可以随便选。但从专业角度考虑,你应该选印度学和藏学。当然,如果你认为太吃力,可以选中文作副科,你是中国人,这样可能对你更容易些。”
不知深浅的我天生又喜欢迎接挑战,面对挑战我感到十分兴奋。我按照埃墨利克教授的要求选择了我的主科课程:①于阗文,②阿维斯塔文,③巴利维文,④现代波斯语,⑤奥塞梯语。我选择的副科是藏学和印度学。第一个学期是学习藏文,并且跟维茨勒教授读梵文古典诗“鸠摩罗出世”。
埃墨利克的教学方式和我在国内遇到的大相径庭。我的几门课都是埃墨利克教授亲自教的,如奥塞梯语。这是一门比较难学的现代语言,名词有九个格变化,以俄语字母做文字。第一堂课,埃墨利克教授不讲字母,不讲发音,不讲语法,上来就要求我翻译一篇奥塞梯语的短篇小说。我和一名德国姑娘一起上课,那姑娘被认为是尖子学生,是位多年不遇的天才学生。我只翻译出了第一句,剩下的全部文章都是那姑娘完成的。于阗语课的情况也是这样,德国姑娘独领风骚,她可以就一些释读方法和埃墨利克教授交换意见,而我只能坐在一旁听。那种滋味真不好受。埃墨利克教授偶尔看我两眼,那眼光似乎都是鄙视的。
我不服气。想想自己在大学时,在研究生时,成绩一向是好的,难道我这个中国高等学府的高材生,真的不如外国人吗?不服气也没有别的好办法,还得靠用功。我发誓要让外国教授也承认,我也是一名好学生。研究生时期培养出来的自学习惯这时有了用场。逐渐的,德国大学的教学方式反而非常对我的胃口。从前在国内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即什么是科学,怎样开始科学研究等等,很快就迎刃而解了。这是因为,在人文科学方面,西方学者经过上百年不间断的努力,已经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而这一体系本身就是推陈出新的。除了基础课以外,教授上课时就把本学科发展的最新动态,本学科要解决的问题带到了课堂上,使学生一开始就了解到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尽管埃墨利克教授十分严格,一丝不苟,但他给我的感觉他不是神,而是人,他不是权威。他批判自己的老师的错误,同时使我知道,名人也会出错。他启发我大胆地去解决问题,当我真的在他面前解决了一个他没有想到的问题时,他由衷地为我高兴,同时也使我懂得世上没有权威。
留学的第一个学期末,我已改变了课堂上由那个德国姑娘一言堂的局面。等到我以优秀的成绩通过了各门考试之后,真感到非常高兴。埃墨利克教授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之一,这已经是对我的最高评价了。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我的博士论文。我之所以自豪,并非是因为这篇论文是用德文撰写,在德国出版,而且以优秀的成绩通过考核,而是因为,它是我完成的一件老实的事情。它是实实在在的,仅有的两句废话也被埃墨利克教授毫不客气地删除了。我在博士论文中解决了于阗文中一些遗留的问题。这些问题剑桥大学的贝利教授曾试图解决,但他没有做到。我吸收了贝利教授的研究成果,埃墨利克教授的研究成果,以东方人的长处解决了他们难以解决的问题。更使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科学,怎样从事科学研究。我认为,博士学位的获得不是终点,而恰恰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它只能说明你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而科学之路漫漫。
除了读书以外.我还有许多爱好,喜欢游泳、跳舞、拉手风琴,也喜欢时装。我有一个家,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儿子。我比较喜欢挑战,教书时不喜欢教自己学过的东西。在当前的经济大潮面前,我虽没有完全去弄潮,但也偶尔试试身手。有了种种经验之后,有时朋友们相聚,说到世界上什么事情最有趣时,有人说是谈恋爱,有人说是赚钱,我认为都不是,这两件事不过是世上最容易的事,但最有趣的是从事科学研究,因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你功夫下了一,它对你的回报就是一,功夫不到,你就见不到成果,而且,科学永远不负忠实于它的人,因此,我爱科学。
 (第二排右一为段晴老师)
(第二排右一为段晴老师)
(选自魏国英主编《她们拥抱太阳:北大女学者的足迹》,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362—369页,向筱路录文)
- 0004
- 0006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