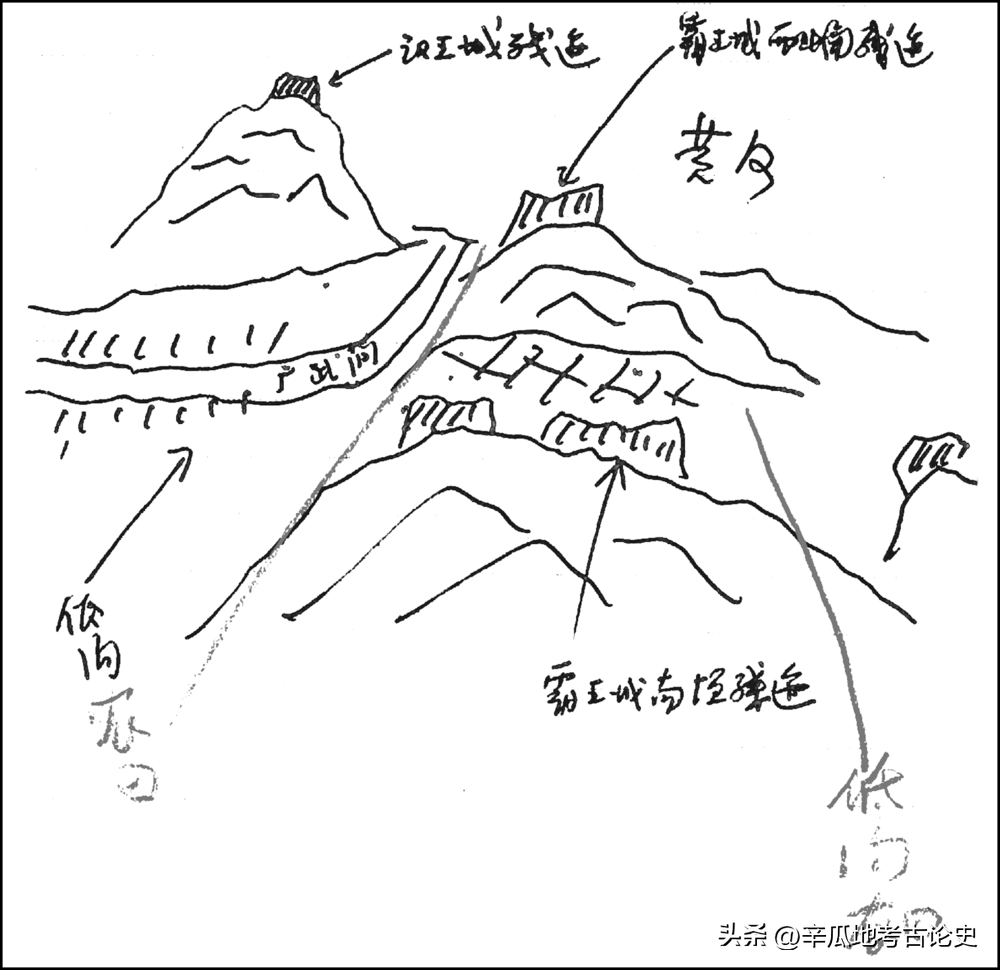“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梁思永
一、李济的预言
1927年1月,梁启超给正在哈佛大学学习考古学的儿子梁思永的信中说: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李济的期待和梁启超的嘱托最终均得以实现。1930年,梁思永回国后旋即投入到田野考古之中,北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之后的五年间,梁思永在考古领域完成了三项杰作:安阳后冈遗址发现了著名的“三叠层”堆积;山东城子崖遗址的发掘和整理,编写出版了考古报告《城子崖》;安阳西北冈超大规模发掘,发现了殷王陵。从后冈到城子崖再到西北冈,梁思永的考古之路见证了中国考古学起步阶段的探索与辉煌。在《后冈发掘小记》一文中,梁思永指出后冈遗址在中国史前史上具有“钥匙的”地位。尹达对此评论道:有了这把钥匙,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的关键问题。而对于大规模考古作业的西北冈殷王陵发掘,夏鼐赞叹说:规模宏大,工作精细,收获丰富,在国内是空前的。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奠基者和第一代掌门人的李济,称自己是半路出家而梁思永才是考古专门家,这番话不仅仅是一些谦虚和客套,更多的是在深谙世界考古学发展之趋势,并在亲身经历了田野考古经验之后的一种行家理想。因此,与其说李济格外看重梁思永,不如说是李济看清了中国考古学将来发展的方向和实现的途径。李济对梁思永的预言,实际上即是对中国考古学未来发展的规划。这一点应是不可忽略的李济对中国考古学的又一贡献。

二、后冈:考古地层学实践的经典
后冈遗址的重要发现是与城子崖遗址相辅相成的。1930年秋,城子崖发掘黑陶文化遗址。1931年春,梁思永主持了后冈遗址第一次 发掘,当年10月又奔赴山东主持了城子崖第二次发掘,11至12月再次返回后冈主持了后冈第二次发掘。一年之内相继发掘两处遗址 并两次发掘后冈,梁思永考古思索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这一历程中尽得彰显。后冈首次发掘发现了与城子崖大致相似的遗物,证明城子崖文化所及范围甚广,因此便有了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而城子崖的再次发掘,则又促使了后冈的第二次发掘。两年时间里城子崖与后冈两处遗址相继各发掘两次,互为因果与促进,相辅相成而相得益彰。梁思永奔走穿梭于两个遗址之间,最终促成了后冈三叠层的发现与辨识,凭着智慧与经验完成了他考古生涯的第一个杰作。后冈发掘发现并分辨出了小屯、龙山和仰韶三个时期文化层的清晰堆积,此即著名的三叠层堆积。梁思永在发掘小记中对文化层堆积有详细描述,其科学之操作技术于今不仅无过时而且犹不及。后冈的文化层既非只有三层,亦非是整合的序列,而是各层单一或其中的两层或多层互叠散布于四处。梁思永田野考古技术的重要意义,在于动态而全方位地观察整个冈地文化层(包括遗迹如白灰面)的纵横布局。地层归并后的三叠层,也不是1—2—3三层依次叠压,而是1—2、2—3的情形。梁氏不仅搞清楚了其全部顺序,更重要的是还搞清了每一层的平面分布范围以及厚度变化,由此建构了整个冈地文化层堆积的三维立体图形。然后再纳入每一层的出土遗物特征,又全方位了解遗物的分布情景。后冈遗址的发掘虽说是殷墟总体发掘中的一个环节,但却是以城子崖的发掘为契机的,正是后冈将仰韶、龙山和殷墟三者有机而有序地联系起来,梁思永据此写出了《小屯龙山与仰韶》等著名论文,由此成为解开中国史前文化之谜的钥匙。后冈考古的重要发现,得 益于主持者梁思永的慧眼与操作,特别是在发掘技术层面的进步,堪称是考古地层学实践的典范。对此陈星灿曾总结评论说:结束了 以往人为的水平层位的发掘,而开辟了以文化层为单位的发掘历史。
三、城子崖:考古遗物整理与报告编写体例的标准范式
毫无疑问,梁思永在后冈遗址的收获得益于城子崖考古的不少经验。梁思永在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时,进行了不少的考古操作改革,其中多涉及田野考古之细节,如:每坑作业工人降至最低限度以提高效率;以布袋代替麻纸包装,既可多次使用节约又不易损坏而紊乱;改善出土物标签的记录方式,详细标明出土地点等等。但梁思永在城子崖更重要的贡献是在出土物整理与报告编写方面,主要由他构建的整理方法及报告编写体例,开创了中国考古报告的先河,此与他早年曾整理研究过李济所发掘的西阴村资料有着很大的关系。1934年,中国第一部大型考古报告集《城子崖》出版。李济在序言中说,报告的体例大部分是梁思永创制出来的。这一体例的基本框架与精髓一直传承沿用至今,成为考古发掘报告编写的一个标准范式。《城子崖》的编写体例是建立在科学的田野发掘和资料整理基础之上的,不仅包括规范的考古基本概念和术语,更重要的是一套完整的文字和图片表述系统。如:分区域观察整个遗址的地层堆积,详细划分文化层的土质和土色;对出土陶器按照色、质、制、文、功 用及结构等进行了详细分类并统计,陶器功能分类计有:2门、9 式、35种,并结合出土地层,对器物年代作了推断,尤其还注意到了陶文,并与甲骨文金文作了比较;对石骨角蚌及金属器也作了相应的分类和统计,另对出土人骨及动物骨骸等也作了鉴定。在图版编排方面,遗址状态有实测总平面图和地层剖面图,器物反映包括线图和照片,其中陶器线图包括静物素描和侧视剖线图,另还有陶片纹饰拓片等。城子崖的资料整理及报告编写,与后冈三叠层发现为代表的田野考古操作技术一起,共同奠定了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第一层基础。
四、西北冈殷王陵:大规模考古发掘作业的典范1928年,“中研院史语所”成立并开始组织发掘殷墟,李济作为考古组的负责人同时又兼起殷墟发掘的重任。1930年夏,梁思永回国后即受聘于考古组。李济后来赞说:梁君是一位有田野工作训练的考古家,对考古组的组织上及方法上均有极重要的贡献。这一评价不仅是指后冈和城子崖的工作,更主要是指殷墟本身的考古,即西北冈殷王陵的大规模发掘。1934年—1935年,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三次发掘安阳侯家庄西北冈,领队为梁思永,李济、傅斯年等为视察人。西北冈发掘共计清理王陵级大墓10座、中小型墓1200余座,王陵大墓多建有四墓道,小型墓中许多为葬有殉人的祭祀坑。这一发现是自殷墟发掘以来的重大成果,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第一个顶峰,引起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北冈发掘是一项空前浩大的考古工程,不仅需要高超的考古理论与技术支撑,还需要复杂的人员组织与实施。梁思永完美地完成了这项工程,西北冈发掘因此也成为大规模田野考古的榜样。石璋如评论说,西北冈是殷墟考古中工程最大、收获最多的地带,在中国发掘史上占据首要地位。李济感叹说:梁思永是中国最杰出的考古学家,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五、中国考古学的先觉和先驱
梁思永以其杰出的考古成绩,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考古学的先觉与先驱。但这一历史进程的顺利完成,凝聚着许多学者的心血和智慧。这里必须提及的是傅斯年与李济,他们堪称是梁思永先觉之前的先知者,正是由他们主持组织的殷墟发掘才使得梁思永的考古才能有了用武之地。1926年,李济发掘西阴村遗址。1928年,傅斯年邀请李济担任考古组主任并主持殷墟发掘,另在谈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时发表了著名的理论:我们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我们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后,李济开始主持了殷墟最初几次的发掘,但最重要的是招揽和培植了一批考古学者,其首要即梁思永。在殷墟系列发掘的实际经验中(后冈与城子崖均是殷墟发掘的 延伸),不仅收获了中国考古学的首金,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中国考古学的两种主要研究方法:即地层学和器物形态学。因此,张光直曾说:殷墟发掘每进一步,便是中国田野考古经验每进一步。这种进步的推动者就是李济和他所组织的参加殷墟考古的学者们,其中当以梁思永为佼佼者。梁思永的杰出考古成果,不仅名副其实成为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更重要的是掌握了考古学这门学科本质的钥匙。这把钥匙的精髓所在就是坚实而高超的田野考古功力,这种功力不仅来自于西方考古学的系统训练,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浸润,更有梁思永本人热衷于亲吻土地般的田野考古操作激情,同时还凝聚着傅斯年、李济以及中国考古第一代同仁的经验和智慧,梁思永无疑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杰出代表。从后冈到城子崖再到侯家庄西北冈,这一系列考古经典作品,已经成为中国考古学初期发展的典范经验。在智慧发挥与经验积累基础上日渐成熟的中国田野考古学,开启并奠定了延续传承至今的中国考古学优秀传统。梁思永所掌握的钥匙已广泛掌握在今天的考古人手中,并不断更新而附加了新的内涵和功能。
- 0002
- 0000
- 0000
- 0000
- 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