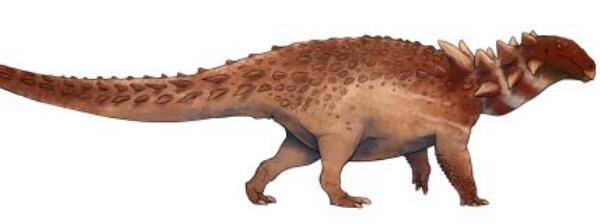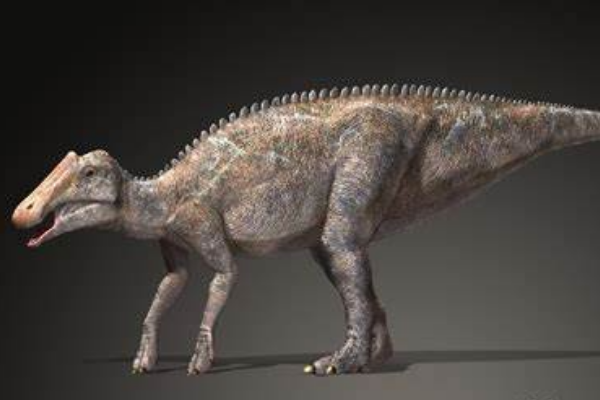茶托、发酵茶和汤剂——以考古发现切入中国早期茶史
宽泛的中国茶史研究包含了茶业经济史、茶业科技发展史和茶文化史三大领域。茶业经济史主要是涉及茶叶生产、茶叶贸易和茶叶消费等方面的讨论。茶业科技发展史主要联系于茶叶的化学、药学分析,茶树栽培与管理技术的发展。茶文化史则主要对茶具、茶艺、饮茶习俗及茶与文学、美学、宗教、哲学等展开探究,对中外茶文献加以辑佚、校注、汇编。本篇文稿,笔者以考古出土的南朝洪州窑茶托为切入点,先揭示公元5至8世纪这类瓷质茶具的稳定形态结构,然后由器形推及器用,试从其仪式功能联系到曾盛行一时、但详情已不甚清楚的中古制茶工艺,并通过复原中古发酵茶制作工艺,使人豁然会悟:源远流长的中国人对茶的利用、加工和饮法,一直是受到中药方剂,尤其汤剂制作实践与理论的推动,才依时代先后,表现为从食用、药饮到保健养生的有序嬗变。
一、斜收腹(碗)盏和托,相扣成套可称为“茶托”
2002年5月,南昌县小蓝乡县烟草公司宿舍工地出土一套南朝洪州窑青釉碗托与碗(图一、二),2004年4月,南昌县富山乡柏林工地又出土一套南朝洪州窑青釉碗托与碗(图三、四),这两套青瓷器具的发现,使得以往的类似发现,被贯穿起了一组饶有意味的链接。
 图一: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一: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二: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二:江西南昌县小蓝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三:江西南昌县富山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三:江西南昌县富山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四:江西南昌县富山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图四:江西南昌县富山乡出土洪州窑茶托
如1957年在陕西西安市曾出土七枚刻铭自称为“浑金涂茶拓子”银胎鎏金茶托子,其标记铸造时间是唐大中十四年(860年)。1987年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唐僖宗(874—889年在位)所施一组茶具里,亦有一副“瑠璃茶椀柘子”。(图五、六)。若再将同时期(820—900年)唐长沙窑产的带自名的“荼埦”(图七),以及浙江临安市吴越国康陵出土的五代(约939年左右)“越窑青釉盏托、侈口碗”(图八),都用来跟“洪州窑青釉碗托、碗”,进行早晚排比,便几乎肯定——尽管由不同的材质制作,尽管有略微不同的地域形制风格差别,但整体上看,承盘内底附着一周凸棱的托以及底足与那周凸棱正可扣合的斜收腹的碗、或盏,在南朝的宋齐年间(待后笔者有详论),已成为一套造型特征十分显著的组合器物。
 图五: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五: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图六: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琉璃茶托
图六: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琉璃茶托
 图七:湖南长沙市长沙窑之茶碗
图七:湖南长沙市长沙窑之茶碗
 图八:浙江临安市吴越国康陵之越窑茶托
图八:浙江临安市吴越国康陵之越窑茶托
冯先铭、孙机早指出这种器物组合,即古代文献中屡屡提到的饮茶器具“茶托子”,它们首见唐李匡文的《资暇集》:
始建中,蜀相崔宁之女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倾,乃以蜡环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环代蜡。进于蜀相,蜀相奇之,为制名而话于宾亲。人人称便,用于代。是后传者更环其底,愈新其制,以至百状焉。
后来它们在北宋高承的《事物纪原》里,又被称作“托子”,在南宋程大昌的《演繁露》里,或曰“盏托”。由于确凿的考古发现已把这套器物的确立时间往前推了二、三百年,进而也就否定了崔宁之女的发明专利。可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仍不妨给予这套年代跨度七、八百年(东晋晚至元代初),其间虽有型式细节变化,但整体形制基本维持稳定的器物,以一个简㨗和新的科学概括,即命名为“茶托”(含托与碗或盏)。在本文排出的南朝至五代的茶托演变略图里(图一到图八),可发现碗或盏的形制,总在强调腹部的斜收。这或许与饮茶时,方便茶末和配料的顺利倾倒有内在的关联,并很契合陆羽所说过的瓷质茶碗“口唇不卷,底卷而浅”的特征。器形和器用的关系,可谓一目了然。此外,承盘内底附着的凸棱随时间的推移逐渐地增高,以至到晚唐,呈现为明显的托圈。这固然出于隔热防烫的需要,但何尝又不是反映了当时饮茶活动的仪式要求和审美要求呢?《茶经》的《四之器》篇中,有两段紧要的文字经常被后人引用。
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
陆羽应该在比较了盛于不同窑口出产的茶碗里“沫饽”(汤花)与茶汤,跟各种瓷釉相映衬出的不同色泽和色调后,才评鉴出“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如此的唐代六大名窑的座次。因而,追究那时的饮茶为什么会汤花堆白和茶汤泛红,便成为我们下面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跟诸釉色茶托相辉映,引人注目的是发酵茶的汤花和茶汤
洪州窑创烧于东汉时期,主要分布于今江西丰城市境内赣江或与赣江相衔的药湖南岸的山坡、丘陵冈埠以及清丰山溪河的河东岸畔丘陵地带。然其在陆羽时代已由盛而衰、颓势尽显了。《茶经》云:“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可如果往前推早到隋代和南朝,情形还是很不一样的。南北朝时,虽然北方战乱频仍、政治动荡,但南方地区人口增加、经济繁荣。这时的洪州窑窑场由于使用东晋晚期发明的匣钵装烧工艺,使坯件避免了明火接触和窑顶落渣对釉面的污染,进而器皿受热均匀、釉面光润,瓷器的质量大为提升。那些的青釉瓷产品,胎质细腻、质地坚密,纹样别致。尤其是釉色青里泛黄,色调与光泽犹如早春植物的萌芽,招人喜爱。加上器物的类型丰富,造型规整,精美絶伦。此阶段洪州窑生产的瓷器,较同时的越窑有过之而无不及,亦胜于同期诸名窑出品。隋代洪州窑瓷器,从胎料淘洗,到规模使用单体戳印技法以及有效地控制高温焙烧,制作工艺又有较大改进,其流布范围不仅覆盖今江西地区,还流向今湖北、安徽、江苏、浙江、广东、广西和陕西的一些地方。虽说釉色逐渐偏向了不讨人欢迎的酱褐色,但挟持着东晋以来的影响力,直至唐天宝二年(743年),洪州窑瓷器仍被当做珍贵的地方特产送至长安给君王唐玄宗展示。由上可得知,南朝洪州窑茶托的横空出世,正值洪州窑烧造工艺的巅峰时期,当时洪州窑特有的青中闪黄的釉色与“白红之色”的茶水,交互辉映、一定是分外的好看。
根据现代科学对茶叶所做的物理、化学分析能知道:在茶树鲜叶中,水分约占75﹪,干物质为25﹪。茶叶的干物质组成非常复杂,它们由3.5﹪~7﹪的无机物和93﹪~96.5﹪的有机物组成,可正是这些有机化合物,构成了茶叶色香味品质特征与药用疗效的物质基础。有唐一代的文化精英们,对茶的汤花之美的惊艳,好像远超过对于茶汤之甘滑的兴致。因而,在制茶、碾茶、筛茶、煎茶、盛茶、品茶,乃至于饮茶的每个环节,让茶汤泡沫如何获得一个合适的量,成为彼时茶师苦心孤诣的首件要务。已有的实验研究证明,茶叶的有机化合物中所含的“茶皂素”,是茶汤泡沫生成,或有利于泡沫持久的决定性物质。由于溶液中皂素类浓度仅只要0.005﹪左右,即能形成稳定性的泡沫,所以,无论哪一类茶的茶皂素含量,实际上皆是足以起泡的,但想使泡沫(汤花)量多,而且又洁白、持久,那制茶工艺里的“发酵”环节就至关重要了。 笔者曾细读《茶经》的《三之造》篇,得知唐朝时饼茶的制作包括:“采之、蒸之、捣之、拍之、焙之、穿之、封之,茶之干矣。”这段简短扼要的文字,经过今天学者研读,或可以这样解释:茶叶采来后,先放在甑、釜中蒸一下,然后将蒸软的茶叶用杵臼捣烂。再把捣烂的茶叶透凉了弄成末,放它们在铁制规承(亦即模)中拍压成团饼。最后,将茶饼穿起来烘焙,封存藏养至干。倘若,再去检阅《茶经》的《二之具》篇,则又提到一件耐人寻味的制茶器具——“育。”
育,以木制之,以竹编之,以纸糊之。中有隔,上有覆,下有床,傍有门,掩一扇。中置一器,贮煻煨火,令煴煴然。江南梅雨时,焚之以火。育者,以其藏养名。
作为收藏、保养茶的“育”,大概是这么一个物件:先是用木制成框架,再编织上了竹篾,后又将纸糊好。中间是隔开的,上面有盖,下面有托架,旁边还有门,并且关上一扇。在“育”中放置了一个容器,里面贮盛带火的热灰,让火势保持微弱。由于江南梅雨季节,气候潮湿,便要生起明火。换言之,那已经拍好、焙好、穿好的“茶饼”,最后得要封藏在“育”中,保温养干。如果将上述细节都联系起来,其实并不难意识到:陆羽所记载的大部分唐代饼茶,它们实际该算作微发酵或半发酵茶。因为制茶过程中存在了发酵工艺的运用。比如蒸之后的“捣”、“拍”,茶体都仍然和水、空气保持有接触。而饼茶最后的封藏养干又是在持续的保温中进行的。所以,因存在水份和温度的条件导致发酵,使多酚类物质氧化,形成大量网状结构物质,这些便奠定了能产生耐久泡沫的物质条件。于是,沸腾的茶汤出现“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的奇观。并且也只有当饼茶中的有机化合物茶多酚,由于发酵又氧化,形成了高聚合的茶黄素、茶红素、茶褐素时,茶汤才可能在瓷釉的映衬下,呈现出“茶色红”、“茶色丹”、“茶色紫”,亦即黄红色;或呈色为“茶色绿”,亦即黄绿色的样子。《茶经》中专门提到“茶作白红之色”,亦即指汤花之白与茶汤之红的混合。当然,实际情况也许要复杂得多,因为在唐代文人笔下,令他们赏心悦目的汤花(“沫饽”)和茶汤的混合状态,既可能来自于发酵茶,也可能来自于非发酵茶。前者像:“碧沉霞脚碎,香泛乳花轻。”(曹邺:《故人寄茶》)。——碧褐的茶末,在红色的茶汤中翻滚浮沉,乳白香溢的汤花轻轻堆起。“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清言。”(颜真卿等:《五言月夜啜茶联句》)。——以茶代酒,邀请来尊贵的客人,面对着汤花泛起,大家言辞清新、兴逸遄飞。“育花浮晚菊,沸沫响秋蝉。”(张又新:《谢庐山僧寄谷帘水》)。“薤叶照人呈夏簟,松花满碗试新茶。”(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铫煎黄蕊色,碗转曲尘花。”(元稹:《茶一字至七字诗》)。这些犹如晚菊、松花、曲尘花的黄白相间的茶水,在今天的我们看来,不正是发酵茶才能产生的美丽的现象? 后者如:“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炒青而制成的茶叶已经满室生香,再配以名贵的金沙泉水。山间松涛汇入了火炉上沸腾如雨啸的茶水之鸣,进而白云似的汤花涌起,缓缓漫布到碗盏边沿。“朱唇啜破绿云时,咽入香喉爽红玉。”(崔珏:《美人尝茶行》)。“惟忧碧粉散,常见绿花生。”(郑愚:《茶诗》)。细究起来,原来非发酵茶也是可以发出白洁的泡沫,但茶汤却呈现为翠绿之色。至此,笔者终于弄明白:陆羽生动描绘了各种的发酵茶和非发酵茶的茶汤之艳。
如枣花漂漂然于环池之上,又如回潭曲渚青萍之始生,又如晴天爽朗有浮云鳞然。其沫者,若绿钱浮于水渭,又如菊英堕于鐏俎之中。饽者,以滓煮之,及沸,则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
总之,茶圣提及的唐代四大成品茶——粗茶、散茶、末茶和饼茶,除了连同嫩茎一起采摘并加工成的粗茶,一部分蒸、或炒后直接烘干的散茶,它们当属于非发酵茶的范畴。而那些经过了蒸、捣、焙、封的复杂程序制成的大部分饼茶以及蒸、捣后干燥而成的末茶,却大约属发酵茶的一类了。故笔者有充足理由认为,中唐以后,皇室、贵族、文化精英们主要饮用的乃是以饼茶为核心的发酵茶,当他们在各种充满仪式意味的场合,手把茶托激动抒发起“楼中饮兴因明月,江上诗情为晚霞”(刘禹锡:《送蕲州李郎中赴任》)的情怀时刻……中国茶文化的艺术品饮形式,已然十分成熟。这种情况还可能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三、饮茶方式变迁,其实受制于中药汤剂制作的演变
1.“荼”、“茶”之惑那便让我们凭借以上讨论的有关唐代发酵茶的知识背景,辅以相关较早的文献佐证,再来审视一组考古出土的、并是年代清楚、完整成套的“南朝洪州窑茶托”。1975年7月,考古人员在江西吉安县长圹公社屋场大队(即今凤凰镇屋场村),发掘了一座南朝齐永明十一年(493年)墓。墓中出土的一组“青瓷莲瓣纹托盘”、“青瓷莲瓣纹碗”,它们正好又构成一套有明确纪年的“南朝洪州窑茶托”。令人击节欣喜的是这套茶托与南昌县小蓝乡县烟草公司宿舍工地、富山乡柏林工地发现的茶托非常相似。笔者即而推定:最迟在420—557年的南朝宋、齐、梁年间甚或更早,长江中下游地区的饮茶,仪式环节已然郑重其事。很可能仪式的物质载体就是如洪州窑茶托这样的物件。成书于南朝宋,由刘敬叔撰写的《异苑》云:“剡县陈务妻,少与二子寡居,好饮茶茗。以宅中有古冢,每饮辄先祀之。”南朝齐武帝萧颐在《遗诏》中特意强调:“我灵座上慎勿以牲为祭,但设饼果、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因而,西晋杜育《荈赋》曰:“器择陶简,出自东隅”,其意实即“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亦等于是谓:六朝时代的越州等地早就在生产特别的茶具,用于程式化、仪式化的饮茶活动之中。再有,陆羽曾直指《荈赋》“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如春敷”该段文字它们的内涵等同“重华累沫,皤皤然若积雪耳”。这也意味着早在晋代,包含发酵环节的饼茶制作工艺已经出现。笔者认为:唐人将茶饼,炙、碾、罗之后,变成细细的茶末,投到水中煎煮的作法,可能就是模仿秦汉以来,把中药材粉碎成粗颗粒或粗末后进行煎煮,滤取药液或连同药渣服用的“煮散”剂型。而这种“煮散累沬”的饮茶方式,由前述已知,在六朝时即亦存在。倘若进一步地追问:“煮散累沫”的饮茶方式的前世,更早的茶文化确立期的茶文化传播方式是什么样的状态呢?学界多倾向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正式颁示天下的《开元文字音义》,要比陆羽初完成《茶经》时(760年左右),早了二十多年已隶定了“茶”字。无独有偶,清初音韵学家顾炎武亦推测,在南朝之梁代,“茶”字已读今音。
荼,宅加切,古音塗。按,荼荈之荼与荼苦之荼,本是一字。古时未分麻韵,荼荈字亦只读为徒。汉魏以下乃音宅加切,……梁以下始有今音,又妄减一画为茶字。
如再往上追溯,在文献里不光是提到了茶,并且最早明确谈及茶事的,大概非西汉晚期王褒的《僮约》莫属,其中蜀地“烹荼尽具”、“武都买荼”故事,使得“荼”即是“茶”,差不多成为了不易之论。 但在周代结集的《诗经》之《邶·谷风》、《大雅·绵》、《豳·七月》;《郑·出其东门》、《豳·鸱鸮》;《大雅·桑柔》、《周颂·良耜》中,虽屡屡出现“茶”的前身——“荼”字,可都和山茶科的“茶”,不能直接划等号。自西汉毛亨、南宋朱熹以来,《诗经》里的“荼”,一直被密切关注,然经过现代植物学和中医药学的重新检验,才弄清了它们大体包括:①可食用蔬菜中之一种或数种,属菊科植物(如《谷风》:“谁谓荼苦,其甘如荠”)。②摇曳生姿的禾本科芦苇属植物(如《出其东门》:“出其闉闍,有女如荼”)。③为野草或杂草(如《良耜》:“其镈斯赵,以薅荼蓼”)。公元前11—前6世纪的《诗经》时代,华夏雅言系统所云的“苦荼”,实际是指菊科苣荬菜属的一种或数种植物。其既可当蔬菜供人食用,还可因为具备苦寒性味而制成汤液供人药用。故而,它们另外被叫做“苦菜”。问世于500年(南齐永泰二年),也即中药本草经典《本草经集注》中,陶弘景为后世留存了《名医别录》和《神农本草经》之一些珍贵的文字,里面就有提到四种苦菜。
①《名医》曰:一名游冬。生益州山陵道旁,凌冬不死,三月三日采,阴干。②析蓂子:味辛,微湿。主明目,目痛泪出,除痹,补五脏,益精光。久服,轻身,不老。一名蔑析,一名大蕺,一名马辛。生川泽及道旁。③败酱:味苦平,主暴热火创,赤气,疥搔,疸痔,马鞍热气。一名鹿肠。生川谷。④苦菜。味苦,寒。主五藏邪气,厌谷,胃痹。久服,安心益气,聪察少卧,轻身、耐老。一名荼草,一名选,生川谷。
按照南朝晚期颜之推《颜氏家训》的说法:(游冬)“叶似苦苣而细,断之有白汁,花黄似菊。”很明显,“游冬”和《诗经》里的“荼”,即菊科苣荬菜属是一类的,而那接近十字花科荠属的“析蓂子”和“败酱”,它们在外观上也跟游冬较相像。只有第④种亦即“苦菜”,因它的功效为“安心益气,聪察少卧”,且两晋之交的郭璞(276—324年)曾注:“树小如栀子,冬生叶,可煮作羹,今呼早采者为荼,晚取者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菜。”这使只要略具生活常识的人都能联想到:此“苦菜”,应为今天我们饮用的山茶科的茶叶了。根据“药食同源”的基本原理,鉴于《本草经集注》所记四种苦菜,皆是生长在川谷环境,又都具有味苦、性寒的中药共性,因而笔者以为:中国茶文化的发生与传播,是以山茶科的茶之药用功能,从食用的菜蔬类及苦菜类里得到辨认和区分为条件的。由于山茶科的茶树并不适应北方偏低的气温,故茶文化的发生与传播就先启程在了中原地区的外围。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中歌唱的“荼”,多和菊科植物有关,可和山茶科植物无涉的原因。不过,既也作为苦菜,那么华夏雅言系统对于“苦荼”的发音,便成为了我们破解“荼”、“茶”之惑的钥匙。将目前所知道中古以前或已流行的“茶”之别称,比如:“荼”、“槚”、“葭萌”、“蔎”、“荈”、“茗”等聚拢来考察,笔者发现(1)它们都是“茶”字确定前的一组假借字;(2)它们也是一组形声兼会意字,从声符(含构造)出发,可找到与其所谐字的意义关联。像“茗”和“荈”,当假借来对早采、晚摘两种不同形态茶叶的指称。“蔎”,借来对飘逸茶香加以描述。“槚”,大概是借来指示茶的木本状态。西汉人扬雄、晋人郭璞等,慧眼识金指明了“槚”、“蔎”、“荈”字的先秦音和巴蜀方言密切相关,说明对茶的认识和利用,的确先发生于巴蜀地区,时间当早到商周之时。而相对要晚些时候的西汉司马相如、东晋常璩所说的“荈诧”、“葭萌”,亦即“荈”、“槚”的相似、或相同表达罢了。但三国时陆玑特别强调了“蜀人作荼、吴人作茗。”或许这个“茗”字是源自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对茶的特定称呼。只要去浏览一下《茶经》的《六之饮》、《七之事》篇,陆羽搜罗的六朝文献凡有提到“茗”,一般多涉及长江中下游地区。
《神异记》:“餘姚人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至瀑布山。……《续搜神记》:“晋武帝世,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广陵耆老传》:“晋元帝时有老姥,每旦独提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竞买。……鲍昭妹令晖著《香茗赋》。
笔者推测,在巴蜀地区的人们知道辨认茶、利用茶之后,茶文化的主流沿着茶的植物分布空间,顺长江而传播到长江中下游及邻近区域。有一条较早的材料前推到齐景公(公元前547—前490年在位)为晏婴提供的膳食中,含了道“茗菜。”这或提示我们,早在东周时期,对“茗”的加工、并煮饮的生活方式已由长江之南,北传至强大的齐国。特别引起我们关心的是:“槚”跟“荼”、“葭萌”之“葭”、“苦”,在上古音里同属于鱼部,并且“槚”、“葭”是见母双声;“槚”、“苦”亦是见溪旁纽;虽然“苦”、“荼”为溪定邻纽,但“苦”发舌根音、“荼”发舌音,两者的区分不算明显。亦即“槚”、“葭(萌)”、“荼”与“苦”,在西周时已发音相近。所以笔者大胆推定:茶文化传入中原的时间虽然至少晚于西周,但是至东周时,巴蜀和中原地区都流行用雅言“苦荼”、“苦菜”来对茶的令人“少睡”、“悦志”功能予以说明了,而长江中下游的人们则另外使用着“苦茗”一词。这里用华夏雅言的发音对山茶科的茶之性味苦、寒的强调,既是汉语逐渐稳定的明显表征,更是茶的饮用方式根本上受到了中医药实践与理论、尤其汤剂制作技术制约的结果。2.从“煮羹配伍”到“煮散累沫”,再至“炮制冲点”和“揉捻冲泡”有学者猜测,陆羽主要利用唐初虞世南、欧阳询等人编著的《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等类书,方汇集到这么多的茶史材料。然而,笔者反倒是相信,陆羽当阅读过大量已经亡佚的各类写本文献,分类摘录了其中与茶相涉的资料,除了在《七之事》篇,还在《一之源》、《六之饮》、《八之出》等篇里加以援引。它们和类书所抄的文字,部分是有共同源头的,另也有部分来自于其他的出处。因此,笔者自始至终尊重《茶经》所录的史料,以它们为讨论的支点,进而建立本文的诸多论证。有两段西晋时的文字,正好反映了巴蜀和长江中下游两个地区,不同的茶艺特征或茶文化不同的主要传播方式。
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橘木兰出高山。(孙楚:《出歌》)。水则㞴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惟兹初成,沫沈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杜育:《荈赋》)。
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将“桂”、“茱萸”和“荈詫”排在了一起,而保留在宋初所编《太平御览》卷八六七引三国魏人张揖《广雅》曰:“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如若再联系唐代樊绰《蛮书》“物产”中有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但“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煎之”。我们即可明白,陆羽很不以为然的“用葱、姜、枣、橘皮、茱萸、薄荷之等,煮之百沸,或扬令滑,或煮去沫”的饮茶习俗,应当起源于巴蜀先民从食用的菜蔬及苦菜中认识了茶的苦寒药性及“主五藏邪气,厌谷,胃痹”功效后]有意地与偏性温的葱、姜、桂等配伍,煮为羹汤药用,以达到消食健脾、胃,提神益气及针对西南地区的瘴气而驱寒、解毒的效果。如此“煮羹配伍”的饮茶方式,即是伴随着茶文化药用功能确立过程,所形成的第一种比较流行的茶文化传播方式。笔者以为“煮羹配伍”的饮茶方式,其滥觞于巴蜀文明期,也即相当商周之时。那时的巴蜀人,借来了“槚”、“蔎”等字,并用地方方言表音,称谓山茶科的茶。秦汉以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新兴起了一种所谓“煮散累沫”的饮茶(茗)方式。前引过的《广雅》佚文提到:“荆巴间采叶作饼,……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说明早在三国之际,长江中游的荆州已经采造出茶饼。随后,又有传晋时丹阳郡之弘君举所撰《食檄》云:“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这分明描绘了发酵茶才会产生的“焕如积雪,晔如春敷”的汤花。南朝宋元嘉到齐天监近百年的时间(424—519年),这种被尊贵的刘宋皇族刘子尚、刘子鸾叹为“甘露”的“茶茗”;被南梁刘孝绰夸如琼玉之粲的“茗”,其实就是高僧释法瑶、昙济,借以款待吴兴郡赫赫“沈氏”望族中沈演之等名流贵人的饼“茶”。
新安王子鸾、豫章王子尚,诣昙济道人于八公山。道人设茶茗,子尚味之曰:“此甘露也,何言茶茗?”羞非纯束,野麏裛似雪之驴;鲊异陶瓶,河鲤操如琼之粲。茗同食粲,酢颜望楫。宋释法瑶,姓杨氏,河东人。元嘉中过江,遇沈台真,请真君武康小山寺。年垂悬车,饭所饮茶。
若是再多了解一点南朝的历史,就知道活跃于今浙江德清县的沈氏家族,在能征善战的武夫沈田子、沈林子、沈演之、沈庆之之后,涌现的反是沈约、沈浚这样的文豪才子。似理解了这边是刘宋皇室末日的暴戾恣睢,那厢却是王子们在八公山品茗悟佛的反差人生。我们猜测,沈约的好友刘绘之子刘孝绰,这位《昭明文选》的最主要编纂者,回首六朝的关键时期也即——齐、梁朝,应该明察到了中国文化正朝文人自觉建立规范、法度,突显抒情、传神的特质,追求意象遥深、幽微婉约之美而转折的大势所趋。这刘孝绰喜爱不已的或盛于越窑、或洪州窑茶托里“煮散累沫”的茶茗,亦就是大趋势过程里,长江中下游人们对“煮羹配伍”饮茶方式的一种改造,并慢慢地成为唐代饮茶主要的形式。“茶”字的发音和书写,已然稳定成型。南朝时期,应是中国茶文化符号正式设立和稳定为日用生活方式的时期。再后来才轮次上演茶在宋、元、明、清几个朝代,被“炮制冲点”和“揉捻冲泡”饮用的图景。汤剂,古称“汤液”,亦俗称“汤药”。是中药饮片加水煎煮,去渣取汁的液体剂型。由于它溶剂廉价、制备方法简单易行,通过煎煮,可以充分发挥方药的各种成分,人体吸收快、奏效迅速,故而成为中药里应用最早和最广泛的方剂剂型。西晋皇甫谧《针炙甲乙经》自序载:“伊尹以亚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书·艺文志》的“方技略”已记录了“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前面笔者考证过,在公元前16—前9世纪的商周时期,巴蜀人已能从食用的菜蔬及苦菜中分辨出茶,并与葱、姜、桂等配伍煮羹而药饮。这明显是借鉴了中医药实践里汤剂之常见的“煮剂”制法。煮剂特点为煎煮时间较长,药物形态相对较大。大约在公元3—5世纪,可能因大量生产茶和远程运输的缘故,还因魏晋名士服散的影响,长江中下游人开始将茶制成如“丸剂”一样的饼茶。“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再捣碾为粉末煮(浇)散而饮用,以达到“轻身、耐老”的功效。若按中药学的概括:丸剂,系指中药材细粉或药材提取物加适宜的黏合剂及其它辅料制成的球形或类球形剂型的统称。对照相传是出于《广雅》的文字,可说基本合榫。由于中药服用主要通过肠胃道给药,所以,无论是固体的散剂(由一种或多种药材混合制成的粉末状制剂),或丸剂,皆仍然在服用环节上,与汤剂发生较多的交集,即所谓的“煮散”。煮散,乃药材颗粒与水共煮而制成的液体药剂。其特点是煎煮时间相对较短,药物形态相对较小,它发生的时间八成在秦汉时。东汉张仲景《伤寒论》的经方中,虽无“煮散”二字,但以煮散之实应用的方剂并不乏其例。而据孙思邈的《急备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大致到唐代前期,煮散的使用已相当广泛。煮散,当为继汤剂之煮剂之后的第二种制法,它直接导致了“煮散累沫”饮茶(茗)方式的形成。在本文第三部分还谈到了唐代饼茶制作中存在着发酵工艺的有意识运用。但公元3世纪饼茶起源之时,发酵工艺肯定是偶然被发现的,它之所以会被反复使用以及后来宋元人更多凭借中药炮制技术加工茶饼,跟中古以降的人们越来越追求饮茶的仪式美感与享受口感的“香甘重滑”,是有极大关系的。从公元10世纪五代开始,饼茶制作的繁琐、复杂,比唐代远胜之。由南宋赵汝砺的《北苑别录》可知:采摘来的茶叶,要经过严格的选择,选过之后,要加以洗涤,然后才蒸,蒸过后,榨去尽茶叶中所含的水分及茶汁(即膏)。蒸过的茶叶叫做“茶黄”,将之取出先用水淋几次,然后入小榨,把水挤压干净,再入大榨,用力榨去茶汁(即膏)。在入大榨之前,把茶用细布或绸布包住,用竹篾捆好,然后才榨。榨一次后,取出来揉匀,再捆好入榨,这一次叫翻榨。这种人力操作的茶榨,竟要昼夜不停,以至于“彻晓奋击”。如再継续观察后面的“研”、“造”、“过黄”等工序,会发现五代和宋、元的加工饼茶的作法,应明明模仿了中药制作中的“炮制技术”,尤其所谓的“水火共制法”。炮制,系加工处理中药的技术和方法。古代又称为炮炙、修事和修治等。公元5世纪南朝刘宋雷敩撰写的《雷公炮炙论》便是第一部中药炮制的专著。而水火共制法,指将药物通过水、火共同加热,以改变药物性质与形态的方法,主要包括了蒸、煮、熬、潦(即挤擦)等四种。宋徽宗赵佶的《大观茶论》恰巧赞叹了:“夫茶以味为上,甘香重滑,为味之全,惟北苑、壑源之品兼之。”福建建安县北苑贡茶,炮制技艺源远流长、传承有绪,其实现目标即通过蒸、潦(即榨)等炮制技术改变茶的性味,使茶由原来的味苦性寒,变得味甘性温且健脾、养胃。不仅中药炮制技术深深影响了五代以后饼茶的制作,另外,对汤剂之饮剂制法的效仿,也是引致“煮散累沫”饮茗之后,“炮制冲点”茶文化传播方式产生的关键。饮剂,即以沸水浸泡药物后再服用的方剂剂型。它因可以灵活掌控药物的服用剂量和时间,故自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首载“饮剂”后,其作为汤剂中特殊的一种制法,亦常施用于一些不宜久煎久煮的药物。将灵活的饮剂制法移植于茶事活动之中,方使得一手执壶,一手执筅——注沸水和旋转打击茶盏中的茶汤,这样高度技巧性的两相配合成为可能,以创造出“斗茶”(亦即“分茶”)艺术的最佳效果。只是从公元12世纪的南宋便初现端倪:采造极繁复、成本高昂的饼茶,以及“炮制冲点”方式发展到极致而催生的奇幻的“茶百戏”、“水丹青”,终究离茶文化形而上的最高要求“茶性俭”渐行渐远。当叶状散茶登上了茶饮茶艺的历史舞台,并受到饮剂制法制约,新的一种——可称之为“揉捻冲泡”饮茶方式就逐渐成形了。这种饮茶方式在元、明时代的确立,亦意味着中国茶文化功能由药饮转变为了保健养生,这是茶文化继由食用转变为药饮之后,又一次极其重要的转折。笔者拟另撰文加以探讨。 上古至中古中国人烹饪与制剂的关键因素,其实在于“水”和“火”。或许日复一日的平淡生活却让老百姓于水、火相济之间,发现了中国的茶道。若纵览中国早期茶史,那在诗词歌赋被中反复吟诵的煎茶、分茶、团茶、斗茶、谷雨茶……,都不过是历代各色文化精英、皇家贵胄在中医药日用实践与理论的静水深流之上,扑腾起的一朵又一朵美丽浪花。说中国茶文化是发端于民众的日常实践,却确立于社会精英所操弄仪式的文化传播运动并不为谬。只是要了解和认识这样具有多层面貌的复杂文化运动,我们不仅得去搜寻新材料,更需要改变以往狭隘的学术视野与趣味。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