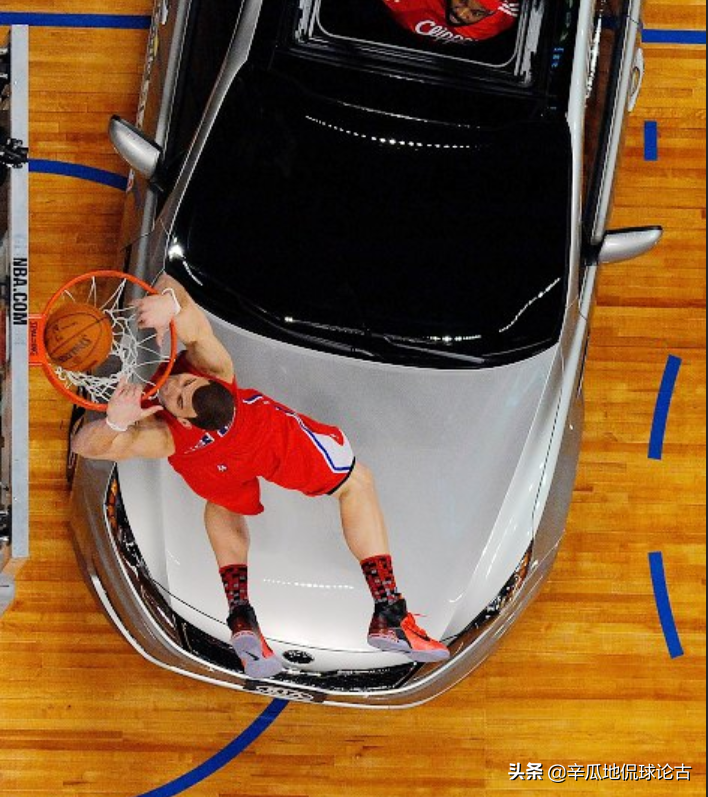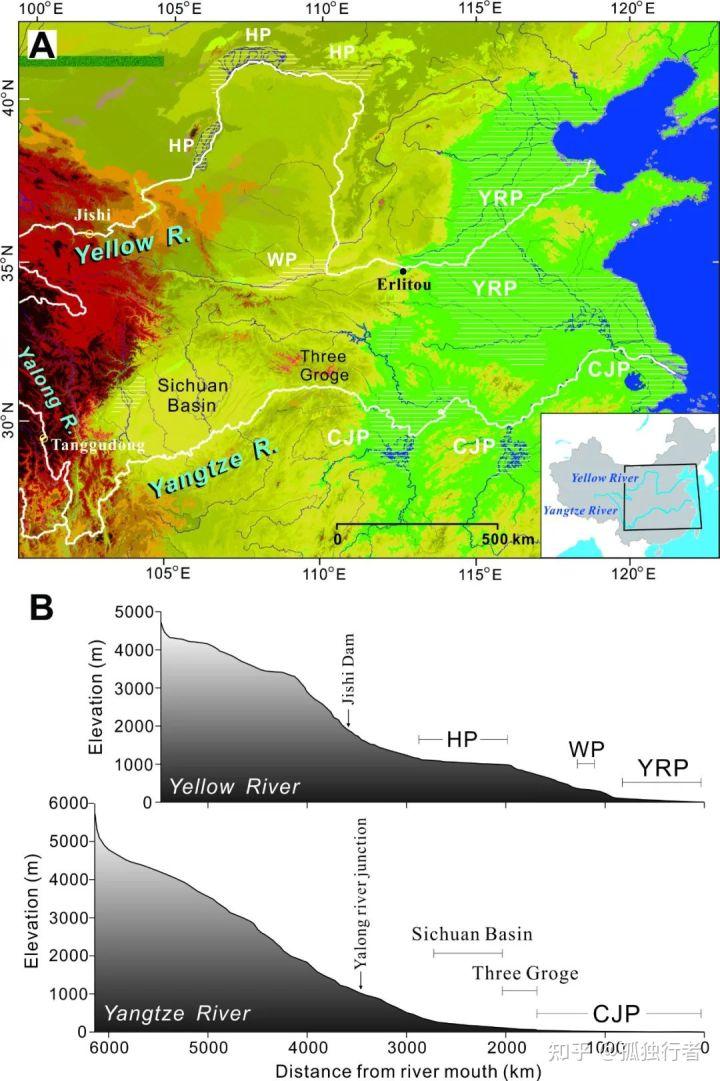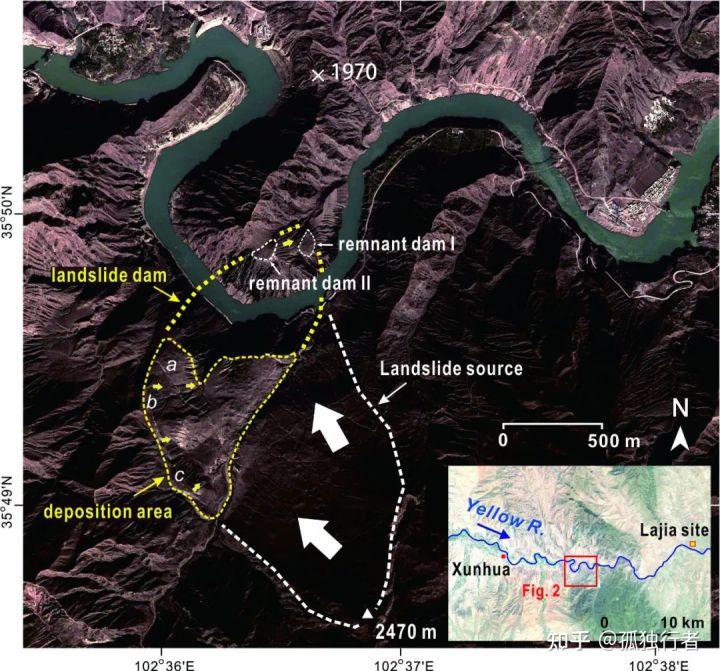作为女权主义者如何从事考古学研究
#翻阅2021#小编按:论文作者Alison Wylie是加拿大考古哲学家与女性主义科学哲学家,目前执教于英属哥伦毕业大学哲学系,她在女性主义科学哲学、考古学的学术史与考古哲学、研究伦理和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都著作颇丰。她是美国考古学会(SAA)考古学伦理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在2008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女权主义哲学杂志Hypatia的资深编辑,并在2013年被哲学界妇女协会评为年度杰出女哲学家,是科学哲学协会的现任主席(2019—2020)。
这篇论文选自考古学方法与理论(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杂志2007年9月的特刊,收录有共7篇性别考古学领域重要学者如Conkey和Gero等开创者的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来源于1998年4月的由美国研究学院主办“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考古学”研讨会,本篇文章为特刊的开篇总括,后续将会翻译余下六篇从不同学科角度具体展开的文章。这些文章着重讨论了女权主义学术和考古学在性别考古这一交叉领域中的碰撞与关联。
国内的性别考古/女权主义考古学发展方兴未艾,关于女权主义学术思想应当参与还是远离考古学研究的争论时有出现,从定名上即可发现,对于女权主义/女性主义词汇与思想的规避是一种共有的现象。这本特刊或许能对中国性别考古研究的发展与未解之惑提供一种参考。能力所限,文中所涉及的女性主义科学哲学或其他哲学领域术语翻译和理解有很多错漏之处,还望指正。

现在关于妇女和性别的考古学研究丰富且广泛,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极大发展。但是,尽管在社会与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紧密结合的领域中,女权主义研究的活跃传统已被很好地建立起来,性别考古学的女权主义归属却一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Hanen 和 Kelley (1992) 惊讶地指出,在 1989 年第一次北美公开的性别考古学会议即Chacmool会议上被提交的摘要中缺乏女权主义内容(Walde 和 Willows 1991)。她们发现 80% 的撰稿人避免使用女权主义(feminism)或女权主义者(feminist)等术语,很少提及女权主义著作、作者、影响或思想(Hanen 和 Kelley 1992:198)。当我在 1990—1991 年对 Chacmool会议的贡献者进行调查时,我了解到这准确地反映了大多数参与者自我表述的对于其他领域的女权主义研究和女权主义活动的熟悉程度。尽管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先前对性别研究有兴趣,但不超过一半的人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者,而且许多人对这个标签持强烈的保留态度(Wylie 1992, 1997: 94—95; Wylie 2002)。Conkey 和 Gero (1997) 认为这种与女权主义学术和政治的脱节继而成为了性别类型考古研究的特征(另见 Conkey 2003)。
虽然这种女权主义参与的缺乏最初可能是无意的——这是考古学现有学科传统的男性中心主义的一种功能,也许是学者不确定在哪里可以找到与新提出的关于女性和性别的问题相关的知识资源——但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它反映了对女权主义学术和实践活动更深层次的矛盾心理。正如 Engelstad在本期特刊的文章中所描述的那样,在对“性别体裁”进行了十年的高产研究之后,其中几位最热烈的倡导者已经公开赞同与女权主义的分离,作为性别考古学的明确承诺。在一个特别强硬的声明中,Sorensen (2000) 声称性别考古学深受女权主义的影响,如果它要蓬勃发展并被主流考古学的“既定结构”认真对待,就必须远离这些“政治色彩和关联”,因为在这些既定结果里性别研究仍被视为“值得怀疑”的对象(Sorensen 2000:5)。Sorensen 用流行的刻板印象来定义这些女权主义的影响,这种刻板印象让人想起1970 年代激进或文化女权主义的卡通版本,以及 1990 年代对身份政治的焦虑;她认为这是一种基于性别差异的本质主义政治承诺,是“消极的,且仅仅是反动的”女权主义(Sorensen 2000:5)。她自己的书,《性别考古学》,旨在矫正这种现状:学界真正需要的,如她所言,是一种更加复杂,在考古学上更可行的性别概念,而这一概念只能通过“粉碎…女性(woman)一词所显示的更多政治含义”来实现(Sorensen 2000:11)。
女权主义被认为本应已对性别考古学产生了强大的(负面)影响,讽刺的是,基于Hanen 和 Kelley(1992)、Conkey和Gero( 1997)和现在Engelstad提供的事实,女权主义实际上长时间在性别考古学中缺位。更具讽刺意味的是,Sorensen将性别理论的不成熟归因于对女权主义影响的妥协。Hanen和Kelley在 15 年前就表示担忧,除非充分利用相关领域中女权主义学者几十年来的学术成果,否则不能指望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在智力上蓬勃发展。特别是,正如Engelstad,K.A.N.(woman in archaeology in Norway,最早的性别考古学刊物)的挪威创始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张的那样,如果考古学家要阐明一种作为分析类别的性别概念,避免众所周知的狭隘的性别本质主义的陷阱,这种其他领域内女权主义学者积累的智慧将是特别关键的。性别考古学开始在英美形成发展的时候,Sorensen关心的普遍化、具体化的性别假设在过去十年间一直是旷日持久的辩论焦点;关于性别/性别系统”(Harding 1983)的不安分的、动态的传统已经被尖锐的批评和实证、实际的参与所改变,这些参与展示了性别建构的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偶然性和交叉性。它为考古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源,特别是当女权主义者摆脱了最极端的建构主义、转而选择性别扮演模型(performative model of gender),这些模型在对性别本质论的应对中产生,并考虑了性别身份的实际体现方式、制度结构的物质结果,并沿着性别路径追踪社会分化的不平等现象(Moya和Hames—Garcia 2000;Alcoff 2006)。
《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本期特刊的催化剂是一种信念:应当承认考古学可以从高度复杂、多样化和快速发展的女权主义研究传统中获得许多好处。事实上,本期的撰稿人分别就考古学实践的不同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性别研究 ”与女权主义学术的剥离,而非与女权主义的联系,才是值得被密切关注的问题。那么,关键的问题是,女权主义学术和女权主义政治能为考古学提供什么?政治对考古学有什么帮助?将明确的女权主义视角的资源用于考古学的实践有什么意义?
这一期的几篇文章源于1998年4月由美国研究学院主办的研讨会,在此背景下焦点问题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研究考古学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一直是 “女权主义方法辩论 ”的关键,当时女权主义社会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认为,寻求一种独特的方法或独特的女权主义调查形式——一种被看作能够解决那些主流传统中的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对于经常被忽略或者被边缘化的问题特别重要的“女权主义科学”方法——是适得其反的。Longino认为,询问 “作为女权主义者从事科学研究 ”意味着什么(Longino 1987: 53)会更有成效,并需要认识到在实践中这个问题的解答就像是:“成为女权主义者意味着什么”一样答案十分多样化,就像女权主义者承诺 “进行科学研究”的领域一样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着这种精神,女权主义社会科学家们制定了一系列准则作为女权主义者在各个领域进行广泛研究的规范(Eichler 1988, Fonow and Cook 1991, Hesse—Biber and Yaiser 2004, Hesse—Biber 2007)。这些准则都集中在四个被普遍接受的承诺之上(Wylie 2007)。第一个承诺是对女权主义研究目标的具体说明:作为女权主义者进行研究,意味着要解决与女性相关的问题,或者更广泛地与那些被性别结构的不平等系统所压迫着的人相关的问题,并且提供为改变这些压迫所需要的理论。第二个承诺是女权主义者应将其研究建立在女性和那些被传统的性/性别结构边缘化的人群的经验之上。正如Smith在1970年代初所阐述的,以及后来Harding(1993)所阐述的那样:女权主义者应该以女性的日常生活作为研究的“起点”:她们应该追寻问题并采取策略,使得社会生活中那些(性别)方面的问题和理解形式成为关注的焦点,而这些问题通常被传统社会科学规范中的男性中心视角所“掩盖”(Smith 1974;1987:85)。关于 “经验证据”(Scott 1991)的地位和正当性的辩论,反驳了任何将经验视为既定的或天然正当的、作为认识论基础证据的倾向(Wylie 1992)。性别化的经验和自我理解是女权主义研究者的重要资源——在理解现有研究传统的局限性时,在构建新的研究问题时,在扩大解释或说明性假设的范围时,以及在判断描述性或分析性结构的合理性时——但它总是可以受到批评性的审查。Anderson(2004)对性别化经验和女权主义价值观如何在所有这些层面上为研究提供有效信息做出了特别引人注目的说明。
第三组原则规定了女权主义研究的伦理和实用规范;女权主义者应该对研究对象和受研究过程及其结果影响的人负责。至少,女权主义研究本身不应该是一种剥削性的研究;理想情况下,它应该是建立女权主义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场所。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女权主义者进行科学研究意味着实施平等的、合作的知识生产形式,旨在抵制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统治实践”形式时的权力动态和等级制度(Smith 1974)。在这一点上,女权主义实践的承诺一方面与激发各种形式的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基于社区的合作研究的理想相一致,另一方面也与Longino(2002)提出的“民主化”的科学的认识论相一致。对Longino来说,广泛参与的条件有助于实现认识论的目的;只有当一个研究团体成功地将不同的批判观点引入其主张,并确保这些观点得到采纳时,它才有理由将其调查过程中产生的主张归纳为“知识”。她提出了一个优先考虑这些程序要求的客观性概念。能证明客观性的并非中立假设——效仿“从无处看世界”(view from nowhere,托马斯·内格尔的哲学观点,我不了解)——而是对不可避免会影响调查的利益负责,体现在变革性批评的社区机制中。(Longino 1990: 71——74)。
最后,几乎所有关于作为女权主义者进行社会研究的指导原则都把反思性作为核心优点。这一作法的出发点是从女权主义科学研究中认识到,研究的所有方面——它的预设、实践惯例、产品——都反映了其制造者的处境和实用利益。但是,这种洞察力并不是对科学和客观性理想的愤世嫉俗的谴责,而是对提高认识论标准的承诺;这种承诺的出发点是作为女权主义者从事社会科学,需要在研究中建立起一种对其偶然性、文化与实践过程的特殊性的系统批判性理解。这一指示不仅体现在既定的学科传统中,也延伸到女权主义研究者所发展的反传统中。至少,培养批判性反思性立场的指示要求女权主义社会科学家将他们的研究背景化。“说明他们的前提,而不是隐藏他们”(Reinharz 1992: 426)。在更强烈的表述中,它要求他们考虑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利益和价值观念是构成其研究过程以及它所产生的理解的多个源头(Fonow和Cook 1991;Mies 1983)。Harding将此描述为对“强客观性”(strong objectivity)的要求:实证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工具应该被(反思性地)应用于研究过程本身,实际上是将其结果与它的生产条件进行索引和校准,使它的结果与其生产条件相适应(Harding 1987, 1993)。
在元(meta)层面上,Longino论证了“方法论的临时性”的指导原则:女权主义者应该准备根据她们从实践中学到的东西来修改她们的任何规范(Longino 1994: 483)。所有这些原则的根据,以及评估和修订这些原则的基础,就是Longino所说的“底线”的女权主义承诺:女权主义者采取的任何方法论规范都应该 “防止性别消失”(Longino 1994:481)。请注意,根据这些原则,在任何特定的研究领域中,性别是否或以何种形式被证明是一个相关的坐标轴,都是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些问题只能通过系统的经验调查和探索性的概念分析来解决。作为女权主义者进行研究的要求是,这些问题必须保持开放,并列入研究议程,而且预设和调查的结果必须对女权主义者在追求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负责。
这期特刊的稿件以不同的方式体现了上述每一条准则。考古学中的性别研究已经非常有效地将被忽视的有关女性和性别的问题纳入该领域的研究议程。我认为,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性别研究者利用了他们在学科中的处境和性别经验的资源,在这个学科中,女性代表的重大变化至少打破了关于女性能力和角色的一些既定假设(Wylie 1992, 1997)。女权主义视角所带来的是一种批判性的、理论和经验上的关于知识生产的立场。在本组论文里,这体现在对考古学的文化和机构如何复制性别规范惯例的持续分析中,不仅是在提出的问题和考虑的变量中,而且在于构建这些问题和文化主体的条件的潜在假设中(Wylie 2003)。例如,Moser和Tomaskova质询了构建考古学至关重要的田野工作中的男性规范,和田野工作作为专业社会化的主要背景对考古学的学科身份的决定性作用的影响。关于学科实践如何对考古学招聘模式和社区动态产生影响,Moser提出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无论这些规范是否是有意为之,它们都构成了强大的“守门”力量,在背景上有效地限制了情境知识(situated knowledge)的形式和认识论资源的范围,在前景上建构了研究议程和学科的可信规范。在对“理论的性别”的补充性分析中,Conkey追溯了在接受和回应方面的性别差异的影响。“边缘化的技术”——它往往是无意和未被承认的,却有力地限定了什么是理论,以及谁会被归为理论家,其影响之深远与机制之微妙不言而喻。同样,它们在背景中发挥作用,巩固了可信度的规范,这些规范表面上可能没有性别之分,如对简单性的承诺,对剥离背景的一般性的偏爱,但却系统性地使性别 “消失”,正如Longino在提到生命科学中对本体论和因果简单性的偏爱时所描述的一样(Longino 1994, 1995)。
从考古学田野工作和理论的具体细节中抽身而出,Gero确定了普遍存在的认识论和本体论规范——寻求封闭、减少复杂性和模糊性的冲动——是所有形式的考古学实践的基础,并且以不同的方式预示着这些实践。正如Longino所说,这些是“社区价值”,它们被视为不可避免的、实践的基础性承诺,尽管它们同时不可避免地是学科发展的具体轨迹的产物,在经验和概念上都是不确定的。在与学科实践的这些特征保持距离并对其进行批判性评估时,这些文章都指出了将分析建立在他们的经验基础上,而且建立在明确的女权主义立场上可以获得什么。这使他们能够推动反思性分析,超越过去对于相关问题的漠视,并提供对条件的诊断——基本假设、实践形式、认识论规范——这些条件往往在无意中复制了性别考古学所要纠正的差距和扭曲。
在不同的方式和程度上,本期特刊的作者也都考虑了将这些批判性的见解转化为建设性目标。Moser、Conkey和Gero争论的正是各种责任——即恢复产生“社区价值”的历史偶然性,这些价值设定了当代考古学的各种实践背景——女权主义者已将其作为一系列社会科学中女权主义实践的基石。将调查“语境化”,划定其独特的偏见形式(delineating its distinctive forms of partiality),为确认目前被边缘化的观点提供了实质性的基础,这些观点可以为调查提供特别富有成效的起点,并为变革性批评提供资源。Tomaskova认为,当有关目的和认识论可信度的假设得以明确时,就会出现各种可能性;她“确定了一系列可能的替代方案”,以女权主义地理学家的实践为例。本着这种精神,Joyce和Tringham提供了一个持续和丰富的论证,承认数字和超文本媒体是女权主义实践的重要资源。这些媒体不仅极大地扩展了考古学交流的范围,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重新设定考古学家与不同的专家和非专家群体的接触方式。Tringham专注于考古学图像制作,看重建立彻底、多元、可互动和可视化形式的潜力,而Joyce呼吁对过去的景观进行坚决的多声部、“异质”的探索。二人都敦促使用这些技术来分散传统权威等级,使得不同位置的对话者参与其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看到了建立合作、民主化的实践形式的潜力,而这正是女权主义者在规范(伦理和政治)和认识上所倡导,并且在一系列的学术和活动背景下努力实现的东西。
那么,这些论文所涉及的挑战是,如何发展一种考虑到其自身偏见性的考古学。同时充分利用其潜力,作为一门实证学科,打破既定的假设,教会我们关于文化历史和我们自身的新知识。性别考古学当然已经并将继续贡献关于文化历史复杂性的重要见解。但是,鉴于女权主义承诺要考虑并对影响其研究实践的认识论和政治承诺负责,这种自觉的女权主义考古学为在更深层次上重塑研究实践提供了前景。有了这种广泛的女权主义参与的愿景作为试金石,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进行考古学研究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意味着了女权主义承诺怎样能够促进一个概念上更丰富、经验上更强大、以及更广泛的负责任的未来考古学。
- 0004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