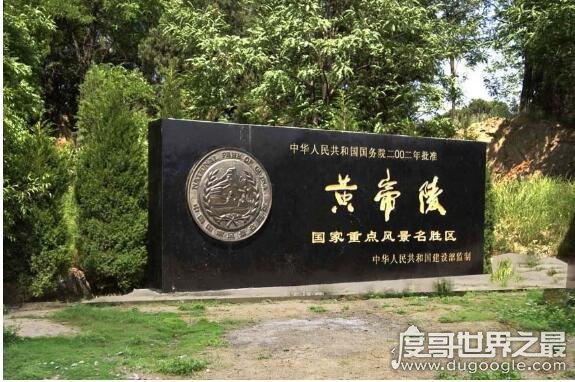曹操放火烧山方才逼出此人——他是谁,有何过人之处?
(说历史的女人——第1312期)
说起阮瑀,人们都知道他表章书记写得好,他是曹操的司空祭酒,军中文书大多出自阮瑀之手。可以说,他是曹操的首席笔杆子。
相传建安十六年,阮瑀随军西征关中,曹操请阮瑀代笔写一封书信。阮瑀骑在马上沉吟片刻,挥毫点就,呈给曹操。曹操提笔想作些修改,竟不能增损半字。
后来,陈琳也来到曹操麾下后,军中檄文才由他俩人共同承担,自此,阮瑀又成了陈琳的黄金搭档。
阮瑀的表章书记又多又美,他写的快,且铺张扬厉,颇具战国时代纵横家的特色,他的代表作是《为曹公作书与孙权》。
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魏蜀吴三国军事与外交并用,都想争取战争主动,打破三足鼎立的平衡。这时,三方关系很是微妙,既相互对抗,又适当妥协,既彼此防备,又伺机拉拔。建安十三年,为了破坏孙刘联盟,曹操令阮瑀给孙权写了这封书信。

“那时候,车,马,邮件都慢……”这是木心的诗。一个慢,让书信有了慎重和深思熟虑的意味,却也被现在快捷方便的微信远远丢在身后。
不知道才思敏锐如阮瑀,经过了几许思索,几许考虑,但在这封书信里,他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恰到好处,不卑不亢,见字如面。
“离绝以来,于今三年,无一日而忘前好。孤怀此心,君岂同哉?”阮瑀走的是“情”字路线,开篇便放低身份,向孙权示好,话说的情真意切。
接下来,他围绕重修旧好展开话题,既有军事形势的分析,敌我军情的对比,摆明军事实力,向孙权展示硬的一面;又有领地许诺,误会解释,适度让步,是为软的一面;还有援引古代众多典事,从淮南王、隗嚣、彭宠偏听偏信,成为天下笑柄,说到梁孝王不接受公孙诡、羊胜蒙蔽,窦融斥责逐走张玄,二位贤人随后福气满满,指示对方前路,这是理的一面。阮瑀实在是太会写信了,看过这封书信的人,没有不动容的。
孙权收到书信后,是否被说服,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但这篇文章却名噪一时,后被南朝萧统收入《文选》,这也是书信史上一次经过大于结果的成功案例吧。
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会把这封书信看作阮瑀的代表作,这篇作品,站在天下的角度,用的是曹操的语气,代表的是魏国的立场,唯一和阮瑀有关的,只是他的文笔而已。而那只笔,想写的字,想表达的思想,依然由不得阮瑀自己。
所以,我一直觉得,公文后面的那个人,是可悲的。
阮瑀其实是一个很清高的人,他年轻时曾拜当时京都著名大儒蔡邕为师,因得名师指点,文章写得十分精炼,闻名于当时。求贤心切的曹操听说阮瑀有才,就召他做官,阮瑀拒绝了。曹操不甘心,一次又一次派人召见,阮瑀没有办法只好躲进深山,当起隐士。
和苏轼“拣尽寒枝不肯栖”的孤傲不一样,阮瑀压根是逃避的。他的老师蔡邕因为跑到董卓坟上哭祭,引来杀身之祸,政治场上站错队伍,不是一句性情而已就能解决问题的,甚至这个时候,才华也无济于事。政权更迭,动乱频频,让家成为比国更重要的群体,阮瑀不想搅进乱世这淌混水,宁愿退到岸上修心养性,明哲自保。或者说,他还要再观望一下时局变化,看清这纷纷扰扰的尘世。可曹操求贤若渴,竟然命人放火烧山,方才逼出阮瑀,勉强应召。
历史上以放火烧山相逼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晋文公重耳,另一个就是曹操。当年,晋公子重耳流亡时,风餐露宿,饥寒交迫,差点饿晕过去。跟随他的大臣介子推就割下大腿上的肉煮汤给重耳喝。后来重耳返国做了国君,许多人都积极邀功请赏,介子推却带着他的母亲躲进深山,做了一名不食君禄的隐士。为了逼介子推出山,重耳就下令放火烧山,结果介子推和他的母亲都烧死在大山里。
介子推认为忠君的行为发乎自然,而接受奖赏是耻辱的,他不给重耳回报的机会,这让他的忠诚无比纯粹和珍贵,也让他的死,成为晋文公心里永远无法填补的伤痛。
但阮瑀没必要放火烧山不出来,搭上一条命,他和曹操两不相欠,他不用背负耻辱,也无须自证清高,清高就像金子的含量,顶多在世人看来,纯度上打点折扣而已。

做了官的阮瑀,很快表现出他如鱼得水的另一面。他写的那些煌煌大论的檄文就不必说了,那是他的本职工作。他在曹操的一次宴会上,即兴抚弦而歌,不但显现出他在音乐上的过人才华,连这首《琴歌》也写得让人瞪目:
奕奕天门开,大魏应期运。
青盖巡九州,在东西人怨。
士为知己死,女为悦者玩。
恩义苟敷畅,他人焉能乱。
在诗中,他热烈歌颂曹操的事业,是顺应天运的事业,如果曹操在东边建立政权,西边的人就会埋怨,可见民意是如何沸腾地拥戴曹操。他视曹操为知己,认为他对天下士人的恩德谁也无法替代。前一刻还坚定地拒绝做官,后一刻便写出这样精准拍马屁的诗句,不是不会,而是不愿。人们这才明白,原来阮瑀是青蛙一样的两栖动物,在岸上,在水里,都可以生活得游刃有余。
孔子说: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君子痛恨那种不肯实说自己想要那样做而又一定要找出理由来为之辩解的作法) , 阮瑀不辩解,他的人生有N多面,每一次转身得惊艳而决绝。
但真实的阮瑀到底藏在哪一面,在他的一首《无题》诗里,我们却似乎隐约看见阮瑀人生的主题。
民生受天命,漂若河中尘。虽称百龄寿,孰能应此身。
尤获婴凶祸,流落恒苦辛。
我行自凛秋,季冬乃来归。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辉。
念当复离别,涉路险且夷。思虑益惆怅,泪下沾裳衣。
四皓隐南岳,老莱窜河滨。颜回乐陋巷,许由安贱贫。
伯夷饿首阳,天下归其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
白发随栉堕,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惓,行步益疏迟。
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
苦雨滋玄冬,引日弥且长。丹墀自歼殆,深树尤沾裳。
客行易感悴,我心摧已伤。登台望江沔,阳侯沛洋洋。
临川多悲风,秋日苦清凉。客子易为戚,感此用哀伤。
揽衣起踯躅,上观心与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
鸡鸣当何时,朝晨尚未央。还坐长叹息,忧忧安可忘。
在这个人世间,活着本身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阮瑀虽然选择归隐,像商山四皓,颜回,许由那样淡泊世事,但除了保全自己之外,他还想有一份坚持:何患处贫苦,但当守明真。贫苦无妨,颠沛流离亦无妨,路途艰险更加无妨,人生在世,毕竟还是需要有所坚持。他所求的,不只是囿于一方的安然喜悦,而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君子明德。
但他时不时也会沉浸在生命流逝,壮志未酬的哀伤之中:白发随栉堕,未寒思厚衣。四支易懈惓,行步益疏迟。我已经老了啊,一梳头,白发就会大把地掉落。这比杜甫的“白头搔更短”更让人痛惜,尤其在阮瑀写来——他死的时候,也不过是四十七岁的壮年。人生难堪,莫过英雄迟暮。可阮瑀,还未至迟暮,就已有了这样惨淡的心境。
“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自知百年后,堂上生旅葵”。这四句诗是极其沉郁和苍凉的,它写出了许多人哀哀不能言的沉郁,写出了空屋长满野草的苍凉,一个“自知”,是多少人终其一生也看不透的虚无,但阮瑀看透了又能怎样,除了“我心摧已伤”,除了“还坐长叹息”,
从内容来看,这首诗应该写于他应召曹操之前。彼时,阮瑀年华正好,剑未出鞘,却写下这样哀戚颓丧的句子,读来实在让人感伤。
这样的颓丧,其实贯穿了阮瑀的后半生,虽然后来的他,接受了曹操的邀约,有了英雄用武的舞台,看上去也似乎更加的温和冲淡,安然接受属于自己的命运。可事实是,也许是因为他是多栖的,看懂了世间的无常,明白有的事情无法选择,有的事情无法逃避,就只能在被选择的队伍之中,努力做好自己,不积极,不消极,不参与,不放弃。
所以在阮瑀《无题》诗里,还能够看到漫漫的悲哀,穿透千年尘埃也无法掩盖的痛苦心境,而到了《七哀诗》里,就只有一派冷静淡然的陈述,从容不迫地面对死生衰亡。
《七哀诗》
丁年难再遇,富贵不重来。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冥冥九泉室,漫漫长夜台。身尽气力索,精魂靡所能。
嘉肴设不御,旨酒盈觞杯。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
“出圹望故乡,但见蒿与莱。”人生千帆过尽之后,回望故地,视野是开阔的,生命也是开阔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阮籍的亲生父亲,父子二人有一种“老子英雄儿好汉”之势,其子阮籍是“竹林七贤”之首,和他一样天赋异禀,才华横溢,和他一样对政治谨慎逃避,但阮籍崇尚庄子,这使他的行为更加奔放无忌,放浪不羁。山林深野,自然万物,都是他的心灵自由驰骋的大世界,比他父亲阮瑀活得狂放,洒脱。
阮咸,是阮瑀的孙子,阮籍的侄子,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与阮籍并称为“大小阮”,他似乎继承了阮瑀的音乐天赋,精通音律,有一种古代琵琶就是以“阮咸”为名的。
(文/说历史的女人·华之)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