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英国是如何在管辖范围内保护海外臣民的?
#历史开讲#
文|木木
编辑|观星
“唐·帕西菲科”事件发生于1850年,与其说这一事件确立了英国对海外臣民保护的宽泛原则,不如说这一事件是对既往实践的确认和对宽泛保护原则的宣示。
“唐·帕西菲科”事件又引起了帝国保护的另一个问题:谁是英国臣民?
换句话说,在大英帝国管辖范围内的殖民地、保护国、租界等不同类型的领土上生活的人们,谁将有权得到英国的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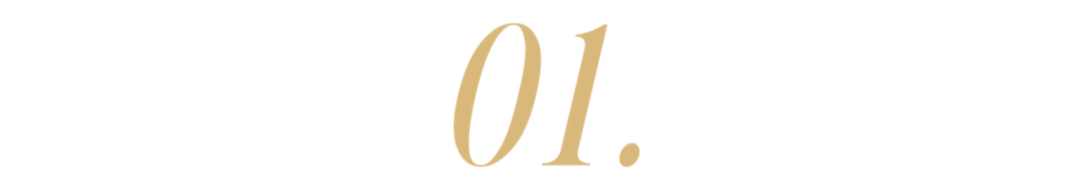
斯托厄尔勋爵在1804年“印度大副号”案的判决书中认为,无论是中立方还是敌对方,只要他们在英国公司或商馆的保护下在东方进行贸易活动,他们的住所均被视为英国的。
在这起案件中,一名居住在加尔加答的美国领事被认定为英国商人,从而可以得到英国的保护。
斯托厄尔勋爵指出,“但是在东方,从古老的时候开始,不混同的特征就一直被保留着;外国人不被接纳为东方国家的成员;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外国人仍然是陌生人和旅居者。
他们并不能在该国主权范围内获得任何国民身份,而他们的国民身份只能来源于为他们的生活和贸易提供保护的公司或商馆之中”。

因此在印度居住的英国公民在将会获得新的处所地,但并不属于印度法上的处所,而是适应印度习俗和种姓制度、有限度地在印度适用的英国法上的处所。
这一判决所确立的不混同原则完全吻合东印度公司的实践,当时主要适用于东印度公司的商人及员工,随后扩展至散商和居住在东印度公司控制范围内的居民。
东印度公司与英国政府构成了一种双政府结构,东印度公司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程度自治独立的政府。因此,对英国本身来说,东印度公司政府已经是外国了。
自然地,与东印度公司建立起服务关系的英国人,若长期生活在东印度公司控制范围内,包括占领的领地或在其他区域开设的商馆,其在英国的本土处所将不再保留。
他们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来的国家而成为这一外国政府的臣民。
皮葛爵士在讨论此案件时赋予了其在英国域外管辖历史上不同寻常的意义,指出了十九世纪英国国家与贸易公司在保护对象的确定与保护的实践上具有含糊性质。
皮葛并不认为斯托厄尔勋爵所作出的判决与英国在东方国家行使的治外法权有联系。

尽管斯托厄尔勋爵的判决是以不混同原则为基础,但是他所指的“陌生人和旅居者”是在英国商馆工作的外国人,而不仅仅是英国人。
这些外国人之所以是陌生人和旅居者,是因为他们不仅没有获得一般主权国家所赋予的国民身份或提供的保护。
他们也没有在本国承认的任何机构或公司之下开展贸易以保留他们原来的国籍,他们获得现在的国民身份是商馆所赋予的,而他们正是在商馆的保护之下生活和开展贸易。
他们的住所不是印度的,是因为印度政府实际上对他们没有管辖权;他们的住所也不是英国的,因为女王对他们尚未取得管辖权。
因此,“这实质上是商馆处所,因为商馆囊括了不同国籍的人们,所有人均不受印度法管辖,而是他们已经建立起处所的商馆和他们接受的国家法”。
尽管存在这种双政府结构的事实,但是东印度公司与英国并非完全独立于彼此,章程仍然由王室颁发,而章程是否续期仍有赖于议会的同意。
在公司-国家模式中,公司主权赋予了贸易公司极大的权力,商馆也只是作为公司管理的一个分支机构。

而并非独立的法律主体,商人、领事、大班和代理人等等所享有的司法豁免权和国家对臣民的保护仍然归于公司,归根结底还是英国国家本身。
进入十九世纪,自由贸易的思想与诉求经由英帝国遍布全球的中层力量逐渐强化,公司-国家模式也走向历史的终点。
皮葛所提出的商馆处所地也远不能满足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活动。

区分处所地并不能必然地为所有英国人提供保护,因为自十六世纪以来有着大量的公司商人在东方国家定居,其子女后代并非出生于英国。
按照英国法的规定为这些人提供保护就无法从处所地出发。1844年“马尔塔斯诉马尔塔斯”案就确立了一项更为广泛的保护海外英国臣民的原则。
此案中,遗嘱人马尔塔斯出生于土耳其的士麦那,几乎大半生都居住在这座城市。他的父母均为英国人,在他六岁时曾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十四岁回到土耳其。

1824年,他再次回到英国,并居住了大概两年时间。在完成学徒后,他以英国商人名义在士麦那经营着自己的业务,并设立了自己的商店。在他死亡之后,围绕遗嘱继承发生了纠纷。
马尔塔斯生前及其父母长期声称自己是英国人,而土耳其当局也将他们按照英国人对待,并且还授予他们英国商人在土耳其领地内所享有的一切特权。
根据奥斯曼帝国的法律,其帝国臣民无权随意处置其财产,但在土耳其人去世时可按照一定的固定比例分割。但是,根据1675年单方让与协定。
若任何英国人或接受英国管辖之人恰好在土耳其境内死亡,其财产应当按照死者遗嘱内容将其交给指定的继承人或英国领事。
在马尔塔斯去世之时,士麦那的土耳其当局将其财产留在原处,按照他的遗嘱进行处置;若没有遗嘱,则按照英国法律而不是土耳其法律进行分配。
因此,死者的财产被认为是英国臣民的财产而不是土耳其人或住所地为土耳其之人的财产。本案法官斯蒂芬·勒欣顿并不认为区分处所对保护在土耳其的英国人有何实际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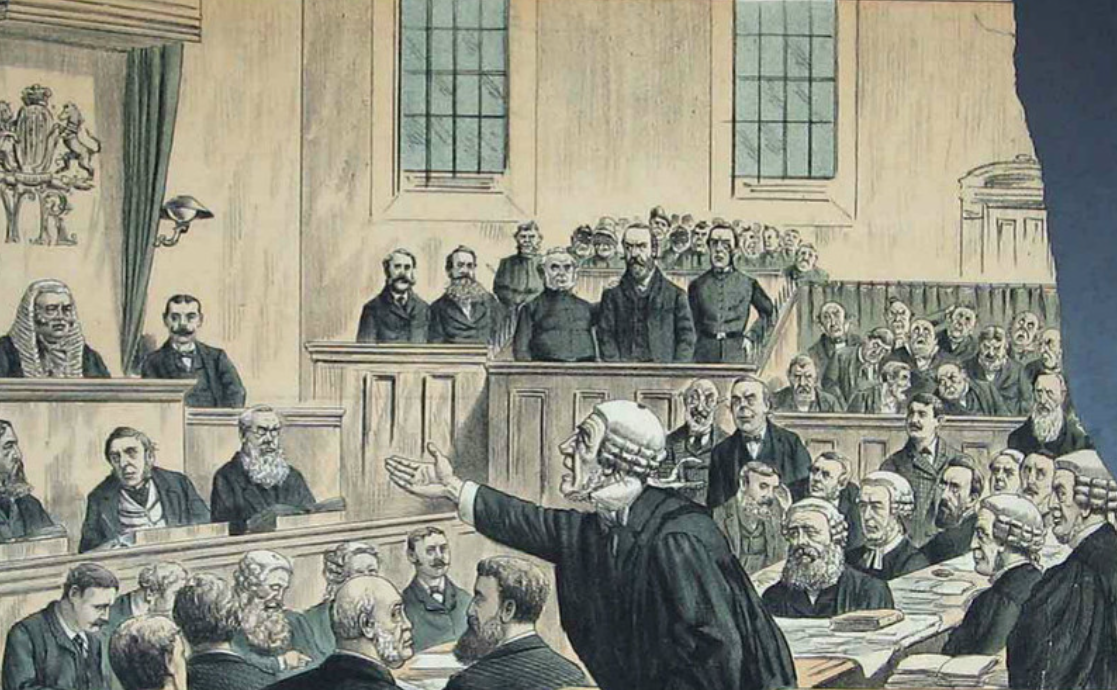
在这份长篇判决词中,他不仅反对1804年“印度大副号”区分处所地的保护原则。
而且提出了英国与土耳其之间的单方让与协定与新签署条约的规定应当使用更加自由和扩张性的语言来解释。
即使到了今天,尽管已经有许多强大的头脑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仍没有普遍同意的关于‘处所’一词的定义,也没有对构成处所的因素达成一致。
确实,我认为这个词有不少于十四个或十五个不同的定义。环境不同,意图不同,居住地或处所的确定也会不同,这两者之间必须明确区分。
因此,如果条约并不适用于确定处所,因为居住地经常与处所混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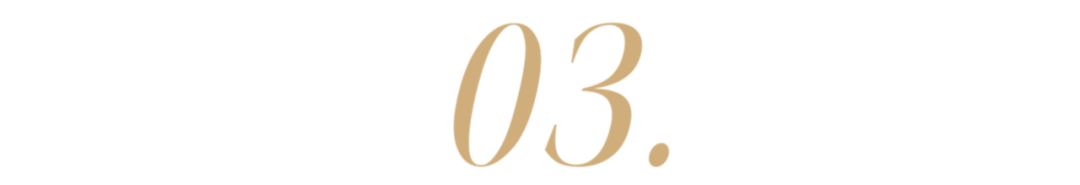
英国商人以及在死亡之后的家属可能会发现突然之间他们要接受一种与他们的宗教、信念、情感、习惯以及他们对个人和家庭福利的考虑完全不同的法律。
这完全与他们的意图不相吻合;而且,他发现,土耳其法不仅适用于遗产的处置,而且还适用于活着的时候,单个人可能在不受任何条约保护的情况下生活在土耳其。
我不知道土耳其有什么样的法律适用于居住在土耳其的英国商人,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完全服从土耳其法律将是对英国商人的基督教信仰、教育和习惯构成严重的祸害。

我想要指出的是,我不希望就这种没有必要决定的任何问题发表意见;因此,如果从法律上来说死者的处所地在土耳其,那么我的判决不会涉及到处所问题。
如果处所地法适用,则土耳其法应遵守条约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财产的遗嘱继承应该受英国法管辖;如果死者并不居住在土耳其,而是在英国居住,则英国法应当适用。
因此,对于英国臣民是否可以获得土耳其的处所,我不发表任何意见。但是,我必须指出——我认为任何推定都违背了英国基督教臣民在奥斯曼高门领地内取得处所的目的相违背。
斯托厄尔勋爵所说的在宗教、习俗和习惯完全不同的国家间处所不混同原则,其推理并不适用于原本信仰穆斯林或打算信仰穆斯林的英国臣民。
如果说1804年的“印度大副号”案件还在纠结于保护对象是否是具有英国国籍或居住在英帝国的领土范围内。
那么四十年后的“马尔塔斯诉马尔塔斯”案已经完全突破了处所地这一国际法上的基本原则。
而是将保护的范围囊括至所有与英帝国产生联系的任何人,这一点类似于现代美国法“长臂管辖”中的最小联系原则。

进一步地,此案还突破了1809年英国与土耳其签订的《达达尼尔条约》第十条关于禁止向奥斯曼帝国臣民颁布保护状的规定。
勒欣顿表示应当在最宽泛意义上理解和解释条约关于保护的规定,还需要考虑到十七世纪以来奥斯曼土耳其与英国之间的单方让与协定。
这样才可以真正实现在英国看来是真正的保护的目的。在大英帝国范围内,保护的对象不再仅限于处所为英国的那些人,而是任何只要与英国产生一定联系的人。
均可有正当理由请求保护,他们可以是公司职员、公司商人以及保护人制度下的任何人,甚至于自认为英国人的基督教徒,都可以获得保护。
正如巴麦尊在1850年“唐·帕西菲科”事件中曾指出,在大英帝国领地内的英国人,在任何一个东方国家。
“无论其父母是什么国籍的,只要涉及到在英国领地内这种性质所附带的任何特权和利益,就可以享有被置于英国保护之下的好处”。
国籍并不能成为阻止英国为其臣民提供保护的理由,保护也是基督教文明国家对非基督教的半文明或野蛮国家而言的。
- 0001
- 0000
- 0002
- 0000
- 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