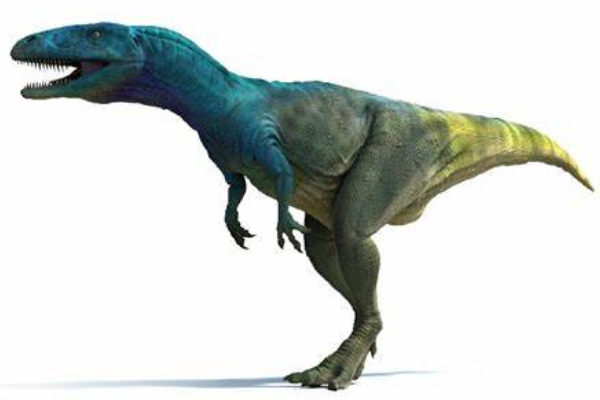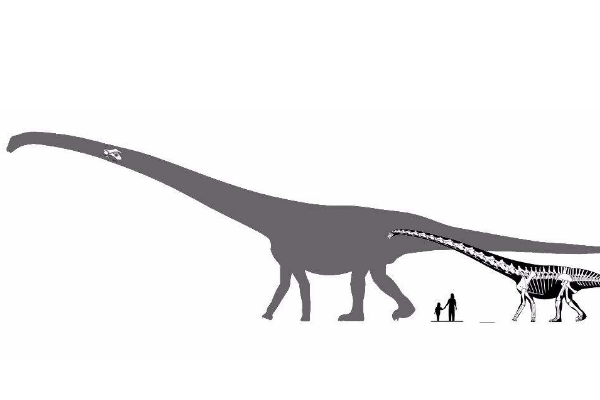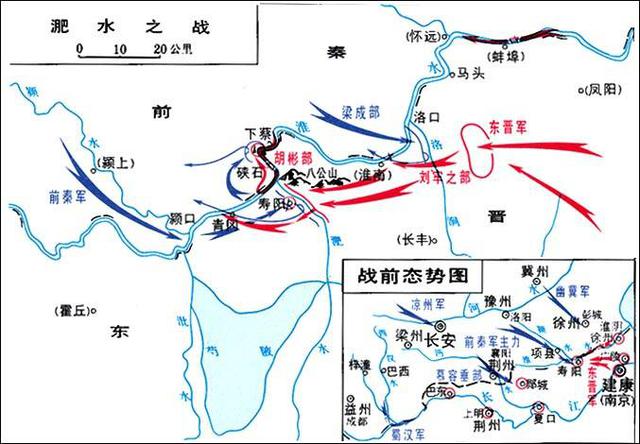论考古学史上的二里冈与二里岗之争
二里岗本是郑州老城东南的一道黄土岗,因距老城区约2华里而得名。20世纪50年代前期,郑州市文物组、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和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等单位曾在此进行考古发掘,遂将其命名为二里岗遗址。遗址内发现有龙山、商和战国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遗存,尤其以商文化堆积最为丰富和重要,发掘者分析认为其年代要早于殷墟,进而提出了二里岗期的概念[1],又称商代二里岗期或二里岗期商文化,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早在1954年,就曾有学者在文中使用二里岗文化来称呼郑州地区的殷商文化,但并未对文化内涵进行详细论述,故应者寥寥[2]。20世纪80年代后期,再度有学者提出二里岗文化的命名,用以指代商代前期的考古学文化[3],逐渐为考古界广泛接受。
自20世纪50年代至今,针对二里岗遗址和二里岗文化的研究持续不断,成果数量颇丰。检视已有研究成果,我们发现一个奇怪的学术现象,二里岗也被写作二里冈,两种写法不但长期共存,而且还相安无事,甚至在同一本著作或同一位作者的不同文章中,都存在着二者混用的情况,不免让读者心生疑窦、无所适从。许宏曾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一现象,提出了“遗址名用字应以经典报告的版权页为准”的观点,但又戏言“不自信”。[4]
究竟是二里冈,还是二里岗?二者孰对孰错?笔者认为有必要进行探讨,本文正是在这一方面的努力。二里岗文化因二里岗遗址而得名,二里岗遗址又是依据发掘地点之地名来命名的,因此,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搞清楚发掘地点地名的准确写法。
一、地名书写的历史变迁:
从二里冈到二里岗
二里岗位于郑州老城东南郊外,东起凤凰台村南地,西和南关外高地相连,东西长约1500米,南北宽约600米,是一道高出附近地面约5—10米的黄土岗地,中部有一东西向山脊,南北两侧逐渐走低,山岗整体并不高大,但起伏比较明显,陇海铁路和陇海马路东段(今货站街)沿东西向穿过岗地。熊耳河自西向东流经南关外,在二里岗西北约80米处,折向东北流去。有一条时令小河自南向北穿过二里岗西头注入熊耳河,当地人习惯把时令小河作为二里岗和南关外高地的分界线,时令小河东边约40米处即南北向的二里岗大道(今郑东南路)。[5]20世纪50年代以前,二里岗作为黄土岗阜的地貌特征比较明显,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郑州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二里岗被规划成了工厂和住宅,岗地被不断平整,二里岗逐渐被一轮又一轮的城市建设浪潮吞没了,原来的黄土岗地逐渐消失了,仅作为地名被保留了下来。
地方史志中有关于二里岗的描述,据乾隆十三年《郑州志》卷二舆地志之冈阜条,“二里冈在州城东南二里许,冈势盘曲,其东北为凤凰台”[6],民国五年《郑县志》卷二舆地志照录此文。由此看来,自清代至民国初年,郑州老城东南的黄土岗地一直被写作二里冈。之所以写冈而不写岗,是因为古代字书多认为岗是冈的俗字,如明代梅膺祚撰《字汇·寅集》关于冈的解释,“俗又加山于上,非”[7],《康熙字典》沿袭此说,明代张自烈所撰《正字通》也认为,“岗,冈俗字”,民国时期权威的《中华大字典》也采纳了这一观点[8]。
但有趣的是,至迟在民国初期,二里岗的写法也已出现。据《郑县志》卷三建置志之七区屯砦条,记有一个名叫二里岗的村庄,“城厢区第七叚:杨庄、二里岗、弓庄、南陈庄、康庄、晋王庙和凤凰台”[9],二里岗村就位于二里岗的南部边缘。同一部志书,却存在二里冈和二里岗两种不同写法,这绝不是笔误,恰恰反映出了当时的客观情况。按照当时的字书严格来说,表示山脊之意时,只能写冈而不能写岗,郑州老城东南黄土岗只能写为二里冈,但用于村名时,岗和冈似乎都无不可,但二里岗村应是当地通行的写法,志书作者经过审慎思考,采取了“名从主人”的原则,这才就出现了二里冈和二里岗村并存的情况。
至迟在20世纪50年代初,郑州东南的黄土岗已经被写作二里岗。此外,郑州市还有许多带有二里岗的地名,如二里岗村、二里岗车站、二里岗大道,当地人们还“习惯上把陇海铁路以北,郑州市东南郊一带地方都称作二里岗”[10]。后来二里岗还成为了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1954年5月,郑州市政府将凤凰台乡的魏庄、柴庄、二里岗三个自然村合并成立二里岗街政府[11],即今天郑州市管城区二里岗街道办事处的前身。在当时相关的新闻报道中,涉及此处的也写作二里岗,如“黄河工程队在二里岗建筑工程中超额完成计划”[1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字典中对于岗的解释已然发生了变化,当山脊的义项时,不再把岗视为冈的俗字,而认为“岗同冈”[13],二里岗的写法与字典解释也没有了抵牾之处。
二、二里岗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二里岗遗址的发现,与韩维周密切相关。韩维周是河南省巩县(今巩义市)康店镇马峪沟村人,现当地还保留有其故居对外开放展示。20世纪20年代,韩氏曾就读于张嘉谋创办的河南国学专修馆,后就职于河南古迹研究会(张嘉谋任该会委员长),担任助理员一职[14],参加了一系列考古调查和发掘活动,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1935年8-9月,韩维周参加了山彪镇遗址第一次发掘,重点清理了东周时期的001号大墓,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是年11月,听闻琉璃阁有古代文物出土,郭宝钧、韩维周等人又赴此进行了调查和试掘,因天冷地冻未进行大规模发掘。1936年10月11日-11月4日,李景聃和韩维周等人在豫东商丘和永城一带进行了为期二十五天的调查,发现了商丘青岗寺、永城造律台和曹桥等遗址。同年11月底至12月间,郭宝钧、李景聃、韩维周以及赵青芳等人又先后在造律台、黑孤堆和曹桥等三处遗址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15]。1937年3月11日到6月26日,韩维周参加了“中研院史语所”在琉璃阁的发掘,历时三个多月,发现战国大墓5座、中小型墓39座,另有殷商及汉代墓葬20余座,出土各类文物数千件[16]。抗日战争爆发后,河南古迹研究会工作宣告结束,韩维周回到家乡巩县,成为一名小学教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韩维周被调到郑州市南学街小学任教,他经常利用闲暇时间到城郊建筑施工现场进行实地调查。1950年秋,他在二里岗一带发现一处范围广大的遗址,采集了一部分绳纹陶片和磨光石器,根据过往积累的发掘经验,他推测这应该是商代遗存,遂将相关情况报告给了河南省文管会,引起了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当年12月,河南省文管会委派赵全嘏、裴明相和安金槐前往郑州调查[17]。1951年春,夏鼐率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调查发掘团再次对二里岗进行考古调查,确认是殷代的遗址[18]。经中央、省、市文化部门的文物机构和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数次调查,证明郑州市地下文物埋藏是重要而丰富的,于是,在1951年5月,成立了郑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该地区的文物保护工作[19]。后来,韩维周也被调入文物部门工作。
对二里岗遗址的正式发掘,始于1952年秋季,当年10月21日至11月25日,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合办的第一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71名学员被分作两组,在郭宝钧、安志敏等指导下进行田野发掘实习,在二里岗大道与陇海马路东段交汇区域开探沟四条,共发掘294.25平方米,清理各时期墓葬5座、龙山文化灰坑3个以及商代灰坑1个,获得陶片等遗物45箱[20]。
1953年1月,为了配合郑州市大规模工程建设,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特派裴文中来河南,组织河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裴明相、张建中、董祥等和郑州市文教局文物干部组成文物发掘组,在二里岗大道以东、陇海马路东段南北即黄河水利委员会建筑区内进行发掘,自1月20日开始,持续至1954年夏,共开探沟55条,发掘商代灰坑24个、商代墓葬3座、战国墓葬212座、汉代及其以后的墓葬20余座[21]。1953年10月,第二届全国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又在二里岗做了一次实习发掘[22]。1954年夏,河南省文化局第二届文物工作人员训练班也曾在此发掘部分战国墓。1954年4月6日,二里岗发现了两座汉画像砖墓,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于6月23至24日进行了清理[23]。
由于郑州市建设工程文物保护工作任务繁重,1954年10月,文物主管部门将郑州市文物工作组改组为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并调华东文物工作队20余人支援[]。当年11月中旬至1955年4月,该队为了配合市政建设,在时令小河以东、二里岗大道和陇海马路交叉点区域进行重点发掘,开10米见方或以上探坑15个,发掘面积1445平方米,发现龙山文化和商文化堆积,共清理灰坑70个、墓葬132座,发现陶片等遗物152583件又16包[25]。
至此,二里岗遗址的发掘基本告一段落。自1952年秋至1955年春,经过数年连续发掘,发现了多个历史时期的遗存,其中,尤以商代早期遗存最为丰富、最为重要,对于了解郑州地区商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三、究竟是二里冈,还是二里岗?
1953年5月,《新史学通讯》第6期出版,刊载了赵全嘏《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一文,这是二里岗遗址发掘和研究成果见诸学术刊物的开端。通过检索中国知网,1953年共有4篇文章涉及到二里岗遗址[26],此外,还有2篇文章谈到在二里岗的工程建设[27],以上6篇文章,均使用二里岗的写法。到了1954年,共有15篇文章的内容涉及二里岗遗址,其中,13篇文章写作二里岗,2篇文章写作二里冈,一篇是安志敏的《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另外一篇是王仲殊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从此以后,学术界就出现了二里岗和二里冈两种写法并行,却又相安无事的学术怪象。1959年8月,二里岗遗址的考古资料经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整理,以《郑州二里冈》为名由科学出版社出版,书名、版权页均写作二里冈,可正文中又写作二里岗,更让人有些无所适从。纵观20世纪50、60年代,使用二里冈写法的尽管只是个别学者,如安志敏、王仲殊、邹衡、安金槐、史念海等[28],但他们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可想而知。故自70年代以后,使用二里冈写法的文章逐渐增多,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直到今天,在相关研究论著中,二里岗的写法虽然仍是主流,但写成二里冈的也着实不少。以2020年度发表学术论文为例,我们分别以二里岗和二里冈为关键词,利用中国知网进行全文检索,经统计,采用二里岗写法的文章有308篇,而使用二里冈写法的也有100篇。
我们分析认为,安志敏、邹衡等前辈学者之所以提出并坚持使用二里冈的写法,是因为《郑州志》《郑县志》均写作二里冈,他们显然受到了地方史志文献记载的影响。安志敏在《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文末的图2郑州附近新石器时代及殷代遗址分布图中标示出了二里岗村,同文使用二里冈和二里岗村的不同写法[29],这一点与《郑县志》如出一辙。再加之,《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等又认为,当山脊义项时,岗是冈的俗字,他们写成二里冈也就不难理解了。但在二里岗遗址发掘前后的20世纪50年代,二里岗已是郑州当地普遍的写法。
四、结语
考古遗址的命名,惯例是以遗址所在的小地名来命名,因此,学界对以二里岗来命名遗址并无争议,分歧的焦点在于二里岗的写法。
上文已经指出,从二里冈到二里岗,地名书写用字发生过历史变迁,二里冈是清代、民国前期等历史时期的写法,而遗址发掘前后至今,则写作二里岗。具体就二里岗遗址而言,遗址名称的写法自然要跟发掘之时一致,而不能遵从历史时期的写法。因此,二里冈的写法是错误的,二里岗才是正确的写法,以二里岗命名的遗址、考古学文化就应该是二里岗遗址、二里岗文化。
注释:
[1] 赵全嘏等:《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
[2] 郑州市文物工作组:《郑州市人民公园第二十五号商代墓葬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12期。
[3] a.余谷:《二里岗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第1期。b.张昌平:《郑州二里冈文化陶器分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资料室。
[4] 许宏:《咬不清的文,嚼不清的字:究竟是二里冈还是二里岗?》,@考古人许宏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29cae10100hm82.html
[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6] 张钺:《郑州志》,第10页,乾隆十三年(1748)刊本。
[7] 梅膺祚:《字汇·寅集》,万历四十三年刻本。
[8] 陆费逵等:《中华大字典·丑集》,第178页,中华书局,1915年。
[9] 刘瑞璘:《郑县志》,第200页,成文出版社,1968年。
[10] 安志敏:《一九五二年秋季郑州二里冈发掘记》,《考古学报》1954年第2期。
[11] 管城回族区史志编纂委员会编:《管城回族区志》,第41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3年。
[12] 王锐夫:《黄河工程队在二里岗建筑工程中超额完成计划》,《新黄河》1953年第12期。
[13] 新华辞书社编:《新华字典》,第226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54年第1版。
[14] 徐玲:《河南古迹研究会与河南博物馆》,《中原文物》2007年第6期。
[15] 孙庆伟:《追迹三代》,第274页注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6] 相关资料见于“中研院史语所”的考古数位典藏资料库。
[17] 赵全嘏:《河南几个新石器时代遗址报导》,《新史学通讯》1951年第1期。
[18] 同[3]a。
[19]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1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0] 同[10],第65-69页。
[21] a.赵全嘏:《郑州二里岗的考古发现》,《新史学通讯》,1953年第6期。b.安金槐:《一年来郑州市的文物调查发掘工作》,《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5期。c.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6、44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22] 王仲殊:《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考古学报》第8册,1954年12月。
[2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岗汉画像空心砖墓》,《考古》1963年第11期。
[24] 尹焕章:《八个月来的郑州文物工作概况》,《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9期。
[2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第5文物区第1小区发掘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5期。
[26] a.新华社:《郑州、洛阳市郊发掘出殷商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科学通报》1953年7月号;b.同[21]a;c.编辑部:《河南省郑州、洛阳市郊发掘出大批古物 有殷商时代的“习刻字骨”和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7期;d.编辑部:《河南郑州二里岗又发掘出“俯身葬”人骨两具和有凿痕龟甲一片》,《文物参考资料》1953年第10期。
[27] a.弓长:《黄河郑州建房工地为国家增产节约二十三亿元》,《新黄河》1953年第11期;b.王锐夫:《黄河工程队在二里岗建筑工程中超额完成计划》,《新黄河》1953年第12期。
[28] a.安金槐:《郑州市古遗址、墓葬的重要发现》,《考古通讯》1955年第3期;b.邹衡:《试论郑州新发现的殷商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c.史念海:《石器时代人们的居地及其聚落分布》,《人文杂志》1959年第3期。
[29] 同[10]。
作者:吴伟 杜娟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李思雨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0003
- 0000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