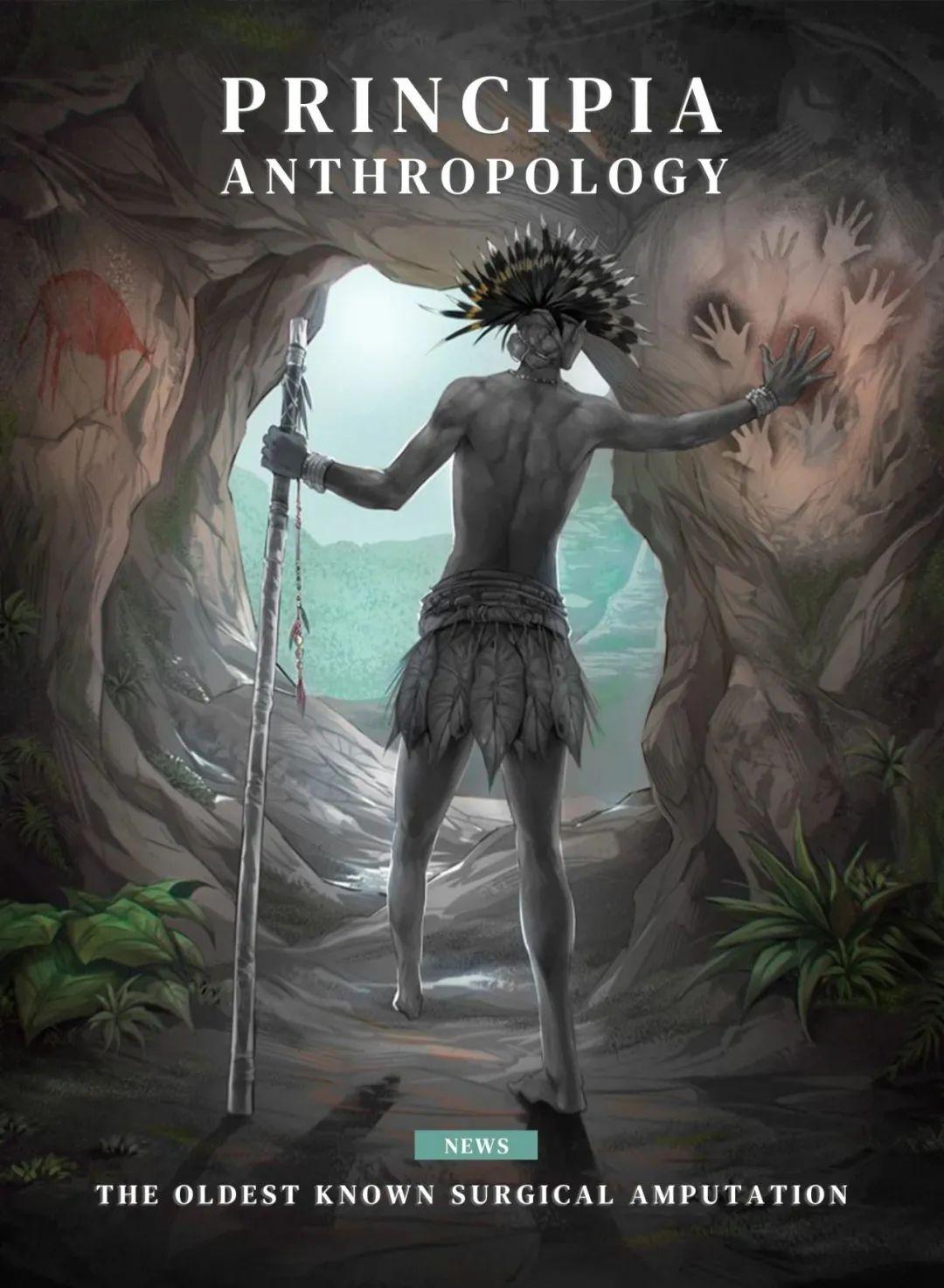日本考古学的三重面相:人类学、文化编年、社会重建
日本现代考古学的诞生一般以美国人莫斯(E·S·Morse)于1877年9月至10月对位于东京都品川区大井6丁目的大森贝塚的发掘为标志。当时的日本学术界很快接受了从西方传来的“三期说”,并将大森贝塚置于石器时代,认为其属于当时分布于北海道地区的原住民阿伊努人的先人所留下的遗存。
十九世纪末期正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处于天皇制绝对主义国家的成立时期的日本为了与欧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进行抗衡,利用了国家主义的思想,自由民权运动受到挫折。这一现实反映在日本考古学上就是当时著名的コロボックル(Korobokuru)·阿伊努争论。学者白井光太郎认为北海道发现的绳文时代遗存属于阿伊努人所留下的遗存,而坪井正五郎则认为这些遗存属于阿伊努人传说中的先民コロボックル(Korobokuru)人群所留下的遗存。将考古遗存与特定民族联系起来是当时通行做法。例如鸟居龙藏就曾将绳文时代的陶器分为“厚手式”和“薄手式”,并认为其分别是古代山岳民族和古代海滨民族所使用的陶器。然而实际上所谓的“厚手式”陶器对应绳文时代中期的陶器,“薄手式”陶器对应绳文时代后期的陶器,二者之间的差别属于时代差别。
客观来看,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考古学研究需要依赖人类学的视角,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对于遗存的年代判断缺少有效方法。因此横向跨文化的类比就成为判断考古遗存性质的主要途径。随着坪井正五郎于1913年去世,这一学术争论逐渐沉寂。不论是争论的哪一方,都认为《日本书纪》《古事记》的记载是正确的,即优秀的天孙民族取代了劣等的石器时代的原住民,这也是在当时天皇拥有神性和绝对权威下最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认识。
日本考古学界第一次转型的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从英国伦敦大学学成归国的滨田耕作于归国后第二年的1917年6月发掘了国府遗址(位于大阪府藤井寺市国府),根据这次发掘,滨田耕作获得了绳文陶器出土于下层层位,弥生陶器出土于其上的层位的层位关系。滨田耕作据此推断绳文陶器和弥生陶器主要是时代差别,而并不能将其对应为原住民和天孙民族。此外,滨田耕作还翻译引进了蒙特留斯的《先史考古学的方法论》一书,引入了类型学的研究方法。另一项标志性事件是松本彦七郎通过将古生物学的“地层层累的法则”和“标准化石的概念”应用于考古学中,并于1918年发掘了宫城县宫户岛里滨贝塚遗址,获得了该地区六期的文化编年。这两件事件标志着日本考古学向实证的文化编年研究的转向。
1928年9月,山内清男发掘了位于千叶县的上本乡贝塚,依据遗址的层位关系区分了绳文陶器的不同型式,确立了关东地区的陶器型式的年代序列为“一、夹杂纤维的陶器型式,二、不夹杂纤维的诸矶式,三、胜坂或阿玉台,四、加曾利E,五、堀之内,六、加曾利B,七、安行”。1935年,专注于弥生时代研究的小林行雄继承了森本六尔的弥生陶器拥有煮沸、储藏两种样式要素单位的说法,提出存在煮沸、供献、储藏三种形态的样式要素,并认为弥生陶器的这些样式要素一同成长、一同持续、一同变化。小林行雄的样式论超出了简单的陶器分类研究,有着复原古代生活的意味。
样式论即同时存在的一群器物是小林行雄建立弥生文化陶器编年的基础。小林行雄于之后的1937年1月与永末雅雄一同发掘了唐古遗址(奈良县矶城郡田原本町),并依据这批材料建立了详细的畿内地区的弥生陶器编年。
由于绳文时代遗址拥有丰富的层位关系且陶器形制多为筒形罐,因此山内清男的文化编年研究方法主要源自松本彦七郎;而研究弥生时代陶器编年的小林行雄则更加关注“组合关系”即他所谓的“样式”,其研究方法直接来自滨田耕作并最终来自蒙特留斯。
实证的文化编年研究阶段最大的成果是山内清男于1937年正式发表了绳文陶器的全国编年(早期、前期、中期、后期、晚期)。1938年,森本六尔和小林行雄完成了从九州到北关东的十三个区域的弥生陶器的编年,并在《弥生式土器聚成图录》中发表。
日本考古学第二次转型是以1947年开始的登呂遗址(静冈市石田)的发掘为标志,通过对包括水田和村落的农耕文化聚落的全揭露来试图进行社会重建。以登呂遗址的发掘为契机,1948年成立了日本考古学协会。
1953年,随着椿井大塚山古坟的发掘,大量的同范镜(使用同一个范铸造的一批铜镜)出土。通过对各地出土的同范镜进行综合分析,小林行雄根据传世镜的埋葬和同范镜的分配,提出了存在古坟时代大和政权对地方首长的支配关系的说法,这一研究通过将考古材料作为具体的史料,向着探究古坟时代的政治的、阶级的关系迈出了一步,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随着1960年代以来在日本各地开展的大规模建设,各地开展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考古材料大为丰富。
同时,这一时期也以科学技术手段的大规模引入为标志。1959年,神奈川县横须贺市夏岛町夏岛贝塚的绳文时代早期的层位采集的碳十四数据正式发表,其年代为9450±400 B.P.。芹泽长介积极使用碳十四数据,认为绳文时代开始于约一万年前,而山内清男则通过遗物的比较年代学的方法将绳文时代的开始定于3000 B.C.(之后又改为2500 B.C.)。1969年,铃木正男使用径迹裂变法研究黑曜石的原产地。1973年,小池裕子引入了对贝壳成长线的分析来确定贝壳采集季节的方法。同样是在1973年,春成秀尔对绳文时代的拔齿习俗进行研究,认为绳文时代即已存在族外婚,东日本由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变。从此以后,日本考古学界对于古代亲族关系问题也开始有所关注。
日本考古学的第二次转型一直持续到了今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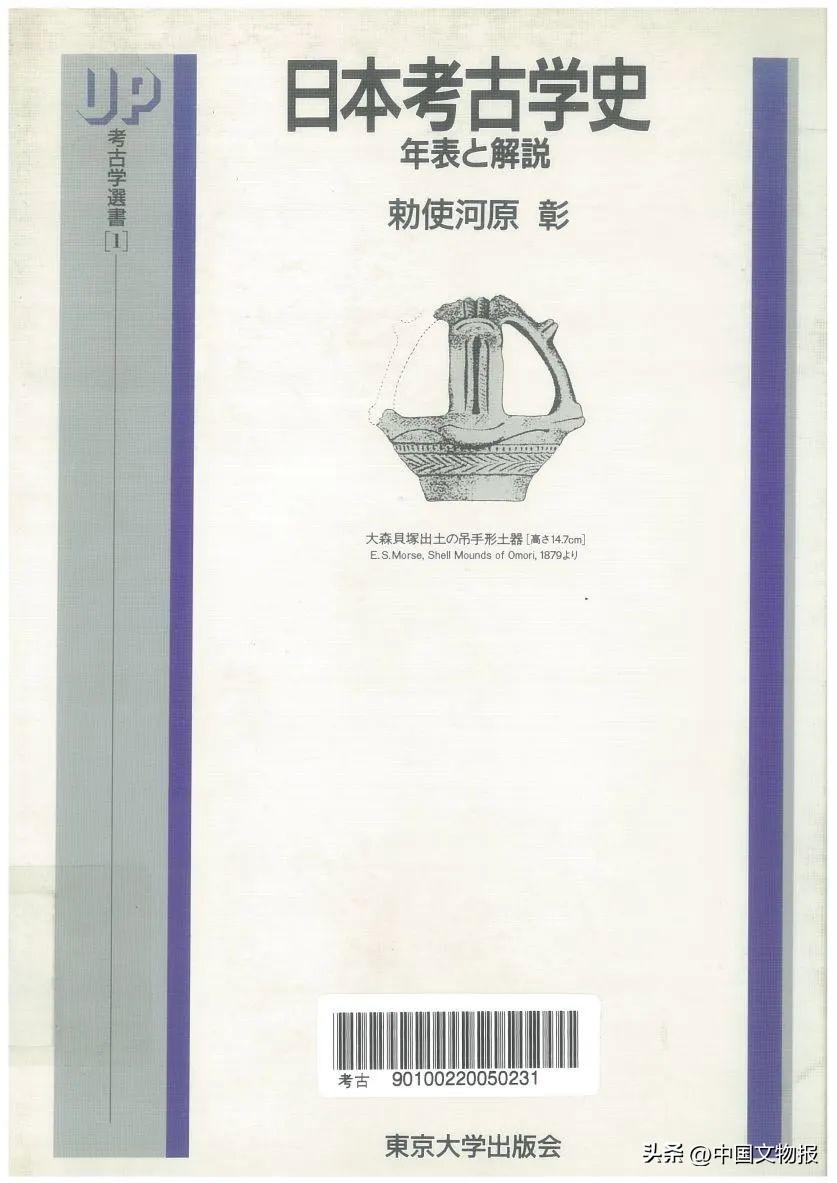
《日本考古学史:年表と解説》
作者:勅使河原彰
出版社:东京大学出版会
出版时间:1988年
售价:1800日元
从勅使河原彰的《日本考古学史:年表と解説》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考古学的三重面相,即人类学、文化编年和社会重建。三重面相并非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方法和研究取向的引入解决了旧的问题,却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明治时代缺乏年代学研究方法,仅仅通过器物之间的类比来进行研究的路径不禁让中国学者想起了安特生的“六期说”以及“仰韶文化西来说”。也可以理解传播论在世界范围内的盛行也与部分地区建立了年代序列而其他地区考古工作开展较少有关系。文化编年研究的路径在日本学界分为两条,一条是以蒙特留斯的类型学方法论为指导的道路,另一条是源自古生物学的以“标准化石”概念为指导的道路。社会重建伴随着大规模考古发掘活动以及学界对于亲族关系、社会分层、社会组织、国家形成的兴趣而产生。
学者的学术背景、科学技术的发展、新的考古发现,这些都会对考古学研究的转型产生影响。考古学研究的转型并不是对过往的研究路径的彻底抛弃,而更接近于“重复书写”(Palimpsest,原意是反复在羊皮纸上进行书写,这里用palimpsest形容对同一批考古材料进行多角度研究),用相应的方法去解决对应的问题,同时要为未知的方法保留空间,意识到研究方法和研究路径的局限性。
对于1988年的勅使河原彰而言,考古学不仅仅是“通过对过去残存下来的遗迹、遗物进行研究以明确过去人类的文化与生活的实际情况”这样的定义,而应该是考古学作为历史学“为了现在以及将来的民族以及人类的最大多数的幸福的实现给予思想上的引导”。需要在一个世纪以来日本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批判性继承的基础上,对古代形成科学、体系性的历史叙述。在某种意义上,对于日本考古学史的了解,也将会为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提供借鉴。
作者:宋殷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本文刊登于《中国文物报》5月5日第6版
编辑 | 张小筑 实习编辑 | 杨晓雅
复审 | 冯朝晖
监制 | 李 让
本号刊载的作品(含标题及编辑所加的版式设计、文字图形等),未经中国文物报社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改编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授权转载的请注明来源及作者。
- 0002
- 0001
- 0004
- 0003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