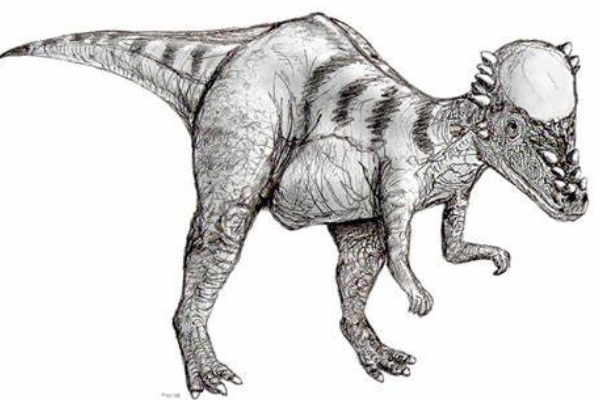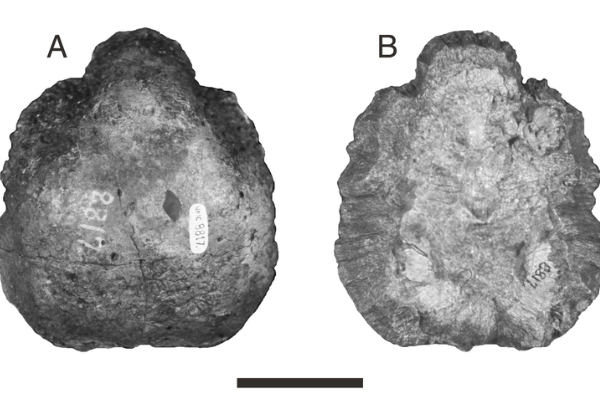孙慧琴:大禹治水及其考古学观察——兼论夏的王朝叙事
大禹治水的传说是见于史籍记载的我国古代国家肇始阶段最重要的政治和历史传说。虽然《尚书》《诗经》《孟子》《墨子》《国语》等先秦文献对大禹治水细节的描述互有抵牾,事件本身的真伪在古史辨学者、专治古史的学者与考古学者之中也有不同的观点,但它确实存在于周人的典籍之中,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历史政治遗产。由夏开始,传统文献开启了朝代循环和天命变化的王朝叙述。从故事本身来说,大禹治水至夏朝建立是一个各种元素都相当完整的王朝叙事,然而很明显,这个故事被极大地历史化、政治化了,治水—王权这一联结究竟是顺承的因果关系还是后人的追溯?是夏朝的政治实践奠定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基础,还是文献形成之际权力对此前的传统进行了精心的改造?一场浩瀚的洪水真正存在过吗?禹究竟是谁的记忆?他真正躬耕于历山、领导过治水吗?
笔者认为,要辨清这些问题,就要将这个故事中真正的历史记忆和意识形态因素区分开来,综合利用神话学、考古学、环境学等研究成果,对相当于夏朝早期的龙山时代晚期、传说密集发生的重点区域进行环境和社会变迁的考察。同时,文本分析也十分重要,顾颉刚先生“古史是层累的造成的”这一思想仍有绝对的指导作用。
就方法论而言,基于物质材料的考古学研究与基于文字记载的文献研究在本质上是客观对等的,是探索古代历史的另一条路径。考古学研究有着独立于文献之外的推演逻辑,即便在完全没有传世文字记载的情况下,也可以自成体系地提供关于古代历史的多方面信息,甚至可以进一步成为检视文献文本的参照物。但事实上在早年间关于夏朝建立的考古学研究中却充斥着文献 考古材料的简单对应,如:在没有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宣称某考古学文化即为“夏族”之文化;不进行文献置信度考量,就直接将考古发现与古史传说相比照,讨论鲧禹治水的发生地、某处洪水为禹治之水等。
在笔者看来,这是把考古学当作文献的附庸,也是对现代考古学作用的低估。没有对早期人类历史和记忆生成特点的掌握,没有对传说文本进行形成过程的分析,就无法对传说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前述研究也是对古史辨思想的一种放弃。为避免这种倾向,本文拟从考古发现和文献传说两条线索出发,针对禹的传说、洪水记忆、治水与王权等问题展开分析,梳理大禹治水传说的产生及流传过程,阐释治水与夏王朝建立之间的关系。
一、禹的传说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较早见于《商颂》的《长发》篇和《尚书》的《尧典》《洪范》《禹贡》篇等先秦文献中,其中《禹贡》篇的记载最为详细。关于《禹贡》的成书年代①,学者们有多种观点,主要包括禹时成书(以司马迁、孔颖达为代表)、西周初年成书(以王国维、徐旭生、辛树帜为代表)、春秋时期成书(以梁启超、白鸟库吉、金景芳、吕绍刚为代表)和战国时期成书(以顾颉刚、史念海、刘起 为代表)四种说法,以战国说影响最大。在主张战国说的学者中,刘起 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他强调古代文籍往往不是成于一时一人之手,而是经过了一个较长的流传时期,由前后不同时期的人递补而成。
邵望平先生曾结合考古发现对禹贡九州的地望进行了细致的考证,认为九州是长江、黄河流域在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形成的自然地理区系,因此禹贡九州不是依战国诸雄分野而托古假设出来的,而是战国诸雄分野的历史前提和依据。李旻先生更是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可能为战国诸子托古新编而成,因为若要全盘伪造,就必须重新建立一整套地理历史坐标,而身处百家争鸣时代的诸子,明显用的是同一套关于“天下”的坐标系统,因而大禹的传说必定是承袭于前的。笔者认同邵望平先生和李旻先生的观点,认为大禹治水应有战国以前的故事蓝本。
考古学证据也为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具体表现在出土文献和青铜器铭文两个方面。上博简《荣成氏》是战国中期人们记载的较为系统的上古帝王传说。据该文献记载,在尧舜之前有荣成氏等多位帝王,皆授贤而不授子,然自禹而始的三代以下,有启攻益、汤伐桀、武图商,则禅让之说废而革命之说起。该文献还记载了“舜听政三年,山陵不序,水潦不湝,乃立禹以为司工”的事迹,表明在战国中期以前,人们就已将大禹治水故事与夏王朝的建立联系起来,治水传说的政治化过程发生在此之前。西周、春秋的青铜器铭文中也直接提到了禹,如早年发现的叔弓镈、秦公簋,2002 年保利博物馆收藏的遂公 ,以及2019年湖北枣树林墓地发现的嬭加编钟等。
叔弓镈铭文中有“咸有九州,处禹之堵”,秦公簋铭文中有“受天命鼏宅禹迹”,表明“至少在春秋之世,东西两大国无不信禹为古之帝王,且先汤而有天下也”。嬭加编钟上“帅禹之堵”的记载则说明春秋中晚期时南方地区也存在“禹迹”之说。最令人振奋的发现是遂公 ,该器铭文开篇为“天命禹敷土,随山睿川”,与《禹贡》开篇“禹敷土,随山刊木”的记载惊人地相似,进一步表明在西周中期“禹的传说无疑已经是相当古老的被人们当作历史的一个传说了”。
综合上述铭文资料和出土文献,笔者认为如今广为人知的大禹治水故事很有可能是来源于西周人的追记,故事的主干内容——“帝”或“天”命禹治理水患并获得成功,应有更早的母本。周人承袭了先前的高地龙山系统,而禹的记忆是这一系统中的重要内容,故禹的传说很可能是来自龙山时代真实的自然环境背景。然而,治水故事虽是来源于较古老的传说,但其有自身的演化路径,在流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上了不同时代的历史色彩。正如顾颉刚先生所指出的,至少在商代就有禹的传说,从《诗经》到《论语》及战国诸子文献,禹由一个独立的传说人物渐渐与尧舜产生关系,最终与夏联系起来成为一代开国君主。
既然传说并非伪造,那么大禹治水确有其事吗?很多学者直接讨论禹如何治水以及治水的范围,这些研究事实上默认了一个前提,即禹为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这不亚于在神话学框架下谈历史问题,混杂了传说的“史实素地”和“神话编码”,是不可取的。禹是人还是神,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许多学者从考古材料出发,认为“登封王城岗应即禹都阳城”,“禹所治之洪水不出豫东、鲁西地区”,这是以推测去证实推测,可能会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牵扯到某地地望、族群与考古学遗存的对应问题,在方法论上总不能令人满意。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必要借鉴神话学以及古史辨派的文献分析法。
针对禹的神性问题,顾颉刚先生最先指出禹本为山川之神,后变为灶神。他认为“禹之是否实有其人,我们已无从知道。就现存的最早的材料看,禹确是一个富于神性的人,他的故事也因各地的崇奉而传布得很远”。这一结论目前仍不可轻易推翻。根据顾氏的研究,周人对禹的认识可归纳为以下四条:1. 禹平水土是受到了上帝的任命;2.禹的“迹”是很广的;3.禹的功绩是“敷土”“甸山”“治水”;4.禹是一个耕稼的国王。除去第4条为《论语》中的后起之说外,其他3条均暗示了禹的天神性。顾氏确实抓住了上古时期先民的祖先和神灵观的特点,即祖先和神灵混杂并处,类似一些记忆碎片,在结构不变的情况下可进行拼合。禹不为商族、周族的祖先,却同时被商族、周族所称颂,其天神的属性非常明显。
另外,笔者认为,从神话学的角度来看,还可补充一点证据。根据艾兰先生的研究,有关夏的神话主题,是殷商神话中与其自身相关的神话的转换。殷商被视作与十日、鸟、扶桑、东方、天空以及生命相联系,而夏则与水生动物龙和龟、若木、西方、黄泉以及死亡相关,鲧、禹都是这一对偶关系中的组成部分,而对偶神话中的内容并不一定真实存在。此外,李旻先生的观点也颇具启发性,他认为禹迹范围广大且多发生于山川形胜之地,说明禹可能为人们所崇拜的山川之神,而《禹贡》可能是巫师表演禹步时所念的唱词。
综上,禹既是与山川水土有关的神,那么治水故事当然不可能真实发生,只能是商以前人们的记忆片段。那么这些记忆从何而来,能否在考古学上观察到其环境和社会背景呢?
二、洪水记忆
在讨论考古学现象之前,我们要先划定可供讨论的时间框架。文献中由禹治理成功的大洪水发生在夏朝建立之初,绝对年代在公元前 2100 年左右,但是考虑到作为一种记忆片段的洪水事件应发生在更早以前,与夏的关系很可能是后来才建立的,因此本文将讨论重点放在公元前 2100 年以前的龙山时代晚期。
环境证据显示,距今四千年前左右,东亚大陆,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经历了气候异动,局部地区降水变率增大,加之季风带滞留、黄河改道、异常天文现象等的影响,植被覆盖率降低,或多或少给黄河上游、下游以及长江流域带来了较为频繁的洪涝灾害甚至大规模洪水。水环境的变化必然对当时的人类活动产生影响,引发诸如人口锐减、迁徙,文化面貌倒退等社会现象。根据张弛先生对龙山—二里头时段文化变迁的观察,公元前2300年到前1500年共出现了两次“文化衰落”,以遗址数量和面积的减少为标志:
第一次是长江中游地区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到晚期的剧变及良渚文化的衰落,第二次是山东龙山文化早中期到晚期的剧变及岳石文化的衰落与河南东南部龙山文化晚期的普遍衰落,中原地区则显示出距离洛阳盆地越远文化越衰落的迹象。有学者认为长江中下游石家河、良渚文化的消亡或与水患有关,北方地区黄河上游齐家文化和黄河下游龙山文化的衰退可能也是同样的原因。而中原地区即靠近晋南和郑洛地区的文化,则因为地理环境上处于黄河中上游、文化上兼容并蓄以及治水成功等最终在环境变化的挑战中脱颖而出,孕育出中央王朝。这一思路看似顺理成章,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近些年来,石家河古城和良渚古城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对江汉平原史前聚落的三维重建表明,石家河等古城的环壕和城垣可能都属于水利设施,生活在江汉平原的史前先民自有一套控制水患的系统。良渚史前大型水利设施的发现更是震惊世人,良渚先民对一系列山体进行改造,在山谷的出口筑坝蓄水,使之具有防洪、运输、调水、灌溉等功能,显示出了良渚人先进的治水理念与高超的水利工程设计、组织、实施能力。
很明显,龙山时代晚期,长江流域的先民们在与自然的长期相处中,掌握了因地制宜治理水患的方法,史前大洪水中断了这些地区文化发展的说法显得不具有说服力。至于黄河下游地区,自龙山文化中晚期到岳石文化结束,一直处于文化衰落期,而洪水造成的影响不可能时间如此之久,范围如此之大。另外,洪水泛滥也并非全为负面影响,洪水携带的大量腐殖质本身有利于农业生产,在洪水结束后,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应有所恢复才是。
除此之外,长期被认为是夏朝活动中心的晋南、豫西一带的考古学现象明显与文献中的洪水事件对应不上。根据张莉对龙山到二里头时代黄河流域聚落和陶器传统的考古学观察,公元前 1900 年左右,黄河流域出现了以人口锐减为显著特征的大灾难,导致了大范围的社会崩溃,其发生在龙山到二里头时代的转折时期(亦即文献体系中的夏代前后期之交),而并非夏代初期。这一灾难既无法与洪水事件对应,也无法在文献中找到相关记载。
综上所述,以洪水来解释长江中下游、黄河下游的文化衰落证据并不充分。因此笔者倾向于认为,龙山时代晚期,由于气候变化,洪水可能在一些小区域内出现,但是大规模的洪水造成文化衰退和禹带领部族进行跨地域的洪水治理这一事件应该是不存在的。
三、治水与王权
钟敬文先生在讨论传说的性质时,认为部分传说可能确实存在过,但经过群体性的艺术加工后,已经失去了原貌。尤其是那种狭义的历史的形式——采用溯源的、说明的态度,并且联系到历史上的人物或当地存在的事物,则起到增加传说真实性的作用。由此笔者认为,大禹治水传说的史实素地可能来源于当时在社会上广泛流传的、对于洪水的恐惧,而禹、九州等细致入微的描述只是用来增加真实性的“障眼法”。大禹治水的神迹遍布九州,这或许是在自然灾害频发的环境背景下,龙山时代先民们对洪水灾变的一种宗教回应。那么,作为一种宗教崇拜对象的大禹,是如何与夏朝的王权扯上关系的呢?大禹治水的故事在夏的王朝叙事中究竟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传统文献给出了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符合人们思维逻辑的夏王朝创始故事:由上天派来的禹在治水成功后获得了空前的威望,最终成为夏王朝创始人。在这个叙事中,禹取得王位有两个关键的要素:一是顺应天命,二是有功有德。这两个要素的意识形态色彩颇为浓厚,与周王朝建立的逻辑非常相似,结合古史辨派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个叙事或许直接来源于周朝。
艾兰先生用以区分史料的方法在讨论此问题上很有启发性:属于信史的资料应当是没有服务于神话或意识形态目的的元素或细节。很明显,大禹治水似乎只是一个中性色彩的神话故事,而有功的大禹建立夏朝则是一则目的十分明确的政治寓言。更进一步讲,大禹治水的传说从龙山时代就流传了下来,商族也有着关于本民族兴起之前与自己呈敌对关系的夏族的传说,这个夏族或许真实存在,但是大禹成为夏朝始祖的过程,很可能是假周人之手。
这并不是说周朝史官意图给灭商、世袭寻找理论支持而擅自篡改了历史。对于周人来说,大禹治水和夏族的故事都是存在于“遥远的过去”,而在尧舜禹的传说中,禹是与夏的时代最为接近的人物,若要补足夏王朝首代圣王之名号,最合理的选择就是禹。从另一个方面讲,为了向被征服的商族人宣传灭商之合理性,传统文献的书写者需要遵循有功之人建功立业这个逻辑,将夏和禹联结起来也就并不奇怪了。
此外,笔者还想就治水和王权联结如此紧密的原因进行讨论。一方面,从周朝开始,朝代循环和天命变化的观念对人们的影响极深,纵贯了古代中国社会近三千年,以至于今天的我们似乎都不能轻易跳出这个强有力的联结。另一方面,参考世界其他文明的历史来看,古埃及王国的统治结构与治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索不达米亚的国家机构杰里科充当着保卫水源及建设供水基础设施的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卡尔·魏特夫首次系统论述了“治水社会理论”,即治水工程需要全国性的合作模式,需要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因此,治水社会产生了“专制主义”。
在魏氏学说中,大禹治水是中国治水社会开启的第一个阶段,这一学说在民国时期左派学者中颇有影响。柴尔德认为灌溉农业的出现导致了原始社会管理制度方面一次重大的革命,即为适应贸易和灌溉的需求,集权化的统治权力出现了。作为世界古代大河文明之一的古中国,对水的抗争、控制和利用催生了最早的王权,这种联结与上述理论暗合,让我们很难跳出大禹通过治水掌控公共权力,最终建立夏王朝这个“完美叙事”。
四、余 论
龙山到二里头时代是整个东亚世界体系改变的时期,也是传说故事集中发生的时期,伴随着气候异常,这一时期自然灾难频发,人群流动迅速,造就了社会的大震荡和大整合。大禹可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一种自然崇拜,体现了当时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
本文梳理了大禹治水传说的产生及流传过程,并提出禹凭借治水功绩建立夏朝的叙事可能是周人构建的。宽泛地讲,这一观点并未超出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者对于夏史和禹的看法。笔者认为,古史辨派围绕“传说的转变”搭建的开放式论证框架仍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其中的思维方式和治学精神应该得到更深层次的挖掘。在今天的考古学研究中,不仅应当呼唤质疑、批判精神的回归,也应反思那些令我们身陷其中的惯性思维。
本文改编自《大禹治水及其考古学观察——兼论夏的王朝叙事》,原文刊载于《文物春秋》2020年第2期。作者:孙慧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考古系。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