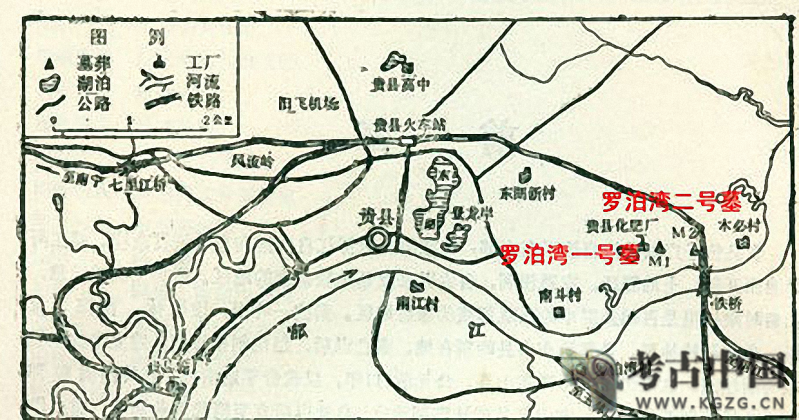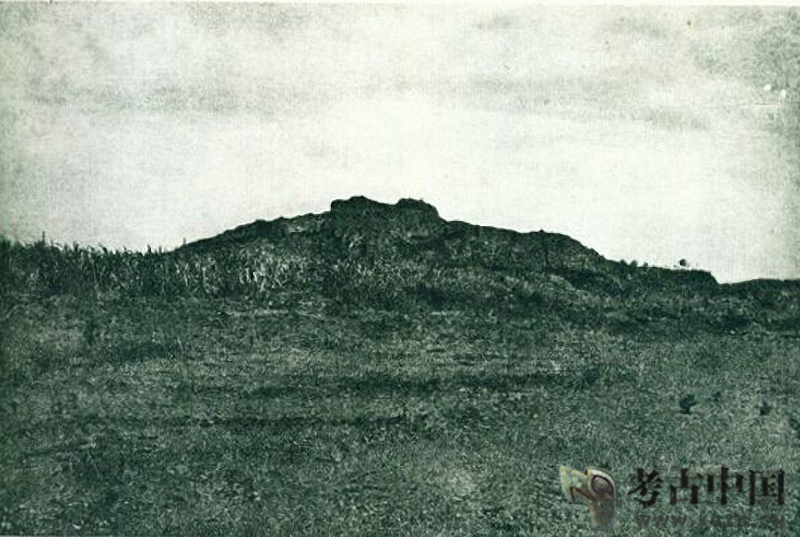雷戈:试论中国古代的史学政策
在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领域,人们的重心大都集中在史学思想和史学编篡方面,而对更具有决定性的史学政策则缺乏充分的认识。一般说,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集团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和总要求。史学政策不同于修史机构或史馆制度,后者只是一个作用有限的学术性的官僚实体,而前者则是一种更为广泛的兼具思想规定和权力约束的政治—学术模式。史学政策不仅体现在修史机构的设置和史馆制度的程序上,而且更多地表现在皇帝和历史学家二者既相互利用又相互猜忌的微妙关系和复杂心态中,它对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定向和史学文化的品格均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所以,研究史学政策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史学史的一个新视角、新维度,它鲜明地体现出政治与历史、权力与史学之间的二律背反。提出“史学政策”这个概念,就是试图从权力角度来对中国古代史学史进行一番新的批判学解读和价值学解构。其目的在于揭示出中国古代史学史所蕴含的极其深厚的权力内涵和极为广泛的政治意义。故而,我们的结论是: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本质特性就是它的政策性。在中国,历史学向来都是最富于政治性的科学。政治干涉对于历史学来说,不但算不上是一种例外,反而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自然现象,以致于历史学与政治似乎从来就是密不可分的统一体似的。
历史学与政治的这种特殊而又密切的关系,虽早就为历史学家注意到,但更进一步的深入论述尚不多见。实际上,历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一种矛盾的外层结构,其内层结构则是经学主义与现实政策的根本关系。所谓“经学主义”是指建立在“六经”基础上的历史思维模式。历史学通过自身的经学主义去沟通政治内部的政策,从而辩证地产生出一种更潜在的矛盾,即史学政策。史学政策不单纯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性产物,而且也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学术性表现。因此,史学政策的政治性就包含有与学术性同样普遍甚至更加普遍的必然性。史学政策本质上是历史学与政治的矛盾关系发展到一个更高阶段的成熟性标志。久而久之,史学政策就自然而然地演变成为历史学的实体本身,成为历史学家必不可少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
当史学政策以一种纯粹形式上的,并且不能给人以任何想象余地的,甚至使人无法作出任何比较的新历史学结构出现时,这就意味着历史学已经完全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了。而史学政策一旦作为历史学家的基本思维模式和心理定势时,就可靠地保证了历史学中绝对不可能产生哪怕是一种极其微弱的异端性思想萌芽,也就是说,历史学永远是一种正统的学术形式,是一种维护和肯定正统的存在,是正统本身。难怪在经史子集结构中,历史学始终属于最确定不移的权威性的学术道统或道统学术地位。历史学通过与政治建立起史学政策的隐结构,就具有自我封闭的强大循环机制,它可以完全不必依赖外界的任何新的批判性理论体系和历史观念而永恒地自我持存下去,并且这种历史学具有一种善于发觉其它异端思想的自我保护性功能。这种自我保护功能保证了历史学几千年的正统性学术地位。而史学政策则使历史学这种消灭异端的自我保护性功能内在为结构形式,使历史学形成一种必须依靠这种结构才能正常存在下去的本能需要。因此,历史学消灭异端,这不仅仅是它本身的自发性需要,而且还是它的自觉性追求。
没有任何一种科学比历史学更具有一种对异端思想的敏感性和恐惧性了,显然,历史学维护正统就不完全是为了作为纯粹他物的政治,而首先是为了自己存在的本质。毫无疑问,既然历史学的这种消灭异端的特异功能被史学政策用一种结构的形式彻底固定下来,这就造成了历史学必然成为所有最专制的、最虚伪的正统思想意识的大本营和大杂烩,以这种方式构成的史学史也就历史地成为不断地消灭异端的疯狂过程。历史学是黑暗时代的产物,本身也有黑暗的思维存在。这就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历史学一直是所有科学中最不能容忍自由思想的学科?为什么历史学竟有那么多如此保守的愚蠢传统?为什么在别的学科都早早地接受新思想新观念之后历史学还死死抱着正统信条不放?史学政策的可怕性在于,它用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隐结构形式把历史学变成了专制政治的学术载体,从史学政策的渠道里能源源不断地输送着黑暗政治的越来越专制的政策性指令信息。同时,又从这条渠道反馈出不计其数的越来越庸俗、越来越软弱无力的学术性宣传和欺骗。
中国古代历史上短暂统一的朝代,总有一番特别惊人的行动和创举。政治上和文化上尤其如此。秦废封建行郡县,焚书坑儒;隋废九品而行科举,禁止私人著史。如果说,汉代在肯定了秦政治制度的同时却否定了秦的文化措施的话,那么,唐之于隋则是既肯定了它的政治制度又肯定了它的史学政策。
隋文帝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下诏说:“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对于这样一条重要的诏令,许多研究者向来不予重视,只是作为禁止私著国史的法律性开端而泛泛提过。隋文帝有此诏令,并非是他本人不愿读史,其实,他自己倒颇喜欢阅读史书,留意典章。灭陈之后,任命史家姚察为秘书丞,继续著述“梁”、“陈”二史。文帝读史心切,竟让姚察作成一篇就马上呈送之。透过这条诏令,至少可以暗示出五层内容,也就是说,由这五个焦点构成了封建政治控制历史学的又一个更专制的新光环,它是封建史学政策一个转折性的标志,是专制政治性历史学家本来就已经没有多少自由并且日趋衰老和僵死的头脑上套上的又一个更加严密的紧箍咒。
第一:隋文帝自己的帝位来历并不光彩,私史四出,其隐情必然会被暴露出来;第二,史官、史家多是南方之士,许其作史,必有怀国思旧之心,如此则不免“借古人酒杯浇自己垒块”,以古薄今,流言纵横;第三,魏晋南北朝以来确立并且日益强化的史官制度和北齐大臣监修著史的先例,都给隋文帝的垄断国史提供了历史依据;第四,实行科举制度,如没有统一的国史,则众说绘纭,难以选择人才;第五,高丽、日本等国多遣使臣入朝,经常购求大批史书典籍,如果私史流行,则朝廷隐私恐皆为外国异邦知晓,中国天子尊严何由保证。
贯穿在里面的核心是皇帝对史学的性质和著作的认识有了深化,他更直接地把国史看作自己个人至多是本家族的历史。这种史学与其说是提供借鉴,勿宁说是表现一般。
六朝以来各种史学体裁大多具备,由于官府和历史学家的共同努力,到这一时期已经积累了大批的史料典籍,而当时却没有创造出一种比较先进的编篡方法,所以史料的大量堆积和政府的迫切需求之间就发生了冲突。私人著史一是材料缺乏,因为每一新朝建立,总是先把旧朝的政府书库里的典籍全部垄断过来,并诏令州县私家广献秘书珍本,许以布帛财产的赏赐和入仕做官的优越权利,这样,民间的史书就很有限了;二是政府史官修史,若单独经营,各自为战,则史料浩瀚,难以遍览,记事抵牾,不易考订,况且人非马、班,岂能传、志皆精?加之著作时间长久,其评述,其论点,也不一定皆吻合于皇帝的心思。与其由私人累年修改,倒不如让官府短时完成。这样,观点统一,效果显著。况且,皇帝满意,史官轻松,何乐而不为?对于集中于官府修史机构进行著作,史官们是没有什么异议的,因为自魏晋以来的几百年的史学历程,已使历史学家们养成了一种可怕的惰性,习惯于服从皇帝的指示,而不肯去理性地思考一些问题,提出一些包含有自己史学修养和历史见解的观点。如果说政治上,大臣们多少还保持着一些有限的自由权利,敢于向皇帝提出建议、批评,甚至面折廷争的话,那么,在史学上,史官们则从没有一个敢于把自己观点毫不隐晦地上呈皇帝,或如实地记载和描述当朝皇帝的登龙术和发家史的。尽管可以对皇帝的现在表示某些不满,但决不允许对皇帝的过去有丝毫批评,因为,现在只是现在,而过去已成为历史。
事实上,皇帝对史书作用的理解是愈来愈深刻的,这一点,在开国君主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他们是经过了一段可以被称作“历史”的人。比如,北魏的宣武帝就曾迫不急待地要求崔鸿把未作完的《十六国春秋》一部分半成品送给他看,隋文帝也是如此。我们不是指责这种皇帝个人的行动,只是批判这种皇帝个人所代表的专制政治。到了唐太宗,干脆把二十余家《晋书》全部废掉,并对南北朝史书进行改造、编篡。历史活动的剧烈程度决定了表面上起支配作用的统治集团对历史问题观察的广度和理解的深度,他们就依据这个标准来制订史学政策,规定史学任务和方向。同时每一个王朝的上层人物与一般学者对共同的历史的看法也都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而决没有本质的对立观点——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所谓异端历史学家。如果有分歧,那也只是在个别问题上和史学的具体手段上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每个新兴的王朝的要求不一样,而且是越来越专制,但史学家却很快能够适应这种环境,扩展这种环境。令人惊奇的是:他们还能在这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史学天地里很不错地生存下去,创造出新的作品。在这里,显然不能片面说皇帝喜欢专制,而史学家则不喜欢专制。事实上,在专制与否的看法上,皇帝与史学家往往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也就是说,二者都是在认真思考的,二者都在各自的领域内对历史和历史学的关系进行了深思熟虑的总结和反省。双方都共同趋向于专制的目标。当然,不可否认,皇帝与史学家的关系也会破裂,那只是因为专制的程度更强了一些,专制的要求过多了一些。但史学史的曲线向我们清晰地显示出,无论如何,史学专制的色彩是越来越浓厚了。
官府修史一般都有着相当严格的程序,史臣们分工修完史书,先经监修国史的宰相审查过关后,再奏请皇帝御览,不满意的重修,如此几个反复,一部史书才算正式定稿。唐太宗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雄才大略,在史学上也是如此,他对史学的认识无疑总结了前代所有皇帝制订史学政策的利弊得失。正由于他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本质有着敏感的把握,才导致他把皇帝对史学的垄断化正式法定下来,形成严格意义上的史学政策,并取得了骄傲的成功。隋朝虽有诏令禁止作史,但却没有一整套完善的修史机构,也没有举行过大型的修史活动,只对个别史书做过些微不足道的改作。唐高祖虽然正式下诏作史,但没有什么成绩,《旧唐书》说“(萧)瑀等受诏,历数年,竟不能就而罢。”(卷七十三)这主要是因为修史者多非史才,说明单有官方的政治优势,而没有第一流的历史学家的得力配合也是不行的。唐太宗接受了这个教训,选拔和重用令狐德棻和素有家学渊源的姚思廉和李百药。甚至他还亲自作了《晋书》的四篇史论:《宣帝纪》、《武帝纪》和《陆机传》、《王羲之传》,以表示自己对历史人物的见解和对史书作用的重视,实际上这已经开了清朝乾隆帝御批《通鉴》的先例。世界史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君主象中国古代的皇帝那样对历史学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和特殊的关心。同样地,也从来没有一个民族的历史学始终不谕地向着高度专制的国家政权表示出这般忠诚的爱情和赤裸裸的献身精神。这正是中国历史学的最光彩的优点,也是它最糟糕的缺点,既是它的本质,又是它的表象;也就是说,在中国史学发展的历程中,它生命赖以存在的精神秘密和表现形态完全吻合为一了。在这里,不存在有灵魂与肉体,本质与现象之间的差别,可以说,这种内在与外观合一的特征,既是中国古代史学异常发达的必要因素,同时更是它畸型、空虚、苍白的决定因素。这就意味着中国历史学的价值只能与其国家政治的命运相共存,永远是它的附属品,而丝毫不能脱离它的母体而先行一步。
唐代皇帝之所以对纪传体表示出热烈的兴趣,绝不只是因为它体例完备,包罗万象,足以反映一代风貌,而是认为纪传体在承认帝王将相为历史主体的前提下,更加鲜明地突出了皇帝个人的绝对权威。列传人物千差万别,形形色色,不管是平民,还是大臣;不管本朝,还是外国,全被置于列传之中,显示了他们在皇帝个人面前都具有平等的地位,也就是说,他们都是皇帝个人的直接臣民。在纪传休这种多层次的体裁中,皇帝个人在本纪中的独尊地位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一种存在,他的功德再小,也不能低于列传的最高标准;而列传人物的品行再高,也不能超过本纪的最低限度,本纪和列传使用的是两种语言和标准。在史学政策支配下的历史学,对语言的使用有着极为精确的讲究和规定,而本纪显然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史学语言形式。宋元以后,尽管编年体和通志体一度较为盛行,甚至在清朝时由于《资治通鉴》的巨大影响而将编年体也列为正史,但真正的正史仍然是纪传体,而不是编年体。清政府网罗众多史家名流用长达百年之久的时间精心修撰《明史》就充分说明这一点。需要指出,《明史》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官方编篡正史所经历时间最长的一部,当然也是官修史书质量最高的一部。《明史》编篡的过程是与清朝史学政策直接联系并不断适应的,因而,《明史》修撰本身就已经成为清朝史学政策的一个关键部分。比如对南明朝臣的态度,对明末建州卫的记述等,都极鲜明地体现了史学政策的核心要求。所以,《明史》的完成,也就标志着清朝史学政策的最后形成。而作为中国古代史学史上最后一部钦定的纪传体正史,《明史》的本纪性语言无疑也就最为生动和具体地反映了史学政策的特定内涵,并以此成为直接的史学政策本身。可以说,正史的本纪性语言正是史学政策的历史学形式和历史学存在。皇帝历史的虚伪性和现实的专制性都通过这种本纪性语言而冠冕堂皇地列入史学语言的最高等级和史书体例的最高层次。而正史的本纪性语言实乃历史的禁区和语言的禁忌。皇帝的历史就是禁区的同义词。皇帝的历史既一目了然地异常清楚,又神秘无比地极端模糊。皇帝通过本纪的语言公开自己的历史,也通过本纪的语言来封锁自己的历史。反正都是一回事。专制政治向历史学家宣布:最高权力者的历史从来不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而仅仅是史学政策的服务对象。而在绝对专制的国家里,一旦决定一切历史的最高统治者的历史成为历史学的天然禁区,那么,还有什么历史更值得研究呢?形式上仅有一个人的历史不能被研究,实质上,则是所有人的历史都不能被研究。表面上,所有的人都有自己的历史,本质上,只有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然而,正因为这一个人有自己的历史,才使得历史学家无法对他进行研究。这样,这个人的历史性就剥夺了历史学对它研究的可能性。这个人用自己一个人的历史去否定了所有人的历史,并且否定了所有人对自己历史提出怀疑的权利,也否定了历史学家对这种历史研究的权利。这种纯属个人的历史不但剥夺了他人的历史,而且也剥夺了历史学的历史。历史学家成为历史学王国的失业者。既然唯一有历史的人的历史不能被研究,那么,其它没有历史的人的历史又有什么必要和可能去研究呢?这样的话,历史禁区就失去了原有的含义,而变成无处不在的界限了。历史学没有可供研究的历史,它失去了对象。整个历史都对历史学封闭起来,全部历史都成为禁区。这正是对历史学无历史性的绝妙注释,历史学的无对象性和无历史性不能不成为同时丧失的辩证本质。因此,一个不值得惊奇的奇迹就是,在中国这个号称史学大国的国家历史中,竟然存在着如此众多的历史空白和史学禁区。一个无须论证的假设则是:中国史学史的超常发达正是以不可计数的史学禁区为其必然前提的。史学政策采取的方式基本有两种:一是在向历史学提供对象的同时也给历史学提供了正史的本纪性语言,告诉历史学家如何用这种本纪性语言去说明历史,去写作正史;二是既不向历史学提供对象,也不向历史学提供语言。对于前者,历史学家说了等于没说;对于后者,历史学家没说也等于说了。因为他无话可说,无话可说就是不用说,不敢说。对象性与历史性之于历史学,是互相依赖的悖论性关系。整体性的史学禁区的存在不但使历史学的研究成为问题,而且也使历史学的思考成为问题。即,历史学的不可能性恰恰存在于史学政策的可能性之中。更主要的是,史学政策与其说是直观的法律性规定,毋宁说是具体的权力性约束。史学政策通过史学史的普遍必然性而显示出自身的内在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也就是现实性,而且是不可改变的历史现实性。这种史学政策的可能性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可能,而是一种历史学意义上的现实。它给历史学家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种软宗教的温床,一方面史学政策允许历史学家去自由地研究一切历史;另一方面,史学政策同时又限制了历史学家无法去自由地思考一切历史。即,好象是什么都让历史学家去研究,但又什么都不让历史学家去独立地思考;它仿佛使历史学家看到了一切应该看到的东西,却又不许历史学家按照自己的方式和语言说出这些东西。这便必然造成了历史学家的精神分裂,他总是处于绝对自由和绝对不自由的双重挤压和肢解中。自由离他太近,又距他过远。无所适从感是伴随历史学家常有的现象。在史学政策的结构中,历史学家往往产生一种玩魔术的感觉,他在无所顾忌地玩弄着历史,可他又被史学政策更加随心所欲地玩弄着。于是,一种完全化的禁忌性思维就形成了,它迫使历史学家把毕生精力都花费到如何寻找那些难以捉摸但又不得不挖空心思地去捉摸着的禁忌性界限上面,因为这是历史学家存在的死亡线。禁忌性思维造成了历史学家先天性的恐惧感和不安全感,史学语言的分寸感是他们终生都难以熟练掌握的生命技巧。
历史已经过去,历史学也在成为历史。但史学史留给我们的沉重遗产还远未得到全面的清理和批判,无论是历史观还是史学观,在某种意义上,它都指向了史学政策这个内在的权力结构。它使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学的本质和精神的认识而言,史学政策乃是一个绝对必要的真实向度。
来源:《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