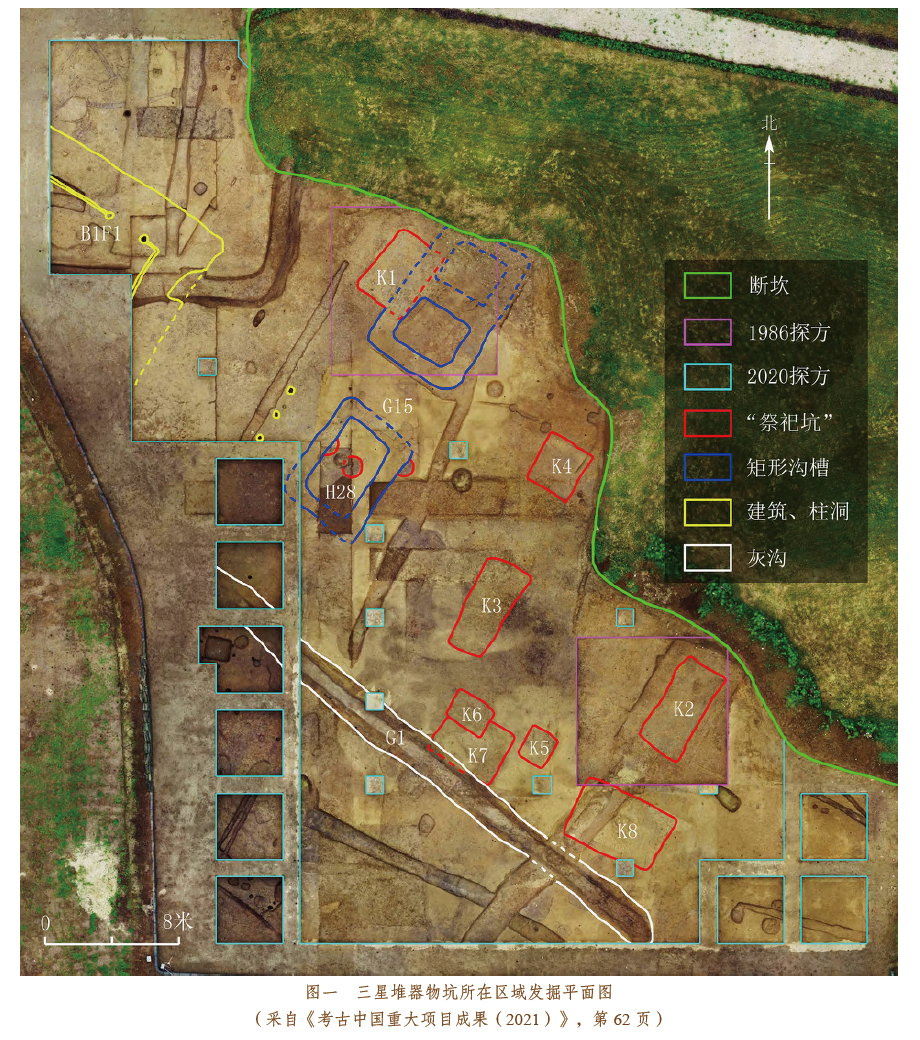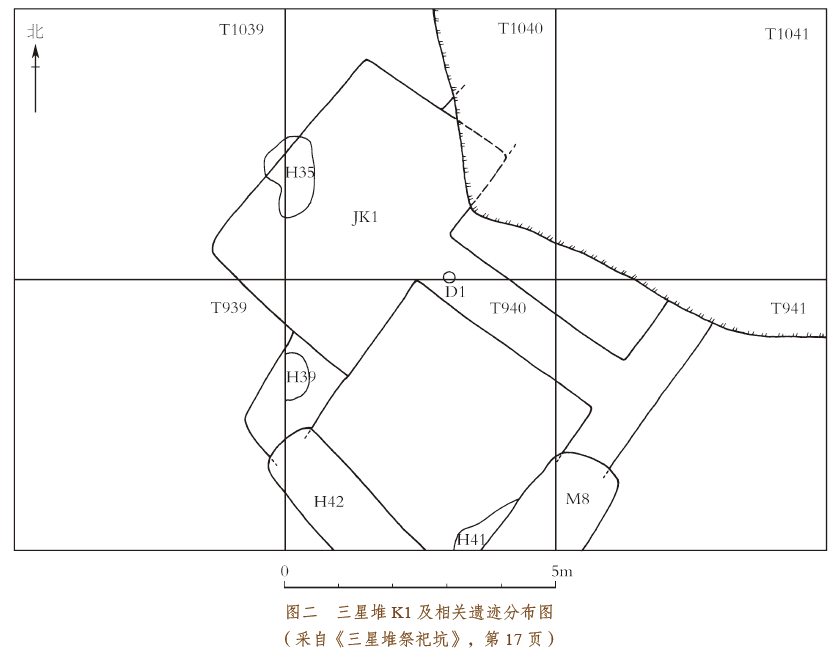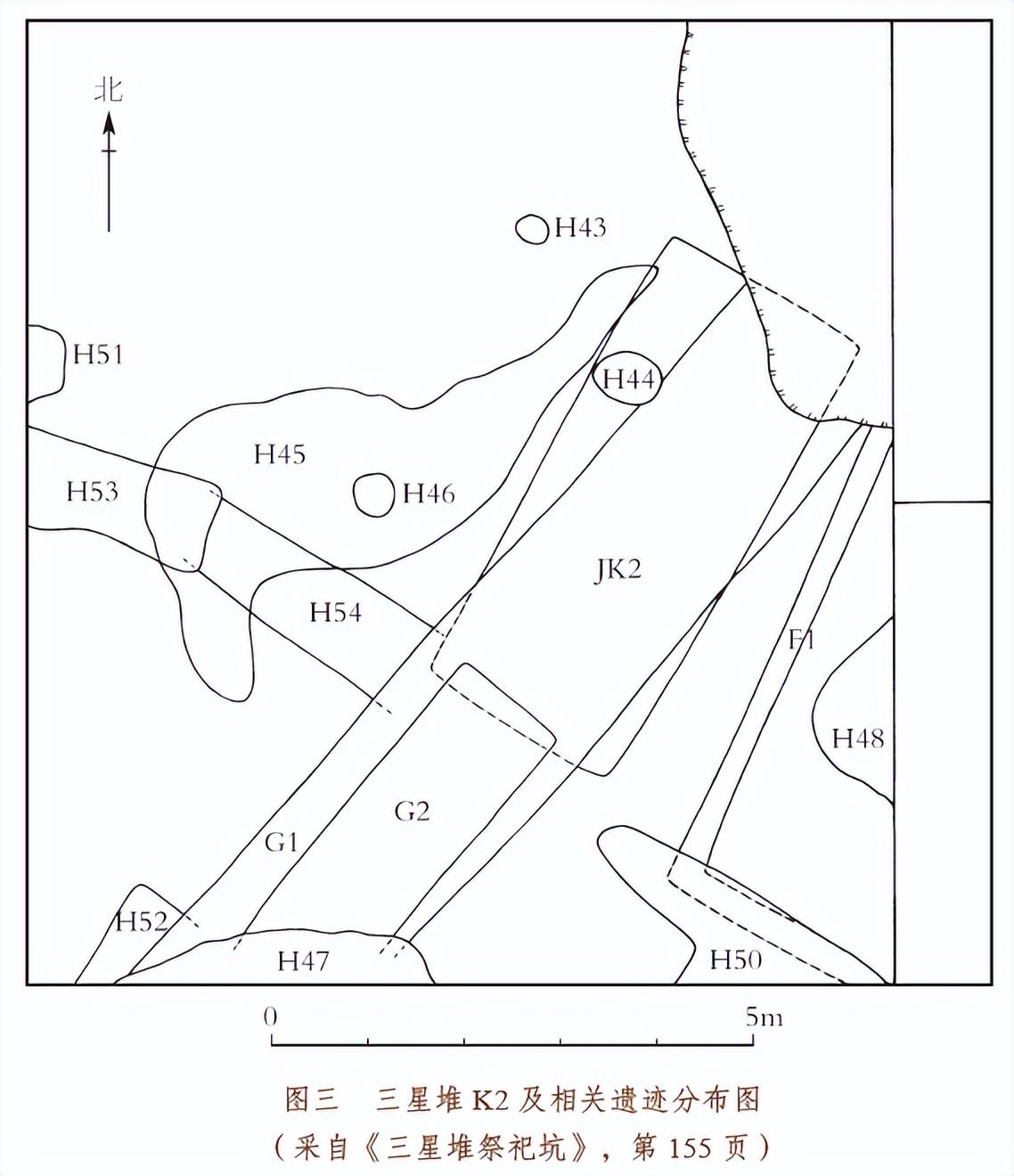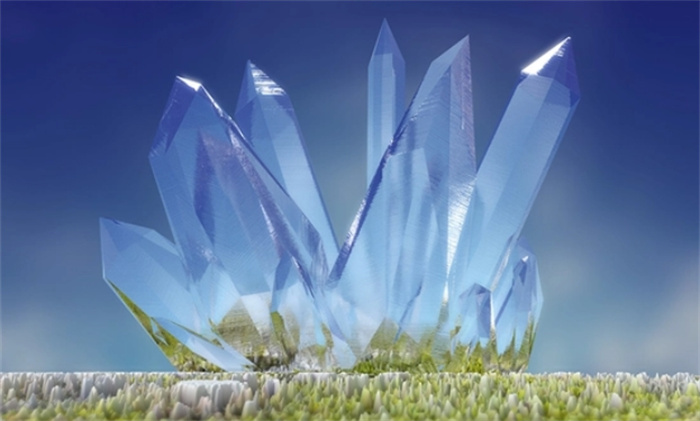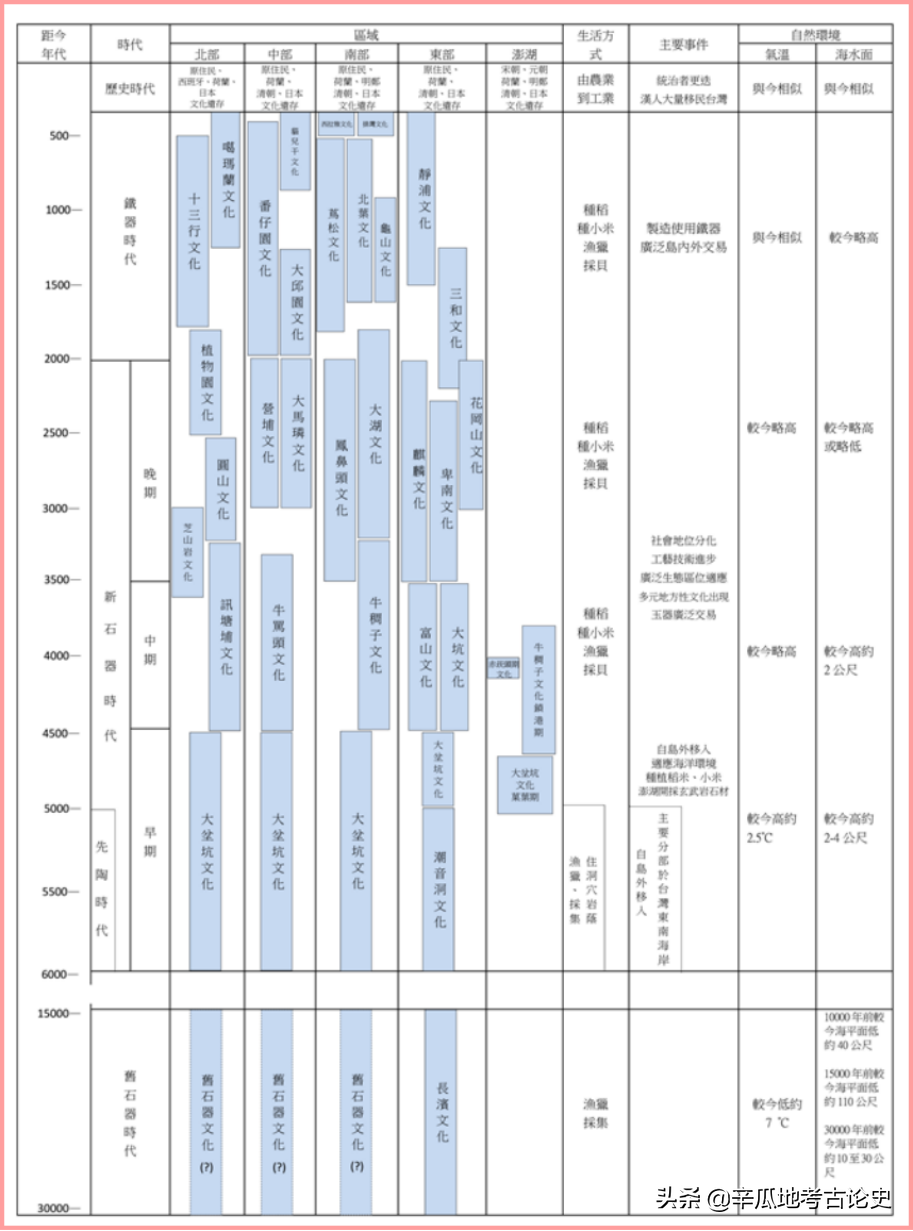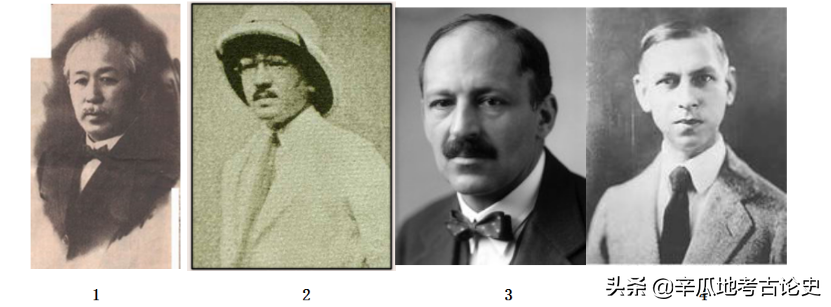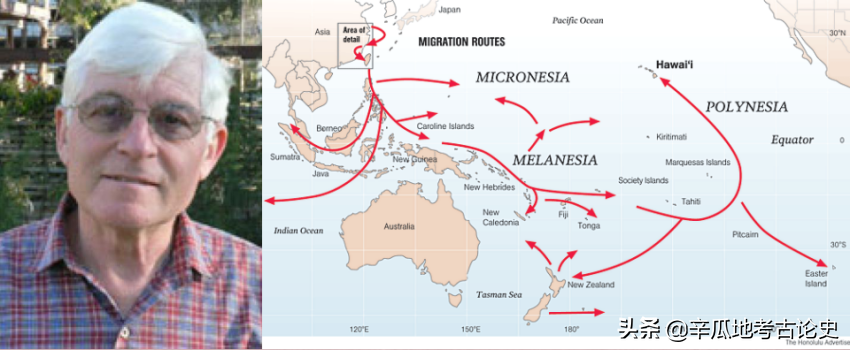雷戈:破碎的心镜——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分析
一般而言,心理障碍对于历史学家的影响往往是隐性的,但却又是持久的。它比认知层面和思维层面的局限性更隐蔽,但也更长久。所以,细致的心理分析对于历史学家同样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历史学家更明晰地洞察自己的能力和缺陷。它的意义在于,时至二十世纪末,我们迫切需要对历史学家作出更加全面和客观的认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心理分析则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种心理分析也可以使我们从另外一个迥然不同于知识层面和思维层面的角度去观察当代那些导致历史学家命运多舛和历史学危机重重的复杂机制与因素。
一、心灵原因
对中国当代史家来说,历史观向来是历史学的理论基础,这一基础地位向来也没有受到有力的挑战。这种对历史观功能的盲目崇拜与狂热迷信从五十年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历史观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被人为地从历史学体系中割裂出来,作为凌驾于历史学之上的一种理论权威。人们不加思索地相信历史观对历史学的绝对优先性和正确指导性。天真(可悲的天真)地相信有了“科学”的历史观就等于有了“科学”的历史学。于是,几乎所有史家都舍本求末地去追逐历史观而抛弃历史学。这样,一种近乎怪诞的现象便产生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不去研究历史,而在那里整天高喊历史观;他们不去研究真实的历史过程,却在那里颂经般地宣传历史观的只言片语,以致于,不知不觉地竟然用对历史观的肤浅宣传代替了对历史的深入研究,最后,进一步用历史观代替了历史学本身,甚至是代替了历史本身。
当然,从政治的角度看,这对普及和宣传唯物史观是有好处的,它可以起到强化人们使用唯物史观的自觉意识(但很难起到使人们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解的正面作用)。或者是东施效颦,或者是邯郸学步,其中的辛酸与笑料也许只有当事者才能略知一二。但至少在表面上,经过自上而下雷厉风行地推广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和常识,历史学家绝大多数都已百分之百地变成了唯物史观的忠实信奉者。他们坚决地拒斥和批驳其他一切历史观,异口同声地指责其他所有历史观都是“唯心的”、“不科学的”、“荒谬的”、“反动的”、“有害的”、甚至是“有罪的”。他们痛心疾首地控拆和声讨唯心史观对自己的“欺骗”、“污染”。他们要洗心革面,反戈一击。他们在历次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都争先恐后地表白自己已经从唯心史观转到唯物史观的立场上,同时还不失时机地抨击他人还没有真正完成这种历史观的革命性转变。他们幼稚地相信,历史就是政治,历史观就是政治态度,选择历史观就是选择政治立场,就是选择人生方向。他们把抽象玄虚的历史观同自己的具体实际的现实存在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唯物史观能决定自己的存在境遇和人生命运,认为信奉唯物史观就等于在生命的旅途中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和归宿。
就大多数人而言,他们接受唯物史观,并不是基于一种自由的理性批判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政治威胁和行政压力所致;并不是出于自己内心的思想需要,而是出于对自身的生存利益的考虑。这就决定了他们很难对唯物史观作出积极深刻的独立判断和思想分析,当然,他们更不可能对唯物史观和其他一切非唯物史观之间进行客观、公正的比较和评估。因而就必然导致了中国史家对唯物史观采取一种投机取巧的实用主义态度,盲目接受、机械运用、死搬教条、胡乱比附、浅尝辄止。历史学家不知不觉地放弃了对历史过程积极的理性探索精神,习惯成自然地丧失了历史批判的科学能力。历史学家变得僵化了、教条了、浅薄了、庸俗了。但由于他们还偏执地迷信历史观对历史研究的神奇效力和魔术功能,故而依旧沉溺于企图凭借历史观去全盘改造历史的幼想之中。
然而,历史观终于从高高在上的主宰地位退隐下来。历史观不再奢望去改变历史的发展方向,甚至也不再试图去干涉历史学家的研究过程。历史观退守到一个较为具体和有限的圈子里面,保持着自己的明确的要求和目的。这不但对历史观是一种解放,而且对历史学更是一种解放。历史学独立了。历史学不再是历史观的一部分,而成为与历史观平等的另外一种独立的理论知识体系。当然,历史观可能要深刻一些、普遍一些,但这并不能因此成为历史观就有权利去过多干涉历史学的真正理由。历史观可以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也可以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但它不能使人们迷信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历史的全部技巧似的,更不能使人们误认为懂得它就等于懂得了历史,研究它就等于研究历史,甚至它就是整个历史学。
历史观必须从无限性退回到有限性。因为它的权威地位正越来越明白无误地受到历史感的有力质疑和挑战。历史感显然是另外一种东西。它是新的。所谓新,不仅指历史感不是来源于历史观的理论构架,而且是指历史感不是来源于历史学的知识系统。历史感的神奇性在于,它不但有一种感性形式,而且还有一种理性内涵。这就足以使它有力量推翻历史观的霸主地位和摧毁历史观的霸权统治。近些年的纪实文学的异军突起,充分显示了历史感在洞察历史真相和理解历史意义方面较之于历史观具有更大的优势和潜力。纪实文学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分析和描述充分展示了历史感的厚重份量与深刻意蕴,它与历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学研究的平庸乏味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历史感构成了一种参照。这种参照使历史学家意识到历史观的力量不但是有限的,而且历史观的结构本身是有缺陷的。历史观的僵硬体系完全需要历史感的鲜活生命来予以充实和改造。
如果说,历史观使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异己存在,那么,历史感就使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的本己存在;如果说,历史观使历史变得陌生,那么,历史感则使历史变得熟悉;如果说,历史观使历史学家远离历史,那么,历史感则使历史学家贴近历史。二者的强烈反差,更显示出历史观的脆弱和无能。因为历史观始终也无法真正深入到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而历史感恰恰是从历史学家的心灵深处直接生发出来的独特体验。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在理解历史时,必须在原有的思维活动之外还要加上一种新的心灵活动,而这对于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单一化的历史观的僵硬体系控制下的只能教条地思维而不能深刻地体验的历史学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大的考验。故而,他们的心理就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失重和分裂。
二、视觉原因
对历史近距离的审视在今天变得可能了。但在四十多年前,这一切还都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五十年代新政权的建立,使得人们一股脑地将历史与传统抛向遥远的过去了。历史永远过去了。封建制度永远过去了。专制传统永远过去了。过去和现在完全不同。需要从政治和历史观的高度来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那个时期,历史学家的普遍心理感受就是:历史距离自己已经很远很远了。自己已经有可能依据新的历史理论去对过去的历史加以科学评判。
可以说,历史学家的视觉中普遍存在有两个误差,一是相信历史已经过去,二是相信过去已经距离自己现实很远。正是这两点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心理上的普遍的稳定性基础。他们相信自己生活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这就使自己完全有条件去对过去作出科学的认识。历史学家这种绝对稳定性的心理基础主要来源于历史学家对现实社会的过度迷信和盲目崇拜。当战争与饥饿一度在自己的身边消失时,他们肯定感到自己是最辛福的。现实太美好了,在美好的现实的反衬下,过去则显得更加丑恶。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史家与传统的彻底决裂,对封建社会的道德性谴责,对历史传统的全盘否定,如此种种,除了政治的高压与威胁之外,主要是历史学家的心理原因所致。
中国大陆史家急需要通过否定历史来完善现实。恰巧中国历史的多灾多难又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可能。他们越是美化现实,就越是丑化历史。从总体上看。中国当代史家大都经历过这种病态的心理过程,对现实的绝对肯定是其病态的原因,对历史的绝对否定是其病态的表现。一方面,中国当代史家是急功近利地强调“历史为现实服务”;另一方面,中国当代史家又实在无法使“历史为现实服务”。因为,他们把历史与现实的差距拉得如此之大,以致于谁也想象不出历史与现实之间究竟有何联系。这样一来,中国当代史家孜孜不倦地致力于的“历史为现实服务”就自然而然地失去了内在根据,于是,他们只好从历史中间翻找出一些最能说明现实必然性、合理性和优越性的材料和证据来三番五次地重复论证,以期达到“历史为现实服务”的最终目的。
可是,真正的现实又决不是中国当代史家心目中所幻觉的那么完美无缺。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中国史家开始逐渐地(尽管是非常有限地)改变了自己原来形成的那种过于浮夸的现实观念。一旦改变了现实观念,也就立刻拉近了自己与历史的距离。现实观念的改变,使第一次真切地感到历史与自己的距离竟是如此切近,历史非但没有远离现实,反而越来越迫近现实。
然而,历史对现实的贴近究竟又意味着什么呢?恐怕没有几个历史学家心里有数。他们只是朦朦胧胧地感觉到:当历史像大山一般地压向现实的时候,他们自己似乎再也没有一块“世外桃源”般的立足之地了。历史学家仿佛被历史完全驱逐出了现实领域,而变成了毫无现实感和现实依据的空心人。在这种不断失落的境遇中,现实感与历史感完全成为一种东西。由于历史与现实二者之间原有界限的消失,历史学家自己似乎也变得盲目起来。他们怅然若失,无所适从。历史与现实的一体化,使得历史从“远在天边”走到了“近在眼前”。但这个变化又实在过于突然,以致于历史学家思想上根本无法适应这种变化。他们总习惯性地认为:历史只有停留在远处才能看清,研究起来才会放心;否则的话,历史一旦来到人们眼前,人们就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般的拒绝和本能性的恐慌。历史一时间仿佛成为一个“死而复生”的可怕怪物似的。历史学家对历史是又敬又畏。敬的是历史是一个研究对象,畏的是历史成为一种现实力量。
作为活生生的现实,历史似乎不再有被把握的任何可能。作为现实的对立物,历史在历史学家面前是被动的、静态的,历史学家可以变着花样去切割和点缀历史,所以,在历史面前,历史学家始终像是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最高主宰者一样对历史评头论足;作为现实本身,历史在历史学家面前成为主动的、动态的,现在是由历史来支配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去支配历史了。这样,历史变成了被历史自身审视的对象。在历史的现实权威面前,历史学家简直失去了最基本的理性判断能力,他几乎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他总觉得历史距离他太近,对他是一种莫大的威胁和压力。所以,他必须想方设法地摆脱历史。这样,尽可能地、不顾一切地摆脱历史,便又成了历史学家在目前的当务之急。
因为,在中国当代史家看来,历史一旦成为现实,那么,他们就无从下手去对历史作出任何客观的分析。历史介入现实事务的程度越深,历史研究就越是危险。历史对现实进程的影响越大,历史认识就越是不可能。“近在眼前”的历史,使历史学家根本分不清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现实。而在所有的历史学家眼里,首先明确区分出历史与现实的界限,乃是正确地认识历史的基本前提。不划分出什么是历史、什么是现实,那么,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当然,这根本不同于“文革”时期的“影射史学”。因为“影射史学”的根本前提在于承认历史与现实的绝对差异)。这种视角上的偏差,使得中国当代史家越来越感到:历史研究现在越来越失去了传统的规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历史研究变得越来越不规范了、越来越不科学了、越来越无效用了。
这种视角盲点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的思维盲区,从而在心理上就产生了视觉障碍。
三、物质原因
无论如何,中国当代史家在五、六十年代乃至七十多代,虽然学术研究开展得并不顺利,精神上的种种压力也非常大,但物质生活上还总算是有所保障的。那时的工资当然很低、待遇当然很差,但当时整个社会的基本经济状况就是如此,人们的工资收入普遍都偏底。在计划经济的统一管制下,人们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都被国家一手包办下来。一切都是“大锅饭”式的。收入平均化,生活大众化,虽不甚丰盛和宽裕,但在节俭的条件下也基本够花。因为,过于贫乏的物质条件使人们没有任何过高的生活要求和奢望。五、六十年代,无论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都刚刚从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和国内战争中缓过气来。相对于那段时间的饥寒交迫的悲惨状况而言,五十年代的衣食无忧堪称“美满幸福”了。再加上,历史学家都忙于思想改造和学术围剿,谁也顾不上对自己的生活条件、物质待遇发什么不满和牢骚。他们相当心满意足。他们固然穷,但国家也穷,其他人都穷。故而,他们也就没有意识到,有朝一日自己的生活也会发生问题。
而现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打乱了原有的生活秩序。早已习惯于那种低水准的平平安安的生活状态的历史学家对于历史学的穷途末路深感惊慌。中国当代史家素来信奉唯物史观,但他们却从来没有从物质基础来解释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们从来没有用物质生活来解释自己的思想观念。好像信奉唯物史观就应该是天经地义似的。可现在,一旦历史学家的物质生活资料发生了危机,历史学家反而又开始抛弃唯物史观了。这对唯物史观是否公平呢?中国当代史家嘴里喊了几十年唯物史观,可恐怕他们连什么是唯物史观都没有真正弄清楚。唯物史观作为一家之言可能是最有力的,可作为包打天下的独家之言肯定是最无力的。现在,历史学家还要分出精力应付那些数不胜数的“史”外难题。他想走向市场,但举步维艰,力不从心。他想退守书斋,但又壮志未酬,实不甘心。他满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平均状态,痛苦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生活水准的两极分化。
历史学家一旦考虑这个问题,他的心理就变得不平衡了。生活的危机比什么都重要。如果说,计划经济体制是把历史学家的一切都包办起来之后再让历史学家去无后顾之忧地改造思想的话,那么,市场经济体制(我指的是目前的不完善、不健全、不正常、不合理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把历史学家的思想给全盘管制起来之后,再放开历史学家的手脚让历史学家自己去自谋出路。换言之,如果说,计划经济时代历史学家是只有思想压力而无生活压力的话,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历史学家则是既有思想压力,又有生活压力。一旦生活压力大到极限,历史学家就会精神崩溃,就会产生逆反心理。他就会近乎绝望地追问自己:作一个历史学家究竟值不值?研究历史到底有无意义?
可以预言,生活危机对于中国当代史学来说,既非暂时性的,也非局部性的。故而,它就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心理障碍的物质病因。
四、人格原因
中国当代史学对自身人格的明确意识还是近几年的事,而在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历史学家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过自身存在的人格问题。对人格的毫无意识,就决定了历史学家根本不可能有真正独立的人格。因为人格意识是人格独立的前提。所以,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史家的人格基本上是一种依附性的人格,而且这种依附还是一种心甘情愿的、主动的、自觉的依附。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并不觉得自己是不自由的,是无人格的。他们甘作“螺丝钉”,任意让人随便改变和扭曲自己。在“批俞平伯”、“批胡适”、“反右”、“拔白旗”等运动中,许多史家尽管心里并不完全同意别人对自己的指责与批评,但嘴上却还得表示赞成。虽然,事后一些史家回忆说自己作的检讨是违心之论,可他们的态度在当时却是真诚的。至少他相信领袖是绝对不会错的,自己的观点虽然不一定就错了,但起码不符合领袖的观点,起码自己还没有对领袖的理论吃透弄懂。所以,他们本着对领袖的观点要理解、理解、再理解和“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态度,无不虔诚地去拚命钻研经典著作,以期从中寻到解决自己思想问题的灵丹妙药。
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学家是借助历史学而把自己无条件地奉献给政治了。所以,中国当代史家的无人格性并不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历史学没有自己的不同观点,而是指历史学家不能立足于学术立场而对政治持一种严肃的批评态度。所以,历史学家不仅把自己出卖给政治,而且也把自己所热爱的历史学出卖给政治。这样一来,历史学家同时就犯了两个错误。历史学家不但不能在政治问题上表示不同意见,甚至在学术问题上也不能随便发表不同意见。因为,学术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学术上的不同观点就是政治上的不同立场。要么是“修正主义”,要么是“资产阶级”,要么是“唯心史观”,要么是“反党分子”。
所以,历史学家除了凭借历史学这层伪装去紧紧地依附于政治之外,简直别无选择。而不选择就没有人格。没有选择意识就没有人格自觉。所以,中国当代史家缺乏人格自觉,并不是历史学家的思维能力所致,从根本上说,乃是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和高度一体化的意识形态体系所致。可以说,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历史学家思想中所确立的唯一史学观念就是,历史学是政治斗争的工具,是阶级斗争的武器。从阶级斗争的历史观到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史学观,历史学家的全部价值都系在了政治这一根飘忽不定的绳子上。而历史学家的无人格性缺陷也由此被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
中国当代史家的无人格特性作为一种非学理性缺陷在较短的时间内似乎还不能一下子看出来。但时间一长,当它暴露出来时,便显得比一般的学术上的理论、方法、观念等缺陷还要严重和糟糕。以致于可以说,无人格性对历史学家的伤害是致命性的。这使历史学家长期以来都缺乏一种庄严的自信和高贵的自尊。历史学家总觉得自己做了什么错事似的。对不起政治,对不起国家,对不起社会,对不起时代。甚于这种忏悔感和自卑感,历史学家总想牺牲自己的一切以求报答党对他们的知遇之恩。历史学家的自卑感在50年代以前表现为自卑自己所学的都是错误的,80年代以后则表现为自卑自己所学的都是没有用的。这种自卑情结反映在人格上,就是用政治人格代替学术人格,用学术人格代替思想人格。在政治前提下,学术、思想统统不复存在。所以,几十年内,历史学家都没有提出一个有深度、有价值的历史问题。因为他们的学术自信和人格自尊早已被政治摧残殆尽。
八十年代后,痛定思痛的反思结果,使中国当代史家开始意识到自己人格的缺陷和人格的独立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初步涉及是在“史学危机”讨论时提出来的。但一般来说,历史学家对自身人格的独立性还很少有深刻的思考和坚定的态度。人们大都是在讨论知识分子的人格时才捎带着提出历史学家的人格问题,而且,在这个时期,中国当代史家似乎更关心自己的“主体价值”,而对自己的独立人格缺乏较大的兴趣。
在我看来,如果历史学家没有独立的人格,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学理上的自信;而缺乏学理上的自信,就不可能提出有价值有思想的历史问题;如果提不出有价值有思想的历史问题,就不可能彻底突破统治史学界几十年的规范认识和正统模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历史学家的人格比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史学观念更为重要。然而,正如同历史理论、研究方法、史学观念都不仅仅是理论、方法、观念自身的事情一样,历史学家的人格也决不仅仅是历史学家自身的事情。说到底,历史学家自己根本决定不了自己有无人格。与五十年代相比,那时是历史学家本人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是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不等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解决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了历史学家在现阶段的能力。
历史学家的人格在现实处境中仍然是依附性的,而非独立性的。区别在于,现在的依附是一种消极的、非自觉的的依附。简言之,如果说,五十年代开始的那种依附是一种紧密型依附的话,那么,八十年代形成的这种依附则是松散型的依附。尽管从形式上看,从紧密到松散有了明显的“自由”、“开放”和“进步”,但从实质上看,依附关系仍然存在。所以,充其量,现在的中国史家只能算是一种“半独立性”人格。
如果根本意识不到人格,那么人格对历史学家就不是一个问题;如果意识到人格,而又没有人格,这对历史学家就是一个问题。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对自身人格的敏感性和需求性才越来越迫切。这样,它就必然构成了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障碍的人格病因。
五、地位原因
有史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史学大国,至今依然。据此一点,便可看出历史学在中国社会上的地位与份量。在此文化背景下,历史学家在国家的权力金字塔中和政治等级秩序中的特殊作用也就显而易见了。所以,中国古代,史家就是史官。除了《周礼》中对史官的分类和定位夸张和拔高得有些离谱外,一般而言,史官在古代社会中还是受人尊敬的。尽管唐代的刘知几曾借着美化前代史官的权力和地位来对自己时代史官作用的下降表示不满。但一般说来,史官在封建国家的政治生活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尽管史官的品级都不高,但由于他们写的是皇帝自己的事情(不管是前代的皇帝还是本朝的皇帝,只要是帝王的活动他们都关心),所以,史官就有条件去接近皇帝、劝谏皇帝,向皇帝传授历史教训和知识,以达到阐述自己的政见和参与政治乃至影响政局的目的。这点,我们在“二十四史”以及《资治通鉴》、“三通”的编纂经过中就能清楚地看出来。
这个传统流传到现代,在一定程度上,又有所发扬光大。五十年代,为了提高各级干部的文化水平,便让全国一批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去为他们专门编写了一部中国通史,这就是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并且还在专门培养高级干部的中央党校里,定期请一些权威历史学家去为高级官员们讲授历史知识。郭沫若作为中国最有声望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成为文化学术界人士在政府担任最高职务的人。这当然不是说,郭沫若就因此参与了军政大事的决策与制订,但起码在国家的文化学术发展的规划和方向上,他是发挥了自己独特的作用的。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史家参与政治的一种表现。尽管这种参与政治的方式很有局限,它对政治本身的影响也不大,而且它局限在极个别的影响大的历史学家身上,远非大多数历史学家都能“利益均沾”地参与政治。
当然,中国当代史家参与政治还有另外一种较为特殊和极端的途径,那就是在“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为了发动舆论、制造声势,官方动员一大批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来按照它们的旨意撰写历史。从上海一批史家写的“评《海瑞罢官》”到北京一批史家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他们不仅亲自参与了当代政治,而且还直接影响了现实政治。“文革”时期,“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等“史学”运动,又把一批历史学家派上了用场。对那些当事人来说(比如“梁效”写作组中的某些历史学家),这未必不是他们“学以致用”(“经世致用”)的一个绝好机会。其实,不光是搞“文”的政客们需要利用历史学家来为他们提供历史材料,而且就连那些搞“武”的政客们也需要拉拢历史学家来为他们充当活字典。因为在那个历史文化氛围笼罩一切的年代,历史似乎成了政治斗争的最有力的工具和改朝换代的最有效的武器。历史简直成了升官的捷径和做官的诀窍。那个时代的荒诞文化现象就是:人们一方面不可自拔地沉溺在最最现实不过的事务中,一方面又忘乎所以地钟情于最最古老不过的事件上。一个证据就是:几乎所有的文科刊物都被取消和停办的情况下,《考古》和《历史研究》却率先发行了。在那个时候,《历史研究》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可以说是统治中国思想舆论王国的三大支柱和三大主力。
凡此种种对于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都是一种特殊的刺激和启示。历史学家总是要参与政治的,只有参与政治才能实现自己价值。正因为如此,中国当代史家对政治尤为敏感。中国历史学家好像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政治温度计。历史学家跳起来,政治就热了;历史学家不跳了,政治就冷了。中国当代史家总习惯于围绕政治来展开自己的话题,总喜欢围绕着政治来说明历史问题。中国当代史家总是问史学应该为政治做些什么,而从来不问政治应该为史学做什么。
前有“殷鉴”,后有“党鉴”。历史学家要么做官,要么参政,这都可视为历史学家的绝好出路。可现在不行了。八十年代以后,历史学家虽然还是“干部”(按大陆的行政序列定位),但亦算不上是“官”了,至于参政,那机会就更少了。历史学家不再是“官”,而差不多沦落成了“民”。而作为“民”,他便再不能去参政,充其量只能去“议政”。但即便是议政,也不能信口开河地随随便便议来议去。总之,比起古代,中国当代史家当官的机会少了;比起八十年代以前,中国当代史家参政的机会少了。历史学家的地位真可说是一落“十”丈。作为一介“平民”,他只能空头议论。所以,在远离政治之后,历史学家终于也开始失去了政治。几十年的政治运动已使政治本身厌倦了历史学这种借古喻今的斗争方式,而更需要一种更富操作性的权力工具,于是,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应运而“生”。
历史学被排挤出原来的政治圈子,由权力中心跌落到权力边缘。历史学家只能听别人在权力中心滔滔不绝地议论政治、纵横捭阖地操纵政治。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较之于历史学家更容易接近权力中心,更容易发挥学术影响,而历史学家则只好叨陪末座,只剩下洗耳恭听的份了。可以说,与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等一批“政治显贵”比较起来,历史学这个原有的“政治贵族”现在真可以说是赤裸裸地“平民化”了。作为无权无势的“平民”,历史学家的发言可以说是人微言经,历史学家的话对社会政治不再有任何威慑和影响。这种地位上的落差可以说就是构成中国当代史家心理障碍的地位病因。
六、结语
综合起来,中国当代史家的心理是不健全的,心态是不平衡的,总体上看,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一种心理缺陷或心理障碍。当然,有的人表现在多方面(即有多种表现,可称之为综合表现),有的人表现为某一方面(即只有一种表现,可称之为单一表现)。清醒地意识到这点,有助于中国当代史家对历史与历史学的关系作出正确的判断。就目前而言,调整自己的心态是最为重要的,否则,很可能就会在“四面楚歌”中陷入灭顶之灾。我相信,二十世纪的心态没有理由继续成为二十一世纪的心态。中国当代史家也没有理由必须要把二十世纪的心态带到二十一世纪中去。所以,心态的调整与转换对于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史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这一点能否得到证实,还取决于历史学家如何面对自己的心理障碍。
我希望通过这番分析,使每一个历史学家都能够在中国当代史学的序列中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即自己来给自己定位。如果大家都能这样,那么,中国当代史学的方向也就自然确定下来了。因为历史学家给自己的存在定位,也就等于是给自己的思想定向,也就等于是给历史学的发展定向。可以说,中国当代史学的革命性转折完全有赖于历史学家的这种努力。
来源:《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4期
- 0001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