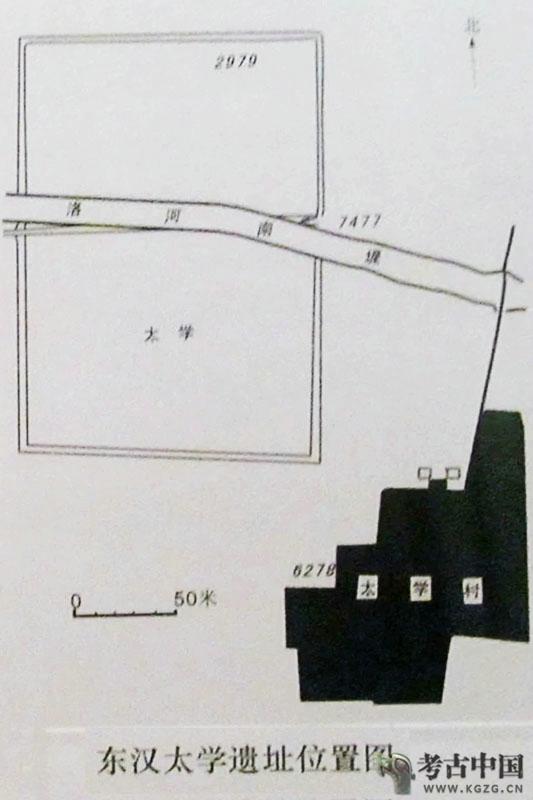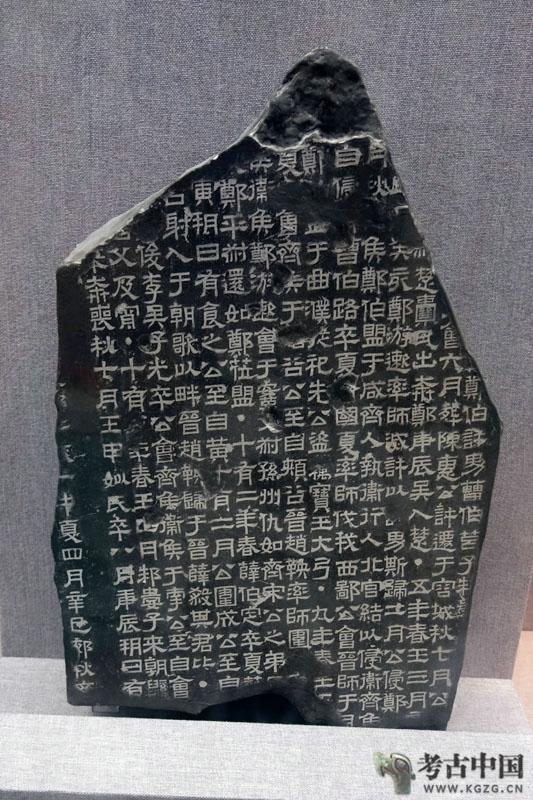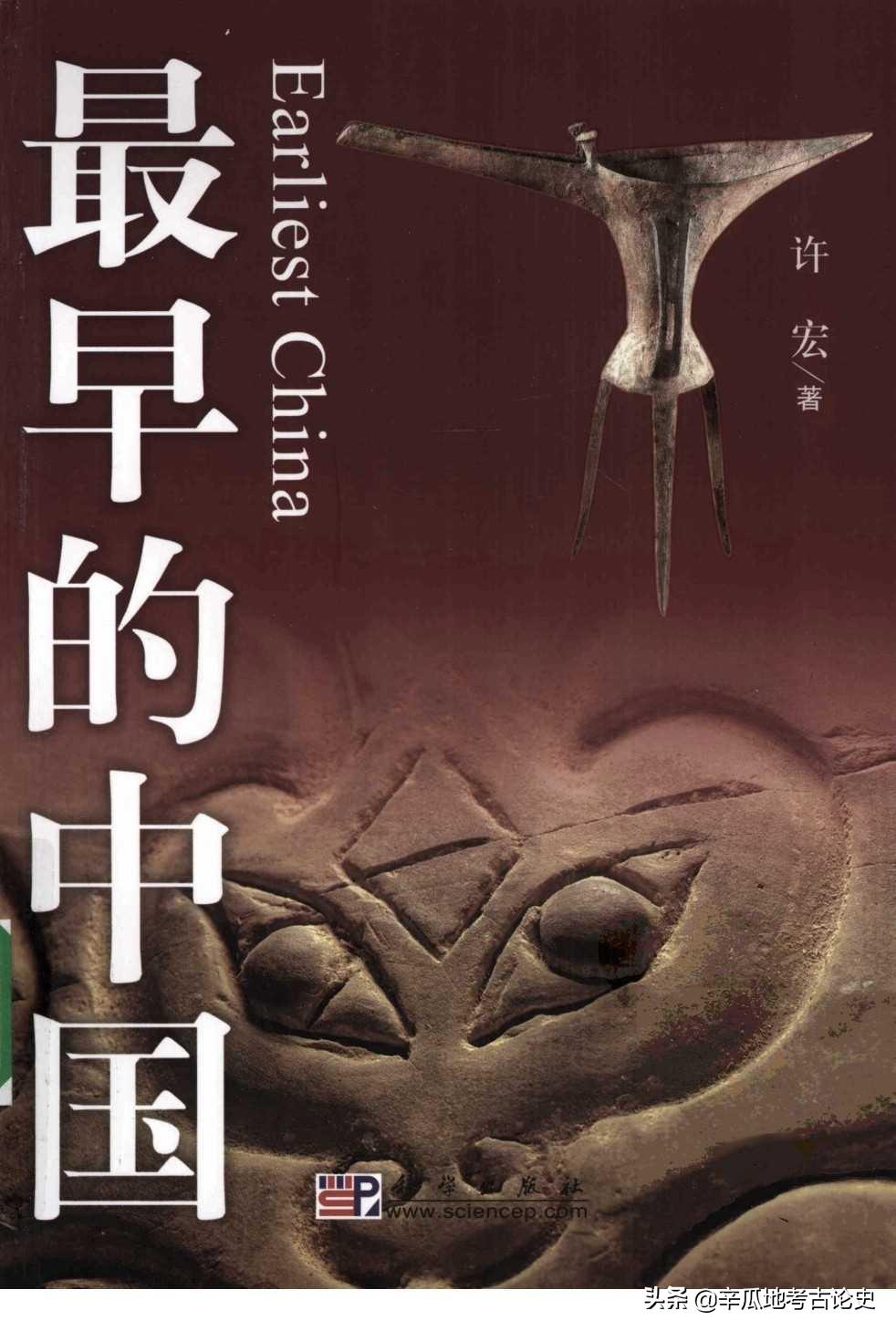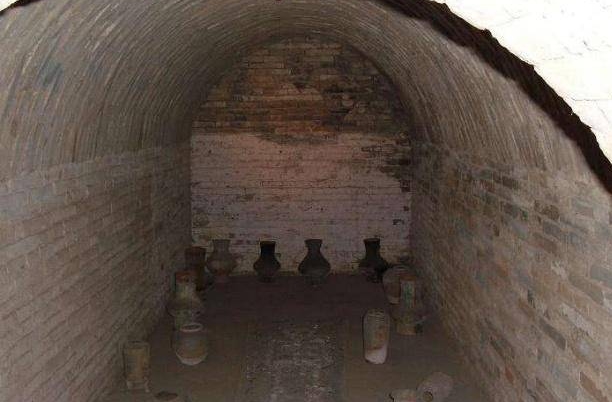李学勤:对古书的反思
中国以其绵远悠久的古代文化著称于世,其标志之一是传世古籍的丰富繁多。人们形容中国典籍,常说汗牛充栋、浩如烟海,并非夸大之辞。古书可以认为是前人遗留的信息。过去的世代早已消逝,但就像我们的感官接受远方传来的声波、光波一样,通过书籍所蕴含信息的传递,能够认知古代的存在。
在历史上长远的时期里,书籍是认识古代文化的唯一渠道。人们一代一代地传播着这种信息,古书在传抄,在出版,维持着古代文化的生存。书籍的绝大多数读者是信息的接受者,对古籍中显示的信息是信任的,只是对这些信息作出不同的解释说明,很少有人去考察信息本身的传递过程。直到近代,当我们的传统文化不得不变革的时候,才出现对信息的怀疑,要求对传世古籍重行系统估价,于是涌现了“疑古”或称“辨伪”的思潮。大家都记得,这一思潮怎样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形象,有着深远的影响。这可说是对古书的一次大反思。
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发展,为认识古代文化提供了另一条渠道。文物和遗迹的发现和研究,是对古代遗存的直接接触,与通过书籍取得的信息难免有某种变形是不同的。上面谈到的对古书的反思,仍然是就书论书,一般只能是揭示古书内容可能存在的种种矛盾。考古学的成果则在书籍之外提出客观依据,特别是近年,从地下发掘出大量战国秦汉的简帛书籍,使人们亲眼见到未经后世改动的古书原貌,是前人所未曾见的。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将能进一步了解古籍信息本身,知道如何去看待和解释它们。这可说是对古书的新的、第二次的反思,必将对古代文化的再认识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能对上一次反思的成果重加考察。
研究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传流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值得注意的情况:
第一,佚失无存。地下发现的简帛本古书,不少是不见于现存著录的佚籍。例如在最近发现的江陵张家山竹简中,有一种数学书题为《算数书》,其写成年代早于今本《九章算术》的成书,堪称中国数学史上的惊人发现。这部书并未见于《汉书•艺文志》以及其他著录。另外还有一些简帛本书,虽曾见于著录,却在时间的长河中久已湮没无存。例如临沂银雀山竹简中的《孙膑兵法》,当即《汉书•艺文志》记载的《齐孙子》,可是此书估计在东汉末年即已散佚了。如所周知,《汉志》著录的书籍能保存至今的不很多,看来《汉志》没有著录的古书还不知有多少种[1]。
第二,名亡实存。有的简帛古籍前所未见,实际其内容仍保留在后世的书里。例如最近发表的长沙马王堆帛书《胎产书》[2],其开首一大段托名禹问、幼频答。这篇帛书字体较早,很可能抄于秦代,内容应是先秦作品,而上述一段现存于隋唐著作《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中,只是语句略有改易,却被说成是北齐名医徐之才的“逐月养胎方”。《胎产书》的这一段,事实上并未佚失,只是被改头换面,以致无人得知。
第三,为今本一部。马王堆帛书有《战国策》,发表时称《战国纵横家书》,共二十七章,其间十一章见今《战国策》或《史记》。按传本《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纂辑,其叙云:“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脩书》。”帛书本应为其中一种,只能算今本的一部分,但就其性质而言,仍然属于《战国策》。
第四,后人增广。古书开始出现时,内容较少。传世既久,为世人爱读,学者加以增补,内容加多,与起初大有不同。如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都出有一种竹简古籍。审其内容,大多述孔子及其弟子言行。查《汉书•艺文志》,记述孔门事迹的书有《论语》、《家语》,此书体裁与今《家语》接近,许多内容同于《说苑》等,也与今《家语》一致。今本《家语》久为人所怀疑,指为王肃伪作。从新发现看,《家语》还是有渊源的,只是多经增广补辑而已[3]。今本后序所述《家语》传流经过,也许并非尽出子虚。
第五,后人修改。古书传流多赖师传,有时仅由口传,没有书于竹帛,因而弟子常据所见,加以修改,不能斥为作伪。在新出简帛中,例如长沙马王堆帛书和江陵张家山竹简都有《脉书》(帛书发表时题为《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阴阳脉死候》),经研究系今传《内经•灵枢》书中《经脉篇》的祖本,有很多文句是相同或类似的。不过,《经脉》比《脉书》要丰富得多,而且即以最中心的脉数而言,《脉书》是十一脉,《经脉》则增加到十二脉。这不只是文字内容加多,而是在观点上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虽有这样的重大改动,仍不能否认《脉书》是《经脉》的滥觞。
第六,经过重编。以马王堆帛书《周易》为例[4]。帛书有经有传,其传文多与今有异。与今《易传》“十翼”对比,可知“十翼”中的《系辞》《说卦》都曾经重新编写,其文字和编次有许多不同。帛书本好些富有哲理的段落,也不见今本。至于帛书《周易》的经文部分,是对传世本加以重编,在卦序上更合于阴阳学说,其年代反晚于今本经文的成立[5]。因此,出土古籍有时也不一定是最早的本子。
第七,合编成卷。如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以《老子》两篇同《五行》《九主》《明君》《德圣》四篇抄在一起,成了一卷书。这些内容思想倾向很不相同,虽然有某种联系,却分隶不同学派。尤其《五行》出于子思、孟子一派之手,和《老子》不能同日而语。传世古书也有这一类混编的情形,如《逸周书》《管子》之类,各篇年代和思想多有差异。《管子》中收入《弟子规》,尤为明显。帛书《老子》甲本,以《黄帝书》(可能即《汉志》的《黄帝四经》,发表时称《经法》等)同《老子》合写,虽同属道家,有“黄老”之称,究竟不出于同时同人。不加区别地抄为一书,总是易滋误会的。
第八,篇章单行。古人抄书很不容易,书不易找,书写材料也有困难,因而大部头的书籍有时只有部分篇章单行,普及于世。清人刘宝楠《愈愚录》曾专论及此,举了不少实例,其间有《保傅传》。《保傅》是贾谊《新书》里的一篇,又收入《大戴礼记》。现在在定县八角廊竹简中,果然发现有单行的《保傅》[6]。由这个例子,可知新出简帛中有些单篇,不一定意味当时还没有全书,只不过藏简帛的墓主人仅有此篇就是了。
第九,异本并存。上面已经谈及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竹简的《脉书》。书中发表时题为《阴阳十一脉灸经》的部分,又抄在《导引图》帛书上。马王堆帛书该卷,在《脉书》前又有现题《足臂十一脉灸经》的一篇,也是论十一脉,而又有不同。同样是《灵枢•经脉》的渊源,但同见于一卷帛书上面,显然是不同本子的并存。帛书《周易》与传世本经文是并存的,上文已论。同样,帛书《老子》先《德篇》后《道篇》,曾引起学者惊异,而今传河上公注本实际也不是晚出的,汉初也可能存在。这些,都是异本并存的例证,不可见新发现之本而摈斥传本。
第十,改换文字。古人传流书籍系为实用,并不专为保存古本。有时因见古书文字艰深费解,就用易懂的同义字取代难字。《史记》引用《尚书》便用过这一方法,看本纪部分即可明白。临沂银雀山竹简《尉缭子》的发现,初看与今本不同,颇多艰奥文句,细察也是经过类似改动,以致面目全非。这大概是由于《尉缭子》是兵书,更需要让武人能够学习理解。
以上十点,概括得恐怕不够完全,希望读者由此能认识到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总的说来,除了少数经籍早已立于学官,或有官本,古籍一般都要经过较大的改动变化,才能定型,那些仅在民间流传的,变动自然更甚。如果以静止的眼光看古书,不免有很大的误会。
通过这些年来整理出土简帛的经验,又使我们认识到古代发现佚书时,整理的要求和标准可能和今天不一样。历史上有两次发现大量古籍,一次是西汉时的“孔壁中经”,一次是西晋时的汲冢竹书。壁经以古文《尚书》为主,汲冢所出则有《纪年》、《穆天子传》、《师春》等等。古文《尚书》东汉末始多流传,今本出于晋代梅赜所献,自孔安国起的整理过程是很漫长的。清代学者批评今本古文《尚书》,其中有些问题也许就出于整理的缘故。至于今本《纪年》,有的疑难同样可能是当时整理方法的结果。[7]这个问题,我们将另文讨论。
对古书形成和传流的新认识,使我们知道,大多数我国古代典籍是很难用“真”、“伪”二字来判断的。在“辨伪”方面清代学者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也有不足之处,其一些局限性延续到现在还有影响。今天要进一步探究中国古代文化,应当从这些局限中超脱出来。从这个角度看,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在学术史研究上也有方法论的意义。
注释:
[1]陈国庆:《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第234-235页,中华书局,1983年。
[2]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汉墓帛书(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
[3]参看陈士珂《孔子家语疏证》序。
[4]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
[5]李学勤:《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卦位》,《中国哲学》第14辑。
[6]定县汉墓竹简整理组:《定县40号汉墓出土竹简简介》,《文物》1981年第8期。
[7]参看陈力《今本竹书纪年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8辑《研究生论文选刊》,1985年。
来源:《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李学勤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5-20页。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