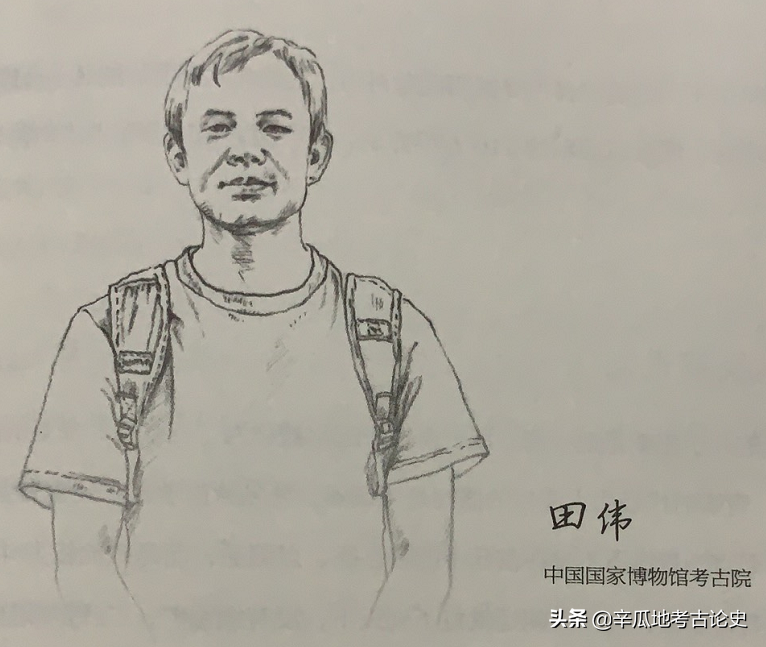罗炤:中国人从未主动利用丝绸之路吗?——与葛剑雄教授商榷
去年年底从网上看到葛剑雄教授在上海图书馆增爱世界文化论坛上做的题为《丝绸之路与一带一路》讲座的报道,葛教授说:“尽管丝绸之路在历史上起了很大作用,但中国人从未主动利用这条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获利。”“古代中国海上从来未开放外贸,还经常实行海禁、迁海,民间对海外的贸易长期被禁。只有元朝对外有短暂时间允许商人出海去外国贸易。”“海上丝绸之路开辟的原因是公元755年,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断绝,加之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海上运输巨大经济利益驱动、瓷器外销的可能,诸多原因共同推动了这条商路的产生。”看到这些文字,我非常诧异。
但是,网上的报道是另外一位作者写的,不敢确定原话是否确为葛教授所说,因而没有特别在意。今年7月又看到葛教授做了有关丝绸之路的演讲,再次强调:国内“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历史上中国并没有主动利用丝绸之路,它主要的动力是来自外界。”(见凤凰网历史栏目7月31日报道)这一次的报道文本在结尾特别说明:“本文系葛剑雄教授在2018年‘汉学与当代中国’座谈会上的演讲,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因为是“根据现场录音整理”的文本,而且这次和七个月以前说的“中国人从未主动利用这条路,也很少从丝绸之路获利”完全一致,虽然“未经主讲人审阅”,但属于葛教授的原话应该没有问题。
最近从社科在线上看到葛教授又在上海图书馆演讲《丝绸之路的历史回眸》,不仅再次说:“(历史上)我们不主动经营外贸,主要利益都是由外方所得,而对民间贸易是一贯限制甚至禁止,或者课以重税,以致民间非走私就不能获利。”而且说:“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是谁建的呢?阿拉伯人。”“现在留下来的郑和的记录中,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针路’,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术叫‘牵星过洋’,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靠看星来定位。”这些有违史学常识的话,让我瞠目结舌。至此,不能不撰文与葛教授商榷了。
一、海上丝绸之路何时开辟
葛教授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著名学者,《汉书·地理志》应当是烂熟于心的基础文献。《汉书·地理志》第八“下”记载:“粤地,牵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接下来详细地记述了“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儋耳、珠厓郡的民风、物产、武器、历史沿革等,然后是航海至都元国、邑卢没国、湛离国的日程。从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
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这是中国古代文献首次对于汉武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以及中国人“赉黄金、杂缯(丝绸)”,航海赴东南亚、南亚贸易,到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返航的详细记录。
罗马帝国大博物学家普林尼(另一译名“白里內”,公元23—79年)的名著《自然史》(另一译名《博物志》)的相关记事,恰恰可以和《汉书·地理志》以上的记述相互印证。《自然史》说:赛里斯(中国)“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
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罗马Claudius皇帝(公元41—54年在位)时,锡兰(古称师子国,今斯里兰卡)“岛王乃遣拉切斯等四人为使者至罗马”,拉切斯的父亲曾到过赛里斯经商,“事实上彼等(赛里斯人)对于奢侈品的交易不自珍惜,而且对于货物的流通地点目的及其结果,心目中已经了然。”普林尼慨叹:“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赛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赛斯透司,此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0—22页。)
公元5世纪初的名著《佛国记》记载:师子国“其国本无人民,正有鬼神及龙居之。诸国商人共市易,市易时,鬼神不自现身,但出宝物,题其价直,商人则依价直直取物。因商人来、往、住故,诸国人闻其土乐,悉亦复来,于是遂成大国。”这些文字可以进一步印证《汉书·地理志》和普林尼的记录真实可靠。
南宋时期祝穆《方舆胜览》卷四十二《雷州·徐闻交易》条的记载,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汉朝时期中国官民双方主动利用海上丝绸之路获利致富的景象:“《元和志》:‘汉置左右候官在徐闻县南七里,积货物于此交易。谚曰:欲防贫,诣徐闻。’”
近几十年来,广东、广西考古工作者在徐闻县和合浦县沿海地区发现或发掘了大批汉代遗址,在徐闻出土了“万岁”文字瓦当以及玻璃珠、琥珀珠、玛瑙珠、水晶珠等海外舶来品;在合浦县堂排的4座西汉墓中,出土了天蓝、湖蓝、绿色的玻璃珠1656粒;在合浦母猪岭6座东汉墓中,发现玻璃珠860余粒。出土实物印证了《汉书·地理志》和《方舆胜览》的上述文字记载。
中外学术界早已公认汉武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南北朝时期更有很多南亚和东南亚的佛教僧人从海路来到中国,中国高僧法显也是搭乘商船从师子国经印度洋和南海回国的。作为知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和关注丝绸之路的学者,葛教授不可能不知道上述史地古籍的记载,不可能一点也不知道多年来在徐闻和合浦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怎么能断言海上丝绸之路是“安史之乱后丝绸之路断绝”才“开辟”、“产生”的呢?
葛教授说:“海上丝绸之路也不是中国开辟或者掌握的。是谁建的呢?阿拉伯人。”以上《汉书·地理志》、普林尼《自然史》、《佛国记》和《方舆胜览》的记载清楚显示:早在公元前的汉武帝与罗马帝国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已经开辟,而且是由中国人、东南亚人、师子国人、天竺(印度)人、罗马人、波斯人和阿拉伯半岛居民等共同开辟的。需要注意的是,汉朝和罗马帝国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居民,与公元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以后的阿拉伯人有一定的性质上的差别,因而更不能笼统地说汉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是“阿拉伯人建”的。
二、星占、指南针与航海
葛教授说:“现在留下来的郑和的记录中,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针路’,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用的技术叫‘牵星过洋’,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靠看星来定位。不要以为中国古代有指南针,指南针只能小范围用,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这里涉及的是航海史和科技史领域的重大问题,中外学术界长期讨论,有的早已明确解决,有的尚存分歧意见。葛教授不是研究航海史和科技史的专家,触及自己外行的领域,本当谨慎从事,没有想到他竟然在大众化的讲演中“一锤定音”,替皓首穷经潜心研究航海史和科技史的中外学者们下了结论。胆量虽可包天,学风却不敢恭维。
研究航海史和科技史的专家们都知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五星占》,其中记录了占星的角度单位“指”。公元前2世纪的《淮南子·齐俗训》中,已经记载:“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寤矣。”这是中国最早的舟行水上占星导航的记载。有关航海与星占的书籍,《汉书·艺文志》著录了“《海中星占验》十二卷,《海中五星经杂事》二十二卷,《海中五星顺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国分》二十八卷,《海中二十八宿臣分》二十八卷,《海中日月彗虹杂占》十八卷。”公元前的中国古人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海中星占知识。
到北宋时期,中国进一步将指南针运用于航海事业,并将星占与指南针结合在一起导航。成书于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的《萍洲可谈》记载中国商人下南洋贸易(“北人过海外”)情事甚详,其中有“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这是世界航海史上最早使用指南针、以及将星占与指南针结合运用的记录。宣和七年许兢所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航海情状更加详细,对于观星导航、使用指南针确定海上方位之事,其卷三十四记述的十分具体:“舟行过蓬莱山之后,水深碧色如玻璃,浪势益大。……是夜洋中不可住,维视星斗前迈,若晦冥则用指南浮针以揆南北。”《宣和奉使高丽图经》的这一记载与《萍洲可谈》的以上记述仅相差六年,一者说的是远航南洋的情事,一者讲的是北渡东海、黄海、渤海的状况,一南一北,且同时代,恰可相互印证。
现存最早的“针路”记录,出自成书于13世纪末的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总叙》,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干支、八卦“丁未针”和“坤申针”,而不是葛教授说的“(郑和)航海图里面用的概念是‘针路’,这个概念就是阿拉伯人的概念。”《真腊风土记》所记之事早于郑和下西洋一百多年,郑和航海图岂能舍弃自己的老祖宗早已熟练掌握、属于本土语言文化、且长期行之有效的“针路”,颟顸地去采用“阿拉伯人的概念”?
中国从宋朝开始,航海已经普遍使用指南针导航,宋、元时期的著作中还有很多记载,限于篇幅,本文不能一一列举。断言中国古代发明的指南针“真正在海里是没有用的”,过于轻率,不应该出自葛教授之口。
至于“牵星过洋”的技术,学术界现存三种见解:一种认为属于中国传统的航海天文学,一种认为受到阿拉伯人航海术的影响,一种认为是中国传统航海天文学和阿拉伯人航海术相融合的产物,目前尚无定论。作为外行人的葛教授,竟然断言“也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不该是学者应有的严谨态度。
三、古代中国海上从来未开放外贸吗?
葛教授所说“古代中国海上从来未开放外贸,还经常实行海禁、迁海,民间对海外的贸易长期被禁”,则更非事实。《汉书·地理志》和《方舆胜览》的上述记载已经证明葛教授此说之误,汉朝以后更有不胜枚举的中外文献和实物,能够证明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繁荣昌盛,本文难以具列,仅以宋朝为例:
《宋史·食货志》下·八记载:“雍熙(984—987)中,遣内侍八人赉敕书、金帛,分四路招致海南诸蕃。商人出海外蕃国贩易者,令并诣两浙司市舶司请给官券,违者没入其宝货。”《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记载:“端拱二年(989)五月诏:‘自今商旅出海外蕃国贩易者,须于两浙市舶司陈牒,请官给券以行,违者没入其宝货。’”这是在北宋建国尚不足三十年,由第二位皇帝宋太宗发下的诏令,反映出中国的商人们在此之前早已经出海从事国际贸易,而且还不需要得到官方的批准,从雍熙—端拱年间开始,北宋朝廷才要求他们必须到两浙市舶司申请许可证。此后,为便利海外贸易,宋朝政府又在沿海地区陆续增设了几个市舶司。这是政府行使正常的管理职能,现代世界的各国外贸企业也都需要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申领资格证书。
宋高宗进一步将海外贸易作为南宋立国的根基之一,高度重视,频繁过问,宽待海商。《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记载,绍兴七年(1137)“闰十月三日,上曰:‘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尔。’”因为宋高宗高度重视、用心扶植,绍兴年间海外贸易收入大增,缓解了南宋建立之初的危难。为鼓励海外贸易,增加财政收入,宋高宗甚至用加官晋爵的手段奖赏地方官员和中外商人。《宋史·食货志》下·七记载:“(绍兴)六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啰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
由于海外贸易利润丰厚,宋孝宗初年“海南州县”为了更快、更多征收国内出海商船的税收,限定他们的航海时间,尽量缩短日程,要求尽快返航回港完税,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宋会要辑稿·职官》四四记载,隆兴二年(1164)“八月十三日,两浙市舶司申:‘……缘其间或有盗贼、风波、逃亡事故,不能如期,难以立定程限。今欲乞召物力户充保,自给公凭日为始,若在五月内回舶,与优饶抽税。如满一年之内,不在饶税之限。满一年已上,许从本司根究,责罚施行。’”宋孝宗御批执行。由此可以进一步看出,南宋朝廷不仅允许国内的商船出海贸易,而且对于出海贸易的商人们还有所体谅,适度地呵护他们的利益,不许地方官员过度地索取。
南宋淳熙五年(1178)周去非撰写的名著《岭外代答》,其卷六《器用门·木兰舟》一节,是在以上历史背景中写出的,具体记述了航行到南海、乃至更远方的商船及船上的情况,可以让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南宋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径入阻碧,非复人世,人在其中,日击牲酣饮,迭为宾主,以忘其危。舟师以海上隐隐有山,辨诸蕃国皆在空端……盖其舟大载重,不忧巨浪,而忧淺水也。
又大食国更越西海,至朩兰皮国,則其舟又加大矣,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或不遇便风,則数年而後达,非甚巨舟不可至也。今世所谓‘朩兰舟’,未必不以至大言也。”周去非在广西钦州、桂林地区为官前后六年,以上记载应该是他在钦州沿海亲见、亲闻,其中所记“豢豕、酿酒其中”以及船的航向,显然说的是中国的商人出海贸易之事,可与上述南宋朝廷极其重视海商市舶的政策相互呼应,更加全面地反映出南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景象。
事实上,在《岭外代答》成书近六十年之前,《萍洲可谈》已经非常详细地记述了北宋时期广州等地的中国商人远航南洋贸易的各方面情况。如果说汉朝时期中国人远航海外还不够多、不够主动,宋朝时期的中国人则全方位跨海越洋,外出内引,迈进海上丝绸之路空前繁荣的时代,并且为元朝时期更大规模、更加开放的亚、欧、非三大洲海洋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会要辑稿》和《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岭外代答》都是研究宋代历史地理学的必读参考书,以上所列宋朝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史实,葛教授应该早已知晓,怎么还能说“古代中国海上从来未开放外贸”?
明朝前期和清朝初期,由于军事等原因,确曾“禁海”、“迁海”,“片板不许下海”,但均不能长久维持。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勃雷所著《海外华人》一书的《序言》中记有伟大航海家郑和劝谏皇帝保留船队的话:“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上…… 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我国船队战无不胜,可用之扩大经商,制服异域,使其不敢觊觎南洋也。”明朝中期以后,漳州的月港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厦门岛由此地位大大提升。
郑成功能够长期抗清并收复台湾,与月港带动起来的闽南民间海商集团有很大的关系。清朝则更快地开辟了江、浙、闽、广四个对外通商口岸,尤其是批准广州十三行专门从事海外贸易,粤海关成了“天子南库”。乾隆时期虽然收缩到广州一个外贸口岸,但此时欧洲商人的对华贸易规模已经极大扩展,清朝政府、外商和十三行均从海外贸易中获取了巨大利益。
综上所述,葛教授说古代中国“经常实行海禁、迁海,民间对海外的贸易长期被禁”,与历史事实不符。
四、丝绸之路与中国的世界性影响
最让人难以认同的是,葛教授说“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东西)可以用百位数来计算,但中国传到外国的却只有个位数”,意思是中国通过丝绸之路从外国受益极大,贡献于世界的却甚少。本文不想重复丝绸在罗马帝国的影响,以及十七、十八世纪欧洲启蒙时代的中国热等等学术界尽人皆知的事情,在此仅指出以下两项:
(一)1620年,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划时代的名著《新工具》中写道:“我们还该注意到这些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这几点是再明显不过地表现在古人所不知、较近才发现、而起源却还暧昧不彰的三种发明上,那就是印刷、火药和磁石。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第一种是在学术方面,第二种是在战事发明,第三种是在航行发明;并由此又引起难以数计的变化来;竟至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何星辰对人类事务的力量和影响都仿佛无过于这些机械性的发现了。”(英)培根著、许宝骙译:《新工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一书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 “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
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马克思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译:《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67页。)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都源于中国,都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阿拉伯世界和欧洲的,尽管有些外国学者在细节和传播路线上提出了一些异议,但它们从中国传出的基本事实则是确定的。在十三、十四世纪,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发明(以及《马可波罗游记》和东方传入的黑死病)促动了欧洲十五世纪以后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变革,尽管这三大发明在中国本土并未充分展现其威力。
(二) 17世纪以后的欧洲国家、特别是英国,和广州“十三行”交易,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贩卖中国出产的茶叶,利润丰厚。英国征收100%以上的高额茶叶进口关税,引发北美十三州兴旺的走私中国茶叶的生意。为杜绝走私,英国制定了《茶叶法》,授予东印度公司在北美殖民地销售中国茶叶的垄断权,由此十三州的茶叶走私商和英国的利益冲突愈演愈烈,终于发生了1773年的“波士顿倾茶事件”,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起爆点。现今的世界霸主美国,是从贩卖中国茶叶的商业纠纷中孕育、诞生的。
以上两大历史变革说明,通过丝绸之路,中国传到外国的即使“只有个位数”,但在这“个位数”中,却有翻天覆地的能量。事实上,经由丝绸之路从中国传到外国的,远远不止葛教授说的“只有个位数”。在这一研究领域,有些西方学者知道的比葛教授多得多。
五、“海上丝绸之路”是谁、何时提出的?
久仰葛教授大名,不过,从他一年来几次丝绸之路的讲演看,可能尚未对海上丝绸之路做过深入研究,“硬伤”不少。葛教授说:“比如说‘海上丝绸之路’,这概念是日本的学者到上世纪80年代才提出来的。”我很诧异,葛教授怎么会不知道,“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是法国杰出的汉学家沙畹(Emmanuel-èdouard Chavannes,1865-1918年)在1903年出版的名著《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occidentaux)一书中指出的:“丝路有陆、海二道,北道出康居,南道为通印度诸港之海道。”冯承钧先生翻译了此书,并做了校勘史料、改错补漏、整合译名等工作,还对书中的文献资料添加附注,进一步提高了此书的学术价值,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后六十多年海峡两岸又有多家出版社多次重印。
《西突厥史料》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必读书,葛教授应该很熟悉。(据说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的《中国》第一卷的一幅地图上,标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名称,笔者未见原书。)1955年,季羡林先生发表长篇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重点论述中国蚕丝输入印度“有五条道路:南海道、西域道、西藏道、缅甸道、安南道”,南海道是季先生论证的首要路线。此文的论述“南海道”一节引用了《汉书·地理志》的“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这条最早的史料,论证中国蚕丝从南海道的“雷州半岛发船”输入印度。
1957年,季先生又发表论文《中国纸和造纸法最初是否是由海路传到印度去的?》,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与印度的海路交通问题。至于现今使用的“海上丝绸之路”一词,是日本考古学家三杉隆敏在昭和四十二年(1967年)出版的《海のシルクロードを求めて—東西やきもの交渉史(探寻海上丝绸之路——东西陶瓷交流史)》一书中首次使用。饶宗颐先生1974年6月发表的《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之中、印、缅交通》一文的《附论:海上之线路与昆仑舶》,研究了以广州为转口中心的“海道丝路”。
1978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航运史话》,在国内第一次记述了“海上‘丝绸之路’”。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陈炎先生从1980年开始进行“海上丝绸之路”专题研究,1981年在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交《略论海上丝绸之路》一文,是中国大陆学者发表的第一篇以“海上丝绸之路”为题的专论。1989年陈先生出版专著《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1996年又出版《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一书,在国内做出开拓性的贡献。
葛教授说“海上丝绸之路概念是日本的学者到上世纪80年代才提出来的”,不知道是否读过以上学者的相关论著?
不揣冒昧,直抒己见,敬待葛教授批评。
2018年11月27日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