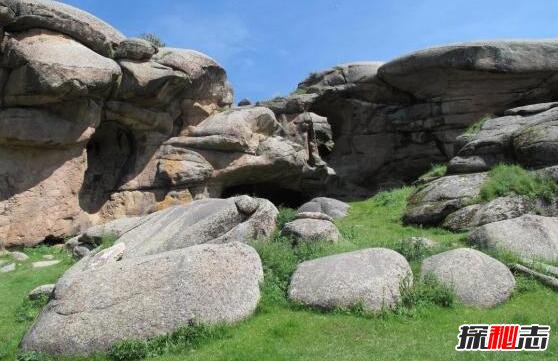章开沅:论史魂
史学寻找自己
这些年,我在海内外各地,经常讲的一个题目就是:史学寻找自己。
史学之所以需要寻找自己,是因为史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而首先是因为许多历史学者在不同程度上已经自我迷失。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屈原的《楚辞》招魂篇即已发出“魂兮归来,反故居些”的千古绝唱。直至本世纪30年代,偏僻的江南农村,由于缺医少药,还保持着“叫魂”的古老习俗。病者的亲属一人在自家门口反复呼唤:“××(病者小名)回来呀”!一人则在远处高声回应:“回来了!”其声摇曳凄惋,闻之令人心碎。特别是在严冬傍晚,这种悲切之声从远处传来,更增添天寒岁暮的几分苍凉。
如果不算夸张,我正是带有几分苍凉为史学招魂:“魂兮归来,反故居些!”
史魂即史德,用现代话语来表达,就是这个学科固有的独立品格。而与此相对应的,就是以史学为业者必须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
这绝不是什么空穴来风!我们的祖师爷司马迁,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即已给史学以很高的定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究,要通,才能有所成;也只有抱持一家之独立品格,才能究有所明,通有所识,而不至于人云亦云地“炒现饭”。去年冬天辞世的匡亚明前辈,认为孔子思想的可贵之处,即在于“提出了有独立人格、独立个性和独立志气的人的自觉”,讲的也是同一意思。
唐代刘知几也对史学与史学家提出很高要求:“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楩柟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旧唐书·刘子玄传》)清代章学诚肯定刘氏“史才三长”之说,但认为“犹未足以尽其理也”。他更为强调的是“史德”,指出:“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术以议史德,乌乎可哉?”(《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以著书心术论史德,堪称一绝,实乃大彻大悟之言,至今犹足以警世醒俗。
章学诚既强调“笔削谨严”,又强调“别识心裁”,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独立思考。他本人就是这样,当时人“纷纷攻击”《通志》,“势若不共戴天”的时候,章氏却挺身而出,再三为郑樵辩诬,申言:“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文史通义》卷五内篇五)
把引文的注释(“自注”)提高到史德(心术)的层次,章学诚亦能言前人所未曾言:“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智,且愈出而愈工焉。在官修书,唯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文史通义》卷三内篇三)
我们现在所缺少的,正是“辩心术以议史德”的高度自觉,所以敷衍塞责者有之,剽窃成书者有之,精品难出,膺著充塞,乃至在史学界也需要厉行打假扫劣。
半个世纪以前,法国年鉴学派的先驱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的导言中,用天真的小儿子的一句话作为开头:“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而这正是至今仍使我们感到困惑的一个问题。布洛赫极为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他说:“无疑,有人会认为孩子的问题未免太幼稚了,可在我看来,这个质问切中了要害。……一位年迈的工匠(布洛赫自称—…引者)扪心自问:花一生的精力来从事这行当值吗?这时,他心中难道不会忽然产生一阵疑惑吗?‘历史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已远远超越了职业道德之类枝节问题,事实上,我们整个西方文明都与之有关。”(此处用张和声、程郁译文,下同)为此他写了这本书,不仅是回答孩子的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回答学术界和整个社会的质疑。
我也有类似的经验。1990年秋天,在弗吉利亚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侄子到普林斯顿来探亲,经常开车陪我到远处旅行。年轻人性急,车速快而路又不熟,因此经常迷路。每逢这种情况,他必定问我:“我们在哪里?”于是我立即翻开地图,对照路标帮助他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确定继续前进的方向。如此反复多次,我受到某种启示,也不禁反躬自问:“史学在哪里?”
长期以来,史学走过的并非全是康庄大道。过去是政治干扰太多,往往使史学受损害太多,甚至湮没自己的本真。80年代以后,政治对史学已渐宽容,但又遭到商品大潮更为猛烈的冲击。过去,史学尽管受到这样或那样磨难,但史学工作者总算还有铁饭碗可端。现在的处境更为困难,简直是面临存亡绝续的严重关头。若干大学的历史系已经改办旅游系、旅游学院,有的考古专业则开珠宝古玩店,为数不少的年轻历史学者干脆下海或从政,真正专心致志坚持在漫无边际的史学海洋中执着远航的人,为数已经愈来愈少。加以现行学位制度与职称评定中存在着严重问题,学术领域的急功近利导致率尔操觚之作泛滥,而直接的或变相的抄袭之风愈演愈烈。
我决不认为史学现在已经是漆黑一团,史学仍然在困境中挣扎前进,优秀的人才与优秀的论著仍然在不断涌现,但消极的现象毕竟已经十分严重,我们怎能熟视无睹!最令人担忧的是,许多人已经不再注重史德或心术,而刻意追求的只是个人的眼前利益。“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者所以自谤”,正是这些人最好的写照。我郑重呼吁史学同行认真阅读布洛赫此书,他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全部书稿,便为反法西斯伟大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他为我们留下的是对民族与史学的无限忠诚,而这正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史德或心术!
治学不为媚时语
顾炎武与友人书曾云:“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日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者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亭林文集》卷四)以“采铜于山”与买旧钱以铸劣币相对照,与焦裕禄“别人嚼过的馍不香”寓意相通;就史学而言,则如同章学诚所云“笔削谨严”、“别识心裁”,然后庶几能得佳作。以亭林之博学多才,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一年“仅得十余条”,此《日知录》所以历经三百余年而魅力仍不稍减。
真正的学者与真正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都具有超越世俗的纯真与虔诚。工作对于他们来说,奉献更重于谋生,其终极目的则在于追求更高层次的真、善、美。唯有如此真诚,才能不趋附、不媚俗、不作违心之言。也只有这样的心术,才能获致“秽史自秽,谤书自谤”这样的觉悟。而现今专事剪刀浆糊、电脑拼接,剽窃之法日巧,附会之智愈工,以出书多而且快自炫之徒,对此能无愧怍?
对真善美的追求,不仅需要毅力,需要胆识,更需要大无畏的气概。孟子曰:“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这是我国数千年来士大夫的优良传统,也是真正的学者区别于政客、市侩的根本特征。真实是史学的生命,求实存真是历史学家无可推卸的天职,因此也就更加需要孟子所提倡的大丈夫刚直的浩然之气。
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题诗云:“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80年代以来,我常以此语自勉并勉励青年学者。我认为史学应该保持自己独立的科学品格,史学家应该保持独立的学者人格。史学不是政治的婢女,更不是金钱的奴仆。优秀的史学是民族的文化瑰宝,而且可以为全人类所共享,流传于千秋万载,这就是真诚的历史学者终生追求的学术永恒。尽管史学在社会暂时受到冷落,但历史学者千万不可妄自菲薄,必须保持学者的尊严与良知,以高品位的学术成果争取社会的理解与支持。我深信,除非是史学自己毁灭自己,只要还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存在,史学就绝对不会灭亡。何况当今真正的史学家何止一个,有的是一批乃至一大批。勇敢地迎接权势与金钱的挑战吧,史学与史学家。
历史的公正
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第四章“评判还是理解”一节中,提出历史的公正这一重要命题。
他认为有两种形式的公正无私,一是学者的,一是法官的。两者的基本共同点是忠于事实,但学者只限于观察事实并作出解释,而法官则必须依照法律作出裁决。学者的公正表现为尊重“与其最偏爱的观点相悖的事实”;法官的公正则表现为尊重证据而不管其内心倾向于何方。
古往今来,实现历史的公正或公正无私的历史,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很困难的。按照布洛赫的说法,史学家往往把自己的角色误认为是法官。“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布洛赫不同意这种作法,指出:“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加以绝对化,并以此去非难苏拉统治时期的罗马和黎塞留任枢机主教时的法国的道德标准,这是多么荒唐啊!而且,这种评判极易受集体意向和反复无常的个人爱好的影响,就没有什么比它更容易变化了。加上人们重视汇编荣誉名册,轻视搜集随笔记录,种种因素使历史学天然地蒙上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亲罗伯斯庇尔派,反罗伯斯庇尔派,发发慈悲吧!仅仅告诉了我们罗伯斯庇尔是怎么一回事。”我相信,当今中国读者对此都会产生共鸣,因为我们对于这种空洞的责难与空洞的翻案的游戏,已经是太熟悉了。
布洛赫的感慨是深沉的:“我们对自己,对当今世界也未必有十分的把握,难道就这么有把握为先辈判定善恶是非吗?”这又使我想起清代学者崔东壁所说的一段话:“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于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相度。往往径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考信录提要》卷上)可见,真诚的历史学者的心总是相通的,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国度。
东壁还为我们讲了两个“以己度人”的故事。其一: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大半为不能通车的山路。有个和尚急公好义,主动募捐修路,因布施者甚少,“乃倾其囊以成之”。这本来是损己利人的善举,但许多人却议论说:和尚原意是想借“多募以自肥”,只是由于捐款者少,才不得已而拿出自己的积蓄修路。其二:东壁本人在福建任内,“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其清廉为当地百姓与上官所深知。回故乡后,住在山村,每餐不过一盂饭、一盘菜,堪称清贫淡泊。但故乡之人反而认为是携有重赀而不愿露富。所以东壁慨叹:“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
我也曾多次讲过一个故事。吴县沈寿是清末民初刺绣大师,但体弱多病,家庭处境亦不甚佳。南通张謇担心其艺失传,不仅借宅供她养病,而且亲自协助她整理出《绣谱》一书。沈寿死后,张謇挽联极为沉痛:“真美术专家,称寿于艺,寿不称于名,才士数奇,如是如是;亦学诗女弟,视余犹父,余得视犹子,夫人为恸,丧予丧予。”稍知张謇者都了解,此人不是庸俗的市井商贾,他不仅在实业与教育两方面都有很大的抱负与成就,而且对文学艺术也有较高的素养与执着的癖爱。他在南通女子师范学校设绣工科,随后又创办绣织局与女工传习所,目的都是推广与发展沈绣的技艺。他还在南通创办伶工学社与更俗剧场,聘请欧阳予倩主持戏剧改良,嗣后又在剧场建梅欧阁并刊印《梅欧阁诗录》,大力奖掖梅兰芳、欧阳予倩这样的年轻表演艺术家。所以,当时京沪两地许多著名演员或后起之秀,都以能得南通张四先生的品题与墨宝为殊荣。但是1986年某电视台为纪念张謇逝世60周年而制作的电视剧《杜鹃啼血》,却把张謇与沈寿的爱情作为此剧的主线,看后令人啼笑皆非。这可能是出于票房价值的考虑,但确实使稍知张謇者有“以今度古,以己度人”之感,仿佛男人与女人关系比较密切就必定会谈恋爱,而下海从商的大老板更必定会“包二奶”。
60年代初年,我曾就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与《林则徐》故事片导演郑君里多次通信讨论。我认为历史学家应对文学艺术持宽容态度,在必然性与可能性的前提下,文艺作者应能拥有想象驰骋的广阔空间。但文艺家亦应尊重历史,应该充分研究当时当地的情、境、人、事,不可毫无根据地主观臆测。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应该尽量贴近其本来的性格、情操、心态,否则就不宜自称是历史剧。文艺家常常抱怨史学家在史实情节上的挑剔,这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史学家的职业规范。布洛赫说得好:“历史是历史学家的暴君,它自觉或不自觉地严禁史学家了解任何它没有透露的东西。在文献上没有记载墨洛温王朝时期的物价,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列出当时的价格统计表。”史学家并非出于忌妒而是由于谨奉“暴君”的指令,严格得近乎苛刻地批评文艺家在史实描述方面的随心所欲。但是,文艺家也不必对史学家绝望,因为布洛赫在同一本书中又说过:“历史学所要掌握的正是人类,做不到这一点,充其量只是博学的把戏而已。优秀的史学家犹如神话中的巨人,他善于捕捉人类的踪迹,人,才是他追寻的目标。”在对人的执着追寻方面,史学家与文艺家是否也有灵犀相通之处呢?
作为历史学家,布洛赫希望自己的同行不要扮演法官角色,但我们过去却长期习惯于用法官的眼光看待历史上的人和事。所谓“三七开”或“四六开”之类的功过区分,往往成为盖棺论定的套语。
这种传统来自古代史学的正统观。王夫之曾把它总结为:“论人之衡有三:正邪也,是非也,功罪也。”划分正邪、是非、功罪的标准,当然是统治阶级的价值体系与道德规范。但船山不愧为颇具史识的大儒,他反对简单化的两极评判,强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指出:“正邪存乎人,是非存乎言,功罪存乎事;三者相因,而抑不必于相值。正者其言恒是而亦有非,邪者其言恒非而亦有是,故人不可以废言。是者有功而不必如其所期,非者无功而功固已施于世;人不可以废言,而顾可以废功乎?论者不平其情,于其人之不正也,凡言皆谓之非,凡功皆谓之罪。乃至身受其庇,天下席其安,后世无能易,犹且谪之曰:此邪人之以乱天下者。此之谓不思其反,以责小人,小人恶得而服之?已庇其身,天下后世以安之而莫能易,然且任一往之怒,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小人之不服非无其理也,而又恶能抑之?”(《宋论》卷六)这番议论堪称至理名言,所谓“平其情”与“思其反”,都是史家应该特别注意的要领,否则便只能“效人之诃诮而诃诮之”,难以形成自己的真知灼见,自然也就无从寻求历史的公正。
值得注意的是,被船山贬之为“论史者之奖权谋堕信义”,而且“益鼓其狂澜而惑民倍烈”的李贽,倒是船山平情思反的同调。他不满于班氏父子讥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反驳说:“若必其是非尽合于圣人,则圣人既已有是非矣,尚何待于吾也?夫按圣人以为是非,则其所言者,乃圣人之言也,非吾心之言也。言不出于吾心,词非由于不可遏,则无味矣。有言者不必有德,又何贵于言也?此迁之史所以为继麟经而作,后有作者,终不可追也已。《春秋》者,夫子之史也,笔则笔,削则削,初未尝案古圣人以为是非也。”(《藏书》卷四十)而且他还认为“迁、固之悬绝,正在于此”。所谓此,就是前者具有旷古只眼的“独见”,而后者则不过是按古圣人以为是非的“文儒”。
类似的语言,我们可以在培根《新工具》一书中发现。作者在解释困惑人们心灵的“洞穴”等假象之后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被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他把出于先入为主的判断和凭依他人权威而形成的同意,斥之为“苟从与附合”;并且强调:“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培根还尖锐地批评了16—17世纪英国的各级学校与各种学术团体:“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经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若有一二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须是全由自己独任其事,不能得到有人相伴之益。而如果他们对此也能忍受下去,他们又会觉到自己的这种努力和气魄对于自己的前程却是不小的障碍。因为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中译本,商务,1984)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文化背景的三位思想家,在自主判断与学术自由方面的认识却如此契合,这除了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从中世纪走向近代或前近代)以外,主要还是由于他们都具有高度的学术良知。用我的习惯语言来说,就是学者的独立人格与学科的独立品格。没有这个前提,就谈不上什么历史的公正。
求实存真是历史公正的基础,努力贴近并维护历史真实应是史学家的职业道德。因此,由于史学家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他所厕身于其中的社会有许多现实因素对其工作产生影响或干扰,诸如社会心态、文化趋向、意识形态、权势干预、金钱诱惑、人际关系等等,他们需要有极大的勇气与毅力才能维护史学的自主与尊严。在我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至今仍然是比较敏感的话题。史学当然无从也不应脱离现实政治,但两者之间应是平等关系而非隶属关系。史学是在保持独立的前提下关注现实,其中也包括关注政治,而决不是供政治任意驱使的臣仆。在布洛赫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公正与社会正义的完美结合,捍卫史学尊严与捍卫民族尊严在他的生命中融为一体。因此,法西斯的子弹只能结束其肉体的生命,却无从阻遏其精神与学术通往永恒。
参考文献
[1][法]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2][英]培根:《新工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3]章学诚:《文史通义》。
[4]王夫之:《宋论》。
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1期
- 0000
- 0000
- 0005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