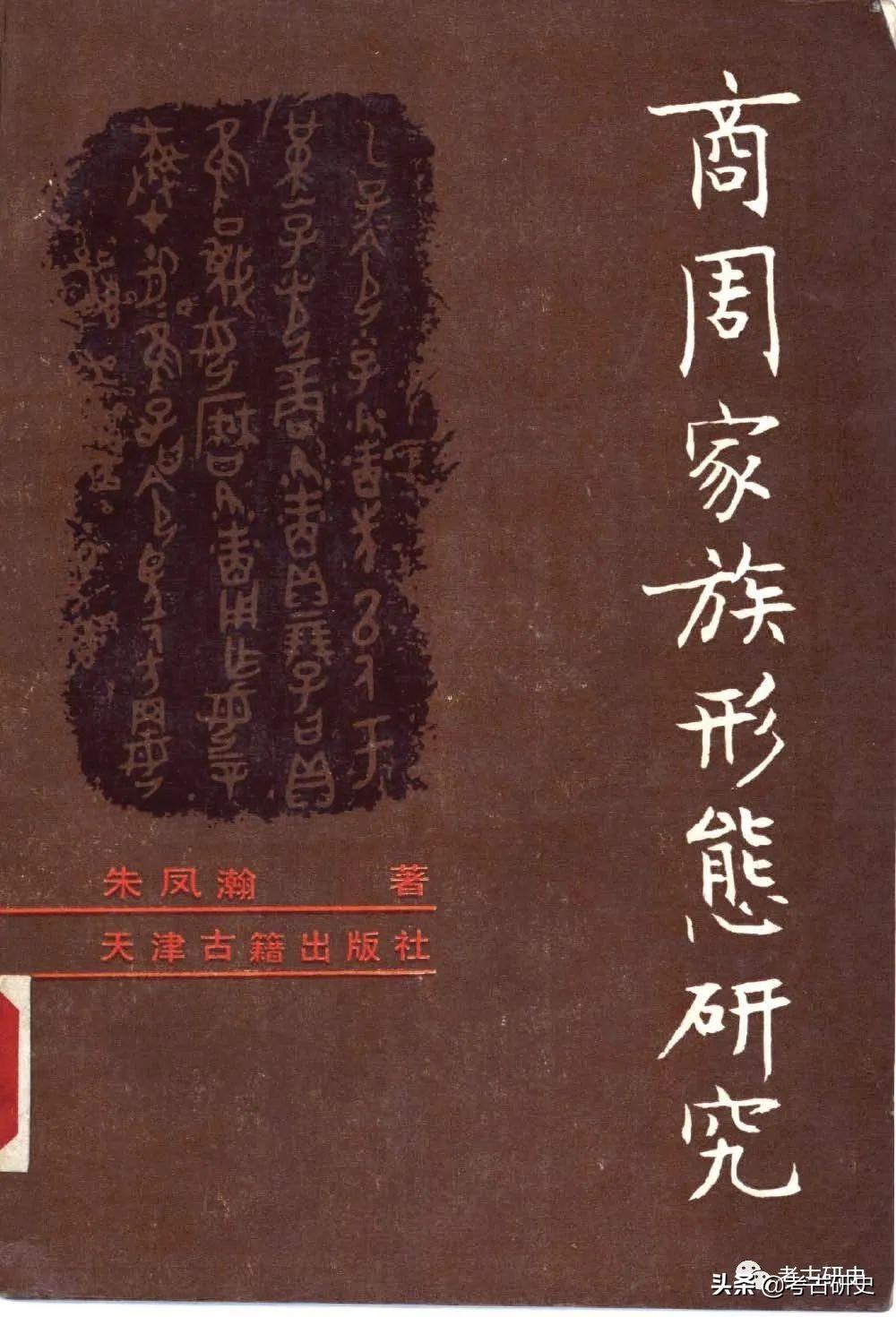黄颖:从十大考古新发现到金手铲——再谈考古知识的普及问题
◆用全新的眼光审视考古的价值
一年一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选结果又在众多考古学者的期盼中揭晓了。从12年前设立此奖项至今,该项评选已然成为中国考古学界的一大盛事,其在学界的影响和地位使得获此殊荣成为了无数考古学者尤其是年轻一代考古学工作者的光荣与梦想,并为此孜孜奋斗,埋首于不为外界所知的田野工作的第一线,艰辛自知,甘苦自品。有学者将考古比喻成一项在飞扬的尘土中于寂静中触摸历史脉搏,拼接历史骨架的工作,它是如此的寂寞而遥远,甚至有点“出世”之味,无怪乎在很多的公众眼中,考古学家被视作“荒郊野外间在一堆古旧的陶片中寻寻觅觅的白发老人”,这一形象定位多少有那么点让人啼笑皆非,也许考古离常人的世界真的太遥远了。值得庆幸的是,迄今已步12届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评比活动为考古学工作者创造了一个从幕后走向台前的大舞台,这种将在别的行业如体育、影视、商界已多见的评比意识的引入不能不说是考古学界推陈出新的一大举措,几者虽不可同日而语,但本质上相似的在于一种竞技精神的引入,以一种新的眼光和价值观来审视自己的存在价值,这对于增强考古发掘的活力、提高发掘水平和增进考古学发展的动力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英国“考古学奖”的主要用意是普及
看罢国内,不由联想起前些时候看过的其他国家有关的考古评选活动,似乎印象最深的倒要算是英国“考古学奖”了。这个从19世纪就开始科学考古的老牌国家,在评选活动的机制和运作上也可为人称道。且看一下其所设奖项和奖励对象:金手铲奖——奖励某项考古技术新发明;重要学术贡献奖——奖励某项开创分支学科研究的新领域;英国遗产奖——奖励在长期保护古建及纪念物中作出贡献者;钢铁大桥奖——奖励对古建进行合理再利利用并作出成就的项目;其他还有考古著作奖;最佳广播节目奖;考古新闻奖;普及考古知识奖;考古俱乐部奖。纵观这些奖项,着眼于从手段与方法的创新、研究与保护的进步、如何使考古学走近公众三个层面来设立。奖项的名目和体系本身实质上蕴涵了更深层次对于考古学自身定位和价值观的取向的思考,并将之物化为一种外在的形式以便于倡导和传播。尤其值得注目的是后4大奖项的存在,似乎“考古之外”或者说“考古后续”的故事在此演绎得相当浓墨重彩,占据了近半的笔墨,而其用意直指二字——普及。我国十大考古发现的评比是个举措,它搭了个台,让考古发现粉墨登场来唱戏。和一些国家如英国相比,虽则中国目前所有的奖项如考古发现奖和田野考古奖也颇具特色,但尚未加以如此系统化和层次分明,而且至少从奖项设立而言在普及上下的功夫太少。一来这奖的评比还是专家坐镇,学术把关,属于单学科的内部消化,外界包括大众知之甚微。二来,这评比结果除了是对那些艰辛可敬的考古学者工作的肯定外,是不是能为考古学尤其是普及工作创造更多现实价值。也就是说,评比活动的意义应该超越结果本身,而提升至一个向外宣传普及考古知识的窗口和扩大考古发现影响的契机。三来,从学科的内涵和外延来看,考古发现毕竟只是个基础,对它的介绍也只能是普及工作的初始一步,从这一点说,我们要走的路还很长。
◆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
“普及”二字,《辞海》如此释义:普遍地传播和推广,普,全面广大。《墨子·上贤》云“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易·乾》载“见龙在田,德施普也。”要传播,使得对主角的特性多加琢磨,以方便对症下药。多见学者讨论文物的特性,却少有人思考考古发现的特性所在。笔者不惴浅陋,以为考古发现所具之现实特性有如下几点:
第一、具象性,有人称其为“触手可及的过去”,意盖于此,它以具体、生动、形象的物质形态再现了业已消逝的人类历史,将人类童年的梦想复原得何其逼真,如此次位列十大发现的青海民和喇家文化遗址中所见的灾难场面,足以使任何的有关历史的真实的言辞汗颜。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能起到历史再现功能者舍考古发现而其谁?同时这种特性也是它有别于很多其余门类发现如哲学、物理、化学等的物质基础所在。其次,考古发现的时代特点和特定的时空属性又赋予其通常所说的历史性、不可替代和不可再生性等特征。
除了上述这些客观属性之外,需要强调的是考古发现所具备的情感属性和由此带来的社会属性。正如未来常常令人憧憬与遐想一样,渺远的过去同样吸引与困惑着人类,而考古发现正是谜底所在,好奇心在此得到满足,困惑与迷惘在此得以消除,考古发现以无言的方式调适、平衡与安抚着人类那越来越敏感的心灵。如此,它便又滋生出一些别样的亮点,而且越来越得到张扬。
如时效性,这一点体现在“新”字上,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为考古发现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潜力和发展空间。
神秘性,在大众眼里,考古发现往往被与探险、历奇、寻宝联系在一起而具有了神秘的特质。
轰动性,考古发现的新闻轰动效应独一无二。
震撼性,重大考古发现给人视觉与心灵所带来的冲击谁能否认,如敦煌壁画之辉煌绚丽、兵马俑之磅礴气势、民和喇家文化遗址中大难临头母子相拥之感人,怎不叫人动容。
正是考古发现所具有的这些特性,才为其走近大众,普及推广至社会创造了前提条件。
可能性是基础,可行性却是关键。50余年的中国文物考古成就,曾与我国航天事业和体育运动一起被海外并列为最令人信服和惊异的三大成功,在世界上享有无可争辩的赞誉。但是,“墙里开花墙外香”,海外知之者多,海内知之者少;行内知之者多,行外知之者少;专家知之者多,百姓知之者少。考古发现乃至于考古学犹如娇小姐般“养在深闺人末识”,在这个人人思变的信息时代,是引领这位小姐走出闺房,走近大众,走向社会的时候了,也让昔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一言概之,考古亟需“入世”。
◆让考古“入世”的尝试
最近出现了一些这方面的尝试,归纳起来可分为几种:
其一,由文博部门牵头,与有关单位合作举办的各种学术讨论会与社会宣传活动。如2000年由国家文物局主办的“文物保护世纪行”活动;《中国文物报》社与《光明日报》联合举办的“城市发展中的城市考古和历史文化名城学术研讨会”等。
其二,新闻媒体的直接介入,包括现场直播和新闻报道等形式,如中央台对老山汉墓发掘的直播、浙江卫视对桐乡新地里良渚墓葬群发掘的直播、上海电视台随同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考古队赴重庆录制三峡考古的专题节目等,报纸上有关考古发现与发掘的报道更是日见增多,且不谈在这些报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如炒作之嫌,谁能否认随着考古上镜率的增多,它正从想象的云端渐渐降至现实的国度,成为眼可见耳能闻的过程,考古学家也脱掉了白发苍苍的龙钟面容显露真实可亲的学者风范。
其三,考古学通俗读物的出版和发行。最近见着原本亦颇严肃的历史学界在史学的社会功能和社会普及的探讨中提出了“史学的消闲功能”一说,不由令人感触。培根有言云:“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此言可谓真灼。有很多睿智的考古学家早已以身作则,如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便是一本以简单而形象的语言系统表达其毕生研究的传世之作,以先生自己的话说,这是“一本我的大众化著作,把我一生所知、所得,简洁地说出来”,老人家为考古科学化和大众化所作的贡献令人景仰。近来又喜见一批融雅趣与俗语、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体的图文并茂、雅俗共赏的考古读物全新登场,如由王仁湘主编的《华夏文明探险丛书》,被张文彬局长誉为“近年普及考古学知识和宣传考古学重大发现及研究成果优秀著作”,还有齐东方的《走进死亡之海》、李伯谦等编著的《考古探秘》、陈立基的《趣说三星堆》、王天权主编的《震惊世界的考古大发现》系列丛书等都是为考古走近大众牵线搭桥的可荐之作。
其四,与企业联合,如“2000年十大发现”中的成都酒井坊遗址就与四川某酒业集团合作,以发现为企业树形象,以企业为发现造声势和实际效益,这也是考古发现与社会地方经济发展相结合的可喜尝试,值得借鉴。
其五,网络传播。如国家文物局主管,《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中国文物信息网”是作为文物信息传播的专业网站也为考古信息发布打开了一扇窗口,但考古只是其中一块,而且多为考古发现和相关活动信息的公布,未有系统专业的考古网站。
以上列举均是考古知识和考古发现走向社会大众的可喜尝试,但存在的问题是以上形式多是一种单向的知识传输型,受众多处于被动的接受地位,而未曾营造公众主动了解、积极关注甚至亲自参与的全民意识。如在丹麦,平均每100个公民中就有1个人订阅考古杂志,而日本的考古发掘中多见经过培训的志愿考古者的身影,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与自觉乃至自在的对考古学的理解、关注和浓厚的情谊血肉相联的。当然,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很复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我以为其中相当关键的一环在于社区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社区——中国考古普及工作的盲点
社区本为一社会学概念,最初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Tonnies 于1881年提出,描述一种以礼俗为特征的社会团体,在后来的社会学文献中,被广泛运用,以分析人类社会的空间与地域结构,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的解释,社区就是“通常指以一定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至少包括以下特征: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并有较密切的交往。”社区没有统一的规格和模式,它可大可小,存在着不同的层次和内容,小至一条街道、一所学校,大至一所城市、一个国家都可包括在内。考古普及的社区化在日本很受重视,日本的考古普及多以町为代表的社区开展,并纳入社区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中,在社区的会馆中进行类似于考古发现发布会的展示活动,展示社区周边地区的考古发现或者邀请附近社区的此类展览,并散发简易的宣传单,如爱媛县越智郡大西町在1994年的“町民祭”节日活动中就包含了妙见山古坟发现的展示与介绍活动。
正因为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是认识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最佳途径,因而近年来社区及其建设正成为社会学家关注的热点,并正逐步转向社区文化的建设,所谓社区文化在社会学上是指“通行于一个社区范围之内的文化现象。包括社区内人们的信仰、价值观、行为规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地方语言和特定象征等。社区文化是构成社区的重要因素之一。社区文化是社会的地域特点、人口特性以及居民长期共同的经济、社会生活的反映。”
通俗点讲,社区是社会的子体,社会大众的生存之所;社区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次文化,是大众直接呼吸的文化空气,因而要想使考古走进大众,就得在形式上走进社区,内容上渗入社区文化。目前中国的社区文化活动中多为群众文化甚至群众文艺活动,在深度和广度上尚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发展,也为考古普及的社区行为提供了巨大的渗透空间。
具体而言,在形式上可以以图文声像等辅助手段进行考古发现的现场发布,普及首先是一项宣传工作,因而首先必须有吸引人的亮点,而发现所具的实物性和神秘性恰好符合了人固有的好奇心,此其一。一旦该发现在地域上属于所在社区或与社区的某项文化传统、习俗故事有所关联,那效果更佳,如此次十大发现可以在各自所属省市乃至社区内开展类似的展示活动。注重将过去与现实相连接,或者说将原本古旧的考古发现与百姓现有的某种知识和情感联系起来,例如说“甑”,“就像现在的蒸笼”这种解释恐怕比咬文嚼字的“古代炊煮器”更有用。因此,所用语言越通俗越好,此其二。第三、不妨在造声势上多下点功夫,这就涉及到如何合理而充分地发挥媒体宣传的作用,在学科允许的尺度内多见报多上镜,媒体渠道打开了,最佳节目、最佳新闻乃至“考古普利策奖”这种品牌奖项的出台也便水到渠成。第四、网络技术的出现使得“虚拟社区”成为实体社区内涵和外延的拓展,因而也应将考古信息传播渗至网上社区的建设之中。
新近,复旦大学文博系在田野考古发掘实践和学术研究创新的基础上,又在考古普及的理性思考和具体实践上多有建设,尤具开创性的是在考古普及的社区化导向上勇拓新路,隆重推出了一场立足校园区域面向大众走入社区的考古主题展,别开生面。考古展览的制作和展出这一形式可谓独树一帜。往常至多在博物馆里见着一幅考古发掘现场的图片,也是作了器物的陪衬,而专门为普及考古发现和考古知识度身定造的专场展览鲜有耳闻。复旦大学文博系考古队自1999年起4次赴重庆库区以教学实习形式开展考古发掘,每次实习结束返校后都由学生动手制作展览置于校宣传栏,一届一度,交相接力,从未间断,大大拓展了考古学在校园的呼吸空间,“三峡考古展”已成为文博系考古队的校园形象代言和特色品牌。观展者如织,留言者如云,考古的实体效应、情感效应和社会效应由此发挥得淋漓尽致,着实在校内乃至校外掀起了不小的观潮,为考古普及的社区走向和社会目标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以展览为先导,更可进一步续之以考古沙龙、考古知识讲座、有奖知识问答、普及读物音像制品和纪念衫赠送、发售、短期考古志愿者招募、荣誉队员评选等活动,甚至可以以社区为单位举行全国范围内的“我眼中的十大考古新发现”有奖评比,在考古走向大众的基础上,更吸引大众主动走近乃至走进考古。
◆亟待引入的标识品牌意识
普及活动说到底是一种信息传播行为,因而必须符合传播学的行为准则和方式,从这一点而言,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特征化传播标识或者说品牌的创立。标志作为一种特定的视觉符号,是事物形象、特征的综合与浓缩,从这种角度来看,标志不仅是一种代表符号,而且是沟通主体与受众、专业与社会最直观的中介之一。标志具有符号化特点,人们为了传播信息而创造符号。为此,标志的本质是信息传递,这是现代标志设计的核心。从功能需要为出发点,明确标志设计的内涵,这是现代标志的重要前提。这个时代是标识和品牌意识的时代,各行各业都在树形象立品牌。如电影有金像奖、金鸡奖、金马奖,琅琅上口,耳熟能详。考古普及也应与时俱进,引入标识品牌意识,塑造自己的品牌标志。为使标志具有独创性,用言简意明的要素完成视觉传达任务,在设计中应遵循下列原则。(1)图形识别化,即先营造一个特有的图形识别体,把标志想要传达的意念表达出来。(2)标志个性化。标志的功能之一,是传达独特个性。因此在设计上必须匠心独运,使标志富有特色,并且通过不同的标志表达不同的特点和格调,使人们看到标志后立即能联想到所指主体。(3)图形简洁化,易认易记,在信息视觉化过程中以最凝炼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涵。
从这些标准出发,再结合考古学科特点,笔者要再次提及金手铲奖。手铲乃考古发掘必需之物,犹如战士之钢枪,诸多著名考古学家都视手铲为考古学根基之象征,在论述中每必提及,如张光直先生言:“考古学的理论必须适应于考古学家用手铲挖出的古代的物质遗存。”英国以之命名技术与方法创新奖,用意也在于此。所以以金手铲为考古标识品牌当真不失为一计。显然,“金手铲奖”听来要“入世”的多了,接过一把“金手铲”之时,是否也如“金像奖”般更令人瞩目呢?它的内涵的推敲自属学科内部之事,但作为学科的对外形象自当让入耳目一新,印象深刻。当然,此仅为一种方案,中国考古丰富的特色与内涵赋予了形象标识无限可能性,首要之处在于学界自身观念上的认同。
与形象标识相当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尚有一层——意识标识。考古与大众之间的距离很远也很近,路是人创出来的,那路的尽头是什么呢,或者说考古普及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呢?我想最终一切都要回归到一种意识境界的提升与升华,即唤醒人类对过往的认识与尊重,对文化遗产的珍惜与爱护,最终实现人与环境,包括自然的和文化的的和谐共存。在这一点上,自然环境保护所经历程颇可借鉴。人类需要家园,他们向自然索取生存家园,却忘了还自然以尊重和爱护,自然环境污染愈演愈烈,于是以“绿色环保”为口号的环境保护运动警醒于世,环保意识与行为发展至今,已卓有成效。而相似的命运又降临到文化遗产身上,人们从过往索取心灵家园,却不思还过往以尊重和爱护,文化环境损毁屡屡可闻,文化遗产破坏视若无睹,心多焦虑。近蒙大家启发,得“古色文保”一词,意在以此为标识大力传播文保意识,并期待一场全民动员的文化遗产保护运动,考古普及与社会化的最高境界恐也不外于此。当一日,“古色文保”如“绿色环保”之深入人心并行之有效之时,考古学离更深远意义上的“黄金时代”便也近在咫尺了。
来源:《中国文物报》
- 0000
- 0000
- 0000
- 0002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