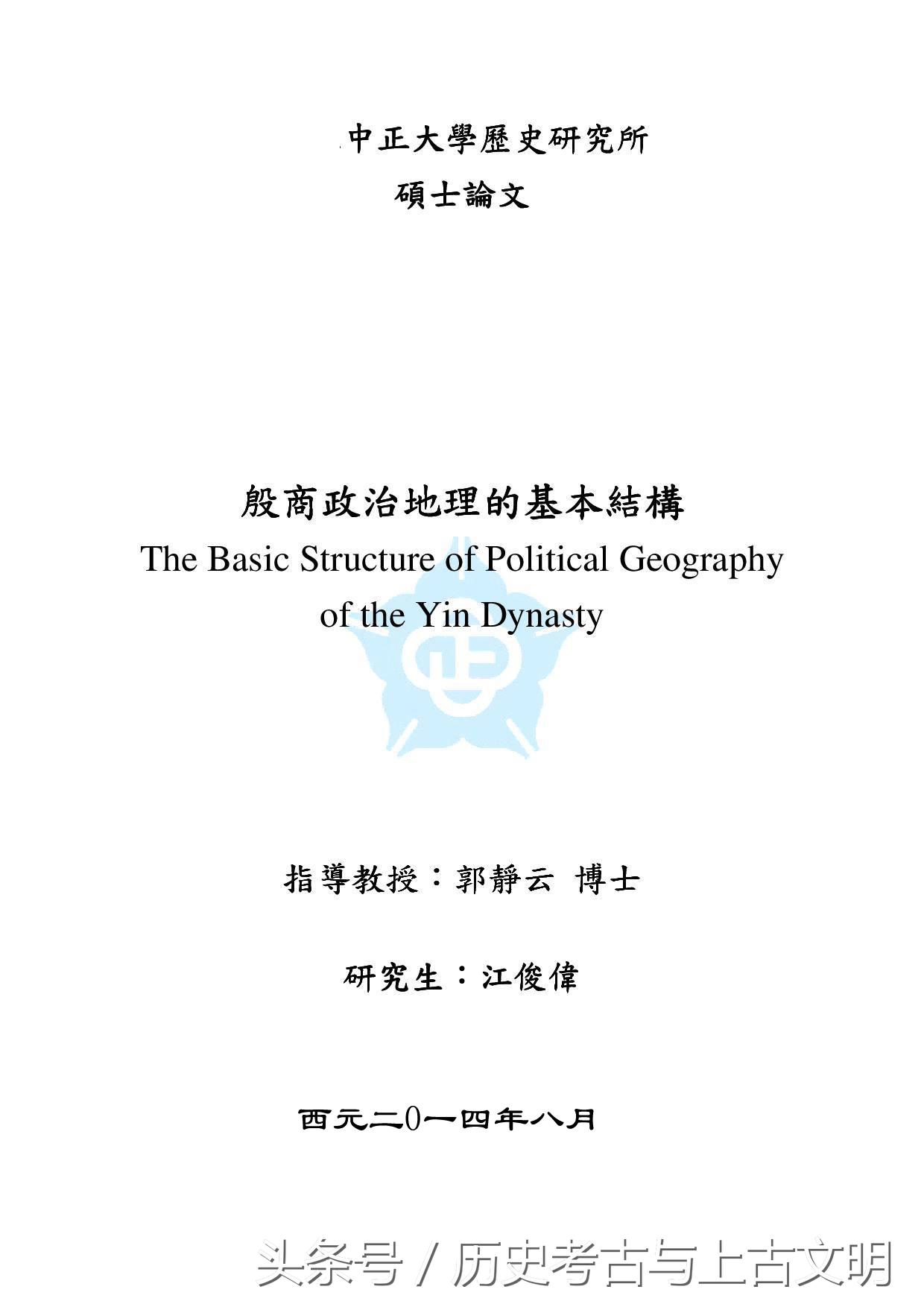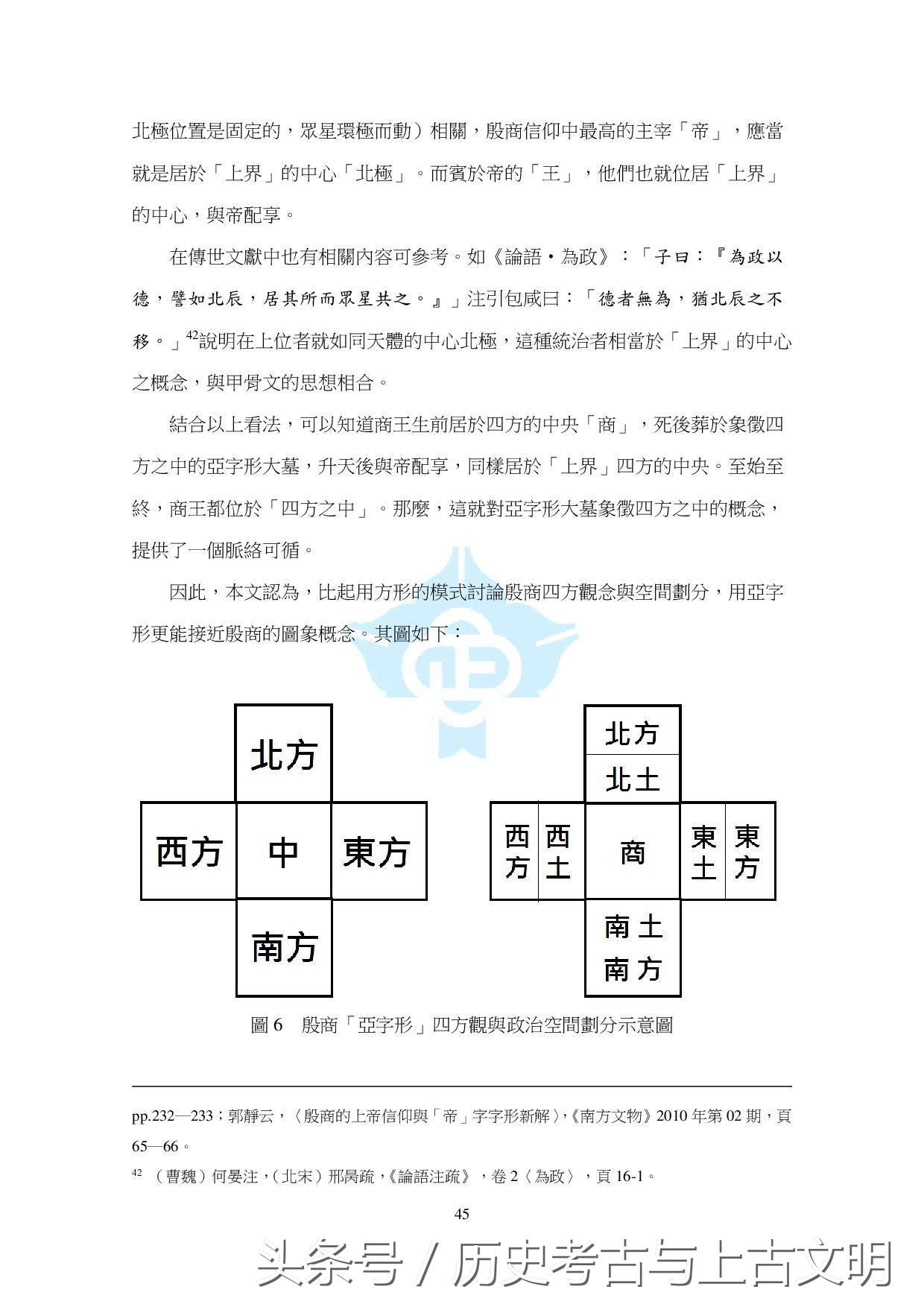王玉哲:西周国家的历史作用
我们认为夏和商的前期,阶级和奴隶虽然都已出现,但阶级矛盾尚未发展到不可调和的程度,依照恩格斯对“国家”特征的学说看,那时统治者的政治机构,只能说是“国家”的原始雏形阶段,还不能称之为正式的“国家”。何兹全先生也曾说过:“由阶级出现到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由国家萌芽到国家产生,有一个过程,而且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不是一有阶级就是阶级社会,就产生了国家。”(注:《关于古代史的几个理论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1期。)这话说得极有道理。从中国的具体历史看,一直到商朝末期,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才逐渐达到你死我活的阶段,“国家”也从长期量变达到质变,正式、成熟的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应运而生,负起了对社会应有的责任。西周这个正式国家也未超过初期阶段。
“国家”这种新的机构产生之后,它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国家”对社会发展起过什么作用?这是历史学家责无旁贷、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国家,建国以来历史学界确实有不少学者,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新观点,对国家的历史作用进行过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对西周国家政治的机构、军队的组织、监狱的设施、刑法的渐密等等,不但有不少研究论文,而且还有一些专著,对国家机器如何对人民大众进行统治和镇压,作出了详尽而完整的描述,这个成绩是巨大的。
但是,“国家”既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又能长期久远地存在下去,那就可能有它历史存在的合理性。过去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对“国家”这个统治、镇压人民的机器,往往只强调了国家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这一方面。国家机器对社会的发展,难道就一无可取之处?事实上恐怕并不是这样。
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一般事物的看法,都是一分为二的。对“国家”的作用,既要看到它对人民的镇压方面,也要看到它对社会发展起过的正面好的作用。关于西周“国家”的进步作用,据我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
第一,国家的出现,挽救了社会不致毁灭。人是群体的动物,离开群体,个人几乎无法生存。原始社会时期,个人是依靠氏族血缘组织的群体(或名共同体),到阶级社会就依靠由武装、政治力量组成的“国家”的保护而生存。另外,“国家”对人类的生存、社会的延续,还起过挽救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在原始社会的末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导致出现了阶级和阶级矛盾,而且劳动者与剥削者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矛盾会越演越烈,达到无法调和的程度,最终酿成阶级之间的战争。劳动者所生产的一切物质财富,都被战争破坏掉。又由于长期斗争或战争的影响,劳动人民失去了从事生产的环境,变成一个只有破坏,没有生产的社会,这是很危险的。假如长期这样下去,两个对立的阶级连同社会,势必会同归于毁灭。只有在“国家”出现后,“国家”的武装与政治力量促使矛盾双方以相互有限度的让步和妥协来打破僵局、形成某种平衡,从而使阶级矛盾维持在“相对和平”的阶段,社会才能继续向前发展。恩格斯就曾明确地指出:“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6页。)由此可见,国家机构挽救了社会的危亡,其历史作用之伟大可以想见。
第二,建立了有利于生产的“和平环境”。人类的历史,主要应是生产劳动的历史。人类可贵的精神,就是不断的生产劳动的精神。如果没有这一宝贵的生产劳动精神,人类将不成为人类。离开这一宝贵的劳动精神,人类一切文明的光辉都将熄灭,人类将永远停留在野蛮、蒙昧的境界。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曾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又说:“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甚至还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注:《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08、513页。)这就足以说明人的劳动之可贵了。但是, 生产劳动必须具备一个劳动的环境。若天天处在残酷的战争、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如何能进行生产劳动?这是极为明显的事实,无须多论。所以,凡是能给人以劳动的环境、给人以劳动条件者,起码的前提是使阶级矛盾限制在相对的“和平”阶段,生产劳动才有可能。国家机器对劳动人民除了镇压一面,还有创造“和平环境”以利生产的一面。并且,这才是“国家”职能的主要方面。即便专从统治阶级利用国家机器对人民镇压的目的上论,也同样是为了“和平”。因为劳动人民只有在和平环境中才能生产物质财富,社会中有了物质财富,统治阶级才能进行更多的剥削。因之,国家创造“和平”环境的目的,虽然不光彩,但客观上,其历史作用的进步性是不能抹杀的。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所说的“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就是说的“国家”起到缓和阶级矛盾的作用,使社会出现相对的、有秩序的、可借以从事生产劳动的环境。许多古史研究者对恩格斯这句名言,不知征引过多少次,但对国家这方面的历史作用并未提高到应有的重视程度。据我所知,只有晁福林先生首先明确地运用恩格斯这段“缓和冲突”的理论,说明了殷周时期“国家机构的职能主要应当是两方面的,一是镇压,二是调节。……国家机构通过调节各集团、各阶层的利益和关系,以缓和冲突的作用,远比后代为甚”。又说:“其主要职责是联合,而不是镇压。”(注:晁福林:《试探商周史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见《天津社会科学》1988年第4期。)这种论断可谓卓识。
社会各阶级在激烈斗争之后,只有协调、联合起来,在相对的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劳动,社会才能发展,文明才能昌盛,人类才能延续下来,这是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
法国有位文学家叫莫罗亚,写过一部《法国战败了》的书,还写过一部《英国史》。这两部书曾轰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读书界。莫罗亚有什么神通,竟能使其著作发生如是其大的影响?60年代时,有学者认为他是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通过主观的取舍,选择了丰富的合于自己口胃的史料,用来证明英国人民的历史绝对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阶级协作的历史;莫罗亚歪曲了历史的真相,借此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的目的,“莫罗亚的反动技术,可谓巧妙已极,其为害就更厉害。” (注:李亚农:《欣然斋史论集·总序》, 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9—20页。)对莫罗亚的这种批评对不对呢?我认为只说对了一半。莫罗亚是资产阶级学者,夸大了国家机器所具有的阶级调和作用,而掩盖了其残酷镇压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否认,他的著作也含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的一方面。他是不是正确地抓住了国家职能的“协调方面”,并以文学家的叙述故事的天才,娓娓道来,非常动听,从而具有了极大的吸引力呢?我们应做具体的分析,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
资产阶级史学有时也包涵着朴素的唯物主义因素,不管莫罗亚本人意识到没有,他看到了资产阶级“国家”具有协调的职能,这就在客观上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一致。
第三,负有对社会事务管理的职能。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而社会则是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的共同体。人类的生活既是社会性的,自然就会产生很多共同的、必不可少的事务,如共同的社会秩序、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等。这就需要有专人或专职机构去负责管理。任何社会概莫能外。
在原始社会时期,社会的管理是由原始民主制的氏族机关承担。进入阶级社会后,经济发展日盛,社会关系益形繁杂,社会事务愈来愈多,这就更需要有这方面的专门管理。“国家”就成了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
前面说过,国家的职能对劳动人民除了统治、镇压的一面,还有创造相对的和平环境以利劳动人民从事生产的一面。在此,我们还应当再举出国家负有对社会的经济、文化、教育以及环境卫生等方面的事务管理的职能。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只是片面地谈论国家机构对劳动人民的镇压,至于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职能则很少人论及。只是近年政治理论界才有一些学者提出讨论(注:例如陈炳辉:《国家的管理职能新探》,《福建学刊》1991年第3期;王振海:《论国家功能》, 《东岳论丛》1995年第6期;王作印:《国家社会管理职能初探》, 《洛阳师专学报》1997年第6期。)。其实马克思、 恩格斯并不是把对人民的政治统治职能看成是国家的惟一职能。马克思在论述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的同时,也多次地论述了国家还具有社会管理职能。例如在其名著《资本论》中,论述国家职能“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2页。)。所以, 探讨国家的职能必须注意其具有的这两重性。当然,这些具有进步作用的职能从根本上讲,也同样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第四,对大一统的中国奠定了基石。夏、商时期,以华夏为中心的“天下”,由氏族结合与武力合并,逐渐形成了松散的方国联合共同体。到西周开创、推行分封制度后,大大地加强了天下一家的观念。
周武王以“小邦周”姬姓氏族为中心的军队,与其它众多氏族、部落和方国的联盟大军,合力摧毁了商纣的军队,建立了西周王国。初期的周王国是以“盟主”的地位与其他“友邦”联盟的关系,这和过去夏、商时的所谓邦国联盟式的“国家”形式是一样的。周武王所建的这种初期的王国,与各地方上的诸国是同盟的关系,地位上几乎是平等的,没有什么君臣尊卑、上下的观念。所以,到武王死后,武庚、三监及东方各诸侯发生了大规模的破坏统一的大叛乱,周公率军平叛三年,才把乱事平定。为了巩固周王的政权,使之长治久安,周公才从夏、商、周的兴亡历史中总结出历史经验,创立起一套新的分封制度。
西周的国家运用这套分封制度,更充分发挥了国家机器缓和冲突的职能,起到协调联合的作用。如对异族武力征服之后,即想方设法予以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如对于齐国故地的大批殷遗和莱夷,“从其俗,简其礼”,从而使其民“归之”(注:《史记》《鲁周公世家》、《齐世家》。)。周公命康叔在卫国要实行“义刑义杀”,要“明德慎罚”;周人犯酗酒罪即“予其杀”,而对殷遗,念其旧习一时未能遽改,则“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注:见《尚书·酒诰》。)。其它如对殷遗较多的鲁、卫二国,则命“启以商政”;对封于戎狄环绕的夏虚之唐叔,则命“启以夏政,彊以戎索”(注:见《左传》定公四年。)。其因地制宜对待已服之异族,其为缓和冲突、重在联合的用心可知。
周公制定的分封制度,目的在于“封建亲戚,以藩屏周”(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或谓“并建母弟,以藩屏周”(注:《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可见周初受封的诸侯,主要的是周之王室姬姓大宗族中之子弟和异姓功臣。据说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注:《荀子·儒效篇》。)。这些姬姓同族子弟之分封,是依据宗法制度所规定的“嫡长子继承王位,余子分封外地”的原则分封的。在宗法体系中,周王是姬姓大宗族中之族长,称为“宗主”或“宗子”,其后嗣世代的嫡长子则为世代的“宗子”。这一系列的支族称为“大宗”;世代的次子、庶子为“小宗”。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有权传宗接代,地位自然高于次子、庶子,也就是“大宗”高于“小宗”。由周王分封的诸侯和卿大夫,大都是王的次子、庶子,也就是小宗,小宗对大宗有尊从的义务。所以,周王与诸侯构成双重关系:一方面,从政治上说,周王是各地被封的诸侯的共主;再一方面,从宗族礼俗上说,诸侯既为小宗,就必须尊从周王这个大宗。有的学者指出周的国家政权与宗族组织水乳交融,因而构成“周王室具有宗主国的崇高地位,诸侯形同一个个卫星国,对王室有强烈的向心力,形成了拱卫王室的局面。同时,周人还创设了一系列制度以维系这种政治格局。因此,周代(特别是西周)的诸侯国只是相对独立的国家政权,对宗主国周王室有多方面的从属关系”。又说:“周王国与诸侯国的纵向联系和诸侯国之间的横向联系空前加强,为后来封建统一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注:周苏平:《周代国家形态探析》,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下册,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7页。)这种分析、 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周王室对异姓诸侯的联系,虽不能利用血缘性的宗法制度,但同样也可以用分封制度与之联合。因为分封制度主要的内容是“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注:《左传》隐公八年众仲语。)。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赐给被封者以人民和土地,并承认其建立一独立的分族和国家。立国必须有土地和人民,如周初鲁、卫受封,就由“聃季授土,陶叔授民”(注:《左传》定公四年。),西周康王时铜器也有“受民受疆土”的铭文(注:《大盂鼎》。)。但这决非周王室单方面的无偿奉送,在举行受封典礼时立有盟誓,载明周王与受封诸侯之间,不管是同姓或异姓,都要建立主从关系。异姓诸侯也同样可以建立一个半独立性的国家政权,有其独立的军队、独立的刑政,只有在礼节上与同姓诸侯的先后排列次序稍有不同,“周之宗盟异姓为后”(注:《左传》隐公十一年。)而已。所有被封诸侯,对王室都负有贡献的义务。如春秋时齐侯以诸侯之师伐楚,楚人质问为何伐楚,管仲即以楚对周室久未贡包茅为由。而楚也感到理亏,答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给。”(注:《左传》僖公四年。)春秋时郑子产也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注:《左传》昭公十三年。)东周人说西周事,应当是可信的。足见诸侯纳贡于王室,是周制规定被封诸侯不可回避的义务。周王室对诸侯还有征役的权力,如东周敬王就说过,周成王的东都成周是令各诸侯国派出民役,合力筑成的(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载周敬王说:“昔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
另外,从春秋时的史料看,周室有难,诸侯还有勤王的义务。如周襄王以戎难告急于齐,齐令诸侯各发卒戍周(注:见《左传》僖公十六年,《史记·齐世家》,《左传》僖公十三年。);周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也曾征诸侯兵戍周(注:《左传》定公六年。)。王室有内乱,诸侯有出师平乱的义务。如周襄王时有王子带之乱,周敬王时有王子朝之乱,均赖诸侯之兵,勤王勘乱(注:周襄王事见《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二十五年;敬王事见《左传》昭公二十二——二十六年。)。据说诸侯对周王还要按时朝聘(注: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襄公二十四年,僖公十三年,襄公二十六年;《国语·周语》。)。战国时孟子甚至说:“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注:《孟子·告子下》。)这些都反映春秋时诸侯对周室应负的责任和隶属关系。春秋时周室已衰微,而周天子在诸侯的心目中尚且有如此威信,则当隆盛的西周时代,周天子的地位自可想见。
总之,周王与各诸候之间的关系,自从周初实行分封制度以来,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大变化,即由过去夏、殷之王以诸侯之“长”或“盟主”的身分,至周则一变而为诸侯之“君”,诸侯对周王是从属关系,毫无平等之可言。这一大的历史变革,近代有些学者早已洞察到了(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一○;晁福林:《试论西周分封制的若干问题》,载陕西省博物馆编《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45—757页;周苏平:《周代国家形态探析》,《西周史论文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31—744页。)。这是西周“国家”政权推行分封制度的结果。西周王室与各地诸侯建立的虽然是不平等的从属关系,但另方面却使时人心目中构成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整体,使各地居民对周王室有一定的向心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广大群众也逐渐形成了“中国”天下一家的观念。春秋时人已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注:见《论语·颜渊》子夏语。)的思想,其根源亦应上推到西周。
西周这种大一统的初步格局的形成,使中国历史后来所走的道路与西欧古史便完全不同了。西方古希腊、罗马当时实行的是松散的城邦联盟,加盟的城邦诸国都有很大的自主权。所以,联盟的任务一结束,城邦各盟国很快就分崩离析,后来分裂成许多独立的国家;而西周的各地诸侯国是周室分封的,一开始即与周王维持着从属关系、君臣不平等的关系。周王对各诸侯有巡狩、保护等权力,诸侯对周王有贡赋、朝聘等义务,这种联系一直不断。所以,后来才产生一个地大物博的、统一的东方中华大国。如果没有西周王国,也不会有今天的中国。
从以上所论,我们可以明确地下一结论,“国家”机构对社会发展所负的职能,概括起来不外两个:一个是起“缓和冲突”、促进联合以及对社会的管理等方面的作用;另一个是对人民实行镇压和统治方面的作用。“国家”最大的历史作用是起缓和冲突的方面,而不是镇压和统治的方面。
来源:《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