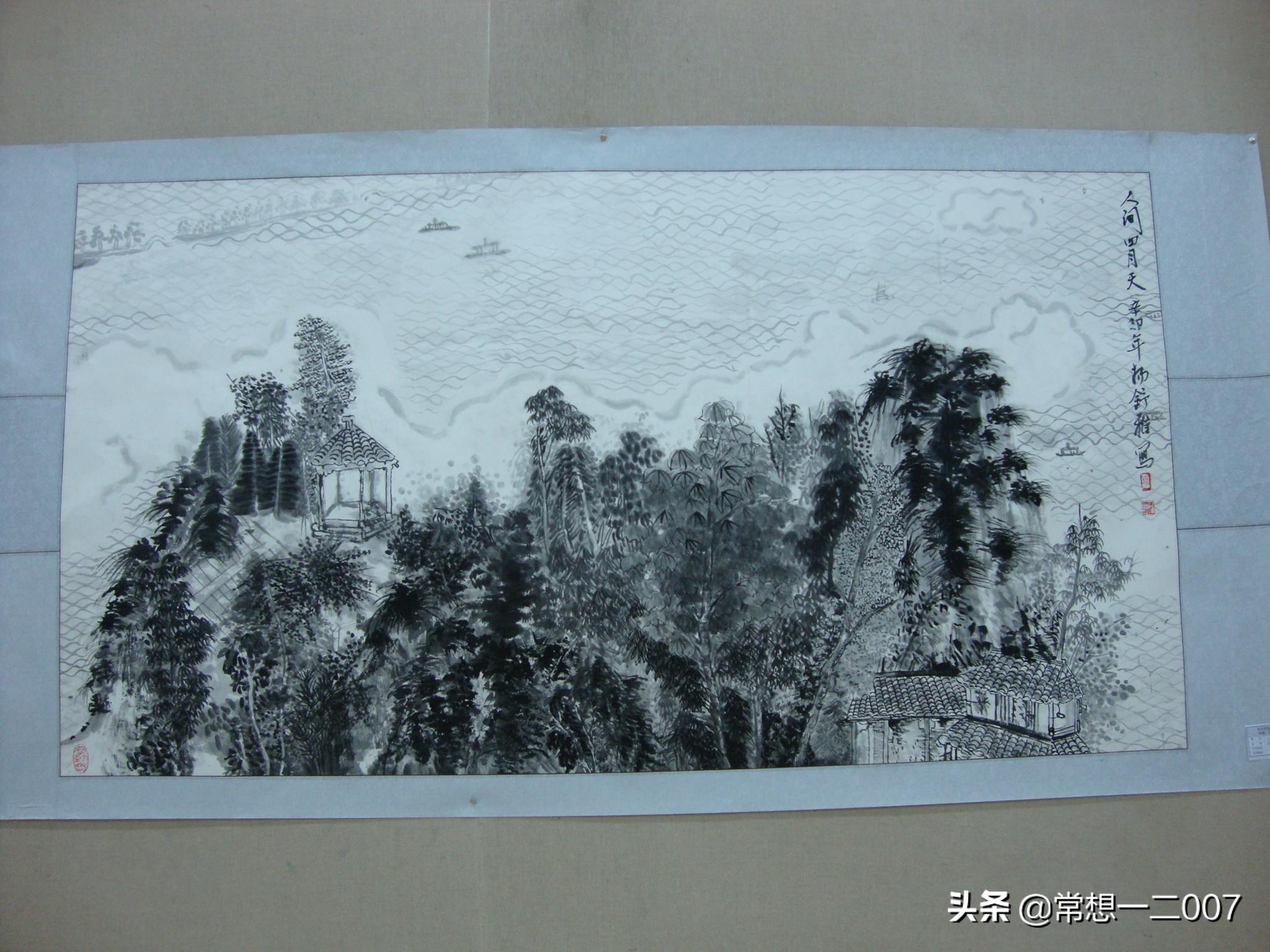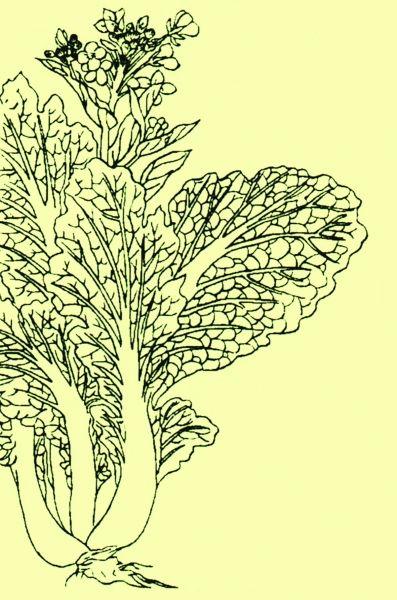谢维扬:中国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古国”问题
中国早期国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探索。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和古史学界在这方面用力甚多,收获颇丰,是最引人注目的领域之一。尤其是考古新发现的层出不穷,改变和补充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政治组织演进问题的许多原有的认识。但随着大量新资料的出现,学术界也面临着对这些资料作出正确解释的挑战。这项工作,就目前的进展来看,在许多重要和基本方面还有待于深入。从某种意义上说,近年来考古工作的丰硕成果能否对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产生积极的意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解释性工作中的成果。而这需要考古学界与古史学界通力合作,在认真的讨论中取得进展。
在当前依据新出土考古资料、主要以考古学方法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做出的大量解释中,在一个概念正在被频繁使用,那就是“古国”。这一概念最早由苏秉琦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用来描述新石器晚期某些新发现的有较高分化程度、较高生产力水平、较大社会规模的考古文化单位,如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某种单位等(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苏老在对新石器晚期考古遗存的性质的解释中使用“古国”这一概念是有深意的,即认为这些遗存表明有关的考古文化在主要的政治、社会、经济特征上已经超出了人们过去所熟悉的典型氏族社会制度的范畴,而需要某种特定的概念来描述之。他在评述新发现的辽西喀左东山嘴祭坛遗址和凌源、建平间的“女神庙”与积石冢遗址时明确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根植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说明他从红山文化的表现中已经看出了一种“高于”典型氏族制度(亦即苏老所说的“公社”制度)的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存在。这一见解对于推进学术界关于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总的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实际上表明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国内长期以来比较熟悉、然而并没有经过针对中国个案的深入辨析的那种单一的“从典型氏族社会中演化出国家”的想法已经难以解释新了解的事实。但是苏老在80年代提出“古国”概念时没有对他所使用的这一概念的确切含义进一步作明确的界定和充分的说明,因此他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整个看法当时还不完全明朗。1998年,苏老的重要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出版)问世,从书中我们看到了苏老对于“古国”概念的明确界定和更为详尽的说明,由此得以准确地把握苏老关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基本想法的完整内容。近年来学术界尤其是考古学界在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频繁使用“古国”概念,在整体上是源自苏老的见解,并基本接受了苏老90年代末对“古国”的界定,进而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对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一种较有影响并值得重视的解释性意见的框架。因此从近年来国内研究的实际来看,“古国”问题涉及到对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整个理解,意义十分重大,而其中有些问题似乎还可以作深一步的探讨。本文拟就此略陈若干粗浅的想法,尚祈学术界同仁指正。
一、“古国”的提出对中国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有重大影响
“古国”一词在古代文献普通的用法上,是一个不必与现代的“国家”在含义上有直接关联或等同的概念。“国”在字源上原同“邑”有关联,初从邑,为“邑”之同意字,均指人所居住的地方之意(注:参见于省吾:《释中国》,《中华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林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式的几个问题》,《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8年出版。)。但在后来的用法中,“国”与“邑”的含义发生分化,“邑”之所指较宽泛,而“国”则指邑之有特别品级者。周代文献常见的用法是“国”特指包含众多邑在内的一块有紧密政治关系、具有一定自治性的地域,也指此种地域的中心区域(首府),即居其领导地位的某个大邑或邑群,文献称之为“都邑”。此外,由于作为都邑的“国”往往是特定地域范围内最城市化的部分,又通常在其中心位置,故在文献中又常与其外围的“郊”、“野”等构成相对待的概念。要之,“国”在周代文献中最基本的用法只是指称在其内部拥有某种政治联系并相对自治的、由土地、人民构成的社会—政治单位或其中心区域。在这两种情况下,“国”都不涉及有关地域的主权的特征,也不表明有关地域上的政治制度类型,也就是并不对应于现代所说的“国家”。在周代典籍中,被称为“国”的社会—政治单位最常见的是作为商周时期地方势力的诸侯国,但有时具有主权国家资格的商王朝或周王朝本身也可称为“国”。如《周礼·天官·大宰》载:“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孙诒让《正义》云:“上言邦者,据王国而言;下言邦国者,总举大小侯国通言之。”古“邦”、“国”通(《说文·邑部》:“邦,国也”),“建邦”也就是“建国”。孙读可从。可见在是否涉及主权的问题上,古代“国”这个名称并不加分别。同样,对于所指称的土地—人民单位,“国”也不特别反映其政治制度状况或类型,正因此,它还可以更一般地指不同时期中对于一定的地域和人口有实际管辖权的各种社会—政治实体,当然也包括早期的一些政治实体,而不论它们是不是国家。如《尚书·尧典》中说尧时“协和万邦”(《史记·五帝本纪》作“合和万国”),应该就出于这样一种记法,其原意并不包含暗示这些“邦”或“国”就是国家的意思。先秦此种文例非常普遍,如《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四》云:“大禹之时,诸侯万国。”《荀子·富国》曰:“古有万国,今有十数焉。”这些大致亦属相同记法。以上数条,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在我国传说时期的后期,中国境内存在过“万国”。对于这些“国”,若无特别证据并经特别论证,当代学者一般不会径直将其认作国家。事实上,如果禹时有“万国”,其政治发展程度也肯定不会完全一致,文献一律称之为“国”,正说明“国”的用法无关乎现代关于“国家”的概念。
苏老将我国新石器晚期某些发展程度较高的文化所反映的某种古代社会—政治组织称为“古国”,如果是在古代文献普通的用法上,并不失为一项对古文献有传神之妙的概括。因为如上所引证的,古人对这一时期的人群组织或社会—政治单位本来就有“万国”之说。而且苏老的提法在80年代的研究中至少起了两个重要作用:第一,帮助人们认识这一时期人群组织的复杂程度,包括它们在政治上不同于所谓“公社”即典型氏族制度的特征,而80年代以来国内研究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上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对前国家时期政治组织的类型和特征有了新的认识,包括对酋邦问题的了解;第二,促使人们对了解这一时期除中原以外的广袤地域内人们政治组织演进的全貌有足够的重视,从而认识到需要完整地了解和解释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但苏老在90年代末发表的与“古国”有关的一系列全面的论述,开始明确地将他所使用的“古国”的概念与“国家”的概念等同起来,从而他所使用的“古国”已不再同古代文献普通用法上的“古国”相当,这就使问题的意义发生重大变化。
苏老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谈到红山文化时说:“红山文化在距近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经产生。”(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37-138页。)这里非常明确地把红山文化作为“古国”认定为国家。这个看法在苏老80年代的表述中尚未得见。对于良渚文化,苏老的看法还要进一步,把它看作是夏以前“方国”的“最典型的实例”(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5页。)。而所谓“方国”,在苏老的术语中是较之“古国”更高一级的阶段,即如他说:“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5页。)可见对良渚文化政治上的发展程度,苏老的估计甚至超出国家形成的时期,已经与商周属于同一阶段或类型。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在苏老90年代的理论中,“古国”确实已经是国家,只不过还属其“原始”的阶段而已。苏老整个理论的重要性是在于,它不认为距今四五千年前的“古国”的问题只涉及少数特定的个案(如红山、良渚等),而是当时整个中国范围内同步发生的一个很广泛的过程。他说:“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40页。)因此,“古国”的提出及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在文献所载夏以前政治组织演进的整个理论(以下简称“古国理论”),是对长期以来人们所熟悉的对于中国国家形成和早期国家进程解释的基本框架的重大改变。就其主要结论而言,这一理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是突破迄今为国内学术界多数人接受的关于中国国家起源和早期进程的基本的解释性框架的:首先,这一理论把中国形成最早的国家的时间大大提前了,亦即提前到距今五千年前,而不是夏朝建立时的大约四千年前;其次,由于将作为新石器文化的良渚文化等认定为“方国”,亦即与商周国家在发展阶段上无异的较成熟的国家,因此中国古代较成熟国家出现的时间也大大提前了;其三,这一理论在关注广泛区域内早期国家进程的同时,并不认为中原地区形成的国家有特别的历史的意义,而夏商周也都只是“方国”而不是王朝,因此由早期文献记录的自夏朝以来的古代王朝政治的历史地位将变得很暧昧,对整个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描述也将有根本的变化。所有这些结论,其意义无疑十分重大。苏老的理论的基调是将中国早期国家进程发生的时间大幅度提前,这实际上也是目前相当一部分学者在这一课题上工作的基调。促使人们在这种方向上调整原有认识的主要原因,无疑是近年来大量出土的具有复杂社会内涵、较大规模、较高物质文化水平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导致人们对这一时期人群的政治—社会发展程度有新的估计。但问题是,目前在这一方向上的工作在体现有关论证所应有的要求上究竟情况如何?对此恐怕在事实和理论两方面都还需要经过非常深入的、全面的研究和讨论。从这个角度说,对围绕“古国”概念形成的关于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上述解释性框架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讨论,应该是非常必要的。
二、“古国”作为国家的考古学证据的认定问题
古国理论的基础是对有关的一些新石器晚期遗址内涵的意义的认定。考古学界迄今在这方面所作的工作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其中最关键的一点是在对这些遗址内涵确认的基础上,使人们对中国古代距今四千至五千年分布在广袤区域内的众多人群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状况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些认识概括地说应该是:第一,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广泛地出现了具有相当高的物质生产水平、有较大的社会规模、社会分层高度发展的社会—政治单位,它们在基本特征上已超出了典型氏族社会的水平,而且有相当稳定的、持续的发展历程;第二,在这些人群单位内部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个人性质的权力和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控制机制,少数有特别权力的人统治社会整体的情景依稀可见;第三,有些由文化认同现象暗示的、规模十分庞大的这类人群单位,很可能已包括了众多较低级别的更小的人群单位,而所有这些单位的组合应该是建立在某种强力控制的基础上,而不是在平等联合的基础上;第四,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属于这些社会—政治单位的、能够确切无误地表明比较正式的国家制度存在的证据,包括表现国家制度存在的某种官署和其他强力机构或组织存在的证据,因此这些具有复杂政治特征的社会个体应还处于前国家时期。这些应该是我们从考古学界近年来围绕“古国”问题所作的大量有益工作中目前能够确认的主要新认识。这是非常重要的进展,对中国早期国家研究更深入地进行极有价值。
然而至90年代,古国理论在对有关考古遗存的意义的认定上又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即把所有这些考古资料所反映的远古社会—政治单位认定为国家。这一推进是否更逼近古代历史的真实?我感到这似乎尚需经过一些讨论才能最终断定。因为从考古学证据认定方法的角度来看,这一认定中不确定的成分还相当多,结论也并不成熟。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某些必要而与此相关的考古学证据认定论据上的问题尚没有被认真对待,造成这一认定在方法和内容上均有某种缺陷。
从方法的要求上看,这一认定的最主要的缺陷是:在作为古国理论基础的有关考古工作中并没有发现对于国家制度存在能够自明的考古学证据。众所周知,国家制度本身只是一种政治关系,属非物质性的事物,即在考古上是不可能直接观察到国家或国家制度的。正如德国政治学家赫尔佐克所说:“早期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是不能从地下挖掘出来的。”(注:[德国]罗曼·赫尔佐克:《古代的国家》(赵蓉恒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因此在严格的规范上,考古学只能通过确认与国家制度有关的某些物质性遗存类型的物件来推断国家或国家制度的存在。但必须看到,具有此种说明力的考古遗存类型并不如有些研究者想象的那么多。在单独依靠考古学证据下结论的场合下,真正直接和最为重要的证据类型当然是能够反映某种比较正式的管理机构亦即官署运作的物件,如官印、符信、文书之类,以及记载或反映官署运作的某种文字资料,如同某些金文资料那样。但这些类型的证据资料在我国新石器晚期遗址中尚未有发现,而且这类证据甚至迄今在夏代考古中也还是空白。究其原因很复杂,这里暂且不论。近年来频频在国内研究中被作为主要证据类型来谈论国家制度形成问题的是各种大型公共建筑,包括房屋、祭祀场所、墓葬、聚落设施等。然而,这种类型的证据资料对于国家制度存在的说明力其实并不如人们希望的那样确定或肯定,亦即这些类型的证据资料在表明是国家还是前国家政体存在的问题上并不能自明。其原因就是早期的大型公共建筑并不一定与国家制度有必然联系,在前国家时期的文化中这类遗存同样可能存在。考古学史上属于史前亦即前国家时期文化的大型建筑遗存屡见不鲜。美国学者哈斯就曾经着重讨论过显示“史前社会行使权力程度”的“大规模工程”的问题(注:[美国]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148页。)。原因很简单,那就是某些前国家复杂政治制度看来已经具有相当有效和有较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和组织能力。因此没有国家制度,许多远古人类仍然有能力实施并完成这类大型工程。可见将大型工程遗迹与国家制度的存在简单地等同起来是不可取的。由于事实上很难得出大型公共建筑(甚至某些大型聚落)的技术性指标本身对政治制度的系统的反映关系,因此仅据这类遗存的技术性特征,显然尚不足以对有关文化或人群的政治制度状况作出确定无疑的判断。这一点,在现代重视考古学证据意义认定规范问题的早期历史研究中已颇受关注,是值得从事考古学解释工作的学者思考的。
古国理论在证据认定上的上述缺陷是同这一理论内容上的特征直接有关的,那就是:古国理论不包含关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概念,从而放弃了对国家形成前夕可能存在的接近于国家的社会—政治形式的探讨。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制度的存在是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深入研究的中国国家起源过程中的重要和基本事实。但这方面问题在90年代的古国理论中几乎完全没有涉及,因此很自然,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亦未纳入其对考古学证据意义的解释中。这样做无疑提供了支持其大幅度提早中国古代国家进程的主要理论条件,但同时也意味着这一理论的事实基础至少是还不确定的。自现代人类学在早期政治组织演进问题上发现并深入研究了作为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酋邦以后,前国家时期人类在政治制度上所达到的复杂程度使人们对国家制度产生前后政治组织演进的实质和细节都加深了认识(注:参见拙著:《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3-234页。)。这对有关考古学证据意义的认定上提出的问题是:虽然考古学证据作为物质性的遗存对于一个早期复杂社会个体在社会规模、社会权力结构特征、社会控制力水平、社会分化程度、工艺和生产力水平以及文化统一性程度等方面的表现,确实可以有直接的和比较确定的说明意义;然而由于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存在,一个古代社会个体在所有上述方面的表现,在其形成国家制度前后实际上并不一定会有截然不同的特征。因此,在直接发生导致国家制度形成的事件的时段内,在一个社会个体的上述表现方面,我们并不一定能够观察到足够明显的和意义确定的变化。换言之,在大多数物质性表征方面,酋邦与国家实际上是非常接近的,因而在考古实践上往往很难区分。美国学者塞维斯曾就早期国家与酋邦的不同提出两项要点:(1)早期国家的政治统治更正规化、形式化、专业化,并更多地以对武力的垄断为基础;(2)社会分层现象已发展成明确的阶级区分(注:E.R.Service:Profiles in Ethnology,p.498.)。另外,我们当然还可以想到国家应该有对特定地域实行更稳定的控制的概念和相应制度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如何在物质遗存中被反映,也还是非常复杂、并且是目前考古学中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点是明确的,即我们已经不能轻易地只是依据有关社会个体的复杂程度来判断其是否进入国家化进程,也不能无条件地依据有关社会个体的工艺和经济活动总量的规模来下结论。“古国”问题最初在80年代被提出时,在当时的表述上完全有可能进一步发展出关于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的完整思考。苏老80年代所概括的“高于公社的组织”,实际上应该就是指前国家复杂政治组织。但这一思路在90年代的古国理论中消失了。在由《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完整表述的古国理论中并没有对前国家时期复杂政治组织的讨论。在书中苏老还多次明确地将中国国家起源的过程概括为“氏族向国家转化”、“由氏族向国家的过渡”(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3、137页。)。可见古国理论确实不再将前国家复杂政治制度作为一个有自身地位和完整特征的范畴从“氏族制度”中分离出来。由于重新对前国家时期问题采取长期以来被认可的较简单的所谓“氏族模式”的理解,因此对明显超出氏族制度特征的现象,古国理论显然只能用国家制度来解释。这导致它简单地将特征接近于国家的社会个体直接认定为国家。这在证据认定的理据方面缺乏深入的讨论而较显简单化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
三、古国理论与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
中国国家起源的研究不同于许多完全缺乏有关文献依据的个案,中国古代遗留下来可供我们讨论早期国家问题的文献资料是大量的。当然古代的记载并不等于全部事实,但在中国早期历史的研究中,一般地谈论这类原则并不足以充分揭示和贴切地体认中国古代的文献资料作为史料的特性。这是因为古代中国文献不是一些相互孤立的资料,它们在总体上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文献传统的产物。也就是说,在对古代事实的记录和叙述上,文献总体是依托古代中国十分发展的文字记录传统的。这种传统的内容就是:具备完善的原始记录系统(史官制度)、很高水平的资料整理系统(实用文献和古书的出现)、具有一定专业水平的资料著录系统和检索方法(目录学的雏形和对古书引用的传统)、一定程度上的批评系统(史官职业准则的形成和非官属著作活动的出现),以及文献作为国家政治活动一部分的严肃的地位。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发展是古代中国历史非常有特点的因素。因此对早期文献资料的可信性问题的判断,应当在对古代文献总体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这是近年来学术界在对大量新出土文献研究基础上,对于中国古代文献作为历史性资料的特性问题所获得的最重要的认识之一。那种孤立地对待单项文献资料的方法并不能真正解决古代与文献有关的重要课题,反而可能在最终结果上失误。近年来对历史上“疑古”方法的反思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注意到早期文献对于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研究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们为我们了解早期历史的诸多细节从正面提供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料和信息,有赖它们,我们才得以对阐述早期国家活动有较多的依据。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总合在一起,实际上也在为我们讲述古代国家的历史和特征给出一些不支持“非法”通过的“底线”;当我们的研究可能超出这些“底线”时,在方法上应该有更严厉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合理的原则是:如果我们如实地整理出所有古代文献或者文献总体所反映的一些基本的古代事实,我们就可以将这些基本的事实看作是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从而成为我们讲述古代历史的一些“底线”。就是说:除非有真正完整的论证,否则在这个“底线”之外来讲述古代历史就是所谓“非法通过”,其说明力和价值是不高的。
在古代国家的问题上,传统文献总内容的“内核”之一,就是同古代中国在进入国家进程时期广大地域内政治组织演进的一般状况有关的。尽管在细节上对有关资料的读法可能不尽相同,但总体上古代文献没有提供任何关于在夏朝国家形成以前中国境内还有其他具有国家特性的社会—政治单位存在的可确认的资料,这还是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确认夏朝是国家,依据的是早期文献总体所反映的夏政治活动和制度的诸多情节;但对夏以前人群单位的政治状况,文献提供的情形则明显不同,事实上很难找到能表明其具有国家特性的明确的材料。因此在对古代文献总体解读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只能认为夏朝是可辨认的最早出现的国家,而且这一点就其被记述的广度、持续性以及记述所包含的特征性内容而言,正是我们所说的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一个“内核”。现在可以追问的是,古代文献的这一“内核”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到以夏代国家为开端的华夏文化和华夏国家政治传统的产物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华夏文献确有可能漠视周围异族国家制度和国家进程的存在。但应该看到,虽然我们现在粗略地可以把古代所谓“华”、“夷”之辨理解为某种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映,然而在古代,这种观念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对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认定有关。也就是说,古代文献所说的“戎夷蛮狄”包含了认为这些人群和社会个体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这在古人看来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上程度较低的意思。顾颉刚先生曾说:“申、吕、齐、许者,戎之进于中国者也;姜戎者,停滞于戎之原始状态者也。……由其入居中国之先后,遂有华戎之判别。”(注:顾颉刚:《九州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陈梦家先生则对相似的看法有更明确的表述:“有与此等羌同族的夏,……在夏商时代已进入较高级的形式,……凡此‘诸夏’属于高级形式之羌人,以别于尚过游牧生活的低级形式的羌人。”(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82页。)因此,华夏文献亦多有称三代王室先祖为“戎”、“夷”、“狄”者。所以这样,从某个角度说,似亦与三代人尚知其远祖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包括还没有形成三代的制度即国家制度有关。可见古代文献在总体上对于人群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程度之高低是有敏感反映的。而文献对较后时期里异族人群中国家化进程正面记述的例子(比如对徐戎的大量记载),说明对异族国家活动古代文献并无绝对回避的成例。故没有理由假设对于在夏代国家形成时期与夏有接触并已自动地进入国家化进程的人群或社会个体,已知文献总体有一个系统隐匿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项完整的论证要求,古国理论显然有必要对古代文献总体内容上的“内核”与其结论之间的明显差异做出合理的解释。然而这一点在古国理论中却是被忽略的。
从可确认的事实来看,以夏朝为开端的中原王朝的主要政治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显然并不能说是受周边其他高级政治形式影响的结果。夏朝的国家政治与商周时期相比,尚属十分原始的阶段。而就是这样,夏朝政治已经是当时的新事物。《淮南子·齐俗训》在提到与夏王朝对抗而被剿灭的有扈氏的故事时说:“昔者有扈氏为义而亡,知义而不知宜也。”“宜”,便宜也,就是指变革和新事物。因此夏朝政治的形成是一个创造性的发展,这也说明夏朝形成时周边人群的政治发展程度并不高于夏。这个估计应当说也同古代文献总体内容的“内核”相一致。而在这个问题上,古国理论对所讨论的考古文化作为“国家”制度的载体在嗣后历史中的表现和影响没有做出必要和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对这些“国家”的活动与文献所载中原王朝国家历史的可能的互动关系语焉不详。但这是形成完整的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解释框架所必需的。以良渚文化为例,其延续时间很长,并且其与中原的交往可以从两支考古文化遗存的器型学比较中得到证实。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原在进入国家化进程前后受到来自良渚文化地区某种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政治进程的压力和重要影响。这同古代文献内容的“内核”关于这一时期这两大地区关系记述的基调恰好是吻合的。如果认定良渚文化地区在夏代国家进程以外、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国家,这无疑将使我们对古代文献总体对环太湖地区历史及其在中原国家进程中作用纪录的内容和方式都感到不解。这一点显然并不一定与文献有否失记有关,而更可能或至少不能排除是历史的真实内容所致。事实上,如果真的在夏代前夕,在实际上与夏有接触和交往的环太湖地区存在良渚“国家”的话,不仅良渚地区,而且整个中原地区的历史也都可能会与我们现在了解的大不一样,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将是难以回答的。这也表明抛却古代文献内容的一些“内核”来重构古代历史的整个框架,只有在弄清这些“内核”确属失实的情况下才可能是必要的。古代文献留给我们的历史纪录当然是要由现代研究以现代规范来加以整理和重新解释的,这是现代历史学的使命;但就对中国古代的研究而言,现代规范中应该在更深的理解上包含这样的认识:中国古代文献总体作为非常具有历史性的文字活动的产物,其对于古史真相的说明力和保存这一真相的容量是不可低估的。
来源:《学术月刊》2001年第4期
- 0000
- 0000
- 0001
- 0001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