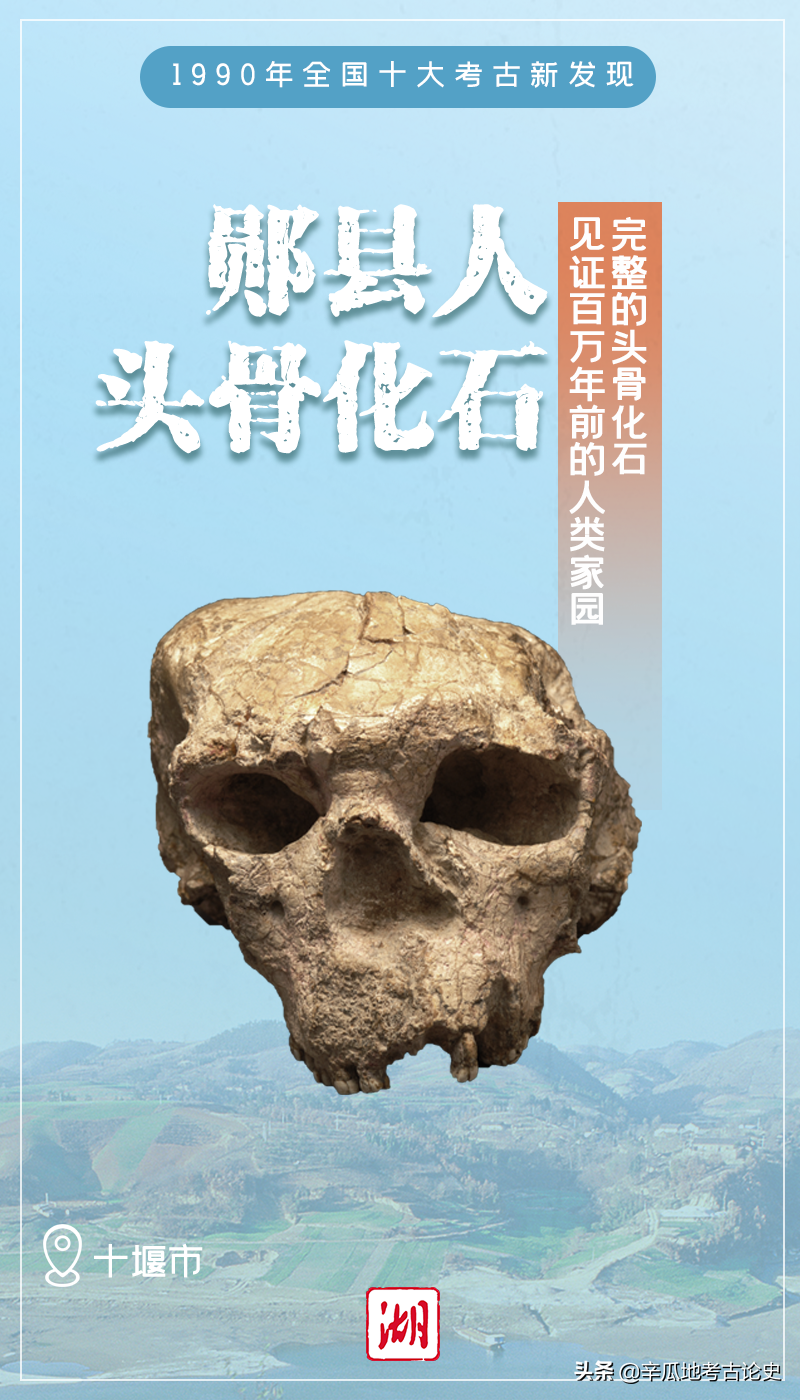曹兵武: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
在中国的史前遗迹中,城址是规模最大且最引人注目的[1]。1930年山东历城(今属章丘)城子崖首先发现了典型的龙山文化城址,稍后,安阳后冈也发现了时代相近的城址。近年来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郑州西山,山东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桐林,内蒙古包头阿善、凉城老虎山等地陆续发现了同一时代的史前遗址。长江中游地区的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湖南澧县南岳城也发现了年代相若的史前城址,而在内蒙古赤峰市英金河、阴河流域的调查,一下子就发现了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40余座城址。这一系列的新材料再一次触发了学术界极大的兴趣,人们纷纷撰文,发表自己对这些城址的看法,并论述它们在古代中国文明和国家起源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一种十分普遍的观点是,这些城址作为龙山时代的中心聚落,标志着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与组合能力,标志着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掠夺战争的频繁、持久和残忍。因此,“城的出现,是国家和文明形成的主要标志,说明龙山时代已经步入古国时代”[2]。
城作为史前遗迹之一种,和其它遗迹一样,当有其产生的主客观条件、独特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如此众多的城址突然十分普遍地在中国很大的范围内出现,并且在地域的分布上也呈现出某种规律性,因此,只有将它们放置于当时考古学文化的宏观背景下做动态的检视,即进行文化过程的复原与发生学的诠释,才有可能理解蕴含于其中的真正意义。本文即试图通过重建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变化、环境变迁的历时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文化因素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来揭示中国早期城址的起源与功能以及史前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
一、需要、知识和技术:城产生的前提
前述史前城址,根据城墙的修筑方式,可粗略地分为三类:A、夯筑;B、石块垒筑;C、先夯筑再以石块包嵌加固。前者如王城岗、平粮台、郝家台、西山、城子崖、桐林、石家河等,主要分布在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后者如新店、迟家营子等,主要分布在内蒙古南部或东南。第二类石块垒筑城址也主要分布于内蒙古地区,并在当地城址的数量上占了绝大多数。在外形上,这些城址普遍为正方形或者近正方形,反映了这个时代人们特定的空间观念和审美能力,也有一些圆形的如湖南城头山、郑州西山,主要应是仰韶时期圆形聚落、圆形房屋在早期城址上的残存形态。还有一些近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的如阴河流域的一些石城等,则应是地貌因素与建筑材料等制约的结果。修筑这些史前城址需要两种知识和技术前提,其一是关于“城”这一特定空间概念的构思,其二是夯筑或垒石的技术。而作为一种特定类型的聚落——城与一般聚落相比,又具有下列三个特点:(1)特殊的防御上的需要;(2)特殊的建筑技术和知识;(3)广大的社会动员力量——种种迹象表明,这一力量可能远远超出城址以外。
龙山时代,人们关于“城”的知识的最初概念应当从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的历史演变中去寻找。在中国早期城址出现以前,曾经存在过聚落遗址的发生(新石器时代早期)、扩大(新石器时代中期)、发展(新石器时代晚期)、分化(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四个阶段,而在大约公元前6000-5000年的扩大期,聚落的内部布局便已略具体系,有了居住区、墓葬区以及其它生活、生产区的分化[3]。这一时期内蒙古东部敖汉旗兴隆洼遗址甚至已经出现了宽约150-200cm环村而修的壕沟。约当公元前5000-3000年,即聚落遗址的发展期,聚落的布局基本成熟,居住区、生产区、墓葬区等功能区既明确划分又紧密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性的生活单位,同时聚落外部与内部因社会关系的变化,在结构上也渐趋合理与完美。姜寨是最典型的代表。这时候,环绕聚落的壕沟似已成为较普遍的遗迹,见于报道的除姜寨外,还有西安半坡、甘肃秦安大地湾甲址、山东广饶傅家、安徽尉迟寺等。目前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普遍为局部性的调查和发掘,如果今后更多地采用全面揭露的方式,发现环壕的数量当会更多。这些壕沟主要应是用于防御的,在姜寨遗址与壕沟同时发现的还有哨所的遗迹,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如果我们将深陷的壕沟与高耸的城墙联系起来,那么可以说,龙山时代的城墙就是仰韶文化的壕沟在形态和功能上的进一步发展。
再来看看筑城技术的历史。最简单的夯筑就是在一个面上累土并以砸击的方法使之结合、坚固,这种技术也出现得很早。定居一开始人们就习惯于对居住面进行修理和加工,使之坚硬、光滑,起到既美观又实用的作用。仰韶文化后期,地面加工的技术已经十分高明,除了将地面砸硬之外,还往往涂上石灰或其它的饰物,懂得了平地挖槽再起建墙壁的技术;龙山时代,在发现城址较多的河南、山东地区,已常有建在夯土台基上的房子。近来在更早的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的某些遗址中,也发现有夯土遗迹,而且有的规模相当惊人,有人认为大汶口文化中的颅骨变形习俗与稍后阶段较先进的板筑夯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4]。郑州西山发现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夯土城墙,集中体现了城址初兴阶段的夯筑技术。而对龙山时期王城岗、平粮台等城墙的解剖,说明此时的夯筑技术虽仍比较原始,但已有了显然的进步。山东城子崖、田旺的台式城址——在高台上加筑夯土台,然后挖掉周边的慢坡,形成陡直的城边的做法,更为清楚地表明了城址这一文化现象在当时的迫切的社会需要。
既然防御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且许多关于城的知识与技术前提似乎也早已具备,为什么只是在龙山时代偏晚这段时间里,史前中国的城址大批涌现(在数量上数倍于稍后的夏商时代的城址),并在聚落的某些特点上发生了如此鲜明的变化(比如防御的色彩得到空前的加强)?我想,其动因主要应当是社会文化方面的,它至少体现了:1.战争的扩大。相对于仰韶时期,战争可能更加频繁,更加残酷与持久——这是以高耸的城墙取代仰韶时期环村而修的壕沟的主要原因。2.聚落之间重要性程度的分化。战争期间,一些聚落或地区比另一些聚落或地区更为重要,因此更值得保卫。3.社会动员力量的进一步加强。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虽然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不容否认,但是,已有的考古资料说明这两个时期的工具并无特殊的不同,因此,城墙的广泛修筑,应是建立在对更广大地区、更众多劳动力的动员与支配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劳动者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机制更加完善的基础上。
二、从仰韶到龙山:城址兴起的社会、文化与自然背景
龙山时代,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出现如此众多的史前城址,那么,在社会与文化领域中,是什么力量一下子激发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动员能力?这些城址又是什么人修筑并用来防御什么人的?先民们在这个时候究竟为什么要兵戎相见、大动干戈呢?考古学材料的性质决定了城址本身不可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而需要从包括城址在内的所有考古学现象所体现的龙山时代的总体背景中去寻找线索。
约距今五千年左右,中国所有史前考古学文化发达的地区(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生了一次剧烈的分化与重新组合,其结果是实现了一个分布地域更广阔、相互之间文化特质更为接近的龙山文化在各个地区对仰韶文化或其同时期文化(本文简称仰韶时期)的取代。严文明先生曾经对各地龙山文化的特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认为:鉴于它们地域广阔、发生的时间大致相同,而相互之间的差异程度比史前任何时候各文化之间都小,故可以用龙山时代一词涵盖这一时期的考古学文化[5]。与仰韶时期相比,龙山时代具有如下鲜明的特点:
1.遗址的分布:龙山时代,仰韶文化的中心区域比如关中、豫西地区的遗址大为减少,似乎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空心化运动;另一方面,许多仰韶时期人迹罕见的地方比如豫东与山东交界之处,豫东南、鲁西南和皖西北交界之处,此时则已遗迹广布。另外,在许多地区,龙山时代的遗址普遍较仰韶时期占据更高的地理位置,这一点在河流的中、上游及一些山间河谷和盆地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6]。总之,遗址的空间布局有所变化,存在于仰韶时期各文化区之间的空白和缓冲区域正在迅速消失。
在遗址的大小和功能上,龙山时期也较仰韶时期有更大的分化。仰韶时期的早期,数万平方米的遗址是较为常见的遗址,十余万或几十万平方米的遗址已算是很大的遗址了。仰韶时期的晚期,遗址之间的差别逐渐显示出来,到距今约5000年时,开始步入早期龙山时代(即中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时),则出现了大地湾晚期遗址、红山文化后期的牛河梁、东山嘴以及良渚、石家河、陶寺等这样一些明显具有特殊功能的大遗址集群,某些遗址甚至达上百万平方米。而城址的普遍出现,则把遗址间的分化推到了一个高潮。
2.陶器:龙山时代,轮制或慢轮修整取代了仰韶时期的手制,成为制陶的主要技术特色;陶色方面,以灰、黑陶代替了仰韶时期流行的红、褐陶,标志着陶器焙烧技术的变化,即以密闭还原式的陶窑代替了开放氧化式的陶窑;器形方面的变化也是明显的,主要体现在袋足的鬲、斝、鬶等在全国各地的普遍推广与使用,构成了炊器领域中一支新兴的有生力量。纹饰方面灿烂多姿的彩陶文化的普遍消失。其原因除了陶器的焙烧技术的变化、深色陶器施彩困难之外,还应当与制陶工业中效率的提高、生产的专业化、组装、批量化等的出现以及工艺上某些尖端技术的产生,使陶器制作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等有关。龙山时代陶器给人的总体印象不是更美,而是更分化、更多样、更实用(包括新分化出来的礼仪之用)。
3.房屋建筑:一方面是个体之间居住条件的分化在继续加剧,另一方面是方形的、分间的房子普遍取代了仰韶时期流行的圆形单间房子[7]。方形房子的出现,除了适应新的社会组织、家庭结构的需要之外,可能和土坏、石块以及废弃的红烧土块等建筑材料对木材等植物性材料(包括地穴、半地穴式房子用于焙烧的材料)的大幅度取代不无关系。而发生在建筑材料领域的这种变化,又大大加强了房屋的坚固程度,同时也可能更加保暖和舒适。
4.墓葬:单人葬取代了以前较为流行的多人合葬、二次葬以及仰韶文化独特的小孩瓮棺葬,成为主要的葬式,标志着社会组织的某些变化;随葬品不但种类更加齐全、侧重有所不同,数量也普遍增加,并且墓与墓之间的分化相当严重。在陶寺等墓地,大墓的随葬品可以是小墓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而且大、中、小墓在数量上也构成一种似“金字塔”结构。在东南沿海的反山、瑶山、福泉山、草鞋山、张陵山,山东的西朱封,山西的陶寺等[8],大墓与小墓都是分开埋葬的,不但突出了个体之间的差别,更对这种差别以类而聚,宣告了仰韶时期发达的氏族公共墓地制度的彻底解体。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现象是女性地位的显著下降。虽然对仰韶时期的女性地位问题和是否存在母权制阶段目前尚有争议,然而,起码没有材料可以证明在仰韶时期女性地位较男子要低。龙山时代这样的证据却普遍出现了,不少地区已发现了些夫妻合葬墓,其中一些墓男性仰身直肢,女性屈肢面向男性。
前述龙山时代文化特质的各种变化,舍弃其中包涵的技术发展、社会组织进步等动因外,开源节能似乎是其共同的主题。陶器形的变化特别是其中袋形三足器的推广,不但使用起来方便、稳当,同时扩大了炊器的受火面积,极大地节约了燃料;而吉德炜先生推测,陶器颜色的变化,也可能起源于节约燃料的动因[9]。柴草作为当时的主要能源,其紧张与短缺对人类应具有较之其他任何能源都更为广泛的影响,因为它们本身既是能源,又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主要构成部分,也是食物直接的来源或食物生产必须依赖的外部环境,其紧张则标志着人类居住场所生态环境的普遍恶化,标志着获得食物及其它生活资源困难程度的增加(这并不意味着产量的必然减少,而是意味着获得同样多的产量,可能要投入更多的劳动、技术和社会组织力量)。当然,也有资料表明当时的人均消耗可能较前大为增加,比如,墓葬随葬品更加普遍并严重分化,不过另一方面,这些和陶器的制作与使用一样,也可视为人类面对能源紧张所做出的文化调适行为——正是因为能源的紧张,人们才改变了关于能源的传统观念和能源利用的传统方式,才激发了人们的占有欲,使之加强了对生活用品的控制与占据。私有观念的产生应建立在这样两个基础之上:其一是剩余产品的增加,其二是人类在主观愿望上对财产的所普遍存在的紧张与短缺感,两者相辅相成。其它的文化现象也可作如此解释。而墓葬方面的变化则可被视为人类在社会制度和礼仪观念上对这些变化的调适,夫妻合葬的出现、小孩瓮棺葬的减少乃至消失,主要应与当时的家庭结构发生变化有关,另外可能也与后文所述的环境恶化、土地负荷力有限所引起的生活动荡有关。有人认为,仰韶时期普遍流行的小孩瓮棺葬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孩子的爱心与珍惜[10],当社会感到人口过多了,生存变得更为艰难,妇女与小孩自然不再受到原来那样的爱护与尊重了。
霍德在研究史前欧洲的陶器制作时,也发现了与此大致类似的现象:当公元前5000-4000年的欧洲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劳动力的再生产、妇女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时,日常生活用品特别是陶器显得特别精雕细饰;而到公元前3000年以后,大地上人口已近饱和,社会的控制和调节策略发生变化之后,生活用陶不断简化,相反,一些仪式性用品则被加强[11]。这些与中国彩陶的衰落、一些特殊陶器类型如蛋壳陶的出现等文化现象是符合若节的,可能体现了人类文化和心理方面的某种共同性的规律。
总之,在仰韶文化中后期,特别是庙底沟类型之时,史前人类与自然之间已达到一种饱和型的平衡,文化繁荣发达。稍后,史前文化即进入一个剧烈的重新分化与组合的时期,其原因或者由于前期人类对某些宜居地区的过度开垦与利用,或者由于自然环境自身的演变,人类生活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发生了普遍的紧张与短缺,各文化区之间原有的空白边缘地带被迅速加以利用,而且为了寻找更多的可资利用的资源,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新的移民浪潮,这是龙山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同性趋强的根本原因。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随着人口的增加、技术的发展,移民活动一直持续不断[12],然而,龙山时代的移民与早期有着根本的不同,早期移民一般是扩张性或殖民性的,是为了解决各宜居地区日益增加的过剩人口,是从中心地区向人口稀少的边缘地区疏散多余的人口,而中心地区的位置一般难以动摇。这在资源丰富、文化发达的仰韶文化半坡和庙底沟时期表现更为明显[13]。到龙山时代,随着边缘缓冲地带的迅速消失,移民运动一改往昔和平牧歌式的情调,变成一种不同人们共同体之间对日益紧张的生活资源的争夺甚至取代。这样,在考古学文化上表现为,仰韶时期,从早到晚往往以某个共同的祖先文化为中心,繁衍出许多具有血缘关系的平行的文化或类型来,即苏秉琦先生所称的兄弟文化[14],比如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秦王寨文化、后冈一期文化和红山文化,可能就是这样的关系。而同时期的其它地区,比如山东、长江中游、东南沿海,各考古学文化同样也存在一种连续的扩张的过程;龙山时代,一方面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共同性有所加强,另一方面则类型众多,取代频繁,在许多地区存在间断,致使某些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来龙去脉难以弄清,比如辉煌的红山后期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后裔,目前都是大家谈论的热门话题,而龙山时代某些文化或类型由于其兴起于先前的空白地区比如豫东,又由于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内涵方面的质的转变,关于其前身也存在着一些疑问。
环境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力地支持了龙山时期资源紧张的推测。全新世是人类诞生以来的最佳气候期之一,但也可以划分为几个阶段,即早、中、晚期,其中中全新世约当距今7500-2500年,又可以距今5000年为界划为早、晚两段。早全新世与中全新世早段为气候的上升期,中全新世晚段与晚全新世为气候的下降期。也就是说,在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适宜程度达其高峰并开始走下坡路,其表现是,当即就有一次比较普遍的降温事件。与此同时,在孢粉资料中,中国出现了栎等阔叶类树种比例的下降事件[15],欧洲出现了榆下降事件[16]。栎与榆均是两地全新世高温期阔叶林的主要构成树种,其下降即暗示了森林植被的大幅度减少及整个生态系统方面的某些变化,与考古学现象所揭示的能源作用方面的适应性变化不谋而合。
气温频频波动并不断下降的另一个结果是对地理地貌的塑造与改变。有资料表明,距今6000-5000年,由于气温高,大陆冰川的融化使海平面上升达其历史上的最高点,而从距今5000年起,海平面又慢慢开始下降,到距今2500年,达其在全新世中的又一个较低点[17]。海岸线的后退直接影响着沿海地区人类活动场所与生产活动的选择与分布,另一方面,海平面的下降必引起河流侵蚀基准面的相应下降,河流下切作用普遍加强和河口三角洲堆积发育迅速,也引起下游地区湖泊、沼泽的相应消亡与一些旧有遗址周围可用水源的变化。在全新世地理地貌发育史上,这一系列的变化不啻为一场革命,同时也应是龙山时代遗址分布规律新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豫东地区从此时开始遗址广布就与此有关[18]。
气温是构成气候的主要因素,气温的下降,必引起气候带的整个南移。现在,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亚热带与北温带的分界线,全新世高温期即仰韶时期亚热带的北缘具体在什么位置,学术界目前存在较大的争论,然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关中地区、晋南、豫北及山东地区应包括在当时的北亚热带之内。孢粉资料显示,不仅当时阔叶林乃至常绿林的某些树种在这些地区多有分布[19],连一些对气候变化反应极其敏锐的亚热带类型的动物在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址中也屡有报道,比如仰韶时期中华竹鼠、猕猴等喜暖动物在关中的姜寨、北首岭、半坡等都有发现;在河北桑干河流域(阳原丁家堡水库)曾发现亚洲象的遗迹;在山东的王因等遗址,发现有现今分布在长江流域的扬子鳄等遗骸。到龙山时代,动、植物不但在总的丰度上大为减少,这些亚热带类型在黄河中下游也销声匿迹[20]。这种情况在商代可能略有改善,但也未能改变气温下降这一总的趋势。
气候的另一个因素——降水的情况尚不太清楚,但有迹象表明到龙山时代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史前遗址多傍水而居,遗址分布方面的变化暗示了水资源可能发生了变化。龙山时代所有的新发明中,水井是很重要的一项。水井的发明一方面可使人类摆脱某些水文因素的局限性,但主要应是对水资源短缺的一种适应。学术界一般把龙山时代看作与仰韶时期一样,是气候比较温暖湿润的,总起来说这没错,但是温暖湿润的程度已经大为下降,降水可能也应当有所下降,气温与降水的正相关是气候学上具有普遍性的规律。另外,降水的时间分布可能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同样的年降水量,在时间上均匀合理,则表现为风调雨顺,如果季节性过强,则易酿成水、旱之灾。许多史家考证,洪水传说应为事实,而且就发生在龙山时代[21]。
由此看来,龙山时代人类生存环境是普遍恶化了,这既有仰韶时期某些地区过度开发、打破了区域内生态平衡的因素,但主要应是自然环境的退化,严重消弱了自然界恢复平衡的能力,并毁坏了某些地区旧有的生物资源。另一方面,河流的下切、新的河流阶地(北方各河流的一级阶地)、冲积平原与河口三角洲的发育、干涸的沼泽,又提供了新的比较适宜的居住场所。这种情况下,再加上仰韶时期业已奠定的庞大的人口基础和新的技术、新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出现,各考古学文化之间的重新分化和组合是不难理解的,而这种重新分化与组合的中心,当是对生存资源的重新分配和瓜分。反映在各考古学文化内部,则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分化及不同个体对资源及生活资料的占有与使用上的显著不同。
三、关于城自身的若干问题
在一个生存环境普遍恶化、资源紧张、对生存资源进行重新瓜分的时代,城的普遍出现就不是什么意外的现象,问题是:城既然是防御的,那么谁是进攻者?城到底保护什么?这样的进攻和防御具有怎样的性质?这是有关中国早期城址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核心问题。
我已经略述了资源紧张和私有观念的关系。私有观念主要是调节群体内部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标志着群体内部个体之间对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从而改变了龙山时代人们共同体的面貌和性质。而在群体之间,资源的紧张与短缺则可能促进“国土”概念的萌生与发展——因为土地面积的广大和种类的多样化,可能从另外的角度弥补资源的紧张与不足。这一点对理解史前中国的城址是至关紧要的,因为,史前中国诸城址中,至今没有发现规模巨大的、典型的、结构完整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没有发现它们作为中心聚落的实质性证据。就目前已发表的资料看,淮阳平粮台保存最完整,城内遗迹发现有十余座房子,但根据房子形制特别是房子内部构造和发现物来看,与当时其它遗址中的一般民居并不完全一样,因此,似不宜定为一般民住房,它们或许就是某种性质的公房。同时发现的还有所谓的墓葬,但也多为小孩的瓮棺葬和乱葬坑,与一般墓地中墓葬相距甚远,说明了这些遗迹的非常规居址的性质。郝家台也有排房发现,其情况应与平粮台的近似。这些城中也未发现高级民居或者宫殿式的建筑,王城岗有较多的夯土遗迹,可惜破坏过甚,难于判定其确切的性质。也许王城岗和平粮台中的炼铜遗迹在当时的确是十分领先的,但龙山时代晚期炼铜遗迹的发现在中国已有多处且目前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铜器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已如其在夏商时期扮演着重要作用——这种文化选择需要时间和种种机遇。总之,虽然可以将城址视为当时的聚落遗址,但除了城墙以外,没有其它资料可以说明它作为中心聚落特别是作为当时各文化类型之中心的特征。与此同时,同一时期一些规模更大、更具中心聚落特征的遗址如陶寺、良渚以及山东、河南一些面积极大的龙山文化遗址,则并未发现可与城墙相比的防御性设施。因此,看来这些高耸的城墙并非是为了保护某些社会高层分子已经聚敛起来的财富,相反,它们的功能应是对外的,应是保护修筑城址的整个人们共同体及其生存资源的,更直接地说,它们是用来保护整个人们共同体所赖以生存的一方水土的,以防止它被其它的人们共同体所冒犯乃至取占。这一推测也有助于理解在尚无确切证据表明社会分化已经达到一部分人可以任意驱使另一部分人、社会的通讯联络与协调组织力都相当有限的史前时期,龙山时代的人们何以具有如此巨大的社会组织与动员力量,可以以简陋的工具完成如此巨大的社会工程。
按照这种推测,这些城址应当大多数修建在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边缘地区,特别是环境变化最明显和人们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最激烈的地区。而事实表明,这些史前的城址正大致上符合了这样的条件。黄河中下游的孟庄、后冈、丁公、城子崖、桐林、边线王,恰恰位于仰韶温暖期暖温带与北亚热带可能的交界地带上。而内蒙古、辽西地区城堡的连线性、组合式分布,则活脱脱就是后来长城的雏形,并可能昭示着当时暖温代与寒带的界限。而且,按照这种推测,也恰恰解释了为什么史前城址发现越来越多,而我们对城中发现物却越来越失望的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史前城址与西亚、印度的早期城址以及商代以后作为都城的城址相比面积普遍过小的原因。
史学界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应大体上与龙山时代相当。五帝时代就是不同族群、不同部落之间相互争战、相互融合的时代,而五帝活动的舞台背景又恰是仰韶文化与龙山时代各文化发达的区域,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由于这一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气候变化、资源危机,并使水温失调、洪水泛滥,当然以这一地区受害最甚,而气候带的南移,也当以两气候带相交汇的区域感觉最显。文化作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亚系统,受环境变化的影响是必然的。因此,史前城址在今长城东北部沿线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率先出现并普及,也就可以理解。这些城址大多只能被目为在资源紧张、人口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一群人用来抵抗另一群人的军事城堡,它们和历史时期的边城有些相似。这一大的社会分化与重新组合活动,在这一地区一直持续到距今2500年左右,随着气候凉干的大局已定,河流一级阶地的最终形成,特别是秦汉之际汉民族的形成,才渐渐平息,从而使这一地区在国家与文明的起源、中化民族的诞生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22]。相反,在这一气候巨变中受冲击较小的关中、甘青等地区,虽然也有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则至今未发现城址,以后发现城址的可能性也当不大。长江中下游发现城址很少,特别是其下游地区,虽然曾有发达如良渚那样的文化,但由于其所处环境位置及其他原因至今也未发现城址。
夏商周三代与龙山时代紧相衔接,史前城址的这种功用和分布当然也有体现。有可能是夏之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商代殷墟以及周代前期的诸都,目前都没有发现环绕的城墙,除殷墟的大壕沟可能具有防御作用之外,其他诸遗址连壕沟这样的次一级防御设施也未见报道。相反,商代的几座城址如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湖北黄陂盘龙城、山西垣曲商城、夏县东下冯商城,则都是修筑于当时疆域的边缘地区[23]。虽然其中如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在征战过程中因军政首领长期前敌等原因,也可能曾做过一段时间的都城,但也不可能改变其当时位于边缘地区以及防御的性质和事实。可见直到此时,争夺资源、争夺疆域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生活中的主要矛盾,而夏亡于商、商亡于周,也正是这一矛盾的继续。三代之中尤以商代城址最众、布局最清,但是比之龙山时代,在数量上仍然逊色不少,这一点正体现了龙山时代社会大转型的时代特点,说明夏商周时代虽然族群矛盾仍很激烈,但毕竟锋头已过,而龙山时代在中国国家、文明以及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
这些史前城址的产生,说明在人们共同体内部已经存在着具有极大的号召与组织能力的领袖阶层,由于此时的墓葬资料等尚难以说明这些领袖的宗教或世俗性质,难以对领袖与民众之间的分化程度与性质作定性定量的解释,目前还难以将这些领袖阶层与统治者同等看待,不过可以肯定,龙山时代领袖对于人们共同体的作用比仰韶时期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些城址也说明当时“国土”观念已经萌芽,人们保卫领地的观念,已突破仰韶时期的一村一寨,扩大至整个地区人们共同体的生存空间。虽然没有确切证据说明国家的存在,但“国土”观念、私有观念与领袖阶层,共同构成了国家产生的前提,至少可以断定,龙山时代中国已经迈上了国家形成的道路,而夏、商、周国家的形成,是在不同族群之间对生存资源的重新瓜分与分配中完成的,社会内部的分化即阶级的产生同样在中国国家形成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但其本身也受到了不同族群之间争夺生存资源的战争的有力推动、完善与巩固。在中国的早期国家中,阶级矛盾似乎屈从于族群矛盾,这种情况大约一直持续到秦汉之际。
国家发生问题,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也是世界各古老文明中心考古学研究的焦点。人们一般看法是,在近东与新大陆,宗教是文明与国家形成的契机,早期神庙是社会分化与凝聚的核心,宗教与世俗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盟、斗争关系,导致了业已凝聚在宗教周围的人们共同体向国家迈进[24];在古代埃及,宗教与治水共同缔造了早期国家[25]。而在史前中国,虽然曾发现如牛河梁、东山嘴、反山、瑶山那样宏伟的祭祀遗址,但宗教在龙山文化和三代文明中,似并无如此显赫的地位;虽然传说夏王朝的产生与大禹治水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考古学资料特别是如此众多的具城堡性质的史前城址则似乎表明,早期国家乃是在部落与部落之间的频繁争战中呱呱坠地的,而位于当时北亚热带以北、寒代以南的暖温带范围内的北方中国,由于环境与文化的双重原因,在这个过程中被首先卷入。因此,中国国家、文明起源的道路,在世界文化中是特殊而完善的现象。这种国家形成方式对历史时期中国国家的体制与社会制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探索世界历史的进步过程具有标本意义。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