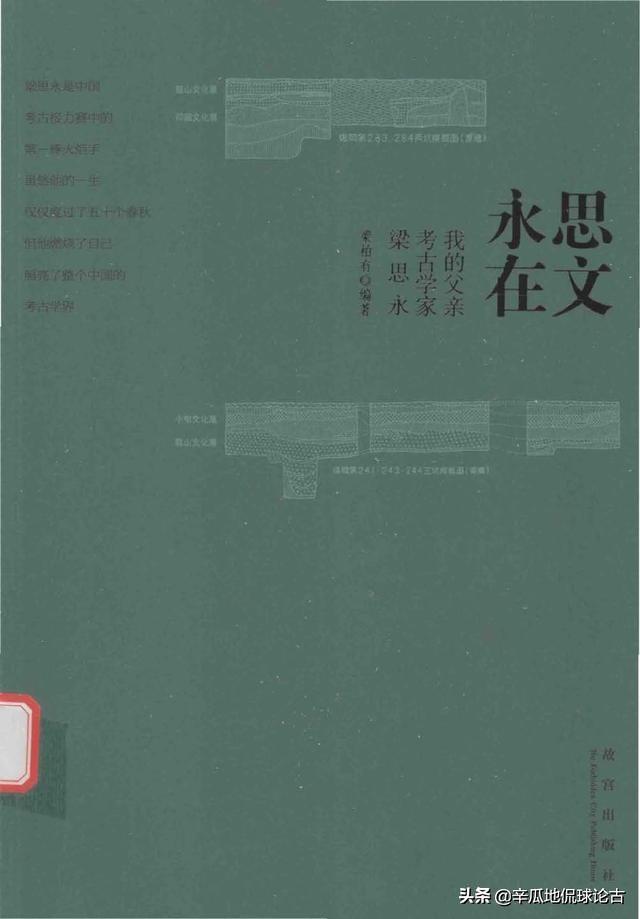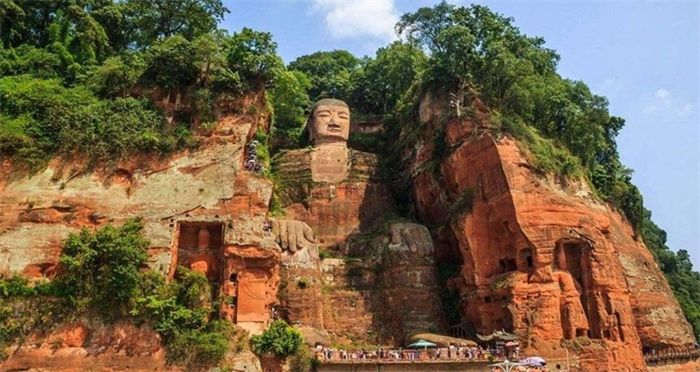印刷术的发展
印刷术是本书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这不仅是因为印刷术本身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技术,而且因为印刷书籍随处可得,更能培养人们抽象思维的习惯。本章即会展现这种习惯是如何应用于分析各种问题的—从地图到机械制作,从轮子和杠杆到化学物质,不一而足。
到1600年,亚洲所有的大国和帝国都在制造枪支,但在一些国家,包括波斯,印刷术都尚未被普遍采用。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因为波斯在1294年就接触到了印刷术,当时波斯的蒙古统治者想发行纸币,便雇用了中国印刷工来进行印刷工作。但直到16世纪,波斯—就像奥斯曼帝国一样—尽管经济繁荣,艺术昌盛,但印刷术仍未被采用。其中一个原因是,通过手工抄写生产出的书籍数量已足以满足需求,因为当地有许多专业抄写员,而他们的工资普遍很低。此外,用手抄写《古兰经》也被视作一种虔诚的行为,而书法也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在土耳其,许多显赫人士,甚至苏丹和维齐尔都会抄写《古兰经》,而一个专业的书法家一生可能会抄写50份。18世纪2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项目之一,就是在伊斯坦布尔成立了一家印刷厂,它主要生产西方书籍的译本,但这一短暂的尝试对奥斯曼帝国和当时其他伊斯兰帝国占主导地位的“手抄本文化”(manuscript culture)影响甚微。
除了受手抄本光环和其低廉复制成本的影响而难以发展外,在亚洲,印刷常常受到保守派的反对,因为它被打上了基督教技术的负面印记。印刷机通常由基督教传教士引进,用于印刷和传播《圣经》、其他基督教文本,以及有助于宣传信仰的字典或语法书。16世纪50年代,葡萄牙人统治下的果阿地区的一个耶稣会传教士就组建了这样一个印刷厂,于1572年出版了一本基督教教义书的泰米尔语译本,这是第一本在印度印刷的印度语书籍。在印度境内,基督徒聚集区的印刷厂持续为一小部分皈依者印刷作品,不过意料中的是,印度教和穆斯林精英们对此兴趣不大。直到19世纪,在欧洲殖民国家支持下,基督教传教士大量涌入,亚洲各国政府也承认西方的学术和制度是生存的关键,此时印刷文化才开始流行起来。
在这些国家,枪炮被迅速采用,而印刷术的普及却进展缓慢,二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意义非凡。枪炮符合既有统治集团的利益,集团成员往往是军事精英,枪炮使他们能够巩固其权力并扩大领土边界。印刷术则与这些目标无关,甚至会颠覆他们的权力。然而,在中国,正如前一章所指出的,情况却截然不同。朝廷的文官是一群文学精英,其成员对艺术、儒家哲学和他们的田庄兴趣浓厚。他们对书籍永不满足的需求推动了彩色印刷等创新。16世纪80年代,中国使用五色印刷系统制作了第一本带有彩色插图的书籍。而早在1340年,就已有了双色(红色和黑色)印刷的试验。
尽管朝鲜和日本的口语非常不同,但是使用的文字基本上与中国相同。中国印刷的书籍也会出口到这两个国家。朝鲜有完善的印刷工场,其产品在中国很受推崇;朝鲜的技术中也有活字印刷术。而在日本,直到1600年左右,雕版印刷几乎只用于佛教寺院的活动。1592年,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他的战利品之一就是活字印刷设备,这些设备很快就在宫廷中流行起来,用于印刷典藏版的日本文学经典作品。1590年,耶稣会传教士引进了一种西式印刷机,也使用活字,用于印刷基督教文本和字典;但由于基督教在1597年被禁,这种印刷机在当地没有激起什么水花。
到1640年,朝鲜和西方的活字印刷术都已不再于日本使用,日本的印刷者们用起了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对于许多流行文学的自由版式而言并不适用。然而,比用什么印刷技术更重要的是,日本正在产出有关技术主题的新书,包括关于航海(1618年)和数学(17世纪20年代)的作品。在这些书中,有几本采用了中国的彩色印刷法,让图表呈现得更加明晰。公元1700年后,艺术书籍和彩色印刷品的生产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16世纪和17世纪,中国也印制了一些技术书籍,不过数量少得出人意料。一部名为《天工开物》的作品,是我们了解明代技术的主要知识来源。该书首次印刷于1637年,由生于1587年的江西地方政府官员宋应星撰写。该书描述了食物、衣服以及日常生活中必需的大多数物品的全部生产过程,并配有极为清晰的插图。这部书共分为三个部分,详述了各种工艺和技能,其中重点突出了农耕(“五谷”)和纺织技术,而金属和武器的生产则在第三部分单独讨论。在这之间,第二部分描述了一系列杂项工艺:造船、马车制造和造纸。还有一部分详细讨论了陶瓷,其中内容包括砖、瓦以及陶器的制造。
不过,宋应星这本书特别意味深长的一点是,他似乎对写这种普通无趣的主题感到愧疚,将自己写书的动机归结为“任性”。他写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雄心勃勃的学者无疑会把这本书扔到他的桌子上,不再理会;这是一部与官场上的晋升法门毫不相干的作品)。他的态度与一些历史学家对中国文化的解释是一致的,即儒家统治阶层对数学和物理现象兴趣索然,因为他们宁愿通过良好的组织能力和高效的政府来解决现实问题,而把机械和生产留给手工业者和企业家去琢磨。
在当时,这种态度似乎相当合理;彼时中国经济强盛,其中农业产量不断攀升,各类行业蓬勃发展(包括纺织、陶瓷、炼铁,当然还有印刷)。然而,一些历史学家却认为,这一时期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停滞期。那时正是欧洲科学革命的阶段,这样比较来看,中国似乎已经落于人后了,尽管北京的耶稣会传教士依然在将欧洲的发展情况告知朝廷官员,同时也将中国技术成就(包括农业、蚕工、瓷器生产等)的信息传回欧洲。例如,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就有一本于1615年用中文印刷的关于天文学的小书,他在其中加入了一页关于望远镜的内容和一幅土星的插图,这幅图原出自1610年伽利略出版的一本有关他借助望远镜获得的发现的著作。邓玉函(Johann Schreck)与王征合作,于1627年出版了《奇器图说》(Diagrams and Explanations of the Marvelous Devices of the Far West),其中就包括对望远镜的介绍。此后不久,望远镜就在中国得到了制造和使用。而在1644年最终颠覆明朝的危机中,耶稣会传教士还在枪支制造方面提供了建议。
若要对上述现象做出评述,我们就须得了解欧洲的科学革命是如何使西方较之其他文化逐步取得技术优势的。这里我们采取的观点是,重要的不是某个发现或发明,而是一系列处理技术信息和整合技术(及管理)理念的新方法,即基于测量、数据表格、分类和次级分类的手段来进行分析,甚至还要用到绘图和物理模型。
本文整理摘编自《世界文明中的技术》,[英]阿诺德·佩西 [英]白馥兰 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3.1
- 0000
- 0003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