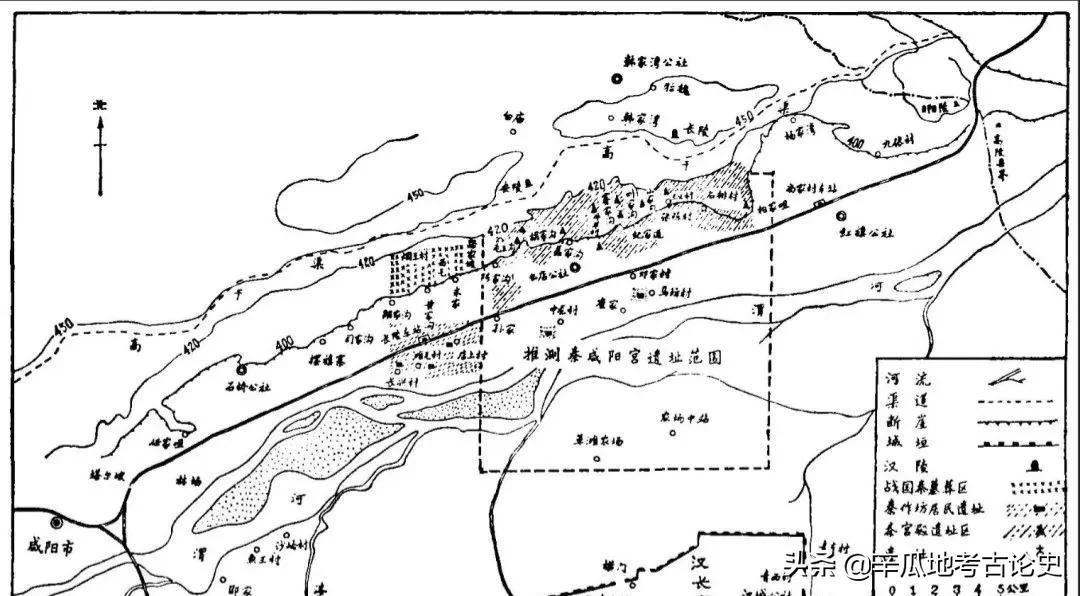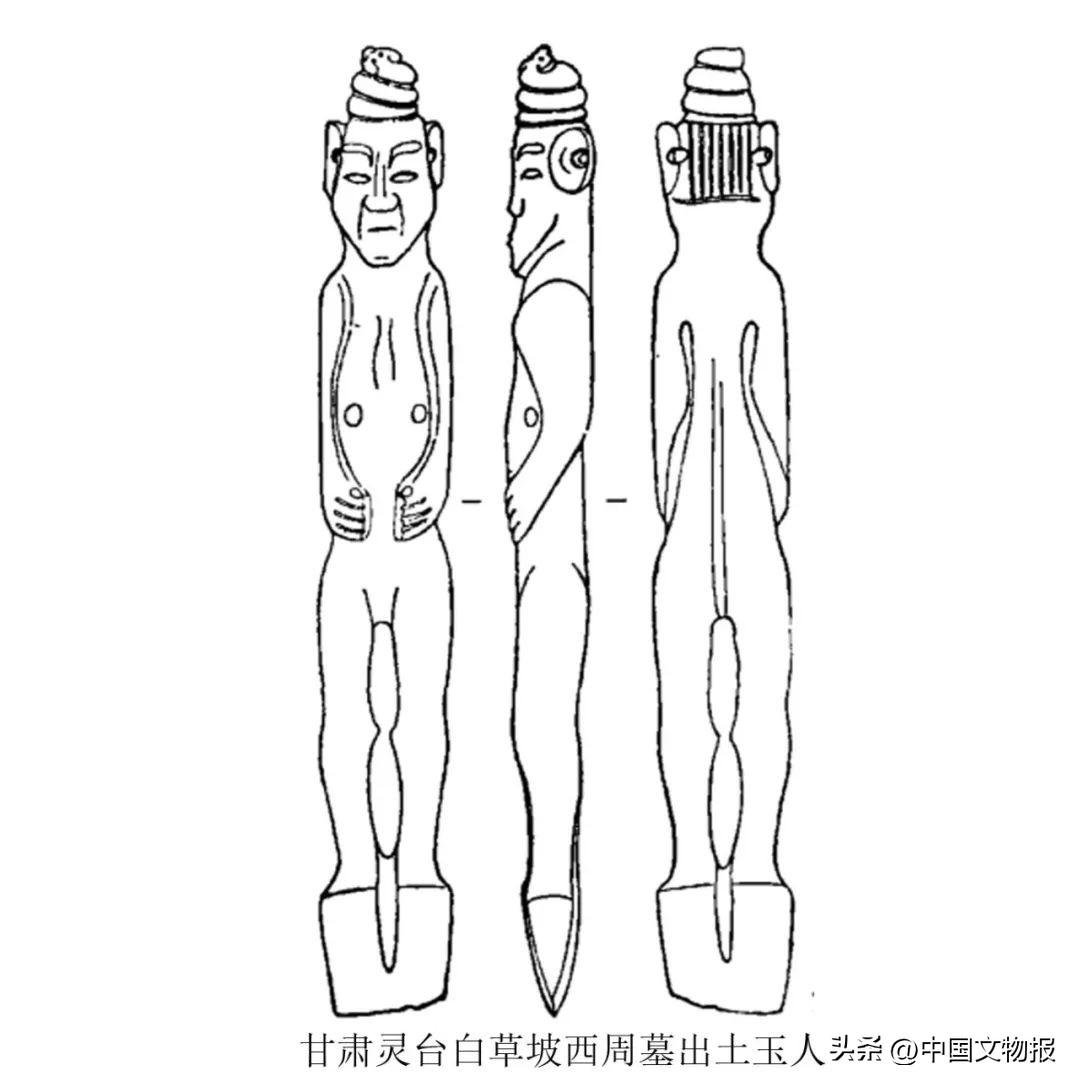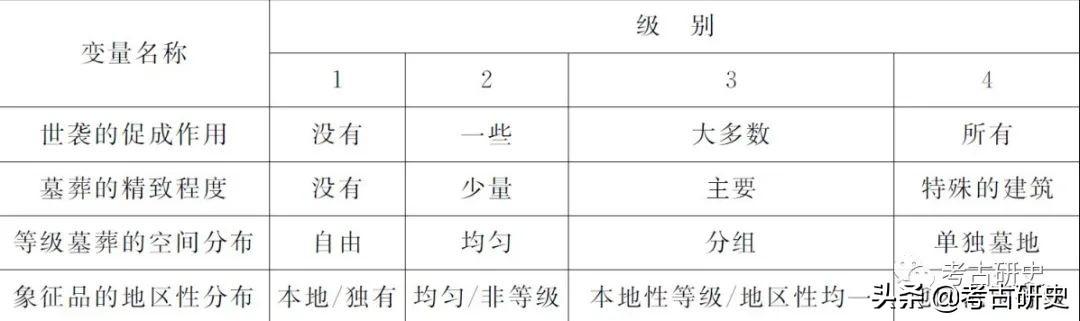周振鹤: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
将近九十年前,匈牙利作家梅尔彻·伦吉尔(Melchior Lengyel)写过一个剧本,名为《台风》。在这个剧本中出现了一批在巴黎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剧中有如下的对白:
“西方数千年来发展起来的古老文化,我们日本人只要十五年就把它变成囊中之物了。西方学者花费三十年取得的研究成果,我们只要读五天书就握于掌中了。”
“让欧洲人去费脑子好了!让欧洲人去干好了!等他们创造出什么好东西,我们再学过来那该多好!”
“为了达到今天的水平,欧洲人已牺牲了多少代人,有多少人成为殉道者而倒下。但我们只用十五年就把西欧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变成自己的了。”[(1)]
这些话是作为讽刺日本人在文化方面吃现成饭的事实而设计的。该剧写于1909年,去日俄战争不远。正当日本人在十年的时间里相继打败了中国与俄国两个庞然大物后,用这样的话来描绘他们当时的洋洋自得的粗俗嘴脸是并不过分的。
日本留学生是不是说过上面那些话不必当真,但这些话却是道出了日本文化幸运的一面。所谓幸运就是指他们在历史上有几次直接输入了比自身文化先进数百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的外来文化,从而使自身文化发生真正意义上的大跃进,跨越了其他民族必须循序渐进耗时费事而无法省略的社会发展阶段。
但是日本文化也有不幸的一面。日本文化的不幸就是在自己的文化尚未成熟时,已然遇上外来的发达的大文化,这个大文化压制未成熟的日本文化的自然发育,使之在精神方面始终处于侏儒状态。前述的文化方面的大跃进其实主要只是在物质方面与部分的制度方面。
无论中国,无论欧洲,其精神文化都是在物质文化的发展上同步发展起来的,自身精神文化的建立绝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观念的东西很难超越。对任何一个民族而言,不与其他民族发生文化交流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当这一交流发生时,往往使自己的文化产生新的活力,不但在物质文化方面增添新的内容,使之更显丰富,而且也在精神文化方面有所更新而发出异彩。但不管如何变化,对于循序渐进的民族而言,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是齐头并进的,不会发生上下不整合的现象。无论是卡尔·马克思所认为的: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不过是作为基础的物质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反映;或者是马克斯·韦伯所主张的:一个社会的伦理道德是既定的,任何一种类型的经济如果与这种伦理道德相一致,就必然要兴盛起来;上两理论说的都是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一致的问题,尽管两人的观点完全相反。但是当一个弱势文化受到强势文化的影响而发生文化上的大跳跃时,情形就有些两样。在这种情况下,弱势文化常常发生物质文化方面的跳越发展阶段的变化。但是跳越物质文化发展阶段的民族,也必须跳越精神文化的发展阶段,否则必然要发生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在意识形态方面与伦理道德方面出现痛苦的分裂现象。
日本人的不幸即在于他们的物质文化已经发生大跃进,他们的精神文化却产生分裂,一部分随着物质文化一起跃进,几乎是全盘接受外来的意识形态与伦理道德;另一部分却依然停留在跃进前的水平之上,仍然以自己日常生活中总结出来的行为方式来应付外部世界。这就使得日本人成为世界上最为奇特的民族:他们既好斗又和善,既尚武又爱美,既彬彬有礼又妄自尊大,既温文尔雅又蛮不讲理,既刻板又富有适应性,既顺从又不甘任人摆布,既忠贞不二又会背信弃义,既保守又善于接受新事物,既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又常常一意孤行。[(2)]而且更要的是,这一切相反的行为方式又都是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使人很难对日本民族的性格下一个准确的断语。
为了理解日本文化的幸与不幸之间的矛盾,我们必须作一个简单的历史回顾。
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被称为绳文文化的日本土著文化已经在日本列岛自生自长持续了八千年之久,发展速度十分缓慢。公元前三世纪,大陆上的稻作民族携带金属工具移来,使日本一跃进入水田农耕阶段,变成为弥生文化,日本文化似乎从婴儿一下子长成小孩。从绳文文化进入弥生文化并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侵入的缘故,只是这一外来文化的载体不是典籍或工具,而是移民本身。这些来自大陆的移民与土著居民,所以日本民族的主要成份还是绳文人,但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具有土著民族的融合形成今天的日本民族。当然,在数量上大陆移民不会超过土著居民,所以日本民族的主要成分还是绳文人,但大陆移民带来的新技术和新知识具有土著文化无可比拟的先进性,使得日本文化发生质的变化。因此有人借用后世“和魂汉才”与“和魂洋才”的提法,戏称这一质的变化为“绳魂弥才”,意思是:人还是绳文时代的土著,而精神却已步入弥生阶段。究其实,这时日本民族的精神文化有可能是伴随新知识新技术而来的新观念与新意识和绳文时代土著观念与意识的混合,而不一定全是移民的新观念,但是由于年代久远,而且没有文字的记载,今日已难得其详。但这种混合观念使日本得以在后来的八九百年时间建立了许多奴隶制的小国,而摒弃绳文时代的蒙昧状态,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把日本文化的发展比喻成原子核外层电子的跃迁,是一点也不为过的。这样的跃迁在日本历史上经常发生,上面的绳文文化到弥生文化是一次,公元六七世纪之交(中国的隋唐之际),又是另一次。这一次是圣德太子推行的“推古朝改革”与接踵而来的大化改新,又一下子将日本从奴隶社会推进到律令国家。儒家理念与佛教思想成为国家的主导意识。而不幸的是在儒学和佛教进入以前,日本尚不存在可以称之为宗教或其他什么基本成形的意识形态体系,因而拿不出自己的思想尺度去衡量外来思想的异己度,亦即无法判明外来思想的好与坏,分别什么应该接受,什么应该排斥,只能囫囵吞枣照单全收。但是这时已可看出日本传统的天神的概念并不因为佛教与儒家学说的传入而隐退,而是与佛儒杂然并陈。大化元年(645年,唐贞观十九年)八月的诏书就有“随天神之所奉寄,方今始将修万国”的话。这种杂然并存的上层建筑,贯穿于整个日本历史以至于今。一方面全盘接受的是与当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先进的外来的意识形态,另方面又保留文化未跃进以前旧有的思想观念,两种精神文化之间存在巨大的时差,又焉能不使整个日本文化时时处于矛盾之中?
大化改新以后,日本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以至精神文化都全面地受到唐文化的辐射,以至于形成所谓唐风文化。一切文化样式都是“唐模样”,辣椒要叫唐辛子,南瓜要叫唐茄子,甚至胡麻要叫唐胡麻(胡麻对中国来讲已是外来的,故冠以胡字,传到日本后,是双重外来,故其上又加唐字),连傻瓜都要叫做唐变木。而且直到本世纪初,进口货还叫唐物,洋货店还叫唐屋。但是在民间社会里所接触到的唐文化仅止于物质文化,至多只及于部分的制度文化,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只在上层社会传播。据研究,儒家伦理直到千年以后的德川幕府时代,还未在民众中普遍传开。这是另一个分裂现象,即上层社会与民间社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裂。这是使日本文化出现他人不能理解的矛盾乖张的原因之二。
第三个分裂的现象也随之产生,即时时形成与外来文化尖锐对立的文化或思潮。对于任何有识之士来说,全盘接受外来文化而无视自己的民族文化到底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于是在唐风文化盛行了二三百年之后,随着唐朝的衰落和其它原因,日本停派遣唐使,开始发展所谓“国风文化”。这种文化是处处要求体现日本固有的民族风格,从创造假名开始,直到在绘画、书法和建筑方面逐渐营建出一种日本风格来,并使佛教也趋向于日本化。尽管国风文化并不能完全割断与中国文化的联系,假名仍由汉字变形而来,儒教伦理仍然保持,佛教各宗派至今也还经常要到中国来寻根,但对日本而言,毕竟是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文化,而且这种文化从此被当作日本民族文化的基础长期延续并不断丰富其内涵。以此为标志,其后的日本文化在吸收一段时期的外来文化后,总要产生一股反向的潮流,强烈要求回到日本的固有文化去。这种要求有时并非产生于保守的思想流派,甚而是产生于那些原来积极要求学习外来文化的人当中。
明治维新是日本文化的第三次大跃迁,这次跃迁把日本推向国际社会,使之迅速成为亚洲强国。但是在这次跃迁中,狂热吸收西方文化主要在明治时期的头二十年。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明六社”不遗余力地开展启蒙活动,号召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吸收。作家森鸥外至于宣称:“彼(指西方)之所长并存于精神与技术两方面,我国人唯予模仿与崇拜可也。”表现出一种狂热的状态。但是进入明治二十年代以后,国粹主义之风兴起,猛烈批判“文明开化”运动是“以美为母,以法为父,妄自移风易俗,傲奢淫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国粹主义还发自启蒙者本身。最明显的莫过于福泽谕吉。从幕末一直到明治初年,他一直是西方文明的鼓吹者,但到明治十年时,就已变了调子:“察日本近年之情况,被文明的虚伪之说所欺骗,抵抗精神渐趋衰颓,忧国之士不可不讲求防救之术。”隔了一年,他又说:“吾人看法与(西方文化)醉心论者全然不同,吾人对于我国不是一个新的西方国家不唯不为之愤[疾],反为试图做西方国家的想法而深感忧虑。”好象他自己从来没有醉心于西方文化,也不曾主张过脱亚入欧论,一心一意要使日本挤入西方国家的行列似的。
国粹主义行时了二十年,因为没有理论基础,在精神文化方面建构不出自己的体系,在社会上已经失去魅力,甚至引起人们的反感,如夏目漱石就调侃道:“要为国家而吃饭,为国家而洗脸,为国家而上厕所,真受不了。”因此从明治四十年代起到昭和五六年间(本世纪一十年代后半到三十年代初),日本人又热衷于接受西方的理论与学说,这明白地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使自己显得有教养,有文化,而国粹主义者是拿不出什么人道主义和德谟克拉西这类时髦的学说与概念来的。可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外侵略野心大为膨胀,日本主义又大行其道,到处清除欧洲文化的影响,甚至于宣布日语中某些外来词为“敌性语言”而加以清除。不过这一过程只有十五年时间,二战失败后,日本又进入一个新的狂热学习西方文化,尤其是美国文化的阶段。战败以后的严重的自卑感引发了比文明开化时期更为激烈的自暴自弃的言论,有些西化的主张依中国人的传统看来简直是奸言论,如志贺直哉主张原封不动地采用法语作为国语,更有人主张日本不如干脆成为美国的一个州。整个日本的精神文化似乎处于真空状态,一切以美国文化的马首是瞻。
但是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以后,形势又逐渐起了变化。日本民族自信心好象得到了迅速的恢复,不断抬高日本文化的地位,并强调其独特性,而且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说明日本文化的优越性。先是在五十年代中期,加藤周一发表《日本文化的杂种性》一文,坦承日本文化是东西方文化的杂种,然而该文的目的是为了证明杂种文化并不比纯种文化如英法文化差劲,而且还连带把德国文化也拉下水,认为它也是不错的杂种文化。过了两年,梅棹忠夫更著《文明的生态史观》,正式把日本文化看成是与西方文化相平行而不稍次的文化。这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关于日本成功的著作越来越多,甚至外国人也加入了高歌称赞的行列。自信心演变为自尊心,更进而在部分人中间恶性膨胀而变成妄自尊大。虽说不见得是直接后果,但却至少是间接后果,那就是日本的政客们因此而不愿承认二次大战中日本战犯对亚洲人民所犯下的罪行。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问题,有的能够很快与之水乳交融,两者之间没有太大的隔阂;有的要经过长时期的消化才能接受,而接受以后就成为自身文化的一部分,也难分彼此。但是像日本文化这样始终不易与外来文化融合的情况却很少见。有人曾把日本文化比喻成海绵,能大量吸收外来文化,可谓生动。但这个比喻也可曲为之解,即把海绵一挤,水便全部出来了,与海绵终归不能一体化。因此之故,日本文化时时要出现与外来文化的对立,尽管它曾一度热烈地吸收过这一文化,并受惠于它。
纵观日本文化发展历程,可以看到日本的精神文化始终处于弱势的地位。全盘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吧,又与本身原有的精神文化不能合拍,于是常常要发生回归日本文化的运动;全盘拒绝外来精神文化吧,自己原有的精神文化又要与已跃进了的物质文化发生裂痕,又不能不接受外来的精神文化以弥补这个裂痕。的确是处于两难的境地。这种尴尬局面的产生只能解释为日本文化不具备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或者说来不及消化与自己差距过大的外来文化,因此便只好简单地包容它,或者如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比喻的,只是将外来文化当衣服穿,而衣服是不能与躯体合二为一的,所以外来文化的成份在日本文化中始终清晰可辨,不会与日本文化相混淆。对于这一点,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观察最说明问题。二战后,爱伦堡到日本访问时,就很惊异于任何一个日本人竟然每天要过几小时欧美式的生活,也要过几小时传统的日本式的生活这种奇怪的现象。因此他说:“在日本人中,不同的世界同时并存。”这不同的世界其实就是指不同的文化。
物质文化的跃进已为日本民族证明是可行的,但精神文化的跃进却也由日本民族证明是不可行的。有人估计日本的绳文文化只相当于中国的仰韶文化,但在数百年间便跃进到接近先秦文化的水平,而这段路程中国走了二三千年。从秦代到盛唐,中国又经历了差不多千年之久,但推古朝改革与大化革新及其后的唐风文化又不过只有二三百年。西方从文艺复兴到殖民主义时代经过数百年,而明治维新却只有数十年。这种极其成功的文化上的跃进在世界上除日本外无第二例,充分显示了日本民族的聪明才智。但是这种成功实际上只有一半的价值,另外的一半即上层建筑的构建并不能算成功。所以日本哲学家井上圆了才会说:“日本古来诸学诸派,皆自支那传来,不闻有一国固有之学,故东洋哲学,唯支那印度两国而已。”中江兆民才会坦承:“我日本自古以来没有哲学。”虽然我们不能说现代化速度太快不好,但弊与利如影随形,由于现代化(这里的现代化是广义的,包括自古以来日本文化的几次大跃进)的速度过快,使得日本民族来不及发育自己意识形态,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他人的思想体系(即以中国文化的丰富底蕴,消化佛教尚且要上千年时间,后来的基督教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消化而始终与中国文化显得格格不入),因此,日本的没有哲学,实在是很自然的事。上层建筑构建未能成功,便与经济基础发生脱节,进而使日本民族出现许多其他民族难以理解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方式。
在文学方面,已有评论者指出,由于日本近代化的过程太迅速,使敏感的作家们难以接受,遂纷纷创造出一个个梦幻的世界,如泉镜花的《高野圣僧》(1900)同夏目漱石的《旅宿》、川端康成的《雪国》以及安部公房的《砂女》(1962)等小说就是对梦幻世界的描绘。
在政治上,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许多可以说清楚的问题,在日本就夹缠不清。譬如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日本人不知道应把好的日本人与坏的日本人区分开来。以为只要是日本人就都是好的,只要是死于战争,就是忠于民族的英魂。所以问题不仅在于政治人物应不应该参拜靖国神社,而在于根本不应把东条英机等战犯的牌位放入靖国神社中去。哪一个民族都有败类与英雄,有些日本人至今还没有学会把他们区别开来。这就是文化上的毛病,这就是思想意识方面的缺陷。
其实无论是亚洲人民还是全世界人民,对待日本都是持极其宽容的态度,只要日本政界表示那怕一点忏悔,舆论就都表示欢迎。例如“日本五政党认为利用慰安妇是战争犯罪”与“桥本龙太郎表示不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消息见诸报端时都是暗含赞许态度的。善良的人们都希望日本政治家能认识过去的错误,因此一次一次地以舆论的形式表示欢迎,结果希望却是一次又一次地破灭。本来利用慰安妇就是彰明昭著的犯罪行为,承认有罪是理所应当,五政党不过是为了大选需要才做此表示,但即使如此,也总还是进步,然而就连这样起码的表态,另外两个重要政党也一点不吭声。后来自民党更是变本加厉,竟然打算把要求外国首脑参拜靖国神社写进党纲中。而桥本的表态则纯粹是欺骗世人,因为即使他以私人身份参拜,也是一种政治行为,也是对亚洲人民的侮辱。
日本是念念不忘要做政治大国的,但并不是世人无端鄙视他们,而是日本至今仍不具备做政治大国的背景。无论从个人而言,或从民族整体而言,日本人都显示了太多的小家子气。在义利之辨中,有些日本人是只取利而不取义的。这种利有时关系到自己,有时关系到主子,有时关系到民族,但却从来没有关系到全世界,关系到整个人类。日本对广岛原子弹事件始终不忘,但他们对亚洲人民在二战中所受到的惨重的牺牲有那么悲痛吗?广岛事件是很悲惨的,死了那么多人,但比较起来,仅南京大屠杀就死了三十万人,还不说这些人死时的悲惨程度,竟有人是死在作杀人比赛的军刀之下的。广岛却是一颗炸弹下来,不分清红皂白死去的。日本有多少人对南京事件表现过与广岛事件一样的痛心疾首呢?
因此,与其努力于做政治大国,不如汲汲于做文化大国。麦克阿瑟是一介武夫,但他对日本民族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他认为从精神上说,日本人不过是一个孩子。虽然这句话在日本备受批评,但如果从哲学的发展与意识形态的完备方面来看,这话是有三分道理的。日本文化的昭示并非在于不要急速的现代化,而是在于如何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但是矛盾也接踵而来,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如果速度过慢,会造成落后就要挨打的局面。如何使国家迅速现代化而又保留自身优良的文化传统,本是一个难题,而对日本文化而言,难题不在于此,而在于在已经现代化了之后,如何改变自己的文化形象,以免沦为经济动物,以免在亚洲或在世界上成为孤立状态。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发展日本固有的文化,并将其从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小文化发展成为有自己完整哲学与意识形态体系的大文化,对日本来说将是比做政治大国更重要的事。今后的世界是容不得哪一个民族或哪一个国家一意孤行的世界,是一个必须学会共处的世界。日本当权者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将会把日本民族拖入一个尴尬的漩涡中去,虽富足而始终充满失落感与孤独感。
其实日本人本身有时也很痛苦,时时徘徊在矛盾暖昧之中。例如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责任,理智要其承认错误,情感却怕受到屈辱。这是耻辱感战胜了罪恶感。于是就只有两种人能反省,而这两种人又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一种是理性的学者和作家,一种是受到良心责备的人。而恰好更重要的两种人无此背景,一是政治家,他们所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当然以国家利益为虎皮;一是青年的一代,他们既无从感受良心的责备,又不大可能作理性的思考,再加上教科书的被篡改,就连历史真象也不清楚。于是随着时间的逝去,日本文化与其他文化的隔膜就会越来越深。1994年大江健三郎获诺贝尔文学奖。在授奖仪式上,大江以《我在暖昧的日本》发表演说:“我觉得,日本现在依然在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暖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暖昧的进程使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就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3)]
要摆脱孤立,只有从文化建设入手,提高全民族的精神素质。热衷于接受现成东西的人没有创造性的思维,只会模仿改进的民族难以养成发明的机制,在上层建筑方面尤其是这样。日本民族有足够的聪明才智,相信他们能在文化方面达到和魂和才的新阶段,脱离过去那种在自卑与妄自尊大之间来回援摆的现象,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化大国。
注释:
(1)转引自武安隆《文化的抉择与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2)参见露丝。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对日本人矛盾性格的描述。
(3)许金龙译,载《世界文学》1995年2月
来源:《复旦学报:社科版》1997年第3期
- 0002
- 0000
- 0001
- 0000
- 0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