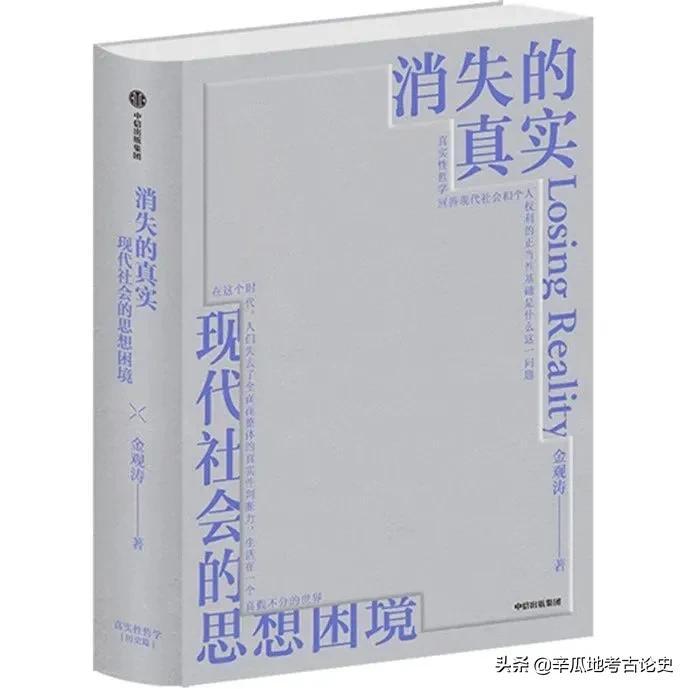葛剑雄:研究中国移民史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内容提要:本文是作者撰写《中国移民史》过程中对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归纳和总结。文献研究仍是中国移民史研究的主要手段,其来源包括:官方史籍的记载、其他古籍中的记载、家(族)谱、地方志等。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中,对间接的记载也应充分重视。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是必要的补充手段,在文献无征的情况下更是唯一的途径。这类研究方法一般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如考古学、人口学、历史地理学、地名学、语言学、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手段和成果等。尽管我们最大限度地综合运用上述研究方法,由于移民历史毕竟不同于现实;仍会有不少无法了解的方面。
关键词:中国移民史 研究 方法 手段
在中国移民史上人数最多的是两类移民:一类是统治者运用官方的权力和财力加以引导、组织或者强制推行的,以及在社会的或自然的外力压迫下大规模爆发的。一类是下层民众为了逃避天灾人祸,维持生存,追求温饱而自发进行的。前者不仅数量大,迁移的时间地点集中,而且移民中往往包括大批贵族甚至帝王、官吏、文人以及随同的艺人、工匠、商人、将士、奴婢等,因而对迁入地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些移民运动在史籍和其他文学资料中留下比较详细的记载,得到比较全面的反映,并且一定受到历史学家的重视,成为研究的重点;如西汉的实关中、移民西北边疆,永嘉乱后、安史乱后和靖康乱后的人口南迁等。后者则是无组织的、零散的、缓慢的,迁移的对象大多是底层的农民或贫民,他们的文化程度低,社会影响小,对迁入地区不会产生急剧的、巨大的影响。这类移民多数不见于史籍的直接记载,数量更不易推断。即使在一些发生过相当集中的移民的地区,往往也只能在地方志中留下一鳞半爪的痕迹。年代久远的,甚至已经没有片言只语可寻了。如明清时期南方由平原向山区的移民,由内地向边疆的移民。但是这类移民几乎随时都在进行着,由于持续时间长,涉及范围广,累计的总数就非常大。尤其是在边远地区、山区和其他处女地的开发,大多是由这一类移民进行或奠定基础的。
当然,我们很难说哪一类移民的意义更重大些,而且在不少情况下还很难将二者加以区别。我们也不能说对前者的研究已经足够了,但是对后者的复原和研究进行得实在太少却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也是有关学者们的共识。由于史料的缺乏,对后者的研究无疑更加困难。而且即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也只能发现其中的一小部分。可是如果缺少了这一部分,就不可能有完整的中国移民史,所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是史学工作者无可回避的责任。对近代以前的移民过程,要运用文献研究以外的方法加以复原,或者通过实地考察来解决全部问题,大概是不可能做到的。因此,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仍然是我们研究的主要手段。
一、文献资料
在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方面,前人和当今的学者虽然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却并没有挖掘殆尽。一方面,这是由于传统的检索方法的局限,对分散在一些非专门史籍中的资料还没有充分地利用。例如在唐宋人的传记、墓志铭、神道碑、序跋和诗词文章中就有不少有关个人或家族迁移的记载,是研究移民史的重要材料。另一方面,有些类型的史料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或者人们还来不及加以整理利用,如家(族)谱和地方志等。
1.官方史籍的记载
历史上一些重大的移民运动往往会在官方史籍史留下记载,有的还是唯一见于文字的记载。如传说中的夏都的迁移、商都的迁移就见于《竹书纪年》、《尚书》等典籍,秦汉以来的规模较大的移民在二十四史、十通、明清《实录》等史籍中都有所记载。
这些文献资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往往成为我们最重要的或唯一的文献依据。由于官方史籍大多数是纂修于当朝或下一朝,基本都是原始档案或官方文件的根据,所以所载移民的迁移原因、时间、迁出地和迁入地等一般是可信的。特别是某一次移民的总的数量,除了这类记载外,就找不到其他史料来源了。如秦始皇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咸阳,汉高祖迁齐、楚大族,燕、赵、韩、魏之后及豪杰名家10余万口于关中,汉武帝时迁关东贫民72万余口于西北——要是没有《史记》、《汉书》中的记载,现在就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研究出这样具体的数字来了。特别是一二千年以前的移民,现在早已无踪迹可寻,在其他古籍和家谱、地方志中也找不到可信的资料,离开了官方史籍就无法查考。
但官方史籍的局限性也是很明显的。首先,作者所记内容自然以对当时统治者的重要性及有利无害为取舍的标准,因而所载移民一般只包括由官方组织实施或强制实行的,至多只记载了那些得到官方认可的自发移民,而不会包括大多数自发移民。甚至连官方实施的移民也只有十分简略的记载,或者只记录了其中一些片断。如明初的大移民涉及上千万人口和大半个中国,但在《明实录》、《明史》等官书中只有寥寥数段,使后人长期忽略了这次移民运动的规模和范围。其次,官方所载移民情况往往有头无尾,只有皇帝下令迁某地多少人至某地,结果如何?究竟有多少人迁成了?是否真在迁入地定居了?书中再也找不到答案。再次,史籍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错漏脱讹在所难免,不能完全信从。如前面提到的汉武帝迁关东贫民于西北,《汉书》上就多了“会稽”二字,一些学者信以为真,认为西汉时江南已开始大规模输出移民,由此引出一系列错误结论。
2.其他古籍中的记载
这些古籍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虽非官方史籍、却是以官方的文献资料为主要依据而编纂或撰写的,这类书的价值与官方史籍的价值是相同的。唐以前的官方史籍传世不多,这类书就更加珍贵。有的虽然仅存残卷甚或片言只语,但还是能证实某一方面的问题。如《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注文中有一些类书中所引的佚书,往往包含了重要的史料。第二类是已经著录的出土文献,如古代的墓志铭、神道碑、碑刻、石刻、题记文字等,相当大一部分已在出土后被收录进有关的著作。有的原物早已不存,但却留下了拓片或传抄的文字。有的原来仅见文字记载,以后又为新出土的原物所证实。如在鄂伦春旗嘎仙洞发现的鲜卑石室中的石刻文字就与《魏书》所载基本相同,这就证实了《魏书》这一部分的真实性,为确定早期鲜卑人的活动范围和以后的迁移路线提供了很可靠的根据。这类记载的价值与出土文物基本相同,尽管其中难免有一些文字错误,也可能有个别伪作,但绝大多数可当作第一手的史料。第三类是或多或少记载着与移民研究有关内容的各类古籍,如公私文件、日记、行记、游记、奏章、传记、神道碑、墓志铭、诗文、书信、序跋、题记、歌谣等。由于内容非常分散,获得有用的资料就如同沙里淘金,往往翻遍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也不一定能找到一二句话。但正因为作者当时并非有意作正面或全面的记载,所以倒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某一个侧面的情况。例如某人的传记中讲到他何年何月从何处迁至何处,很可能正好证实了某一次移民中的重要一支;一份奏章中报告的内容,可能就是一次移民的具体原因;一种游记记录的某地人文景观,足以证明该地移民的重要地位;等等。当然这类记载也有其局限,如诗文内容往往多夸张,行记、游记所记可能出于道听途说,传记、墓志因扬善隐恶而失真,诸如此类必须在运用中加以注意。
3.家(族)谱
在现存的超过4万多种家(族)谱中,每一种家谱一般都详细地记载了先辈在何时由何地迁到了何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该家族迁移的历史。对于一些自发的、小规模的、分散的移民,有关的家谱可能已成唯一的文字记载来源了。因为普通的一家一姓的迁移,对社会固然不会有什么大的影响,自然不可能有载诸史籍的价值;但对于该家族的后裔来说,却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大规模的、官方安置的、集中的移民,正史和其他史料的记载也往往失之粗略,缺乏具体而详确的叙述,更没有定量分析。究竟有多少人?从哪里迁到哪里?迁移的路线有哪些?多少人定居了?多少人又返回或迁走了?移民的成份有哪些?等等,大多是找不到答案的。尽管一二部、一二十部家谱也不一定找得到完整的答案,但如果能集中若干种有关同一次迁移的家谱,就有可能作出比较具体的分析。在这类资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再运用科学的计算方法,就会获得相当可靠的结果。
家谱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一般的家谱都要找出一位煊赫的祖宗,不是帝王、圣贤,就是高官、名人,甚至要追溯到三皇五帝。由于这些上古贵人基本都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要使本家特别是不在黄河流域的家族与这些祖先联系起来,就只能编造出一段迁移的历史。
一部分家族的确是有过迁移的,但为了把他们祖先的迁移史附会于历史上确实存在的大移民,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所以具体的迁移时间、地点就不一定正确。由于这些移民都是历史事实,所以人们往往会对这些家族的来源深信不疑。但因为这些家族的祖先实际上并不是那些移民运动中的迁移对象,所以如果轻信了这些家谱中的记载,就会影响我们对移民的历史的正确复原。例如,不少客家人的家谱中都有本族的始祖是东汉末年或永嘉之乱后从北方迁至今闽南、赣南或粤北的,国内外的客家研究学者大多都以此为根据肯定这是客家人的第一次大迁移。但如果我们对公元2世纪末至4世纪的北人南迁作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就不难发现当时南迁的浪潮所及还离闽南、赣南很远。即使有一些零星移民迁至这一带,也不足于形成一个能使自己长期不被周围土著居民融合的独立群体。事实是,客家人的南迁并形成一个不同于土著居民的群体并没有那么早,客家家族谱中关于始迁祖的记载并没有可靠的史实依据,而是出于后人的附会。
另一些家谱中所载始祖的迁移时间并没有错,但地点和原因却不一定对。这是由于有些家族始迁到某地的祖先当时既没有社会、经济地位,更没有文化,有的甚至还是以罪犯的身份被强制迁去的。到了有条件修谱时,一个家谱一般都已支派繁衍,人丁兴旺,并有了相当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有的还成了书香门第、官宦人家,子孙们即使对祖先的来历弄不清楚,也不能在谱上出现空白;或者知道祖先是如何迁来的,却不愿意留下不大光彩的记录。常用的办法,一是根据当地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将本族的祖先当作其中的一员,一是将迁入时的目的或身份改得尽可能地体面。例如,苏北地区不少家谱都说祖先是明初由苏州或苏州阊门迁来的,其中大部分就不一定是事实,有的可以肯定不是来自苏州,而是迁自江南其他地方。主要原因是当时朱元璋的确曾从苏州迁过一批富户到苏北,这批人虽然被迫迁移,但毕竟有经济实力,文化水平也较高,自然成为苏北地区移民中的上层和主流阶层。迁自其他地方的零星或贫穷移民,当即既没有必要也不敢冒称来自苏州,但到他们的子孙发达后修家谱时,无论是弄不清祖先从哪里来,还是故意回避,写上祖先由苏州迁来都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又如一些家谱称始迁祖是在明初“奉旨分丁”、“奉旨安插”,或者是来某地当官、驻防的,实际上可能朱元璋根本就没有下过这样具体的圣旨,这些始迁者也不是什么官员或将军,所谓“奉旨”无非是流亡到此开荒定居后得到了官府承认被纳入编户,或者就是被绑着双手押送来的。
以上两种情况尽管在具体情节上有出入,该家族是移民后裔倒是事实,所以只要认真分析,再结合其他史料,还是可以大致弄清历史真相的。但第三种情况就根本不存在迁移的事实,家谱中的记载千万不可轻信。这主要发生在南方或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中。随着汉族移民的增加和经济文化的进步,当地一部分少数民族家族也发达起来,但在封建社会民族歧视政策的影响下,要取得与汉族同样的社会地位还是相当困难的。所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少数民族家族,就通过修家谱将自己的祖先说成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如谪居的官员、从征的将士、流落的文人等。由于这也满足了汉族官员和士人的民族优越感,所以很容易得到他们的认可。如从唐朝后期起世居贵州的杨保族,到明初就编出了是北宋杨家将之后的谱系;不少广西的壮族家族都说祖先是宋朝随狄青征蛮而迁来的;清朝贵州独山学者莫与俦、莫友芝父子明明是布依族,却要说是迁自江宁。这一假象如果不识破,我们就会编造出根本不存在的移民史来。
4.地方志
现存的8000多种地方志,绝大多数纂修于明、清及民国时期。这些方志在追述历史及引用其他史料时往往会错误百出,但在记叙当地、当代的事件与状况时却大体是可信的。尽管也颇有详略失当之处,却保存了不少不见于其他任何书籍的史料。与家谱的记载相比,方志的史料一般更加集中、更加重要,大多是对该地方有相当影响的移民及有关情况。此外,方志中还保存着一些有价值的原始资料,如有关的文书、告示、诗文、歌谣等等,以及反映移民背景的记载,如风俗、方言、物产、会馆、祠庙、氏族、户口、赋役、地名等等。有些资料的原物早已不存在了,就靠方志的记载或总结才得以保存至今。如方志中的“氏族”一门所依据的家族谱牒,今天一般已难收罗得如此齐全。尽管我们无法见到原本,但利用这一门的统计数还可以分析移民家族的来源、迁入时间、定居后的具体分布和规模。正因为如此,要研究明代以来的移民,就绝对离不开方志。仅仅依靠全国性的史籍和其他著作,就不可能取得具体可靠的研究成果。
近年来已经问世和正在编纂的新方志大多承接以前的志书,填补了数十年或百余年的空白。在编纂的过程中,各地搜集和记录了大量珍贵的史料。许多地方还利用地名普查和人口普查的资料和数据,编成了地名录、姓氏录、人口志、民族志、氏族志等实用的工具书。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资料来源。
在以上这些文献资料的收集和运用中,对间接的记载也应该予以充分的重视。这是因为移民和人口一样,是社会、自然和人类自身活动的复杂产物,不仅有深刻的原因,也会产生其必然的广泛影响。所以有关其原因和影响的记载反过来也能用于复原移民史的某些片断,考察移民本身的过程、范围和数量等各个方面。
不过,文献资料毕竟是有限度的,直接的记载更是可望而不可及。即使作出更大的努力,文献资料中存在的巨大空白,特别是唐宋以前的阶段,显然还将是无法填补的。这就需要寻求非文献的研究方法,使用新的研究手段。
二、文献以外的研究方法
运用文献考证以外的研究方法,其原理与前者并无二致,只是适用的范围有所不同。这是由于移民的影响或痕迹有的本来就没有进入文献记载,有的虽曾进入却早已散佚了。但在一些相对闭塞、流动较少、发展缓慢的地区,以往移民的影响或痕迹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尤其是在风俗习惯、方言、宗教信仰、姓氏、地名、建筑形式、文物古迹等方面,有可能通过调查考察加以收集,并通过各相关学科的研究手段加以复原。由于这些事例或数据大多既零散又繁琐,而且分布不均、多寡悬殊,非有合理的抽样方法和缜密的统计手段不可。
文献记载与实地调查考察这两方面实际上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把这两方面的研究结果互为补充,互相印证,才能相得益彰。不进行实地考察固然无法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也不能使抽象的记录具体化;但如完全脱离文献记载,实地考察的结果也不可能全面深入,更不可能与当时全国或更大范围的移民形势联系起来。
非文献的研究方法一般都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手段和成果,主要有:
1.考古学的方法
主要是通过考古发现或鉴定的遗址、遗物及其地理分布来证实、否定或补充文献资料的记载。对离今天较近的移民运动有可能进行实地考察,因为在移民的迁入地或迁出地都可能找到能够反映移民现象的一些实物,并可能向移民本人或他们的后裔以及其他人员作调查,收集口述史料。例如对本世纪三四十年代向东北地区的移民作研究时,我们完全可以在非东北各地或山东、河北等输出移民的地区找到移民本人、他们的子女后人以及直接了解迁移的具体情况的人,也可以发现很多第一手的档案文书、照片和实物。但对上古时代或数百上千年前的移民就无法作同样的调查,除了文献记载外就只能依靠考古研究的成果。
考古发现的遗物和遗址是当时社会和人们物质生活的一部分,尽管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片断,但毕竟真实地保存了这个片断,为我们正确复原历史事实提供了可靠的基础。例如,《后汉书·西羌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伐戎。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之旄牛种,越裔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
根据这一记载,羌人的一部分在公元前四世纪后期曾经有过一次大迁移,从渭河上游迁至黄河上游河曲地区,又南下直到今四川西都和云南。由于这段文字相当简略,有关这次移民的具体情况语焉不详,究竟是否可信不无疑问。但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在今横断山脉地区、四川岷江上游和川西其他地区存在一种“石棺葬文化”,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色,其渊源就是西北甘青山区的氐羌文化。这一文化的年代上限相当于西周晚期,而盛行于战国至西汉时期。这就证明,羌人的南迁确有其事,并且在西周晚期就开始了。
又如扬雄的《蜀王本纪》的佚文是目前传世最早的关于蜀地先民来源的资料,但其中羼杂着神话、传说的成份,加上内容残缺,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
蜀王先名蚕丛,后代名曰柏濩,后者名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皆神化不死,其民亦颇随王化去。鱼凫田于湔山,得仙,今庙祀于湔。时蜀民稀少。
后有一男子,名曰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日郫,化民往往复出。
望帝积百余岁,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
这里提到蚕丛、鱼凫、杜宇、鳖灵的来历,实际上是不同部落首领的迁移和消长,但仅仅依靠这几句话是很难作进一步推断的。而近年来对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文物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已有可能对其中一些部落的兴衰过程和大致时间作出新的判断,至少证明了扬雄的说法并非完全出于后人的附会和想象。
又如《史记》载周人古公亶父之子太(泰)伯和仲雍由今陕西迁至江南,在今无锡一带建吴国。到周武王克殷后,其五世后人虞仲又被封于中原今山西南部。但1954年在江苏丹徒烟墩山出土的《宜侯矢簋》上的铭文和周围地区出土的大批文物都证明,江南的吴国是在周康王时由山西的虞国分封出去的,其地先在长江北岸今江苏仪征一带,以后迁至丹徒附近,再由宁镇丘陵发展到以东的平原地区的。
当然考古学的方法也不是万能的。考古研究的依据是山土或传世的遗址和遗物,但经过数百年数千年自然和人为的破坏,能够保存到今天的遗址和遗物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并且因各地区间自然与社会条件的差异而多寡悬殊。如在西北人口稀少、气候干燥的地区,古代的遗址遗物保存较多,受到破坏也较少;而在东南人口稠密、气候湿润、地下水位高的地方,遗址遗物存在的可能性就要小得多。其次,古代遗址遗物发现的多少还取决于人们发掘的状况,已经发现的文物并不一定反映了它们存在的实际情况。至今没有发现或很少发现古代文物的地方不等于就没有或很少存在文物,更不等于说历史上就没有存在或很少存在过这些物品。可是考古研究却只能以已经发现的遗址遗物为根据,只能据已有的证据说话,所以即使是最完满的研究成果也不可能完全取代文献资料,不能运用于所有的历史时期或各个地区,更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除了某些特殊情况外,遗址遗物中的文字资料是相当有限的,所以根据考古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很难在时间、地点、数量、名称等方面作出精确的判断,需要与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互相印证,相得益彰。
运用考古成果时,还应注意将遗址和遗物区别开来。遗址是不能移动的,据此判定的地理位置是不会错的。但遗物一般是可以移动的,其原因又极其复杂,所以遗物出土或发现的地点并不一定就是该物的原产地或原持有人居住的地方。例如春秋吴国的器物在楚国的地方出土,不能据此就断定吴国人曾经迁移到了楚国,或者曾经占领过这个地方,因为楚国人或其他人也可能将这些器物带到了楚国。而且有些器物是可以长期保存或使用的,这些器物的出土并不一定能为某一历史事件确定时限。如在某地出土的明代的瓷器很可能是清代的移民由外地带来的,不能因此肯定这里必定有明代迁入的移民。
2.人口学的方法
移民本身就是一种人口现象,属于人口学的研究范畴,人口学的方法用之于移民史研究自不待言。但在移民史的研究中,由于资料的不足,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成果往往能起特殊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一个范围固定的区域中,人口数量的变化就决定于两方面:人口的自然增长和因迁移造成的机械增长。在不发生大规模的天灾人祸的条件下,一个地区在较长时期内的人口自然增长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在自然和社会条件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地区之间也不会有很大的差异。根据这一原理,一个地区的人口实际增长率、特别是地区之间和不同年代之间的比较,可以作为判断是否有过移民的根据,也可以用于推算移民的数量。
假定一个地区的常年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作为参照的同类地区同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为R[,1],要进行研究的某一特定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为R[,2],如果R[,1]与R[,2]有较大的差距,而在这一阶段又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天灾人祸,那么就可以考虑该地属于移民迁入地或迁出地的可能性。例如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至东汉永和五年(140年)之间,零陵、长沙和桂阳三郡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3.5‰、11.6‰和8.3‰,而同期全国人口的平均增长率估计不会超过7‰,南方其他地区的年平均增长率估计不会高于5‰。据此可以断定,这三郡在这一百多年间有大批移民迁入,属于移民迁入区。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推算移民的数量。设某一地区在特定阶段中的理论年平均增长率(即该地的常年年平均增长率或作为参照的同类地区同阶段的年平均增长率)为R[,1],就可求得该地在这阶段末的理论人口总数P[,1]。以该地该阶段的实际年平均人口增长率为R[,2],即可求得在这阶段末的实际人口总数P[,2];或者可使用现成的实际人口总数P[,2]。P[,2]与P[,1]的差距就是该地在这一阶段间迁入或迁出的人口总数。如果这一阶段较长,如超过了一代(二三十年),那么对迁出来说,这是指迁出的人口的总数;对迁入地来说,是指迁入的人口与他们的后裔的总数。
这一判断似乎相当简单,但在运用时却必须十分谨慎,特别是不能将传统史料中的户口统计数不加分析地当作实际人口数来运用。上面所提到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必须是真正的人口增长率,而不能用户增长率。历史上很多情况下的户口负增长实际上并不反映实际的人口变化,而只是户口隐漏越来越严重的结果。如果误以为凡是没有发生较大天灾人祸期间户口数量有较大幅度下降的地区都是人口迁出地区,那就是上了虚假的户口数字的大当了。同时还应注意数字的可比性,即在所研究的阶段中这些人口数据所代表的地域范围必须相同。由于历史上行政区划的变化有时十分频繁,在不能选择相同的地域范围的条件下,就应充分考虑这一因素产生的影响。
一个地区人口性别比的变化也能反映移民的特征。一般说来,在输出和输入移民都很少的地区,人口的性别比较稳定,在短期内不会有大幅度的变化。但在移民迁入地区,特别是移民占当地人口大多数的地区,人口的性别比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并且因移民成份和迁移条件的不同而有明显差异。移民的家庭结构和规模(户均人口)也有这样的变化特点。和平时期移民的性别比和家庭规模比较正常,战乱时的移民因残破家庭及单身较多,迁移途中死亡率高,所以在定居后性别比往往偏高或偏低,户均人口少。上层移民和官方资助的移民性别比和家庭规模比较正常,下层移民、自发的开发性移民、军事移民、由农村迁入城市的第一代移民中间男性人口的比例较高,单身多,户均人口少。迁出地区一般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但如果迁出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不高,这些结果不会有明显的影响。人口结构的这些变化规律反过来可能用以推测移民的状况,但由于历史时期基本上没有性别比统计数据,缺乏可靠的家庭规模数据,使这一方法在多数情况下只具有理论上的意义。
3.历史地理学的方法
移民史研究的很多方面与历史人口地理的研究是重合的,而历史人口地理是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所以历史地理学的多数研究方法完全适用于移民史研究。而且,同一切发生的历史时期的事件一样,移民史研究离不开具体的疆域、政区的范围和地理坐标的确定,也离不开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复原,这些都得借助于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历史上的移民既有适应地理研究的一面,也有促使地理环境——无论人文的还是自然的——发生变化的一面。因此,通过复原历史地理环境及其发展变化的过程,有可能显示出移民过程及其影响的某些片断,弥补文献资料的不足。这里举两个例子:
政区设置过程的分析。在正常情况下,新的政区的设置与地区开发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因此分析某一地区中行政区域设置的过程和这些政区相互间的关系,就可以复原出该地区的开发过程,也就可能了解该地区内的人口迁移过程和方向。
谭其骧先生从行政区域的设置过程着手,论证浙江省的开发过程,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见《浙江省历代行政区域——兼论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原载1947年10月4日杭州《东南日报》,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见《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和省界、地区界的形成》,载《历史地理研究》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也是移民史研究可以利用的成果。他的根据就是“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始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弄清了一个新县是从哪一个或哪几个老县分出来的,也就大致可以肯定开发该县的动力,即最早来那里开垦的人民是从哪里来的。”根据浙江省各县设置的先后和析置所自,推断出省内移民的时间、过程和范围。在研究及复原相邻地区间的移民时,这种方法无疑是有其应用价值的。边疆地区、新开发地区行政区域的设置过程往往也是与移民定居过程和数量增加相一致的,所以也能应用这一方法。
迁移路线的复原。对移民的迁移路线,史料中往往缺乏具体的记载,即使是一些规模很大的移民运动也不例外,有关早期的移民迁移路线的记载更加简略。在机械交通工具问世之前,地理环境对人类的交通具有很大的制约性。尽管可能出现个别特殊情况,大多数移民的迁移路线还是会取在当时条件下克服地理障碍最便利的一条。因此,我们只要复原出当时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环境,或者复原出当时的交通路线,再结合史料中的记载,就可能大致确定移民的主要迁移路线。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既要了解古今地形、地貌、水文等自然地理景观的变化,也要充分注意到人文地理因素的影响。例如黄河下游的改道、海河水系的形成、长江三角洲地区水道和海岸线的变化,都会使通过这些地区的交通线发生变化,运河的开凿或废弃、河堤和海塘的修建也会改变交通线和交通方式。
4.地名学的方法
移民的迁入地、迁出地以及迁移路线都涉及大量地名,这些地名的点、线、面的确定虽然主要通过历史地理的方法,但也离不开地名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移民还导致地名的发展和变化,所以对这些发展和变化的考察又反过来可以用来发现或证实移民的事实。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各种差异使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民族的人们命名了各种不同的地名,其中一部分在读音、用字、意义、结构或命名方法上具有鲜明的地区、时代或民族特点。通过对这些特点的收集、归纳和分析,往往可以了解历史上某一类人口的分布和迁移过程。例如江南的很多古地名都以于、余、姑字开始,显然都是由古越人命名,证明这些地方曾经是越人的居住区。山东半岛在秦汉时还有不少以“不(音夫)”字开头的地名,这类地区的分布反映了此前土著民族的分布范围,也可以看出由西周分封而来的鲁、齐二国与土著的消长过程。在不同类型、不同时期的移民交错迭加的地区,这类地名往往成为判断不同移民群体的界线的依据。
古代的非汉族基本上没有留下系统的文字记载,现存的历史地名大多是用当时的汉语读音记录下来或翻译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时一定要注意区别地区不同的民族语源和方言来源。不能认为是同一个汉字的地名都出于同一来源,更不能望文生义,只用汉语的意义对非汉族地名作牵强附会的解释。有人把带有一个汉字的地名都看成某国或某族的迁移所及,因而得出了与历史事实大相径庭的结论。
由专名和通名组成的地名,通名部分的不同往往直接反映了移民的结果。如按照明朝的制度,土著之民编为里,迁发之民编为屯,所以华北各地带屯的地名一般都起源于移民村落,一个地方里、屯的数量和比例大致能代表土著、移民的数量和比例。西南地区带屯、营、堡、旗的地名,往往与明清时的军事移民有关。各地的卫、所,基本上都是明代卫所制度的产物,可以追溯到明代的军事移民。专名部分的特点虽然没有那么明显,但也可以作为研究的线索。例如在“迁安”、“来安”、“归安”一类祈愿性的地名集中出现的情况下,一般都可以作为存在着移民聚落的佐证。
由于人们有将原来的地名使用于新迁入地的习惯,所以历史上出现过无数地名搬家,原来在北方的地名以后出现在南方,本来应在沿海地区的地名却转到了山区,域外民族和少数民族的地名却在汉族聚居区落了户。原始地名的转移过程在很多情况下是与当地人口的迁移过程一致的,而且由于少量的、流动的人口一般不可能引起这种转移,所以一个原始地名转移的完成实际上就标志着一次移民运动的完成。如从甲地迁出的一批移民,如果他们只在乙地停留了一个短时期,或者其中有少量的人迁入丙地或丁地,一般是不可能将甲地的地名转移到乙地、丙地和丁地的,要等到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戊地定居后才有可能用甲地的地名命名他们的新居住地。在文献资料缺乏的条件下,这无疑又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手段,使我们得以通过考察地名转移的过程来复原移民的迁移和定居过程。如商人喜欢将他们的部落首领居住的地方或都城称之为“亳”,所以在黄河中下游留下了不少带“亳”的地名,以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确定这些亳的存在年代或出现先后,就可以描绘出商人的移民过程。当然商人在迁移过程中居住过的地方不止这些亳,但我们可以肯定亳是数量较多、地位较高的商人比较稳定的、主要的定居地,研究这些地名比其他地点具有大得多的意义,也更符合我们所规定的移民的定义。
在原始地名出现过大规模的、系统的转移的情况下,这种方法就更加有效,有可能据此复原整个移民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西晋永嘉之乱后北方人口南迁后,东晋在南方大量设置侨州、郡、县。这些侨州、郡、县不仅使用原来的行政区域名称,其居民也主要由原政区的人口构成。北方除了地处辽东的平州外,各州都在南方设置了相应的侨州、郡、县。这些侨置政区的设立过程和地理分布,基本上也就是北方移民的定居过程和地理分布;谭其骧先生《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一文(原载《燕京学报》第15期,1934年6月;收入《长水集》上册,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就是运用这一原理的成功范例。根据这些侨郡县在南朝宋时的户口数,还可大致推算出这次移民的规模。
又如:明初的洪武、永乐年间曾多次将大量山西人口迁至华北,所以在今北京市郊县至今还保留着大量以山西地名命名的村落名称。如在今顺义县西北有绛州营、稷山营、河津营、夏县营、红(洪)铜(洞)营、忻州营,今大兴县凤河沿岸有石州营、霍州营、解州营、赵县营、留民营、沁水营、长子营、河津营、北蒲州营、南浦州营、上黎城、下黎城、潞城营、屯留营、大同营、东潞州、包头营、山西营(转引自尹钧科《明代北京郊区村落的发展》,载《历史地理》第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值得注意的是,凤河西岸还有北山东营,与文献所载永乐二年也有山东移民是一致的。全面调查这些地名的分布情况和规律,无疑能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有助于确定山西移民的具体来源和定居过程。
运用这种方法时,必须注意地名在转写、转译过程中的变化。古汉语的发音与今天不尽相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对同一个地名的发音也会有差异,在将非汉族的地名翻译或转写成汉语的过程中也会产生误差,原来不同的地名可能会变成相同的汉字,而同一个地名却会产生不同的译名,因此简单地根据汉语地名或今天的读音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西汉张掖郡有一个骊靬县,而汉朝的史料如《史记》、《汉书》、《说文解字》等将大秦国(罗马帝国)称为黎靬、黎轩、犁靬、黎污或丽靬等,所以长期以来人们都认为这个县的来历与大秦有关,甚至认为此县就是以大秦的眩人(杂技演员)或降人设置的;也有人认为骊靬是亚历山大的异译,所以此县应与亚历山大有关。但是在《汉书·匈奴传》中还载有一个匈奴的犁污王,他曾在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率4000骑入侵汉朝的张掖郡,被击败后仅数百人逃脱,立下战功的义渠王被封为犁污王。以后的骊靬县就在这一带,所以得名于犁污王的可能性更大,而此县与大秦国的关系倒缺乏可靠的证据(详见拙文《天涯何处罗马城》,载《往事和近事》、三联书店1996年版)。
在一个新开发地区,随着定居人口的增加和新的聚落的形成,必然会有新的地名陆续出现。在原来已有一定开发程度的地方,如果有大批移民迁入并且保持聚居的话,也会出现一批新的地名。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新地名的出现可以视为一次移民运动完成的标志。明清时期,大批移民陆续迁入南方和西南山区,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个居民点。这些居民点一般都以移民的原籍为基础,所以如果能查清它们的建立年代和各自的移民来源,就为这一移民过程确定了时间和空间的范围。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台湾和东北的移民过程中,因此也可以由这一途径入手进行研究。
对移民形成的自然村的统计和分析,可以作为移民作量化分析的基础。尽管自然村有大小之分,移民数量有多少之别,但在同一阶段形成的同类自然村——如明朝永乐年间在平原地带形成的自然村——的人口数量不会有太大的差别,可以大致作为同一个数量等级。但由于移民定居后的自然增长,不同阶段形成的自然村最终的人口数量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形成的时间越早,人口数量越多。所以,如果我们掌握了一个地区内由移民构成的自然村的形成时间和数量,就有可能作出比较正确的数量分析。
5.语言学的方法
方言众多是汉语的一大特点,语言学家根据各种方言的基本特征及其地理分布,在汉语区划出了若干方言区和亚区。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与历史时期的移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同样,历史时期的方言区也与此前的移民活动有密切的关系。原始方言区主要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但当人口在不同方言区之间迁移时,移民就对方言区的变化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来自其他方言区的移民对迁入地原有方言有影响取决于四个主要因素:
一是移民的数量,既包括其绝对数量,也包括其相对数量,即在迁入地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数量太少的移民一般不可能对当地的方言造成明显的影响,只能被当地的方言所同化。数量稍多的移民可能会对原有方言造成影响,使其发生一定的变异,但还不足以完全改变或取代原有的方言。只有数量相当大,如占压倒优势时,才能使原有的方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或者能够用移民自己的方言取代原有的方言。但数量的标准不是绝对的,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
二是移民的集中程度。所谓集中,既指居住地的集中,也应指迁入时间的集中,即足以在一个特定时期内产生使移民在迁入地的全境或某一局部占压倒优势的条件。有时迁入的移民绝对数量并不少,但由于居住分散,所以还是淹没在土著人口之中;反之,聚居的移民尽管人数不多,却能在局部地区形成自己的数量优势,或形成一个相当封闭的语言环境。同样,分散在很长阶段内迁入的移民,由于每年迁入的数量有限,所以也先后被当地方言所融合,很难形成外来方言的优势。
三是移民的社会地位。移民的社会地位越高,文化经济上的优势越大,掌握的行政权力越大,他们的方言对当地原有方言的优势也越大。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地位高、文化经济先进或大权在握的移民不仅有强烈的方言优越感,而且可以利用自己的影响和权力来保持和推行自己的方言,至少可以不受到迁入地原有方言的强制同化。另一方面,土著居民为了迎合这些上层移民的需要,或出于对先进文化的仰慕仿效,或受到官方的压力,会改变自己的方言,甚至完全放弃原有方言,改而采用移民的方言。如在南宋的都城杭州城中,来自北方特别是首都开封的移民不但数量多,而且包括皇帝宗室、文武高官、富商大贾、文人学士等上层人士,使移民拥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文化优势,天长日久,原有的杭州方言被一种新的、带有明显的开封话特色的方言所取代,以至时至今日,杭州话还是带北方味的半官话,与毗邻地区的方言完全不同。又如明朝随卫、所驻屯而迁入各地的军事移民,尽管一般数量不多,但由于居住地高度集中,在当地居统治地位,又有较严格的军事组织,所以他们的方言得以长期延续。客家人虽不一定有高于迁入地土著居民的社会或经济地位,但他们有强烈的方言意识,因此也一直保持着自己的方言。
四是移民的方言与迁入地原有方言间的差异。差异越大,语言上的冲突越激烈,不是“你死我活”,一种方言消灭另一种,就是势均力敌,长期并存。而在差异不大的情况下,往往容易相互影响,使原有方言发生微小、缓慢的变化。
上述这些因素不是孤立存在的,也不是孤立起作用的。移民与迁入地的土著居民间的方言关系是如此,不同来源的移民群体间的方言关系也是如此。历史上和当代汉语方言区的形成与移民有如此密切的关系,那么通过对这些方言区及亚区的考察自然也可以反过来复原历史时期移民活动的若干片断。如上面提到了杭州的方言与北宋末开始的北方移民的迁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缺少文献资料的情况下,方言往往能成为确定某次移民运动是否存在,移民来自何处,何时迁入等问题的重要证据。
汉语区中还存在一种“方言岛”,即一个或大或小的地区内的人口使用一种与周围地区不同的方言。方言岛与移民的关系更加密切,特点也更明显,尤其值得移民史研究者重视。
6.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
人口是文化最基础的载体,迁出地的文化通过移民这些载体传播到他们的迁入地。与方言一样,迁出地文化在迁入地会发生各种变化,或兴或衰,或存或亡。由于物质的、精神的文化现象异常复杂,传播和存在的条件迥异,所以有的很快消失,有的却能长期存在;有的天下皆然,有的却独此一家。我们要研究移民史,就得选择既与移民活动有因果关系,又能在较长时间内稳定存在的文化现象,利用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进行考察和分析,作为移民历史的佐证。
在物质文化方面,民居的建筑形式是有代表性的。民居不同于官方建筑,后者是权力和制度的象征,所以必须有一定的规范;前者虽然也受到气候、地形、地势、建筑材料等条件的制约,但在形式上却比较自由,因此有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些特色往往会随着移民的迁移而扩大到他们的迁入地,并且保持相当长的时间;不同来源的移民会有各自的民居特色,一段时间内能在同一迁入地并存;但先进的、适应本地条件的民居形式最终会取而代之。如江南古越人住的是干栏式建筑,但北方汉人迁入后逐渐消失。唐宋时今湖南很多地方的民居是板屋,以后随着江西移民的迁入,板屋为砖房所取代。清代后期迁入广西桂平县的移民主要有广(州)肇(庆)派、嘉(应州)惠(州)派和闽派三大集团,也保持着各自的住房形式。
在精神文化方面,民间信仰和崇拜又是有代表性的。在众多的民间俗神中,有一部分是具有强烈的地方特点的,如妈祖、许真君、二郎神等。但移民打破了原来的信仰地域,将它扩大到了新的居住地,出于对这些地方神的崇拜而建立的宫观寺庙也出现在移民的迁入地。这类建筑物的出现不仅是某地移民存在的证据,而且说明他们已有相当的数量,并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如万寿宫、萧公祠是江西移民的专利,妈祖庙或天妃宫是福建人或客家人的活动场所,玉王宫、寿福寺为湖南人所建,蜀王庙必定来自四川。城隍庙虽各地都有,但各个城隍爷却都是具体的人物,移民往往会将故乡的城隍爷搬到迁入地去,如18世纪时很多西南城镇的城隍爷都是四川、湖南、江西籍贯,这些城隍庙显然是移民所建。
民俗可谓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混合,因此移民既要保持并传播其迁出地原有的风俗习惯,也不得不加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物质条件。一般说来,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大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习惯只能适应迁入的环境,所以改变较快;而婚丧节庆、祭祀、禁忌等活动以及较少受到物质条件限制的某些生活习惯、称谓等往往能在迁入地保持很长的时间。所以,某种喜庆仪式、丧葬方式、禁忌、饮食癖好、装饰、称谓就能成为区别移民与土著、不同来源的移民、迁入先后的移民的标志。
由于我们需要研究的是历史时期的移民,绝大多数已不能通过实地调查的方法来加以考察,所以以上6个方面的方法一般也离不开文献资料的帮助,并且很难依靠某一方法解决全部问题。尽管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但多种方法的结合、文献资料的研究与非文献资料的研究结合,就为我们提供了最大限度地复原移民历史事实的可能性。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历史毕竟是历史,总有一些历史事实是永远无法了解的,移民史也是如此。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1997年第4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4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