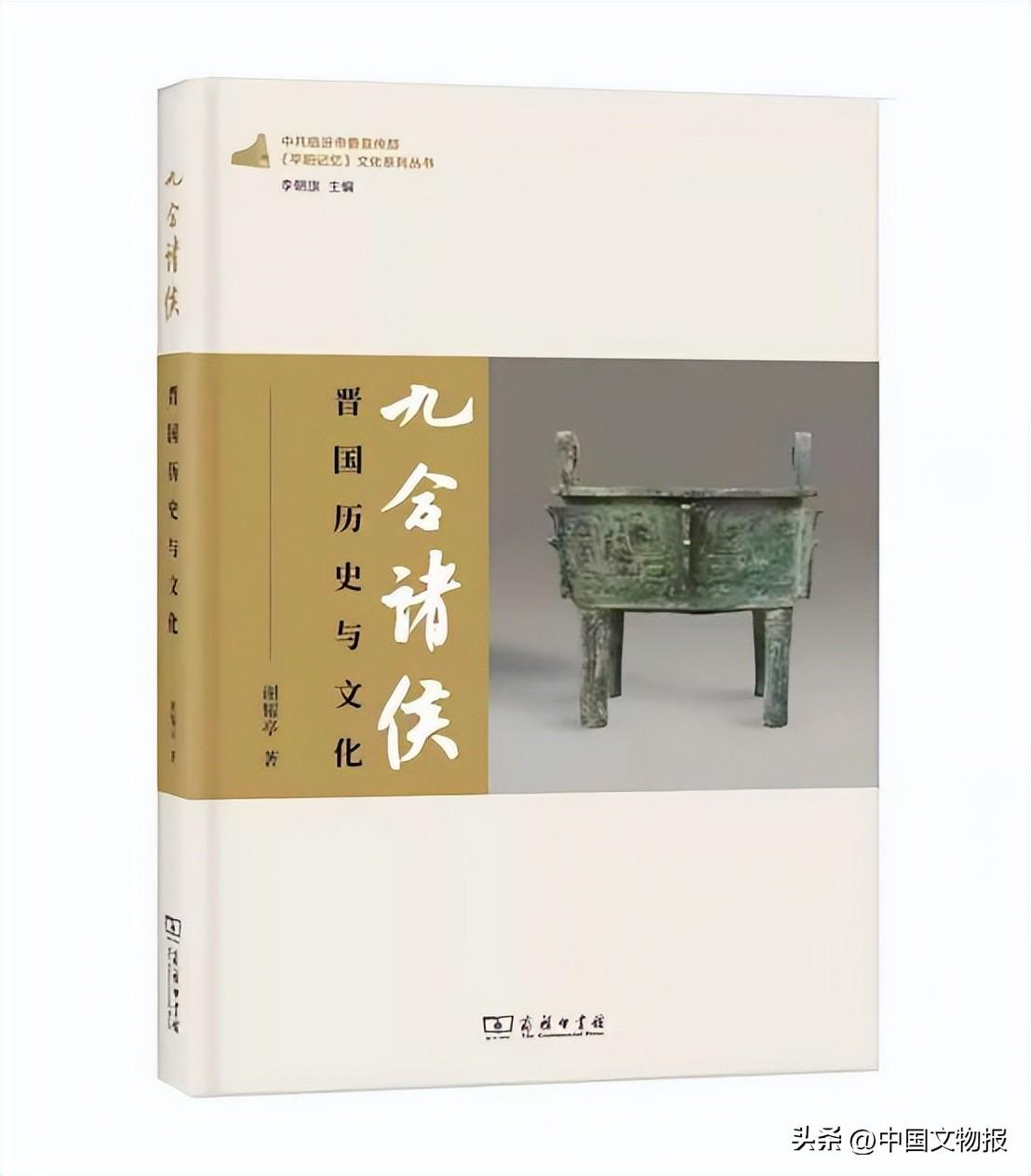郑蓉妮;梅建军;潜伟:研究盗掘文物的学术伦理问题评析
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来研究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作为知识和理论的集合,考古学本身不涉及道德判断。但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考古学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所使用的研究材料的获取途径和性质,却有可能涉及学术伦理问题。近三十年来,欧美学术界对研究盗掘或来历不明文物正当性的质疑日益高涨,引发了人们对研究盗掘文物的学术伦理问题的关注。本文从实际案例入手,考察欧美学界对研究盗掘文物行为的争议和思考,并结合国内的实际,探讨这些争议和思考的启示意义,以期引起国内学界的讨论。
一、使用盗掘文物进行科学研究所引发的争议
1.案例一
因使用盗掘文物进行研究而引发争议的著名案例,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学者唐纳(C.Donnan)对秘鲁的锡潘皇族墓葬文物所开展的研究工作。1988年,唐纳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上的研究文章中涉及来自私人藏品的盗掘文物。1990年,亚历山大(B.Alexander)在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著文,对唐纳使用盗掘文物开展学术研究的行为表示质疑,并提出:考古学家不应研究盗掘文物以增进历史知识,因为这等于是默许了盗掘。[1]
1991年,唐纳在《科学》上发表了回应文章,阐发了如下两点看法:[2]
首先,他解释了《国家地理》杂志发表文章的基本规则:要求文稿遵守相关的国际公约和文物所在国的法律。1988年的文章虽涉及盗掘文物,但这些文物并没有违反相关国际公约而从秘鲁非法出口。在秘鲁私人拥有文物是合法的,只要这些文物被国家文化机构正式登记过;《国家地理》杂志上公布的那些文物已被秘鲁官方登记在册。
其次,他认为研究这些盗掘文物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们对古代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和认识。在他看来,盗掘的发生是一种悲剧,因为某些历史信息会因此而永久丢失。但考古学家如能尽其所能对这些盗掘文物做一些记录和研究,或多或少能弥补一些因盗掘而造成的损失。
针对唐纳事件,学术界出现了不同观点。秘鲁考古学家、锡潘墓葬的发掘者阿尔瓦(W.Alva)对唐纳的文章表示支持,认为其有助于增强公众对锡潘墓葬的了解。但秘鲁国家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卡比亚(F.Cabiezas)却认为,利用盗掘文物进行研究违反了学术道德。美国人类学会主席萨波罗夫(J.Sabloff)也对唐纳提出批评,认为其行为等于是宣布了盗掘的合法性。
2.案例二
另一案例涉及到英国剑桥大学的著名考古学家伦福儒(C.Renfrew)及其1991年编辑出版的《基克拉迪精神》一书。美国波士顿大学的伊利亚(R.J.Elia)教授在《考古学》杂志上撰文对其提出了批评。基克拉迪文化为公元前三世纪爱琴海南部的文化,因大量石雕像的发现而著名。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克拉迪雕像日渐成为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们的收藏对象,从而刺激了盗掘行动,导致上千座墓葬遭到破坏。古兰德利斯(D.Goulandris和N.Goulandris)夫妇是基克拉迪雕像最著名的收藏者,但他们的收藏基本上都是通过市场购买得来的,没有一件有明确的考古发掘背景或来历。伊利亚指出:“正是对文物的渴求制造了需求市场,这一市场需求鼓励了文物盗掘和走私活动。而盗掘反过来又促进了文物伪造,因为当市场充斥着大量没有考古学来源的文物时,赝品才得以鱼目混珠无法分辨。这两种现象——盗掘走私和赝品——从根子上彻底腐蚀了古代艺术史领域的行业道德。”[3]
《基克拉迪精神》一书正是在这对夫妇设立的私人基金会的资助下完成的。伊利亚认为,伦福儒在学界享有很高的地位,在他们的资助下对这些来源可疑的文物进行研究,这样的行为十分不妥。伊利亚进一步指出,这些盗掘文物只能被当作艺术品,因为没有确切的考古来源,所以在科学研究上没有多大意义。文章还指出,由于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赝品,这些被研究的雕像是否是真品也很难辨识。最后,伊利亚提醒伦福儒不能不考虑盗掘及其后果的严重性。
伦福儒随后在《考古学》杂志上发表了回应文章,[4]指出伊利亚关于学者应回避没有确切考古来历的文物的建议将问题简单化了,而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希腊之外的伦敦大英博物馆、巴黎卢浮宫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都收藏有早期基克拉迪雕像,而这些雕像当时被发掘的细节,以及是否还伴随有其他发现物等情况都没有留下记载,即这些旧时收藏也非科学发掘得来。如果研究的标准局限于合法发掘这一前提,那么只有20多个雕像满足此标准。伦福儒承认,盗掘确实对后续研究造成了极大的困境,但完全回避这些盗掘文物并不合适。不过,他也接受批评,认为把自己的名气借给古兰德利斯夫妇的收藏确有可能导致更多的文物被盗掘,而收藏家则会因为市场兴趣的上升而从中获取巨大利益。
伦福儒因为这一批评开始关注考古遗址被盗掘的问题,并认识到文物盗掘和走私的极度猖獗对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存造成了毁灭性的破坏。出于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于1997年在剑桥大学创建了“非法劫掠文物研究中心”,组织专职的研究人员对世界各地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非法盗掘和买卖文物事件进行报道、记录和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伦福儒对学者是否应研究劫掠文物的观点也发生了改变,并对自己早年研究盗掘文物的行为进行了反思。([5],p.74)
二、两难抉择
是否应对盗掘文物进行研究,这一问题引发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争议。针对该问题,学界存在明显的分歧。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观点如下:
1.支持者观点
研究盗掘文物的现象很早就存在,也并不构成问题。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些许变化。彼时,因为世界各地发生的盗掘日益破坏了考古学的研究基础,学界开始重视文物盗掘和非法交易问题。哈佛大学的科金(C.C.Coggin)博士是最早的关注者。她于1969年发表了一篇调查文章,指出盗掘文物因为失去了出土的考古背景而导致失去获取历史知识的可能。[6]而研究玛雅文化的著名学者科依(M.Coe)则表达了不同看法。针对当时出现的一批盗掘的玛雅文物是否应被研究,科依认为:如果只是因为是盗掘文物而不予研究,那将是极大的知识损失。他以罗塞碑为例作为说明:“如果某人出示罗塞碑于我,是否因为它是盗掘文物,我就拒绝研究?我会研究,因为如果它是真的,它在增加我们的历史知识方面将发挥不可限量的作用。”([7],p.38)罗塞碑是在拿破仑征战埃及期间发现的,碑上刻有希腊文和埃及象形文字。罗塞碑的意义十分重大,学者们可以以已知的希腊文文字为参考来对照破解尚未识别的埃及象形文字。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高级研究员慕斯克里拉(O.W.Muscarella)对于研究盗掘文物的问题也表达了支持的态度。[8]有专业组织以联合国通过《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的1970年这一时间点作为划分是否研究盗掘文物的分界线,他对此表达了疑虑:考古学家可以研究一件没有考古来源的文物,而同时却不能研究另外类似的文物,难道只是由于非法发掘的时间有所差异而已?在他看来,无论是1970年以前抑或是之后被盗掘的文物,它们在本质上未有分别,都是盗掘物;不能以盗掘文物获得的时间作为是否可以对之进行研究的判断标准。对于1970年之后的盗掘文物,他认为考古学家也不能忽视它们。不过,针对最近的盗掘文物是否可以研究的问题,他则给予了否定的意见。
对于一些学者而言,文物的考古背景固然很重要,但并非是判断一件文物是否值得研究的唯一因素,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类型学或者技术层面的分析做出某些考古学解释。总之,对于失去了考古背景的文物是否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他们认为取决于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大英博物馆的学者库克(B.F.Cook)是此类观点的代表。他认为,有些类型的盗掘文物,即使失去了详细可靠的考古背景或其他相关联物件,但文物本身还蕴藏着它所产生的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信息。[9]
综上所述,在赞成对盗掘文物开展研究的学者看来,考古学者承担着促进学科的科学目标达成的义务,应该对所有被发现的文物予以认真研究,不应以文物发现方式的道德性作为研究取舍的标准。他们认为,盗掘已经发生无可挽回,但对盗掘文物进行研究至少还能获得某些古代历史的信息或知识。即便考古学家通过研究后得到的只是有限的碎片化的历史信息,也甚于一无所有。总之,研究者们不应回避盗掘文物,应对其开展研究,提取或揭示其蕴涵的知识信息。
2.反对者观点
对研究盗掘文物持强硬反对姿态的学者也阵容强大,包括秘鲁国家博物馆的前任馆长卡比亚、美国人类学会的主席萨波罗夫、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考古研究中心主任亚当斯(R.E.W.Adams),美国考古遗产管理委员会主席波士顿大学教授伊利亚,英国剑桥大学的考古学家奇平戴尔(C.Chippindale)博士和英国斯旺西大学的考古学家吉尔(D.Gill)博士等。
在他们看来,首先,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盗掘文物与科学发掘的文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科学的考古发掘,不只是发现器物,还需要对所有考古背景信息进行详细记录,即发现地的地层情况、器物的原始出处、与其一起发现的物品的空间排列关系等。这些层位关系和共生关系能提供这些器物产生、使用和遗弃的信息和线索,正是根据这些线索,考古学家才能推断遗存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行为与思想意识。完整的考古背景是复原和重建人类历史的关键。盗掘文物通常是脱离了考古背景的孤立器物,没有了详细可靠的考古出处,很多重要的原始信息因此而永远失去,很难作为确凿的物证去解答考古学的诸多问题。面对这类文物,考古学家对它们的解读工作变成了一种猜谜活动。有学者认为“从考古背景剥离之后,这些文化孤儿将永远沉默无声,实际上已失去研究的价值”[10]。
其次,缺乏了考古背景不仅使得盗掘文物的研究价值大打折扣,还牵涉到这类文物究竟是否是真品的问题。因为盗掘文物或来历不明的文物通常没有明确的出土信息,其真伪性自然成为困扰研究者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文物作伪水平的不断提高,科学检测也并不能被视为是辨别赝品的绝对的保障手段。如果不能辨别文物的真伪,而以伪造文物作为研究的对象,可想而知,所获得的研究结果不仅毫无学术价值可言,而且会严重干扰研究者的视线。对希腊基克拉迪岛(Cycladic)雕像进行的科学研究就存在研究基础的真确性问题。[11]在相关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了雕像是依据一定的几何学的标准比例而制作的学术观点,例如雕像的头部比例占整个雕像长度的四分之一,以6×8的宽和高的栅格比例制造雕像。奇平戴尔和吉尔两位考古学家则认为,这些研究所用的雕像材料只有个别有明确的考古学来源,而其他的雕像没有确切的出土地和出土时间,无法断定是否是赝品。因此该研究是建立在一些来历不明的雕像基础之上的,其提出所谓的标准比例自然很成问题。此外,博物馆或私人收藏者的照片上,该雕像的一般摆放姿势为竖立。两位考古学家发现雕像的足部非常窄小,它们不可能自己站立,雕像站立的摆放姿势是以钢架支撑的。由于这些雕像失去了考古背景,所以也无从判断原初的摆放方法。鉴于盗掘而来的文物丧失了发掘地层、发掘的环境、组合物等可靠的背景信息,考古学家对这些文物几乎无法进行有意义的研究。
此外,很多学者反对研究盗掘文物,则主要着眼于这种行为所引发的负面后果。在他们看来:“研究来历不明的文物并发表研究文章,等于是为这些出处不明的文物提供了某种来历——学术身份,学术价值有可能转化为市场价值,这将刺激为寻找类似的文物而产生进一步的盗掘活动。”[12]换言之,对盗掘文物开展科学研究并公布研究结果,不仅证明这些文物的真确性,而且也提升了其市场价值,从而刺激了世人对此类文物的渴求,并带来进一步的盗掘恶果。考古学家维塔利(K.D.Vitelli)在一篇文章中记录了泰国班清(Ban Chiang)地区考古遗址遭盗掘的事件,揭示了考古专业人士发表研究结果的行为在引发文物市场需求方面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分量。([13],pp.143-155)1966年,一位美国大学生在泰国参观了一个名为班清的村庄,并带回了一些当地的文物交与其曼谷租住屋的屋主。屋主将其中的一些陶瓷残片出示给她的朋友鉴赏,后者又将其送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进行材料分析。分析结果显示,这些文物约为公元前5世纪到前4世纪的遗物。班清的当地村民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两百多年,不曾挖掘地下的遗物。即使在1967年,泰国当局开始对此地进行试发掘后,该地区也未出现严重的盗掘现象。然而,1970年,当陶片的分析结果公布后,形势却发生了变化。班清地区的文物吸引了收藏家和文物商人的目光,相应的市场迅速形成,最终该地区的考古遗址遭到严重盗掘。学者哈林顿(S.P.M.Harrington)在一篇分析美国阿肯萨斯州的考古遗址被盗掘的文章中表达了如下观点:“考古学家公布有关重要文物的资料,结局就是带来推土机——相关文物被售卖,有人开始意欲收藏此类文物——每当我们公布资料,我们就帮助和煽动了市场。”[14]可见,即使是科学发掘的文物的分析数据公布都可能会刺激文物市场,研究盗掘文物的行为,其负面效果则更为严重。
综上所述,在反对研究盗掘文物的学者看来,这类文物失去了考古背景,其科学研究价值有限,并且也很难辨别其真伪,在此基础上开展研究是不足为据的。此外,即使考古学者利用盗掘文物开展的研究工作获得了一些数据和历史信息,但这一行为将刺激文物盗掘和非法贸易。为考古学科未来的发展计,很多学者认为学界应拒绝研究盗掘文物,以减弱或阻止在世界各地日益蔓延的对考古遗存的大规模盗掘和永久破坏。
三、美洲考古学会制定新的道德规范
研究盗掘文物现象长期存在于学界,并且在过去并不成为问题。但在文物市场的急剧扩大下,学界对自身职业伦理的认识和反思也在不断深化。面对是否可以研究盗掘和非法交易文物的问题,作为专业组织的美洲考古学会(The 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1992年,美洲考古学会的学术期刊《美洲考古》(American Antiquity)宣布该期刊不能为此类研究文章提供发表的场所:“考古的、人类学的、历史的文物是以未经系统描述它们的出土背景方式而获得的,或其被发现的方法最终导致遗址或纪念物的破坏,或是违反原产国法律而出口,凡涉及到上述情况的文物的研究文章不予发表。”[15]
美洲考古学会期刊编辑原则的制定,标志着学术界对研究盗掘文物的问题开始有了深刻的认识。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美洲考古学会期刊制定了严格的学术伦理标准,不再为盗掘、非法出口和以破坏遗址方式获取的文物的研究提供发表机会,以阻止因为学术研究而导致盗掘文物的市场价值得以提升。针对研究盗掘文物而涉及的考古伦理问题,美洲考古学会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专门的考古伦理工作组讨论相关事宜。最终,执行委员会一致同意重新修订学会的规范。1996年,美洲考古学会新的伦理规范出台,最重要的是第一条:
考古档案如考古材料和遗址、考古收藏、记录和报告是无法被代替的。考古学家的责任是通过看管的方式而致力于长期保护和保存考古档案。[16]
以保护原则为基础和出发点,美洲考古学会反对有可能对考古资源造成损害的一切商业化行为。该规范的第三条针对的就是“商业化”的问题,规定如下:
学会认识到买卖脱离了考古背景的文物会加速美国和全世界的考古遗址的破坏。文物的商业化——为了个人的享受或利益使文物作为商品被利用——会导致考古遗址被毁坏、以及对理解考古资源来说非常重要的背景信息的破坏。考古学家因此应仔细衡量项目学术性的益处以反对有可能增强文物的商业价值的行为。
商业化包括了任何增强或便利于文物市场化的行为。学者研究和使用盗掘的或私人持有的文物材料,发表相关研究文章和著作的行为,就可能间接导致文物商业化。因为这种行为实际上为这类文物做了学术确认,其学术价值有可能转化为商业价值。
追溯历史可以看到,美洲考古学会的伦理规范发生了变化。1960年,美洲考古学会发起了制定专业标准和伦理道德规范的讨论,并起草制定了《考古学的四项声明》。([17],p.11)这份规范包含的内容重点是学科的科学目标、科学研究方法和专业标准。20世纪60年代后,世界各地的遗址因盗掘而遭到极大的破坏。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美国学界加强了在考古遗址保护方面的关注和努力,考古学学科不再只是聚焦于获取知识这一唯一的目标,考古资源保护成为新的学科发展目标。对比1961年的《考古学的四项声明》,1996年的伦理规范中,保护考古资源成为了考古伦理责任的中心。可见,“保护”已成为考古学最重要的价值追求。这种从思想层面的认识向规则制定的转变,反映了美国学界对盗掘与非法文物交易的危害以及对考古遗址保护的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深化过程。
四、思考与启示
从上文的案例和分析可以看出,西方学界和社会对盗掘文物是否可以无条件地进行研究的问题,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反观国内,学界和社会对这一问题却尚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国内学界研究来历不明文物或盗掘文物的现象还是相当普遍的。
值得欣慰的是,近几年,国内已有个别学者开始关注研究盗掘文物所涉及的学术伦理问题。北京大学罗新教授著文思考了盗掘与学术伦理的关系问题。[18]他在文章中描述了墓志盗掘在近年的猖狂态势,也提到自己在学术研究中所用的一些墓志不具备确切的出土记录。他指出,如果学者们纷纷将这类墓志纳入研究范围,此种热衷无疑是在鼓励盗掘。又如,2009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姜广辉教授在《光明日报》刊发文章,对“清华简”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质疑,由此对竹简的真实性表达了怀疑。[19]他建议,不购买来历不明的文物。否则,不但达不到抢救国家文化遗产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将假历史当作真历史。[20]更为关键的是,这些来历不明的文物大多是经盗掘而走私流入国际市场的,不能不考虑到国内的购买行为实际是对盗掘行为的背书。
目前,盗掘文物是否可以研究已成为一个西方学界热切关注的话题。赞成研究盗掘文物的学者考虑的是促进科学发展。而随着文物市场的扩大,科学研究活动的影响已不仅限于学术圈内,还可能对文物商业市场带来极大的影响。追求科学目标和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这两种价值的矛盾冲突,应该引起学术界的思考,不宜简单的只从科学研究目的出发认为所有考古材料都可研究。从另一方面而言,某些盗掘文物的确可能蕴涵着重要的信息,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也不符合科学理性。因此,对于盗掘和来历不明文物是否可以进行研究,我们认为可从下述方面来考虑:
其一,世界各地的考古遗址遭到大规模盗掘,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湮灭。考古资源是了解人类历史的证据,考古遗址遭到破坏,考古学科本身的发展基础也将不复存在。职业伦理要求考古学家们关注考古遗址的安全和完整等更宏观更迫切的问题。
其二,考古遗址的保护应上升为考古工作的第一原则,有损于保护原则的行为都应慎重甚至拒绝。盗掘文物是以破坏考古遗址方式获得的文物。利用这类文物开展研究是对盗掘行为的默认甚至支持。而且,对盗掘文物的研究很可能导致其商业价值的提升,从而间接刺激进一步的盗掘以及相关的非法转运和交易。考古学家们有责任去思考和避免自己的研究活动可能带来破坏考古遗址安全的后果。
其三,对大部分的盗掘文物应持基本放弃研究的态度。如果经初步判断此类文物可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也应先予存疑而不是急于开展研究工作,申请由相关部门召集学术共同体中的专家进行论证,衡量这些文物的学术价值究竟多大,若不研究,可能的损失又怎样。如果经过学界充分论证后,某些文物确实具有重大的研究价值,可以考虑开展相关研究,但为避免刺激新一轮盗掘和非法交易的发生,学界应考虑推迟研究及其成果发布的进程。
是否拒绝对所有盗掘或来历不明文物开展研究的问题已引发了西方学界的持续关注和讨论,虽然对此问题仍存有某些争议,但不少学者已经身体力行拒绝研究此类文物。我国学界目前尚未就此问题展开讨论,抵制研究盗掘文物也远未形成一种共识,这背后的原因固然复杂多样,但随着对考古遗址盗掘和损毁的形势愈演愈烈,我国学术界迟早需要面对这一问题,并采取相应的行动。西方学界所经历的争议、困惑和反思过程可以引以为鉴。总之,遏制对考古遗址的疯狂盗掘、保护珍贵的考古资源是中国学术界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待更多学者的关注和担当。
参考文献:
[1]Alexander,B.,Archaeology and Looting Make a Volatile Mix[J].Science,1990,250(4984):1074-1075.[2]Donnan,C.,Archaeology and Looting:Preserving the Record[J].Science,1991,251(4993):498.[3]Elia,R J.,A Seductive and Troubling Work[J].Archaeology,1993,46(1):66-69.[4]Renfrew,C.,Collectors are the real looters[J].Archaeology,1993,46(3):16-17.[5]Renfrew,C.,Loot,Legitimacy and Ownership:The Ethical Crisis in Archaeology[M].London:Gerald Duckworth & Co.Ltd.,2002,74.[6]Coggins,C.C.,Illicit Traffic in Pre-Columbian Antiquities[J].Art Journal,1969,Fall:94-98.[7]Meyer,K.E.,The Plundered Past[M].Athenaeum:New York,1973,38.[8]Muscarella,O.W.,On Publishing Unexcavated Artifacts[J].Journal of Field Archaeology,1984,11(1):64.[9]Cook,B.F.,The Archaeology and the Art Market:Police and Practice[J].Antiquity,1991,65:536.[10]Cannon-Brookes,P.,Antiquities in the Market-Place:Placing a Price on Documentation[J].Antiquity,1994,68:350.[11]Gill,D.,Chippindale,C.,Material and Intellectual Consequences of Esteem for Cycladic Figures[J].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1993,97(4):601-659.[12]Brodie,N.,Gill,D.,Looting:An International View[A].Zimmerman,L.J.,Vitelli,K.D.,Hollowell-Zimmer,J.(Eds.),Ethical Issues in Archaeology[C],New York:Altamira Press,2003,39.[13]Vitelli,K.D.,The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ntiquities:Archaeological Ethics and the Archaeologist's Responsibility[A].Green,E.L.(Eds.),Ethics and Values in Archaeology[C].New York:Free Press,1984,143-155.[14]Harrington,S.P.M.,The Looting of Arkansans[J].Archaeology,1991,44(3):28.[15]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Editorial Policy,Information for Authors,and Style Guide for American Antiquity and Latin American Antiquity[J].American Antiquity,1992,57:751.[16]Lynott,M.J.,Ethical Principles and Archaeological Practice:Development of an Ethics Policy[J].American Antiquity,1997,62(4):599.[17]McGimsey III,C.R.,Standards,Ethics,and Archaeology:A Brief History[A].Lynott,M.J.,Wylie,A.(Eds),Ethics in American Archaeology:Challenges for the 1990s[C].Washington,D.C.:Society for American Archaeology Press,1990,11.[18]罗新:新出墓志与现代学术伦理[N].南方周末,2008年3月6日。[19]姜广辉:“清华简”鉴定可能要经历一个长期过程[N].光明日报,2009年6月8日。
来源:《自然辩证法通讯》2014年第5期
- 0000
- 0000
- 0002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