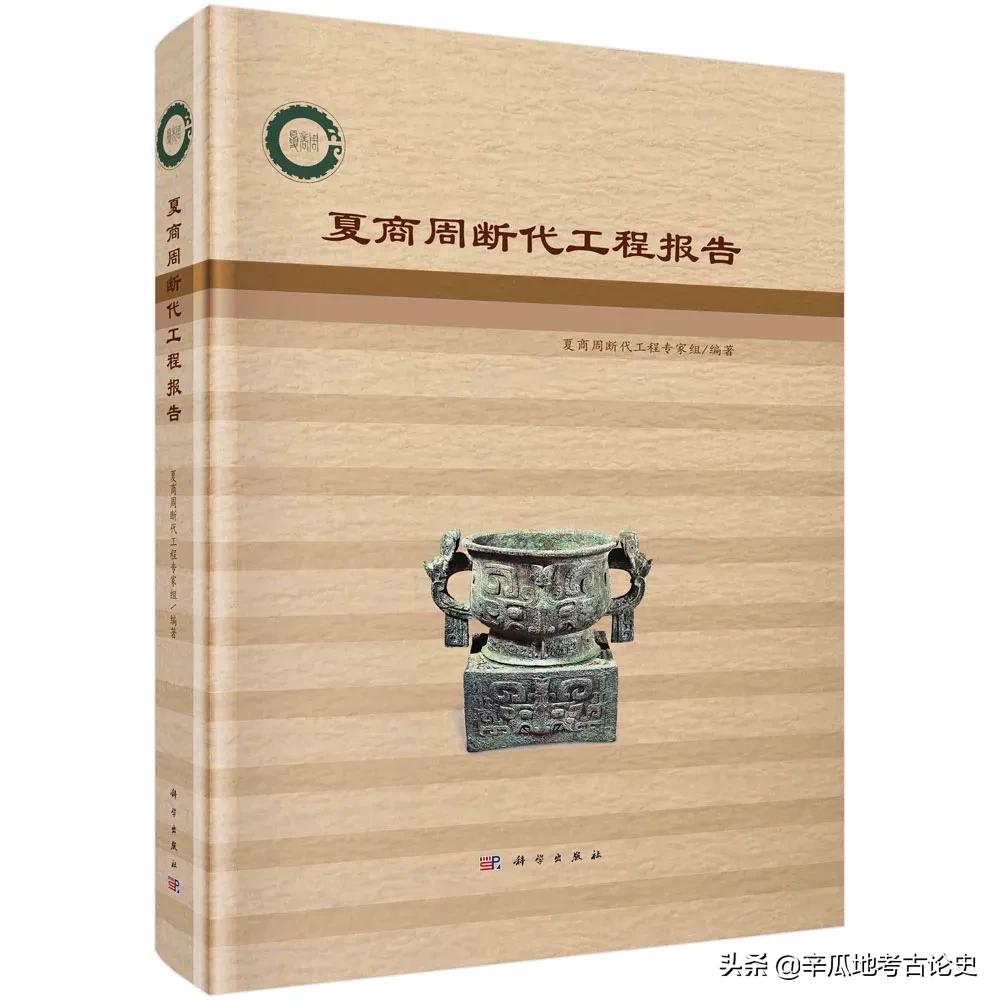宁可:漫谈历史研究与实物、文献、调查和实验的结合
历史研究要凭借史料,传统的也是最重要的史料是文字史料。但是,“文献不足征也”。王国维晚年总结治学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说明了文献与出土的地下材料相结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研究中国古史,最为纠纷之问题,上古之事,传说与史实混而不分,史实之中,因不免有所缘饰,与传说无异,而传说之中,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在中国古代已注意此事。……至于近世,乃知孔安国本《尚书》之伪,《纪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过,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于怀疑之态度及批评之精神,不无可取。然苦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也。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因得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虽古书之未得证明者,不能加以否定,而其已得证明,不能不加以肯定,可断言也。①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的重要贡献,从他的《殷卜辞中所见先王先公考》等论著中可见一斑。但他所注重的地下材料其实是专指出土实物上的文字,即青铜器、甲骨、敦煌写本、汉晋简牍上的文字,而不及未见文字的地下实物,这和他所谓的“纸上之材料”外的“地下之新材料”不免有相去一间之憾。
一
出土的地下实物其实是真实的、直接的、原始的、本来的史料,但也有很大的局限,那就是它只是僵化、物化的人类活动。它本身蕴藏了过去大量的人类活动的信息,但凭本身形式,直接地直观地传达出来的并不多。像它所蕴蓄的关于人物、事件、社会组织、社会关系、人们的思想等等信息就是如此。在这一点上,它不如文字史料(包括语言和图像)。文字史料是经过人们的意识处理过的历史信息,实的虚的、具体的抽象的、个别的综合的都有,实物往往做不到这一点。我们要了解和深入了解实物所蕴藏的更多的更深入的信息,还必须借助相关的语言文字图像,当然,也确实需要借助于原有文献上的记录,以期相互印证。实物上如果有文字图像,那情况就好多了,这时的实物就具有实物和文字图像的双重史料的功能。像中国先秦时期的古青铜器,如果上面有铭文,不仅可以落实其功能,如礼器、酒器、食器、兵器、明器等,还能从中得知是何人何地何时为何制作了这件铜器,是为自己使用,为了祭祀,还是赠人;甚至获知当时的一些重要史实,像大盂鼎铭文中所记的打仗杀人俘人的事,就是了解西周社会的极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没有这个铭文,大盂鼎仍不失为珍贵的实物史料,但其史料价值便将大打折扣;有了这个铭文,就有了关于大盂鼎的故事,亦即有关的人的活动。这是没有铭文的鼎彝所做不到的,或者那只是其中有关人的活动的一小部分(如铜器制作的原料、铸造技术、铜器的形式等等)。有些实物如写卷、甲骨、绘画、雕塑等基本上就是文字图像史料,它们的质地、制作技术、书写方法等史料价值反倒成为第二位的了。
要更多、更好、更深入、更确切地发掘出实物所蕴藏的历史信息,往往还要靠实物以外的文字语言符号、图像材料作为参证。这种将文献记载和实物互相参证的做法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不胜枚举。钟磬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乐器,所谓“金声玉振”。但其编制即编钟编磬是怎样的,又是如何演奏的,文献记载阙如,或佚失不详或不清楚,而以往出土的钟磬又都属零散的个别的实物,只是到湖北随县春秋曾侯乙墓出土了整套的编钟编磬及悬挂的架子簨簴,以文献和考古实物相印证,我们才弄清了这种乐器的真貌,并可再度用它演奏乐曲。
过去在汉墓中经常见到零散玉片或石片,不知是作什么用的。直到发掘了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了包覆在尸体外,以金丝连缀玉片作成的完整的尸衣,与文献相印证,才知这是文献所载的贵族葬法中的“金缕玉衣”(后来还发现次级的“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丝缕玉衣”)。北京大葆台汉墓棺椁之外覆盖的那层厚实的方木,与文献相参证,才知道是过去文献中弄不清楚的“黄肠题凑”、“西园秘器”。像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幅覆盖于棺盖上的长约二米的彩绘帛画,根据文献可知为铭旌一类的东西,但又与文献记载的铭旌形制不甚相合,以致还不能最后确定下来。实物与文献的关系,由此可以想见。
二
文献与实物的互相参证,对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如此,对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尤其如此。
要了解原始社会,我们当然需要有考古发掘出来的当时的遗址、遗物、遗迹,但仅有这些例如石斧、石镞之类的物品还不够,我们还需要有后来文献中像《礼记·礼运》写大同之世那样的关于原始社会的追忆。光有这二者还不行,还要靠现实生活中残留的原始社会的东西,特别是对一些地方的还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群或次原始状态的人群的调查了解。通过这样三个途径,并且把三者结合起来,我们对原始社会就能有真正的比较科学的了解了。19世纪中叶以后是人们对原始社会科学了解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之前,原始社会对人们来说并不存在,至多是极模糊的记载和一些猜测。19世纪的欧洲学者最初研究了德国残存的马克(公社),包括语言、社会组织、民俗等等,并同古籍中所载的有关古日耳曼人社会(如罗马恺撒的《高卢战记》、塔西陀的《日耳曼人志》)相参证,确认了古日耳曼的马克(公社)制度。随后这一研究又扩展到东欧的社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俄罗斯等),认识到了这种原始社会末期向阶级社会过渡时的公社形态的普遍性。但是在这之前又如何呢?美国人摩尔根作为北美印第安易洛魁族的养子,长期同他们住在一起,弄清了印第安部落的原始社会性质,并在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化人类学兴起,一批学者如马克莱、马林诺夫斯基、弗雷泽等在非洲、大洋洲对原始部落作了大量调查,把公社以前乃至印第安部落以前的原始人群的情况弄得更清楚了。这样,我们才对原始社会有了比过去大为不同的清楚的科学的认识。人类历史上有一个最早的原始社会阶段已是确定无疑了,其基本面貌也大致呈现出来了。
中国的56个民族中,建国时的社会发展程度不一样,有的处在典型的封建社会,比如傣族;西藏则为封建农奴制;四川凉山彝族是奴隶制社会;还有些民族则处在原始社会阶段,像东北的赫哲族、鄂伦春族,云南的独龙族、佤族等都是。20世纪50年代曾进行过一次普遍的社会调查,对历史上已经逝去的社会形态提供了活生生的标本,大大加深了我们对过去社会形态的认识。如婚姻关系,最古老的是乱婚;后来把不同辈分的人排除,氏族的同辈男女兄弟姊妹之间互为婚姻,是为血族群婚;然后是亚血族群婚,即氏族内部不通婚,而与另一个氏族的同辈男女互为婚姻;再往后是对偶婚,即一男一女互为夫妻,但均可与另外的男女有非固定的性关系;最后才是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一妻多夫),以纳妾作为补充。像匈奴的单于死后,其继承者可与他的阏支(王后)成婚;这里有把妻子作为财产加以继承的因素,看来也是古代乱婚制的一种残留。古希腊传说中,俄狄浦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杀父娶母,知情后造成内心的极大痛苦,成了古希腊悲剧中最悲惨的人物,可知在其传说形成的时代,人们已经排斥了不同辈人之间的婚姻,那已被视为不能容许的乱伦罪恶。希腊神话中的天神宙斯与天后赫拉原是兄妹,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原来也是兄妹,后来结为夫妻,反映了古代血族群婚的状况。古希腊有一个风俗,每年有一天女子到神殿去,把自身献给任何见到的男人,这是从对偶婚制遗留下来的风俗。中国云南的摩梭人有一种“阿柱”制度,男女婚后,仍可有“阿柱”(朋友),越多越以为荣。有位老年妇女自诩有一百多个“阿柱”,这是一种对偶婚制的遗留。
王国维把文献与实物结合起来研究称之为“二重证据法”,文献、考古和现实调查三者的结合互相印证,或者可以称之为“三重证据法”,它能大大促进对历史真相的认识。有些学者提倡,对没有文字时期的历史,考古和调查的作用极大。文字则由于是后出,记载少而又多经后人以后来的观念扭曲,仅凭它已很难了解历史本来面貌②。《礼记·礼运》所记禹以前的大同之世,那是凭着春秋战国对过去的认识特别是经过儒家思想加以扭曲的原始社会的记录,仅凭它不可能弄清原始社会的真貌。但是有了考古和调查的成果,《礼记》大同之世的记载就可以剥去和滤掉后世的不准确的叙述和儒家理想化美化的外衣,而成为原始社会真貌的一种印证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到了有文字记载的时期,尤其是保留下来的文字记载越来越多的时期,实物和调查不像对原始社会的认识那样极端重要,但它们仍可作为文字记载的重要参证,仍能发掘出一些文字所不载、或不详载、或未明载的东西。这是认识历史非常重要的途径。
三
实物、文字、调查三者结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般来说,三者结合能促进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深化和具体化,但也可能误导我们的历史认识。实物是历史最过硬的物证,然而对实物的解释却有赖于认识者的知识、科学技术水平和思维方式。有了实物不一定就能对它有科学的正确的认识。文字经过记述者的思维,是否真能反映真相很成问题,需要研究者对它进行判断。对现实社会中历史的方面的调查,也因为时间的剥蚀,原来的东西无法完全保留下来,并且往往不是原生的形态,而是次生的形态、萎缩扭曲的形态或衍生的形态,由此上推历史的原貌不是那么容易的。在这里,研究者的成果不仅要取决于他所处的时代总体的知识水平、技术水平、认识能力、认识方法,尤其要取决于他本身的品质、素养、研究目的、方向、知识水平、方法,乃至个性、心态等等。在这种主客观的交互作用下,认识主体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而出现的情况也是各色各样的,不算弄虚作假、蓄意歪曲、捏造篡改之类,正打正着的不少,而歪打正着,正打歪着,打而不着,空打空着的也不少。如对浙江龙游石岩背村、黄山市屯溪区花山村地下石窟群的各种猜测,最大的可能就是石窟是为了凿取石材,但不见记载,而石材的去向也不清楚。其实目前最好的答案是,所有的猜测还不能证实,只有进一步的调查发掘③。再比如有名的阴山岩画和贺兰山岩画,人们对其年代作出了种种推测,但目前还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能够确定它们的确切年代,种种说法就无非都是一种假说。
想象力是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入探究世界的动力,这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人类活动的最大优点。想象力并非凭空而来,即使是那些最离奇空幻的想象,也是建立在人的现有知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及技术方法的基础上的。如果只停留在想象层面而不去深入探究落实,在探究中排除不正确的可能性,寻求真实的答案,那并不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如果把想象当作真实的答案,那就更糟,认识还会倒退。科学上的假说其实也是一种想象,但一般来说,它还不是那种纯然虚幻的想象,总要有几分事实根据。如果因此以假设作为结论,那就不好了。胡适和傅斯年说过,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这是很有道理的。然而,这样的拿想象当作真实的毛病,我们是时常会犯的。不仅是有意为之,即使是认真严肃的学者,也往往由于认识水平和认识能力的限制而不免出现这种情况。
也许是中国文化实用性特点所使然吧,中国古代诗歌往往是见物起兴,感事抒怀。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诗人具有丰富浓烈的历史感,好发思古之幽情。古今对应,古迹典故入诗很多,反映了一种将现实的和文献所载史事、人物联系起来的历史手法。不妨举两段我们熟知的诗词:
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是他在谪迁为黄州团练副使时写的: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这里,故垒、赤壁是与由文献所知的周瑜、赤壁之战、火攻联系起来了。然而在这阕词里,苏轼的历史认识还是来自于文献,故垒、赤壁这类古迹,只是由头,而且全靠不住。——故垒,苏轼看来只看了一眼,没有调查与赤壁之战是否有关,至于三国周郎赤壁,则是“人道是”,即来自传闻。湖北中部的长江和汉水上有好几个赤壁,一说有五个。通常认为在赤壁市(蒲圻),但长久以来争论不休。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赤壁之战在武昌西南长江上游右岸的石矶④,苏轼所游的赤壁则在武汉长江下游的黄冈城外,两处直线距离有一百多里,可谓风马牛不相及。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对于“人道是”这样的传闻,不去核实是不对的。如果苏轼轻信,是学风不慎密谨严,如果知道不对却还要用,那简直就近于弄虚作假了。但是作为诗人,这倒没有什么,《念奴娇·赤壁怀古》仍是一阕绝妙好词。好的诗人必须有学,学者也不妨兼作诗人。但是学术与艺术的差距也还是存在的:诗人不妨尽力驰骋他们的想象编造,九天揽月,五洋捉鳖,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而对学者来说,再丰富的想象也需要落实到事实的大地上。
再看一首杜牧的《赤壁》: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杜牧比苏轼好像更科学些,他简直是在做一次考古发掘,从沙中得到一个折断的戟头,自己磨洗清理认出是前朝(三国?)的东西(可能上边有铭记),这才引发他的历史感慨。然而,“东风不与周郎便”恐怕还不能从折戟上看出来,那是从文献上得到的历史知识,“铜雀春深锁二乔”的推断就更是如此了。
杜牧的考古是亲临现场,自己动手,但把发掘地点选错了。杜牧终身行迹没有到过嘉鱼或蒲圻,自然无从在那里“发掘”。他曾几次由北方经汉水、长江往返江南,并曾出任黄州刺史一年多。大概跟苏轼一样,误听传闻,把黄冈赤壁当成三国赤壁战场了。这样,他的“考古”与文献的结合也就成为空谈了⑤。
四
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那就是19世纪下半期轰动欧洲的德国考古学家施利曼(Heinrich Schliemann)的发掘⑥。其之所以轰动,是由于施利曼发掘了在欧洲几乎是家喻户晓的公元前9世纪希腊古诗人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故事里的特洛伊古城。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摇篮,但19世纪中叶欧洲学者对古希腊的有纪年、有当时文字记载的历史只能追溯到公元前776年。再往前就只有神话和传说。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可说是集这些神话和传说之大成。《伊利亚特》讲的是公元前12世纪(前1193)希腊各邦国攻打特洛伊城的故事。可19世纪欧洲的学者们认为那纯属虚构,既没有荷马,也没有特洛伊城乃至特洛伊战争。然而,一个12岁的德国孩子施利曼却相信那是真实的历史。他对他的小伙伴说,我要去找特洛伊和国王留下的珍宝。他家境贫寒,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当过学徒、店员、书记、船上的杂役,甚至一度求乞。但他发财的本事惊人,终于成了富翁,积累了发掘的资金。46岁的施利曼决定退出商务活动,全力以赴地去实现他寻找特洛伊城的梦想。他的语言学天赋使他学会了十几种文字。1856年,他用一个半月时间学会了现代希腊语,又过五个月已经精通了荷马所使用的古希腊文。
1868年,他根据荷马的描写确定了特洛伊城位于土耳其小亚细亚濒临爱琴海的一个小山丘上。次年,他娶了一个在他看来像海伦一样美丽的希腊妻子。1870年起开始了发掘,妻子成了他忠实的助手。他从小丘顶部开了条大沟直至坡底。成百的工人熙来攘往,32500立方码的土石被移开。古城出现了,但不止一座,从最底层的还不知使用金属的石器时代遗址至最上层的希腊罗马作品中所传的波斯王泽西斯和亚历山大祭祀的地方,层层叠叠共有九层之多(施利曼当时认为是七层,今天知道有十几层),到底哪座城是特洛伊呢?在从下往上数的第二层、第三层之间,发现了焚烧的痕迹,残存着巨大的城墙和城门,荷马史诗片刻不离手的施利曼眼前出现了特洛伊城被焚的熊熊火光,这就是荷马描述的特洛伊城斯悉安门,美人海伦正是坐在那里看她的前夫墨涅加阿斯和拐走她的巴里斯王子单身相斗。他宣布:特洛伊城发现了!就在他准备在1873年6月15日结束工作的前一天,他在泥土里发现了金子。他遣走了工人,在摇摇欲坠的坍塌的古建筑石块下,用一把大刀以最快的速度挖掘这些财宝。他的妻子在旁用红披肩把挖出的金王冠、别针、链条、纽扣、耳环、金杯、金钱、手镯等等包起来搬到屋里,—特洛伊王普里阿摩斯的宝藏找到了!特洛伊发掘达到了最高潮。
施利曼的发现轰动了欧洲的学界和公众,家庭中、马路上、驿车里、火车上、餐馆里都在谈论特洛伊,有的赞赏,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像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也都参加了争论。大多数学者不相信这座用小石头和泥土筑成的城就是九年久攻不下的雄伟坚固的特洛伊城;而发现的古物,也比荷马所描述的粗糙:兵器是铜制,而荷马史诗里除青铜外还有铁制兵器。后来大家认识一致了,施利曼发现的不是真正的特洛伊城。施利曼也承认了这一点,但他仍坚信真正的特洛伊城还是在那土丘下面,1882年又回到那里继续挖掘。1892年他死后继续发掘才证明第六座城是真正的特洛伊城。施利曼当年认定的特洛伊城其实比真正的特洛伊还要早一千年。施利曼那种大面积开沟,一掘到底大量弃土的粗糙方法,不仅损毁丢失了大量文物,而且忽视了更上层面的考察,使他与梦寐以求的特洛伊城失之交臂,但却使他发掘出了比荷马时期更早一千年的文化。施利曼笃信荷马所述为真实的历史,促使他依据荷马的叙述去发掘和依据发掘所得去证实荷马的叙述,这里,我们看到文献(传说)与实物的结合。施利曼的成功在于此,而他的缺点与失误也在于此。他虽然把荷马史诗中关于神的记述排除在外,只信关于人的记述,但他还是太过信书了,把荷马的记述与考古的发现作一种固执的比附。而对于考古发现,他太执著于寻找荷马的特洛伊城了,以致缺乏根据地去急于用发掘所得去印证荷马时期的历史,在思路和方法上都出现了问题。施利曼的这些问题,与前述苏轼、杜牧诗词的情况颇有类似之处。其实,施利曼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是他所没有想到的,他的发现不仅在于证实荷马史诗的记述,而是发现了远在荷马之前的一种古文化,第一次使人们注意到去研究欧洲文明的源头,虽然施利曼的发现是在亚洲的土地上。
施利曼特洛伊城的考古喜剧又以不同的脚本再演了一次,这次是在希腊的迈锡尼。1876年,施利曼想到土耳其继续发掘特洛伊城,但由于他违反与土耳其政府的协定,把前次发现的“普里阿摩斯宝藏”⑦ 偷运出去,土耳其政府制止他再度发掘。于是他在荷马史诗和传说的魔力下,转而去希腊寻找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统帅阿加绵农的坟墓。
在传说中,阿加绵农从特洛伊胜利归来,回到他的国家(其实是一个酋邦)迈锡尼,他的妻子克吕涅斯特拉和她的情人埃癸斯托斯共谋把他杀了。公元2世纪希腊人帕夫萨尼亚斯的《希腊指南》上载迈锡尼有一座狮子门(今天还在),那里有阿加绵农的坟墓和宝藏。以前也有人想从这里发掘取宝,但不得其门而入。施利曼先是在狮子门内发现一处圆形的石坛和比这坛略高的地方的一圈石板,施利曼自信已经找到阿加绵农和希腊英雄们的聚会商议攻打特洛伊城的会所。这些石板最低的也有3尺,最高的则达5尺,荷马的英雄们只有都是巨人才能围坐在这里。其实这更可能是祭地。施利曼认为,依照当时的“习惯”,死者就葬在下面,这倒不错。再掘下去,果然发现好几座大坟,坟中出土有许多精美的金、银、铜、象牙的面具、手杖、指环、宝剑、酒杯等,施利曼惊喜地宣布,这就是阿加绵农和他被杀同伴的墓。施利曼在迈锡尼的发现,同样轰动了欧洲,也同样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学者们认为坟中器物并不属于同一时代,死者人数与男女性别,也和帕夫萨尼亚斯所记不同;至于葬式的纷乱,则是由于被杀后匆促下葬,以及坟顶坍陷所造成。这样,人们开始由惊羡转为讥笑施利曼的幻想与对于荷马的过度热心、轻信。然而人们又渐渐看到施利曼发现的真实价值,是否真是阿加绵农的墓虽然是有趣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荷马所述的那个英雄时代的希腊,证明那不是传说,而是真实的历史,从而把古希腊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第一次奥林匹亚赛会上推了五百年。有了特洛伊城的发掘,迈锡尼的发掘,以及后来20世纪初伊文思在克里特岛对爱琴文化的宫殿城市的发掘(那里同样有希腊英雄提秀斯进入克诺孛斯王的迷宫,杀死人头牛身的怪物民诺托,救出美女美狄亚的传说),终于找到了欧洲文明的源头,把欧洲的文明史提到3500年以前,几乎与埃及文明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鼎足而三。这是施利曼没有想到的。
人们既有的知识(有些不那么准确,或有疑义)引导人们去发掘未知遗物,探索新的未知领域,居然大有成就,而这种成就反转过来又否定了或部分地否定了人们既有的知识,却又开辟了新的境界,或者得出全新的东西,这在认识史或科学史上并不少见。像天文学史上的第谷、刻卜勒和牛顿,物理学史上的居里夫妇的发现镭,哥伦布西航目标是印度,但却发现了美洲而又不自知,等等。正打歪着、歪打正着等等情况比比皆是。那么,从学术的角度历史地看,我们对前面那些诗人的诗词中所反映的历史认识缺陷,也许需要抱一种更为宽容、更为积极的甚至是赞赏的态度。
五
实物与文献的结合,如上所述,还有一个与调查即与现实生活中的历史的东西的结合的方面。除了观察与调查之外,还可以考虑模拟或实验古人的活动,也许可以把它当成历史认识在文献、实物、调查之外的第四个方面,类似自然科学上的实验。历史不可能复制重演,但对某些方面的某种模拟还是可以的,而且对于了解历史真相很有帮助。原始石器的打制,原始陶器的制作,都可以模仿出来。用南美古印第安人一样的工具技术,伐树挖心做成独木舟,可以了解当时的生产效率;模仿古埃及的工具材料、技术、方法在现代人尸体上制作木乃伊;用相当于当时的工具、材料及技术(如不用当时没有的轮子及滑车,仅利用当时已知的斜面滚轴和杠杆的原理),采石运石树石,以了解方尖碑、金字塔,以及英国的大石圈这些巨型石构是如何建造起来的,等等,都是以实验模拟古人的活动。这里我们再举一个挪威学者海尔达尔(Thor Heyerdahl)的模拟古人的航海活动的例子⑧。
在东南太平洋一座孤立的小岛——复活节岛上,充满了种种神秘的东西和气氛,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几百尊矗立着的几米至十几米高的大石像。它们的脸型完全不同于现在岛上的居民⑨,现时岛上的居民也完全不晓得它们从何而来,何人所雕树,为什么雕建。
从1722年复活节岛被荷兰航海家发现时起,人们就纷起企图破解复活节岛之谜。复活节岛的居民和文化是从哪里来的?它经历了什么样的变迁?众说纷纭,其中当然也少不了外星人和与亚特兰蒂斯(大西洲)相似的《太平洲》学说(好像除作者外,几乎没有什么严肃的学者相信)。岛民的一个传说是有一群由白色神王康谷率领的白皮肤、红头发、蓝灰眼睛、鹰钩鼻子的人,最早从东方太阳火烧的大陆渡过辽阔的太平洋,来到岛上。这群人很久以前就消失了,让位给后来的居民,现在岛上混血的居民中还有一些白肤红发的人。这些最早的居民应当是来自南美洲的秘鲁。现在岛上的建筑格局、宗教仪式、神话传说、语言等方面,还可以看出和秘鲁古印第安文化相似的痕迹。而秘鲁的印第安传说中,太阳神叫康提吉,他率领一群白皮肤长胡子的人从北方来到印加,教导当地印加人耕种、建筑和礼仪风俗。后来跟一批印加人打了起来,遭到屠杀。康提吉带了一批属下逃到太平洋岸,航海而去,不知所终。
然而,复活节岛与南美洲大陆相隔4000浬,其间没有陆地,在古代,只有石制工具的南美洲人怎能航行到复活节岛去呢?海尔达尔认为:利用一股从南美洲向西去的洋流,乘古代印第安人的大木筏是可以漂流过去的。他做了一个试验,完全按照印第安人的做法,砍下安第斯山林产的高大质轻的筏木,用绳索捆绑起来,制成了一具15米长的有一个橹和一个帆的大木筏,带上食物和淡水,唯一的现代化的设备是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和四个同伴从秘鲁出海,顺西去的洋流漂流了101天,航程4300浬。在1947年4月到了复活节岛北面的土莫阿土群岛。此后又有人几次做过类似的试验。1960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学者们终于有了共识,—玻利尼西亚文明的一个源头来自南美。这对解答复活节岛之谜大有帮助,虽然它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复活节岛文明的一个源头来自南美那些“白人”。美洲大陆的印第安人是一万年至二万年前从亚洲大陆经过最北方的白令地峡来的亚洲黄种人。他们的文化传承的线索还不清楚。中南美洲的玛雅、阿兹泰克、印加等古文明发展程度远比北美从事渔猎的印第安人高。似乎不是从原来文明发展程度较低的印第安人那里来的。传说中,这些东西是从海外来的又被印第安人打败走了的长胡子的“白人”留下或教给印第安人的。其中有一支就败走到了复活节岛。
这些长胡子的“白人”及其文化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比较各地古文明,常可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对此的解释历来有传播说和孤立说之争。传播说认为,各地古文明的相似是文化由一地向另一地传播的结果;孤立说则认为各个古文明是独立发展的。相类似的环境和发展水平自然会使它们存在若干相似之处。一位孤立学派的学者曾指出秘鲁古文明和地中海古文明(特别是埃及)有60个相似之处,如金字塔、大石像、把太阳称为“拉”(Ra),鸟头人等等,都是世上少见,而又是这两个地区古代文明所共有的。但由于两地隔着大西洋,地中海古代仅有的芦苇船无法横越。所以这60个相似的文化特征只能是两地分别独立地发展起来的。
海尔达尔注意到了芦苇船。在复活节岛一些石像的胸前以及石壁上,镂刻着几艘有桅有帆的大型芦苇船。复活节岛居民的祖先还用它出海捕鱼。造船用的托托拉芦苇的故乡,则是南美的秘鲁。在秘鲁,大大小小的芦苇船至今还扬着布帆或芦苇编织的苇席帆在世界最高的大淡水湖(海拔3812米)的的喀喀湖上行驶,最大的可载重50-100吨。这种芦苇中空,藏有很多空气,造成船在水里至多散架而不致沉没。而最古老的芦苇船的形象、模型,则出自埃及古王墓和绘在壁画上。迄今,非洲中部的乍得湖上,还行驶着芦苇船。于是海尔达尔再做一次实验,证明古代浮力很大,不易沉没的这种芦苇船是可以横渡大西洋,把地中海古文明带到美洲去的。
海尔达尔从尼罗河上游的埃塞俄比亚找到了纸莎草,请来乍得湖的黑人,照古埃及芦苇船模型所显示的技术在金字塔下仿造,运到非洲摩洛哥西海岸下水;循大西洋向西去的洋流航行。但是在接近美洲的洋面上,芦苇船出了毛病,尾巴垂了下去,吸足了水拖在船下,船走不动了,也要散架了。这次航行失败了,距美洲陆地仅200浬。总结经验,发现原来芦苇船并没有完全照古埃及的技术造作,系起那高高跷起的船尾的排架和缆绳的做法不对,以致船尾吃不住长期风浪而下垂散掉。这次,从的的喀喀湖请来了印第安工匠,严格地按照古埃及的技术制造,再度出海。航行57天,行程3270浬(6700公里),终于抵达了中美小安的列斯群岛中的巴巴多斯岛。
海尔达尔的航行证明了,古代地中海地区、美洲乃至复活节岛之间的文化是可以通过远航联系的。在古代,大海大洋虽然严重阻碍了两岸人们的交往,但打破这种阻隔并非绝不可能。文化孤立学派的一个重要根据被推翻了。不过两派的争论仍旧没完没了地继续下去。此后,海尔达尔又乘两河流域苏美尔型芦苇船走出波斯湾,驶入阿拉伯海,再向西进入红海,他的航行和沿途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印度河谷和埃及这三大古代文明地区间的海上联系。
其实,实验的方法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常用的方法,海尔达尔的远航只是最为瞩目。这种方法更多地采用,使得西方兴起了一个“实验历史学派”,即把考古和文献调查以及实验结合起来,重新演绎历史活动的某些部分和某些方面,通过亲自体验以更好地理解历史。这也是对历史的摹写,或者叫做模拟。但已不是意识上、文字语言或音像上的摹写,而是照古代的办法,通过现代人的行为、活动所进行的摹写了。现在,计算机的发展出现了“虚拟现实”、“虚拟历史”,当会有很大的前途。
也许我们可以把这类实验和模拟从现实调查中分出来,作为认识历史的第四个途径。
六
既然已经有了模拟和实验人的某些历史活动,那是否可以在已有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水平上重演或复制过去的历史呢?例如:利用电子计算机像虚拟现实那样去虚拟历史,或者用时间机器或设法通过时空隧道(虫洞)回到历史上的真实的古代去,或者干脆运用克隆技术,再克隆一个或一批历史人物,让他或他们去重演一遍过去的历史。假如是这样,我们在认识历史的道路上又多了若干途径。目前这些离奇但不失新颖的设想还没有人试过,但已经在科幻作品中大量出现了。像唐朝张鷟的《游仙窟》,题为牛僧儒作的《周秦行记》,英国雪莱夫人的《佛兰肯斯坦》;美国马克·吐温的《亚瑟王朝的康涅狄克人》和后来的《回到中世纪》及多集同名电影;著名美国电影《回到过去》和《终结者》;还有近些年来一度在网上大量流行的穿越小说等等。其实,穿越时空的始作俑者当数庄子,他在梦中把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醒过来以后已经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蝴蝶还是庄子了。
历史有一个根本的特点,那就是它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也就是特定的物质世界中,历史发生的特定的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特定的空间也随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了面貌,更由于内部外部各种因素掺入而发生变化。人们常常感慨“物是人非”,其实已是“人非物也非”了。
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说过:“人不能两次趟过同一条河流。”他的学生克拉底鲁进一步引申——连一次也不可能,因为当整个身体浸到水里的时候,水已经不是原来的水了。因为一切时刻都在变动,过程不可逆,因此,重演和复制历史是不可能的。
拿现代人的知识、技术或思维形式去重演或复制历史,无论如何也逃不掉现代人的印记,即使把过程重演或复制出来,那也不是过去的真实真正的历史。运用电子计算机来虚拟真实的历史,需要建立某种类型的模型,一个好的模型需要具备简单性、清晰性、无偏见性和易操作性⑩,但要具备这些特性却很难臻于理想,自然现象如此,人文现象则更难达到。
要具备简单性,但历史模型要求输入更多的更复杂的因素及其互动才能更接近真实,并且还需要通过它们的不断增减、冲突与转移,才能实现历史的运动。就像群星闪烁的夜空一样。要具备清晰性,然而无数的历史因素的组合及运动偏偏不具备清晰性,尤其是判定的各种因素的性质和数量,以及它们在系统中的地位以及结合和运动的后果效应,这里会出现无数的不确定性和灰色地带,也会出现不可预计的历史效应。要具备无偏见性,人文现象很难做到。除了理性思维之外,还需要考虑到感性思维、心理的和情绪的思维,连区分因素的主次和重要不重要都是很困难的。要具备易操作性,各种类型的模型都有这个困难,尤其是对那些不可估量的因素的作用更是如此,简单的模型难于反映真实复杂的历史,跟美国经常现场演出的南北战争时期盖底斯堡战役秀也相差无几,而高层宏观的复杂的模型都难于操作,或无法操作。
至于克隆历史上的人,目前从技术上讲可能还不是做不到。但一旦克隆成功,完全重现所有的历史上的活动,还要表现出他的种种心理、情绪上的活动,那确是难以控制的。佛兰肯斯坦的最终失败,就是明显的一例。如果在克隆人之外更要加上真实的环境和历史气氛,那就更难了。因此,即使满足了重演历史的种种条件和气氛,要那个或那批克隆人真正重演历史那也是匪夷所思的。即使去掉一个因素或加入一个因素可能引起的蝴蝶效应,则是人们所难于预料的。
至于运用时间机器,或通过时空隧道回到历史,目前的技术还远远不能做到,即使能够做到,也会碰到难题。第一,你是作为参与者还是旁观者,如果是参与者,像身处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必定具有自己的地位、角度的局限,只能接触到和作用到身旁较为有限的一批人和事物;而旁观者虽能鸟瞰全局,却又难以深入,尤其是挖掘当事者的心理和情绪。第二,你既然参与了历史活动,也就改变了历史,使它完全不像过去那个真实的历史的再现,而只能是另一种“历史”。第三,你既然是从现在回到了真的历史,那你就是带着现代的意识和心态情绪,去面对过去的历史人物和环境,那只能是互不搭界,成了两股道上跑的车。如果你回到过去也回到了人的一切意识和心理素质,那你创造的“历史”也就无法为今天的人所认识。换言之,要么就是进入历史的不是历史的人而只是现代的人,那他的活动就不是历史;要么就是历史的人在创造历史却无法为现在的我们所认识。这是一个悖论。
总之,在现有的知识、意识、技术、环境的条件下,我们仍然无法通过对过去历史的重演和复制去认识真正的历史,所能做到的只是失去真实的、可笑的、粗糙的、模拟和较为局部的实验的再现,那不是历史的真实,也失去了历史的精神。
也许我们还只能满足于把这种实验和模拟当现实调查之中分出来,把它作为文献、实物、调查之外的认识历史的第四个途径,也许可以仿王国维的先例称为“四重证据法”。它距离我们认识真正的真实的历史的那个目标还很遥远,还只能假以时日,而有待于我们的进一步努力了。
注释:
① 王国维:《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3页。
② 社会学或文化人类学的调查方法,早就有了,而且在中国早被“引进”过来(像马长寿先生就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建国以后,范文澜先生曾发表过一篇文章《介绍一篇待字闺中的稿件》(《光明日报》1956年5月6日),特地介绍了刘尧汉先生关于彝族地区调查所得的有关彝族社会发展过程的变化。
③ 王雪生:《追踪两千多年前的战备工程》,《炎黄春秋》2004年第6期。
④ 张修桂:《“赤壁之战”的赤壁在何处》,《文史知识》2004年第6期。
⑤ 杜牧此诗一题李商隐作,杜、李集中均收。李商隐倒是几次经过武昌蒲圻一带,未见得不能写出《赤壁》这样的诗来。不知为什么,大家好像只把这顶桂冠加到杜牧头上。
⑥ 参见[美]欧文·斯通:《欧文·斯通文集:希腊宝藏》,刘明毅译,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9年;[德]C.W.西拉姆:《神祇·坟墓·学者:欧洲考古人的故事》,刘迺元译,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郑振铎:《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⑦ 这批宝藏后来藏在柏林,二次大战后期在战火中和其他一些古物被损毁,大部分陶器分散保存在小城利布斯,在战后散失了,最后只找到几个陶罐和一堆陶片。此后一位女学者找到利布斯,用五十镑糖果刺激小孩去找,小孩们把找到的陶器打碎分送回来以便多得一些糖果。只有几件在乡民家的陶器还是完好的,这里希腊时代餐桌上的坛坛罐罐被当地居民拣来作生活用品了。另外的陶器命运更悲惨,德国战败后,利布斯的居民看到许多箱保持在古堡里的陶器,完全不知道是什么。随着生活与生产的恢复,村里办喜事时,村里的青年来到古堡,就推出一车陶罐,高兴地把它们砸在新婚夫妻的门框上。因此珍贵的遗物完全没有了。
⑧ 参见[挪威]托尔·海尔达尔:《孤筏重洋》,朱启平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太阳神号草船远征记》,李泽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复活节岛的秘密》,王荣兴、董元骥、李乃坤、李成领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⑨ 据近来学者的研究,包括在复活节岛居民在内的波利尼西亚人,来自南岛语族,他们最早来自中国台湾,辗转东移到太平洋诸岛,于公元300年到达复活节岛。通俗的描述参见阎守邕:《扫描南太平洋岛国》,《中国国家地理》2008年第11期。
⑩ 参见[奥地利]约翰·L·卡斯蒂:《虚实世界——计算机仿真如何改变科学的疆域》,王千祥、权利宁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28-30页。
来源:《文史哲》2011年第6期
- 0002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