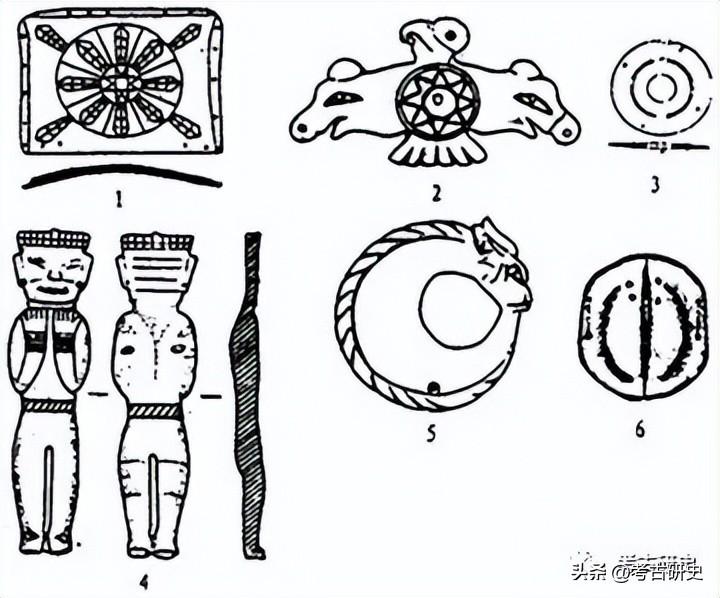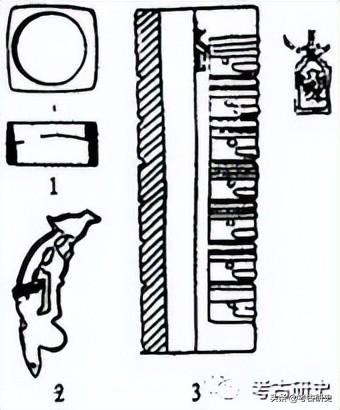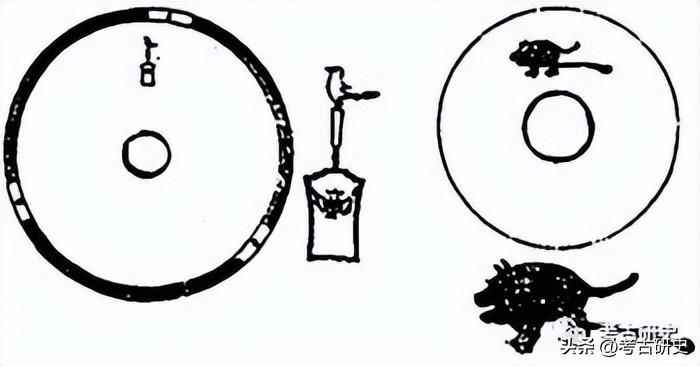王仁湘:仰韶文化渊源研究检视
中国考古学上仰韶文化的确立,已经有80多年的历史。仰韶文化的研究不仅成为中国考古学的中心课题,也是一些考古学家治学立业的基础。仰韶文化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可以列举出许多,这是20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灿烂的篇章。可以说,没有仰韶文化的研究,也就没有中国史前考古的今天。当然出现在学者们笔下的纷争也不算少,学术上也留下一些没能完全解决的世纪难题。关于仰韶文化来源的研究就是突出的难题之一,虽然不少学者尽了许多努力,一步步向着目标接近,但至今我们依然还没能获得理想的结论。
在追寻仰韶文化源头的过程中,研究者经历了许多的曲折,有失败也有成功,不断有后来者发现新证,否定旧说。现在回顾这个探索的过程,回首20世纪走过的路程,寻找新世纪的方向,应当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一、80年确定仰韶文化源头的历程
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除了对这个文化的内涵进行阐释外,研究者还要考察它的源流。一个文化的源头与流向,应当有非常明确的轨迹可寻。当然追寻这种文化轨迹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这种轨迹并不是一开始就那么清晰可辨。对仰韶文化源头的研究,就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而且时至今日我们还不能说这个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探索仍在继续。
在仰韶文化刚刚确立不久,人们就开始关注它的来源问题。起初安特生将河南与甘肃发现的彩陶,同中亚土库曼的安诺文化彩陶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两者有密切的联系,提出了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为演绎中国文化西来说作了很大努力。他根据英国考古学家、大英博物馆郝伯森(R·L·Hobson)的意见,认为彩陶技术的始源地是巴比伦,仰韶彩陶技术是由中东传来的。他还据此推定仰韶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它早于夏代而晚于近东最早出现彩陶的公元前3500年(注: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为了证明这个推论的真实性,他在发现仰韶以后,便一头扎到中国西北,认为仰韶文化最近的源头在那里,因为那里应当是中东彩陶东传的必由之路。经过几次田野考察,觉得努力有了成效,他在甘青一带发现了许多彩陶遗址,同时也发现了彩陶较少的遗址,他真的以为找到了仰韶文化的源头,以为解决了这个问题。1925年,他在所撰的《甘肃考古记》中,根据自己的调查,对甘肃史前文化提出了所谓仰韶文化“六期”说(注:安特生:《甘肃考古记》,1925年。)。这六期从早到晚依次是齐家、仰韶、马厂、辛店、寺洼和沙井,前三期划归新石器时代和铜石并用时代,后三期则归入早期铜器时代。列出这样的分期表,是为了明确地表述“仰韶期”来源于“齐家期”,因为齐家期少见彩陶,认为它的年代较早。可惜的是,他把远古世界的年轮弄颠倒了,结果得到的是本末倒置的结论。
当时中国学者对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年代表,有着各不相同的看法。1931年,梁思永先生发现了安阳后岗“三叠层”,在依据地层证据研究仰韶与龙山文化相对年代关系的基础上,在仰韶期之前增加了一个后岗期(注:梁思永:《小屯、龙山与仰韶》,见《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9年。)。1939年,尹达先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注: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见《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55年。),将仰韶分为后岗、仰韶和辛店三期。中国学者当时的研究,无异于是说仰韶期是在后岗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他们想藉此否定“中国文化西来说”。
1943年,安特生又发表了《中国史前史研究》(注:安特生:《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将仰韶文化的绝对年代作了较大的改变,但并没有改变各期的相对年代关系。中国学者通过自己的实践一步步否定了安特生的结论,当时取得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将齐家期从仰韶中分离出来,独立命名为齐家文化,而且从地层关系上明确它的年代晚于仰韶文化,彻底否定了安特生的“六期说”(注:a.夏鼐:《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年;《齐家期墓葬的发现及其年代之改定》,《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年。 b.裴文中:《甘肃考古报告》,见《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尹达先生曾多次撰文批评安特生在仰韶文化分期及绝对年代判定方面的种种误说,他1955年发表的《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则是全面分析安特生错误根源的一个系统总结。他认为安特生对于中国新石器时代分期问题上的基本论点,是所谓单色陶器早于彩色陶器,这个错误的理论使他对中国新石器文化的相对年代的估计出现了严重问题(注:尹达:《论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关于安特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分期问题》,《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当然,安特生的这个错误,也直接影响了他研究仰韶文化起源的正确性。
安特生的学说维持了约20年左右后,就完全成为了历史,仰韶文化“西来说”被中国学者纠正了。虽然仰韶文化西来说的观点被否定了,但学术界并没有立即解决它的来源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黄河流域都没有发现年代更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存。正如陈星灿先生所说的那样,“安特生等考古学家所以把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指向西方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早于仰韶的史前文化的缺失”(注: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
20世纪50年代以后,黄河中游地区田野考古工作蓬勃开展,中国学者很快建立起了一个新的仰韶文化体系,对仰韶文化来源的研究也有了全新的认识。20世纪50~60年代之际,仰韶文化研究的主要成就是确立了半坡和庙底沟两个文化类型,正是这两个类型体现了仰韶文化的主要内涵,学术界对仰韶文化的研究也就有了新的起点。虽然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绩,研究者之间在认识上却又出现了新的差距,他们对这两个类型内涵的认识有大体相似的意见,但对它们之间关系的认识却难以一致。有的意见认为半坡早于庙底沟,有的则正相反,有的又认为两者大体同时。这样一来,究竟是由半坡还是由庙底沟去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都难以确定。
进入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后,随着陕西境内北首岭、老官台和李家村遗址的相继发掘,发现了不同于仰韶文化的新一类遗存,在许多人还不知道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发现时,敏锐的研究者很快认定它们与仰韶文化存在渊源关系,这让学术界看到了新的希望(注: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这一类遗存,后来被有的研究者命名为“老官台文化”和李家村文化等。从此以后,研究者在讨论仰韶文化的起源时,很自然地把眼光放到了这些目标上。这与安特生的研究相比,可以说是令人耳目一新了。对于这样的新发现,夏鼐先生一直都比较冷静,他仅在196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及西乡李家村、宝鸡北首岭和元君庙下层遗存比仰韶文化时代更早而且具有密切关系,“是探索仰韶文化前身的一个较为可靠的线索”(注:夏鼐:《六十年代前期的考古新收获》,见《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在1977年发表的《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考古学》一文中,他也只论及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年代早晚关系,没有具体讨论仰韶文化的来源问题,因为早期的年代数据还没有测定出来(注:夏鼐:《碳-14测定年代和中国考古学》,《考古》1977年第4期。)。他在1979年所写的《三十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和其他论文中,虽然提到了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仅说它们早于仰韶,没有说明是否有渊源关系。1983年在日本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时,仍没有明确提及仰韶文化的源头在哪里(注:夏鼐:《六十年代前期的考古新收获》,见《夏鼐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最早对仰韶文化来源问题进行实质性研究的是苏秉琦先生,他在196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已经注意到宝鸡北首岭和华县元君庙下层与仰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注: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代早于半坡类型的遗存在渭河流域有较多新的发现,经过正式发掘的地点有秦安大地湾、临潼白家村、渭南北刘、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等处,有的研究者又将它们重新命名为“大地湾文化”或“白家村文化”,从而进一步确认了它们与同地区仰韶文化之间的渊源关系。1981年,苏先生在讨论姜寨遗址发掘意义时说,仰韶文化一期的代表遗存有两个:秦安大地湾一期和宝鸡北首岭一期。他是将当时所知的前半坡遗存都划归仰韶早期(注:苏秉琦:《姜寨遗址发掘的意义》,《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2期。)。1986年,在不同的场合,他都讲到前仰韶问题。在兰州的“大地湾会”上,他明确表示赞同将大地湾一期作为前仰韶看待,认为同类遗存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注:苏秉琦:《“大地湾会”讲话(提要)》,见《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他曾特别提及北首岭遗址底层或许代表中心区典型的“前仰韶”文化遗存(注: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仰韶最近的渊源。
几乎与此同时,在河北和河南地区也发现了一批早于后岗类型的仰韶文化遗存,这就是很快确认的磁山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它们与同地区的“仰韶文化”也被认为具有渊源关系。
这些发现表明,至少在陕西和河南两大区域内,传统上认识的仰韶文化并不是只有一个来源。学术界在为这些新发现感到高兴的同时,也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这一种多源现象开始令研究者迷惑不解,一些为仰韶文化释源的研究成了当时中国新石器考古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成果。有研究者指出,从发展序列看裴李岗和磁山两个文化早于仰韶文化,它们的某些因素又见于仰韶文化的早期遗存中,这为仰韶文化起源研究提供了新证。虽然如此,当时对仰韶文化同以裴李岗、磁山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之间究竟是直接承袭,还是交错存在而互有影响,并不是很清楚。有的研究者将一般认定的“老官台”和“北首岭下层”遗存归纳为仰韶文化的“北首岭类型”,所以不能明确豫、晋、陕一带仰韶文化的起源是怎样的(注:安志敏:《裴李岗、磁山和仰韶》,《考古》1979年第4期。)。不久,研究者肯定了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都属于仰韶文化的先驱,强调仰韶文化是黄河流域的主要遗存,它继承的是早期裴李岗文化和磁山文化,下接龙山文化,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表明中原文化基本上是一脉相承的(注:安志敏:《三十年来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考古》1979年第5期。)。后来研究者又以“北首岭类型”为基础,提出了“大地湾文化”的命名(注:安志敏:《关于裴李岗文化的性质和年代》,《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1期。),并且将它与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相提并论,都归入早期新石器文化范畴,不再作为仰韶文化看待,认为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和大地湾文化代表着中原地区三种较早的遗存,与仰韶文化的早期阶段有着密切的联系(注:安志敏:《略论中原的早期新石器文化》,见《磁山文化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
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已经达成的共识是:在仰韶文化分布地域内陆续发现了老官台文化、磁山文化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直接脱胎于这三种早期新石器文化,是在这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老官台等三种早期新石器文化的发现,从事实上和理论上都解决了仰韶文化的渊源问题(注: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20世纪末,由于陕西临潼零口、山西垣曲古城东关和枣园等遗址的发现,在介于老官台和仰韶文化之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遗存。它的相对年代虽然比较容易确认,但对它的性质却是议论纷纷,有说它是半坡最近的源头,也有说它是庙底沟的源头。对此,我们在后面还要讨论。这样一来,庙底沟类型的讨论又成了新的热点,这就重新提出了一个旧的问题:庙底沟类型的形成如果与半坡类型没有任何关系,仰韶文化体系的讨论必须得推倒重来,那么它的来源问题岂不是也要从头论起?
我们将上述论点综合起来,发现学者们先后认定的仰韶文化祖源有下列若干个。
1.齐家期。
2.后岗期。
3.老官台文化(或称大地湾、白家村文化)。
4.李家村文化。
5.北首岭下层文化。
6.磁山文化。
7.裴李岗文化。
8.零口文化。
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是这样无法确定。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涌现,研究者们的认识经历了不断充实和逐渐修正的漫长过程。我们今天也许很容易对其中的认识作出十分明确的评判,可以很容易地指认哪一种认识最接近正确,要知道我们能够达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该是多少学者用了多少时间的努力才得来的!
二、从多源观到一源观
对于仰韶文化来源的研究,出现的争论很多,其中一源与多源认识的不同,就是很突出的一个分歧。而“分源”问题的提出,则是研究上取得的重要突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仰韶文化探源的研究出现了新局面。发现一多,研究者就有了更多的思考余地,研究的深度也大为扩展了。关于仰韶文化的源头,有一源观,也有多源观。多源的说法一般较为笼统,研究者大多是将仰韶文化分布区的更早的遗存都列为源头,认为仰韶是起源于老官台、李家村、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的。这样的说法虽然相当含糊,但学术界还是接受的。一源说则明确指出仰韶是源于老官台文化,或是源于裴李岗文化。严文明和张忠培先生几乎同时发表了相似的“分源”观点,将仰韶文化起源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1979年,严文明先生提出老官台文化的命名,指出它是半坡类型的前身。他认为“由老官台文化发展为半坡类型,再由半坡类型发展为庙底沟类型以及更晚的一些文化类型,这条线索是比较清楚的”,仰韶文化中的“后岗类型是在继承了磁山文化的许多因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磁山文化发展为后岗类型,再发展为钓鱼台类型和大司空类型的线索也比较清楚”。同时,他还认为红山文化和青莲岗文化也继承了磁山文化的一些因素,如篦纹陶、直筒罐和圜底钵等(注:严文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新发现》,《考古》1979年第1期。)。他在这里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这种文化来源不同出发,建议将仰韶文化“一分为二”,将后岗—大司空和半坡—庙底沟作为两个不同的系统区分开来。
1979年,张忠培先生也提出了老官台文化的命名,认为由老官台发展为半坡类型(注:张忠培:《试论东庄村和西王村遗存的文化性质》,《考古》1979年第1期。)。两年后他又专论老官台文化,不同意将它纳入仰韶文化范畴,明确指出“仰韶文化是包括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乃至不同系列的许多种文化的庞大概念。因之,分布在一定地区的老官台文化只是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的前身”。他还指出,磁山和裴李岗文化的后继者是后岗类型(注:张忠培:《关于老官台文化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
魏京武先生也提出了“分源”问题,他讨论了老官台、李家村、裴李岗文化的内涵、命名和年代,认为是老官台和李家村发展到半坡,裴李岗发展到后岗(注:魏京武:《李家村、老官台、裴李岗——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张瑞岭先生根据陕西渭南北刘遗址的发掘,也得出了与魏京武先生相同的认识,他们都注意到不能笼统地谈论仰韶文化的起源(注:张瑞岭:《渭水流域新石器早期遗存的文化性质与年代》,《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发掘了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的郎树德和赵建龙先生,在肯定老官台文化与半坡类型有着一脉相承的因袭关系后,认为笼统地说老官台、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为仰韶文化是不正确的。具体来说,“半坡的彩陶之所以比后岗发达,后岗的鼎类器物之所以较半坡多见,后岗的素面陶比例之所以超过半坡,是因为两者继承的不是一个文化,换言之,两者不是一个文化源头”(注:郎树德、赵建龙:《关于老官台文化的新认识》,《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6期。)。
丁清贤先生也觉察到了其中的不妥,他在1985年发表的《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一文,对各地划归仰韶文化系统的遗存进行了粗略分析,认为仰韶文化实际上包含着三支各具特征、不同源流、分布在不同范围内的原始文化遗存。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渊源于李家村、老官台文化,发展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包括鄂西北,不包括豫西)的仰韶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发展为当地的龙山文化;河北、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的仰韶文化,渊源于磁山文化,分别发展为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他认为仰韶文化只能包括分布在关中、豫西和晋南的遗存,建议将河南的仰韶遗存命名为大河村文化,而陕西的仰韶遗存则命名为半坡文化(注: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第3期。)。
苏秉琦先生将仰韶文化划分为中心区(以半坡和庙底沟的早期遗存为代表)、东区(以大河村和王湾为代表)和西区(以大地湾为代表)三个区,他说寻找这不同区系的仰韶文化的源头,需要分别进行,“当我们着手探索它们的渊源问题时,不得不分头进行,而不能设想可以一揽子地解决,一劳永逸”。他认为北首岭遗址底层或许代表中心区典型的“前仰韶”文化遗存,“至于东西两区系自己的‘前仰韶’遗存是什么,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北首岭提供的条件,暂无从猜测”(注: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
1986年,石兴邦先生有一篇专论前仰韶文化的论文,也提出“分源”问题,明确指出半坡类型源自白家—李家村文化传统,而后岗和下王岗一期文化则是由磁山—裴李岗文化发展而来(注:石兴邦:《前仰韶文化的发现及意义》,见《中国考古学研究(二)》,科学出版社,1986年。)。
20世纪80年代末期,“分源”的认识已成主流。杨亚长先生论南郑龙岗寺“前仰韶”遗存,便直言龙岗寺李家村类型是半坡类型的直接渊源(注:杨亚长:《龙岗寺“前仰韶”遗存有关问题初探》,《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1989年,李友谋先生在《裴李岗文化发现十年》中(注:李友谋:《裴李岗文化》,《中原文物》1989年第3期。),认为裴李岗文化直接为仰韶文化所继承,但裴李岗文化和仰韶时期的半坡类型文化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半坡类型文化的来源是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与后岗类型文化似乎也没有渊源关系,后者可能来源于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应该归宿于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石固遗址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的仰韶遗存,接近于大河村的一、二期遗存,属于大河村文化系统,裴李岗文化的直接继承者当为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曹桂岑先生在《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一文中(注:曹桂岑:《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见《考古文物研究——纪念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四十周年文集》,三秦出版社,1996年。),也表述了相似的观点。他说在新郑唐户、长葛石固、汝州中山寨等遗址,都发现“仰韶文化”层叠压在裴李岗文化层之上,在豫中地区两者的分布地域大致重合,在文化面貌上也有明显的承袭关系,“裴李岗文化直接发展为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仰韶文化找到了源头。”
从其他许多学者的论著中,我们知道“分源”说已为学术界所普遍接受。可以说,在仰韶文化发现近60年的时候,研究者关于仰韶渊源的探索有了较多的共识。最主要的收获是,认为不同地区的“仰韶”有着不同的来源。这个认识是在80年代初形成的,至90年代后,基本为学术界接受。杨肇清先生在总结20世纪仰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时,说“仰韶文化的源与流的问题也已大致搞清,仰韶文化早期各类型各有其来源”,具体说半坡类型源自大地湾一期文化,大河村类型源自裴李岗文化,后岗类型源自北辛、磁山等文化(注:杨肇清:《20世纪仰韶文化的重要发现与研究》,见《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由以上叙述,我们看到了对仰韶文化研究有过重大建树和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许多学者们的论说,从中我们得知获取正确的认识是多么的不容易。考古学家是最具备实事求是胸怀的,他们能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由于资料局限形成一些不成熟的认识,应当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以体谅的,我们终究是越来越接近正确。
三、关于仰韶文化与仰韶体系
随着仰韶文化内涵的不断外延,它的分布范围越划越大,类型越定越多,它的源头也就由本来的游移不定而变得越来越多。来源不同的文化,本来具有一些独到的特点,长期以来却被看作是同一个文化,研究者们没有觉得这里面有没有费解的地方。用一个比喻来理解,这就好象是几条溪流汇进了一条大川,而大川之中的水流又都各不相干,它们各自流到了不同方向,又变成了一条条溪流。不用说,自然界是没有这样的大川和溪流的。
研究仰韶文化的来源,必须追本,才能究源,追本最为切要。仰韶文化之本是什么?
如果我们现在给仰韶文化下一个定义,不同学者之间的分歧肯定是不小的。在根本出发点存在分歧的情况下,也就是人们在什么是仰韶这个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的时候,要确切地谈论仰韶的来源是不现实的。我们通常说仰韶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分布地域又很广,各地的遗存表现出的差异比较明显。为了区分这些差异,类型的划分成了热点课题。对仰韶文化类型的研究,开始于半坡和庙底沟两类型相对年代与性质的讨论。半坡和庙底沟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仰韶文化的两个主要类型,也奠定了仰韶文化研究的新基础。对这两个类型的关系,起初有认为半坡早于庙底沟的(注:a.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考古》1959年第10期。 b.严文明:《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也有认为后者早于前者的(注: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b.杨建芳:《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2年第1期。),还有认为两者是同时的(注:a.石兴邦:《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第6期。 b.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论还依然存在,多数意见认为两个类型具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也有人认为并不能完全肯定谁早谁晚,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著作中还认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解决(注:a.严文明:《论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 b.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c.安志敏:《略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年代问题》,《考古》1972年第6期。 d.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现在对这两个类型间关系的讨论还在继续(注:戴向明:《试论庙底沟文化的起源》,见《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系建系十周年纪念文集》,知识出版社,1998年。),同时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在两个类型之外又命名了一些新的类型,又有了许多认识上的分歧。
随着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表现有仰韶文化某些特点的遗存在更广的范围内有了更多的发现,研究者将仰韶文化的分布划分为关中—陕南—豫西—晋南区、洛阳—郑州区、豫北—晋南区、丹江区、陇东区、张家口区、河套区等几个大的区域。根据区域特征命名的地方类型有:陕西的半坡、史家、泉护、半坡晚期、北首岭类型;山西的东庄、西王村、西阴村、义井类型;河南的庙底沟、大河村、后岗、大司空、阎村、下王岗、王湾、秦王寨类型:河北的下潘汪、三关、钓鱼台、南杨庄、百家村、台口类型;内蒙古的海生不浪类型;湖北北部和陇东发现的仰韶遗存,分别归入豫、陕仰韶系统,没有新的类型命名。
从命名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开始,仰韶文化类型的命名已增加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个之多,这些纷繁的名称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仰韶体系。有的研究者认为,陇东—关中—晋南—河南的仰韶文化,还可以细划为三区,即宝鸡至陕县一带的中心区,以半坡和庙底沟早期遗存为代表;东区为河南中部地区,以大河村和王湾为代表;西区为陇东地区,以大地湾为代表。三区间的模糊分界是崤山和陇山(注:苏秉琦:《纪念仰韶村遗址发现六十五周年》,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5年特刊。)。有些研究者大而化之,认为仰韶文化大致可以分为以渭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和以中原地区及其周围地区两个大的区系,前者以半坡—庙底沟类型为主,后者以后岗—大河村类型为主(注:魏京武:《汉江上游及丹江流域的仰韶文化》,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即便是对河南境内的仰韶文化,在分区研究上也有诸多不同的意见,如有的分为豫西的庙底沟,豫中的大河村,豫北的后岗、大司空,豫西南的下王岗等五个类型;有的则认为豫西为庙底沟类型分布区,豫中为大河村文化分布区,豫北为后岗、下潘汪文化分布区,宛襄为下王岗文化分布区(注:a.杨育彬:《关于河南地区仰韶文化的两个问题》;张居中:《仰韶时代文化刍议》,见《论仰韶文化》,《中原文物》1986年特刊。)。
这些研究表明,现在构建的大仰韶体系内涵并不是单一的,不仅有中心分布区与周边分布区的不同,还有内涵上的不同和源流上的不同。根据这些区别和近年来学术界的研究倾向,我们建议将分布在陇东—关中—陕南—豫西中心区的仰韶文化,分别命名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和西王村文化,它们或可合称为典型仰韶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将这个区域一度划属仰韶早期的北首岭下层类型归入前仰韶文化;将周边分布区与仰韶文化关系密切年代相当的遗存,与中心区明确区别开来,分别命名为后岗(一期)文化、大司空文化、大河村文化和下王岗文化等。我们希望经过这样的整理,能使仰韶文化的面貌更加清晰一些。
在以往一些论著中,研究者将仰韶文化的内涵不加限制地扩展,致使仰韶文化的一般特征丧失,所以我们在这些论著中不容易见到关于仰韶文化一般特征的描述。我们以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类型作为仰韶文化的主干,作了这样的限定之后,仰韶文化的总体特征可以概括为:在定居的农耕村落基础上出现了大型环壕聚落,聚落中的居址构成几级社会结构。居址以圆形和方形半地穴式建筑为主,建筑方式主要为木骨草拌泥墙、红烧土地面。居址附近有大规模公共墓地,成人以单人一次葬为主,一度流行二次合葬,幼儿多采用瓮棺葬。随葬品以实用陶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生产工具和装饰品。日常生活用具主要为陶器,早期以红陶为主,器表装饰多见粗细绳纹,也有弦纹等,有一定数量的彩陶,器形有罐、瓮、尖底瓶、碗、钵、盆,多为平底器;中期灰陶比例增大,新增器形有釜、灶、鼎和豆,彩陶纹饰有所变化。生产工具有石器、骨器、陶器,以石器和骨器为主。早期有一定数量的打制石器,磨制石器主要有斧、锛、凿、铲和长方形小石刀。骨器大多磨制较精,多见镞、锥和针等。装饰品有骨珠、骨笄、陶笄和陶环等。
这便是仰韶文化的本。我们要探求的源头,应当就是这个“本”的来源。而这个本的早期阶段,是半坡文化。简而言之,寻找仰韶文化的源头,就是寻找半坡文化的源头。半坡文化以原来的半坡类型为基础命名,因陕西西安半坡遗址的发掘而得名。也有人将它的后半段独立出来,以渭南史家墓地为典型地点,命名为“史家类型”(注:a.巩启明:《试论仰韶文化》,《史前研究》1983年第1期。 b.王小庆:《论仰韶文化史家类型》,《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半坡文化陶器为手制,质地多为夹砂和泥质红陶,有少量黑、灰色陶器。器形主要有圜底和小平底钵与盆、深腹盆、细颈大腹壶、小口尖底瓶、深腹罐,多圜底、平底和尖底器,少圈足器,无三足器。晚期出现葫芦瓶、带盖平底小罐和高领罐。纹饰有绳纹、细绳纹、弦纹、锥刺纹和黑彩图案,彩绘纹样有宽带纹、三角、折线等几何纹,和网纹、鱼纹、人面纹、鹿纹、鸟纹等象生图案,常见内彩,有些钵、盆类陶器上有不同的刻划符号。生产工具中的石器以磨制的为主,也有打制的,主要器类有斧、铲、锛、刀、凿和磨盘等,以一种两侧带缺口的石刀最具特色。还有大量磨制精细的骨器,器形为镞、针、锥三类。工具中还常见有陶锉。
半坡文化居民建有大型环壕村落,居址排列有序,以圆形半地穴为主要建筑形式。村边有公共窑场,村外有公共墓地,墓穴排列整齐,早期多单人葬,晚期流行多人二次合葬。儿童多使用瓮棺埋葬,一般埋葬在居址附近。
半坡文化主要分布在关中、陕南、陇东与晋南地区。寻找仰韶文化的来源,就是确定半坡文化的来源。按一般规则,半坡文化的祖源应当在它的分布区域内寻找,可是发现和研究已有半个世纪之久的半坡文化,它的源头至今却并不那么明晰。就中国史前考古研究走过的探索之路而言,寻找半坡文化的起源,也不会容易!
四、前半坡的来源问题
我们不能否认,许多学者在探索仰韶文化来源问题时,他们实际上也是在探索半坡文化的起源。寻找前仰韶文化,实际上就是寻找前半坡文化,虽然目标已经缩小了许多,但我们现在只能说,前半坡依然是踪影不明。
1984年,通过发掘临潼白家村遗址,我与另外几个同行合写了一篇论文(注:吴加安、吴耀利、王仁湘:《汉水上游和渭河流域“前仰韶”新石器文化的性质问题》,《考古》1984年第11期。),也论及仰韶文化的起源,提出前仰韶文化研究还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主要有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与仰韶文化早期的关系,以及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的分期问题。还特别指出白家村一类文化遗存与早期仰韶文化之间还存在缺环,白家村文化(大地湾、老官台文化)并不是仰韶文化的直接来源。在《临潼白家村》的结论中,我们一方面指出由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发展的趋势,另一方面还特别强调了二者之间的区别。区别表现在十个方面,特别是陶器形制,白家村文化的碗、钵、罐多为三足、圜底或圈足,至半坡时期却全部消失,器物群完全不同了(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临潼白家村》,马蜀书社,1994年。)。1987年,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发现白家村文化与北首岭下层类型的地层叠压关系,使得相关的认识又有了深化,认为“北首岭类型”似乎是白家村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一个中间类型,是已知的仰韶文化最近的渊源。不过北首岭类型究竟如何过渡到仰韶文化,并没有充足的论据进行证明,在北首岭类型和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之间还有一段不小的缺环。从绝对年代数据看,也可证实这一点。半坡类型最早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是用北首领中层标本测出的,为距今6140±120年(ZK-516),其校正年代为距今6790±145年,与北首岭类型的年代有约300年的间隔。这两个文化(白家村文化和北首岭类型)发展阶段尽管都属前仰韶时期,却不是仰韶文化最直接的渊源,在它们与仰韶文化——主要是指半坡类型之间,可能还存在一个未知的过渡阶段(注:王仁湘:《论渭河流域早期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两个阶段》,《考古》1989年第1期。)。在学术界认为仰韶起源早已解决的时候,这样说显然有些不合时宜。
一些专门研究半坡文化的论文,在讨论它的起源时,依然维系原有的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老官台文化在年代上早于半坡,分布地域也重合,只有它最可能是半坡文化的前身(注:赵宾福:《半坡文化研究》,《华夏考古》1992年第2期。)。当然也有人指出陕南区与泾渭区的半坡文化可能有着不同的文化渊源,前者主要来源于陕南的北首岭文化,后者则与泾渭区的北首岭文化有关(注:孙祖初:《半坡文化再研究》,《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有的研究者特别强调,在老官台文化、北首岭文化和半坡文化之间,先后承继的文化关系表现得最为明显。这里所指的“北首岭文化”,主要是宝鸡福临堡、陕南龙岗寺和北首岭遗址的早期遗存(注:孙祖初:《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向晚期的过渡》,《华夏考古》1997年第4期。)。也有研究者将北首岭早期作为老官台文化的一个类型,认为是它演变发展为仰韶早期的半坡文化(注:戴向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格局之演变》,《考古学报》1998年第4期。)。
近年来,探索仰韶文化渊源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山西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现的“仰韶文化早期遗存”中,发掘到了数量不少于3个的标准陶鼎,鼎体为圜底罐形,有高高的锥状足,口径在14~16厘米之间,高度不超过20厘米。据发掘者判断,这个遗址的时代与半坡遗址的早期是接近的,内涵也有相似之处,主要区别在于这里没有半坡文化常见的尖底瓶和富有特点的彩陶,而环状口小平底瓶、假圈足盆、缸、盔形器盖、尖锥足鼎、弦纹罐等,却不见于半坡文化的其他遗址。认为它的一些特点有承自裴李岗文化的因素,也就是说它明显接受了东来文化的影响(注:a.中国历史博物馆考古部等:《山西省垣曲县古城东关遗址IV区仰韶早期遗存的新发现》,《文物》1995年第7期。 b.中国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类似的发现在晋南地区还有更多,如翼城枣园(注: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枣园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报告》,《文物季刊》1992年第2期。)、垣曲东关古城、万荣西解等遗址(注:陈斌:《万荣西解遗存的发现及其在仰韶文化中的位置》,《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第11期,1989年。),都见到相似的文化遗存。值得注意的是,类似遗存在关中地区也有发现,1994年在面积约2万平方米的临潼零口遗址,发现了前仰韶、半坡和西王村文化的连续堆积,而且在半坡文化层之下,还有一个介于前仰韶和半坡文化之间的中间层堆积。这个中间层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陶,主要器形有环形口小平底瓶、假圈足钵、深腹钵、器座、弦纹罐等,器表装饰多素面少彩绘,它被暂时称为“零口遗存”(注:周言:《专家论证零口遗存》,《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6期。)。零口遗存的确与垣曲古城东关遗存相似,而且其层位是在前仰韶和半坡文化之间,将它作为半坡文化最近的渊源所在,也就是典型仰韶文化的起源所在,自在道理之中。
零口遗址的简报近年已正式发表,按照发掘者的研究,“零口文化”可能是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直接前身,而且与庙底沟类型有一定的渊源关系(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临潼零口遗址第二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6期。)。发掘者还特别指出,零口文化的形成曾受到裴李岗文化的影响,表明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应当是同祖同源并行发展的(注:阎毓民:《零口遗存初探》,见《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普遍的认识是,这一类遗存在时代上早于半坡文化,有的说它直接发展为半坡文化,也有的说它直接发展为庙底沟文化,有的则直接将它列入仰韶文化早期(注:中国历史博物馆博物馆部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不可否认,关中和晋南地区零口一类前仰韶文化遗存的发现,让人们看到了仰韶文化探源研究的新希望。但是在这个希望面前,我们还是应当谨慎一些,仰韶的源头可能还有疑惑。且不说研究者对零口一类遗存的归属尚有分歧,冷静一点看,这类遗存其实不论与半坡还是与庙底沟之间,距离都是很大的,现在将它作为半坡或是庙底沟文化的源头,都还显得有些为时过早。果不其然,最近又有人发表了新的意见,认为零口遗存本身内涵也并不单纯,它既包含有老官台和北首岭下层遗物,也有仰韶文化早中晚不同阶段的遗存,不能笼统地命名为一个文化。更不能由此得出“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是同祖同源、两者并行发展”的结论(注:吉笃学:《“零口文化”试析》,《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3期。)。
在此我们想作一点简单的个案研究。我们先关注一下三足器。半坡人是绝对拒绝使用三足器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半坡人中断了黄河中游史前居民用鼎的传统。如果从这个角度认识,半坡的这个传统应当来自关中以外的其他地区而不是它的东方,因为东方及关中都有使用三足器的传统,前仰韶时期的白家人、裴李岗人、磁山人、北辛人,都大量制作和使用三足器。1981年,魏京武先生虽认为老官台、李家村和裴李岗是仰韶文化的源头,但同时也曾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作为早期陶器特点的三足器和圈足器怎样会发展为仰韶文化的平底器和尖底器?(注:魏京武:《李家村、老官台、裴李岗——关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4期。)由前仰韶盛行三足器,到半坡不见三足器,两者之间实在看不到有什么一脉相承的关系。这么说来,用鼎的零口文化居民虽然生活的时代与半坡文化居民相当接近,却也并不是一回事,认为半坡文化发韧于零口文化,还需要斟酌。
还有仰韶的尖底瓶。尖底瓶的意义主要可能还不在于它是一种欹器,不在于它在汲水时表现出的特别的力学特征,而主要在于它的小口,可以保存盛水不致蒸发或荡溢,这是干旱少水地区的特有水器,它分布的范围最能说明问题。尖底瓶的起源并不清楚,虽然在零口文化中见到小口瓶,它能否演变为后来的尖底瓶,现在也还没有定论。
另外还有绳纹问题。半坡文化主要以各类绳纹作装饰,它的绳纹并不直接承自白家村文化的传统,前者主要采用斜绳纹,而后者则以交错的网状绳纹为特征。更重要的是,处在两者之间的零口文化发现绳纹极少,并不以绳纹作为陶器的主要装饰。仅此一点,就可以证明半坡文化不会直接源于零口文化,当然更不会是直接源于白家村文化了。
我们不能否认,零口文化的出现非常突然,它切断了建立在学者们论著中的仰韶与前仰韶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们以前用心探求的前仰韶,它的传统并没有为仰韶文化所继承。这个事实对我们的打击显得太残酷了一些,它致使我们过去精心构筑的仰韶文化源流体系几乎瓦解,也似乎让我们过去在这方面做的所有研究顿时没了什么实际意义。
但是,零口文化的发现具有重要价值,它的价值不仅在使仰韶文化探源研究增加了新的难度,而且还透露了一个重要的远古文化变革信息。对此,还准备另立课题进行深入研究,这里不拟展开讨论。
半坡人的传统显然来自干旱的黄土高原,这传统很让人怀疑可能生长在甘肃、青海地区,仰韶文化的正源,似乎要从关中以西的地区去寻找。这似乎有点不合常理,又与安特生当年的想法相似,他在发现仰韶村遗址后不久就去了甘青,指望在那里寻找到仰韶的源头。现在我们旧事重提,与安特生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有根本性的不同。
五、前仰韶:20世纪没有完全破解的谜
自仰韶文化发现之日起,学者们就为探寻它的起源付出了许多的辛劳。从安特生等西方学者的西来说,到我们自己创立的本土说和多源说,都没有或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西来说认为仰韶文化与域外文化的传播有关,这个认识的出发点是,彩陶技术始源于中东地区。我们已经发现了前仰韶文化时期的原始彩陶,说明黄河中游地区也是世界上的一个彩陶起源区域。人们有理由认定,中国的彩陶技术可能并不是由域外传来,那仰韶文化起源的西来说也就不可能成立了。
西来说的另一个重要前提,是当初黄河中游地区没有见到年代更早的古文化遗存。在仰韶文化分布区内大量前仰韶文化遗存发现以后,在前仰韶与仰韶文化之间,研究者可以找到许多亲缘关系,仰韶的出现,有本土的父本母本。这是本土说的重要根据,西来说由此彻底瓦解。当然本土说只是一种笼统的说法,仅对否定“西来说”具有意义,并没有解决实质问题。
多源说是本土说的具体化,也是一种很不严格的观点。若干个文化源头——老官台、李家村、磁山、裴李岗文化,孕育了一个大仰韶,而这个大仰韶东西南北面貌各异,多源而实际上又并不同流。这种多源说不仅在文化内涵的演变上讨论不充分,在逻辑上也得不到论证,它实际上只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过渡性观点。
分源说最切实际,确定主源,然后理清其他源流关系。分源说认为山西、河南仰韶的起源与关中不同,其源头应是裴李岗文化或其他同期文化。关中及附近地区的仰韶文化,大而言之是起源于白家村(老官台、大地湾)文化,这也就是狭义的“前仰韶”,是专指典型仰韶文化的源头,也即是半坡类型文化的源头。半坡文化最直接的源头起初有认为是北首岭下层文化,后来又进一步被认定是零口文化。但是,由于所获资料有限,问题的解决还不能说“完全”。现在所知的在半坡文化分布区内最晚的前仰韶遗存是零口文化,还不能说它一定就是前半坡文化,同样也不能十分明确地认定它就是前庙底沟文化。
寻找源头,是个很艰难的工作。不能以为是一条大河,源头一定会十分彰明。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就不是一下子确定下来的,历史上经历了多次认错源头的事情。对于仰韶文化的研究也是如此,我们的前人没有找准源头也是很自然的事,后来的学者一步步接近正确,都有前人的辛劳。探求一条河流的源头,是往河流最远的延伸方向横向寻找。探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源头,却是往这个文化早期发展的最近方向纵向寻找。这两种探源各有特点,相比而言,考古学文化的探源可能会更为困难一些。干流上有千万条支流,那条主源其实与许多的支流非常相象,人们会误将某条较大的支流认作源头,特别是在主源还没有进入视线的时候,这是不可避免的。一个考古学文化层的下面,不同地点会有不同时期的文化堆积,我们先见到了A期文化,会很自然地将它认作渊源之所在。后来又见到B期、C期文化,因为年代更为接近,于是又会一次、再次地重新认定这个考古学文化的渊源。当年代最相当的新的D期文化发现时,也许我们会恍然大悟,寻它千百度,真正的渊源原来在这里。不过我们也要谨防历史设下的一个陷阱,如果这D期文化是一个意外的迁徙体,那它又怎么能充当源头呢?如果再设想得复杂一点,我们所研究的这个考古学文化兴许本身就是一个外来体,那么在它扎根生长的地方恐怕也就永远寻找不到渊源了。
寻找仰韶文化渊源的探索,我们似乎已经到了接近破解谜底的最后关头,但是20世纪已经结束,学者们在旧世纪来不及完全解决这个世纪难题。我们寄希望于新世纪之初,曙光应当就在前头。
来源:《考古》2003年第6期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