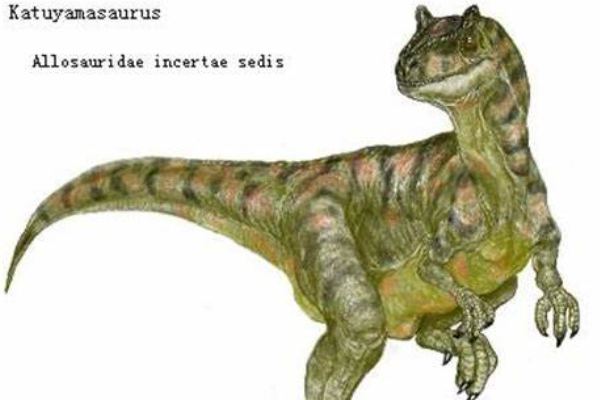靳松安:论龙山时代河洛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及历史动因
龙山时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的过渡阶段,也有学者称之为铜石并用时代,绝对年代约当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2000年[1](P10-16)。龙山文化大体以公元前2500年为界,可分为早晚两期,各期又可细分为前后两段。这一时期,以嵩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和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地域相邻,其间没有高山大川的阻隔,双方的文化交流、传播与影响较为频繁,相互关系甚为密切。对此,虽有不少学者有所触及,但目前尚缺乏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讨论。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分析考古材料入手,结合历史地理研究成果和文献记载,旨在系统探讨此时期双方文化交流的具体内容、途径、方式和历史动因,廓清各自在文化交流格局中所处的地位,以期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有所裨益。
一、龙山时代早期两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龙山时代早期,分布于河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大河村五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其中前两者又可分为早晚两期[2](P51-71);而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则是大汶口晚期文化,亦可细分为早晚两期[3](P69-113)。据研究,它们的年代基本一致,其早晚两期也大体相当。
现有考古资料表明,仰韶时代晚期伴随着仰韶文化的衰落和大汶口文化的崛起,已有少数大汶口人西迁至豫东和豫中地区,周口烟草公司仓库M1~M4、尉氏椅圈马M2、M6以及郑州大河村M9等墓葬遗迹,恐怕“就是西迁的大汶口人先驱们遗留下来的”[4](P45-58)。龙山时代早期,大汶口文化居民开始大举西迁并进入鲁西南、皖西北和豫东等地,驱除和同化了当地的土著文化,从而在这一区域形成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个新的地方类型,有学者将其命名为“尉迟寺类型”[4](P45-58),也有的研究者称之为“段寨类型”[5](P43-46)。从现有材料看,河洛地区目前发现的尉迟寺类型遗存集中分布于豫东周口和商丘地区,向西可达豫中南部地区的沙颍河中游一带。已经发掘或详细调查的遗址主要有夏邑清凉山、鹿邑栾台、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商水章华台、襄城台王、平顶山寺岗、禹州吴湾、瓦店等;出土陶器的种类计有横篮纹罐形鼎、袋足鬶、罐形盉、背壶、长颈壶、宽肩壶、圈足罐、直领罐、翻沿浅盘镂空豆、圈足簋、高柄杯、觚形杯、筒形杯、花边钮器盖等。依据对器物形制的类型学研究,可将河洛地区的尉迟寺类型遗存大致分为三个不同的年代组,即相当于栾丰实先生所分的大汶口文化晚期第9至11段[3](P69-113)。如果从地域上考察,位置偏东的遗存年代较早,而位置靠西的遗存年代都比较晚,这与大汶口人由东向西不断开拓的西进路线相吻合。尉迟寺类型的形成不仅彻底改变了豫东等地原有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而且极大地拓展了海岱文化区的分布范围。这一情况可以说是大汶口文化向河洛地区传播的最直观的反映。
与大汶口人西进浪潮相适应的是,河洛地区的大河村五期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中发现有大量来自于东方的文化因素。这些外来文化因素可以明确地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因素,第二类是被改造但还部分地保留着传统文化风格的因素。龙山时代早期河洛地区所见的上述第一类文化因素,在地域分布上前后两段之间似有所不同。前段,只在嵩山以北、以东地区的大河村五期文化与伊洛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中有发现,而豫西、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和豫北地区的孟庄龙山早期文化中尚未见到,这应与前者地域居东、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毗邻有密切的关系。时代演进至后段,大汶口文化因素不仅在豫中地区有较多发现,而且在豫西、晋南以及豫北等地区也有所发现,这表明大汶口文化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已明显加强。
龙山时代早期前段,河洛地区属于典型大汶口文化的因素主要见于大河村、禹州谷水河、巩义滩小关、里沟、偃师滑城、二里头和洛阳王湾等遗址中的长颈壶、袋足鬶、平底尊、簋形圈足杯、觚形杯、筒形杯、高柄杯、背壶和大口筒形尖底缸(或称为尊)等器型中,形制与曲阜西夏侯、泰安大汶口、邹县野店、蒙城尉迟寺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上述器类均属大汶口文化晚期前段的代表性器物,它们在河洛地区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大汶口文化直接影响的结果。
龙山时代早期后段,河洛地区发现的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主要见于谷水河、汝州大张、登封告成北沟、滑城、洛阳矬李、新安冢子坪、渑池仰韶村、灵宝涧口、垣曲古城东关、丰村和辉县孟庄等遗址出土的长颈壶、平底尊、筒形杯、高柄杯、罐形鼎、圈足罐、大口筒形尖底缸等,其造型与西夏侯、大汶口、野店、尉迟寺和莒县陵阳河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器类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遗存中出土数量甚多,其中横篮纹罐形鼎、圈足罐则是尉迟寺类型的典型器物。很明显,河洛地区发现的此类器物当直接源自大汶口文化。
这一时期,河洛地区所见属于变异的大汶口文化因素主要有矮圈足杯和垂折腹罐两类器物。矮圈足杯见于大河村、新安太涧等遗址,形制为窄折沿、直腹、厚胎、圈足甚矮,器身形态与大汶口等遗址出土的高柄杯比较接近,应与其影响有关。垂折腹罐则见于大河村、孟县许村等遗址,形制为侈口、折沿、腹部垂折、平底,整体造型与西夏侯等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平底尊有些相似,显然前者是后者在河洛地区的一种改进形态。
从目前已发表的考古材料看,伊洛平原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中,不仅包含有大量的大汶口文化因素,而且在有的地点还发现过大汶口人的墓葬,如偃师滑城M1等,表明此时可能已有少量大汶口人迁入了该地区。这些来自东方的大汶口人,逐渐将自身的传统文化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极大地丰富了该地区龙山早期文化的内涵,其中不少文化成分如觚形杯、浅盘豆等又被其后继起的王湾三期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所继承,从而为王湾三期文化的崛起以及夏文化的形成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是,迁入这一地区的大汶口人并未能彻底改变当地原有文化的性质,因此那种将伊洛地区龙山时代早期文化视为大汶口文化地方类型的观点[6](P157-169),恐怕是不太合适的。
在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中也存在着少量来自河洛地区的文化因素,其表现在陶器上主要有带流盆、带流罐、深腹罐和小口瓮等。带流类器物是河洛地区由仰韶时代中期过渡到晚期的标志性器物之一,其在该地区龙山早期文化中又发扬光大。大汶口文化晚期发现的少量带流盆,依其形制可分为A、B两型。A型为敛口弧腹,口外或有凹槽,主要见于西夏侯和尉迟寺遗址;B型为敞口斜腹,见于尉迟寺遗址。这两类带流盆分别与新安西沃、古城东关等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所见同类器相似或相同,应是后者影响的产物。带流罐见于尉迟寺遗址,其形制特征以及腹部施鸡冠耳的作风均与古城东关遗址的同类罐酷似,唯前者腹部饰有方格纹。夹砂深腹绳纹罐在大河村五期文化中数量甚多,是其主要炊器。见于瓦店遗址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中的夹砂深腹篮纹罐,整体形态与大河村遗址出土的同类器较为相似,只是纹饰不同,其出现应与后者的影响有关。小口瓮在豫中地区出现较早,数量也比较多,发展脉络较为清晰。瓦店遗址出土的小口瓮,形制与谷水河遗址大河村五期文化遗存所见同类器基本一致,应是两种文化相互交流的结果。从地域分布上考察,大汶口文化晚期所见的外来文化因素大多都发现于分布地域靠西的尉迟寺类型之中,鲁中南地区的西夏侯类型仅有零星发现,而其他地区却很难见到。这说明河洛地区龙山早期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较为微弱。
由以上分析可知,龙山时代早期两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趋向,明显是以海岱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占主流,并且从早至晚呈现出逐步加强的态势,同时期河洛地区所见典型大汶口文化因素在地域分布上前后两段的变化,即是其最好的证明。这一时期,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西进浪潮及其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不仅为大河村五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等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了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且对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的崛起乃至夏王朝的诞生,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贡献。相反,河洛地区龙山时代早期诸文化对大汶口文化的影响却比较微弱,在双方文化交流格局中显然处于从属地位。
二、龙山时代晚期两地区文化的交流与影响
龙山时代晚期,分布于河洛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有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三里桥文化,存在于海岱地区的则是龙山文化,它们均可分为年代大体对应的早晚两期[7](P229-282)。
龙山时代晚期前段,河洛地区龙山晚期诸文化早期遗存中所见的龙山文化因素并不是很多,目前能够确认的只见于平粮台、杞县鹿台岗、孟庄、安阳后岗、汤阴白营、郑州站马屯、汝州李楼和古城东关等遗址出土的平折沿弧腹或卷沿折盘豆、铲形足或鸟首形足(俗称鬼脸式足)鼎、单把筒形杯和双横耳圈足盆等少数几种器物,形态特征分别与兖州西吴寺、泗水尹家城、章丘宁家埠、茌平尚庄和诸城呈子等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早期同类器酷似。这些器类均系较典型的海岱地区文化因素,其在河洛地区的出现无疑应是海岱地区同期文化影响的结果。
龙山时代晚期后段,河洛地区所见来自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大量增加,其中以后岗二期文化最多,其次是造律台文化,而王湾三期文化和三里桥文化数量较少,这应该与前两者分布地域与龙山文化毗邻、受东方影响较强烈有关。这些外来的文化因素大体又可以分为两类,即典型的东方文化因素和加以改造并注入本土文化传统风格的因素。
关于后岗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的典型东方文化因素,已有学者作过分析[8](P435-442)。蕴含这类因素的考古遗物数量甚多,主要见于孟庄、后岗、白营、安阳八里庄、大寒南岗、永年台口、长治小神等遗址中的斜流袋足鬶、鸟首形足鼎、子母口瓮、宽横耳直口瓮、双横耳有领瓮、子母口罐、折盘豆、横耳圈足盆、子母口盆、子母口盒、筒形杯、子母口器盖、喇叭形纽器盖和筒形器盖等,形制与西吴寺、尹家城、尚庄、茌平南陈庄、禹城邢寨汪、阳谷景阳冈、邹平丁公和胶县三里河等遗址所出龙山文化晚期的同类器基本相同。毫无疑问,上述器类均应是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直接传播而来的。此外,见于后岗、磁县下潘汪等遗址中的圆形箅子,可能也是受龙山文化影响的产物。
造律台文化晚期遗存中也存在着相当数量典型的龙山文化因素,比较明确的主要有尉迟寺、清凉山、鹿台岗、平粮台、永城王油坊等遗址中的斜流袋足鬶、子母口罐、子母口瓮、子母口盒、三瓦足盆、“V”字形足鼎、单把筒形杯和覆盘形器盖等,其造型与尚庄、尹家城、济宁城子崖等遗址出土的同类器近同。显然,这些器物也应是受龙山文化影响而产生的。
据已发表的考古材料看,王湾三期文化晚期所见典型的东方文化因素数量较少,而三里桥文化晚期只有零星的发现。其原因之一可能与二者的分布地域和龙山文化相距较远有一定关系。王湾三期文化中来自东方的文化因素,目前能确指的大体有大河村、站马屯、王湾、郑州阎庄、汝州煤山、新密新砦、济源苗店、淅川下王岗等遗址中出土的斜流袋足鬶、单把筒形杯、子母口罐、子母口盒、“V”字形足鼎、三足盆和圈足盆等几种器物,其形态特征与西吴寺、尹家城、城子崖、尚庄等遗址所见龙山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相似。陕县三里桥遗址也发现少量圈足盆,亦是三里桥文化晚期仅见的来自于东方的文化因素。从地域上考察,这两支文化中所见的东方文化因素有可能是通过豫东等地的造律台文化传播而来的。
此外,河洛地区龙山时代晚期诸文化中的少量黑陶,似乎也应是龙山文化影响的结果。而其晚期阶段黑陶以及黑皮陶数量的明显增加,则表明东方对河洛地区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又有所加强。上述河洛地区来自于海岱地区的典型文化因素,除斜流袋足鬶以白陶稍多之外,其他器类大多都是黑陶。
河洛地区龙山晚期文化中,不仅存在着大量典型的东方文化因素,而且还发现一些将其加以改造后又注入了本土文化传统风格的因素。这类因素主要有子母口尊(或称为缸)、子母口钵、子母口矮领瓮、子母口圆腹瓮、平流袋足鬶等。子母口尊在造律台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是其比较有特色的器类之一,始见于早期偏晚阶段,形制为矮子母口、鼓腹、假圈足,腹部多饰弦纹,它或许是造律台文化居民吸收了龙山文化子母口器作风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器型。此类器物在海岱地区极为少见,目前仅在尹家城遗址的龙山文化第四期遗存中发现1件(M3:20),整体造型与王油坊遗址造律台文化晚期偏早遗存中的同类器较为接近,唯前者腹部还附加有双横耳,它可能是受后者的影响。子母口钵和子母口矮领瓮均见于煤山遗址,这两类器物除口部具有东方文化风格外,器身及纹饰都系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特征,它们显然是两种文化风格的糅合。子母口圆腹瓮见于新砦遗址,形制为矮子母口、圆腹微鼓、小平底、下附4个瓦形足,中腹偏上有对称的4个桥形横耳,外表饰成组的凹弦纹,底部饰篮纹。从造型上观察,此件器物的口部特征及横耳作风系典型的东方文化因素,足部又具有后岗二期文化的风格,而器身、纹饰和小平底作风则为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特征,据此可推测此件器物应是三种文化因素融合的产物。王湾三期文化和三里桥文化比较多见平流平底鬶,有的底部还附加3个小乳足,此种形制的鬶在后岗二期文化和造律台文化中也可见到。而斜流袋足鬶则是龙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类。见于鹿台岗、孟庄、煤山、李楼、三里桥等遗址中的平流袋足鬶,或许是河洛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居民将本地区原有的平流作风,移植到来自东方的斜流袋足鬶上而产生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新器型。
龙山时代晚期前段,海岱地区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同样存在一些来自于河洛地区的文化因素,主要发现于鲁西北地区的城子崖类型和鲁中南地区的尹家城类型。在陶器上比较明确的有出于尚庄、西吴寺、泗水天齐庙等遗址中的方格纹卷沿深腹罐、绳纹或篮纹甗、折腹盆、四瓦足盆等几类器物,亦属较为典型的中原龙山文化因素,其形制与孟庄、后岗、鹿台岗、王湾、登封王城岗等遗址中所见后岗二期、造律台和王湾三期文化早期的同类器相同或相似,前者应源自于后者,或是在其影响下产生的。此外,龙山文化西部早期遗存中所见一定数量的灰陶和绳纹、方格纹等,也应是受河洛地区同期文化影响的产物。
龙山时代晚期后段,海岱地区也明显存在着一些来自于河洛地区的文化因素,其仍然集中发现于鲁西北地区的城子崖类型和鲁中南地区的尹家城类型中。这些外来文化因素主要表现在“白灰面”房屋建筑和陶器两个方面。
“白灰面”房屋是河洛地区龙山时代晚期文化中普遍存在的一种建筑形式,尤以后岗二期文化最为常见。例如,后岗遗址1979年发现的39座房址中,有31座为“白灰面”建筑;白营遗址早、中期的17座房址中,有4座为“白灰面”建筑;晚期的46座房址中,“白灰面”房址就有29座。“白灰面”房屋建筑在后岗二期文化中所占比例高达50%~80%。海岱地区龙山文化中所见的“白灰面”房址较少,而且大多发现于尚庄、南陈庄、丁公、尹家城等遗址中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考虑到此类房址在后岗二期文化中出现的时间较早、数量又多,龙山文化城子崖类型以及尹家城类型很有可能是在受到前者的影响之后,才开始建造和使用“白灰面”房屋的[8](P435-442)。
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中,明确来自于河洛地区的陶器器型主要见于尚庄、南陈庄、西吴寺、尹家城等遗址中的绳纹或方格纹折沿或卷沿深腹罐、罐形斝、篮纹小口高领瓮和钵形圈足盘等,形态特征与王油坊、清凉山、孟庄、后岗、淇县王庄、瓦店等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基本一致。这些器类系造律台文化、后岗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其在海岱地区的出现,无疑应是从河洛地区直接传播而来的。此外,龙山文化晚期陶器中,灰陶及绳纹和方格纹所占比例均有显著增加,尤其在西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也应是受河洛地区同时期文化影响的结果。上述龙山文化中发现的来自河洛地区的陶器器型多属于灰陶。
河洛与海岱地区龙山晚期文化中,除了各自存在一些属于对方文化因素的成分之外,还有一部分为双方共同拥有的文化因素。至于这一类共同因素在房屋建筑以及生产工具方面的表现及其形成原因,已有学者进行过概括性分析[8](P435-442),此不赘述。这里仅对两地区共有的陶器器类作一必要说明。
目前可以确认属于双方共有的陶器器型,主要有平底盆、单耳罐(或称杯)、盆形圈足盘、斜腹碗(或称覆碗形器盖)、覆盆形器盖等。平底盆在两地区龙山晚期文化中均较常见,共同特征为敞口、大平底。两地区平底盆的演化规律也大体相同,早期多为浅腹、斜壁,晚期腹变深,腹壁经内曲向直壁方向发展。单耳罐也是双方较为多见的器物,其共同特征为侈口、粗颈微束、鼓腹、平底,口和上腹之间有桥形单耳,多为素面或磨光,少数饰弦纹。盆形圈足盘习见于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以及龙山文化的城子崖和尹家城两类型之中,形制为直口、宽沿、曲腹、粗圈足,圈足部分饰镂孔或凸棱。其中造律台文化和尹家城类型此类盘的圈足底部,有的呈台座式,这在其他地区则不见。斜腹碗在两地区龙山晚期文化中出土数量甚多,形制为敞口、斜壁、平底较小,有的底缘稍外突,倒置做器盖时可当作捉手之用。龙山文化的此类器物多数被称为覆碗形器盖。覆盆形器盖主要见于后岗二期文化和龙山文化城子崖与尹家城两类型,另在造律台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龙山文化姚官庄类型的个别遗址中也有少量发现,其共同特征为大敞口、斜壁、平顶较大,腹壁近顶部有对称的宽横耳一对。这类器盖在两地区的出现及其流行时间基本一致,演化趋势也大体相同,即整体由矮向高发展。此类共同因素很可能是由双方所处时代相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近而各自创造的器类。
综上所述,龙山时代晚期两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趋向,大体可分前后两段。前段,双方的文化联系比龙山时代早期有所减少,从龙山文化早期遗存中存在数量较多的典型河洛地区文化因素,而河洛地区具有东方色彩的器物发现较少,以及造律台文化在豫东、鲁西南、皖西北地区的出现等方面考察,此时期双方文化交流的趋向,似乎是河洛地区对海岱地区的影响稍占上风。后段,两地区文化交流的趋向发生了逆转,河洛地区对海岱地区的影响迅速衰落,而后者对前者的文化传播与影响却急剧增强,在双方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中,海岱地区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时期河洛地区存在大量来自于海岱地区的文化因素即是最好的证明。
三、龙山时代两地区文化交流的历史动因
龙山时代河洛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互动,是源于当时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以及人类自身生存能力的提高诸因素。龙山时代中晚期,河洛与海岱地区诸文化的农业和制陶业水平都有所提高,所取得的成就也较为突出。例如,农业生产工具比较先进,形制复杂多样,种类有铲、镢、刀、镰等;农作物种类较为丰富,有粟、黍和水稻等[9](P78-83),据研究,海岱地区可能还有麦类作物[10](P247-266);鬹、蛋壳杯、筒形杯、觚形杯等酒具的大量出土,表明酿酒饮酒之风盛极一时,它应是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反映。制陶业系两地区十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此时期已普遍采用了快轮制陶技术,烧制火候比较高,有的可达1000℃以上;陶器种类繁多,陶胎较薄,质地坚硬,造型规整、匀称,龙山文化蛋壳黑陶的烧造代表了该时期陶器制作的最高水平。社会生产的发展还表现在畜牧业的发达、冶铜业之兴起以及玉石器制作技术的进步等方面。从海岱地区出土玉器的地点较为集中且多出自于晚期规格较高的大中型墓中的情况推测,这一时期的玉器制作似是专为显贵们服务的,有些成品可能已具有礼器的性质。
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势必导致社会关系的重大变革,从而使社会组织更加复杂化。此时期城址的普遍出现即是其标志之一。据统计,目前两地区发现的龙山晚期城址明确的已近20座,这些城址的面积大小不一,社会功能各异,不少城址中还发现了可能具有宫殿性质的大型夯土基址。城址的出现昭示着城乡的分野与对立,“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11](P27-34)。社会组织结构的复杂化亦反映在墓葬规格等级分化的日益明显、贫富差距悬殊、阶级对立可能已经产生以及文字的发明等方面,这在海岱地区表现得尤为清楚[12](P1-6)。学术界一般认为,城址、冶铜业、文字和礼仪性建筑并存是我国古代文明诞生最主要的物化表现。若是,河洛与海岱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可能已跨入了初级文明社会阶段,即所谓的“酋邦”社会[13](P46-52)。
社会组织结构复杂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与生产力的进步和人类自身生存能力的提高密切相关。这一时期生产工具门类比较齐全,不仅有前述的农业生产工具,而且也有手工工具、渔猎工具等,其制作均比较精细,形制规整,刃部大多较为锋利。此时期的人们可能已开始制造水上交通工具——独木舟,使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大大提高,从而为两地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物质基础。这些考古学证据可以为龙山晚期河洛与海岱地区的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以及豫北、冀南和鲁西北这两条途径来实现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从现有材料来看,龙山时代两地区的文化交流和影响,与当时的人口迁移关系密切。现代考古发现证明,早在仰韶晚期已有少数大汶口人西迁至河洛地区,周口烟草公司仓库M1~M4、椅圈马M2、M6和大河村M9即是西迁大汶口人先驱们的遗存。自此之后,大汶口人的西迁举动逐渐形成为一股潮流,到龙山早期后段达到高潮。大汶口人西迁进占皖西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后,驱除和同化了当地的土著文化,从而在这一区域内形成了大汶口文化晚期一个新的地方类型——尉迟寺类型。目前河洛地区发现的尉迟寺类型遗址集中分布于豫东周口和商丘地区,向西可达豫中南部地区的沙颍河中游一带。从地域上考察,位置偏东的遗存年代较早,而位置靠西的遗存年代都比较晚,这与大汶口人由东向西不断开拓的西进路线是吻合的。尉迟寺类型的形成,彻底改变了豫东等地原有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进一步拓展了海岱文化区的范围。这可以说是大汶口文化向河洛地区挺进的最直观的反映。而此种方式的文化传播,恐怕只有通过战争才能实现。
尉迟寺类型形成以后,为大汶口文化进一步向豫中、豫西等地的大河村五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施加影响建立了比较稳固的前方基地。豫中和豫西等地龙山早期文化中含有大汶口文化因素的遗址发现较多,这些遗址大多集中在颍河上游及伊洛河下游地区,大体呈东南-西北走向的带状分布。嵩山以东以南地区和伊洛平原一带的部分遗存年代较早,属龙山早期前段;而豫西、晋南和豫北地区的遗存年代较晚,均属龙山早期后段。其由东向西传播的趋势十分明显。
但是进入豫中、豫西等地的大汶口文化,并没有改变当地原有考古学文化的性质,而是与其逐渐融合为一体,丰富了原有文化的内涵,对当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表明其与这些地区龙山早期文化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应当是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的。因而,这些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性质与豫东以及皖西北、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有着质的不同。
在古史传说中,太昊是东夷人的先祖之一[14](P48-56)。《左传》昭公十七年云:“陈,太昊之虚也。”陈的地望在今河南淮阳,广义上可以认为在豫东一带。太昊的后人多居鲁西南地区。《左传》僖公二十一年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太皞即太昊。任在今山东济宁,宿在东平县,须句在东平县东,颛臾在费县西北。假定这些文献记载不误,分布于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就应属太昊部族的遗存[15](P1-12)。有关“太昊”的传说在这一地区的广为流传,也可以作为其旁证之一。
至于太昊部族的始居地及其外迁原因,有学者曾作过分析研究,认为其最初是活动在苏北地区,后来迫于良渚文化北进的强大压力,自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斩次从苏北地区西迁至皖西北、鲁西南和豫东地区,同时也有少部分迁往鲁东南地区[16](P3-18)。从花厅墓地所透露出的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战争信息[17](P18-20),以及苏北地区罕见大汶口文化晚期遗存和豫东等地大汶口文化与鲁东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之间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等情况来看,这一观点是比较可信的。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尉迟寺类型的出现及太昊部族在豫东等地的兴起,应是龙山时代早期两地区文化交流格局形成的历史背景。
龙山时代晚期前段,两地区文化交流的趋向是以河洛地区对海岱地区的文化传播和影响占据上风,其比较突出的表现就是造律台文化在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的出现与发展。从文化的基本特征分析,造律台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后岗二期文化等一样同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而与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差别很大。造律台文化的兴起,使豫东等地的文化序列发生了彻底变化,即由海岱文化系统突变为中原文化系统。这种文化序列的突变,当与此时期华夏和东夷两大集团之间的战争有密切关系。
《逸周书·尝麦解》云:“昔天之初,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黄帝与蚩尤之战,据《史记·五帝本纪》的说法,于黄帝一方还有炎帝。《盐铁论·结和篇》云:“黄帝战涿鹿,杀两曎、蚩尤而为帝。”两曎当即两昊[14](P53)。这说明涿鹿之战蚩尤一方还有太昊和少昊。太昊部族的遗存主要是指分布于豫东等地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则太昊、少昊、蚩尤所处年代大体应在龙山时代早期[15](P1-12)。至于黄帝的年代,已有学者指出大体也应在这一时期[18](P161-169)。由此可以推测,涿鹿之战极有可能是发生在龙山时代早晚两期之交。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以蚩尤被擒杀、东夷集团势力受挫、华夏集团取得胜利而告终,其在考古学遗存上的反映,就是属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造律台文化向东挺进至豫东、鲁西南和皖西北地区,并替代了这里的大汶口晚期文化——尉迟寺类型,从而扩大了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分布地域,也使其在双方文化交流中占据了比较有利的地位。这可能即是龙山时代晚期前段两地区文化交流趋向与早期相比发生较大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
尽管涿鹿之战使东夷集团势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挫伤,但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其发展的基础。因此,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之后,东方的龙山文化在两地区文化交流活动中重新赢得了主动,并使双方文化交流的趋向又回复到以海岱影响河洛为主的局面。这一文化交流格局大概一直延续至夏代末年。
参考文献:
[1]严文明.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J].中原文物,1996,(1).[2]靳松安.河洛与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融合[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3]栾丰实.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A].海岱地区考古研究[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4]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J].考古,1996,(4).[5]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J].中原文物,1991,(2).[6]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J].考古,1992,(2).[7]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A].海岱地区考古研究[C].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8]栾丰实.论城子崖类型与后岗类型的关系[J].考古,1994,(5).[9]孔昭宸等.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八千年前水稻遗存的发现及其在环境考古学上的意义[J].考古,1996,(12).[10]栾丰实.山东龙山文化社会经济初探[A].山东龙山文化研究文集[C].济南:齐鲁书社,1992.[11]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J].文物,1999,(10).[12]靳松安,赵新平.试论山东龙山文化的历史地位及其衰落原因[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13]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J].文物,1998,(7).[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5]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J].文物,1989,(9).[16]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J].中国史研究,2000,(2).[17]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J].文物天地,1990,(6).[18]曹桂岑.龙山文化与中国古代文明[A].河南文物考古论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
- 0001
- 0000
- 0000
- 0003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