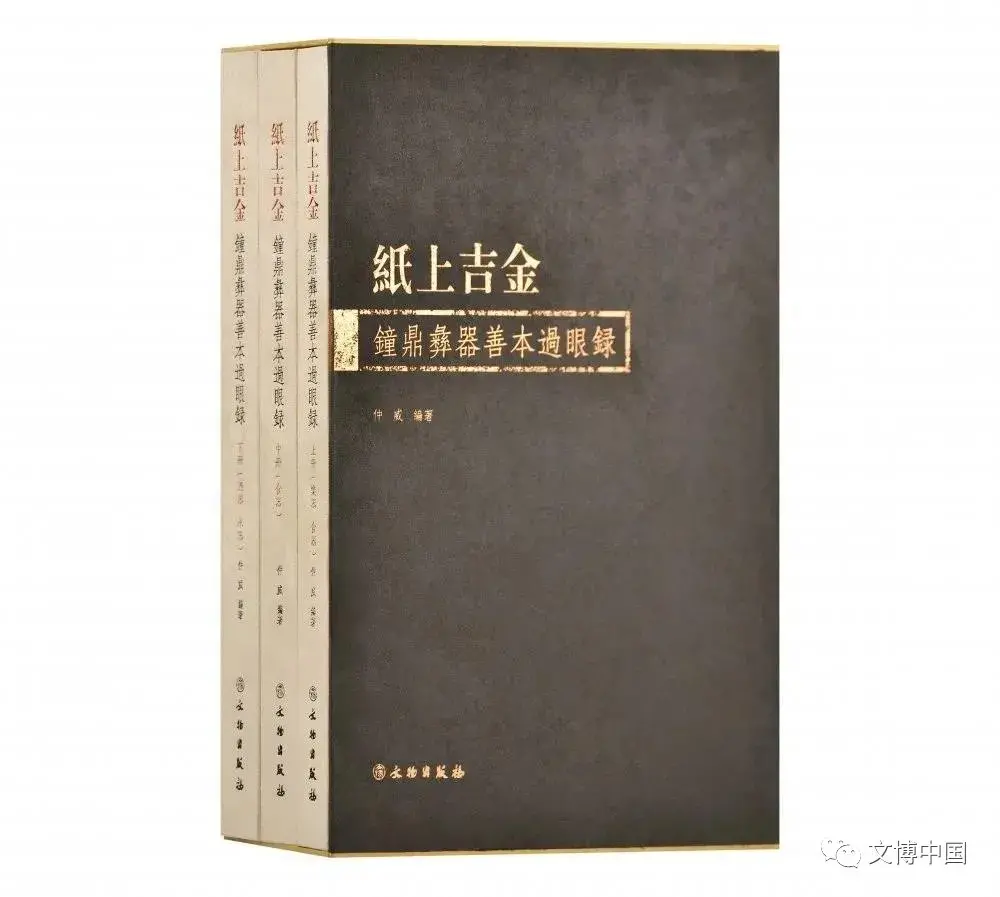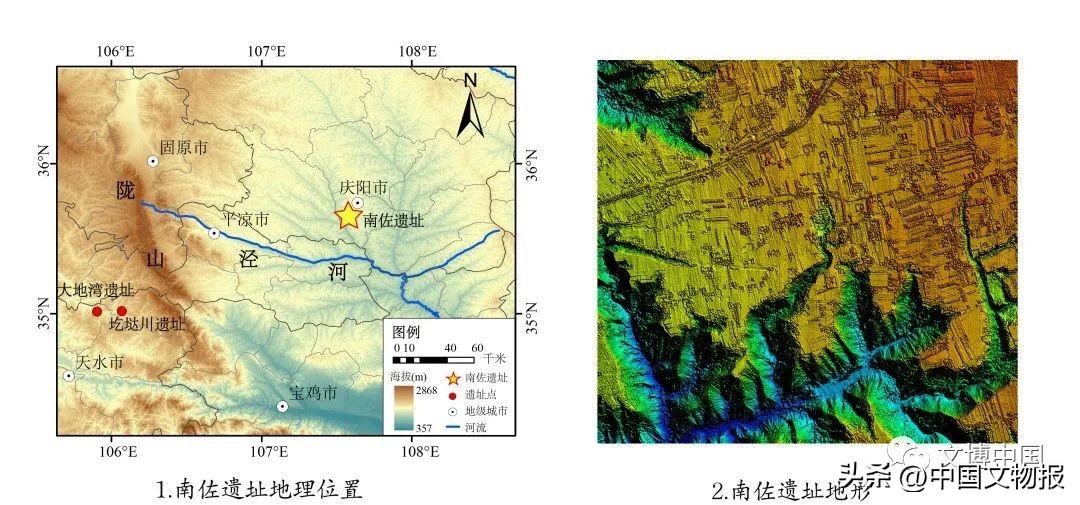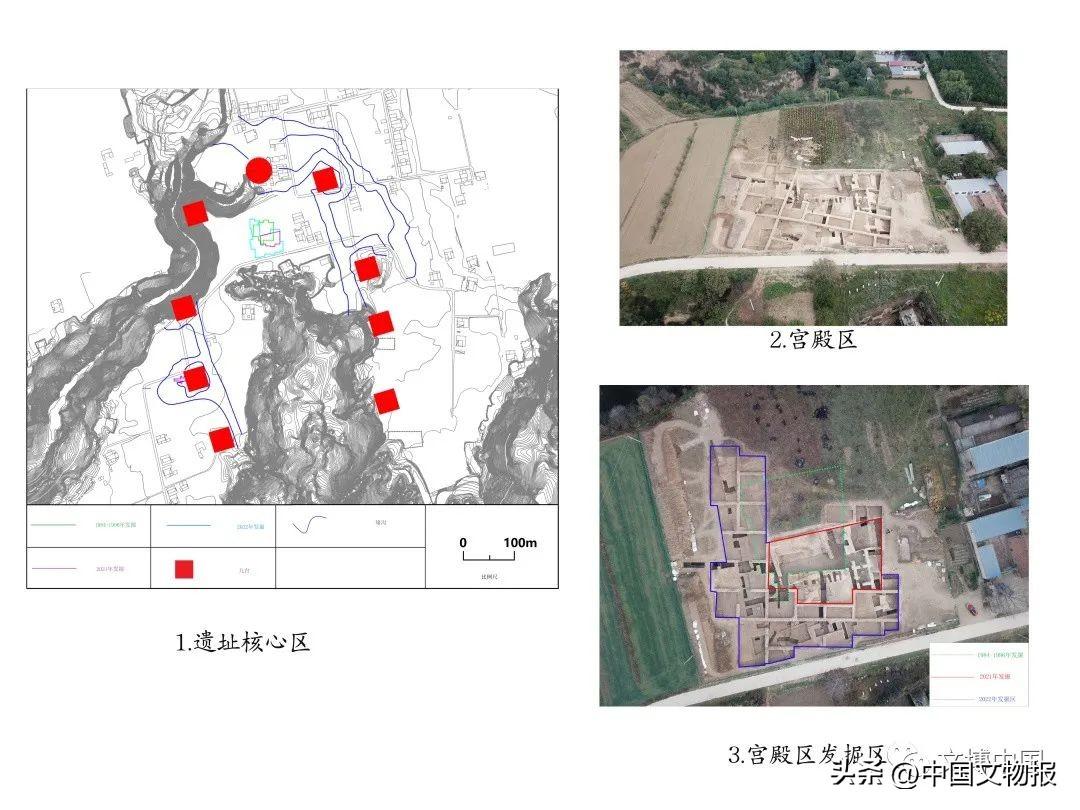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认定和相关理论问题
一
对于早期国家起源的研究,在大部分个案中,历史学的方法还是基本的方法之一。从证据的角度说,这意味着对于有关文献资料的研究和援用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已充分认识到考古学证据对研究较大区域内人类早期政治组织进程的特殊的补充的作用。这一点在对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的研究中尤其突出。但在这个方向上的研 究,方法上的考虑尤为重要,包括恰当地对待考古学证据的意义的问题。目前中国早期 国家问题研究的焦点之一是在具有十分相似特征的早期复杂社会个体或政治实体中区分 出可以被认为已经具有国家特性的个体。由于国家的特征作为一种复杂政治关系的表现 ,本质上只有在其历史性的运动中才能被观察到,因此能够根据总体上对古人在历史上 的活动有较多记载的文献资料做出判断,是在关于国家形成问题的个案研究中,在证据 方面所能期待的最理想的条件之一,也是在这项研究中运用历史学方法的基础。目前, 在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中,我国许多学者所接受的关于中国在夏代国家形成时 开始进入国家进程的结论,就是在这种比较理想的证据条件下得出的。这方面的研究如 果经过:(1)对有关文献成书情况的认定;(2)依据考古资料对有关文献记载的内容所作 出的证实,那么,应当说可以期望最终得到某种确定的结果。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工 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张光直先生在《剑桥中国上古史》(Cambridge History of Ancient China)中对于夏代历史问题所作的阐述就表明了这一点(尽管该书其他一些作 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尚有不同)。
近年来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研究的一个引人注目的情况是:随着众多反映古代复杂社会 个体存在的新石器时期考古遗存和遗址的发现,在夏代国家进程之外的一些由这些新出 土的地下资料所揭示的古代社会个体在政治组织方面的状况与特征被认为与各该地区的 国家化进程有关,甚至有不少研究已经提出了其中某些社会个体业已具有国家特性的结 论。这几乎是当前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的一个很大的兴奋点。而对于这些被认定的 国家化进程,在文献中并没有足够的记载,甚至有些在文献中没有丝毫反映。很显然, 在对这些缺乏或几乎没有有关文献资料可供判断的个案的研究中,考古学证据的含义的 认定问题便成为决定性的。而在这方面,无论在考古学或是历史学中,以往的讨论都还 很不够,并没有就在这个课题上为考古学证据的合法运用问题确立比较完整而合理的方 法上的原则达成明确的共识。因此我国学者近年来在这方面所开展的大规模的探索与研 究是极富挑战性的。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随着研究的深入和越来越多属于早期复杂 政治实体的考古遗存的发现,对这方面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的探讨将越来越重要和关键。
二
在涉及国家制度形成的问题上,考古学证据单独发挥作用的能力,就目前来说,仍然 取决于:(1)为考古学证据的解释提供基础的早期国家理论的进一步成熟与完善;(2)对 大量被认为处于国家制度形成前后的遗址和其他考古遗存的内涵与特征的整理和在比较 基础上的深入的分析。尤其是后者,对于考古学来说仍然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这里 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考古学证据作为物质性的遗存,虽然对于一个早期复杂社会个体在 社会规模、社会权力结构特征、社会控制力水平、社会分化程度、工艺和生产力水平以 及文化统一性程度等方面的表现,确实可以有直接的和比较确定的说明意义。但是,一 个古代社会个体在所有上述方面的表现,在其形成国家制度前后实际上是一个渐进发展 的过程;因此在直接发生导致国家制度形成的事件的时段内,在一个社会个体的上述表 现方面,我们并不一定能够观察到足够明显的和意义确定的变化。所以即使对于上述这 些方面的表现在考古上可以根据一定的方法确认其物质证据,却不一定能够或很难依据 已经由物质证据确认的这些方面的表现,就与这些考古遗存有关的社会个体是否已经形 成国家制度问题做出连带的判断。在由考古学证据单独对有关个案作出判断的情况下, 尤其如此。
从现代早期国家研究所依据的事实来看,在大部分情况下,社会个体在国家形成前后 在上述表现方面没有根本的不同。现代早期国家研究的主要学者、美国人塞尔维斯就早 期国家与酋邦的不同所提出的两项要点是:(1)早期国家的政治统治更正规化、形式化 、专业化,并更多地以对武力的垄断为基础;(2)社会分层现象已发展成明确的阶级区 分(注:E.R.Service,Profiles in Ethnology,P.498.)。而对这两项特征在物质遗存方 面如何被反映,现在我们还形不成系统的、准确的认识。我曾就酋邦向国家转化时可能 采取的“政治技术”归纳了八项内容,其中包括为确立国家制度的合法性所采取的一系 列政治创造(如确立一个作为国家的首脑和代表的最高统治者的正式身份和创立维护国 家统治的合法性的意识形态等等)(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233—234页。)。但是所有这些方面的表现如何在物质遗存中被反映,也 还是非常复杂、目前在考古学中尚未真正解决的问题。
完全依据考古学资料确认一个早期国家进程的存在,需要非常好的条件。因为从理论 上说,我们目前还不清楚,在上面提到的与社会政治制度演进有关各个方面,国家制度 的形成会对其程度与量的表现带来什么系统的、规律性的变化(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区 域或文化传统的范围内)。如果我们期望单独依靠考古学证据来作出判断,那么,从原 理上说,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应该是有关考古遗存要能够确切地反映出有关社会的政治制 度是正规的或正式的,即达到一定的形式化水平。这个问题过去在考古学中也许还没有 着重注意过,但它是按照问题的本意逻辑地提出的。应该说,考古遗存某些内涵的规模 和品质对于政治关系的正式性或正规性等等,可以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同时,某些特定 的能够说明正规政治统治制度存在的遗存类型,例如反映官署活动的文字证据(如反映 此类情况的大量金文)以及官印、符信之类,在确定其含义之后,也是非常有力的证据 。但是,就目前来说,在中国个案中,具有这种条件的对象往往是在相对国家形成阶段 来说较晚时期的(例如商代和周代)。在早期资料的解释方面,如果我们要作重要的判断 ,目前也只有在对各自都具有非常典型和确定含义的特征的个案(例如当我们把仰韶时 期的遗址同夏代遗址)作比较时才是比较有把握的。这些个案实际上是明显处于不同考 古学时期的。而我们现在根据问题的要求所要比较的对象则是处在同一考古学时期,在 这样的精度上要对不同个体之间的异同作出有重大意义的判断,就目前的条件来说还缺 乏全面的和确定的方法的基础。
三
在上述问题上,过去在许多历史学和考古学著作中被用来作为国家形成“标志”的一 些考古学遗存类型,例如城墙、文字系统、大型公共建筑、大型和有复杂内涵的聚落( 可以被解释成早期城镇)等等,虽然在许多早期国家个案中可以观察到,但这些遗存类 型本身并非无条件标志国家制度存在的材料,同时这类遗存也并不能单独用来区分前国 家社会与国家社会。关于这个问题,我曾引用过国际早期国家研究学者的一些意见。如 主编《早期国家》一书的克列逊和斯卡尔尼克就说过:“许多早期国家形成时根本没有 城镇和城市。”(注:H.S.M.Claessen & P.Skalnik,The Early State,P.644.)世界史 学者斯塔福利阿诺斯也说到过有些文明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注:斯塔福利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这些 说法都表明“标志”说的局限性,是值得重视的。美国学者哈斯更明确提出:“应避免 把孤立现象诸如纪念性建筑、文字和城市与国家这样的复杂的政治组织相提并论。”( 注:哈斯:《史前国家的演进》,求实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页。)这应该说是完全 正确的意见。
但是近年来的研究中仍不时可以看到有些学者非常喜欢使用“标志”说方法,甚至把 它提升为一般方法的某种原理。如杜正胜不久前还说:“沉默的城墙经考古家发掘后, 终于如实地提醒我们,可以从它身上读出恩格斯界定‘国家’的一项要素——公共权力 ,……这也是我们讨论国家起源是特别重视出土古城的原因。”(注:杜正胜:《考古 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考古》1992年第4期。)实际上孤立地依据某个古代城墙遗址 ,并不能确定地读出有关社会和政治制度的重要信息。中国早期城墙的发展有很多独特 的地方,其含义还需要全面和深入研究。如河南辉县孟庄的龙山文化遗址有较大尺度的 古城址,其年代在夏朝历史之前(有人以与传说中“共工氏”有关(注:袁广阔:《孟庄 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是与中原早期王朝发生有最接近关 系的古代城址之一。但目前考古学界的意见并没有能够肯定此项遗存与国家制度的直线 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中国早期,城墙出现在国家制度形成以前这种情况是可能存在 的,这一点应该引起学者们从新的角度去思考,至少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诚如前 引作者所着力强调的,古代城址对于社会的分化程度和社会组织的动员能力以及工艺水 平等等是有其明确的说明力,但这同说明国家制度的存在仍然不是一回事。对于龙山文 化时期前后众多古代城址的性质和意义的分辨和确认,仍然是当前中国早期考古学正要 着力解决的一个前沿性的课题。
关于各种此类“标志”的假说,从方法上说,正是由于对考古学证据在说明早期政治 关系问题上的上述复杂性和局限性估计不足而提出的。现在看来,对这些证据的含义只 有在考虑每一个个案的具体条件的情况下才能确切地认定。简单地或绝对地把它们当作 “标志”来使用,无论在理论上或具体研究中,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当然从另一方面 说,考古学在积累了足够数量的个例以后,可以而且也应该就不同物质遗存对于政治制 度所能说明的问题得出某些有用而有某种系统性的结论,但这些结论就其内容而言,显 然不会只是提出一些简明的所谓“标志性”遗存类型而已,而很可能是很复杂的,而且 看来也不会是无条件的,而更可能是分别与特定的、一定范围的地区和时期有关的。
四
中国早期国家研究在证据方面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它拥有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资料的 品质不一是不争的事实,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相当高的品质也是不争的事实。另一 方面,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文献对研究的作用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们为我们了解 早期历史的诸多细节从正面提供了大量极其宝贵的资讯,有赖它们,我们才得以对阐述 早期国家活动有起码的自信。而另一方面,所有这些文献资料总合在一起,实际上也从 对面为我们讲述古代国家的历史和特征给出了一些不支持非法通过的“底线”,当我们 的研究可能超出这些“底线”时,在方法上应该有更严厉的要求。这里有一个值得引起 思考的问题是,对于中国古代文献总体所体现的一些内容上的基本的“内核”的把握, 是把文献作为证据对待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对此我们应当有意识,并予以重视。其中的 道理就是:资料总体给出的讯息不等于个别和片断资料给出的讯息的简单相加;资料总 体会给出它独有的一些重要讯息。这虽然是在对待中国古代文献方面比较难以把握的一 种态度和方法,但我认为在证据学的角度上我们还是应当思考这个问题。
现在应该可以认为,古代数量众多、品质不一的文献资料至少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各自 的独立来源的。过去所说的对文献系统造伪的过程现在知道并不存在。如果这些有着各 自独立来源的资料对某些基本的古代事实有相同或相近的记述,那么对于这些事实作为 证据的品质和在古代文献传统中的地位就应当特别认真地对待。换言之,如果我们确实 准确地整理出所有古代文献或者说文献总体所反映的一些基本的事实的话,那么这些基 本事实应该可以看作古代文献总体所包含的“内核”的内容,而它们也成为我们讲述古 代历史的一个“底线”。除非有特别有力的理由和给出完整的论证,否则在这个“底线 ”之外来讲古代历史就是所谓“非法通过”。
在古代国家的问题上,传统文献总体就有着一系列这样的“内核”的内容,其中有一 些就是同古代中国在进入国家进程时期广大地域内政治组织演进的布局有关的。对有关 的资料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读法,但总体上古代文献不支持在夏代国家进程以外在中原 和周边地区还有其他独立的国家进程的说法,这还是可以确认的。现在要追问的是,古 代文献的这一“内核”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这些文献本身是以夏代国家为开端的华夏文化 和华夏国家政治传统的产物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逻辑上应该是成立的,因为华夏文献完 全可能漠视周围异族国家制度和国家进程的存在,但是说清这个问题需要证据。关于这 个问题的讨论同确切了解古代所谓“华夷之辨”的观念的含义有关。虽然我们现在粗略 地可以把古代所谓“华”、“夷”之分理解为某种民族自我意识的反映。但在古代文献 中这种观念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同对于文化和社会发展程度的认定有关。也就是说,古 代文献所说的“戎夷蛮狄”包含了认为这些社会个体在社会、文化以及政治制度(这在 古人看来也是一种文化)的发展上程度较低的意思。顾颉刚早年关于这个问题就提出过 这样的解说:“……然则申、吕、齐、许者,戎之进于中国者也;姜戎者,停滞于戎之 原始状态者也。……由其入居中国之先后,遂有华戎之判别。”(注:顾颉刚:《九州 之戎与戎禹》,《古史辨》,第七册下编。)陈梦家则有更明确的表述:“有与此等羌 同族的夏,……在夏商时代已进入较高级的形式,……凡此‘诸夏’属于高级形式之羌 人,以别于尚过游牧生活的低级形式的羌人。”(注: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正 因为如此,文献关于三代王室先祖也多有以“戎”、“夷”、“狄”相称者。过去对这 类资料比较多从探讨族系的角度去关注,而现在我们也可以从中感觉到三代作者之所以 对先祖有这样的称谓法,是因为他们还知道其远祖的发展程度并不高,包括还没有形成 三代的制度,即国家制度。因此可以看出,古代文献在总体上对于人群的社会与文化发 展程度之高低是敏感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还可以看到文献对较后时期里异族人群国家 化进程正面记述的例子,比如对徐戎的大量记载。所以应该说,现在恐怕还没有足够的 理由假设,对于在夏代国家形成和活动时期,与夏朝有接触并且已经自动地进入国家化 进程的人群或社会个体,已知文献总体有一个系统隐匿的问题。这是古代文献内容的一 个很重要的“内核”,对于有关考古学解释也是一个不便“非法通过(即不经过全面论 证而通过)”的“底线”。
现在考古学界有些学者对周边若干具有复杂内涵和较高发展程度的新时期文化人群的 政治组织形式估计很高。比如有的学者已经提出了“良渚文化王国”的概念。(注:严 文明:《中国王墓的出现》,《考古与文物》1996年第1期。)也有人提出相对解释空间 较大的概念,如以良渚高级玉敛葬所代表的社会个体是“具有国家性质的方国”(注:高蒙河:《从江苏龙南遗址论良渚文化的聚落形态》,《考古》2000年第1期。)等(相 对于良渚文化而言,对其他一些新石器文化的解释则较为谨慎,如对于拥有牛河梁遗址 的红山文化人群,我们在最新的研究中可以看到以其“还未有进入严格意义上的国家阶 段”的提法(注:刘国祥:《牛河梁玉器初步研究》,《文物》2000年第6期。);但最 近有些报道在陶寺遗址问题上的调子则甚高)。如果这些提法只是不具有严格定义的、 一般联想性的描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而如果这代表某种严肃的理论的话,作为证据 学的要求的一个方面,应当考虑同古代文献“内核”的衔接问题。本文在这方面不能全 面展开讨论,但应该说这方面的问题远不是那么简明(对于有关遗存内涵的意义的讨论 也是其中之一)。良渚文化延续时间很长,其人群与中原的交往可以从两地考古学遗存 的器型学比较中得到证实。然而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原在进入国家化进程前后受到来自 良渚文化地区某种更高水平的文化和政治进程的压力和重要影响。古代文献“内核”关 于这一时期这两大地区关系的基调是同这种情况相吻合的。因此如果肯定良渚文化地区 在夏代国家进程之外、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国家,无疑将使我们对古代文献传统关于这 一地区历史的十分低调的纪录产生疑问。这种与文献“内核”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文献 有没有失记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如果存在作为国家的“良渚文化王国”的话,不仅良 渚地区,而且中原地区的历史都应该会大不一样,由此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将是难以回 答的。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点:在解释古代中国较广大区域内国家化进程时,考古学证 据不仅将用于说明有关人群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特征,而且还应当和需要致力于说明各有 关人群之间、尤其是在古代文献“内核”中处于低调的人群与中原已知的国家进程的关 系。在这类研究中,只是孤立地就某一文化自身的内涵进行阐释,应该说离开真正如实 地探求历史上在这一区域所发生的政治过程还有一定距离。从这个意义上说,文献“内 核”不仅仅只是消极的、防御性的证据因素,在恰当的方法上它们将会引导我们去发现 和探讨更多关于中国早期历史的重要的话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考古学的基本 作用并不在于非要做出突破文献“内核”的发现,而是帮助说明这一时期历史的尽可能 多的、真实的细节。这需要一种较为冷静的、对于证据问题有较全面意识(包括对古代 文献“内核”问题的影响的了解)的态度。
中国早期国家研究目前在许多方向上都面临着进一步深入的要求。对于早期国家研究 理论的探讨是一个重要方面。而认真地检讨和提高对于文献的和考古学的证据运用的水 平,也是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方面。早期历史的研究在证据学上的的特点是要求非常综合 。任何一门学科对于自身方法的意义的不适当的扩张,都可能使整个研究造成偏差或谬 误。我们希望中国学术界加强在中国早期历史研究证据学上的深入讨论与合作,从而推 进中国早期国家问题的研究。
后记
本文系根据作者2000年8月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态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修改而成。属文既早,有些问题在今天应可用较新的资料来加以说明。但由于技术的原因本文已来不及做进一步的修改,尚请读者见谅和批评指正。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1期
- 0000
- 0005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