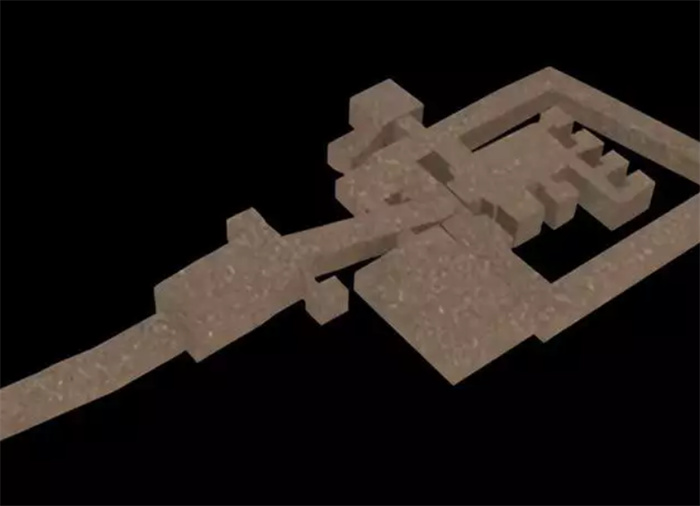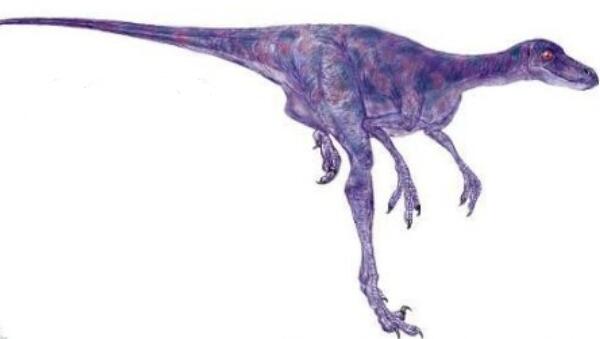栾丰实:太昊和少昊传说的考古学研究
太昊和少昊是中国古代传说时期两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代表着上古时代两个显赫的部族或部族集团。根据文献记载,他们居住在东方,属于夷人集团系统。
关于太昊和少昊的时代、地望、社会发展阶段及相互关系等,曾有不少学者进行过探讨。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梳理关于太昊和少昊的文献记载入手,结合传说地望内的考古发现和考古学文化的变迁,进而对太昊和少昊的相关问题进行探索。
一、关于太昊和少昊的传说
先秦两汉文献中,有不少关于太昊和少昊的记载,下面分而述之。
(一)太昊
先秦时期关于太昊的记载,主要有以下几条:
大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陈,大皞之虚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皞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邾人灭须句。须句子来奔,因成风也。成风为之言于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礼也;蛮夷猾夏,周祸也。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纾祸也。”(《左传》僖公二十一年)
自太皞以下,至于尧、舜、禹,未有一姓而再有天下者。(《逸周书·太子晋解》)
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

,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山海经·海内经》)
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釐,乘釐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山海经·海内经》)
何世而无嵬,何世而无琐,自太皞燧人莫不有也。(《荀子·正论篇》)
历大皓以右转兮,前飞廉以启路。(《楚辞·远游》)
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逸周书·月令篇》)
成书汉代的《淮南子·天文训》云:“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其神为岁星。”与《逸周书·月令篇》、《吕氏春秋·孟春纪》、《礼记·月令篇》等基本相同。
综合以上文献所记内容,我们可以对太昊作出以下总结:
1.太昊不是某一具体人物的名称,应是具有密切关系的若干部族的联合体,可称之为太昊系部族。其时代早于颛顼、尧、舜等,而与黄帝、炎帝、共工、少昊等并列,属于传说时代的偏早时期。
2.太昊被后世尊为东方之帝,表明其事迹和活动区域与东方相关。
3.太昊系部族所在的地望,主要有三个区域:
一是豫东。“太昊之虚”在陈,陈在豫东淮阳一带,广义上可以认为在河南省的东部地区。
二是鲁西南。任、宿、须句三个小国是太昊的后裔。任之所在,杜注:“任城县也”,即今之山东省济宁市,无异议;须句,杜注:“在东平须昌县西北”,即今之山东省东平县东南(或西北);宿的问题比较复杂,需要作简单的分析。
《春秋》隐公元年:“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杜注:“宿,小国,东平无盐县也。”按一般的看法,宿在今山东省东平县东南,与须句的位置相近。另《春秋》庄公十年记载:“三月,宋人迁宿。”《元和郡县图志》“泗州宿迁县”条下云:“春秋时宋人迁宿之地。”(注:《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1页。)从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形势分析,以上两个宿,显然不是一地,杨伯峻先生也认为“此宿恐非隐元年经之宿。”(注:杨伯峻:《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1页。)以宋国(商丘一带)与宿迁的相对位置及宋国的势力度之,宋人所迁之宿,以在靠近宋国的鲁西南豫东皖北一带较为合理。而鲁宋所盟之宿,很可能是鲁国西北边界上的一个邑。如以上所议可从,那么,作为太昊之后裔的宿国就应在鲁西南或豫东皖北地区。
此外还有商周时期的郜国。郜在甲骨卜辞和金文中多作“告”,告与郜同。郜与皓音近义通,皆可通皞、昊,如《楚辞·远游》太昊即为“大皓”。郜国,按《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所载:“……郜……,文之昭也”,为文王之子的初封之地,其国商代已有,周初分封因之,徐中舒先生认为:“皞即商代郜国,属于商之田服。”(注: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9页。)《春秋》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杜注:“菅,宋邑。……济阴成武县东南有郜城。”《春秋》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由上述几条记载知,郜地近宋,初为宋所灭,国之重器归于宋,春秋早期为鲁所取,其地在今之鲁西南的成武和单县之间,旧注多以为在成武县东南的郜鼎集一带。近年,菏泽地区博物馆在郜鼎集西北的城湖发现两周时期古城遗址,应为郜国都城所在(注:郅田夫:《郜国都城探略——试论成武县城湖故城国属》,《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
三是蒙山以东地区。颛臾是和任、宿、须句并列的四个太昊后裔小国之一。杜注:“颛臾,在泰山南武阳县东北。”《论语·季氏》:“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其地在山东省费县和平邑县之间。
此外,夏之“风夷”和商之“风方”,亦为太昊之后裔。按丁山先生的考证,“风夷故地,当求诸汉六安国之安风县”,在今之安徽省的江淮之间一带(注:丁山:《甲骨文所见氏族及其制度·风方》,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9页。)。这里与太昊之虚的豫东邻近, 或许是太昊的后裔迁居之地。
简而言之,太昊的传说及其后裔小国分布的地域,主要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及其周围地区,此外,在蒙山一带也有踪迹。
(二)少昊
先秦时期关于少昊的记载略多,主要有以下几条: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皞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

鸠氏,司马也;鸤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少皞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左传》文公十八年)
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此其三祀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
昔天之初,□(诞)作二后。乃设建典,命赤帝分正二卿,命蚩尤于宇少昊,以临四方。司□上天未成之庆。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乃命少昊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逸周书·尝麦解》)
长留之山,其神白帝少昊居之。其兽皆文尾,其鸟皆文首,是多文玉石。(《山海经·西山经》)
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山海经·大荒东经》)
有襄山,又有重阴之山,有人食兽,曰季釐。帝俊生季釐,故曰季釐之国。有缗渊。少昊生倍伐,倍伐降处缗渊。有水四方,名曰俊坛。(《山海经·大荒南经》)
有人一目,当面中生,一曰威性,少昊之子,食黍。(《山海经·大荒北经》)
少昊生般,般是始为弓矢。(《山海经·海内经》)
少昊金天氏,邑于穷桑,日五色,互照穷桑。(《太平御览》卷三引《尸子》)
少昊邑于穷桑以登帝位,都曲阜,故或谓之穷桑帝。(《帝王世纪》)
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毕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逸周书·月令篇》)。
此外,《吕氏春秋·孟秋纪》、《礼记·月令篇》等也有类似的记载。总结上述关于少昊的记载,可得出以下认识:
1.少昊不是一个明确可指的具体人物,而应是若干部族的联合体,本文称之为少昊系部族。由“及少昊之衰也,……颛顼受之”(《国语·楚语》)和“少昊以前,天下之号象其德,百官之号象其徵。颛顼以来,天下之号因其地,百官之号因其事”(注:[唐]贾公彦:《周礼正义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663页。)可知,少昊的时代早于颛顼,更早于尧、舜、禹,而与黄帝、炎帝相若,蚩尤属少昊时期。
2.关于少昊系部族的分布区域,主要有二:
一是以曲阜为中心的鲁中南地区。《左传》昭公元年:“周有徐、奄。”杜注:“二国皆嬴姓。”《说文》:“嬴,少昊氏之姓。”徐、奄是商代和周初的东夷土著民族的国家,皆少昊之后裔。周初成王分封,鲁公“因商奄之民”而“封于少皞之虚”,杜注:“少皞虚,曲阜也,在鲁城内。”鲁初封于商奄之地,亦即少昊氏的中心区域。关于徐的地望,《春秋》僖公三年:“徐人取舒。”杜注:“徐国在下邳僮县东南。”今人多据此认为徐国在洪泽湖北侧一带,这大约是遭受西周征伐之后的徐国地望。《尚书·费誓》序云:“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由此可知徐国最初在曲阜之东不远,徐旭生先生认为“徐国在周初当在今山东东南部曲阜县附近,以后才迁到南方数百里外”(注: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7页。)。泗水县文物管理所的赵宗秀同志经过调查,认为商末周初的徐国就在泗水县东南的汉舒村古城一带(注:赵宗秀:《试论商末周初徐国之所在》,山东东夷古国史学术讨论会论文,1998年4月。)。因此,以徐、奄为主的东夷旧国之地, 即今之鲁中南的汶河和泗河流域一带,是少昊系部族的主要分布区域之一。
位于山东省莒县的另一少昊后裔的嬴姓大国莒国,是西周偏晚时期才由外地迁到这里来的。而商代的莒国,或依据传出于费县的一组商代有铭青铜器,认为其地就在山东费县一带(注:孙敬明:《莒史缀考》,《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紧邻泗河流域。至于鲁东南的郯城一带,由于郯子自称为少昊之后,故其地也有可能属于少昊系部族,但由于时代久远,郯国又是小国,我们不能断定,郯子的祖先是自少昊时期就世代居于此地,抑或是后来从其他地区迁入的,只是还保留着祖先的传说。
齐地中心区域也是少昊系部族重要的分布区。《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了晏子对齐地历史沿革的追述:“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爽鸠氏,杜注:“少皞氏之司寇也。”齐初的封地,东不过潍坊,西不到济南,大约在这一范围之内。由此可知,鲁北中部地区,也属于少昊系部族的分布区域之一。
此外,《史记·封禅书》云:“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为什么秦襄公被周王列为诸侯后,马上想到要祠白帝少昊呢!这还要从秦人的来源寻找原因。《史记·秦本纪》:“太史公曰:秦之先为嬴姓。”嬴姓来自秦人先祖大费,即辅佐虞舜的柏翳,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至周孝王时,“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柏翳,亦写作伯翳、伯益,《国语·郑语》说:“嬴,伯翳之后也。”韦注:“伯翳,虞舜官,少皞之后伯益也。”由此知秦人之姓“嬴氏”系来自其祖先伯益。伯益是虞舜时期东方夷人的重要代表人物,为少昊之后,这样,秦人也自然就是少昊的后裔了。正因为如此,秦襄公立下攻戎救周之功,被始列为诸侯,在这秦人发展的历史上出现重大转折之际,立即隆重地祭祀其祖先白帝少昊,这一举措可能具有告慰先祖并继续企求得到先祖保佑的多重意义。那么,既然秦人系出自东方的少昊氏,为什么会委身于西方戎狄之间呢?他们又是如何由东方辗转迁徙到西北地区的呢?文献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所以近人对此颇有异辞。对此,傅斯年先生在六十多年前曾指出:“秦赵以西方之国,而用东方之姓者,盖商代西向拓土,嬴姓东夷在商人旗帜下入于西戎。”(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第1121页,1935年。)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对夷人西迁的时间、路线、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讨(注:段连勤:《关于夷族的西迁和秦嬴的起源地、族属问题》,载《先秦史论文集》,《人文杂志》1982年增刊;陈平:《从“丁公陶文”谈古东夷族的西迁》,《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其论据是有说服力的。另外,相应的考古发现也提供了这一方面的线索。如陕北神木县石峁遗址发现的玉器中,时代较早的(属于龙山时代)双孔钺、牙璋、牙璧等(注: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第3期;《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 《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合期;《神木石峁龙山文化玉器探索》,《故宫文物月刊》,台北,总第126、128、130期,1993年。), 在当地找不到来源,而和山东地区海岱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相同。据此可以推测,在龙山文化时期,有一部分东方居民辗转迁徙到了西方地区,他们只是带去了自己比较贵重的玉礼器。随着时间的推移,虽然物质文化已与当地完全融合,但自己祖先的传说仍保留在记忆之中,始终没有泯灭。至于少昊氏在周汉时期的一些典籍中,被尊为西方之神,主秋和日入,当另有原因,容另作讨论。
(三)太昊和少昊的关系
关于太昊和少昊的关系,近人多有论及,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基本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太昊的时代较早,少昊的时代较迟。如傅斯年先生认为“太皞少皞皆部族名号,……至于太少二字,金文中本即大小。大小可以地域大小及人数众寡论,如大月氏小月氏,然亦可以先后论,如大康少康。今观太皞少皞,既同处一地,当是先后有别。且太皞之后今可得而考见者,只风姓三四小国,而少皞之后今可考见者,竟有嬴己偃允四箸姓。当是少皞之族代太皞之族而居陈鲁一带”(注: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第1120—1121页,1935年。),“东土的系统”“当是大皞,少皞,殷”(注: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第243页,1930年。)。唐兰先生也认为:“太昊和少昊,都是国家的名称。太和少等于大和小,是相对的。这两个称为昊的国家,可能有先后之分,在少昊强盛的时期,太昊已经衰落了。”(注:唐兰:《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上限远在五、六千年前》,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127—128页。)“太昊大概在少昊前,所以关于少昊的文献比较多。……少昊之国在黄河与淮河之间,又继承太昊炎帝之后,所以发达得比较早。”(注: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化的年代》,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第81—83页。)夏鼐先生也曾认为太昊和少昊“似为有承继关系的前后两个氏族”(注:刘敦愿:《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后记》,载《美术考古与古代文明》,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398页。)。王树明先生则进一步认为:“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就是这两个不同发展阶段在物质文化上的反映。”(注: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出土的陶尊“文字”》,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第265页。)
第二种观点认为太昊和少昊是同时并存的。如刘敦愿先生认为:“大皞少皞两族都是风姓,也就都以凤鸟为其氏族图腾,氏族图腾相同,也就说明有着共同的起源,大皞、少皞是相对的称谓,所谓大(太)与少,也就是大与小,长与幼,两者是兄弟部落的意思非常明显。现代原始社会史的研究认为,氏族的起源,最初总是表现为‘二元组织’的(或名之为‘两合组织’的),原始部落最初由两个原始氏族组成,在以后的发展中,由两个胞族组成。……风姓大皞少皞两族的关系也是这种‘二元组织’关系的表现。”(注:刘敦愿:《古史传说与典型龙山文化》,《山东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
第三种观点认为少昊较早,太昊在陈地之虚是昊族向豫东迁徙发展形成的。如徐中舒先生认为:“少皞氏故地在鲁,太皞氏在陈,这是皞族迁徙于不同地区而得名的。古史中称一些民族原住地多称为‘少’,少即‘小’,是指该族早期人口稀少势力弱小时期。‘太’即‘大’,乃该族后来迁徙新地人口众多,势力强大时的称号。”(注:徐中舒:《先秦史论稿》,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19页。但徐中舒先生在阅读《中国史稿》的批语中又说:“太者,大也,远也。太昊应在少昊之前。”见同书第349页。)
管见是太昊和少昊两大部族不是前后相继的传承,而主要是一种时代相重叠的并列关系。有以下四证:
1.古代文献记载往往将太昊和少昊并列。如《左传》中所载黄帝氏以云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昊氏以龙纪,少昊氏以鸟纪;《礼记》和《吕氏春秋》中春天之帝太昊,夏天之帝炎帝,秋天之帝少昊,冬天之帝颛顼;《淮南子》中尊太昊为东方之帝,炎帝为南方之帝,黄帝为中央之帝,少昊为西方之帝,颛顼为北方之帝。当然,《礼记》、《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所配备的春夏秋冬或东南中西北的帝名,显然是人为地整齐化了,是当时(或略早)人编纂出来的,并不完全可信,如其中的颛顼就明显较晚,但还是将他们并列。
2.太昊为风姓,少昊为嬴姓,两者姓氏有所区别。太昊之后一直存续,如:唐尧之时,有不服领导(“为民害”)的“大风”,“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邱之泽”(《淮南子·本经训》);在夏代,有后相二年征伐的“风夷”和后泄二十一年所命六夷之中的“风夷”;到商代,有见于甲骨卜辞“……卜其皿(盟)风方……”(《殷契粹编》,1182)的风方;此外,《楚辞·远游》在大皓(太昊)之后还提到“风伯”,亦为太昊之后;而任、宿、须句、颛臾等周代小国,直至灭亡都保持着风姓。少昊的后裔如徐、奄、秦等,一直到周秦时期还保持着嬴姓,历二三千年而不变。他们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太昊和少昊不是时代有先后的同一族系的部族。至于他们都崇拜鸟,或以鸟为图腾,说明两者关系比较密切,或许他们是由同一祖先繁衍分化出来的。
3.由前述分析可知,太昊的分布区域豫东、鲁西南和皖北为主,个别在沂蒙地区,而少昊的分布区域主要在鲁中南地区的汶河和泗河流域,部分在鲁北中部地区。两者很少有重叠分布现象,或者说,两者的主要分布区处于相邻的不同区域。这是他们非为前后关系而为同时并存关系的坚强证据之一。
4.在所有的文献中,没有太昊早于少昊或太昊发展为少昊的记载。当然,由于远古文献保存下来的极少,如果仅此一条,并不能作为谁早谁晚或者同时的证据。但可以作为上述三条的补充或者反证。
因此,我认为姓氏不同且分布区域有别的太昊和少昊主要是一种同时并存关系。
在基本理清了太昊和少昊的关系及其各自的主要分布区域之后,就可以从各地发现的考古学遗存中来分辨“太昊文化”和“少昊文化”了。
二、关于太昊的考古遗存分析
从太昊氏风姓诸后裔的分布,我们将太昊系部族的主要活动区域限定在豫东、鲁西南和皖北一带。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就目前所知,自早至晚依次有小山口下层一类遗存、石山子一类遗存、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和岳石文化。综观这一考古学文化序列,它前后分属于两个文化系统,即以大汶口文化的出现为界,此前的小山口、石山子等为同一谱系的文化,而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则为另一谱系的文化。这两个文化系统基本上是一种替代关系,即在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东方居民渐次西迁,最终融合和取代了当地的土著文化,成为东方海岱系文化一个新的分布区。
根据考古学文化的横向比较和碳十四测年,前一系统大约在距今5300年之前,其上限可达距今8000年前后。由于年代久远,并且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又被外来的文化所同化和取代,所以其族属问题没有线索可寻,很可能已经在历史的记忆中泯灭。后一系统则因为年代较近,且文献中保留着许多传说,可以大致按时代进行分析对应。
这一地区的岳石文化基本上属于夏代时期,它是夏代东夷部族所创造的文化,从族系的渊源关系上讲,应是太昊之后裔所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根据文献记载,我们还认为这一地区的部分岳石文化遗存,是殷之先公时期的商人所创造的,故可称为“先商文化”(注:拙文《岳石文化和郑州地区早期商文化的关系——兼论商族起源问题》,《华夏考古》1994年第4期。)。
对于地处豫东、皖北、鲁西南地区的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的文化性质,学术界的看法不一。由于受先入为主的认识所影响,不少人仍坚持其属于“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对此,我们曾作过专门的辩正,认为其属于东方的海岱龙山文化系统(注:拙文《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初论》,《考古》1992年第10期。),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列之中。关于王油坊类型的族属,或认为是先商文化(注:本世纪七八十年代,有不少学者持这一观点,恕不一一列举。),或认为“可能就是传说中的有虞氏文化”(注: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对此暂不置评。其相对年代是明确的, 即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时代显然晚于太昊。
再往前推就是大汶口文化。按照我们对大汶口文化的统一分期度之,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主要属于晚期阶段,少数可以早到中期阶段后段,如亳县付庄的大汶口文化墓葬(注:杨立新:《安徽淮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载《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版。)。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分析,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传说时期的太昊氏文化相当。故我认为,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其负载体就是文献中记载的太昊系部族(注:由于鲁西南地区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甚少,故以下所归纳的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资料主要取自皖北和豫东地区。)。
如上所述,这一地区本来并不属于大汶口文化的地盘,只是由于携带着自身文化的大汶口人的大量涌入,才使其成为大汶口文化一个新的分布区。那么,我们要问,这些大汶口人来自何地?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他们迁徙到这里来的呢?这就需要从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的特征谈起。
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择其要者如下:
1.遗址大多位于高出地面的岗、丘和堌堆之上;
2.房屋建筑以连间排房最具特色;
3.墓葬中有一定数量的瓮棺葬;
4.偏早阶段(如亳县付庄)有一定数量的多人同性合葬墓,流行拔牙习俗,其特殊之处是上下牙齿都拔;
5.陶器中有一部分少见于山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器形,如瓦足盆形鼎、双曲腹浅盘豆、粗高颈罐、高颈鼓肩壶(罐)、瘦长背壶等;
6.存在图像文字,并且都刻于大口尊的外表,均一器一字,有的还涂朱。
上述特色,第1条是该地区地势低洼、 易受水患的特殊地理环境使然;第2、3、5条,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不同, 或是受到西部或南部地区的影响,或是还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该地区早期文化的流风余韵;第4、6条是追寻这一地区大汶口人来源的重要线索。
皖北豫东与东部其他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距离较近的是鲁中南的汶泗流域,而这一带也是大汶口文化遗存分布得最为密集的地区。鲁中南地区已发现的多处大汶口文化中期墓葬中,迄今尚未见到多人同性合葬墓;而流行的拔牙习俗,则基本上都是拔除一对上侧门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刻划图像文字。
与上面的情况不同,在距离皖北豫东稍远的鲁东地区倒是可以见到这些现象。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诸城呈子(注:昌潍地区文物管理组等:《山东诸城呈子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0年第3 期。)、潍坊前埠下(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潍莱高速公路考古发掘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8年3月8日,第1版。)和栖霞杨家圈(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等遗址都曾发现过多人同性合葬墓;胶州三里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出版社1988年版。)和莱阳于家店(注:严文明:《胶东原始文化初论》,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有拔除上下颌牙齿的习俗;在莒县陵阳河(注:山东考古所等:《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墓葬发掘简报》,《史前研究》1987年第3期;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出土的陶尊“文字”》,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大朱家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莒县大朱家村大汶口文化墓葬》,《考古学报》1991年第2期。)、杭头(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莒县杭头遗址》,《考古》1988年第12期。)、诸城前寨(注:杜在忠:《论潍、淄流域的原始文化》,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日照尧王城(注:《尧王城遗址第二次发掘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4年1月23日,第1版。)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发现有多例刻划图像文字,有的还涂朱,与皖北地区发现的完全相同。因此,我认为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鲁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较之鲁中南地区更为接近一些。两者之间必有更为密切的关系。这就为寻找皖北豫东地区大汶口文化的来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线索。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陶尊上的图像文字。其中两地均见的是由“日”“火”“山”组成的图像,对于了解他们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这种图像是由三个部分上下排列组合成一个完整图形,上部为一圆圈,下部为五个向上的锐角,其分别表示太阳和山,对此,大家无异辞。问题是中间的月牙状图形,或释作“火”,或释作“月”,或释作“鸟”。因为这种图像的上侧中部多有一个向上凸起的尖,所以与新月有明显区别。陵阳河遗址出土的一件简化此类图像(省去了下面的山形),太阳下方的图像显然不是月亮,像火之形。故以释为火较为合理。由于“日”、“火”、“山”或简化为“日”、“火”所组成的图像,在具体的释读上有多种不同意见,或作旦(注: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 或作炅(注: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 或作炅山(注:李学勤:《考古发现与中国文字起源》,《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2辑,1985年;《论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号》, 《文物》1987年第12期。),或作炟(注:王树明:《谈陵阳河与大朱家村出土的陶尊“文字”》,载《山东史前文化论文集》,齐鲁书社1986年版。),或作昊。这一图像的直观含义并不复杂,它就是太阳高高悬于空中之摹画。田昌五先生认为该图像“是一个氏族部落标志,完整地作日月山,山上有明月,月上有太阳;简单地作日月而省去山,其意应是太皞和少皞之皞字,有如后来的族徽”(注:田昌五:《古代社会断代新论》,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3—54页。)。田先生将图像的中间部分释为月尚有商榷之处,但将其与“昊”族相联系是一种极有见地的解释,其说可从。那么,分居于皖北豫东和鲁东两个地区持有这种族徽的昊族居民只能属于太昊系部族。
因为我们已经确知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来自东方,并且他们和鲁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又有这么多更为接近的因素,那么,是否可以认定前者就是从后者分迁出去的呢?我认为还不能下这种结论。
我们注意到,从皖北到鲁东有一个相对较大的间隔地带,即江苏省的淮北地区(以下简称苏北),这三个地区在地理上同属于淮河流域,且均位于淮河的北侧支流发育区:皖北豫东地区位于颍、涡、浍、沱河流域;苏北地区处在泗、沂、沭河流域下游;鲁东地区的南部则居于沂、沭河流域中上游。下面我们按早、中、晚三个阶段(注:大汶口文化延续的时间长达一千五六百年之久,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其划分为早、中、晚三个大的阶段。参见拙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 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9—113页。)来考察大汶口文化在这三个小区域的分布情况。
早期阶段:苏北地区有较多发现,如邳县刘林、大墩子,沭阳万北,新沂小林顶等;鲁东地区的南部据说有所发现,但为数不多,并且迄今未见正式发表的资料;皖北豫东地区这一时期主要属于石山子、双墩一类遗存的偏晚时期,与大汶口文化分属于不同的文化谱系。
中期阶段:苏北地区仍然有较多的发现,如徐州高皇庙,邳县大墩子上层,新沂花厅,沭阳万北等;鲁东地区南部的发现仍然不多,属于这一时期的遗址,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处经过正式发掘;皖北豫东地区在这一时期的晚段开始有零星发现,如亳县付庄和周口市区烟草公司仓库等(注:周口市文化局文物科:《周口市大汶口文化墓葬清理简报》,《中原文物》1986年第1期。)。前者发现的大汶口文化遗存中有较多的本地因素,后者中的非大汶口文化因素则更为显著。此外,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也发现有个别的大汶口文化墓葬(注:郑州市博物馆:《郑州大河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第3期。), 其存在表明大汶口人已经来到郑州一带,但并没有改变这里原有文化的性质。
晚期阶段:苏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甚少,比较明确的,只有苏北边缘地区发现的少数几处,如洪泽湖西北的泗洪县赵庄和连云港市郊区的二涧村等,中期阶段的一些遗址, 一进入晚期就基本消失了;鲁东地区南部的大汶口文化遗址则迅速增多,如陵阳河、杭头、大朱家村、东海峪等,还有许多没有作过发掘的遗址大都属于这一阶段;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呈现迅速增多的趋势,如宿县芦城子、小山口、古台寺,萧县花甲寺,蒙城尉迟寺,永城黑堌堆,鹿邑栾台,淮阳平粮台,郸城段寨,商水章华台等,均属于这一阶段。
分析大汶口文化三个阶段的遗址在苏北、皖北豫东和鲁东南部三个地区分布的变化趋势,我认为,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最有可能是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同时,鲁东沂、沭河上游一带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遗存,其中一部分也有可能来自苏北地区。
基于上述,将文化内涵方面的共同特征和遗址分布规律方面的变动趋势结合起来分析,可以认定,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期晚段开始渐次从苏北地区迁徙而来的。
以上我们论定了皖北豫东地区的大汶口文化系来自苏北地区,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迁徙呢?以往基本上没有人涉及这一问题。我曾经推测可能是由于大汶口文化人口增多、势力膨胀而进行的向外扩张(注:拙著《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现在看来并非完全如此。应该作进一步的探讨。
地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南部的苏北一带,与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文化区相邻,两大文化区系之间一直存在着文化上的交往和联系。对于两者的交往,我们曾作过比较详细的分析(注:拙文《良渚文化的北渐》,《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大汶口文化与崧泽、 良渚文化的关系》,载《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双方关系的趋势是: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到中期阶段,两个地区之间的联系比较平稳,由各自文化中对方文化因素的内容和数量可知,双方互有影响;大汶口文化中期中后段,良渚文化在南方迅速崛起,其分布区的北界已扩展至淮河故道一线,这已为在淮河故道南岸发现多处良渚文化遗址所证实。与此同时,在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区内普遍感受到了来自良渚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明显地呈波状分布,即苏北地区极为强烈,鲁南地区比较明显,鲁北和胶东半岛地区较弱。另外,以文化交流为主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从花厅遗址显示的情况看,双方之间至少是在苏北地区采用了战争的形式(注:严文明:《碰撞与征服——花厅墓地埋葬情况的思考》,《文物天地》1990年第6期。)。即良渚文化在完全占领了本不属于其分布区的苏中地区之后,继续北上,在苏北地区和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展开了一定时期的争夺,结果是两败俱伤。此后,即大汶口文化晚期前段开始,苏北地区基本上没有发现大汶口文化的遗址,应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这一地区发生过大规模的部落战争有直接关系。与此相联系,皖北豫东地区开始出现大汶口文化遗存,沂、沭河上游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也明显增多,在这种历史背景和区域格局之下,他们的来源地只能是苏北地区。
当然,也可能有另外一种原因,即水患。淮河下游地区地势低洼,排水比较困难,洪水可以给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造成极大不便。但促使人们远离故土迁徙他方,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洪水。我想只有一种可能,即黄河改道至淮河下游一带入海。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大规模地依靠人力来治理河道,这样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水灾,使人们原本平稳的生存空间遭到人力无法挽回的破坏,从而导致大量的人口外徙。诚然,在没有得到第四纪地貌学方面的可靠证据之前,这一设想还只能说是一种假说,但其可能性是存在的。
综上所述,太昊系部族最初活动于鲁东和苏北地区,后来迫于良渚文化的压力或水患,才举族西迁到了皖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其时约当大汶口文化中期后段和晚期阶段。由于这一地区地处中原、东方和南方几大区域的中间地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与各大区系的文化交流和接触较为频繁,故保留下来的传说也相对较多。而仍然留在东方地区的太昊系部族的其他支系,尽管也创造了较高的文化,但因为偏居海隅,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被人们淡忘了。不过,太昊后裔之一的颛臾仍居于沂沭河谷的西部,并为东蒙主,或许还与其远祖太昊氏有关。此外,后世一直遵太昊为东方之帝,很可能与太昊氏最初居于东方相关。至于说太昊后裔较少,少昊后裔较多,则可以从太昊西迁之后,相当一部分与中原地区的华夏族融合(注:大汶口文化向西迁徙,侵占了皖北豫东鲁西南一带,成为大昊系部族新的领地,而还有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居民继续西进,来到郑州、禹县、平顶山一线,有的甚至到达洛阳盆地和豫南鄂北一带,他们在较长时期内还顽强地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传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被当地的华夏文化所同化,成为后来夏文化的重要来源之一。参见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 而少昊系部族偏居于东方得以相对独立地繁衍发展中得到合理的解释。
三、关于少昊的考古遗存分析
少昊系部族分布的地望,主要在泰山以南的汶、泗流域,鲁北的济、淄流域也是其重要分布区之一。这一地区内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自早至晚依次为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商代文化、周代文化。在这一长串考古学文化中,从北辛文化到岳石文化已被学术界公认为属于同一谱系,其创造者是时代有先后的同一族系的人们。我们仍然按时代自后向前逐一进行分析比较。
属于周代的考古遗存发现较多,以曲阜为中心的汶泗流域地区属于鲁文化系,以临淄为中心的鲁北中部地区属于齐文化系。他们周围同时还各自存在着一些或臣服于鲁、齐,或相对独立的小国家。如果没有出土特殊的确凿证据(如铜器铭文等),仅凭他们所遗留下来的物质文化遗存,几乎没有办法将其一一区分开来。
商代遗存也比较丰富,从已有的发现看,起自二里冈上层时期,止于殷代末期。如与文献记载的史实相联系,汶泗流域的商代文化遗存主要应属于商奄和徐夷,鲁北地区则主要属于蒲姑(薄姑)。奄、徐、蒲姑,均为商代时期的嬴姓大国,属于东夷土著,系少昊氏之后。汶泗流域的商代遗存与殷墟商文化最为接近,变化也同步,典型的夷人土著遗存在这里基本不见。因此,我认为这一地区和商王朝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这从其名为“商奄”、鲁城内有“亳社”,以及周灭商后,商奄趁政局未稳,率先在东方带头闹事可以得到旁证。与汶泗流域相比,鲁北地区的商代遗存与殷墟商文化的差别较大,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商代遗存中,还保留着极为浓厚的夷人土著文化因素。当然,在整个商代时期,鲁北和汶泗流域还同时存在着许多小国,他们或夹杂在这些大国之间,或散布于周边,形势与周代相差不大。
岳石文化在两个地区均有发现。笼统地讲,他们的族属应与《后汉书》提到的“九夷”中的一部分相对应(注:《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至于具体属于哪一分支的“夷”,则无法确定。在汶泗流域,滕州一带夏商时有薛,《左传》定公元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奚仲迁于邳。仲虺居薛,以为汤左相。”泗水一带夏商时有卞,《吕氏春秋·离俗》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国春秋属鲁,《春秋》僖公十七年:“会齐侯于卞。”杜注:“卞,今鲁国卞县。”今泗水县泉林镇有古城,是卞国故城。因此,薛和卞都是夏代和商初汶泗流域有一定影响的国家。《左传》昭公二十年晏婴所述齐地沿革,鲁北地区在蒲姑之前为逢伯陵,杜注:“逢伯陵,殷诸侯,姜姓。”其时代排在晚商时期的蒲姑氏之前,《续修济阳县志·沿革篇》云:“殷,青兖之域汤隶有逢伯陵”,按此推算,其时代至晚相当于岳石文化晚期。《山东通志》认为“逢陵城在今山东淄川废治西南四十里”。《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一册)将其标于今青州之西。近年在济南之北的济阳县刘台子西周贵族墓地中屡见有“夆”铭铜器,如M6出土7件有铭文的铜器,其中6件为“夆”器,“夆”即逄、逢,此墓为一代“夆”公无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第12期。)。由此学术界认为刘台子是西周时期的逢国墓地,如是,则西周时期逢国的地望可能在鲁北中部偏西一带。由此也可知,晏子所讲述的齐地,是指以临淄为中心的鲁北中部地区。而被取代者,很可能离开此地而迁居他方。
龙山文化遗址在泰山南北地区发现较多。刘敦愿先生曾将其考定为两昊部族的文化遗存。把整个中国上古史与已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对应,龙山文化大约相当于尧舜时期和夏初。如作纵向比较,尧舜晚于少昊已如前述。另外,按晏子讲述的齐地沿革,鲁北地区“逢伯陵”之前是“季荝”,杜注:“季荝,虞、夏诸侯,代爽鸠氏者。”那么,“季荝”所处的虞夏时期就大致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夏初的重要国家有穷,其君后羿,亦作“夷羿”,属东夷部族。与有穷关系密切的寒、斟灌、浇、戈等,都在鲁北地区,且《水经·河水注》载:“大河故渎,……西流迳平原鬲县故城西。《地理志》曰:鬲津,王莽名之曰河平亭,故有穷后国也。”所以有穷大约就在鲁北的中西部。夏初的后羿是灭国之君,其国可上溯到帝喾时期。尧时之羿亦甚为显赫,《淮南子·本经训》记载较详:“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

)、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

,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于是天下广狭、险易、远近,始有道里。”从两者均善射来看,应属于同一族系的先后不同时期。尧的时代约当龙山文化早期,羿所射杀的大风、凿齿亦为东方夷族。青丘或认为在今广饶县内(注: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青州府·乐安县》,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514页。)。《山海经》和《淮南子》所记载的“凿齿民”、“有人曰凿齿”,应为有拔牙习俗的东方居民,而非“齿长三尺”(或云五六尺)的怪物(注:参见严文明《大汶口文化居民的拔牙风俗和族属问题》,载《大汶口文化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1年版。海岱地区从北辛文化至龙山文化时期,居民都有拔牙的现象。如细观之,海岱地区之内的各个小区有较大差别。从总体上讲,以汶泗流域最为流行,潍坊以东次之,鲁北地区较少。),其地望只能从流行拔牙的鲁中南和胶东半岛西南部求之。由此看来,尧时羿的地望也在鲁北中部地区。此外,为恢复夏王朝立过大功的有鬲氏,通常认为在鲁西北的平原县东南,从近年来在鲁北西部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素面陶鬲看,有鬲氏的取名或与大量使用陶鬲相关。
汶泗流域,则应是皋陶、伯益的居地。皋陶的记载见于多种古籍。《论语·颜渊篇》曰:“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作土以理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关于皋陶的事迹,《尚书·尧典》、《礼记》、《论语》、《墨子》、《淮南子》、《史记》等多种文献有载,应实有其人,或者也代表一个部族。《帝王世纪》说:“皋陶生于曲阜。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赐姓曰偃。尧禅舜,命之作士。舜禅禹,禹即帝位,以咎陶最贤,荐之于天,将有禅之意。未及禅,会皋陶卒。”(《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偃与嬴乃一声之转,多数学者认为“皋”即“皞”,再加上居地都在曲阜一带,所以,皋陶和少昊应属于同一族系,只是时代一早一晚而已。
关于伯益的记载更多,见于《尚书》、《竹书纪年》、《国语》、《墨子》、《孟子》、《战国策》、《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等。伯益,亦作“伯翳”、“柏翳”、“柏益”、“后益”、“益”等。其事迹主要有掌山林、驯鸟兽、作井、占岁等。其时代晚于皋陶而与禹、启同时。如《史记·夏本纪》云:“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而后举益,任之政。”不少文献说伯益为皋陶之子,我们固然不必拘泥于这种狭义的父子说,但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两者出自同一族系应无问题。皋陶卒,禹仍在皋陶的同系东方部族中寻求合作者,继皋陶而起的益应是东方部族的首领。那么,伯益所属部族的地望又在何地呢?《今本竹书纪年》曰:“帝启二年,费侯伯益出就国。”《史记·秦本纪》云:“大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看来伯益、大费、费侯为一人,其来自费地。《尚书·费誓》序:“鲁侯伯禽宅曲阜,徐夷并兴,东郊不开。作《费誓》。”周初的费地在曲阜之东,或认为即今费县西南七十里的费城。如是,则伯益所居之费(注:《孟子·万章上》:“禹荐益于天,七年禹崩,……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阴。”(《史记·夏本纪》为“益让帝禹之子启,而辟居箕山之阳。”)有学者认为山东省益都有箕山,伯益所居之地就在益都一带。参见王永波《“己”识族团考——兼论其、并、己三氏族源归属》,载《东夷古国史研究》第二辑,三秦出版社1990年版;王永波、张光明《益都得名与伯益古族新证》,《管子学刊》1992 年第1期。)与皋陶所居之曲阜相距甚近,均在少昊系部族活动的范围之内。由此看来,龙山文化时期的汶泗流域,主要是少昊后裔皋陶、伯益等部族的生存空间。
早于龙山文化的大汶口文化时期,鲁北中部地区应是晏子所述的爽鸠氏的居地。或者说,鲁北地区中部的大汶口文化是由少昊系部族之支系爽鸠氏创造的。另外,一般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另一著名东夷部族蚩尤,其居地就在鲁西北一带。据《逸周书·尝麦解》的记载,蚩尤属于少昊时期。因此,鲁北地区西部的大汶口文化则应是由蚩尤部族创造的。史载,蚩尤曾和炎黄联军大战于涿鹿之野,结果是蚩尤战败,从此一蹶不振。从目前的考古发现看,鲁西北地区的龙山文化遗址绝大多数为晚期,属于龙山早期和大汶口文化晚期后段的遗址甚少,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或许可以用蚩尤战败而导致人口锐减来加以解释。诚如是,则可以从另一角度证明蚩尤存在于大汶口文化晚期,进而表明少昊氏的年代下限也当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际。
汶泗流域是大汶口文化重要的中心分布区,也是目前发现大汶口文化遗址最多的地区,这里的大汶口文化自早至晚连绵不断,清楚地展现了大汶口文化发展变化的完整过程。与其他地区相比,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并且具有鲜明特色如:
1.聚落遗址的面积大小相差明显,在数量上呈金字塔状分布。大者几十万甚至近百万平方米(如大汶口遗址),小者数万甚至不足一万平方米。同时,还发现大汶口文化晚期阶段的城址(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鲁中南考古队等:《山东滕州市西康留遗址调查、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3期;张学海:《浅说中国早期城的发现》, 载《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岳麓书社1996年版。)。
2.墓葬发现较多,同性多人合葬墓消失得较早,而成年男女双人一次合葬墓先于其他地区出现,数量也多。到中晚期阶段,墓葬之间在墓室的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数量的多少和质量的优劣等方面的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表明阶级已经产生。
3.盛行拔牙、头骨枕部人工变形和死者手握獐牙的习俗,其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将石、陶质小球置于口中而导致齿弓严重变形的现象,也仅见于这一地区。
4.大汶口文化的一些特殊器物,如骨牙雕筒、龟甲器和獐牙勾形器等,主要见于这一地区,其他地区数量很少或根本不见。
5.彩陶艺术较为发达,彩陶在全部陶器中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大汶口文化。
此外,在其以东的沂沭河流域和西南方的皖北地区频频发现的陶器刻划图像,这一地区至今未见。考虑到汶泗流域地区经过发掘的大汶口文化遗址数量最多,出土物最为丰富,并且时代有早、中、晚期,遗址等级有高、中、低级,所以不应是由于发掘的遗址分布偏颇所造成的,当另有原因。
如与古史传说的族属相联系,从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分析,这一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只能和少昊系部族相对应,即少昊系部族创造了汶泗流域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如与鲁豫皖地区太昊系部族遗留下来的大汶口文化遗存相比较,保存下来的少昊氏传说,在时间上大约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遗存最为接近。当然,汶泗流域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遗存和更早的北辛文化遗存,毫无疑问与少昊系部族属于同一谱系。只是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保留下来的传说更少,我们已无法再具体的一一指对。
四、结语
以上,我们对古史传说中关于太昊和少昊的记载进行了梳理,并将其与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进行了比较,简而言之,有以下结论。
(一)太昊和少昊是传说时期东方夷人的较早阶段,他们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明显区别,从文献记载的共有崇鸟习俗和物质文化遗存的接近程度看,他们应是同源的。但相互之间又不是直接的前传后承的关系。综合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认为太昊和少昊两大系部族时代相若(至少在相当长时期内两者共存过),分布邻近,文化相似,属于海岱系(或称东方系统)文化的两大分支。
(二)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可以和古史传说记载的太昊系部族相联系。由这一地区大汶口文化遗存的年代可知,文献中关于太昊的传说不会早于距今5000年太远。豫东、皖北和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是由东方迁徙来的,从其与汶泗流域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较远,而与沂沭河流域大汶口文化的关系较近分析,他们很可能是来自苏北和鲁东南地区南部。至于其向西迁徙的原因,则有人为原因(战争)和自然原因(洪水)两种可能性。
(三)经过年代学方面的分析比较,我认为少昊系部族所处的时代与大汶口文化(至少是其晚期)相当,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应从大汶口文化中去寻找。如果说的明确一点,泰山南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遗存应是少昊系部族所创造的文化。从传说和考古发现两个方面看,少昊系部族的主要活动区(或者说中心分布区),大约是在自泰安到徐州一线的汶泗流域地区。
来源:《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