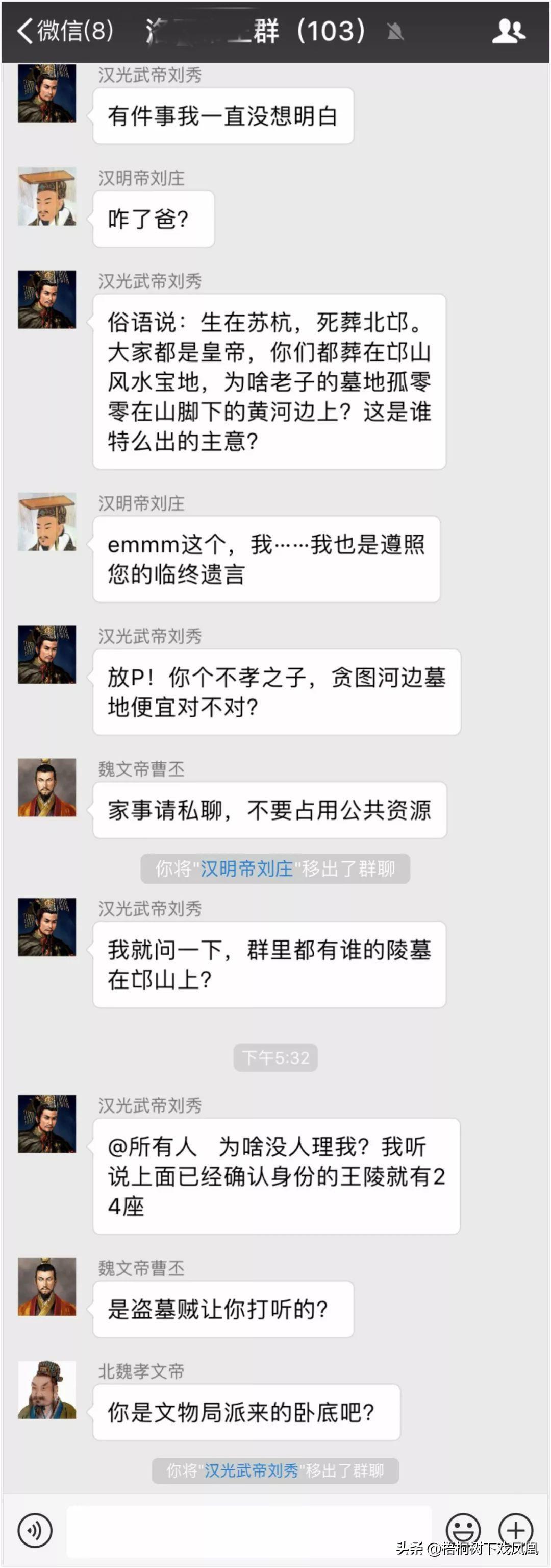李海荣;朱露萍:中国古代青铜器研究的萌芽期与形成期
本文所说中国古代青铜器主要是指中国先秦夏商周时期的古青铜器。
一
从古代文献提供的线索来看,东周时一些学者为了阐明古代文物制度或宣扬自己的伦理政治主张已经注意到了实物资料。《国语·鲁语》中记载了孔子对“楛矢”的研究;《论语·八佾》中谈到孔子对鲁桓公之庙中所放“欹器”的研究;韩非子在《十过》一文中借由余之口指出尧时食饮用“土簋”、“土铏”,舜时斩木漆为食器,禹时更“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殷人则“食器雕琢,觞酌刻镂”。古青铜器当然也是当时学者注意的实物资料之一。《吕氏春秋·先识》曰:“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慎势》曰:“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适威》曰:“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达郁》曰:“周鼎著鼠”;《离谓》曰:“周鼎著倕而龁其指。”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古铜器上花纹的认识。谈及古铜器花纹的始自《吕氏春秋》。从我们现在的中国古代青铜器知识来看,有饕餮、象和窃曲纹,无倕和鼠这些纹饰。《左传·昭公三年》记载了叔向所引谗鼎之铭,曰:“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左传·昭公七年》记载了孟僖子引正考父鼎之铭,其铭曰:“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饘于是,鬻于是,以糊余口。”《礼记·大学》载有所谓“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注:关于《礼记》各篇目的时代,我们从钱玄之说,见《三礼通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钱玄认为《月令》、《王制》、《盛德》、《明堂》、《保傅》、《礼察》等为明显的秦汉之作,《礼记》中的多数篇目则为战国时的作品。)郭沫若先生曾据三句兵考证盘铭应为“兄日辛,祖日辛,父日辛”(注: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金文丛考》。收录于《沫若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是因铭有泐损而误读。《礼记·祭统》又载有所谓“卫孔悝之鼎”的很长一篇铭文,该铭与今存世古彝铭文例大体一致,虽文字多处经后人改易,但“必录自古器无疑”(注:郭沫若:《汤盘孔鼎之扬榷》,《金文丛考》。收录于《沫若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以上所引铭文可以说明当时人们有引用古铜器铭文中语句来佐证自己观点的习惯,自然东周(至迟在战国)人们对古铜器铭文就有了一定的研究。《礼记·祭统》还说:“夫鼎有铭,铭者自名也,自名以称扬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后世者也。”从所述铭文内容来看,应该主要是对西周时期铜器铭文内容的总结。
汉立以后,随着古文经书在西汉初期的重新出现,促进了一些人研究当时已不通行的“古文”。《史记·封禅书》记载,武帝时“上有故铜器,问少君。少君曰:‘此器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已而案其刻,果齐桓公器。一宫尽骇,以为少君神,数百岁人也”。《汉书·郊祀志》记载了宣帝时美阳得铜鼎献上,有人认为应存之于宗庙。当时任京兆尹的张敞好古文字,把鼎上的铭文释读为“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赐尔旗鸾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对扬于天子丕显休命。’”张敞据鼎出于歧东周人旧居之地,认为此鼎是周王褒赐大臣,大臣子孙刻铭颂扬祖先功烈藏于宫庙之器,所以不宜存之于宗庙。张敞不仅释读了铭文,且据铭文内容研究了铜器的用途,据出土地推测了铜器的时代。《汉书·艺文志》杂家类中记有“孔甲盘盂”铭文二十六篇(可惜没有把铭文载录下来),可见班固也是留心古铜器的学者。《后汉书·窦宪传》记载和帝永元元年九月窦宪伐匈奴,南单于于漠北“遗宪古鼎”,其铭为“仲山甫鼎,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东汉古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自序中说:“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说文解字》中收有古文四、五百字,许慎当时肯定重视并参考了前代的铜器铭文。东汉郑玄著有《三礼图》一书,其内容应当有一部分是有关先秦青铜器的,可惜已佚。从后来北宋初年聂崇义据郑玄等六家旧图参互校订加以集注的新定《三礼图》来看,其中所绘商周铜器多与实物不合,但或可窥见东汉《三礼图》的一些面目。
南朝梁武帝时倡导学术,当时有一些学者对古文字和古青铜器有研究。《梁书·刘显传》载:“时魏人献古器,有隐起字,无能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有滞凝,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梁书·刘杳传》记载刘杳和沈约讨论宗庙牺樽问题,沈约用郑玄旧说,认为牺樽上刻画凤凰尾,现无此种器物。刘杳却认为:“此言未必可,按古者尊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顷魏世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贼曹嶷于青州发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物,知非虚也。”刘杳据出土先秦古青铜器驳郑玄之说,体现了他对古青铜器有研究。梁江淹作《铜剑赞》(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梁文卷三十九。),在序中他据出土实物和文献,认为古兵先用铜,在周秦之际铁逐渐代替了铜。这应是对古铜、铁兵器研究的结果。梁虞荔的《鼎录》和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则辑录了有关铜器的一些文献记载及传说材料。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期,不仅经济发展了,史学、经学也有很大的发展。而作为经学组成部分的“小学”中的古文字则与古铜器及其铭文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必然促使一些学者对古铜器的研究。玄宗时的史学家和经学家韦述在其《信州录事参军常曾古鼎歌》中云:“江南铸器多铸银,罢官无物唯古鼎。雕螭刻篆相错蟠,地中岁久青苔寒。”(注:《韦苏州集》卷九。)诗中谈到古鼎的纹饰——螭,所述纹饰与东周铜器大致吻合。《新唐书·杨收传》载:“涔阳耕者得古钟,高尺余。收扣之,曰:‘此姑喜角也。’既劀试,有刻在两栾,果然。”杨收先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研究古钟的,他自然识得古钟上的铭文才能验证其推测“果然”。宋人陈思《书小史》卷九“颜昭甫”条记载颜师古之侄颜昭甫“为天皇曹王侍读。曹王属有献古鼎,篆字二十余字,举朝莫能读,昭甫尽能读之”。“举朝莫能读”说明此古鼎应为先秦时的铜器。宋王应麟《玉海》卷八八“器用鼎鼐”类载:“开元十三年十月壬申,万年人王庆筑垣掘地,获宝鼎五,献之。四鼎皆有铭,铭曰:‘垂作尊鼎,万福无疆,子孙永宝用。’”此鼎的内容和文例与周代铜器一致。
从文献看,自东周至汉唐,不断地有人对先秦青铜器进行一些初步的研究,所涉及的内容可归纳为几方面。其一为铭文的载录,如《左传》所载谗鼎之铭、正考父鼎之铭,《礼记》载所谓“汤之盘铭”及“卫孔悝鼎铭”,《后汉书》所载仲山甫鼎铭。其二为铭文的考释,如张敞对尸臣鼎铭的考释,其考释水平应该说是比较高的。其三为古铜器时代的考证。李少君考定的“齐桓公十年”之器,应该是据铜器本身铭文所载而定,张敞考定尸臣鼎为周器,则是从器物出土地和历史背景的结合而定。其四为古器纹饰的描述,如《吕氏春秋》所述周鼎上的纹饰,韦述诗中所描述的古鼎上的花纹。此外,可能个别学者已利用古青铜器来研究礼制,如郑玄。我们在文献中还可以看出,自东周至北宋以前的这段时期中,文献中涉及古青铜器研究的记载是零星的,只是个别学者偶作研究,没有人系统搜集和整理古青铜器,没有系统的专门的研究方法。清代学者阮元将先秦至唐时古人对古铜器的认识态度总结为“三代时,钟鼎为最重之器,故有立国以鼎彝为分器者”,“自唐至汉,罕见古器,偶得古鼎,或改元,称神瑞,书之史册,儒臣有能辨之者,世惊为奇”(注:阮元:《商周铜器说》下,《研经室三集》卷三。)。这种三代认为是“重器”、汉唐(尤其是汉)认为是“神瑞”的看法,势必影响到人们对古铜器的研究,使研究难以科学化。可以说从东周至汉唐,古青铜器的研究还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系统的学问,只是青铜器研究的萌芽时期。
二
经唐末五代之乱后,宋朝统治者提倡经学以恢复礼制,促进了对与古代礼制有关的金石实物的研究;同时由于当时地主文人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朝廷士大夫均热衷于古代礼乐器物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另外,宋代造纸、印刷业、墨拓技术都得到了显著发展,这就使金石学兴起并风行起来(注:夏超雄:《宋代金石学的主要贡献及其兴起的原因》,《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这样, 有一部分学者就把很大精力投入到了对古青铜器的研究中,真正可以称为青铜器研究的学问是形成于宋代的。
见于文献的宋人研究青铜器始于真宗时。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乾州献古铜器,状方而有四足,有铭文二十一字。真宗命儒臣考证,句中正和杜镐验其款识,识为史信父甗,其铭为“维六月初吉,史信父作鬵甗,斯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注:《金石录》卷十一·二“甗铭”引《真宗皇帝实录》。)。
据翟耆年《籀史》记载,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僧湛洤著《周秦古器铭碑》,著录有古青铜器,是宋代有关青铜器最早的著作。
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宋仁宗诏令秘阁与太常出所藏三代钟鼎,为太乐制作礼乐器的参考。又诏墨器款以赐宰相,这是文献记载的彝器墨拓之始。当时丞相平阳公命杨元明为铭作释文,编为《皇祐三馆古器图》一书,所收共十一器(注:《籀史》卷上“皇祐三馆古器图”)。
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刘敞作《先秦古器图》,共收十一器(注:《籀史》卷上“刘原父先秦古器图碑”。)。刘敞开了私人著录铜器的风气,其所收之器为他私人所藏。从《公是集》和《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所引的几件器物来看,此书有器物图,有铭文,还注明器物得于何处,并有简略的铭文内容考释。
约在神宗年间,李公麟编纂了《考古图》一书(注:《籀史》卷上“李伯时考古图”。)。此书有器物图、铭文和一定的考释。《籀史》说此书当时“天下传之”,且“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伯时为李公麟的字。
可惜上述四书已佚。另外,宋代有关古青铜器但已佚的书还有胡公俛的《古器图》、李公麟的《周鉴图》、董伯思的《博古图说》、赵明诚的《古器物铭碑》、晏溥的《晏氏鼎彝谱》、王楚的《钟鼎篆韵》、薛尚功的《广钟鼎篆韵》、佚名的《绍兴稽古录》等(注:容庚:《宋代吉金书籍述评(续)》,《学术研究》1964年第1期。), 这些书的原貌现在已不能确知。
宋代有关古青铜器现仍存的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类:
1.图铭类 此类书既有器物图,又著录铭文,有吕大临的《考古图》、赵九成的《续考古图》和宋徽宗敕编、王黼等纂的《博古图录》。
《考古图》是现存年代最早且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目列共224 器,除铜器外,还收了少量玉器,所著录的是当时官廷及私人收藏的古器。作者把三代器和秦汉器分开,并按形制和器用进行了一些分类。每器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和重量,对有的器物的铭文和时代作了一定的考证,对收藏处和出土地可考的也加以说明。此书所定器名有很多错误,但在青铜器著述的体例上已很完备,后世的许多青铜器著录书都沿袭了该书的编纂体例。
《博古图录》著录皇室在宣和殿所藏的自商到唐的铜器839件, 是宋代铜器著录书中的集大成者。该书把铜器细分为二十类五十七种,每类有总说,论述器物形制、名称、纹饰、用途及渊源,每类器并且按照时代排列。每器皆摹绘图像,勾勒铭文,并记器的尺寸、容量、重量等,或附有考证,花纹也有一些说明。所绘图旁器名下注“依元样制”或“减小样制”等以标明图像比例(明代缩刻本始删去比例)。可以看出此书在著录铜器方法上比《考古图》有提高,另外此书最大的贡献是对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虽然也有错误,但大多正确并延用至今。
《续考古图》是依藏家编次,不别器类,且伪器错出,定名多误,价值远不及《考古图》和《博古图录》二书。
2.铭文集录类 此类书仅录铭文而不附器物图,有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和王厚之的《钟鼎款识》。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共收511器(除铜器外, 还包括少量玉、石器),所收器物铭文主要取自《考古图》和《博古图录》,又旁及它书广为取资而成,宋代所见彝器铭文大多见于此书。此书在编排上首分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又依器类分排,这在编排上有其特点,并有字形字义的一些考证。
《啸堂集古录》著录商、周、秦、汉、唐的青铜彝器及印、 镜共345器的铭文。摹录铭文,注明出自何器,铭文下附释文,但无考证。
《钟鼎款识》著录商、周、汉代59件青铜器的铭文。铭文摹录,每器皆记出土地、收藏者并考释文字。
3.铭文考释类 此类书无器物图,基本不摹铭文,只作器铭及器形考释,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赵明诚的《金石录》、张抡的《绍兴内府古器评》、黄伯思的《东观余论》和董逌的《广川书跋》。
《集古录跋尾》是欧阳修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汉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400多篇,其中铜器铭文有20多篇,每铭皆录释文,考证其要旨。跋尾这种考订和著录金石文字的形式为欧阳修首创,跋尾随题随录,无一定次序,未按时代先后编排。
《金石录》前十卷为铜器和石刻目录,按时代先后顺序排列,后二十卷是对部分铜器铭文、碑刻所做题跋502条。该书仿《集古录跋尾》,但注意到排序的时代先后,所以又有所发展,且赵氏治学严谨、精于鉴别,故此书学术价值较高。
《绍兴内府古器评》共考评了南宋内府所藏古铜器195器, 考评诸器未经分类和必要的排序。
《东观余论》卷上“法帖刊误”有对铜器铭文的考证,有些考订颇有见地。卷下“铜戈辨”则研究铜戈的形制,记戈的援、内、胡各部位名称,说古戈戟是横刃击兵,不可直刺,以驳郑玄之说。
《广川书跋》前四卷为铜器的题跋,也有一定参考价值。
4.字典类 吕大临撰《考古图释文》,这是我国有关金文最早的一部工具书,此书虽自说是释文,其实为字典。该书采用《考古图》所收铜器铭文,共收821字,据《广韵》四声隶字,每字有隶定和反切, 后列疑字、象形、无所从三部分。
除以上所列四类书外,还有一些有关青铜器的书籍。赵希鹄的《洞天清录集》书录鉴定古物的经验,其中有鉴别古钟鼎彝器赝真的方法二十余条,还谈到古代蜡模法铸铜器的过程。张世南《游宦纪闻》一书中有以款识、制作(形制和花纹)辨别古铜器的部分,另外此书对铜器的分类、定名也有一些正确的意见。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中也谈到古铜器,这里就不详述了。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及著作者主观上的原因,宋代学者在对古青铜器的年代考订、文字的考释、铭文内容的论证以及一些器物的定名上都存在着错误和缺陷。但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的贡献也是很大的。阮元说:“北宋以后,高原古冢搜获甚多,始不以古器为神奇祥瑞,而或以玩赏加之。学者考古释文,日益精核。”(注:阮元:《商周铜器说》下,《研经室三集》卷三。)这就使人们脱离了以前对先秦古铜器迷信的态度,也就能够使宋人的研究趋于科学化。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著录及考订器物的类、名。他们开创了一整套较为科学的著录体例,以《考古图》和《博古图录》为代表,这种著录体例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宋人对于古青铜器的分类和定名多有贡献。分类上已注意到把所谓“相类相须”之器放在一起,据器物用途进行了大致成功的分类。在定名上正如王国维所说:“凡传世古礼器之名,皆宋人所定也,曰钟,曰鼎,曰鬲,曰甗,曰敦,曰簠,曰簋,曰尊,曰壶,曰盉,曰匜,曰盦,皆古器自载其名,而宋人因以名之者也。曰爵,曰觚,曰觯,曰角,曰斝,古器铭辞中均无明文,宋人但以大小之差定之,然至今日,仍无以易其说。知宋代考古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注:《观堂集林》卷三“说觥”。)宋人对古青铜器纹饰所定之名,有的今日仍沿用,如《博古图录》所定的饕餮纹、蟠螭纹、蝉纹、云雷纹、夔龙纹等,此外,鳞纹、连珠纹、乳钉纹、圆圈纹也都是宋人最早定的。宋人描述铜器的一些术语,如珥、兽首耳、贯耳、附耳、圈足、方座、援、内、胡等也延用至今。可以说古青铜器研究的基础是在宋代奠定的。宋人对古青铜器的断代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博古图录》卷十四“商祖乙爵”下说:“三代之器,铭载不一,然愈简为愈古,愈详为愈近,此夏、商、周之辨也。”这是总结出的三代铜器铭文的时代特征。《博古图录》卷十八“商饕餮纹甗”下说:“足间所饰饕餮与商甗皆相类,而两耳纯缘文缕至隔,又与‘商立戈甗’无少异,制练精工,非商器不能及此。”这是用形制及花纹的对比来断代。《考古图》卷一“乙鼎”下说:据其“形制文字及所从得(邺城河亶甲城)”推定为商器。宋代学者研究古青铜器基本已脱离了玩赏的层次,而把古青铜器作为研究古文字、礼制及历史的实物资料来看待,这基本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共识。刘敞在他所著书中提出从三个方面研究古铜器,即“礼家明其制度,小学正其文字,谥牒次其世谥”。李公麟认为“彝器款识真科斗古文,实籀学之原,字义之宗祖”,并认为铜器铭文可以“稽证《诗》、《书》百氏,审禘①若符契而已”。吕大临则说:“……非敢以器为玩也,观其器,诵其言,形容仿佛以追三代之遗风,如见其人矣。以意逆志,或探其制作之原,以补经传之阙,正诸儒之谬误,天下后世之君子有意于古者,亦将有考焉。”《博古图录》爵总说中也提出“凡彝器有取于物者小,而在礼实大”。欧阳修说他著书目的为“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赵明诚说:“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无疑。”正是由于有了看待古铜器的先进思想,把金石刻铭作为历史资料来研究,所以才在古铜器的研究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由于宋代有了一批看待古铜器思想先进的学者,并已形成了一套研究青铜器较为科学的方法,出现了一批有学术价值的有关青铜器的著作,至此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才进入了形成期。
来源:《文物季刊》1999年第1期
- 0002
- 0003
- 0002
- 0001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