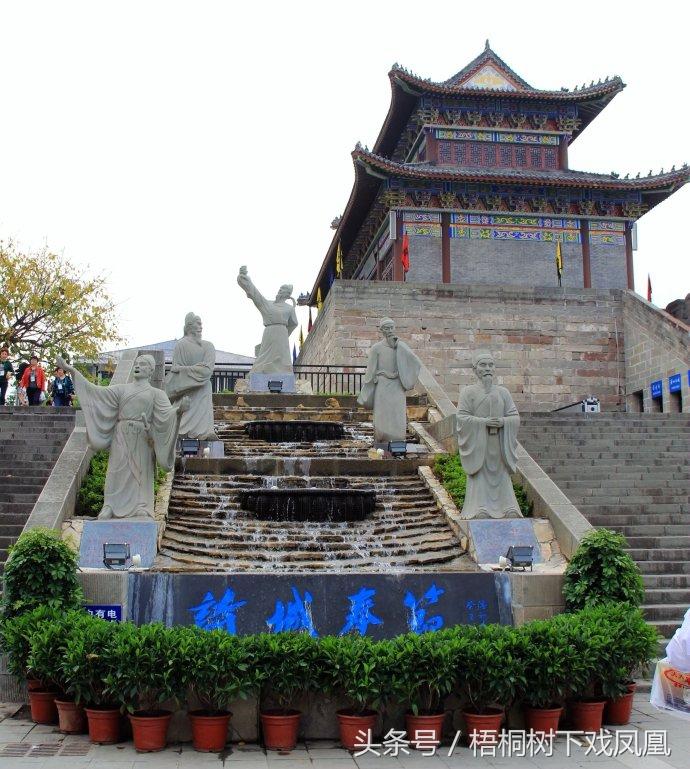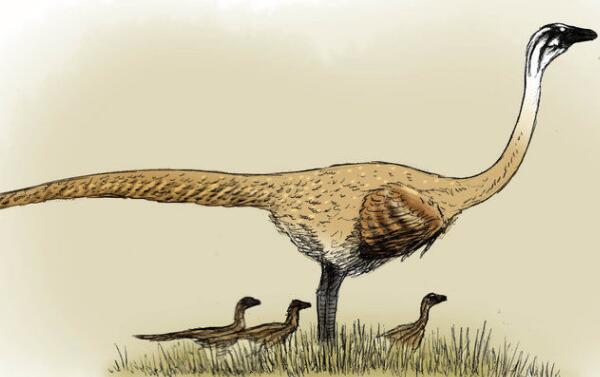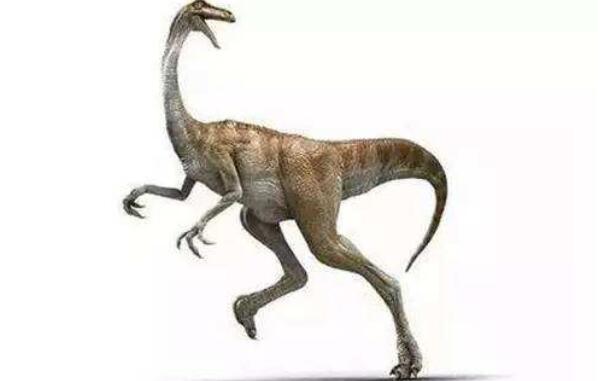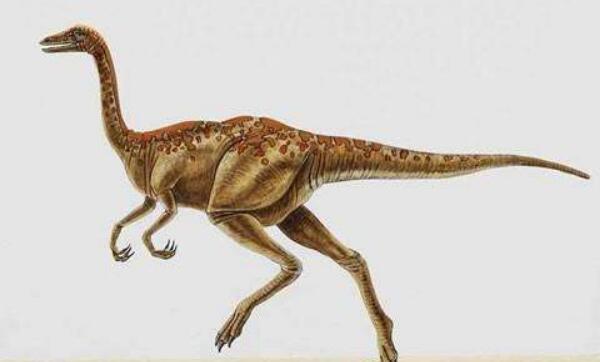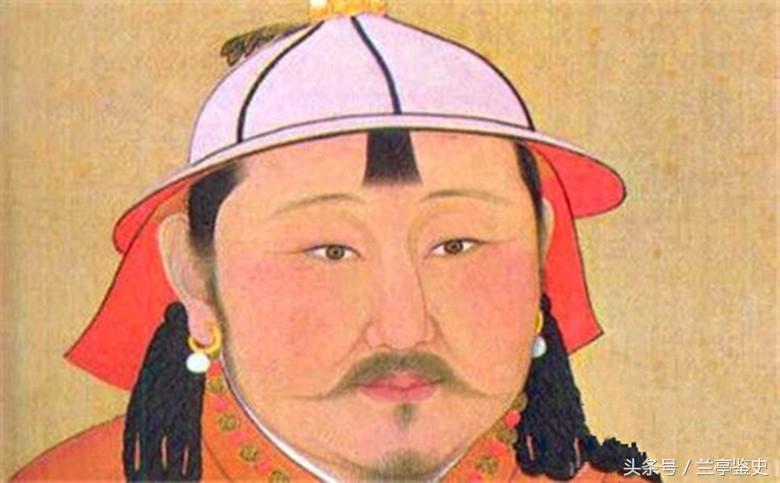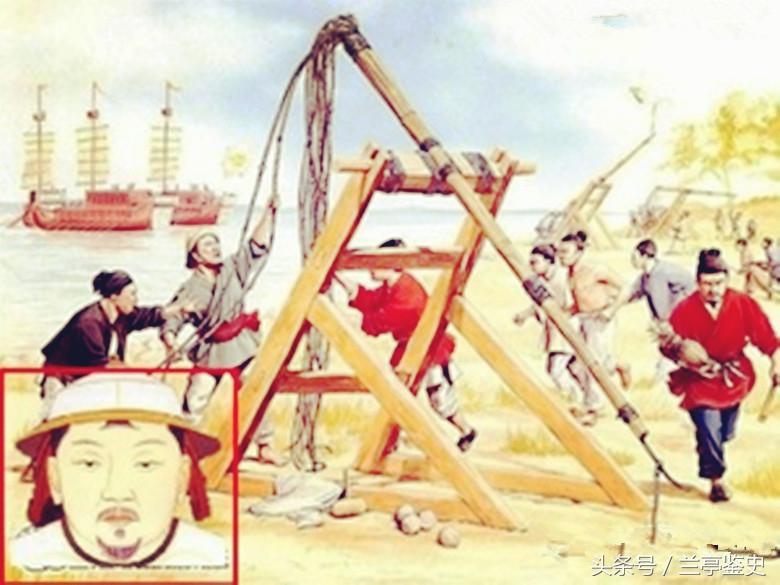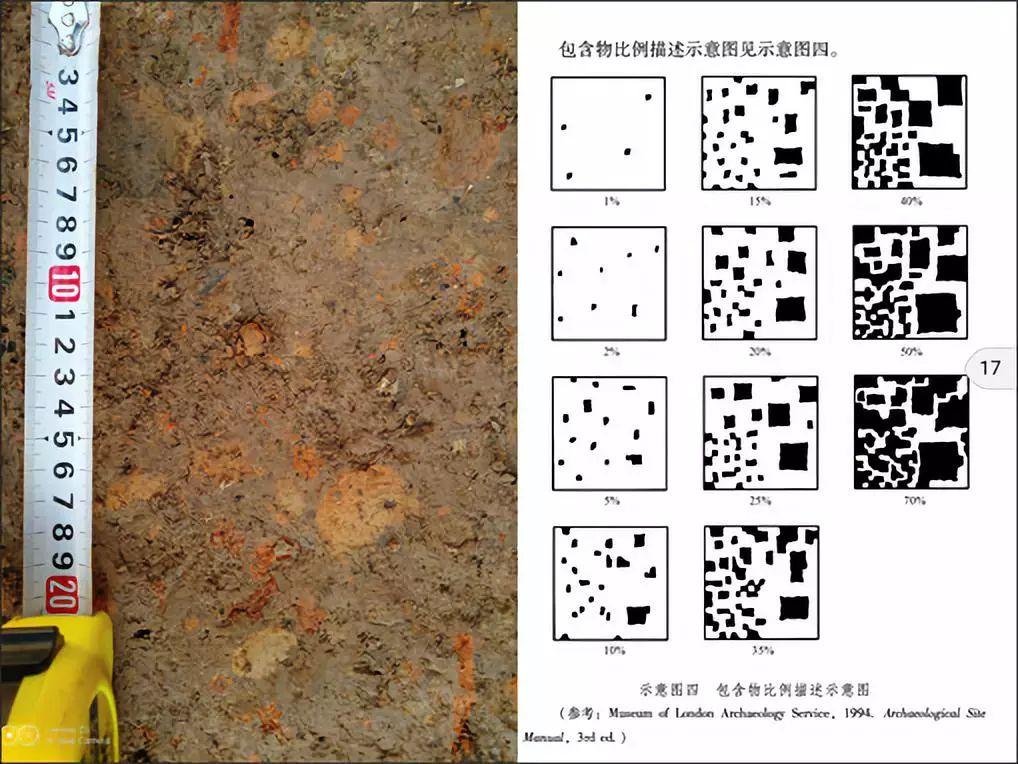张光直:谈考古学理论
(一)
近年来国内的考古学界,主要是受了美国的影响,对考古学的理论有很多介绍与讨论的文章。我在早年曾经对考古学理论有很大的兴趣,在五十、六十年代也写不过不少文章,所以我对国内考古理论的发展,付以密切的注意。前年俞伟超和张爱冰两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六期发表了一篇重头文章,题为《考古学新理解论纲》。去年在十月二十四日的《中国文物报》上,刊登了张忠培先生一篇题为《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对前文加以批评,因为俞、张两位先生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地位,这两篇文章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
英美两国考古学理论近年的突破飞跃性的发展,始于二次大战后,酝酿于五十年代,而起飞于六十年代。我正好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哈佛和耶鲁两大学进修和教书,在这次发展的过程中,可说是一个参与者,对那次考古学在理论与方法上的革新的前前后后是相当熟悉的。今天看中国考古学界也似乎正在理论方法上酝酿一次大革新的前夕,想将我这个在美国参加过类似的一次大革新者事后的回顾和检讨写一点下来或可供国内考古界同仁借鉴与参考。
首先我想应该将英美(尤其美国)六十年代起飞的大革新的始作俑者弄清楚,很多考古学史家用宾弗(LewisBinford)作为所谓“新考古学”的创始人,这是不正确的,向美国传统文化史派考古学开第一炮的是当时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作助理教授的三十六岁的柯菜德克罗孔(ClydeKluckholn),他在1940年出版的《马雅与他们的粼族》这本书里写了一篇十页长的文章,叫《中美洲研究在概念上的结构》,这篇文章有这样一段话:
“首先,让我记录下来我整个的印象是中美考古学这门学科里面的许多学者都只不过是稍微改革了一点的古物学家而已,对一个对这些非常专门的领域来说是一个外行的人,似乎有很多在细节本身上为了细节本身的目的象着迷了似的滚来滚去……在任何一个学科里,不时都应该出现在比较高度的抽象水平上写作的书籍或论文来主张各个范畴的资料与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上有何意义,照我的坦白的意见,中美专家在这方面的工作少得可怜……假使考古学家和民族学家简直还没有开始向他们自己提出来“就怎么样”(sowhat),各个研究基金会和其它研究经费的来源已有提出这个问题的迹象,除非考古学者把他们的工作当作了解人类行为的一般性的研究工作的一部分来从事,我恐怕没过几代以后他们会发现他们自己会给人看成阿鲁都斯赫胥黎笔下一生献身于撰写三个叉的叉子的历史的那位仁兄一类的人物”。
克罗孔批评的对象是“中美考古学”家,但他主要的目标是当时美国考古学界的一位领导人物,阿福瑞祁德(AlfredV.Kidder)。祁德是卡耐基研究院考古部的主任,在哈佛时曾作过梁思永先生的老师,也是克罗孔的老师,克罗孔能如此严厉地对他的老师的考古作法加以批评,而两人一生到1960年克氏先逝为止一直保持密切的友谊,美国学术风气与学者风度可见一斑。
克氏对考古学家只重研究器物的细节而忽略人类行为的批评,在战后促成了他手下一位研究生瓦尔德泰勒(WalterW.Taylor)博士论文《一篇考古学的研究》(《美国人类学者》杂志五十卷第三期附刊,专刊第69号,1948年)的出版。泰勒这本书可以说是新考古学的宣言,他也和克罗孔一样批评了以祁德为代表的美国考古学传统派,专搞年代学与器物类型学,而不重视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泰勒氏主张用人类学与历史学的方法和理论,研究考古学的资料,特别发明了“缀连法的研究方式”(conjunctiveapproach)这个名词,就是说要研究古代人类的行为,可以试将文化方面的遗物缀连起来,重建文化的有机整体,这本书是美国考古学史上第一次具体地提出来从古物研究古人的方法。
就在四十年代的后期和五十年代的中期,文化人类学者朱理安史都华(JulianH.Steward)写了一系列的讨论文化生态学的文章(后来在1955年集成《文化变迁的一个理论》一书出版,四十年代后期,在史都华的影响之下,华盛顿的史密斯生研究院创立了一个在南美秘鲁进行的一个“维鲁河谷研究计划”,从民族、考古、生态科学、民族史等多方面研究这一个小河谷从史前到现在的人地关系的历史,在这个计划之下,戈登魏利(GordanR.Willey)通过聚落形态的研究,讨论了维鲁河谷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社群的发展和变迁,在1953年出版了他的名著《秘鲁维鲁河谷的史前聚落形态》。这本书公认为泰勒所主张的缀连研究法第一次具体的实用。新考古学派所推崇的宾弗写的《作为人类学的考古学》(1962)的出版,已是九年以后的事情了。
(二)
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全世界的青年人中间都掀起了大改革的风潮,这该如何解释,不是我在这里能谈的问题。美国的一些青年考古学者,接着克罗孔、泰勒、史都华、魏利等人发动起来的新作风,要求考古学走出年代学和类型学的老路,以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程序为目标,使考古学成为社会科学,对当代的问题可以有所启示,但是从六十年代的青年人的眼光来看,四、五十年代的这几位改革考古的先驱者,也是老古董了,宜于忽视,以宾弗为中心的芝加哥大学的几个青年学者的研究生,便另起炉灶,从各科社会科学学科借来一套新名辞将泰勒、魏利等人的考古新方法,重新安排了一下,变出来一套所谓新考古学。
最近十多年以来,中国考古学界与英美考古学的接触日益密切,因为过去孤立很久,忽然看到国外五花八门的新技术、新理论、新方法,感觉非常兴奋,所以国内有不少考古工作者,也要在九十年代的中国作四、五十年代美国所做的工作,就是说将考古超越年代学和类型学,超越遗址遗物的叙述,而要进入社群的分析,行为的复建,和一般社会科学原理的形成,我觉得这是非常合理的希望,是将中国考古学向前推进的动力,我觉得今日的中国考古界的气氛很象六十年代美国考古学界的气氛:积极、开放、创造,剔除陈腐,充满希望,许多年轻人整装待发。
中国今天考古学要找寻新的道路,与美国当年比起来要占一个很大的便宜,因为美国这条路已经走了三十多年,今天回顾一下,知道哪条路是康庄大道,哪条路是死路一条,哪条路是近路,哪条路是冤枉路,中国考古学界可以参考一下他山的经验,不妨学其精华,但不必蹈其覆辙。
我先说说在我的意见里,哪些是最危险、最浪费的“覆辙”。美国考古界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所犯的最大的错误,是让宾弗的“新考古学派”唯我独尊,排除异己,自认全国考古界的唯一的正确的路线。大部分的公私学术基金会的评审人员,多是新考古学派的学者,提交的考古研究计划,如果不是用新考古学的观点来设计的,就通不过,有许多比较传统的考古学者,被迫使用新派的名词,把不是用新考古学的观点设计的研究计划,写得象是新考古学派的,只换汤不换药,结果常常得到所申请的经费。但是大部分非新考古学派的学者,就不去这些基金会申请经费,而去想别的办法,有时他们便筹不到经费,或者需要改变原来计划,这二十年中间,美国作了不少新派的田野和室内工作,收获极为令人失望,而且怨声载道。这种情形到了八十年代,新考古学唯我独尊的地位衰微之后才逐渐改善,从这个经验所得的教训,是在一个社会里面的考古界最好采取“理论多元化”的政策,让各种不同的考古学的途径,互相竞争,或彼此取长补短,不必一定要辩论到你死我活,现在美国的考古界可说就是这种情况。
上面说到传统的考古学者,如果使用新考古学的名词,常常可以鱼目混珠,用新名词,说老内容,这是回头看看新考古学的发展史可以汲取的另一个反面教训,就是新名词不一定有新内容,如有新的想法,不要马上就发明一个新词,以表其新,新内容多半可以用很普通的语言表示得很清楚的。新考古学在很多的意义上可以说是国王的新衣,在不少新考古学的著作里,使用了许多从别的学科(如生物学、统计学、电脑学、哲学、商业学等)搬来的新术语,读者看不懂,不敢说话,怕说了给人知道他看不懂,其实作者也未必懂,新考古学者写的书一般都不易懂,而以英国的英年早逝的大韦克拉克氏为最。他在1968年出版的名著《分析考古学》是我平生所看到的考古学书籍文章里面最难懂的一本,从那本书一出来我就向同事承认里面有很多段(常常一段就是一个句子)我看不懂,但是很多人都称赞他这本书是考古学的一个突破,可是今天跟我说他们也看不懂的人越来越多了,这种一窝蜂走时髦不务实的风气希望中国的青年考古工作者不必模仿。
最后值得提出的一点所谓覆辙的教训,是美国新考古学派对资料本身鄙视态度和对所谓“程序”(或社会科学的一般适用性的原则)的过分强调。他们不相信考古材料本身有任何的价值,考古材料只是验证先行假设的原理原则过程中偶然的产物,现在的考古学者回顾三十余年以来的新派考古工作,既看不到任何有真正突破价值的新的社会科学原理原则,也找不到很多丰富可用的考古新资料,这三十年来美国考古学最丰富的收获,照我个人的意见,是许多非新考古学派但是不断采用新的技术和方法的考古学者所积累的许多新资料和用新旧资料研究所得的对古代社会文化及其发展的新看法。
(三)
上文说过我们要汲取六、七十年代美国新考古学的精华,一个风靡一时令一代青年若疯若狂,紧紧追随的学派,必然有它引人之处。新考古学最大的吸引力,现在看来,是情绪上的。四十年代的琐碎性的考古学,以资料为最终目的,以年代学的建立为研究目的,以类型学为唯一方法的老考古学,早已在克罗孔、泰勒等重视社会科学一般原理的人类学者的批评下,暴露出来它应用范围的局限性。在六十年代全球青年不满现实盲目追求理想那个时代背景之下,懂得如何煽动的宾弗等几个年轻学者,登高一呼,指出考古学上必须超越传统琐碎考古作业而达到能够解释人类行为的一般原理,这虽然不是他们的创皿,但他们发明了一套崭新术语,创出来一套自圆其说的理论结构,很快地,一大群青年学者,在宾弗教主的领导之下,在考古学园地里面狂热地耕耘,本来死气沉沉的美国考古学,成为一个活力蓬勃的新天地,在这种气氛之下,美国考古界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领域与新的研究技术和方法。
近二三十年来美国考古学最大的进展可以说是在“技术”上面,绝对年代的断定、古代自然环境和古气候的重建、用遥感和地球物理各种测试技术调查地面下的埋藏、古人饮食的鉴定,还有其它一系列的新科技,将考古学者所能找到的与古人生活有关的资料种类和数量,巨大地增加,对此我们要感谢新考古学对古文化生态学的特别重视。不久以前我在台湾的《田野考古》上写了一篇叫《台湾考古何处去》的文章,其中我建议台湾的考古工作者能够争取达到“理论多元化、方法系统化、技术国际化”的目标,这三条目标,在中国大陆上也可适用,尤其第三项,“技术国际化”,更是当务之急。
“方法系统化”,可以说是美国新考古学最有贡献性的一个特征,传统考古学在解释考古现象时所用的方法,常常是“想当然耳”,或是来自解释者的灵感,多没有系统的方法,新考古学派有一套“假设验证”的明白清楚的程序,其它的考古学者可以对他的结论不同意,但每个人都知道他这个结论是怎样产生出来的。中国考古学者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地层学和类型学,所得的结果基本上有关年代、器物和文化关系,但在人类生活风习、社会结构、经济形态和运作关系,以及宗教巫术等行为的研究,缺乏系统明确的方法,最近在俞伟超和张忠培两位先生带头所进行中的在考古理论上的讨论,希望在这方面有所推进。
看了俞、张两先生的论文,使我想起近年来考古理论论文在中国逐渐增加,所以将美国三十年来考古理论类似的发展中的得失,拣其大者略作介绍,以供国内考古工作者参考、借鉴。俞、张两先生都是我的知交,他们一定知道我这篇随笔没有任何影射的存心。张忠培先生作的陕西华县元君庙的发掘报告公认是研究中国史前时代亲族组织的模范,他虽然在最近的论文中强调地层学和类型学的重要意义,却绝不能比作美国传统考古学的代表祁德。俞伟超先生虽然提倡考古学的新结构,却是中国文明深入研究专业的一员,最近以中国的史博物馆馆长之尊还在主持河南班村的发掘工作,与不与任何一个文明认同而且只讲理论不作考古实践的宾弗教主迥异,他们两位都是理论修养极高的,但注重的方面不同,两人的主张与其说是不同,不如说是互补,这便是我在上面鼓吹的“理论多元化”的萌芽,我自己因为五十、六十年代参加美国考古理论战的经验,对考古理论在中国考古界能达到共识的可能性是不乐观的,甚至可以说我并不以为中国考古界达到理论共识是件好事,因为我担心“唯我独尊”局面的再现,现在俞、张两位重量级的理论家既已出台,看来中国的考古界即将进入一个百(理论)家争鸣的阶段,这是令人十分兴奋的发展,全世界的考古学家都将对此付以密切的注意。
来源:《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8日
- 0000
- 0000
- 0003
- 0002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