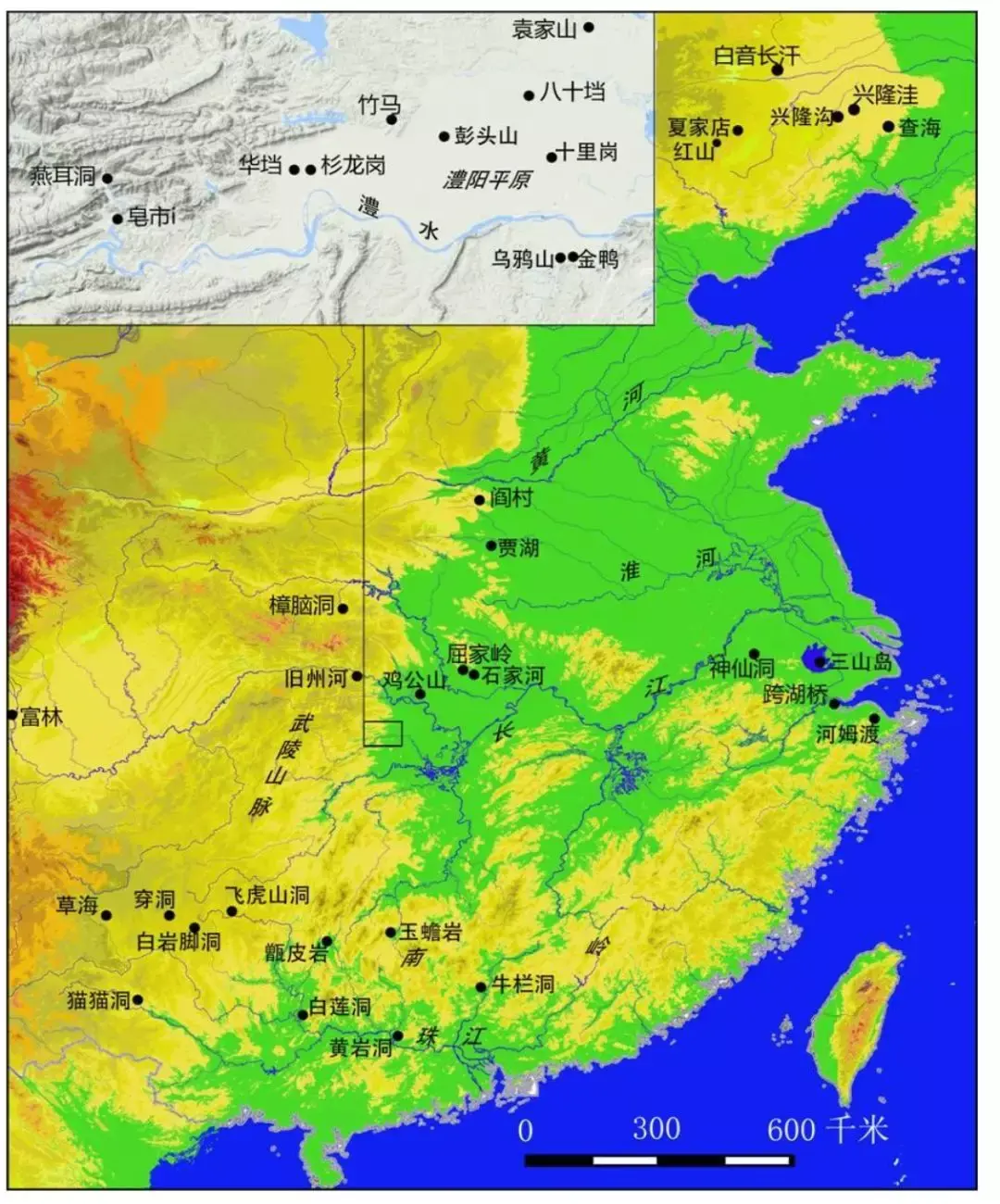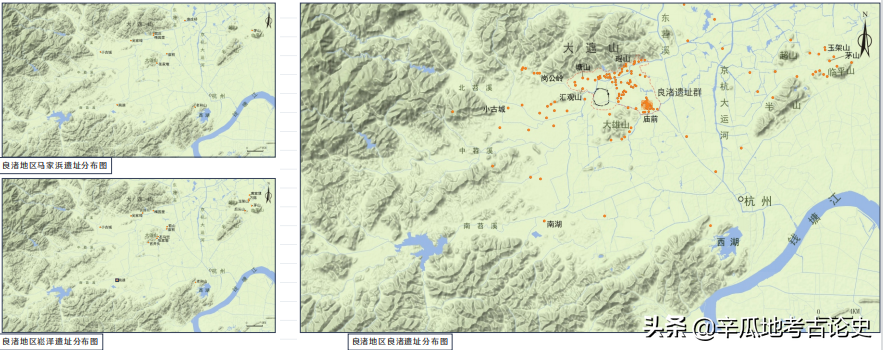邹衡:殷墟发掘与殷商考古学
殷墟发掘在中国考古学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的考古学基本上就是从早年殷墟发掘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新兴科学。殷商考古学,作为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开端于殷墟发掘,并随其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殷墟开始发掘至今已整整六十年了,回顾这漫长的历程,我们也可看到殷商考古学所走过的道路,对于这门学科今后应该如何继续发展将会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有关殷商遗物的研究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早在北宋时期就兴起了金石学,当时的金石学家收录了不少殷商时期的遗物,并进行了初步研究:有的著作不仅记录了器物的名称、尺寸大小等,而且还注意了出土地点,实际上已具备了某些考古学的方法。自清代以来,出土古器渐多,研究已不断深入,尤其在十九世纪末还识别出了甲骨文,这一方面使得金石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另方面又从金石学中逐渐分化出古器物学、铭刻学以及甲骨学等。不过,由于这些材料都来源于传世品,出土情况不明,从而影响了其科学性,使这些学科都不能直接发展为现代的考古学,而这就只有等待科学的田野发掘了。
殷墟的发掘从1928年开始,截止于1937年共进行了15次;而自1950年开始直至今天,殷墟发掘几乎没有中断。这些发掘,从其方法、内容和研究情况的变化;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三个大阶段:
第一阶段,从1928年秋至1934年夏第1—9次发掘,可以称之为开创阶段,又可分为三期:
1928年秋至1929年秋第1—3次发掘为试探期。
殷墟发掘的缘起,是因为河南安阳小屯村曾出土过甲骨,所以第1次开始发掘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寻甲骨。当时的发掘者并不十分了解科学的发掘方法,只是挖了几十个规整而不分地层的探坑,主要采集了甲骨,其他遗物则很少注意。尽管如此,这毕竟是考古工作者首次主动地开掘,总是对以前金石学家完全被动地搜集古物的情况有所突破,而且为以后的科学发掘打开了局面。
第2、3次发掘已有了很大的改进,这就是直接采用了西方的科学考古方法。例如:统一使用探沟开掘,事先并略有规划;兼用文字、绘图、照像记录以及科学测量等;尤其还注意了地层和遗迹的研究。当时曾把小屯地面下的遗存分析为现代堆积、隋唐墓和殷商文化层;并清理出方坑、长方坑、圆坑和墓葬及其葬式(俯身葬);除有字和无字的甲骨外,还采集了一批陶器、玉石器、骨器以及其他兽骨和人骨等。这样,就使得殷墟发掘向科学考古的领域迈进了一大步。
1931年春至1932年夏第4—6次发掘为创建期。这几次发掘最大的进步就是:
一、对整个殷墟遗址做了统一规划,分为A、B、C、D、E、F六个发掘区,以便于计划发掘。
二、正确地运用考古学的地层原理,严格地依土色来划分地层,彻底纠正了以往甚至用绝对深度来划分地层的错误做法。
三、认识了殷墟遗址中的重要遗迹夯土,首次发掘出版筑基址,纠正了过去所谓甲骨是漂流而来、殷墟系水淹形成的错误结论。
四、扩大了殷墟发掘的范围,除小屯村外,还发掘或调查了后岗、四盘磨、王裕口和候家庄等遗址。
这个时期,在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例如:李济曾对殷墟文化做出了三个论证,即殷墟文化层是一个长期的堆积,代表着一个长期的占据;殷墟文化是多元的;殷墟文化是逐渐进步的。这些科学的论断为殷墟文化的分析研究树立了样板。梁思永关于后岗三叠层的报告和论文,首次建立了仰韶、龙山与殷商“三层文化”的年代顺序,明确了殷商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时间地位。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把甲骨文分为五期,并具体指明了各期所包括的殷王,使殷墟遗址有了可靠的绝对年代依据。总之,这些科研成果都具有划时代的学术意义,为殷墟的发掘和殷商考古学的建立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
1932年秋至1934年夏第7—9次发掘为充实期。这一时期无多新创,只是对前一时期的补充,又发掘出一些版筑基址和其他遗迹并遗物等。
第二阶段,1934年秋至1937年夏第10—15次发掘,可以称之为成熟阶段或丰收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1934年秋至1935年冬第10—12次发掘为前期,集中发掘洹水北岸侯家庄的陵墓区;1936年春至1937年夏第13—15次发掘为后期,主要集中发掘洹水南岸小屯村的宫殿遗址区。本阶段主要取得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成就:
在遗址方面,如果说前阶段在遗址发掘中初步解决了地层剖面等纵向年代关系问题,那么本阶段则在纵横相结合的原则下,更多地注意了遗迹的平面排列和分布等横向联系,而且在地层划分上,因为认真观察了平剖面两方面的情况,所以较前阶段的工作更为细致,划分的结果也更加准确。在前阶段,虽然开始了小范围的“平翻”,但基本上还是局限于密集开坑,采用的是(2—40)×(0.6—1.5)米的窄探沟发掘,始终未实现“整个的翻”的设想,因此发掘到的版筑基址不多,只有几处。本阶段广泛使用10×l0米的探方,即全面采用了大规模大面积揭露的先进方法,从而发现了大批遗迹现象,其中有版筑基址50处,窖穴400多个和用途不明的“水沟”30余条,并基本上弄清了它们的结构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在测量、绘图、照相等方面的技术已有进一步提高,至此,遗址的发掘方法已渐臻完善。
在墓葬方面,本阶段也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在侯家庄共发现主要属于王陵的大墓10座和1200多座属于祭祀坑的小墓;在小屯宫殿遗址区也发现了多属祭祀坑的小墓400多座,再加上大司空村等地100余座小墓,墓葬总数已达1800多座,药第于第1-9次发掘所得墓葬总数的三十倍。另外尚有车马坑、马坑以及其他兽葬坑等。通过以上对各类墓葬的发掘,积累了丰富而可贵的经验,使田野操作更加熟练,技术水平空前提高。尤其是大墓的发掘,不仅规模宏伟,计划周全,组织严密,而且工作细致,记录详尽,测绘准确。例如对填土中包含物的处理就极为慎重,不放过每一块陶片和每一残段石块、花骨,给以后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而可靠的资料。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都是值得考古工作者学习的典范。
在遗物方面,其收获已大大超过前阶段。首先是甲骨,本阶段共得18405片,几乎等于第1—9次所得6513片的三倍。特别是127坑,竟出土17096片,其中完整的龟甲将近300版,可以视为武丁时期的档案库。其次是铜器,以往虽有发现,但数量并不多,容器更少,主要是觚、爵之类。第10—15次发掘,无论侯家庄墓地或是小屯遗址都发现了大宗铜器,其中容器器类已有20多种,数量更是以前的数十倍。其他如陶器、玉石器、骨牙器等都有大量发现,其中白陶、花骨、雕石等尤为前9次发掘所少见。
总之,所有这些,把殷墟发掘推向到一个高潮,标志着殷墟发掘已达到相对成熟阶段,同时也为殷商考古学的发展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条件。
第三阶段,1950年春至现在,可以称之为总结与提高阶段,又可分为前后两期:50—60年代为前期,主要是继承前阶段的工作,可称为承袭期;70—80年代为后期,已有某些创新,可称为开拓期。但这两期并不能截然划开,因为这两种性质的工作乃是相互交错进行的,就是说,在承袭中也小有新创,在开拓中也不能离开继承。
前期的发掘曾在洹北的武官村、大司空村和洹南的小屯村及其外围的四盘磨、薛家庄、后岗、苗圃北地、孝民屯、梅园庄和北辛庄等地进行。重要发现主要有武官村大墓、苗圃北地铸铜作坊遗址、北辛庄制骨作坊遗址以及小屯村以西的壕沟等。发掘方法基本上承袭了前阶段的,但作坊遗址在殷墟还是首次发掘。另外在大司空村小墓群中曾发现墓上建筑,但当时并未判明。
后期除继续在武官村和小屯村外围的后岗、孝民屯等地发掘外,也曾在小屯南地和村北做过重点发掘。重要发现主要有武官村的大片祭祀坑、小屯南地数千片甲骨和“妇好墓”及其400多件铜器,其中容器210件已超过第1—15次发掘所得的总和。在方法上首先是车马坑的发掘有了显著进步。车马坑的发掘需要高水平的田野技术,难度较大。在前阶段和本阶段前期虽然都发现了车马坑,但都只剔出了马骨架,车的痕迹仅大体勾划出轮廓。70年代以来,吸取了辉县、陕县等地的经验,先后成功地在孝民屯剔出了两座车马坑,完全可以复原当时的车制。其次,在小屯南地的发掘中,除了注意甲骨出土的地层外,并注意了同层出的陶器,改变了以往使两者脱离的状况,增强了发掘的科学性。再之,在墓葬发掘中,注意了墓群的分组,并对其所反映的社会组织进行研究做了新的尝试。
在科学研究方面,本阶段已有很多新的进展。值得庆幸的是,第1—15次发掘的正式报告已陆续在台湾出版,并初步做出了总结;1950年以来的发掘也不断地出版了大型报告。所有这些资料的发表,都大大充实了殷商考古学的内容,同时也促进了对殷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综合研究。
殷墟文化的研究,首先必须解决分期与年代问题。关于这个问题,董作宾早已在甲骨文方面基本解决。但是,长期以来还无人对整个殷墟文化进行综合分期研究。直到50年代,才有人在这方面进行试探性的研究,而到60年代并已初步研究出比较全面的分期体系。由于70年代“妇好墓”的发现,不仅影响了甲骨文的分期,而且更直接地影响了陶器特别是铜器的分期,至今仍然意见分歧。尽管如此,殷墟文化的发展脉络基本上还是清楚了。这不能不是自殷墟发掘以来所取得的新的重要研究成果。
正是在上述的条件下,北京大学历史系商周组编写出版了综合性的专著《商周考古》,其中商代部分对殷墟发掘和殷墟文化的研究做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对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状况进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对于复原晚商历史的真实面貌做了新的探讨,由此而初步形成了殷商考古学的体系。当然,殷墟的发掘还在进行,在今后的考古实践中还会不断提出新的问题,殷墟文化的研究还要不断深入,殷商考古学还要不断发展。总之,更多的科学工作在等待我们去做,让我们为建立更加完善的殷商考古学体系而共同努力。
来源:《中国文物报》1988年9月9日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