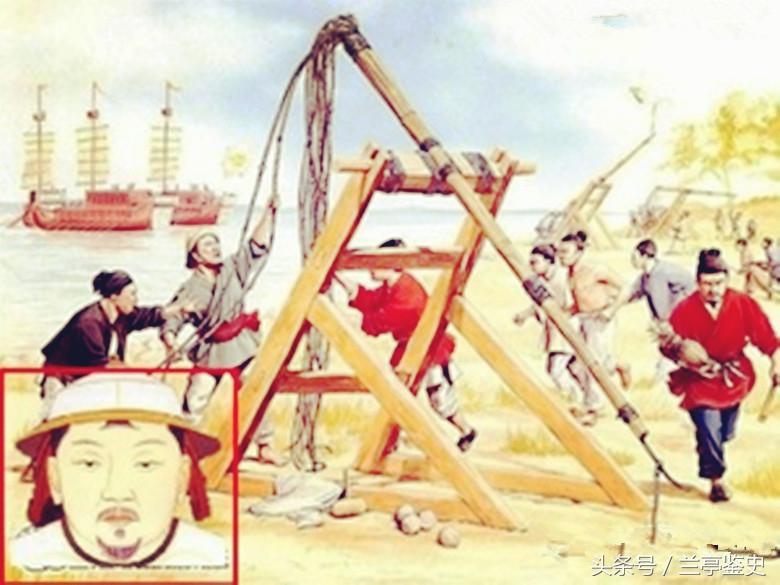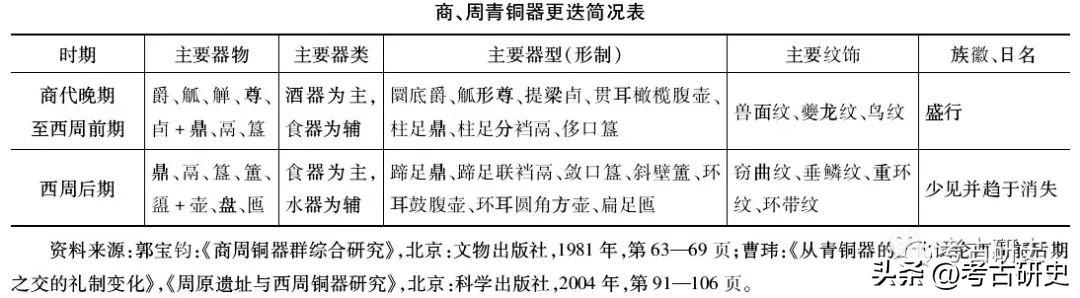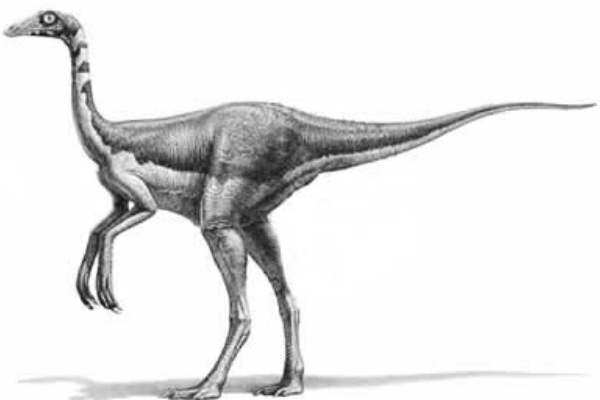王仁湘: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与程序问题
考古发现的诸多史前遗存,有地域的不同,也有时代的区别,为了描述它们,研究它们,需要给它们进行命名,给一个合适的代号,这样就确立了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纯粹是考古学家的主观行为,常常表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还会引发许多争论。为了避免分岐,达成共识,需要确立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根本原则,还要设计体现这些原则的关键程序。
在考古学界,50年代以来对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有过一些讨论,对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也有较为全面的认识,且主流意见都较一致,在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和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尤其是在实施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时,有时表现出的分歧非常明显,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考古学文化的深层研究,现在应当是开始考虑解决这些分歧的时候了。
夏鼐“命名四原则”
命名是人类的文化活动,也是科学活动,命名有文化法则,有科学法则。科学研究上的任何一种命名过程,都要遵循一定的规范,要有一定的原则,不然的话,每个科学家都可以我行我素,以至于政出八门。当然由于科学总是在不断完善和发展,包括命名规范在内的诸多研究方法也会随之产生变化,也会一步步完善。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问题,产生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如天文学为发现的新星命名,有时是用发现者的名字,有时又用另外某一科学家的名字;生物学为新物种命名,有的用发现的地名,有的则用发现者的人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也有类似问题,命名原则也需要进行规范。
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19世纪的考古学研究就已开始关注。考古学家为了区分一个地区处于前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遗存,采用最早发现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遗存的地点作为各个分期的名称。后来为了进一步区分同一地区时代不同和时代相近而内涵不同的考古遗存,产生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过去用作分期名称的地名就很自然地变成了考古学文化的名称。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过程,如安特生将甘肃史前文化最初划分为六期,分别以最先发现的小地名命名为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寺洼期、辛店期、沙井期,它们在后来多数都被中国考古学家改称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
夏鼐在指导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过程中,非常强调这样一个国际考古学界的惯例:考古学文化“大多数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的遗迹的小地名为名”(注: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这个办法最早是19世纪60 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在研究旧石器文化时开始采用的,实际上借用的是地质学上地史分期的命名办法。20世纪以后,这种命名方法被考古学家们普遍采用,中国包括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在内的考古学文化就是这样命名的。
中国考古学界对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的研究,实际上迟至本世纪50年代末才真正展开。1959年为了编写《新中国的考古收获》,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一些研究人员感到考古学文化的命名问题比较突出,为解决这个问题,夏鼐先生当时提出了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些原则,并写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公开发表(注:夏鼐:《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考古》1959年4期。), 中国考古学界一直以他的意见作为指导,命名了一系列考古学文化。
夏鼐先生当时提出了一个成熟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条件,主要有以下三条。
第一,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的特征。根据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说法,一种文化必须有一群具有明确特性的类型品。夏鼐先生特别强调一群的特征至少要在两个不同的地点出现,而一群特征的类型品,却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东西,但它们的内涵须很明确,例如陶器,“必须是用某种质料以某种制法制成的某种(或某几种)形式的和某种(或某几种)纹饰的陶器”,不能是空泛的灰陶或彩陶之类。
第二,同一类型的遗址最好发现不止一处。只有在较多的遗址发现同一特征的文化遗存,才能了解它的分布范围,认识到它的主要内容。
第三,必须对这一文化的内容有相当充分的认识。同类遗存中至少有一处遗址做过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充分认识它的特征,认识构成这一文化的各种“元素”,不能仅依采集的少数材料匆促命名新文化。
这便是学者们常说的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三原则”。由于夏鼐先生的提倡,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大体采纳了柴尔德的观点,是以一群具有明确特征、经常伴出的类型品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的标志。而最终命名的确定,正如夏鼐先生所说: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如何命名,似乎可以采用最通行的办法,便是以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不论是一个墓地或居住遗址)的小地名为名。”我们可以将这个说法归纳为下面的第四个命名条件:
第四,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命名。古文化遗址的命名,一般是用遗址所在的小地名,这实际规定了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确定考古学文化的名称,既要求是第一次发现的遗址,又要求是有典型代表性的遗址,面对几种选择时,定名要适当。
如果加上这一条,“三原则”就成为了“四原则”。考古学界时常也采用以地区或流域命名、以特征遗物命名、以地名加前后缀命名、以族别命名等方法,而以“小地名命名”的方法使用最为普遍。
安志敏先生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的“考古学文化”条目,其中有一节论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他列举了以小地名命名、以地区或流域命名、以特征遗物命名、以地名加前后缀命名、以族别命名的几种方法,但并没有明确认定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些具体原则。他也这样强调:“一个考古学文化包括有不同的文化因素,例如某几种特定类型的住宅、墓葬、工具、陶器和装饰品以及某些特定的工艺技术等”;“至少应对该文化的一处典型遗址作较全面、深入的研究”,如果将这些话作为命名原则理解,与夏鼐先生的“四原则”精神应当是一致的。
命名分歧
对于夏鼐先生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原则,中国考古学界在很长时间内并没有明显的异议,但也不是毫无保留地全都接受,在理解过程中和在实际操作时都没有避免分歧,甚至在对有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时出现了矛盾现象。
1985年,严文明先生在论文《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中(注: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文物》1985年8期。),讨论的两个问题之一就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理论, 很自然地涉及到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他提到中国考古学界使用过特征命名法,还有典型遗址命名法和族别命名法等,以典型遗址命名法采用最为普遍。对于“典型遗址”的理解,严文明先认为随着研究的深化,一个考古学文化最初确定的典型遗址会显得并不典型,也不一定处于文化分布区域的中心,甚至出土遗物代表不了整个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时间上也只是处于整个文化的某一发展阶段,逐渐地这样的遗址就不再成其为典型遗址了。由于更典型的遗址会不断涌现出来,一些研究者就产生了更改文化命名的动议,严文明先生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如果每发现一个更好的遗址就更改一次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势必不胜其烦,并且容易引起混乱。因此名字可以不改,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和由以命名的遗址的具体情况则应在新的发现和认识的基础上加以重新认识和说明。”他所强调的是约定俗成,不要频繁更改命名,但对一个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可以重新进行概括。
1987年,张忠培先生发表了《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一文(注: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详论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他赞同以典型遗址命名,但对典型遗址本身又有自己的理解。他说:“作为考古学文化依以命名的典型遗存,还应考虑其是否具备以下三方面的标准:(一)反映古代居民的活动具有一定的规模以及遗存的保存情况较好;(二)遗存在年代及地域上具有质的相对稳定性,而不是那些过渡性遗存;(三)考古工作有一定的质量及规模。……三项标准是一整体,缺一不可,关键是能否在遗存的研究中概括出对其所代表的考古学文化的稳定的基本内涵、特征及性质的认识。”按照这个理解,对典型遗址的选择是考古学文化命名的一个关键所在,而且考古发掘的规模与质量又是确定典型遗址并由此识别考古学文化的关键。张忠培先生还注意到,典型遗址并不包括整个遗址的全部内涵,它也并不一定包纳了整个文化的内涵,不能一有新的发现便否定原有的命名。这个认识原则上与严文明先生相同。我们特别注意到,张先生虽然肯定了用“第一次发现的典型遗迹”命名的正确性,却并没有强调“第一次”,而是在“典型”遗址的选择上作了充分阐述。
安志敏先生在前文提及的那个条目中说,“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名称的作法,应用得最为普遍”。不过近年有研究者对以典型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做法,提出了否定的意见。如张国硕先生发表《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一文(注:张国硕:《论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方法》,《中原文物》1995年2期。), 对考古学文化的各类命名方式进行了评述,提出了几条具体意见:一是坚持以首次发现的遗址命名,避免以“典型遗址”命名。条件是这个遗址须经正式科学发掘,而且还应是最早公布的遗址。二是在同一遗址首次发现了几种考古学文化,采用“地名加分期命名法”,如某某上层文化、某某下层文化等。三是按时代或族名命名考古学文化,要严格限定在历史考古学范围内。四是摒弃以区域或文化特征命名的方法,也不采用双名命名。
对于以典型遗址命名的缺点,张国硕认为它“违背了国际上以最初发现地命名考古学文化的最普遍原则”。典型遗址和首次发现的遗址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命名时在对它们的选择上往往会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典型遗址的选择很难把握,不同学者认定的典型遗址往往不同,命名自然不会一致。实际上一个真正典型的遗址是很难发现的,最先发现的遗址又一般不会“最具代表性”,所以不必以典型性和代表性来苛求,也不能随着更典型遗址的发现而不断更换考古学文化名称。
原则应当说是明确的,可是实际操作起来并不容易,在不同的研究者之间往往对同一文化遗存出现不同的命名。如二里头文化的命名,经历了由“洛达庙类型文化”—“东干沟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命名,文化命名采用了“淘汰”方式,最终达于“优化”。当然,这种命名的变更实际上是一个不断更换文化的“典型遗址”的过程,它尽管并不符合通行的命名原则,可大家又都乐于接受,这种现象在中国考古学文化的命名中并不少见。
又如对鲁南苏北前大汶口文化的命名,在《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就有两种提法,在条目“青莲岗文化”中将这一时期的遗存命名为青莲岗文化,而在条目“北辛遗址”中则命名为北辛文化。在同一部书中出现这样的分歧提法,是不正常的,这不能认为是学术气氛自由的体现。除了在文化内涵理解上本身存在距离以外,在这一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上体现的问题,正是“第一次发现的遗址”和“典型遗址”两个选择上出现了矛盾,命名为青莲岗文化遵守了“第一次发现的遗址”的原则,而北辛文化的命名则采用了“典型遗址”的原则。
在对考古学文化的实际研究中,我们还感到夏鼐先生当初在阐述考古学文化命名原则时,尚存在有其他一些不十分完备的地方,例如他没有明确陶器群的量化问题,没有强调一个器物群至少应包括几种器型,是3种或是5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只论1—2种器物的相似与否,与论3—5种器物的最后结果区别是很大的,如果取量太少,那么就有可能会出现将一个文化的范围划得比较宽泛的结果。仰韶文化分布范围划得越来越大,就有这方面的原因,有的研究者往往只看遗址中某一种或两种器型与彩陶纹饰存在,就将它归入大仰韶的范畴之内。
我们回过头去看一看,发现研究者们在考古学文化命名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在仰韶文化的研究上表现最为充分,包括对仰韶文化整体及类型的命名,都没有一致的意见。从最初安特生将黄河流域的彩陶遗址都列入仰韶文化的范畴开始,仰韶文化的内涵就很不单纯,经过众多学者的研究,到50年代前后,安特生关于仰韶文化“六期说”的系统被否定,裴文中先生和夏鼐先生等对甘肃地区史前文化新命名了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净化了仰韶文化。
50年代以后,随着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表现有仰韶文化某些特点的遗存在更广的范围内有更多的发现,研究者们在认知过程中又提出了许多地区类型的命名。人们将仰韶文化的分布划分为关中—陕南—豫西—晋南区、洛阳—郑州区、豫北—晋南区、丹江区、陇东区、张家口区、河套区等几个大的区域,根据区域特征提出的地方类型命名有:在陕西有半坡类型、史家类型、泉护类型、半坡晚期类型、北首岭类型;在山西有东庄类型、西王村类型、西阴村类型、义井类型;在河南有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后岗类型、大司空类型、阎村类型、下王岗类型、王湾类型、秦王寨类型;在河北有下潘汪类型、三关类型、钓鱼台类型、南杨庄类型、百家村类型、台口类型;在内蒙古有海生不浪类型;在湖北北部和陇东发现的仰韶遗存,归入豫陕仰韶类型,没有新的类型命名。从50年代末期命名半坡和庙底沟类型开始,仰韶文化类型的命名已增加到了现在的二三十个之多,这些纷繁的名称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仰韶体系。
关于仰韶文化类型的研究,有的比较一致,有的则分歧较大。有的类型的分布,在地域上有较大的跨度,如关中—陕南—豫西—晋南,主要分布的是半坡、庙底沟和西王村类型,在这几个类型的划分上,学术界的意见大体是一致的。有的学者似乎为了摆脱大仰韶体系,提出了分解仰韶的命名方案,有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大河村文化等独立的新命名。如丁清贤先生曾经提出过一个解决仰韶文化命名的方案(注: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3期。),虽是反响不大,却有一定的意义。他认为现在所谓的仰韶文化,还并不是一个考古学文化。他援引尹达先生1963年撰写的《新石器时代研究的回顾和展望》一文中的话说:“仰韶文化,是由仰韶遗址而命名的,这是较早的名称,就约定俗成地沿用下来,但是对仰韶村本身所含的内容并没有弄清楚,从新的资料所反映的现象分析,这一名称并不是那么确切,也还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丁清贤研究后认为,通常所说的仰韶文化实际上是包含着三支各具特征、不同源流、分布范围不同的遗存。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渊源于李家村、老官台文化,发展为客省庄二期文化;河南地区(包括鄂西北不包括豫西)的仰韶文化渊源于裴李岗文化,发展为龙山文化;河北、豫西、晋南和关中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渊源于磁山文化,分别发展为后岗二期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仰韶文化只能包含分布在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河南和陕西地区的仰韶文化,应以新的考古学文化命名,因为西安半坡遗址和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面积大,出土物也丰富,而且在所分布的两个地区也最具有代表性,建议把河南地区的仰韶文化命名为“大河村文化”,把陕西的仰韶文化命名为“半坡文化”。
对仰韶文化作这样的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要让学术界很痛快地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仰韶文化的命名问题,仅以河南地区而言分歧也不小,仅仅是大河村的命名问题,也并不容易统一。廖永明先生在《大河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注:廖永明:《大河村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1989年3期。), 提到了大河村遗址命名上的各种分歧意见:严文明先生认为:大河村一、二期的文化面貌与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有许多相同之处,可以看作是庙底沟类型的“东方变体”,而三、四期则属仰韶文化晚期的秦王寨类型。安志敏先生等学者则认为,与“秦王寨类型”相当的大河村三、四期遗存经过正式发掘,有明确的地层依据,比秦王寨遗址更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所以这类遗存应以“大河村类型”代替“秦王寨类型”的名称。巩启明先生等学者则认为没有易名的必要,大河村三、四期遗存之间存在着较大差异,第四期遗存具有由仰韶文化向河南龙山过渡的性质,因而主张把二者区分为两个类型,即三期仍称秦王寨类型,四期另命名为大河村类型。
在《河南考古四十年》中(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河南考古四十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更有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大河村文化的命名。分布在郑洛地区、豫西南地区和豫北地区的处在裴李岗和龙山文化之间的新石器遗存,都从仰韶文化中分割出来,全部归入大河村文化范畴。在大河村文化之内,又划分出大河村、下王岗和后岗三个类型,大河村类型又分为王湾和大河村两个亚型等。
仅以仰韶文化一例,就能对中国考古学中文化命名存在的问题获得足够的了解。显然,如果不是因为命名的原则还不够明晰,或者已有的原则还欠完备,就是研究者在对原则的理解上距离太大。
我们可以预言,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仰韶与仰韶文化,还将继续是中国考古学文化中辉煌的名字。不过,随着考古学文化命名方法的完善,下个世纪对仰韶文化命名的重新整合,也将不可避免,对其他一些存在命名分歧的考古学文化也是如此。
考古学文化“三要素”
什么是考古学文化?根据以往的研究,考古学文化有一些要素,这些要素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基础。
夏鼐先生在1959年的论文中讨论命名原则之前,就考古学文化的含义进行了诠释,说它“是某一个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的文化在物质方面遗留下来的可供我们观察到的一群东西的总称”。这似乎不是一个太严格的定义,夏鼐先生后来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的前言中,又进一步写下了这样一些话:
在史前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在研究考古学文化时,必须注意各类遗物之间以及遗物与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例如,通过广泛的调查、发掘,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及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等经常从某种特定类型的墓葬或居住址中同时出土,这就证实了它们之间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陶器与陶器之间的共存关系,也是陶器与石器、骨器、装饰品之间的共存关系,而且还是陶器、石器、骨器、装饰品等遗物与墓葬、居住址等遗址之间的共存关系。这样的共存关系,便构成了史前考古学上的“文化”,称为“考古学文化”。
调查发掘工作表明,“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这也即是说,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就可以命名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简而言之,考古学文化必须具备鲜明的时空特征。
安志敏先生在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的“考古学文化”条目中,为考古学文化所下的定义是:“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表示考古遗存中(尤其是原始社会遗存中)所观察到的共同体”。这样的说法,与夏鼐先生的观点没有差别。
张忠培先生在《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一文的开篇,就作了这样的阐述:“分布于一定地域、存在于一定时间、具有共同特征的人类活动遗存,在考古学上,一般称之为考古学文化”(注:张忠培:《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严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中说,考古学文化“专存在于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具有一定特征的实物遗存的总和”(注:严文明:《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两个问题》, 《文物》1985年8期。)。
由上面所引论述可以看出,致力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的定义基本没有什么分歧,在一定时期、有一定范围、有一定特征的考古学遗存,便属于一个考古学文化。
对考古学文化的这个定义,本质上是来自柴尔德的1929年《史前史时期的多瑙河》。对此加拿大人类学家布鲁斯·炊格尔有这样的评述:
柴尔德从未设想给考古学文化下一个正式定义。被当作定义的东西是不完整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会使人产生误解。在《史前史时期的多瑙河》里,柴尔德指出,一个文化,“是某些类型的遗存——罐类、工具、装饰品、埋葬习俗、房屋形制——它们经常一起反复出现……”。我们假设这种组合体是我们今天称为“人”的物质的表现。文化包含有特色的内容,它占据了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而且受到时间的充分限制;以至于可以认为它的遗存再现了一个社会存在同步阶段。(注:布鲁斯·炊格尔:《时间与传统》,104页。三联书店,1991年。)。
虽然柴尔德的定义并不算很明确,但在他的著作中仍然还是指明了考古学文化的时间、空间和特征这三个要素。
考古学文化“三要素”中,最核心的是“特征”,它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确立的最重要的依据。过去的研究表明,文化的时空维度常常是通过文化特征的研究推导出来的,它们在最初并不是完全真实的,结论甚至往往还会出现错误,因为我们不可能在一个新文化确立的时候就对它的年代跨度和分布范围有准确的判断。
如果要求将某一个考古学文化的“三要素”都研究透彻以后,才能给予一个合适的命名,似乎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研究的对象实际上等于没有确立。事实上,一旦开始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它的名称就应当基本确立了,虽然我们习惯于在以后的争辩中还会更换新的名称。过去许多文化的命名都没有真正满足“三要素”的要求,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在最初命名时,都没有真正确立它们的分布范围,也没有真正明确它们的绝对年代,考古学界最初对仰韶和龙山文化的年代估计与后来知道的结果有很大的差距。几乎没有一个考古学文化是真正满足了“三要素”之后才赋予它们名称的,同样也没有一个考古学文化不是在实施命名的许多年后才拥有了它们的绝对年代和分布范围图。
如此看来,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条件要求可以不必过分强调,实际上在考古学文化的“特征”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这样的时空条件,没有一定的时空框架,特征是不会存在的。这样说,并不是讲时空问题不重要,而是说它们是附属于“特征”的,特征的确认,才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关键。这其实也是柴尔德当初阐述考古学文化时的观点,他仅仅明确提到的是“经常一起反复出现”的遗存,这正是考古学文化的内涵之所在。
所以,在对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进行命名时,最需要考虑的是它的本质特征,至于它的时空框架,可以而且应当在今后的研究中去逐步建立。
如果我们的认识能统一到这一点上,那么就可以对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再作一番思考。究竟是选择首次发现的遗址还是典型遗址,关键应当看所取的遗址是否体现了所要命名的考古学文化的基本特征。
如果是首次发现的,而且又是比较典型的遗址,用它来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自然是皆大欢喜。对于不典型的甚至是很不典型的首次发现的遗址,它可能无法完整或者大致完整地体现一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文化命名的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如果还要用它来作为一个文化的命名,对于这一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不会有什么益处,相反还会引发出许多不必要的论争。如果考虑在同类遗存中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遗址来命名,那效果就会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一些大文化中文化类型的命名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这些次一级别的文化类型在命名时,往往经过了对典型遗址的选择过程,多数类型的名称选择的并不是首次发现的遗址,而是典型遗址。当然,也只能说是比较典型的遗址,我们不能肯定今后不会发现更典型的遗址。
“命名确认”程序
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一般而言,并无明显分歧,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应当并不复杂。可在实际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操作上还会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并不一定在有了统一的认识和公认的原则以后,就一定会出现一致的结论。比如在典型遗址的最后选择上,甚至在首次发现的遗址的确认上,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为了解决一定会出现的矛盾,在诸多原则之外,我们设想未来应当有一个“命名确认”的程序,研究者除了有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建议权,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命名。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或是考古学会有可能成立的史前考古学之类的分会,或者在这样的学术机构中成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这个命名委员会,是个权威学术组织,负责审定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经过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可以出现在其他论著或教科书中。这个设想似乎显得有点不切实际,但确实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可以避免各自为阵的重复命名、本位命名、感情命名等随意命名现象,相信它对于维护考古学文化的纯洁性会起到一定作用。
命名的确认,首先是在“原则上进行审查,并根据学术研究的进程适时修订。未来的原则也许是“四原则”或“五原则”,原则既定,就不能网开一面。其次,中国考古学会可以考虑制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操作程序”,内容至少应包括这样几项:1、 有考古学文化命名动议的学者,应当向相关学会提出正式的“命名申请”,提交专门的命名委员会进行审议;2、命名委员会适时召开会议进行审议, 申请者可到会申述,允许不同观点争鸣;如命名条件不成熟可暂缓议决,如意见有明显分歧可采用某种方式表决;3、符合原则的考古学新文化的命名, 在最后通过后要编号发布“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确认书”之类的公告。
其实,夏鼐先生和尹达先生早在1959年论及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意见时,已经提到过这个意见,只是一直没见实行。他们的意见是,当有几个文化名称需要选择时,“最好采用群众路线办法来解决,例如可以在全国性考古会议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称,展开争辩,然后得出基本一致的意见,决定采用某一名称,以求统一。”否则,就不能命名,也不能采用这样的文化命名。
几十年来,我们在一种很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命名了一大批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多数是适时的,也是恰当的,促进了考古学研究。但也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存在严重分歧,研究者往往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将来一旦成立了专门的命名委员会,应当就已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清理,及时废止那些不适当的命名。
我们在上面还提到,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事实上还能通过淘汰过程实现优化,从这一点看似乎“命名确认”程序显得有些多余。但是这个“自然”淘汰过程显得过于漫长,未来的世纪中不能容有这样长久的等待。
来源:《文物季刊》1999年第3期
- 0000
- 0002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