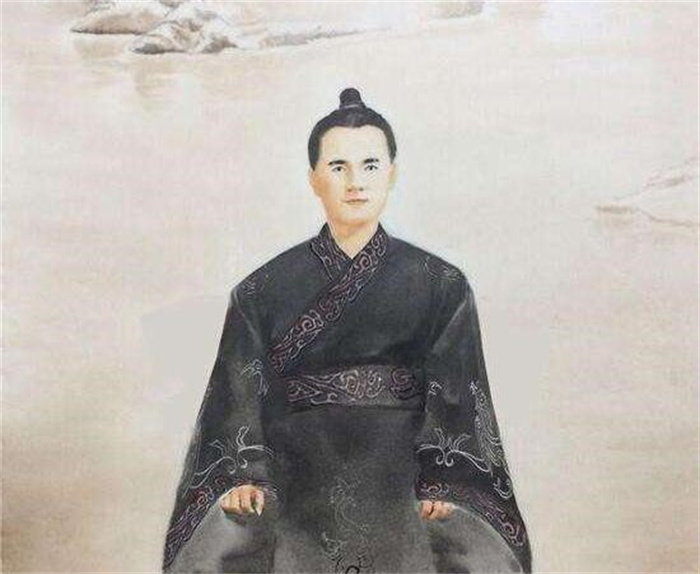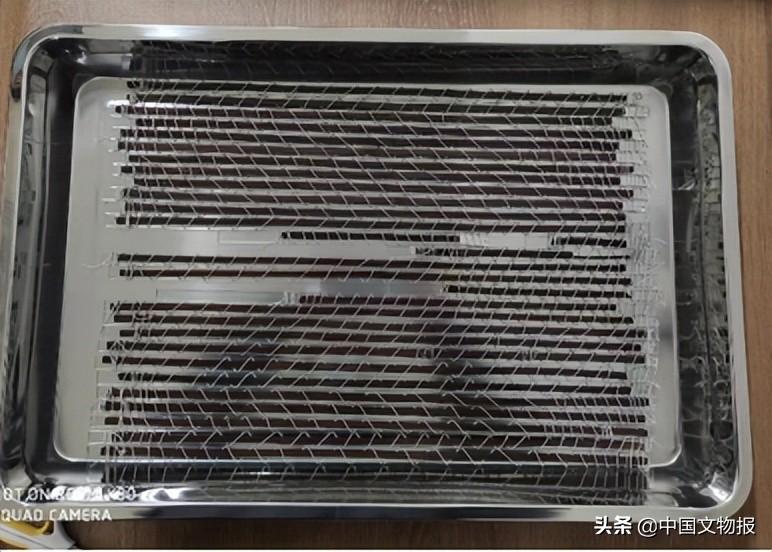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历来有种种猜想与说法。最近几十年,尤其是近30余年,中国古人类学和中国旧、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新发现与研究成果层出不穷,为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因而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的研究,可谓近20年中国人文科学独领风骚的一个领域。
在师辈启迪和社会需要推动下,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从东北史地之学和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过渡到对中华民族进行整体研究,关于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起源,成为我用力较多的一个方面。1984年,阴法鲁教授约我为其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化史》撰写第一章:《中华文化起源和中华民族形成》。1987年我开始就《中华民族的含义与中华民族起源初探》和《中华新石器文化的多元区域性发展及其汇聚与辐射》发表文章。这些文章是受苏秉琦教授关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类型理论的启发,用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和对中国旧、新石器时代文化进行梳理的初步成果,对中华民族的结构也提出了“多元集合体”的观点。不久,费孝通教授召我,说已读过我关于中华民族含义及中华民族起源的文章,指出“中华民族是多元集合体”的提法有些模糊,应是“多元一体”。1989年费老发表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著名论文。自此,我便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核心理论,先后协助费老出版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及其修订本、《中华民族研究新探索》,并出版了个人专集《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在我关于中华民族研究一系列论文陆续发表以来,学术界师友给了我多方面支持,尤其是费老、苏老,都是我在大学时期的老师,他们一再勉励我坚持研究,并指出综合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和古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材料与研究成果一炉共冶,从而得出自己的体会,这种研究方法也很对头。这些支持和勉励,使我在自己学业根底不深且研究条件有种种缺陷的情况下,坚持了20年,取得了一些成果。
总括20年来,关于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已发的一系列文章,其要点包括:
1.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
2.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起源,具有鲜明的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的发展特点。
3.中国的农业从起源时期起就呈现出南北不同,最近10余年的考古发现证明南北农业起源均可追溯至距今万年左右,与世界农业起源最早的各地区大体同步。
4.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萌芽,可追溯至距今5000余年以前。在距今5000年至4000年这一个千年纪,考古学界称为“古文化古国”,我称之为“王朝前古国”。这个历史时期,在考古学上大体相当龙山文化期向青铜器时代过渡;在社会发展方面,是从无阶级社会向有阶级社会过渡;在文化发展方面,是从无文字向有文字文明过渡;在国家和民族发展方面,是从部落联盟向国家和民族形成过渡;在中国文献记载方面,是从黄帝至尧舜的五帝向夏商周过渡。因而,我所说的“王朝前古国”时期,是王朝前夜、文明初曙、国家雏型从萌芽至发展的漫长过程,也可以说是一个历史时代。
5.中华文化的发展在不同区域是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导致了不同区域间的互补关系,是中华文化产生汇聚和向一体发展的动力因素。
6.中华文化的发展延绵不绝,连续而未有中断,与其他任何古老的文明相比都是不同的。但,中华文化又是兼容并蓄的,是一种“和合”的文化,故其“内聚”和“外兼”是对立统一体。正因为中华文化的这些特性,造就了中华文化的丰富与长久生命力,也是中华民族结构形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原因。
应该说,这些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和早期发展特点的认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成就,它凝聚了多个学科数辈学者的共同心血,除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外,还有历史学和民族学的成果。大致说来,对我影响较大的前辈学者除上面已提到的老师,还有顾颉刚、傅斯年、蒙文通和徐旭生等先生。若说我自己还有些成绩的话,可以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时代在进步,而我们站在前辈学者的肩上,故比前辈看得稍微远一些;二是新中国的考古学成就可以说是突飞猛进,日新月异,我们有幸看到这么丰富的地下资料,眼界和认识自然会提高一些。
另外,多年来,曾从事历史地理和民族史研究的经历对我的帮助也甚大。历史地理的背景,使我在历史的研究中时刻关注与空间的关系,考虑空间问题时又会照顾到历史的时序;而民族史的背景,使我更关注“纵横时空网络”中族群关系的变化,由历史事件真实性的探求深入到探讨“中国性”(Chinese-ness)诸问题。
我始终相信,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后人必定要超过前人,所以我的这些认识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被不断补充和发展,我自己也随时准备更新认识,向更高的目标前进。
一
关于中国人及其文化的来源,长期存在外来说和本土说、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争辩[1]。以往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和流行学说的局限,科学发现也不充分,因而很难得到有说服力的认识。如关于中华文明的种种西方起源说,就带有明显的虚构、编撰和假想成分。而且,从18世纪的法国人约瑟夫·德·古尼(甚至更早的17世纪)开始,止于20世纪初叶的安特生之前,所有西来说的立论都是站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立场之上(包括古埃及文明中心说和西亚古文明中心说等)[2]。 考古学发展起来以后,有的研究也不免有种种偏见和浅见。
当前,中国境内古人类学的材料已相当丰富和系统,旧、新石器时代(特别是万年以来)的考古发现在中华大地上已是“遍地开花”。这些系统而又丰富的发现,文化性质明确,内涵清楚,相互关系也易于得到证明,用来与中国文献记述的远古神话传说互相印证,已经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和多元特点,以及新石器时代以来由多元向一体发展的特点。
人类起源于何方?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个中心?学界尚在不断探讨之中。中国古人类学研究有近80年的历史,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坎坷中取得了喜人的进展:人类起源各阶段的人骨遗骸化石材料,在中华大地上均有所发现,且分布广泛;人类起源序列各主要环节,在中国古人类学的发现中没有缺环。从体质特征方面观察,早期智人阶段已经出现了向蒙古人种(黄种人)方向演化的萌芽;到晚期智人阶段,以柳江人(广西柳州市)和山顶洞人(北京周口店)为代表,蒙古人种出现南北异型的分化现象。
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早期遗存有不同于他处的特点,北京人遗址文化堆积之厚、内涵之丰富早已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瞩目。可以说,世界上普遍承认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存在,得益于北京人遗址的丰富文化内涵和鲜明特点。河北省阳原县泥河湾盆地小长梁遗址的遗存,其特点也是非常突出的。主要表现在石器的制作和加工上,大型球状石核以外,其它石器普遍较小,一般重约5~10克,最小仅有1克左右。但数量众多,已发现有2000多件!据其形制可分为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锥型器等,反映了当时人们过着狩猎的生活。从这些细石器的精细程度推测,在此以前其文化当有漫长的发展过程,人们必然具有足以保证技术传授、模仿、改进和继承的语言交流。长江流域也发现了一系列腊马古猿材料。将这些材料综合起来考虑,有理由推断:人类起源当在四五百万年以前,中国处于人类起源地区的范围之内[3]。
早期智人及与之相应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分布范围已明显扩大,尤其以黄河中游及其支流渭河、汾水流域,所发现的地点为多。属晚期智人的几乎遍及整个中华大地,与其相对应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和地点,在现今行政区划的各省均有分布,仍以黄土高原较为密集[ 4]。
从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分析,中国南北的旧石器时代文化既具有不同的风格和传统,又具有共同的特点。至迟到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部出现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发展倾向。
综上所述,人类起源的问题还会进一步争论下去,但人类起源仅非洲一个中心之说,过去就已受到一系列新发现的质疑。最近在中国山西曲垣发现的世纪曙猿化石,对“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论断提出了新的挑战。因资料的限制,“基因证据”的研究也远未解决人类起源到底是一个中心还是多中心的问题。当然,讨论人类的起源不能局限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狭小范围之内,应该站在全球和全人类的视角来讨论和分析问题,实际上,中国人的起源问题正是人类起源问题的一部分。另外,假若“人种”的划分是可行的,中国人的起源问题还涉及到蒙古人种的起源问题。虽然,目前尚难确断中国是否是人类起源的中心地区,但已知的材料已经证明中国是蒙古人种的故乡。谁也无法否认,中华大地上的这些人类化石,从直立人一直到现代人,其体质形态的进化表现出明确的连续性。
将化石材料与现代中国人体质形态的基本特点相比较,也能发现中华民族的历史连续性。正如吴汝康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中国人具有的四大突出特征:(1)铲形门齿,中国人为98%, 白色和黑色人种相加也仅为5%;(2)印加骨,出现的比率也相当高;(3)面部扁平;(4)下凳圆枕[5]。因此,中华民族,包括其主体——华夏/汉民族, 从总体上来说,其远古祖先应是那些起源于中华大地,并留居于本土继续创造历史的人们。
故,中华文明的起源具有鲜明的本土特点[6]。
二
对中华大地上万年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许多学者都有极其精彩的归纳和总结。从这些归纳和总结中,可明显看出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第二个特点,即由多元起源而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传统史观认为,中华民族是从黄河中下游最先发端,而后扩散到边疆各地,于是有了边裔民族。司马迁综合春秋、战国诸说,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这样表述:由于共工、欢兜、三苗、鲧有罪,“于是舜归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这种史观影响甚大,直至近现代也还有一些学者相信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仅起源于黄河中下游。过去史家总是用“礼失求诸野”的观点来推测区域间文化发展变化的关系,把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当作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这就是本土起源说中的一元说。
一元说的论点已被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发现所推倒,中华文明不是从黄河中下游单源扩散至四方,而是呈现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又互相渗透,反复汇聚与辐射,最终形成为中华文明。我在许多场合都讲到过这样的认识,在《中华民族起源学说的由来与发展》一文中,曾对此加以总结,提到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与近代以来史观变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当然,多区域不平衡发展的观点并非我的发明。1927年,蒙文通先生首先将古代民族分为江汉、河洛和海岱三大系统,其部落、姓氏、地域各不一样,其经济文化也各具特征[7]。傅斯年继之于 1930 年和1934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定中华文明来源的两大系统。1941年,徐旭生先生将中国古代民族概括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三大“古代部族集团”[8]。
上述诸说,对考古研究的促进是非常明显的。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创办人,中国学者进行的最早的考古发掘就是由他支持下开展的。他关于“新史学”的主张对古史研究有相当的推动。徐旭生先生参加过1927年的西北考察,1959年又开创了“夏墟”调查和“夏文化”研究。后来,考古学界开创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研究的苏秉琦教授就是他的学生,追溯起来,受他的影响最大。
众多的考古发现,以及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研究成果已经昭示: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对于中华文明的多元性特征,我在《中华文明研究初探》一书的第118 页曾做如下概括:“中华大地上的远古居民,分散活动于四面八方,适应各区域不同的自然环境,创造着历史与文化。旧石器时代已显出来的区域特点的萌芽,到新石器时代更发展为不同的区系,各区系中又有不同类型与发展中心。而神话传说中,远古各部落所奉祀的天帝与祖神及崇拜的图腾也有明显的区域特点。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起源多源特点的科学基础。”
我所以强调考古与神话传说的“相互印证”,就是为了改变“考古自考古,神话自神话”的两分局面。中国没有发达的神话,或者说,中国的神话体系与西方是不同的,它是古史的传说,即古史的一部分。诚如徐旭生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掺杂神话的传说(Legend)与纯粹神话(myth)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古史传说并不是纯粹的神话。但中国的古史传说至迟到战国时期就有了总结和归纳,表明不同来源和世系的各区域文明渐渐向一体发展。
下面就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区系划分,其与远古部落集团的对应文化,及各区系间文化的内外互动、融汇等内容,详为叙说。这是综合我以往发表的多篇论文而成的,同时针对考古研究的新认识(如碳14重新测年数据),结合最近的考古发现作了相应的补充和修订。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新发现的考古学文化密集分布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图之上,我关于中华民族起源及其发展结构的总体认识也因之日趋精确和完善,这些不断丰富的新知识更细致描绘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本土特点、多元特点以及由多元向一体汇聚的特点。
三
据地质学的研究,我们知道公元前1万年左右进入冰后期, 开始了全新世,人类的历史也由此进入新的纪元。
1987年8月,考古学家在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一处距今约10000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了一批陶器、石磨盘、石磨棒等,还发现了一些植物种子,说明农业已经萌芽[9]。此外, 江西的仙人洞下层和广东的玲珑岩和西樵山等地也都发现了万年左右的文化遗存。虽然我们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约公元前6500年之前)只有上述零星的发现,但已足以说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多元起源特点。就旧石器时代文化的面貌和我国比较优越的地理自然环境等条件来推测,我相信未来定会有更多的发现,只是时间的早晚问题。我国也是探寻农业起源的最佳地区之一。
迄今为止,我国已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有7000余处。7000年前的考古学文化几乎已是遍布全国各地,如辽河流域的查海文化、兴隆洼文化,山东泰沂地区的后李文化,关中地区的大地湾和老官台文化,中原地区的裴里岗和磁山文化,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长江中游的彭头山文化、城背溪文化和石皂文化,等等。这些新的发现不仅突破了“黄河一元中心论”的传统认识,更丰富了“满天星斗说”的内涵。苏秉琦先生将这些成果归结为“区系类型理论研究”的必然:“用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对中国古文化进行重新认识,大大开阔了考古学家观察古代各族人民在中华辽阔国土上创造历史的视野,开始了从文化渊源、特征、发展道路的异同等方面进行考古学区系类型的深入探索,过去那种过分夸大中原文化、贬低周边古文化的偏差开始得到纠正,这就为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的突破,开拓了新的思路”[10]。
这与我几年前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中华民族的形成角度对考古发现的归纳基本一致。我在许多场合又进一步强调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主张中华民族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其族体结构与文化发展是以“多元起源,多区域不平衡发展,反复汇聚与辐射”的方式作“多元”与“一体”辩证运动的。这是我试图结合区系类型划分问题,进而对文化发展变化进程的分析和归纳。这个过程是相当复杂的,在具体的细节方面认识还会有不断的反复,但总的进程应是如上所概括的那样。
所以,我坚持认为有两点贯穿了中华文化发展的全过程:一是中华文化的多元区域性不平衡发展,各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各有渊源,又自成系统,分布区域和范围明确,文化内涵和面貌也无法相互重合,可以明显地划为几个独立的文化区系。二是区域性文化呈现向中原汇聚及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双向运动。
上述认识不仅来源于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划分,更来自对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故不妨将具体的划分结果及其认识作下列复述[11],并依照新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对以往的叙述稍作修改。
1.黄河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黄河中游区,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中原为中心,北达河套及长城沿线,南接鄂西北,东至豫东,西抵黄河上游甘青接壤地带。南头庄文化以下,有磁山(前6100~6100年)——裴李岗文化(前6200~前5500年)、大地湾(下层)文化(前5900~前5300年),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前5000~前3000年)(注:苏秉琦将仰韶文化分为“仰韶文化”和“后仰韶文化”,将洛阳——郑州的“仰韶文化”定名为“王湾一期文化和王湾二期文化”,晋南地区则为陶寺文化。详参《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所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三联书店,1999年,页184~185。),中原诸龙山文化(前2900~前2000年)继之。
与这一区域相对应的为炎帝和黄帝两大部落集团,从中可以追溯氐羌与华夏起源,并且大致可以肯定继中原龙山文化发展的是夏文化(晋南、豫西、豫中)、先商文化(豫北、冀南)和先周文化(关中)。炎黄集团起源之地比较接近,无论从文化还是从地理的因素分析,这两大集团都是有共同起源和共同文化特点的亲缘集团。炎、黄同出少典——有峤氏部落,后世成为异姓相互通婚的不同氏族与部落。我认为黄帝起源于陇山西侧,天水地区为近是。在黄帝集团的发展中,陕北是极为重要的地区。相传,黄帝死后葬于桥山。黄帝并非具体历史人物的私名,其陵园所在就表明了陕北在黄帝集团发展中的重要性,黄帝集团另一个最重要的活动地区是燕山地区。该集团从陕北向燕山地区迁徙的证据已得到了考古学的印证。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文化自渭水下游越过黄河后,沿汾河和桑干河北上,与燕山以北红山文化在桑干河及汾河发源的河北张家口地区交汇在一起。两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促进了文明曙光的出现[12]。
《国语·晋语》说,黄帝有25子,因母不同而别为12姓(实则11姓)。这11姓显然不一定出于同一来源,而是不断融合的结果。故传说中的黄帝谱系有不同的称号,如“轩辕氏”、“有熊氏”等,说明这些后加入的群体还有自己的图腾,但均奉黄帝为共同祖神和天神。“黄帝”既是该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所共享的名号。
炎帝又称赤帝,是炎帝部落集团共同奉祀的天帝,也是该集团大酋长袭用的称号。相传,前后承袭炎帝名号者凡8氏,共530年,最后一位为榆罔氏[13]。炎帝集团起源之区当为陕西境内渭水上游和秦岭以南汉水上游一带。其后不断迁移。炎帝的后裔有姜姓诸夏及姜姓之戎,还包括氐羌。后发展为共工、四岳和氐羌三大支系。共工一分为二,即共工和鲧(缓读),说明炎帝集团又有进一步的分化。共工发展于今豫东及冀南地区,徐旭生具体指出其为辉县境内,范围显然过于偏小。鲧兴于崇山(今嵩山),发达于豫晋接壤地区,故,鲧被认为是黄帝集团的一个支系。四岳,或写作西岳,又作太岳。其后裔有申、吕、齐、许等国。申在今河南南阳;吕原在陕西,后迁南阳;齐在山东;许即今河南许昌。炎帝都陈(今河南淮阳),大约四岳一支是炎帝的主流。氐羌则比较复杂,一直处于西北农牧交错地带。传说中,共工与鲧治水失败后,被天帝殛死,鲧化为黄熊或黄龙;共工化为赤熊[14]。这与黄帝集团以猛兽为图腾有相通之处。可见,炎黄两大集团分布的地区内,不仅新石器时代文化系列相同,文化特点亦有相当的相似处,差别只是地方类型和文化中心的差异。神话传说上的共同性更加说明两大部落集团的文化渊源相通。
今黄河下游,以泰山为中心,南至淮,东至海,北至无棣,实际是先秦时期的济水及海岱地区。其文化渊源和承袭关系比较清楚,发展序列完整。后李文化(前6300~前5600年)[15],青莲岗·北辛文化(前5600~前4300年)(注:从前学术界把江苏淮安青莲岗和大墩子下层为代表的一类遗存作为“青莲岗文化”,或作为“大汶口文化一期”。北辛文化早、中期的碳14年代为前4600~前4300年。可参阅华东文物工作队:《淮安青莲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学报》(第九册),1955年;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镇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2期。碳14年代数据依上述考古所新公布的数据。),大汶口文化(前4300~前2500年),龙山文化(前2500~前2000年)和岳石文化(前1900~前1500年),诸文化前后互继。海岱山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神话传说的太昊、少昊部落集团相对应,其中一部分与炎黄集团融合,成为夏人、商人的来源之一,大部分则为夏商周时期的东夷先民。整体上,海岱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应是三代时的东夷及其先民的文化。
太昊,分布偏北,时代稍早于少昊,它是东方的帝,又是风姓的祖神。少昊分布与太昊交错重合而稍偏南,以鸟为图腾,《左传》昭公十五年列举有15个以鸟为氏的部落或氏族。传说中,少昊的后裔有后益、皋陶、蚩尤和羿等,今莒县是其核心区。
2.长江中下游东西相对的两个文化区
随着长江中下游考古发现的增多,我们对于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和结构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括洞庭湖,西尽三峡、川东(今渝东),北达豫南与黄河中游的考古学文化相间分布,是一个自成体系的考古学文化区。关于长江流域(特别是长江中上游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学文化谱系关系,由于两湖和四川、重庆等考古工作者的工作,也由于三峡库区1995年以来的抢救性发掘,有了更新的认识。如青年学者孟华平写的《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结构》[16]一书,对中游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作了很好的归纳,也落实了我原来的一些设想:时代越晚,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越广,其文化内涵包容性也因之越丰富。
传说中,这个区域有三苗集团。按照《国语·楚语》下及高诱注,三苗是九黎的后裔。九黎的分布,文献记载不明。三苗则战国初吴起指出其地望:“昔者三苗所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魏策》)。《史记·五帝本纪》载:“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徐旭生和钱穆均作过考证,所说即鄱阳湖、洞庭湖一带。俞伟超首先从考古学的角度把三苗与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联系起来,认为长江中游“以屈家岭文化为中心的原始文化”属于三苗文化遗存。屈家岭文化最盛时“向北影响丹江和汉水中游,直抵伏牛山麓,使得那里的原始文化从以原始因素为主,转化为以屈家岭因素为主。在洞庭、鄱阳两湖间江西修水一带的南部类型,因自身序列不清,不知始于何时。但至迟到屈家岭阶段,长江中游的原始文化因素已达到那里,并同岭南的石峡文化结合在一起。在前3000年中叶以后,这个文化系统发展到新阶段,文化面貌发生急速变化,可能进入铜石并用时期,并同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阶段诸文化发生更多的接触”[17]。考古学文化的这种发展与三苗集团的分布范围与势力消长大致吻合。从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谱系分析来看,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有明显的北方因素,故有的学者把它们当作“北方系统的考古学文化”。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它们的起源与面向海洋的“鼎文化”传统有内在的联系。如,石家河文化中的陶规受泰沂地区的文化传统的影响。石家河文化的玉器也有明显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风格(如玉凤等)。
可见,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时期大致出现了“一统”的局面,相对稳定一段时间后进入石家河文化时期,此时整个长江中游的文化面貌有较大的变化。“后石家河文化”与石家河文化之间已经发生文化的断裂现象,似乎说明了尧舜禹时期中原对“三苗”的征伐。
另有学者指出,黄帝集团在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发展到长江中游的宜昌地区,与西陵陕一带的土著通婚,衍生出“昌意族”。并从考古学上予以证明,即“仰韶文化南下对大溪文化中心区的影响,也许就有着黄帝与嫘祖传说的历史背景”[18]。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
长江下游,以太湖平原为中心,南到杭州湾地区,北以宁镇地区为中心(包括苏皖接壤地区),是一个自有渊源、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序列完整的文化区系。自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3400年)——马家浜文化(前5000~前4000年)以下,有松泽文化(前4000~前3200年)、良渚文化(前3200~前2200年)(注:考古学界对马家浜文化、松泽文化有不同的意见,或以为前后相袭,或以为并行发展。本文采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附录《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年表》的观点,分为两个并列的文化。)。
这个地区分为三个明显的中心,即杭州湾宁绍地区,太湖周围和苏杭地区,以及以南京为中心的苏皖接壤地区。其文化面貌有自己特点,如稻作农业、干栏式建筑等。特别是,良渚文化出现的成套的礼玉、高坛建筑土筑(“金字塔”)和规划严整的聚落等等,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内容,说明其开始进入等级礼制社会。令人惊讶的是,良渚文化的发展突然中断。其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与后来的青铜文化看不出直接的联系。我曾将其原因推测为自然灾害方面的后果,近来从地理、地质研究的结构基本支持了这个推测:距今4000年前,在长江下游一带发生了大规模的洪涝灾害[19]。
良渚文化明显地影响到南北各地。鲁南——苏北一带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就包含有颇多的良渚文化因素,反过来,良渚文化也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两种文化的陶器和石器常有互借现象。近年来,关于良渚玉器符号和大汶口文化符号的探讨,已表明了两种文化区系间的密切往来。发掘不久的江苏新沂花厅遗址,就是两大集团文化相碰撞的最好证明。在这处属于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所出土的玉器基本是良渚文化的风格。严文明认为这是两种文化“冲击”与“碰撞”的结果[20]。
良渚文化的重要性,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已作了充分的估计,或称其达到“酋邦制”阶段,或认为处于“军事民主制古国”时期。我以为应列作“前王朝古国”时期,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性质与文化内涵,已在引言中阐述,于此不赘。我们清楚地知道,良渚文化的诸多因素为夏商周所吸纳,如礼玉制度,鼎的使用,甚至商周时期的“饕餮纹”也是直接来自良渚玉器上的纹饰[21]。但是,整个三代,长江下游的文化和文明发展都表现出中断和回归的特点,直到春秋中晚叶才重新起步,兴起了吴越文明。也许,正因此之故,在先秦文献及汉晋以来流传的神话传说中,不见远古时期客观存在于这一带的部落与部落集团。相当长时期内,对其认识一直是一片空白。如,前举蒙文通的“三系说”和徐旭生的“三集团说”都将长江下游视作洪荒无人的空白之区。
我们的意见是,伏羲、女娲神话起源于长江下游。由于已在《中国远古的各部落集团》一文做了考证,此不重复。
3.燕辽文化区及黄河上游文化区
燕辽文化区,相当于苏秉琦所说“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文化区。包括辽东、辽西和燕山南北地带的新石器文化。辽西,进入1980年代以来有一系列的重大考古发现,凸显了辽西作为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特别是围绕“坛——庙——冢”及“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讨论,将牛河梁、红山咀等的重要发现提高到文明起源的认识水平,进而中华文明的北方源头已见端倪。不久,又发现最早的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查海遗址位于辽宁阜新,兴隆洼遗址位于内蒙古敖汉旗。两种文化的最早年代均超过前6000年[22]。查海出土十几件真玉制品,包括工具和装饰品,还发现了最早的龙纹图像,被誉为“中华第一村”。兴隆洼遗址是目前中国北方已知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遗址,已发掘的房屋有120多座,排列有序,居于中心的房子面积达140平方米,可知当时的社会结构组织已相当系统和发达。兴隆洼文化的发现,揭开了北方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新篇章。查海文化和兴隆洼文化的玉器是已知最早的中国玉器作品。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还有赵家沟文化(距今7200~6800年)[23],继之为红山文化(距今6000~5500年)和富河文化(距今约5200年)。前述之牛河梁和红山咀均为红山文化,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辽东及旅大地区,为新乐文化(距今7300~6800年)和小珠山(下层)文化(距今6500~4500年)。小珠山为代表的辽东半岛的新石器文化明显受到了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影响。山东长岛大汶口文化遗址的系统发掘,从一个侧面证实了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文化联系的密切性。新乐文化基本是一支独立的文化系统,与红山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一定的关系,如彩陶和“之”字纹的普遍使用等。在内蒙古的中南部已进入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分布范围,此不赘。
由上可知,该区的考古学文化系列比较完整,且自成体系。文化面貌也有自己的特点,如常见细石器,石砌建筑和陶塑像发达,玉器自成系统,等等。这些内涵,都昭示了这是一个独立的古文化区。多年前,我写《商先起源于幽燕说》(与干志耿、李殿福合作)及《商先起源于幽燕说再考察》,论证商起源于幽燕地区,至上甲微以后,南下发展于河济泰山之间[24]。
黄河上游,指陇山以西的甘青地区,分布着马家窑文化(距今5200~4000年)和齐家文化(距今约4000年)。这已进入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大体与中原的龙山文化相当,即所谓的“龙山时代”时期。新石器时代中期,一般认为这里是仰韶文化的分布范围。再向上因材料有限,则无法追溯。
黄河上游的新石器时代文化,是一种旱地农业文化,直至青铜时代早期。但狩猎和畜牧业则一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继续发展的是游牧文化。人们通常不把甘青区划为一个独立的区系,除了囿于材料外,主要没有同时考虑生计类型的文化要素。这一带昆仑神话一直占有重要地位。
4.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心的华南文化区
华南地区,包括今天的两广、闽台和江西等省在内,多为山地和丘陵地带。由于地处东南沿海,是降雨充沛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约万年以前,这里已经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文化可分为早、晚两期。
早期的文化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遗址多分布于洞穴、贝丘或台地。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骨角器、蚌器较为发达,陶器粗糙。采集渔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重要的遗址,如江西仙人洞、广西的豹子头、广东的西樵山遗址等,均在距今8000年以上。仙人洞文化距今约1 万年。新石器时代中期,只有台湾的大盆坑文化,距今约6400年。
新石器时代晚期,已有发达的农业,江西修水山背和广东石峡文化都发现了稻谷遗存。陶器也更为精致,更晚的时候还出现了硬陶。石峡文化距今5000~4000年,山背文化距今4800年。在福建有昙石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台湾有凤头鼻文化(距今4500~3500年)、圆山文化(距今4000~3500年)和卑南文化(距今3000~2000年)等。台湾海峡两岸,是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这些分布于江西、两广和闽台的考古学文化既有地域差别,又有颇多的共性。如,石峡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考古学文化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石峡文化的玉器又受到良渚文化的影响(如良渚式玉琮)。
对于广泛分布于华南地区的几何纹陶和有段石锛、双肩石斧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曾命名为“几何印纹陶文化”,实际上这在年代上是有问题的。“几何印纹陶文化”始自新石器,兴盛于商周时期。
由于云贵高原所知的新石器文化遗存仍然较少,认识也还有限。俞伟超认为,四川盆地的青铜文化一部分就来源于云贵高原的文化(另一部分来自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文化基本未见,晚期以云南的白羊村文化为代表(距今约4200年)。在洱海、滇池地区的这些遗存,表明这里是稻作农业的文化。在西藏昌都,发现了卡若文化,距今5300~4000年,除了旧石器外,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是一种以粟为主要作物的农业文化。
古史记载,这里是远古时期的荒蛮之野。百越系统诸民族当起源于岭南及东南沿海远古文化基础之上。
5.北方游牧与渔猎文化区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划分,通常将兴隆洼——红山文化划入北方新石器文化区,而将黄河上游划入西部文化区。从地域和文化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是有充分依据的。考虑到经济文化类型的因素,我们将上述二区分为燕辽文化区和甘青文化区,包括河套和长城沿线地区。后来相当长的时期,这里都是游牧民族活动的舞台,农牧业交替发展,构成“华夏文化”的边缘[25]。
东北北部、蒙古高原、阿拉善平原和塔里木盆地东缘等地区,普遍分布着以细石器为代表的考古遗存,陶器和磨制石器始终没有得到发展。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农业已经相当发达时,这里仍是以采集、狩猎为主的经济形态。关于中国细石器文化的分布及特点,贾兰坡先生已作过精彩的分析,无需重复。至少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末叶,华北地区已出现了典型的细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遗址,如山东沂源凤凰岭、河南许昌灵井、陕西的沙苑、内蒙古的扎赉诺尔等,细石器的传统都比较发达。随着农业的发展,黄河流域的细石器消失了,仅在红山文化及长城沿线有所保留。在北方和西部草原地区,细石器普遍延续到金属使用以后,说明细石器在游牧区和渔猎区盛行的时间较长,且与华北地区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蒙古草原和***等地,由于细石器的遗存多暴露于沙丘之下,断代相当困难。这里仅以黑龙江为例,将东北北部的考古学文化作一介绍。据《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的归纳,这里的新石器文化可分西部铜钵好赉文化、中部昂昂溪文化和东部新开流文化。其中新开流文化距今6000年,是典型的以渔猎为主的文化,有磨制石器、篦纹陶和细石器共存。昂昂溪文化的农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而铜钵好赉文化则是以狩猎为主的遗存。
关于这些更为边远地区的文化(相对于中原中心),倘若不是借助于考古发现,可以说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系统的认识。在古史传说体系里,也难以落实。
四
讨论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还有必要分析一下经济类型。中华农业起源自成体系,是世界上探讨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自1979年以来,我反复撰文阐述中华各民族的发展,在古代呈现出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的总特点。这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民族统一的过程,也就是统一的多民族中国形成的过程。
所谓东西两大部,是指面向海洋湿润的东南部农业区和背靠欧亚大陆的广大干旱牧区,在牧区中有小块河谷与绿洲农业的西北部。所谓三带,就是秦岭——淮河一线以南的水田农业带,此线以北至秦长城以南的旱地农业带,以及秦长城以北的游牧带(包括渔猎和畜牧)。这三个经济地带,也是中华文化与民族起源与发展的地域空间。
在全面研究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区系特征后,我们进一步深信上述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的发展格局,其起点和萌芽,实可追溯到新石器时代。虽然,就畜牧文化而言,考古学研究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但结合民族学和民族史的研究仍可将这个游牧区的形成,看成是从原始农业中分化出来的,是在金石并用时期和青铜器时代早期,原有在草原边缘地带从事原始农业的诸部落征服草原并与在草原上从事游猎的人们相融合的结果。因此,在中华文化起源与形成的阶段,就已经萌生和孕育了东西两大部和南北三带发展的特点和格局。这是中华民族起源具有多元特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关于上述总特点的具体描述,我们已在许多场合和论著里讨论过,这里仅强调如下几点,作为进一步的小结:
1.农业的起源与进步,是新石器时代最重要的成就,是一场“革命”。
2.中华新石器时代农业所呈现的南北异型,基本奠定了以后我国农业的格局,因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变化,北纬41°~44°同时进入青铜时代后,由原始农业区变成了游牧文化区。
3.河谷地带,农业与游牧文化呈交错式分布,更凸显出两种经济形态的互补与平衡发展的关系,形成所谓华夏“边缘”。更为重要的是,游牧文化与旱地农业文化、水田农业文化的平行发展、相互依存、相互补充,共同缔造了中华文化。
4.这种区域间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中华文化的起源阶段就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在后世得到充分发展,这既是历史传统所致,也与中华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特点分不开。因此,研究中华民族的起源必须考虑到中华大地的地理特点。
公元前3000~前2000年间,是中华文化由多元向一体融合的最关键时期。我们将这一时期,笼统地称之为“前王朝古国文化时期”。
由于农业和其它生产技术的进步,社会财富的积累空前迅速。从考古发现看,这一时期,是一个经济文化发展迅速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时代。首先,贫富分化、社会分化加剧,于是,出现了凌驾于部落成员之上的贵族(常为部落酋长和军事首脑)。战争与土地兼并成为国家孕育的酵母,一方面造就了最早的国家管理者,另一方面造就国家机器本身。原有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逐渐打破部落与地域的界限,因之,考古学上所见到的现象是:文化上呈现出强烈的统一趋势。
具体而言,起源于以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逐步统一了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和燕山南北地区,形成了山东龙山文化、良渚文化(后期)、红山文化(后期),使上述各区系的文化特征都有了“龙山文化”的面貌。虽然仍有地区性特点和差异,但统一的趋势已经完全显露出来。故,考古学者将这一时期概括为龙山文化形成期,也有学者将它直接称为“龙山时代”。
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太昊、少昊、蚩尤,尧舜禹战胜三苗等惊天动地的战争,就反映了当时部落集团间的兼并事实。中华大地上,由多区域文化并行发展的新石器文化,在此一时期进行了反复碰撞、融汇与吸收、涵化,加速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夏王朝的最后形成。所以,中华文化是多元起源,而中华文明却是在中原最早出现。
最近几十年的考古新发现,使我们对中华文明最终形成的过程有了清晰的认识。考古学昭示,在青铜起源与文明初曙时期,燕山南北、黄河上游、长江中、下游本来是与中原齐头并进的,有的甚至走在中原的前面。正是在这些四面八方的先进文化汇聚于中原、各部落集团融合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夏人、商人、周人,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复经春秋战国的民族大迁徙与大融合,形成了稳定发展的华夏民族。华夏民族在中华民族中首先形成,是以炎黄部落集团融合为核心,不断融合太昊、少昊、三苗及其他各部落集团的一部分,吸收四方先进文化大融合的结果。
从华夏各部分来源来看,与四方各民族都有共同的渊源联系。四方各部落与部落集团,都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进入华夏形成的过程,大部分仍沿固有文化传统继续发展。当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也不断吸收邻近各部落与部落集团的文化与成分,发展形成为边疆各民族。同时,华夏民族在形成发展过程中,也不断有一部分分化出来迁徙到边疆,融于当地各族之中,成为当地民族的一部分来源。中华各民族形成发展的这种一方面是融合,另一方面是分化的特点,一直可以追溯到起源时代。这一特点,对中华民族后世历史的发展影响至为深刻,此所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缘故。
附记
正当拙文即将发排之际,新华社6月6日发表了记者池茂花、帅政两位撰写的电讯,报导山西省临汾地区襄汾县陶寺村新近出土距今超出4000年的古城,使尧都平阳得到了考古学上的落实。中国古代第一个王朝是夏代。前此有黄帝至尧舜五帝时期约千年文明形成的历史时期,我将这个千年纪称为“王朝前古国”时期,其年代与性质、内涵已在本文序说中表述,于此不赘。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区系及目前已知的金石并用时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系列古城看,中华文明初曙时期有6 个中心:即长江上中游的成都平原、中游的江汉及洞庭湖平原、下游的杭嘉湖平原;黄河流域上中游的泾渭关中平原、中游的涑汾河洛平原和下游的古河济之间。从古城年代及文化内涵看,两大母亲河6 个中心地区文明因素水平相近,各具特点,而长江流域似略早于黄河流域。然而中国最早的王朝出现在黄河中游,长江流域最早的礼乐文化萌芽,都汇聚到黄河流域,在夏商周礼乐文明中得到了反映。在夏至唐中叶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长期在黄河流域,晚唐至两宋以后才重心南移,而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种格局的形成,鄙意以为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中国游牧民族逐渐形成,与中国农耕民族经济文化既不可分割又互相矛盾,促使中国古代政治、军事重心一直是北重于南;秦以来形成万里长城,把中国农牧民族既分隔开来,又联系起来,正是中国农牧两大类型经济文化与民族之间既不可分割又互相矛盾关系的反映与产物。这些问题容后论述,而中华文明起源6个中心的发展,融汇为三代礼乐文明, 是本文应有之义。但篇幅过长,当另文论述。
参考文献:
〔1〕 陈连开.中华民族研究[C].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2〕 列·谢·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3〕 贾兰坡院士就河北发现世界之最早细石器, 认为人类起源在亚洲[N].光明日报,1994—04—07(2).〔4〕 贾兰坡.中国大陆上的远古居民[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5〕 吴汝康.人类发展史[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8.〔6〕 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J].文物,1987(3).〔7〕 蒙文通.古史甄微[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8〕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增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9〕 保定地区文物管理所等.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92(11).〔10〕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M].北京:三联书店,1999.〔11〕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12〕 苏秉琦.文化与文明:1986.10.5在辽宁兴城座谈会上的讲话[R].辽海文物学刊,1999(1).〔13〕 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北京:中华书局,1964.〔14〕 杨宽.中国之古史导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5〕 王永波等.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的新课题——试论后李文化[J].考古,1993(3).〔16〕 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17〕 俞伟超.先楚与三苗文化的考古学推测[J].文物,1980 (10).〔18〕 王震中.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J].江汉考古,1995(1).〔19〕 任振球.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生的一次自然灾害异常期[J].大自然探索,1984(4).〔20〕 严文明.冲击与碰撞:花厅墓地试析[J].文物天地, 1991(3).〔21〕 李学勤.良渚文化玉器与饕餮纹的演变[J ].东南文化,1991(5).〔22〕 新中国考古五十年[M].北京:文化出版社,1999.〔23〕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24〕 陈连开等.商先起源于幽燕说[J].历史研究,1985(3).商先起源于幽燕说的再考察[J].民族研究,1987(1).〔25〕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4.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5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