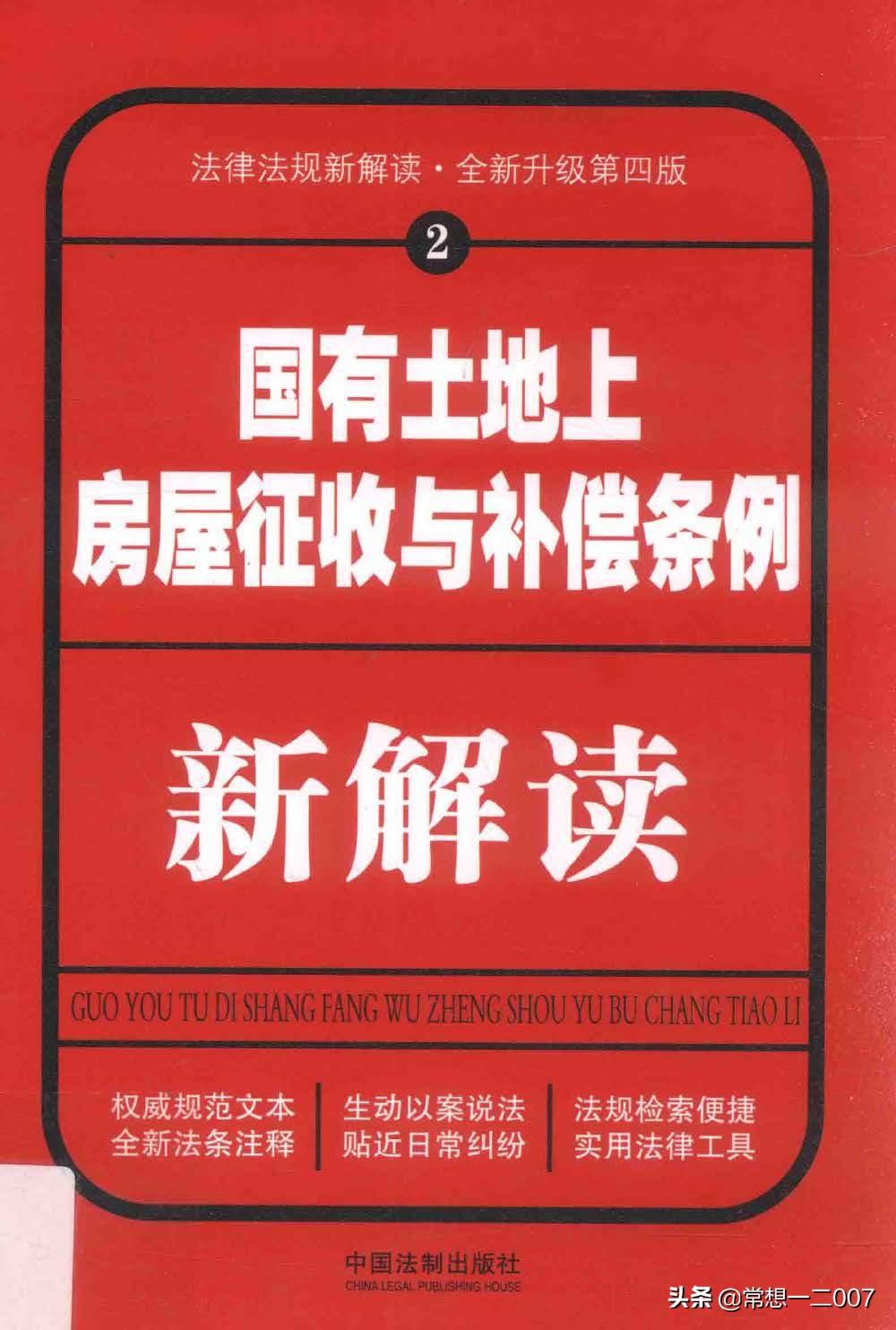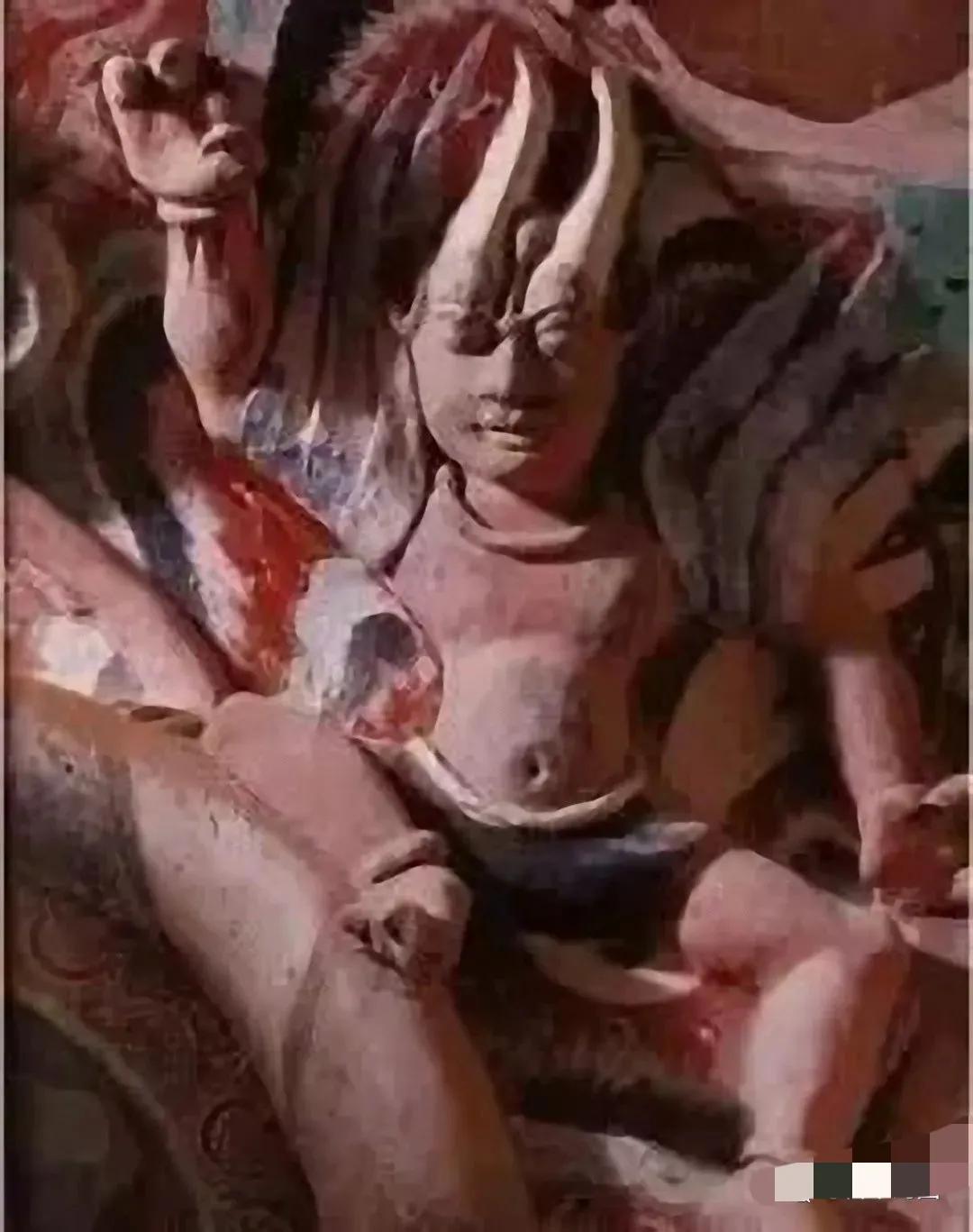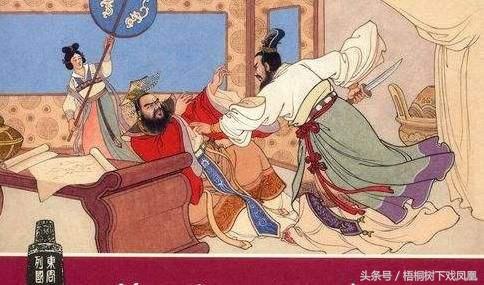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发展的若干问题
如果从1921年仰韶村的发掘算起,中国史前考古学已经走过了70多年的历程。通过这70多年的工作,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根深植于中国史前文化的沃土中。要了解历史时期的中国,必先了解史前时期的中国;要认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和特征,必先认识史前时期中国各地区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特征;要研究中国文明的起源、形成和发展,必先研究中国史前文化的起源、形成和发展;甚至探索汉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也离不开对史前文化的认识和研究。总之一句话,史前考古学不仅在重建中国史前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即使在认识和了解历史时期的中国和中国文明的总体特征方面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过去的近20年里,中国史前考古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整个说来,这一时期科研队伍得到了空前加强;科研组织和管理工作得到了加强和改善;课题意识也不断得到强化;田野工作的规模和时空范围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时期,对史前遗址和墓葬有计划的大面积解剖为解决中国史前文化的起源、形成和特征以及相互关系等问题,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探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在70年代后期发现以来,至80年代后期又有新的突破,农业起源、陶器起源、家畜起源以及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等一系列关键问题有望得到解决或积累起新的线索和材料;新石器时代的一批城址相继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上游地区发现,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红山文化等一系列体现社会分层和等级分化的墓葬和随葬品的发现和研究,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各种专题研究和综合研究空前繁荣,全国出版的定期和不定期的考古文物专业刊物达30多种;地方考古队伍日益壮大,相当一批重要的史前文化的发现是由地方考古机构完成的,考古力量的布局与70年代以前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此相适应,全国各地的考古发现层出不穷,许多最引人注目的考古遗存是在长江流域、东南沿海、长城地带甚至华南和西南地区发现的,长期以来考古工作以黄河为中心的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并最终影响到我们对中国史前文化总体认识的转变。
70年代后期以来,前仰韶文化首先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并得到确认,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和连续发展性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全体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全国各地特别是在长城地带、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等地区的许多重要发现,使史前文化的时空空白得到了逐步的填充,上述各地区史前文化的编年和谱系日益明确。至80年代中期以来,对中国史前文化的总体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现在知道,中国史前文化既不是外来的,也不是从国内某一个中心向外传播的。各地史前文化是在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基础上逐渐发展起来的,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或多或少都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黄河中心论或中原中心论的一元论终于被多元论所取代。史前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也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事实证明,在漫长的史前时期,没有哪一个地区始终占据领先地位。黄河中游的核心地位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但只是在新石器时代的后期才突现出来,并最终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础,而这与它长期处于各文化区的中间地带有很大关系。总之,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向心性、连续发展性、多元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的认识,是70多年来几代考古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结果对于正确地认识中国文明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1〕。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临世纪之交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面前的任务无疑是很艰巨的。根据我们的理解,在最近若干年内,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或者有了新的线索,就会深化我们对中国史前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推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
一、关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
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问题在本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以来,即被提了出来。50年代末期发现李家村等早于仰韶文化的遗存,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华北地区,前仰韶文化和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是在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文化发现之后。原来把它视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最近的看法主要是把它划为新石器时代中期或中期的早段。
早在60年代,江西万年仙人洞等洞穴遗址的发掘就提出了华南地区早期新石器时代的问题。但由于这是个石灰岩所造成的碳十四异常区,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引起足够的认识。70年代以来,湖南石门皂市下层、湖北秭归柳林溪、宜都城背溪,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相继发现年代与华北磁山、裴李岗文化相当的文化遗存,为大溪文化找到了渊源。进入90年代,又在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湖南道县玉蟾岩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存,发现了距今万年前后的陶片和类似水稻的扇形体植硅石,在玉蟾岩还发现了栽培稻的标本,为追溯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起源、农业起源、陶器起源和研究南方地区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提供了新的材料。相比起来,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探索要滞后一些。除了河北徐水南庄头发现万年前后的早期遗存之外,据说最近北京市文研所在潮白河上游的转年遗址也发现了9000年前后的遗存,但报告尚未发表,具体情况不很清楚。总之在磁山·裴李岗文化开始到12000年更新世结束这一段,尚有三四千年的空白。磁山·裴李岗文化已经有了发达的农业、家畜饲养业、精制的磨制石器,制陶也很发达,显然与新石器文化的起源有相当一段距离。要了解这些文化因素的起源,必须在这一段空白里下功夫。目前除了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下追溯以外,地质学家已经注意到,在全新世与更新世之间,在华北地区主要是淡黄色的马兰黄土和橙黄色的全新世黄土之间有一个不整合的侵蚀面,据说郑州织机洞、山西襄汾陶寺、陕西扶风周原等许多地点都发现了这个侵蚀面,东北地区的辽宁本溪庙后山也有类似的侵蚀现象,被认为是可能与更新世结束以后的气候变化带来的暴雨成灾有关〔2〕。因此不排除有些人类活动的遗存已经被破坏,或者因为气候的原因人类活动的地点与磁山·裴李岗时期有很大的区别。目前发现的南庄头遗存是一个湖相堆积,不太像是一个人类居住的遗址。据分析,这一时期的人类应该有了相对稳定的住地和葬地,但要寻找这类遗存,还要充分考虑到文化层薄且不易辨认,陶器少且非常简陋,人类活动的规模小,移动性大,很可能居住在较高的山岗或坡地这样一些特点;在石器的类型上,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共存,从旧石器晚期的细小石器向典型细石器的过渡等这样一些特点,多学科合作,摸索这一时期文化的特点和分布规律,最终解决这个问题。
二、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问题
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从20年代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到后来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再到六七十年代的仰韶——龙山一元发展说,发展为现在的多元说,应该说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是几代考古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3〕。但是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不少的问题,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定性的研究多,定量的研究少
我们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在文明的定性上,这样固然易于把我们国家的文明起源的时间向前推进不少时间,固然有利于正确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殊性,但文明演进的过程特别是文明在一个文化内部从发生、发展、变化甚至衰落的过程却受到了漠视。这是大的方面。从小的方面说,我们通常命名的所谓祭坛、所谓庙等等,并没有经过多少论证,这些所谓坛、庙的发生、发展过程甚至功能的研究,也都停留在平面的定性的层次上,而这些文化现象本身的定性最终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对拥有这些因素的文化的定性。
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的发生是文明起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的非实用品的陶、石、玉、木、漆器等的生产和城墙、大型夯土台基乃至墓葬、棺椁等的建造,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热点。但是上述因素在不同文化、不同地区文明起源过程中的作用有无区别;上述因素的生产和制造体现了多大的社会劳动量;不同质料的建筑比如石砌建筑和夯土建筑在占有社会劳动量方面有多大的差别;壕沟和城墙在占有社会劳动量方面有多大的差别;礼制和社会分层现象是怎样从无到有发生又是如何融入三代社会中去的等等方面,都缺乏具体的定量的研究,而停留在定性的层次上〔4〕。这些都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深层次研究。
2、基础研究薄弱,器物本位的研究有上升趋势
自80年代发现日多的良渚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等史前文化的城址、大型夯土台基、积石冢、带棺椁的墓葬以及玉器等等,本来是开展聚落考古的结果,事实上这些发现也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史前文化的认识。没有这些新发现,我们不可能对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程度及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有现在这样清醒的认识。但是我们有意无意中把过多的精力倾注到墓葬甚至主要是含有丰富随葬品的墓葬的发现和发掘上,而忽视了对遗址本身的研究。统计某些史前文化的研究著作,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是器物学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对玉器及其形式、花纹和功能的研究,而对文化本身的分期、断代、分区等基础研究则无暇顾及,其结果不仅影响到前述的对文化自身发展过程的研究,即使遗物本身的研究比如对玉器的分期、分区及功能的研究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和影响。至于聚落及房屋建筑的特征、分布及演化过程,人们的生活状况甚至生产活动情况在一些地区更是无从谈起,这同以器物甚至是以精美器物为本位的研究取向是大有关系的,值得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在今后的研究过程中加以纠正。
3、把古史传说当成信史,与考古发现简单对应
考古学在中国历来是历史科学的一部分。无论是中国传统的历史观,还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都是把考古学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并最终为复原历史、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服务的,因此史前考古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重建中国上古史〔5〕。如果能够把考古发现和古史传说有机地结合起来,对于我国上古史的重建无疑是大有益处的。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把《五帝本纪》以及其它传说中的史料看成为信史?能否把某一个文化或者它的一个类型甚至某一个遗址或者墓葬同某一个上古帝王联系甚至等同起来?史前考古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重建上古史主要是依赖史前考古学的成绩。在分析、辨别考古材料,把某一个文化或者类型的分布范围、渊源、谱系等研究清楚的情况下,慎重地分析、辨别传说中的史料,积极地吸收“古史辨派”疑古辨伪的成果,追溯某一个集团同考古文化的关系,对于重建中国上古史的工作是有益的;但是对于古史传说采取信史的态度,把传说中的某一次迁徙、某一次战争甚至某一个人物同某一些考古文化之间的类同现象、某一个城址甚者墓葬等同起来,似乎无助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和中国史前史的重建。
4、强调多元,轻视中原文化区的作用
中国史前文化的多元发展理论是长期以来全国考古工作者艰苦工作达成的一种共识,在认识方面是一个进步。在承认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多元性、不平衡性的基础上,在承认中国史前文化中没有一个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各地区文化都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及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有所贡献的基础上,也不能采取平均主义的态度,均衡地看待各文化区对于中国文明形成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否定中原文化区在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中原文化区从磁山·裴李岗文化经仰韶到龙山文化,既对周围地区的文化发挥着重大的影响,也接受了周围地区持续不断的影响。虽然迄今很少发现可以同良渚文化等相抗衡的大型墓葬及精美的玉器等随葬品,也少见甚至不见大型的夯土台基和积石冢,但该地区文化一直处于各文化区的中心位置,是古代文化交流、冲突、融合的中心,相对说来,该地区的史前文化,一直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继承了本地区文化的传统,也接纳了长江流域、黄河下游和上游以及北方地区众多的文化因素,最终奠定了三代文明的基础。我们在肯定其它地区文化的进步、发展并且自成体系的基础上,还要回答中原地区发生三代文明的机制和原因,也还要回答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等迅速崛起而又很快沉寂的机制和原因。而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又同研究上述文化本身的演化过程,同研究遗址的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环境对文化的作用以及分区、分期等方面分不开来。总之,在各地区文化发展的机制不很清楚的情况下,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轻视甚至贬低中原文化区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可取的一种态度〔6〕。
因此加强基础研究,加强聚落考古的研究,以聚落本位代替器物本位,在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比较清楚的地区认真地解剖一两个城址或高等级的聚落,具体地从一个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入手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主要任务。不如此,关于中国史前文化发展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就会停留在表面的定性层次上,而无法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机制和动力有根本的认识和了解。
三、关于聚落考古的问题
聚落考古是80年代以来才日益明确起来的一个概念。因为聚落考古的任务是通过考古学的材料对古代社会关系的研究,所以引起了广泛的重视〔2〕。通过这许多年的工作, 特别是通过对一些典型遗址比如对兴隆洼、姜寨、尉迟寺等遗址的大规模发掘,我们对这些遗址及其周围地区同时代文化的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以及生产和生活状况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江中上游地区相继发现了数十座史前的城址,对于研究中国文明起源和中国史前文化发展的独特道路提供了新的可靠的材料和动力,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有的研究者已注意到在一个小的流域或区域通过对典型遗址的解剖结合系统的调查材料,了解聚落的特征、分布规律及其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聚落考古学走向深化的一个新的步骤。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聚落考古学的任务还很艰巨,这主要表现在1、 我们对史前各时期的聚落特征、演变和分布规律的认识还十分有限,而这是跟典型遗址的发掘面积小、调查不够细致等等情况分不开的。2、 史前城址的发现虽然已经有了一定的数量,但基本上只是对城址的规模、城墙的走向和筑城技术等方面的了解,关于城址内部的建筑布局、城址与周围遗址及其它城址的关系、城址的功能和筑城所需劳动量的研究,都还处于非常薄弱的状态,有些甚至还没有起步,所以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3、我国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只有两次, 目前编纂的中国文物地图册,就主要是这两次调查的成果,这对聚落考古的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依据,但是这些材料大部分十分零星,而目前遗址面临基本建设的破坏又特别严重,在新的形势下,开展对史前遗址的系统调查,就成为聚落考古的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4、 聚落和环境的关系非常紧密,开展聚落考古特别是一个地区和流域的聚落考古工作,研究环境以及环境变迁对聚落的影响及互动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5、在已有的调查和发掘基础上, 对我国史前时期的聚落起源、发展和演变,对由聚落反映出来的社会组织、社会形态、社会关系的总结和研究,也已经提到了日程上来。总之,加强对聚落考古的研究,树立聚落本位,脱离器物本位,才能更全面地为中国史前史的建设服务,也才能更健康地推动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
四、关于史前文化谱系的研究
虽然黄河流域、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及北方长城地带的史前文化的时空框架大致建构成功,史前文化的谱系已经比较清楚,但是还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最近若干年,关于上述地区史前文化及其类型、分期的重新研究和划分,关于上述地区史前文化与古史传说的关系及其在古史上的地位,是考古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也说明谱系的研究即使在田野工作比较充分的地区,也还是比较艰巨的。但是在上述地区特别是在黄河流域,新的大规模的田野工作并不多,大部分的研究只是对原有发掘材料的再探讨,而原有的材料在不少地方也嫌单薄,因此要真正解决史前文化在上述地区的发展谱系,还要作好典型遗址的发掘和调查工作。在对各个地区史前文化的渊源、流向及其相互关系不很清楚的情况下,简单地比照古史传说,就肯定或否定某一种史前文化或者类型在古史上的地位和价值,甚至把史前文化和某一个族或传说人物对应起来,以为这样才是史前考古学研究的目的和方向,才能为中国上古史的建设贡献力量,其实是一种不很正确的研究取向。
在文化的时空框架和发展谱系比较清楚的地区之外,比如华南地区、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和东北地区,基础研究的工作更重。这种情况是同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相关联的,也是同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发展不平衡相关的,要了解这些地区文化的时空框架和谱系,必须以大量的田野调查和选择堆积厚埋藏丰富的遗址个别解剖相结合,同时注意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加强同工作较多地区的文化的比较,积累资料,积极合作,树立课题意识,以期在若干年之内建立起区域年代框架并初步理清文化发展的脉络,最终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前文化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国文明的起源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创造条件。
中国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史前文化的土著性十分显著,并且形成一个向心的有多重文化和类型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的文化共同体。在目前研究工作比较多的地区(比如苏秉琦先生所划的六区)之外,还有至少一层或者层次更多、更复杂的史前文化,它们和黄河、长江流域的文化有密切的联系,和周边国家特别是北部和南部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很紧密,比如岭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同中南半岛和东南亚的史前文化,北方地区的史前文化和作为东北亚洲一部分的西伯利亚等地的古代文化都有较密切的联系,实事求是地开展边疆地区史前文化的谱系研究,对于全面地认识中国史前文化有重要意义。
五、加强田野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质量
田野工作是考古学的基础和灵魂,加强田野工作,提高田野工作的质量,对于我国史前考古学的健康发展,对于中国史前史的建设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史前史虽不等于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的基石是史前考古学,而史前考古的材料来自科学的田野工作,因此任何轻视田野工作,以为只有写文章、作室内研究才是科学研究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近年来,我们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对田野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田野工作的质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高。比如,在调查和发掘中,更加注重对植物种子、孢粉、动物骨骼和人类骨骼的记录、采集、提取、保护和分析,其它与测年、人类的食性、人类生存的环境等相关的人工、非人工的标本的采集和记录,也得到了重视,使以前被忽视或遗漏的大量信息得到了妥善的保护,这是田野考古学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田野工作还存着许多问题,比如,田野工作是一个包括田野调查、发掘、室内整理、研究和报告编写、出版这样一个完整程序的综合工作,但是有许多人往往忽略了这一点,人为地把它们割裂开来,造成田野发掘和报告脱节,影响了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再比如,遗址的地貌、地理特征是我们研究史前人类生存环境、文化变迁、环境变迁的重要依据,但是在相当多的田野工作中,存在着只重局部的发掘,不重整个遗址以及与周围景观的观察和测量的现象,给研究带来很多的不便和困难。史前考古学是归纳、总结、探讨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最重要的一个领域,在田野工作中重视考古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总结和创新,是我们的一项基本任务,不能只重经验,而轻视方法和技术的应用和总结,而我们的一些同志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种倾向。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一次发掘都是对地下资料的一种破坏,因此,在严格执行国家文物局制定的田野考古发掘规程的基础上,如何完善田野工作,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完备的田野工作程序和方法,以期最大限度地准确地提取史前的信息,而不因发掘者的水平差异而在资料的提取上发生很大的变化,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难题。田野工作的质量还受到课题意识的支配,如果课题意识明确往往会发掘出大量的信息,而这是“为考古而考古”的田野工作所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加强课题意识对于提高田野考古的质量,具有现实的意义。另外一个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在田野考古中的应用虽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但还远远不够,对遗址中非人工制品的记录、提取和分析在许多地区还刚刚起步,需要得到进一步的努力。总之,要推动史前考古学的发展,首要的任务是提高田野考古工作的质量,这是我们所应该牢记的,提出来与大家共勉。
*本文是根据作者在1997年6月24—26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精品战略研讨会”上的发言稿加工而成的,任式楠、杨虎、吴耀利和孙祖初先生参加了初稿的讨论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注释:
〔1〕K.C.Chang,The Archaeology of Ancient China,fourthedition,New Heven:Yale University,1986;严文明:《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文物》1987年3期。
〔2〕周昆叔:《周原黄土及其与文化层的关系》,《第四纪研究》1995年2期。
〔3〕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的心路历程》,良渚文化发现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浙江杭州,1996(刊印中)。
〔4〕陈星灿:《玉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求知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5〕张光直著,陈星灿译:《考古学与中国历史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考古学的历史、理论、实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6〕陈星灿:《玉器时代与青铜时代——再论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考古求知集》,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7〕陈星灿:《等级——规模模型在聚落考古中的应用》,《学人》第11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1997年第4期
- 0001
- 0003
- 0001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