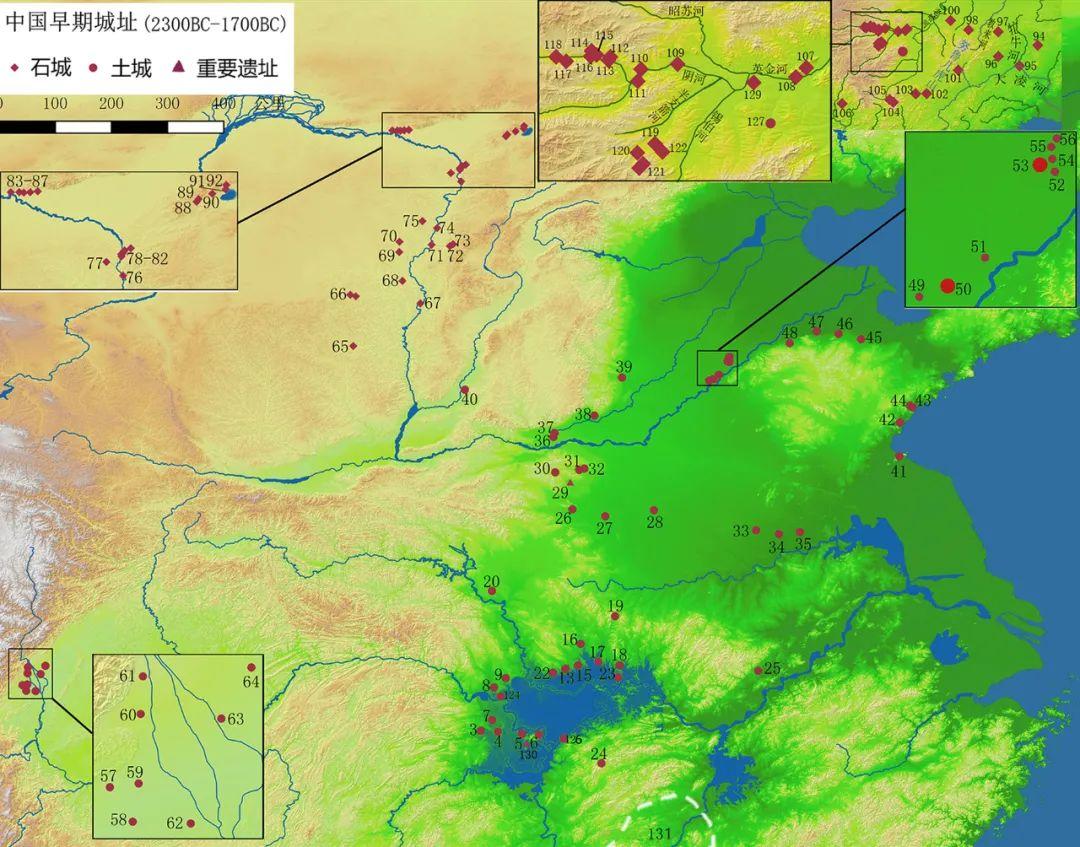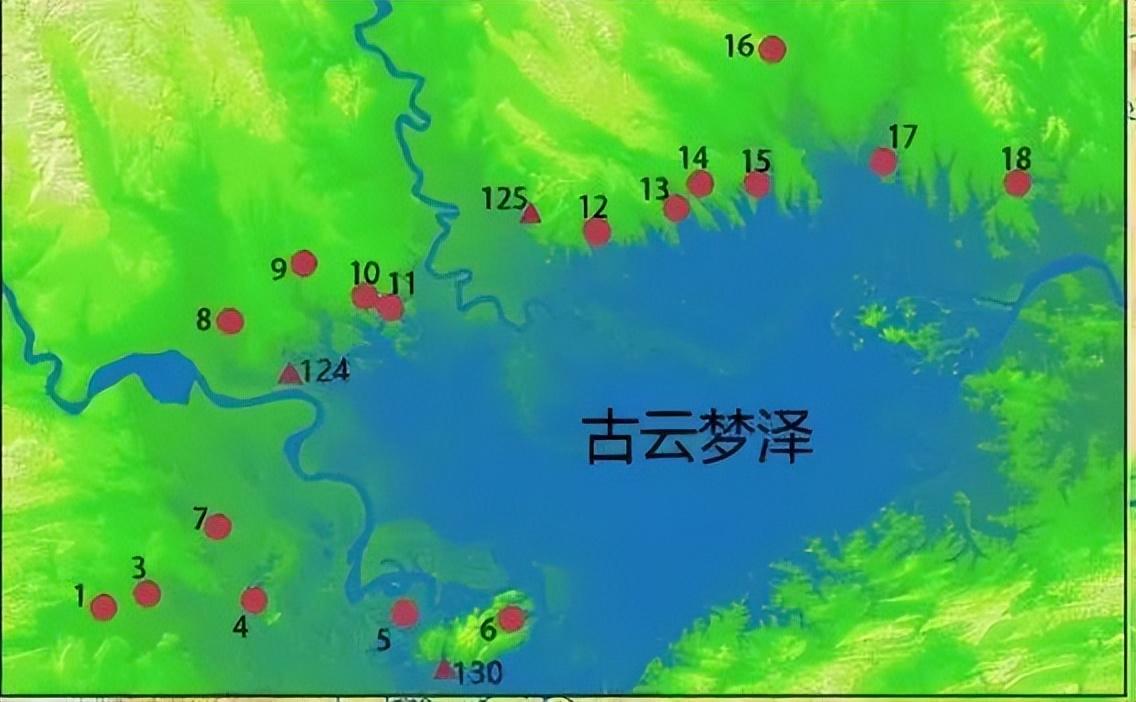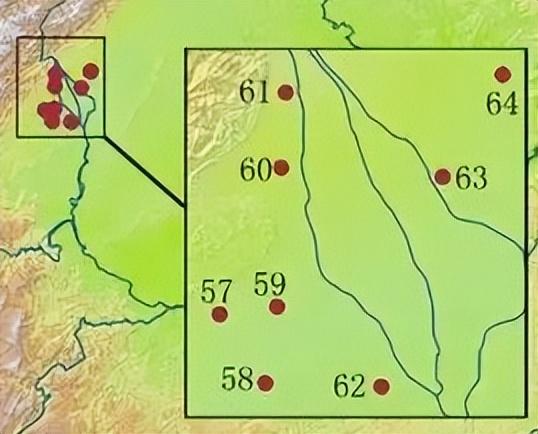桑兵:东方考古学协会述论
中国古代有金石古物学而无考古学,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学术正统,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新国学”的兴起关系密切。因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考古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这一特性的制约,除了与地质学及古生物学联系紧密的史前人类考古,主要还在补证文献记载的历史。就机构而言,其渊源脉络有三,一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考古学研究室,一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科,一是农商部的中国地质调查所。后者偏重于史前考古,北大、清华则更注重文明史考古。从外部影响看,大体上北大与日本交往多,清华与美国关系深,地质调查所则与欧洲联系广。三者起步略有先后,作用则相去甚远,尤其是北大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作为中国乃至东亚最早的专门考古学独立机构,其影响与这一地位很不相称。关键之一,当是与外部联系的成败得失,而中日双方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至关重要。由于利益目的不一,此事的原委始末,有关各方后来的回忆固然不少隐辞,当时记载也不无讳饰。作为典型个案,它集中反映了那一时期关系复杂的中日学术界频繁交往的表面所掩饰的种种内情。比勘各种资料,不仅可以澄清史实,更能进而探讨得失。
一
东方考古学协会由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会和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联合组成,追溯该会缘起,自应详究双方考古学会的来龙去脉及其相互关系。
北大考古学会的缘起与日本及欧美考古学界不无关联。自19世纪末起,日本即开始关注中国的考古发掘。辛亥以后,罗振玉、王国维等人避难京都,所带去的甲骨及殷墟出土古器物引起内藤虎次郎、富冈谦藏等人的极大兴趣。1913年9月, 京都大学决定开设日本最早的考古学讲座。因负责人滨田耕作留学欧洲,由朝鲜史家今西龙暂管。1916年,有日本考古学鼻祖之称的滨田耕作从欧洲归国,正式开设考古学讲座,提出殷代金石过渡期说,并计划发掘遗迹(注: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东京平凡社,1973年,27页。)。东京的林泰辅、鸟居龙藏、大山柏等认为,中国局势复杂,应朝着中日合作的方向发展,较易着手(注:《学问の思ぃ出——梅原末治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38辑,1969年8月。)。而中国方面与此不谋而合, 也在筹划建立新型考古学机构。梁启超虽称“考古学在中国成为一种专门学问,起自宋朝”(注: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欢迎瑞典皇太子演说辞》,《晨报副刊》1926年10月26日。),实则原来只有金石器物之学而无考古学。1908年美国亚洲文艺会书记马克密在北京成立附属于该会的中国古物保存会,响应者达三百余人,均为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和学者,其活动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注:《外交部译发马克密君保存中国古物办法之函件》,《国学杂志》5期,1915年11月。)。随着全球考古发现的重心逐渐东移,欧美日本等国相继在华展开考古探险和发掘活动,所获成果震惊了国际学术界,也引起中国学者对考古事业的关注,作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尤为积极。1918年4月,治古物学的巨擘罗振玉抵京, 北大校长蔡元培亲往其下榻的燕台旅馆拜访,请他担任北大古物学讲座。罗以衰老不能讲演辞,“并言近在日本京都亦不任教科,惟在支那学会中与汉学家时有讨论而已。”蔡“乃与商专设一古物学研究所,请为主任教员,无教室讲演之劳,而得与同志诸教员共同研究,并以研究所组织法及全国古物保存法请先生起草”(注:《罗叔蕴先生来函》,《北京大学日刊》154号,1918年6月4日。)。罗先受后拒, 最终只担任后来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导师。1921年,任职于中国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安特森(J.G.Anderson)在辽宁锦西沙锅屯和河南仰韶村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诞生(注:陈星灿:《中国史前考古学史研究:1895—1949》,三联书店,1997年,90页。)。其成果和所使用的科学方法,很快引起胡适等新进学者的关注,他们积极支持安特森为北大开设比较古物学课程的建议(注:桑兵:《胡适与国际汉学界》,《近代史研究》1999年1期。)。
1921年底,北大调整研究所结构,率先成立的国学门下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 5个研究室(注:《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1卷1号,1923年1月。)。参与其事者受欧美近代学术的影响,认识到“欲研究人类进行之过程,载籍以外,尤必藉资于实物及其遗迹”(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1卷4号,1923年12月。),对于新兴的考古学和风俗学尤其重视。筹设考古学研究室时,曾有意聘请国外学者担任教授。为此,国学门主任沈兼士特委托留学京都大学的张凤举、沈尹默拜访滨田耕作,了解情况,咨询意见,请求指教。这时京都大学的考古学在滨田的经营下,已设陈列室三间,分别展出东亚及西洋、印度的考古资料。但东西两京大学的考古学仍然附属于史学,没有独立。滨田对于中国设置专门考古学研究室十分高兴,详细介绍了日本东西两京考古学的状况,并根据其学养和经验,提出了全面意见和建议。他主张将考古学与美学相联系,而不仅作为史学的辅助研究;应预定计划,以便将来组建独立的考古学研究所;应视考古研究为自然科学,与理科的生物学相等;同时搜集中国和西洋的材料,进行比较研究,以免偏蔽。为此,要积极培养年轻而通外文的人才,设立教授、学生研究室和陈列、实验、图书室,多搜集中国文物,与外国博物馆和大学进行交换;并开列了总价值千余元的考古学应备书目,赠送京都大学出版的两册考古学报告。此外,他还认为:“西洋虽有许多考古学者,但多是历史家兼的,所以言论总难得中……芝加哥大学教授Laufer先生前于东方考古素有研究,著作也忠实,若能请他来,比请别人好。”(注:《张凤举先生与沈兼士先生书》,《北京大学日刊》974号,1922年 3月6日。)这对草创中的北大考古学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后来该研究室的规划设施显然参照了这些意见。
1922年底,代管过京都大学考古学讲座的文学部史学科教授今西龙由日本文部省派来中国研究史学一年,北京大学趁机请其担任朝鲜史特别讲演,并聘为北大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注: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4卷,中华书局,1984年,287—288、309页。)。在华期间,他还分别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和史学会演讲“关于中国考古学之我见”及“中国历史里边的古文书学”(注:《北京大学日刊》1165、1208号,1923年1月26日、4月9日。)。不过, 这时与北大考古学联系的外国学者不止于日本,被国学门同时聘为考古学通信员的还有法国汉学大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923 年, 美国政府斯密苏尼恩博物院调查古迹代表毕士博(CarlWhitingBishop )和芝加哥博物馆东方人类学部长劳佛(BertholdLaufer)相继来华考古探险,其间参观了北大考古学研究室。该室虽已成立一年,因经费有限,只有从古董商人手中收购的零星材料,颇难进行考古学研究,又无力实行探险发掘,所以“本学门一年来关于考古学方面著力较多,而成绩却还不甚佳。中国之考古学向无系统,古物之为用,仅供古董家之抚玩而已。我们现在虽然确已逃出这个传统的恶习范围之外,知道用科学方法去研究,但为财力所限,未能做到自行发掘,实地考证的地步。研究室所用的材料,均由市侩辗转购得,器物之出土地点及其相互联属之关系,均不易知,故进步甚难”(注:《研究所国学门恳亲会记事》(魏建功记),《北京大学日刊》1337号,1923年11月10日。)。考古研究室成立之初,即拟组织一考古学研究会,以便与校外古物学会机关联络(注:《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发言》,《蔡元培全集》4卷,156页。)。后于1923年5月24 日组织古迹古物调查会,由马衡担任会长,计划先自调查入手,“并为发掘与保存之预备”,待经费落实,再组织发掘团。因同志尚少,未能积极进行。美国同行权威远道而来,尤其是毕士博据说预订七八年发掘计划,劳佛则为考古名家(注:有人称劳佛为中国考古学最大的权威。参见岩松五良《欧米に於ける支那学の近状》,《史学杂志》33编3号,1922年3月。),令该会感到中国古代文明有待考古发现者多,“本会当此时机,更应努力进行,以期对于世界有所贡献。”(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纪事》,《国学季刊》1卷 3号,1923年7月。)于是广泛征求同志,以谋发展。其章程不仅要求网罗地质学、人类学、金石学、文字学、美术史、宗教史、文明史、土俗学、动物学、化学各项专门人才协力合作,还规定可在不以输出发掘物品为条件的前提下接受外国财团与私人捐款(该会许可的复出品不在此限),以及与外国发掘财团交换物品。
考古学虽然是北大国学门努力发展的重点之一,但为财政拮据所困,无法着手。该会成立后,除了呼吁保护文物古迹并在北京附近做过几次调查外,只有马衡前往河南新郑、孟津调查出土古物,经费还须校长另行专门拨款。会员发展也不顺利。1924年5月19日古物古迹调查会开会,到会的会员共12人,为:叶瀚、李宗侗、陈万里、沈兼士、韦奋鹰、容庚、马衡、徐炳昶、董作宾、李煜瀛、铎尔孟(Andre d' Hormon)、 陈垣,决定更改会名为考古学会。修订后的简章规定,以“用科学的方法调查、保存、研究中国过去人类之物质遗迹及遗物”为宗旨,强调“与国内外同志团体之互相联络”,特别捐款则不限于外国(注:《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各会章程及纪事录》,《晨报副刊》1924年 6月17日。)。此后直到1926年6月,情况仍无根本改善, 考古学研究室及考古学会主要还是收集或接受外界捐赠古物,制作拓本图录和照像。虽然先后派教授马衡、徐炳昶、李宗侗和会员陈万里调查大宫山明代古迹、洛阳北邙山出土文物、甘肃敦煌古迹以及参观朝鲜汉乐浪郡汉墓发掘(注:《本学门开办以来进行事业之报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 24期,1926年8月。),但除了后一项活动外,其余和近代田野考古学相比,还有很大距离。
二
如果说北大国学门组织考古学会主要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那么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则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与中国的相应机构结盟而成立。
考古重心东移,使得东亚成为国际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日本虽然国力渐盛,教育学术发展迅速,但在考古学这一特殊领域,受制于客观条件,尽管发端甚早,进展却不大。而风气由欧化转为东方主义,迫切需要学术上的解释与表现。对于东亚探险考古活动大都由欧西学者主持,中国学者几乎无关,日本学者贡献也极少的状况,滨田耕作等人感到十分遗憾。要想改变,就必须将考古发掘的现场扩展到日本以外,尤其是中国大陆。而在中国国内政局动荡,中日关系又日趋紧张之际,没有中方的协助,这一目标显然很难实现。
1920年代,日本借退还庚款之名举办东方文化事业,引起中国各界人士的极大关注,长期交涉竞争,纷纷加强与日本的交流。以此为契机,中日两国学者积极开展合作。北大利用其首席国立大学的有利地位,从一开始便展开强有力的角逐。1922年,胡适与蒋梦麟等人拟订计划,主张在中国国立大学和日本帝国大学互设中、日讲座,提倡东方文化研究(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395页;同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257—258页。)。而成立于1923年10月14日的中日学术协会,简直就是东方文化事业的派生物。该会起因为年初北京大学校方召集任教于北大文科的留日出身的教授,如陈百年、张凤举、马幼渔、周作人、沈兼士、朱希祖以及在京都大学进修过的沈尹默等,商议“日本对支文化事业”。是年3月13日,周作人、 张凤举前往日本公使馆找吉田参事官晤谈。刚好这时日本国学院大学教授田边尚雄、京都大学教授今西龙、东京大学教授泽村专太郎等人相继来北大讲学或研究,与北大教授常有交流应酬,显示了北大在中日学术交流中作为国立首席大学的重要地位。9月, 北大诸人与担任北洋政府军事顾问的著名“支那通”坂西利八郎中将及土肥原少佐相识,商议组织中日学术协会。中方以张凤举为干事,日方以坂西为干事,规定每月开常会一次。其实日方成员均非学者,其目的也不在于学术,而是鉴于北洋政府无望,想争取与国民党有渊源者搭桥过渡,以便与新政权接洽,将来谈判时保留日俄战争所取得的权利。所以坂西在成立会上说:“我们怎么配说学术二字,但是招牌却不得不这样挂。”(注: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333—336页。)在此名义下,北京大学与日本教育视察团团长汤原、服部宇之吉及“对支文化部”的朝冈健等人多次就文化事业进行会谈。可惜日方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因形势变化,对北大失去兴趣。(注:详参周作人《苦茶——周作人回想录》,333—336页;《周作人日记》中册,大象出版社,1996年,300—406页。)。一年后该会活动停顿,但北大并未因此而放弃对东方文化事业的竞逐,先是提议推举王国维出任该事业计划中的北京人文研究所主任,以抗拒声望尚隆的研究系领袖梁启超,意图包揽(注:吴泽主编,刘寅生、袁光英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394 页。);后来又有鼓吹“将图书馆及人文研究所馆长、所长归校长兼理之说”(注: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209页。)。
风气转移之下,与日本学术界的交往渐由学者个人进而为有组织进行,如互赠书刊、邀请讲学等。北大国学门借天时地利之便,积极活动,成为其中的要角。与之交换刊物的有日本东亚协会、考古学会、京都文学会、东洋协会学术调查部等(注:《北京大学日刊》1504号,1924年6月25日;1517号,1924年8月30日。)。继今西龙之后,1923年,东京大学教授泽村专太郎、国学院大学教授田边尚雄来华,在北京大学等处讲演“东洋美术的精神”及“中国古代音乐之世界的价值”,北大国学门也聘请泽村为通信员(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1卷4号。)。今西龙和泽村还参加国学门的活动(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之恳亲会》,《晨报》1923年10月1日。)。1925年1月,来华考察的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应邀在北大国学门讲演“风俗品的研究与古美术品的关系”(注:《研究所国学门通告》,《北京大学日刊》1610号,1925年1月9日。)。后来顾颉刚等人呼吁保护江苏吴县保圣寺的杨惠之塑像,即得到大村西崖的响应。他于1926年春专程前来考察,回国后写成《塑壁残影》一书,引起叶恭绰等人的关注,经过努力,终于修成保圣寺古物馆,移像其中。1925年北大筹建东方文学系,固然出于研究日本的时势需要,但也不无东方文化事业这一背景的影响。
中日学术交流升温和北大积极的对日态势,使得急需合作伙伴的日本考古学者自然把目光投向这座中国的最高学府。1925年,滨田耕作和负责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的原田淑人以及朝鲜总督府的小泉显夫、原满铁的岛村孝三郎等人,鉴于日本考古学机构基础不好,欲图振兴,希望与中国学者合作,以便参与殷墟等处的实地发掘。他们选中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为合作对象。日本原有考古学协会,不是由大学的专门考古学教授及其教研机构组成,与北大考古学会的性质不同。为了对等,日方遂筹划以东西两京帝国大学的考古学机构及教授为核心,组织东亚考古学会。该会计划将来扩充到所有公私立大学的考古学专任教官和研究室,但对大学以外的团体加入该会,鉴于中方的北大考古学会未予承认,暂不考虑。只是作为个人会员,则不论是否属于其他团体,均一视同仁。其会则明确规定,以东亚各地的考古学调查研究为目的;如有必要,可与中国方面性质相同的机构联盟。可见其预期目标即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滨田耕作在两年后撰写的纪念文章中对此明白宣示,不加隐讳(注: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2卷4号,1927年5月。感谢狭间直树教授特为复印此文见赠。)。
坚持以大学的专门学者与机构为限,很可能不仅表现了日本学者的自律,更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于日方其他机构乘机插足以图浑水摸鱼的警惕。因为在东亚考古学会的筹备及此后的活动中,朝鲜总督府和外务省文化事业部起着重要作用,满铁和关东厅也积极介入。1916年,日本殖民当局在朝鲜京城设立博物馆,开始为期5年的古迹调查事业计划, 主管机构为日本枢密院。在后来兼任古迹调查主任的关野博士主持下,发掘乐浪郡汉墓,所得丰富宝藏令世界震惊。关野到欧洲访问研究期间,滨田耕作和原田淑人出任调查委员。1921年,朝鲜总督府设学务局,将本来由枢密院管辖的朝鲜半岛古迹调查事业移交该局负责,成立了古迹调查课,从事调查和保存,1931年,以学术振兴会为核心主干成立的朝鲜古迹研究会,继续朝鲜总督府古迹调查会的事业(注:《大正十年度政务提要》,《朝鲜》83号,1922年1月;官藤田亮策编《乐浪の古坟と遗物》,《朝鲜》120号,1925年5月;梅原末治:《考古学六十年》,159页。)。而关东厅和满铁, 则积极参与后来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发掘。
东亚考古学会于1925年秋组织完毕,但尚未正式成立,便直接寻求与北大考古学会结盟。当年9月下旬,滨田、 原田乘再度发掘朝鲜乐浪汉墓之机相继来华,与北京学术界广泛交流意见,“以为东方考古学之研究,非中日两国学术机关互相联络不易为功”,并举行学术报告会,得到北大国学门考古学会的马衡、沈兼士、陈垣以及朱希祖等人的积极响应,双方决定合组东方考古学协会。为此,首先邀请马衡访问朝鲜,参观引起世界瞩目的乐浪郡汉墓发掘。10月中旬,由研究地质、热衷考古的大新矿业公司理事小林胖生垫付资助,马衡由留学北京畿辅大学的智原喜太郎陪同翻译,如约前往朝鲜,先后参观了乐浪郡汉墓、江西郡高勾丽时代的古墓壁画和朝鲜总督府博物馆,与京都大学教授天沼俊一,东京大学教授村川坚固、田泽金吾,朝鲜总督府博物馆馆长藤田亮策、小泉显夫,京城大学预科校长小田省吾、教授名越那珂次郎、高田真治、黑田干一,东京美术学校讲师小场恒吉,新泻高等学校教授鸟山喜一等交游畅谈。归国后在北大国学门举行演讲会,报告此行收获(注:马衡:《参观朝鲜古物报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卷4期,1925年11月。)。
在中日两国考古学界彼此沟通之下,1926年6月, 滨田耕作和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来北京,双方正式结成东方考古学协会(注:《学问の思ぃ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ご》,《东方学》25辑,1963年3月。据顾潮《顾颉刚年谱》,东方考古学会成立于 1926年6月30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127页。该书误记为东亚考古学会)。另参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2卷4号。)。1926年6月6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在公教大学召开第四次恳亲会,小林胖生应邀出席,并发表关于其古代箭镞收集和研究的演说(注:《研究所国学门第四次恳亲会纪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1卷1号,1926年10月。)。6月30日,以北京大学第二院为会场,召开了东方考古学协会的第一次总会即成立大会,中日双方联合举行公开讲演,并得到中日及欧洲学者的祝贺。其会则规定:该会的目的在于交换知识,以谋求东方考古学的发达;研究结果将以日、中、欧三种文字发表;隔年于日中两国轮流召开研究总会(注: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2卷4号。)。此外,选举了委员、干事。7月3日,日本学者归国前在北京饭店设宴答谢中国学者,出席者有沈兼士、沈尹默、张凤举、徐旭生、陈垣、林万里、罗庸、翁文灏、李四光、马幼渔、朱希祖、裘子元、黄文弼、顾颉刚等,其中多数为与北大相关而热衷于考古事业的学者,当是参与东方考古学协会的骨干(注:《顾颉刚日记》1926年7月3日。感谢顾潮女士寄赠此条资料。鲁迅也曾接到邀请,辞不去(《鲁迅全集》14卷《日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606页)。裘子元时为教育部办事员,好金石碑刻。)。
按照双方约定,1926年秋应在日本召开第二回总会,并举行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因预定出席的中方学者有所不便,耽搁下来(注: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2卷4号。)。1926年11月,岛村孝三郎等再来北京,与中国考古学者协商,定于明年3月开会,并邀请中国学者派人赴会(注:《东亚考古学协会》,《文字同盟》1号。)。1927年3月27日,在东京大学召开东亚考古学会成立大会及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回总会,同时举行中日学者的公开讲演会。中方讲演者为北京历史博物馆编辑部主任罗庸和北大的马衡、沈兼士,讲题依次为“模制考工记车制述略”、“中国之铜器时代”、“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日方讲演者滨田耕作、原田淑人、池内宏,讲题为“支那之古玉器与日本之勾玉”、“汉人之缯绢”。池内原定讲乐浪出土之封泥与朝鲜古史的重大事实,后因病未写成文,另外担任东亚考古学会及东方考古学会干事的小林胖生也随同赶赴东京(注:《东方考古学协会公开讲演会》,《史学杂志》38编6号,1927年6月。)。中国学者在东京参观了帝室博物馆、东洋文库等学术机构,并访问京都、奈良、大阪等地。4月上旬, 沈兼士一行取道朝鲜归国,途经汉城,在儿岛献吉郎、高桥亨以及小林、高田、森等日本学者的介绍陪同下,参观了京城大学、朝鲜总督府博物馆、李王职雅乐部,并到清云洞观看韩巫舞(注:《汇报:参观》,《京城帝国大学学报》 2号;天行:《侨韩琐谈》之三《清云巫舞》、之四《雅乐》,《语丝》134、137期,1927年6月4、26日。)。
1927年夏秋,为了抵制占据北京的奉系军阀取消国学门的企图,由叶恭绰主持改组为国学研究馆,叶亲任馆长。研究馆下设总务、研究、编辑三部,其研究部分为哲学、史学、文学、考古学、语言文字学、艺术及其他七组(注:遐庵汇稿年谱编印会编印《叶遐庵先生年谱》,1946年。另据日本《史学杂志》39编5号(1928年5月)《北京に於ける考古学研究机关》,研究部分六组,无其他一组。)。1928年4月 28日至29日,东亚考古学会在京都召开第二次总会,并举行公开讲演会,中方亦派北大国学馆导师马衡、刘复以及馆长叶恭绰的代理阚铎等人出席。会期第一天为东亚考古学会总会,于乐友会馆召开,报告该会进行的事业,并观看貔子窝发掘以及朝鲜庆州古迹调查实况的电影。次日上午到京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参观貔子窝发现的遗物,午后举行公开讲演。马衡、刘复的讲题分别为“戈戟之研究”、“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日方演讲者高桥健和小川琢治(代法国学者E.Licent宣读从天津寄来的论文)的讲题分别为“ 日本上代の马具より见たる大陆との交涉”、“Ordos 河畔に於ける旧石器时代遗迹并びに东蒙古に於ける新石器时代遗迹に关する调查报告”(注:《东亚考古学会第二回总会》,《史学杂志》39编6号,1928年6月。)。
1929年10月19日,东方考古学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三回总会,并举行讲演会,由滨田耕作、梅原末治、徐炳昶、张星烺分别演讲“世界各国研究东亚考古学的现势”、“Seythai 文化在欧亚考古学的意义”、“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古工作之概略”、“中国人种中之印度日耳曼种分子”(注:《东方考古学协会讲演会》,《北京大学日刊》2259号,1929年10月19日。)。
在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名义下,中日象征性地进行了几次合作考古发掘与调查。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联合进行貔子窝发掘,参与其事者有东京大学原田淑人、田泽金吾、驹井和爱、宫坂光次,京都大学滨田耕作、小牧实繁、岛田贞彦,关东厅博物馆内藤宽、森修,朝鲜总督府博物馆小泉显夫,以及东亚考古学会干事岛村孝三郎、小林胖生等人,中方的马衡、陈垣、罗庸、董光忠中途前来参观,并在其中一处亲自发掘。所以滨田耕作称此项发掘虽由东亚考古学会单独进行,却可以作为日中两国学会亲和的一个事例。只要北大考古学会和东亚考古学会不断重复同样的行为,则成立东方考古学协会的效果,将不仅体现于学会本身的事业(注:滨田青陵:《东方考古学协会と东亚考古学会》,《民族》2卷4号。)。1928年10月东亚考古学会发掘牧羊城,北大考古学会派助教庄尚严前来参加发掘一周。作为还礼,1930年北大发掘河北易县燕下都、老姥台,也请日方学者参加。双方还协议互派留学生,从1928年起,日方每年一人,先后派到中国留学的有驹井和爱、水野清一、江上波夫、田村实造、三上次男。中方因经费困难等原因,派往日本的仅有1928年度的庄尚严。1930年3月, 原田淑人由东方文化事业部出资,到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讲学两个月,与北大、清华、燕京等校及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者广泛交流(注:《史学系通告》、《史学系教授会通告》,《北京大学日刊》2341、2367号,1930年2月18日、3月21日。)。其讲演给中国学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北大、清华举行系列讲演“从考古学上看古代中日文化关系”时,因前来听讲的学生人数太多,不得不换到大教室(注:《学问の思ぃ出——原田淑人博士を围んで》,《东方学》25辑。)。
三
日方在东方考古学协会成立后表示:“考古学——特别是研究东亚考古学,实为东方诸学者所负一大人类义务。这是数千年栖息于此、有悠久传统和众多遗产的亚细亚民族的特权。日中两国学者合组的东方考古学协会,可使此‘亚细亚之光’于人类文化史上灿然生辉”,以此为该会存立的意义并预祝其未来的发展(注:《东方考古学协会公开讲演会》,《史学杂志》38编6号,1927年6月。)。而中国学者显然也有借此光大本国文化和发展学术的期望。只是双方对于如何利用这一机缘并发挥各自的作用,想法并不一致。
日方动议日中合组考古学机构,公开宣称是“为促进东亚诸地的考古学研究,与各国特别是邻邦中华民国考古学界增进友谊,交换知识”(注:东亚考古学会:《貔子窝·序言》,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1929年。),实际上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利用合作名义,便于在中国境内调查发掘,尤其想参与举世瞩目的殷墟发掘;二是派遣留学生来华学习和考察。此举与日本的大陆政策以及风尚转向东方主义相吻合,因而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其发掘考察及派遣留学生,均由外务省、关东厅和朝鲜总督府提供资助。而中方虽然也有引进外国财力和技术的愿望,以落实长期不能付诸实现的实地考古发掘设想,却较少政府意愿,并限于学术本身。因此,在东方考古学协会的旗号之下,双方的不和谐时有表露。首先在名义上, 东方考古学协会与东亚考古学会不时混淆。如1927年东京大会,既是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二次年会(注:《新书介绍:考古学论丛》,《北平图书馆月刊》1卷5号,1928年9、10月。), 又是东亚考古学会第一回总会。而1926、1929年的北京会议和1928年的京都会议,则分别为东方考古学协会第一、三回总会和东亚考古学会第二回总会(注:刘复:《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辅仁学志》1卷1期,1928年12月。)。两会的交错和中日双方各自强调与己关系密切的一面, 使得社会上乃至学术界误传甚多。关于第一次貔子窝发掘的主办者, 1927年8月日本《史学杂志》38编8号刊登消息《貔子窝の发掘》,声称系以东方考古学协会名义组织;桥川时雄主办的《文字同盟》3 号报导此事,也以《中日学者合作之发掘古物》为题,称“日方好古之士,与中国国立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国立历史博物馆代表陈垣、罗庸、董光忠、马衡等四人共参其事”。“发掘所得,暂由京都帝大运回整理。俟整理后,运送北京一部分,交北大考古学会及历史博物馆陈列”。而后来日方撰写报告书时,则以东亚考古学会和关东厅博物馆的名义,并得到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和关东厅的援助,报告书出版也标名为“东亚考古学会东方考古学丛刊甲种第一册”。亲历其事的庄尚严回忆,组织东方考古学会除互相观摩、交换学生外,还“互相参加两国自己举办的考古发掘工作”(注:庄尚严:《妙峰山·跋》,引自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65页。)。滨田耕作专文介绍两会的联系与区别,立意之一,当也在澄清误会。
然而,名义上的不协调反映了双方实际利益和态度的差异。在此期间,中日关系以及东方文化事业经历了重大风波。1928年4月, 日本第二次出兵山东,并于5月3日制造了济南事变,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中的中国委员全体辞职以示抗议。日方虽未废止原订计划,但将发展重心转到在国内创办东方文化学院(注:黄福庆:《近代日本在华文化及社会事业之研究》,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45),1982年, 156、178页;山根幸夫:《东方文化学院の设立とその展开》, 《近代中国研究论集》,东京山川出版社,1981年。)。形势逆转之下,1929年北京的讲演会虽仍使用东方考古学协会之名,可是预定发表演讲的协会委员朱希祖不仅未做报告,还于前一天分别向北大考古学会和东方考古学协会提出辞呈,理由是:“本会自成立以来,进行重大事务,如发掘貔子窝牧羊城古物事件,均未经本会公开讨论,正式通过,致有种种遗憾。委员仅属空名,协会等于虚设。希祖忝为委员之一,对于上列重要事件,其原委皆不预闻,谨辞去委员,以明责任。”(注:《东方考古学协会委员朱希祖先生辞职书》,《北京大学日刊》2260号,1929年10月21日。)由此可见,日方在中国东北进行的各项考古发掘,对其国内虽然坚持声称以东亚考古学会的名义,但在中国境内,为了活动与交流的方便,确实借用了东方考古学协会的名义而未经双方具体协商。朱希祖的辞职,代表了参与其中的中国学者对于日方诚意的怀疑和对其行为的强烈不满。
在学术范围内,日方的参加者还能保持学术良知与真诚,没有凭借武力进行掠夺性发掘。其活动以合同方式进行,必须有中国学者到场。在合作的名义下,日本考古学界独自举办的考古发掘顺利进行,还趁机广交中国学者,密切彼此关系。来华留学和访问的日本考古学者、学生因而获见《宋会要》稿本、《皇明实录》等珍稀秘籍,参观中国学术机构在殷墟等地的发掘现场,甚至集体深入蒙古、绥远、察哈尔,考察古长城和细石器文化遗迹,收集匈奴时代的青铜器。1930年4 月来华留学的江上波夫,一年内先后到察哈尔、山东、旅顺、绥远、内蒙考察,活动完成,留学生活也告结束(注:《学问の思ぃ出:江上波夫先生を围んで》,《东方学》82辑,1991年7月。)。东方考古学协会解体后, 东亚考古学会仍在中国境内进行了大量考古发掘活动。
东方考古学协会对中国现代考古学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从事考古活动的中国学者乃至多数在中国进行考古发掘的欧洲学者,大都半路出家,并非考古专门出身。滨田、原田等日本学者,曾在欧洲接受正规的考古学训练,使用的方法十分精密,在乐浪汉墓发掘中实际运用,令前来参观的中国学者颇受启发,而“此种考古途径,在我国尚未有人著手提倡也(注:《新书介绍:考古学论丛》,《北平图书馆月刊》1卷5号。)”,促使中国的旧式金石学加速向近代考古学转化。马衡回国后即派国学门事务员董作宾赴上海请蔡元培组织殷墟和汉太学遗迹等发掘。以后又与北平研究院携手,亲自担任易县燕下都考古团团长,发掘老姥台(注:傅振伦:《马衡先生传》,《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595页。)。1926年10月, 与北大国学门渊源甚深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顷闻北京大学考古学会与日本东京、京都两帝国大学之东亚考古学会,共同组织一东方考古学协会,为国际的研究考古学机关”,要求校方“一面推举代表,参加该会,一面由本校组织一发掘团”,声称:“非实行探险发掘,不足以言考古学的研究”,欲借此使中国的考古学“于世界学术界中占一位置”(注:《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发掘之计划书》,《厦大周刊》158期,1926年10月9日。)。后来又计划与北京大学联合进行风俗调查和古物发掘,“南方风俗则本校担任调查,北方发掘则请北大担任招待,如是既省经费,而事实上亦利便多多。”(注:《国学研究院成立大会纪盛》,《厦大周刊》159期,1926 年10月16日。)
不过,东方考古学协会内部的分歧,最终还是削弱了日本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力,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北大考古学会,影响反而不及清华研究院。日方重视北大国学门考古机构,原因之一,是后者在北京的考古学机关中具有官学至尊的地位,这被看重政府行为的日本学者认为是对华施加影响的有力支撑。与此相对,他们视美国系的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中的考古学机构为“私学”的代表。后者以人类学讲师李济为主,设有考古学陈列室和考古学室委员会,由李济担任主席(注:《北京に於ける考古学研究机关》,《史学杂志》39编5号,1928年5月。)。凭借较多的资金以及和美国考古学家的有效合作,清华的考古学稳步发展,成效明显,后来成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的台柱。据说该组成立时,马衡要求加入,为所方拒绝。在交往过程中,日方似乎察觉到偏颇,注意加强与清华研究院等机构的联系,以图调整弥补。但预期通过组建东方考古学协会达到参与殷墟发掘的目标,因其事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承担,而该所负责人傅斯年素有“义和团学者”之称,李济等人又先此与美国的毕士博合作,日方虽曾通过来访的北京图书馆金石学研究室研究人员刘节了解有关情况,并派梅原末治、内藤乾吉、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前往参观(注:《北支史迹调查旅行日记》,《东方学报》(京都)7册,1936年12月。),始终未能实际参与。
1920年代,中国学术界在疑古风潮的涌动下,对上古文献大胆怀疑,而将信史的重建留待考古学事业的发达。早在1921年1月, 胡适就宣布其古史观为:“先把古史缩短二三千年,从《诗三百篇》做起。将来等到金石学、考古学发达,上了科学轨道以后,然后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长东周以前的古史。”1924年底,李宗侗在《现代评论》1卷3期发表文章,认考古学为解决古史的惟一方法。顾颉刚虽然指其“颇有过尊遗作而轻视载记的趋向”,但只是针对有史时代,总体上则承认其所说“确是极正当的方法”(注:顾颉刚编著《古史辨》(1),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2、268—275页。)。当时王国维以著名的二重证据法重建古史,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高赞誉。其实,王国维的所谓地下资料,仍是传统金石铭文的继续,而非正规的考古发掘,更不是实物形制研究。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自成立之日起,就认定实物与遗迹较载籍之于上古史更为重要。只是一直困于财政与技术,加上其中的专家还有金石彝器的本行,迟迟未将考古发掘付诸实践。在此期间,北大虽然在与瑞典学者斯文赫定联合组织的西北考察团中扮演要角,仍然重采集轻发掘。与日本东亚考古学会合作,本来未必不是良好机缘,可以在重建古史的活动中占据重要位置,因为这恰好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从发端而初盛的时代。以成果卓著的殷墟发掘为代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论,其观念宗旨的渊源明显由北京大学国学门、厦门大学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一脉相承,但具体事业却主要继承清华研究院国学科,以至于后人不免误解抹杀,将北大国学门视为单纯疑古。而北大在实行考古发掘方面陷入困顿,其他原因之外,作为合作伙伴的日本东亚考古学会难辞其咎。正是在与之合作的过程中,北大坐失了天时地利的良机,最终不得不将首席国立大学在这一至关重要领域的应有地位拱手让人。
来源:《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
- 0000
- 0003
- 0000
- 0001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