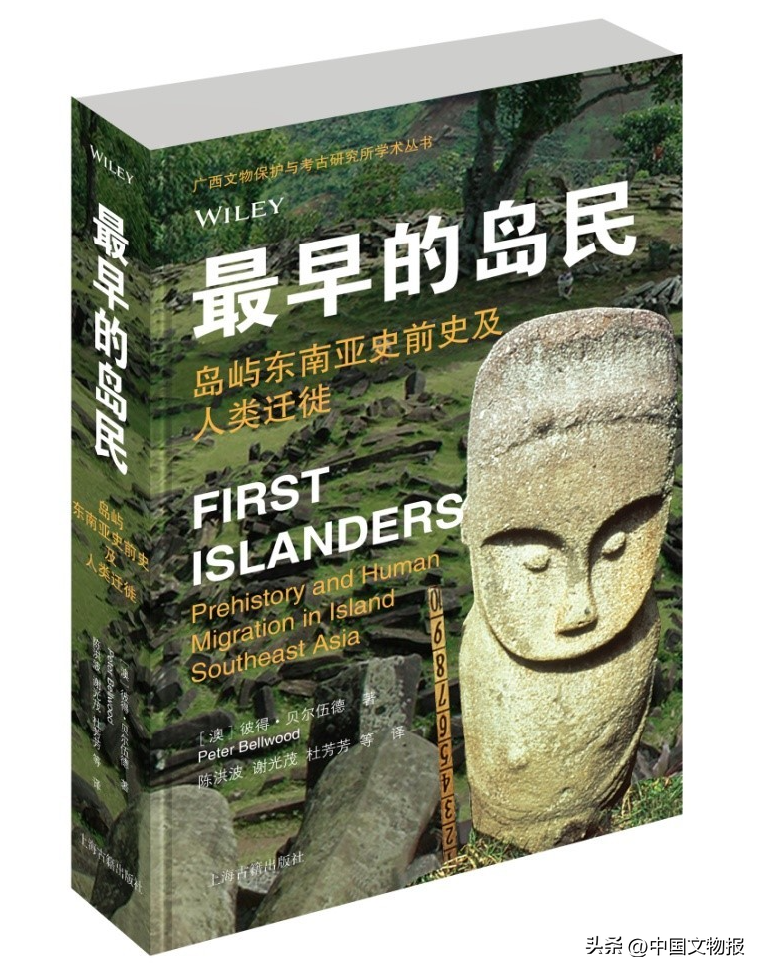朱凤瀚:试论中国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
经过近年来热烈的讨论,大家对中国文明起源这一重要学术课题已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但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仍有较大的分歧。这其中,我以为如何科学地认识与理解中国早期文明(按:这里指社会已进入文明阶段,但处于早期)的物化表现可能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本文仅就此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一
由于中国早期文明的同时代文字记载资料尚未发现,后世的文献中有关的记载也很缺乏,且含有一定传说成份,所以,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主要要依赖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这是大家都没有异议的。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留下的实物,研究文明起源自然也是要发现、考察文明的物化表现。所以,科学地认识、归纳与理解中国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应该是对中国文明起源作考古学观察的基础。
回顾前一阶段的中国文明起源研究,可以说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进行:一是探讨与论证中国早期文明的“标志”或称“因素”(实际上都是指文明的物化表现)包含哪些内容,说明各种“标志”或“因素”的发生、发展的过程,以及某一考古学文化是否具备了这些“标志”或“因素”,即是否进入文明。二是用聚落考古的方法研究文明的起源与形成,这种方法虽然也是在研究文明的物化表现,但重在从聚落形态演变(特别是作为中心聚落的都城的形成)角度阐述文明形成的过程,力图避免上述第一个角度的研究方法中某些不科学的、简单化的倾向。第三种角度则是比较中国与西方在文明起源、形成的原动力及过程(或说程序)上的共同点与差异,比如从金属工艺(如青铜工艺)应用的范畴说明文明形成的动力的差别(是政治因素还是生产技术为主)。
从以上第一种角度作研究,已有相当多的学者提出批评或持保留意见,认为不同地区文明标志是不同的,而且学者之间也往往有不同的看法,企图用比较固定的模式来套中国的情况未必适当。这是有道理的。由于世界各古代民族步入文明时期的人文的、历史的与地理的条件不尽相同,所以其早期文明的物化表现也会有所差别。如果一定要说只有具备哪几种带普遍性的标志(或因素)才算进入文明,确实有不科学的一面。这样一来,即产生一定矛盾,一方面,探寻中国文明时要有可操作性,即需要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与手段去发现和论证中国早期文明形成时的物化表现,找到足以反映文明出现阶段的若干考古学文化特征(这方面形不成一个看法,则以上第二个角度的研究显然就没有一个科学的下限,文明形成过程的研究思路就不会清晰;第三个角度的研究也不可能有作比较的具体对象与考虑问题的着眼点);另一方面,又确实不存在一种为人类社会普遍适应的早期文明出现的物化表征。
因此,解决这个矛盾的唯一方法,是摆脱模式化的研究方法,实事求是地从考古学已揭示的且已为世所公认的中国较早期文明的历史实际出发,归纳出中国较早期文明在特定的人文、历史、地理条件下所显现出来的物化表现,亦即特定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并以此为参照与出发点,通过考古学的方法与手段(并与其他学科相结合)来进一步寻找、发现并认识年代更早的早期文明。
有一个事实是大家都承认的,即迄今为止可以确认的中国比较早期的文明是商文明,能有较多了解的较早期的国家是商王国。约在公元前16世纪始建立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商王国,是自此后约5个世纪内东亚区域内先进文明的代表。而且,据文献记载,在商王国形成前若干世纪(即殷墟甲骨刻辞所示汤以前先公阶段),商民族曾在华北平原内多次迁徙,不仅与其有所接触的古代民族可能有血缘的融合,也必然有文化的融合,逐渐汇成商文明的基本文化特征。而且商民族在南渐过程中,与盘踞在豫西(及晋南)的夏人发生接触与冲突,也必然吸收了应该是已步入文明阶段的夏民族的若干文化因素。所以,商灭夏以后形成的商文明,并不是简单地在一个较封闭的区域内,在一种单一文化基础上形成的,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若干古代民族共有的传统的文化特征。而且商文明在初步形成后凭藉其已具有的国家机构扩张其势力范围与文化影响,同时也就进一步吸收了周边区域甚至更远地区的文化因素。所以商文化的许多特征具有相当宽泛的涵盖面,我们可依据已取得的研究成果,来归纳商文明最重要的物化表现,分析其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因素,亦即对考古学资料作深入的人文历史思考,藉以作为探寻客观上应存在的、比商文明更早的文明之基本文化特征的参考,并以此为基础,加深对有关考古学文化是否具有文明物化表现的意义与其所能反映的文明化程度的理解。这种由下向上推,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由于是从中国历史实况出发的,应该具有可操作性。
二
根据20世纪中国考古学研究对商文明的了解,可以将其主要考古学文化特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以宗庙、宫室等大型夯土台基宫殿建筑群为核心(未必皆在中心位置)的都城(多数有规模宏大的较宽厚的城垣)的设立。
(二)独立于一般非王贵族与平民墓地以外的大型陵墓区即王陵区的存在。王陵有规格远超出一般大、中型墓的巨大的墓室与丰厚的成组的随葬品。
(三)青铜礼器与青铜兵器被比较广泛地使用。
(四)已能记载语言的文字的应用(按:早商时期的文字发现甚少,但殷墟甲骨文系统的文字已是较成熟的文字,在此前必当有一个较长的发展时期。早商时期商人已使用了此种文字,事在情理之中)。
即使不考虑后世文献与殷墟甲骨文资料所指示的情况,仅就商文明以上几点文化特征,也可以认为当时已属于一个比一般所谓复杂社会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已有了国家。因为以上几种文化现象确实包涵着丰富的社会因素,以物化的形式综合反映了一种文明形态。
讲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以往在有关文明起源的讨论中,通常径将文明的诸种物化表现称为文明的因素,严格而言,这是不确切的。现在中国历史学界与考古学界所讲的“文明”,一般是用作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认为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即步入文明阶段,国家是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本文没有在文章开首即摆明所用文明之概念,亦缘于此。但是“文明”一词历来可有多种解释。夏鼐先生在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基本上采用这个说法,但在同文中他也说明有人认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惟读此文,他说文明的“起源”在新石器时代,可以理解为文明初生,也可以理解为文明诸因素的开始出现。夏先生的意思在这里可能是指前者,介绍了“文明”的另一用法)。所以,文明既是指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则它不等于若干考古学文化现象的集合。如果说文明的因素,也应该是指社会因素,诸如:A.社会分工的扩大;B.社会分层化的加剧,等级与阶级的形成;C.作为贵族集团利益代表的君主(王)的出现;D.具有超经济强制权力的政治权力机构的形成(如政府、官吏、常备武装等国家机器)。文明的物化表现,应该是分别地、具体地体现了类似的几种文明社会因素,所以也可以更直接地称为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
上面列举的商文明的几点文化特征,所以能称为是商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从以下表一所列举之更详细的现象及所作更为细致的分析可以看明白。

列出表一的用意,主要是想比较具体地解剖商文明的几种重要的文化特征各自所能象征的文明的社会因素究竟是什么,是对考古学资料做社会的历史学的理解。
对表中所列有关青铜器生产的事项还应再着重作一说明。在目前发现的几座商代都城内及附近,只发现有铸造青铜器的作坊,说明从矿石中冶炼铜及其他矿料应是在采矿地点完成的。根据对从偃师商城时期到殷墟文化三期的青铜器中铅同位素的测定资料,可知这些青铜器中都含有一种地质上十分罕见的高放射成因铅,而出有此种铅的矿产区应该位于与商王国所在地并不近的西南地区(注:金正耀《二里头青铜器的自然科学研究与夏文明探索》,《文物》2000年第1期。类似的看法亦见平尾良光《古代中国青铜器の铅同位体比》,收入《日本中国考古学会会报》第九号,1999年10月。)。所以,在当时开采、运输(也可能包括掠夺、强迫贡纳)、铸造青铜器的金属原料本身即体现了具有相当强的征集、调动人力(包含武装力量)及财富的能力这样一种国家行为。
这几种文化现象中有一部分与西方学者所归纳出来的文明出现的主要现象,即文字、城市、金属工业、宗教性建筑、伟大的艺术(注:张光直《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收入《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从类别上看多有重合。在目前还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说明有所重合缘于文化传播的情况下,则只能用基于人类在思维与创造力上的共性,在物质生产与精神文化发展到类似高度时会造就相类似的文化成果来解释。这也说明,从世界范围看,文明在刚出现时,物质与精神文化方面会有某些近于必然的体现。
但是,上举商文明中有几种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是具有浓厚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特色的。如以宗庙为主的礼仪性建筑在都城中居明显的位置,正合乎先秦文献中所言“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而且宗庙类礼仪建筑与众多贵族墓葬中出土的成组的青铜礼器,都体现了以维护父权宗族内部的等级关系为目的的礼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此外,青铜冶铸工艺基本上未应用(或说未直接应用)于改良农具,而主要是用来铸造礼器、兵器,亦与古代中国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相吻合。
与上述商文明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相联系的是商文明聚落形态中的一些特点,亦即都城布局方面的特点:都城一般有具防御功能的夯土城垣(仅晚商的安阳小屯殷墟遗址尚未发现,惟在宫殿区西、南两面有壕沟环绕。都城在无必要以城垣作防御设施时自然可以不设,西周时亦然,也是特点之一);都城中地势较高处建有以王室宗庙等大型礼仪性建筑为主的宫殿区,实际上构成了都城的中心与重心;以为王室与王朝官吏消费服务为主要职能的各类手工业作坊围绕宫殿区分布;王陵在距宫殿区稍远的高地独立存在;王室宫殿区附近周围分布有贵族及平民的居址与家族墓地。商代都城布局的上述特点显然是与社会分层所形成的金字塔形结构相适应的,尤其是突出显示了王室贵族,特别是王的崇高地位。
以上所归纳的商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形式、聚落形态的某些特征,以及对它们所反映的社会形态的分析,似可以作为追溯、探索比商文明更早的、更古老的文明形态时的参考。也就是说,古代中国比商文明更古老的早期文明很可能有与商文明相近或相类似的上述物化表现。当然,中国地域广大,商文明诞生于黄河中下游,古代中国的其他地域范围内如果有与商文明同时或更早的文明形成,是否一定会与商文明诸因素的物化表现相同,自然不能讲得太绝对。但是如上面所分析的,商文明诸因素的物化表现,既有与世界其他古代民族早期文明相重合之处,又颇具中国古代文化之特色,对在中国土壤上滋生起来的其他文明的探寻应该是有借鉴作用的,至少上面所谈对商文明物化表现内涵之人文的、社会的、历史的理解,对于认识与理解、诠释其他考古学文化中与文明有关的现象是有帮助的。
三
文明的形成必然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以采用有的学者的“文明化”提法,即将“文明化”理解为构成文明的诸多社会因素由出现、发展、汇聚而形成文明的整个经过。上文曾举出文明的几个较重要的社会因素,它们彼此有联系,如A项(社会分工)、B项(社会分层)二者间有因果与相互促进的关系,而C项(君主、王)、D项(政治权力机构即国家机器),应该是在A、B项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会出现,是派生出来的因素。当然,这也即是说,就这些因素本身而言,它们各自所能昭示的文明化程度是不同的,C、D两项可能与文明形成有更直接的关系。但这几项因素本身又各有自己的发展过程,即从萌生、逐渐强化至形成。例如王的出现,虽是社会层级化的最终产物,但对外族的战争也是王权形成的因素,而王权是从首领权逐渐发展而形成。那么所谓文明,应该是类似这些社会因素,在同一个社会共同体范围内,都已各自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程度时的综合体。
按照这种分析,作为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也应该与这些社会因素在文明化过程中的发生、发展、相互影响及最后的综合有大致对应的关系。具体而言,从考古学角度做文明起源的研究,似应该注意以下两点:
(一)单独的文明因素之物化表现的存在虽可反映某一种文化所属社会文明化的程度,但未必即能说明文明已形成。即使是能体现上举C(君主、王)、D(政治权力机构)两项社会因素的出现,也要考虑由于它们本身有个发展、形成的过程而对其反映的社会文明化程度做适当的估计。
(二)只有文明诸重要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在同一时间段、同一地理区域内均以较高的发展水准汇聚为一体,从考古学的角度而言即体现于同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同一时段中,说该社会已进入文明阶段理由才比较充足。
当然,也可能某一文化所属社会已步入文明,只是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或文化遗存保存不好,与文明诸重要社会因素直接相关的物化表现未能得以全部揭露,以致影响对该文化性质的认识。但是从严格的学术研究角度出发,还是以做更深入的工作,或等待更新的发现来做结论较为妥当。
下面,在以上两点认识的基础上,参考商文明的物化表现,对早于商文明的区域性考古学文化所代表的社会之文明化程度做一些思考。
偃师二里头遗址中最能显示其文明化程度的遗存有三点:第一,规模较大的成组的夯土宫殿群基址,附近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第二,墓葬中出土的青铜酒器已属礼器范畴(四期墓已出现爵、斝的组合,这类酒器作为礼器主要用来作祭祀祖先的祭器);第三,出土的青铜兵器中有较多属一次消耗性的镞,反映青铜工艺已较发达。以此几点物化表现与商文明的物化表现相比,显然还是有欠缺的,比如迄今未发现可以认定的文字,没有发现较大型的够上王陵的墓葬。此外二里头遗址内部的布局也还未完全搞清楚,从聚落考古角度看,它与周围其他二里头文化遗址间的层级关系也不很清晰。现在的情况是,多数的中国考古学家已把二里头文化视作夏文化(夏王朝的文化)。得出这种认识恐怕不完全是凭藉对上述文化遗存从文明诸因素物化表现角度所作分析,而是考虑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晚期可以与早商文化相接(末尾可能在时间上有一段重合),其文化分布地域和存在年代落在文献所记夏王朝的主要活动区域和时段内,这种时空关系的相合、文献的印证,坚定了学者们对二里头文化性质的认识,并因而肯定其所属社会已进入文明。严格而言,对二里头文化的认识是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记载进行相互印证的成功探索(顺便说一下,中国原史考古学,能有后世文献记载相佐证,是得天独厚的,而且没有理由认为古人会凭空编出个夏王朝来)。单就其所含有的可作为文明诸因素之物化表现而言,要更确切地证实文明形成,还需要做进一步工作。但是应该指出,将上举二里头遗址中的几种重要的遗存与上文所列举的商文明同类现象相比照,可以认为二里头文化反映了其所属社会中文明的一些重要因素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程度,而且也颇具中国文化特色,所以,二里头文化中更多的文明物化表现如王陵,甚至文字的发现也许是个时间问题。
近年来,在史前(及原史)考古中不断有重要发现,例如辽西属红山文化的凌源、建平交界地的牛河梁的祭祀遗址(发掘者称为“女神庙”)与积石冢群(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喀左东山嘴大型祭祀建筑群址(注:郭大顺等《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0年第11期。);太湖地区位于浙江余杭西部良渚、安溪、长命、瓶窑四乡镇地区内的以莫角山为中心的良渚文化遗址群(含有大型建筑遗迹、祭坛与大墓群)(注:参见任式楠《中国史前城址考察》,《考古》1998年第1期;任式楠《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考古》2000年第7期;严文明《良渚随笔》,《文物》1996年第3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山东境内多座龙山文化城址(注:参见上注[5]引任式楠文;《龙山时代考古的重大收获》,《中国文物报》2000年5月21日;张学海《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文物》1996年第12期;(美)安·P·安德黑尔(陈淑卿译)《中国北方地区龙山时代聚落的变迁》,《华夏考古》2000年第1期;宿白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1997年。)。由于这些重要发现远高出所属文化中一般遗存的规格,特别是多显示了权力体制的形成与社会层级化的鲜明,从而使研究者很自然地将这些发现作为文明的物化表现,并对其所属社会的文明化程度作出较高评价。但是这些遗存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应如何理解仍值得作认真的推敲。
红山文化上述祭坛性质的大型建筑遗址应是属于一个较大规模共同体的祭祀中心,对某种神灵体系的崇拜显然有维系整个共同体的作用。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修筑这种大型祭祀建筑无疑要耗费共同体内大量的人力;而且大型积石冢墓的墓制与随葬品之比较精美,表现出与普通墓葬之间墓主人等级、身份的差异。将这两种遗存所反映的问题相联系,所能说明的是所属社会内社会成员已有较明显的分层,上层成员有支配下层成员从事劳役的权力;积石冢中出土的部分玉饰与大型祭祀遗址中出土的陶塑人像之制作水平,表明当时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程度已达到较高程度,与社会分层的水平相协和。所以,仅就现已发现的资料,即可以认为牛河梁、东山嘴红山文化遗存昭示了其所属社会的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等社会因素已发展到较高程度,在此基础上,共同体的上层首领也已相对显贵化,不仅拥有集中财富的权力,也有支配与役使共同体成员的权力。这都说明这样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的趋势已很明显,应对其文明化的程度有足够的认识。但遗址中冶铸金属的遗存不能证明与遗址同时,且未有文字的迹象,说明社会物质生产的技术水平与知识文化的水准还不是很高,社会分工还未达到文明社会应达到的程度;较大型积石冢墓中随葬的玉饰的情况与墓地的布局(与小型石板墓共处于同一墓地),未能充分证明已有国家君主(王)的存在,也不能反映与父权宗族制度相联系的礼制的形成;而且大型祭祀遗址只能认定为祭祀中心,尚未发现具都城性质的遗址与其他居住址,聚落层级化是否存在亦尚未搞清。鉴于上述情况,现在即认为红山文化已进入文明阶段,已有国家形态似还缺乏足够的物化表现的证据。
相对红山文化来说,良渚文化的遗存所显示的该社会文明化的程度要高出一个层次。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上:(1)良渚文化已存在独立于小墓群以外的较大型墓地(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基地发掘简报》,同上刊。);(2)较大型墓有相当丰厚的远超出一般墓葬的随葬器物,主要是成组的玉器类随葬品,且部分已有棺椁;(3)较大型墓的随葬物已有较固定的组合形式。瑶山墓地中,南组墓出玉钺及石钺与琮,但不出璜,北组墓则出璜、纺轮,不出玉钺。玉钺、琮与璜不出于同墓的情况亦见于反山墓地。随葬玉钺,也可能与商代较大型墓随葬青铜大钺的意义是相近的,是用来象征权力(是否皆象征军权还应再研究)。随葬琮,如果琮有像《周礼·大宗伯》所言有“礼地”的功用,则象征墓主人有主持祭祀礼仪的身份。不同类的玉器既已有社会功能的象征,亦可用来区分身份、性别,即已有了礼器的性质;(4)玉器制作已达到相当精致的程度,特别是其中饰有浅浮雕的所谓神人兽面的玉琮,表现了高层次的专业水平;(5)良渚聚落已形成以莫角山大型长方形土台遗址为中心,含有50多处在规格上有明显级差的遗址(及墓地)之遗址群。上述现象说明良渚文化社会分工、社会分层已更为明显,共同体内的上层在社会地位上比红山文化积石冢的墓主人要进一步贵族化,与中下层成员已有了更明显的差距,有了更大的控制社会财富及支配、调动劳力与专业化的手工业者集团的权力;类似于礼器的随葬物中以玉钺、玉琮配男子,以玉璜、纺轮配女子,体现了对上层成员中男性的统治权力的强化与对女性社会地位的规限;聚落的层级化出现,表现了一个有相当空间范围的层级化社会的形成。
但是,用上文所举出的较早期的文明之物化表现作比较,现已揭露的良渚文化遗存距离充分显示国家与文明之形成亦有一定差距,例如,如果反山、瑶山墓地即是良渚文化最上层显贵的墓地,则从此类墓地的墓位布局看,更像是上层首领与其配偶的家族墓地,两个最高规格的墓,也同时葬有配偶(?)或身份较低的亲属,与王陵独立设置、专门突出王的地位那种“独尊”的局面尚有差别。而且,类似反山、瑶山这样的墓地在莫角山西北不远就有汇现山墓地(其中M4也是厚葬玉器,有玉钺、琮的大墓)(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7期。)。此类墓地的墓主人最大的可能是统属于良渚文化圈内的若干个较大共同体的各自的首领(与其近亲)。此外,大墓随葬的玉器虽已有近于礼器的作用,但不能证明有祭祖先的功能,所以良渚文化遗存所显示的宗教崇拜未必包含祖先崇拜,其所属社会似还没有进入父权的宗族组织阶段。而如上文所述,二里头文化可能已步入此阶段。再有,良渚文化虽有发达的制玉工艺,但迄今尚未发现金属器与冶铸遗存,没有能被确切证明已使用了文字,能够确认是都城性质的遗址亦尚待进一步的揭露与证实,也就是说尚缺少反映社会发达程度的最一般性的物化表现。因此,至少目前在有些工作还需要更深入地去做的情况下,对于良渚文化的社会文明化程度虽应给予充足的评价,但对于其是否步入文明阶段则应持较谨慎态度。
根据现已掌握的资料可将良渚文化所属社会的特点概括为:社会成员明显分层,权力与财富急剧向上层显贵集中,而且形成以显贵居址与大型礼仪性建筑为中心的层级化的聚落布局。对于这样一个处于文明化发展到较高阶段但未必进入文明、未必形成国家的社会,1997年许倬云先生在吉林大学作讲演时曾提出,应将之归属于“离国家形态还远”的“复杂社会”(处于“初期的国家”与“正规的国家”前的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他强调的是社区、社群之间的等级关系(注:许倬云《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北方文物》1998年第3期。)。当然,“复杂社会”也有用得较宽泛的,比如史徒华(Julian H.Steward)所讲的“复杂社会”即包括了国家阶段(注:史徒华(Julian H.Steward)著、张荣启译《文化变迁的理论》一书中第三节《实际研究》中第11小节《复杂社会之发展:早期文明之发展的试探》,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4年11月。)。也有的学者称此种社会为“酋邦”(chiefdom)(注:谢维扬《中国早期国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这种看法肯定了良渚文化的前国家社会之性质。惟“酋邦”概念说法不一(注:参见张光直《从夏商周三代考古论三代关系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收入《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陈淳《酋邦的考古学观察》,《文物》1988年第7期;又上[9]引文。),综合诸家见解,其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像社会显著分层,少数上层成员享受占有各种资源的特权;已有最高首领,只是权力机构还没发展到国家水平;多聚落形成层级关系等,与良渚遗存已揭露的情况大致相合。但是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工作还正在进行,还有待深入。比如独立的较大型墓的墓地的存在,虽显示了上层显贵集团的特权,但尚未能比较明确地显示作为个人的首领的权力;从聚落考古角度看,像莫角山那样的中心聚落内部的布局情况及其与下属各层级聚落及墓地的相互关系(含相对的时空关系)也尚未能取得具体资料。红山文化的社会性质与良渚社会相近,但可能在发展水平上略逊。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众多城址及相邻聚落的研究对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形成有更为直接、更为密切的关系,一是因为在空间上,黄河中下游地区是夏商文明根植的土壤,在文明渚因素的物化表现亦即考古学文化特征方面必然有直接的承袭与影响关系;二是从时间上看,黄河中下游地区龙山时代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至前2000年间,与夏商文明产生年代亦相衔接,自然应成为探寻早期文明的重点。龙山时代的城址,目前在河南和山东都发现了多座。这些城址多是所在区域内规模最大的中心聚落,周围有不同级别的较小聚落,从外观上看,可能也形成了层级化的聚落群结构。在一些城内,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如河南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等,其中像新密古城寨城址内还有大型建筑基址。个别城址内还发现冶炼铜或铸造青铜器的遗存(如平粮台出土有炼铜渣,登封王城岗更出土有铜容器的腹部残片)与陶窑等,平粮台城门道下还铺了陶排水管道。山东邹平丁公城址出土刻有不同于殷墟甲骨文系统的另一种文字的陶片。上述文化现象已与上文所归纳的商文明诸因素的物化表现中的一部分相接近,表现出龙山社会文明化已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但这些城址面积较早商城址都要小得多,而且平面形状也较多样化,可见还处于早期较初级的城市阶段,也不排斥其中较小者属军事城堡。由于大多数城址都未作系统的钻探与试掘,所以城内遗存还多未能讲清,而且中心城址与周边聚落文化的时空关系,与某一特定的中心城址相联系的居住者内上层显贵的墓地(现已发掘的这一地区内的龙山大墓较少,山东临朐西朱封大墓M202及较小的泗水尹家城M4随葬陶器(注:于海广《山东龙山文化大型墓葬分析》,《考古》2000年第1期。),表明已有陶礼器制度,但组合形式两墓不尽同,说明这种组合因地域、家族等因素而有别。但两处墓地都还未发现与中心城址的联系),类似这些问题也都有待作深入的考察。因而,尽管无论从已发现的遗存所带来的信息,还是从历史的逻辑的推测来看,龙山时代城址呈现早期文明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工作还未做得很细致的情况下即肯定其所属社会已步入文明似乎亦还缺乏充分的证据。
四
学者或提出,中国早期文明是以中原为中心的多元一统的格局,意即中原早期文明是中原史前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周围文化的影响,汇聚周围地区多种文化的先进因素而形成的。这一见解,从理论上看是客观的、全面的。但其中有的问题似亦值得思考,如既然早期文明的研究主要要靠考古学的方法与手段,那么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原早期文明中的“多元”亦即多种文化因素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能够说明多少问题呢?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可能只能从已属早期文明,或处于文明化过程中的中原某考古学文化遗存的特征上去考察,比如金属器、陶器、玉器的工艺特征,各类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又比如城垣与建筑的构造形式与建造方法,文字的符号特征等,从这些方面体现出来的周围文化特点来说明中原文化受到哪些考古学文化的影响,与哪些文化有过交流,说明这些文化交流对早期文明的文化面貌的形成究竟起到什么作用。
但是,上文已提出过,严格而言,文明作为一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概念,其形成(对原生文明而言)主要是所在地区内以某种考古学文化为表征的共同体(古代民族共同体)内部诸社会因素(如上文所举出的类如社会分工、社会分层、王与政治权力机构等)自我发展、演进的过程,当然不排斥社会因素也会受到来自其他民族共同体的影响。而上述考古文化遗存中反映出来的多元的文化因素,只是文明诸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在伴随社会因素的发展而发展过程中,由于文化交流而形成的特征。因此,如果把研究仅局限于考察这种物化表现所显示的多元的考古学文化的特征,虽可以了解上文提到的多种考古学文化交流对文明的文化面貌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或进而透过这些现象,去推测民族共同体间血缘的与文化的交融之过程与程度,但是并不能具体地展现文明诸社会因素自身发展到一定高度终而汇聚形成文明的社会的历史的过程。
根据上面的分析,对中原地区早期文明的研究即应该着重从两个方面进行:
其一,是应该加强作为中原地区早期文明“载体”的共同体自身文明化过程的探讨。即通过研究反映该共同体文化面貌的考古学文化的来源、发展、演化过程,特别是研究其中作为文明诸社会因素物化表现的发展过程来系统地说明该共同体步入文明的途径。比如,对于夏文明的探索,似应在以前研究的基础上,在进一步全面揭露二里头遗址文化面貌以更充分地从考古学上证实夏文化的同时,着力探讨其文化来源,探讨反映在二里头文化中的诸社会因素物化表现的初生形态;对于商文明,则应进一步加强对早商文明形成过程的考察,不仅从考古学文化类型角度探寻二里岗文化的直接前身,而且应加强对早商文化中出现的各种文明社会因素的物化表现发展过程的研究。只有通过上述工作,才有可能较具体地勾画出中原地区早期与较早期文明自身形成的主线,并作出历史学的阐释,这将对研究中国文明的形成有极重要的意义。
其二,从考古学文化类型角度,具体地探讨中原地区早期与较早期文明诸社会因素物化表现形式与内涵的多种文化来源,比如反映在各种器类的形制、工艺、艺术特征或其他文化遗存方面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因素,进一步揭示中原早期文明与其他地区文明(或文化)的联系,判断其所受到的影响或相互影响的程度。比如良渚文化虽在发展到一个相当发达的状态后即比较快地消失了,但其以琮为代表的玉器之工艺、形制、纹饰及其使用制度等都可能对商文化有过影响,这是不少学者均曾注意到的,然而两种文化间有较大的时空差距,这种影响是通过何种中介产生的,即是需要细细研究的问题。
来源:《文物》
- 0000
- 0000
- 0000
- 0001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