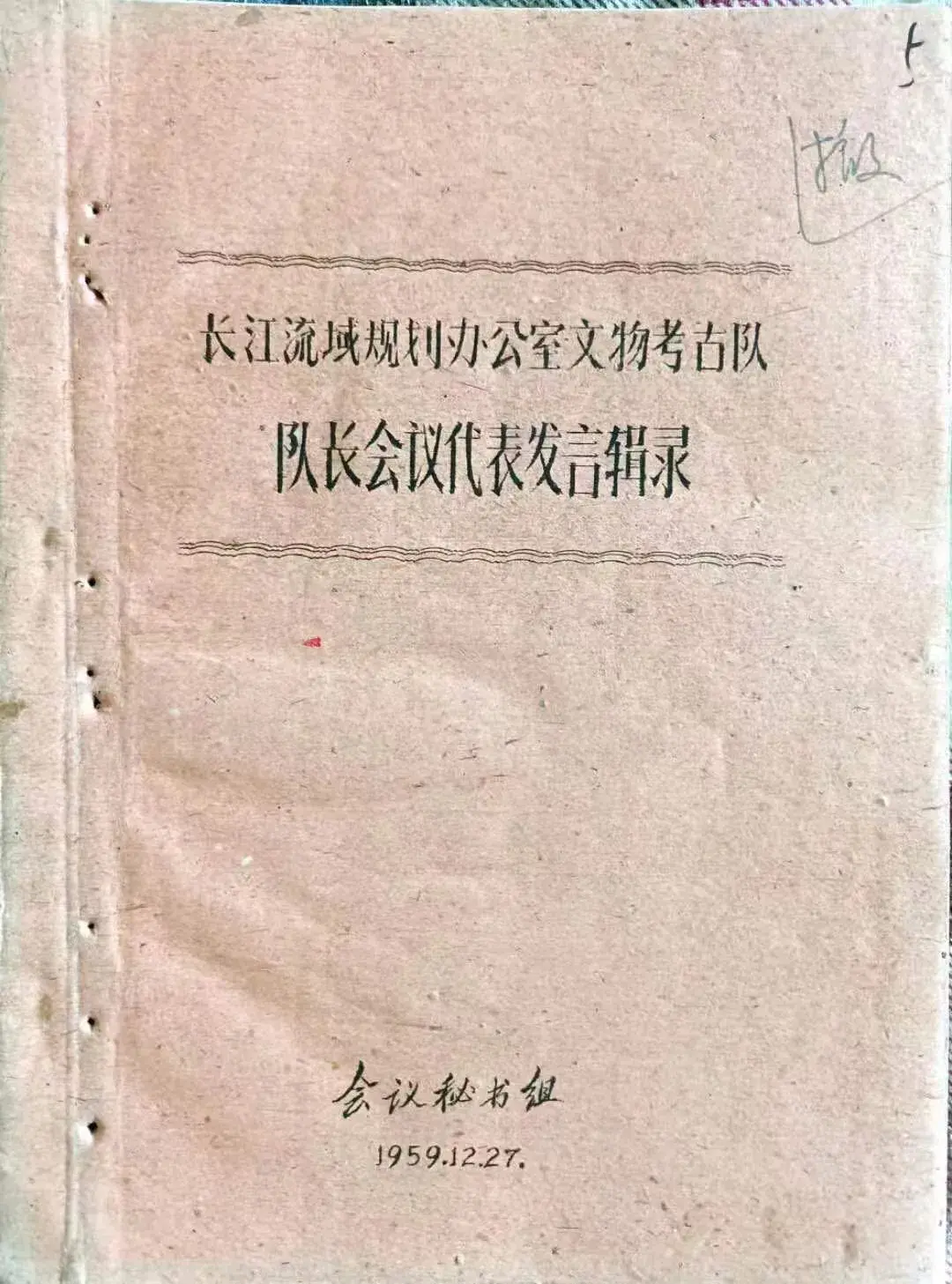李学勤:王国维《桐乡徐氏印谱序》的背景与影响
2005年是清华研究院——即通常说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80周年,大家将纪念这一曾在学术界起过重大作用的机构,缅怀当年于院中执教的诸位学者。
在研究院的四位导师里,王国维先生的任职时间最为短暂,他1925年4月迁来清华,1927年6月2日就辞世了。然而,他在一生的最末段落,继续活跃于学术的前沿,做出了创新的业绩。
本文所要谈到的《桐乡徐氏印谱序》,是王国维于1926年10月左右撰作的,差不多是他关于古史和古文字学方面最后的文章了。从体裁看,虽然只是一篇序文,字数也很少,实际却是论辨性的专论。我们绎读王国维的种种著作,与其他学者往复探讨的固然不少,专作论辨者实很罕见。王国维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写这篇文章的,这篇文章在学术史上有什么影响和作用,是这里想讨论的问题。
王国维立意写这样一篇论辨性的文章,是在1926年8月。查《王国维年谱长编》,该年8月18日条云:“为讨论古文问题,致函罗福颐。”[1](P484)罗福颐字子期,系罗振玉的第五子。王国维的这封书信已录入《王国维·书信》一书,信中说:
近有人作一种议论,谓许书古文为汉人伪造,更进而断孔壁书为伪造,容希白亦宗此说,拟为一文以正之。[2](P435)
结果形成的,便是这篇《桐乡徐氏印谱序》。
《王国维全集·书信》的编者,在对王国维上述信件的注释中已经说明,信里提到的“议论”出自钱玄同先生,见于《古史辨》第一册。
读《古史辨》可知,钱玄同有关许书即《说文》的议论,始于古史讨论刚刚展开的1923年。那一年的4月28日,顾颉刚先生致函钱玄同,有下列一段话:
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上,读到先生的跋。跋上说,“许慎的《说文》是一部集伪古字,伪古义,伪古礼,伪古制和伪古说之大成的书。”我很希望先生有辨《说文》的文字发表。[3](P66)
同年5月25日,钱玄同作《答顾颉刚先生书》,说:
“辨《说文》的文字”,现在还不能就做,因为我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狠浅。我现在只能将疑《说文》的理由简单奉告:
许慎是表彰“壁中古文经”底文字的。“壁经”之出于刘歆“向壁(即孔壁)虚造”,经康有为和崔觯甫师(注:崔觯甫,即崔适。)底证明,我认为毫无疑义了。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所以说是“伪古字”。“伪古义”如“告,牛触人,角着横木,所以告人也”,“射,弓弩发于身而中于远也”之类。“伪古说”,如“楚庄王曰,止戈为武”,(注:按《说文》系引《左传》宣公十二年文。)“孔子曰:一贯三为王”之类。至于“伪古礼”和“伪古制”,这是从伪经上来的,若将伪经推翻,则《说文》中这两部分便不攻而自倒了。[3](P81-82)
这封信曾刊登在该年6月10日出版的《努力周报·读书杂志》第10期。
西汉时出现的孔壁中经系刘歆伪造的说法,如钱玄同自述,是来自康有为,实际上“壁经既伪,则其文字亦伪”,从而否定《说文》所收古文的观点,在康有为的著作里也已经有了。
康有为在有关这一问题的代表作《新学伪经考》的《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下》节中讲:
(刘)歆窥其时学者破碎,枝叶丛蔓,……乘其空虚,挟校书之权,藉王莽之力,因以伪文写伪经,别为《八体六技》以惑诱学士,昭其征应。《说文·序》称:“孝平时,征爰礼等百余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又称:“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然《史记》共王无得古文事,张苍传授亦歆伪托,则是实无古文。[4](P688-689)
他还说《说文》一书,“其说经说礼皆古说,则纯乎歆之伪学也”。[4](P689)不难看到,钱玄同的观点正与康有为一脉相承。
钱玄同关于《说文》古文的意见,有一点是和康有为不同的。
《说文·序》云:“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这是说孔壁中经等古文与出土“鼎彝”铭文即金文属于一系。康有为否定古文,为了反驳许慎之说,竟认为“鼎彝”也是刘歆伪作的:
歆既好博多通,多搜钟鼎奇文以自异,稍加窜伪增饰,号称“古文”,日作伪钟鼎,以其古文刻之,宣于天下,以为征应。以刘歆之博奥,当时不能辨之,传之后世,益加古泽。市贾之伪,不易辨其伪作,况歆所为哉?许慎谓鼎彝“即前代之古文”,古文既伪,则鼎彝之伪,虽有苏、张之舌不能为辨也。[4](P688)
由于古文字学的进展,特别是在金文以外又有了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钱玄同先生自然不赞成康有为的想法,并认为其论“极谬误”。[3](P238)他的看法则是《说文》古文“与甲文金文不合”。《答顾颉刚先生书》曾提到:
至于《说文》中所谓“古文”,所谓“奇字”,乃是刘歆辈依仿传误的小篆而伪造的,故与甲文金文底形体相去最远。[3](P81)
而这个看法又成为他涉及“古文”问题的第二封书信的核心。
钱玄同这第二封信,写于1925年12月13日,后在1926年1月27日出版的《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15、16合期上发表,也收入《古史辨》第一册,题为《论说文及壁中古文经书》。这封信是因为柳诒征先生有《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文,顾颉刚先生作了答复而引起,但也可以说是实现了5月信中写“辨《说文》的文字”的允诺。
信中对《说文》总的评价是:
《说文》“说字”之不“通”,是由于许老爹的瞎三话四。……可惜许老爹既没有历史的眼光,又没有辨伪的识力,竟把不全的《史篇》中的大篆,《仓颉篇》等中的小篆,跟刘歆他们“向壁虚造”的伪经中的古文羼在一处,做成一味“杂拌”,于是今字跟古字,真字跟假字,混淆杂糅,不可理析,不但不可以道古,就是小篆也给他捣乱了。所以《说文》中所列的文字,其价值还比不上《隶辨》、《楷法溯源》、《草字汇》等,只堪与《汗简》跟《古文四声韵》相比耳。[3](P236)
关于《说文》古文,钱玄同说:
我尝稍稍涉猎吴(大澂)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容(庚)诸家之书,觉得《说文》中的小篆近于钟鼎,钟鼎近于甲骨,而《说文》中的古文则与钟鼎甲骨均极相远,而且有些字显然是依傍小篆而改变者。[3](P238)
并引用罗振玉的话证成其说。
罗振玉1910年作《殷商贞卜文字考》,发现甲骨文字“同于篆文者十五六,而合于许书所载之古籀乃十无一二”,认为后者“皆列国诡更正文之文字”;1914年作《殷虚书契考释》,又讲:“许书所出之古文仅据壁中书,所出之籀文乃据《史籀篇》,一为晚周文字,一则亡佚过半之书,其不能悉合于商周间文字之旧,固其宜矣”。钱玄同说:
商代的甲骨文能合于秦汉的小篆跟隶书,反不能合于《说文》所录出于壁中书之古文,则壁中古文之为后人伪造,非真古字,即此已足证明。[3](P239)
这里需要特别说一下,罗振玉在上述两书里所说,兼指《说文》的籀文、古文,钱玄同却只提古文,这可能也是受到康有为学说影响的结果。《新学伪经考》云:
《汉书·艺文志》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则非歆之伪体,为周时真字断断也。子思作《中庸》,犹曰:“今天下书同文”,则是自春秋至战国绝无异体异制,凡史载笔,士载言,藏天子之府,载诸侯之策,皆籀书也,其体则今之《石鼓》及《说文》所存籀文是也。子思云然,则孔子之书六经,藏之于孔子之堂,分写于齐鲁之儒皆是。秦之为篆,不过体势加长,笔画略减,如南北朝书体之少异,盖时地少移,因籀文之转变,而李斯因其国俗之旧,颁行天下耳。[4](P683)
否定了古文,在秦汉篆文以前只有籀文,是合乎康有为推论的逻辑的。不过钱玄同先生没有正面讲到这一方面,这里无须深论。
接着,钱玄同就对王国维作了批评。
原来,王国维在1916年春有一篇著名的论作《史籀篇疏证序》,同年冬又写了《汉代古文考》[1](P144、181),随后都收入1923年初版的《观堂集林》。这些文章根据《说文·序》所言战国时期诸侯力政,“言语异声,文字异形”,集中研究了《说文》籀文、古文,提出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
《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间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5](P154)
并自信“此说之不可易”。[5](P186)他还讲到:
自秦灭六国,席百战之威,行严峻之法,以同一文字,凡六国文字之存于古籍者已焚烧产刬灭,而民间日用文字又非秦文不得行用,……故自秦灭六国以至楚汉之际,十余年间,六国文字遂遏而不行。汉人以六艺之书皆用此种文字,又其文字为当日所已废,故谓之“古文”。[5](P187)
钱玄同针对这一说法,在信里说:
王氏自信“此说之不可易”,据我看来,不但“可易”,而且还着实该“易”,我现在便来“易”它一下。
秦之“同一文字”,……是用专制的手腕,所以要“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秦所要“罢”的系专指形式“不与秦文合者”而言,大不合的固然要罢,小不合的也是要罢,因为目的在于使文字统一。六国的文字究竟比秦文差了多少,这个我们固然不能臆断,但就现存的钟鼎看来(连秦国的),则可以说这样几句笼统话:要说异,似乎各国文字彼此都有些小异,要说同,也可以说是彼此大体都相同;ㄍㄨㄟㄌ一ㄅㄠㄗㄨㄟ(注:注音字母,即“归里包堆”。)一句话,大同小异而已。若区为“东土”“西土”两种文字,则进退失据之论也。[3](P241-242)
所用措词应该说是比较激烈的。
从王国维作出反应的时间来看,他恐怕没有读到最先刊出钱玄同书信的刊物,获知这些“议论”的途径当系1926年6月印行的《古史辨》第一册,以致他给罗福颐写那封信已经是8月中旬了。罗福颐先生专精古玺印研究,所以,王国维信中说:“兄所集大鉨(玺)文字,其中与《说文》古文同者,如‘恒’字之类当必不少,祈录示”[2](P435),可见他正在为论辨文章搜集证据。
王国维的论辨,是有一个过程的。
在致罗福颐的信之后,大约8月、9月之间,王国维给容庚写了一封信。[2](P436-438)容庚先生就是给罗福颐信中提到的“容希白”,1922年经罗振玉推荐,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为研究生,1926年毕业,留北大任讲师,后转至燕京大学任教。[6](P5-6)王国维致容庚的这封信,以反驳钱玄同说为主旨,可与他后来写的《桐乡徐氏印谱序》合读。
9月26日,王国维的长子潜明在上海病故,在此前后,王国维都在那里料理。当时浙江桐乡人徐安(字楙斋)曾请他为所编古玺印谱撰序。10月17日(注:《王国维年谱长编》第483页误为15日。),王国维返回北京。23日,他致函在上海的友人蒋汝藻之子穀孙说:
徐氏印谱其书名已定否?楙斋之名并籍贯并希见示,以序中需此也。序文大致已就,尚未写出,因弟本欲作一文论六国鉨(玺)印、货币、兵器、陶器(与《说文》之古文(注:《王国维全集·书信》第443页误将“古文”排为“故”字。)一家眷属)并当时通行文字,乃欲借此序以发之也。[2](P443)
由此可知《桐乡徐氏印谱序》的内容正是他从8月就计划写的。这篇文章的完成,应在10月末至11月间。
《桐乡徐氏印谱序》继续发挥了“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的观点,其特色是从大量的古文字材料出发,文中称:
三代文字,殷商有甲骨及彝器,宗周及春秋诸国并有彝器传世,独战国以后,彝器传世者唯有田齐二敦一簠及大梁上官诸鼎,寥寥不过数器,幸而任器之流传乃比殷周为富。[5](P182)
他所谓“任器”,是指近世出土的六国兵器、货币、玺印、陶器等,其数量以百千计,字体与秦之文字都不相同,而与《说文》和魏三体石经所载的壁中古文相似。
为了证明壁中古文与六国古文字材料字体的相似,王国维在《桐乡徐氏印谱序》中列举了许多实例,最后说:“以上所举诸例,类不合于殷周古文及小篆,而与六国遗器文字则血脉相通。”[5](P184)六国文字和汉人传述的壁中古文一样,“并讹别简率,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小篆,不能以六书求之”。[5](P182)
王国维说:
世人见六国文字,上与殷周古文、中与秦文、下与小篆不合,遂疑近世所出兵器、陶器、玺印、货币诸文字并自为一体,与六国通行文字不同;又疑魏石经、《说文》所出之壁中古文为汉人伪作,此则惑之甚者也。夫兵器、陶器、玺印、货币,当时通用之器也;壁中书者,当时儒家通用之书也。通用之器与通用之书,固当以通行文字书之。且同时所作大梁上官诸鼎字体亦复如是,而此外更不见有他体。舍是数者而别求六国之通行文字,多见其纷纷也。[5](P183)
这便是王国维对钱玄同提出的问题所作的答复。他以多量的六国文字出土材料作为证据,说明当时东土六国的字体的具体状况,然后证明《说文》等古文与之相似,这样也就推论出壁中古文有其依据,解决了钱文的质疑。
王国维关于六国“通行文字”的论断,在古文字学上是非常有价值的。他在《桐乡徐氏印谱序》里说:“其上不合殷周古文,下不合秦篆者,时不同也;中不合秦文者,地不同也。”[5](P183)是对这种“通行文字”作出时间、空间上的界定,也揭示了六国文字作为中国古文字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意义,开启了这方面的专门研究。
对于《桐乡徐氏印谱序》所取得的成果,王国维先生很是珍视。他当时曾把这篇文章和1916年写的《史籀篇疏证》序及《汉代古文考》里的两篇,作为讲义发给清华研究院学生⑥[7](P11-12),又在11月出版的《实学》第6期发表。12月1日,他还把研究院讲义寄给在北大国学门的友人马衡。[2](P448)
今天,战国文字研究已经扩充成为中国古文字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尤其是六国文字的研究,由于地下材料不断发现,正在突飞猛进。回顾这方面的发展历程,我们应当特别纪念王国维先生的《桐乡徐氏印谱序》这一名文。
来源:《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