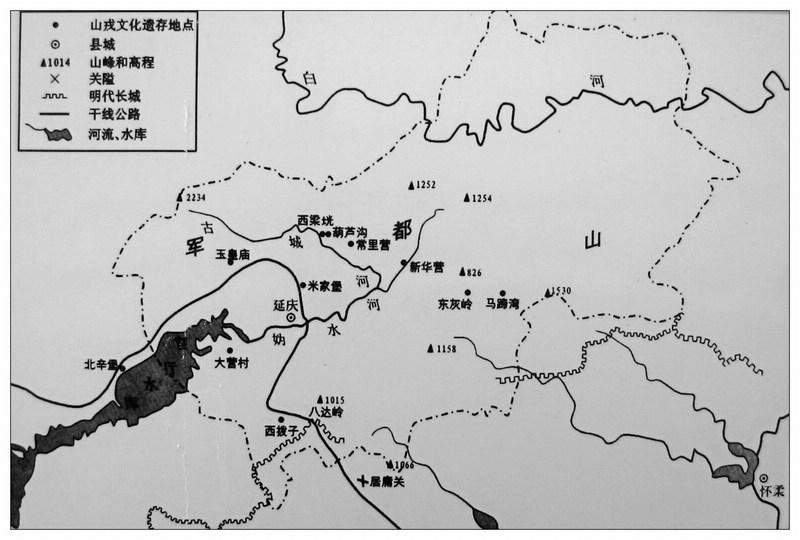李学勤:简帛佚籍的发现与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
中国有着总结学术发展的悠久和优良传统,向上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业已经历了从原始时期到夏、商、西周三代之变。对于错综复杂的远古文化,孔子从学术史的角度将其归结为“六经”。《庄子·天运篇》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孔子对于“六经”虽然做的主要是学术综合的工作,即“述而不作”,但这一开创性的学术总结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中说:“中国学术具最大权威者凡二:一曰孔子;一曰‘六经’。孔子者,中国学术史上人格最高之标准,而‘六经’则中国学术史上著述最高之标准也。”[1](P2)
春秋战国时期,学派蜂起,百家争鸣,学术文化得到了空前繁荣发展。但由于后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经籍百家遭到严禁,致使学术为之一变。汉惠帝时,下令废除《挟书律》,百家思想重新活跃起来,学术为此又起一变。在中国学术史研究方面,汉初有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西汉末期有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别录》,东汉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学术史研究从此绵延不绝,各个朝代官修或私修史书,一般都有总结前代学术的专门章节,或曰《艺文志》,或曰《经籍志》,目的都是为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一
但是,由于秦代毁灭性的焚书,致使中国大量的古代书籍严重失传,以至后代出现了一些所谓续作的“伪书”,而且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传世的书面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总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歪曲和变化。对此,历代学者不断对某些“伪书”进行甄别和审查,其工作具有一定的价值。然而,从清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出现了风靡一时的“疑古思潮”。崔述运用司马迁“考信于六艺”的方法,以经书中的某些记载驳斥诸子百家中所载之古史,写作了《考信录》,认为后世所传的古史大半是战国诸子所假造的,主张中国的信史应始于唐、虞时代。到了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连经书也不信了。认为“六经”是孔子为托古改制所作,孔子不是“六经”的整理者而成了其作者,这就把孔子之前的远古文化大都抹杀了。
实际上,这种疑古思潮不单出现在中国,在同一时期的日本和欧洲,也有人对中国的古史表示怀疑,他们的见解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如日本的白鸟库吉的“尧舜禹抹杀论”,曾经名噪一时。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疑古之风愈来愈盛,胡适先生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上古史不可靠”为由,丢开唐、虞、夏、商,仅从《诗》三百篇讲起。顾颉刚先生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古史辨派”,提出“层累造成”的古史观,认为中国古代有关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尧、舜、禹、汤等传说,时代出现得越晚,内容就越丰富,认为中国人对古代的看法是历代人不断地造伪的结果。
从当时中国思想和文化的实际来考察,疑古思潮具有积极和进步的意义。从中国思想史角度看,疑古思潮的兴起同后来的“打倒孔家店”紧密相联,对于挣脱儒学束缚、打倒经学偶像发挥了重要作用,故从促进国人冲破封建思想的罗网方面来看,疑古思潮在思想史上具有进步的意义。从学术史角度看,疑古派的初衷是为了更准确地把握古史,严格审查记载古史的文献,这对于那些认为古代传下来的经书是万古不变的教条、坚持古代是黄金时代的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解放思想,促进学术正常发展的积极作用。但是,客观地说,疑古思潮也有着严重的问题和缺陷,由于他们的辨伪工作做过了头,把许多古代文献的史料价值全部否定了,以致造成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空白。在当时的疑古思潮中,曾出现一种极端的说法,即“东周以上无史”论。中国原有的五千年历史文化,一下子减少了一半,从而否定了中国上古文明史。
在1992年的一次学术座谈发言中,我提出要“走出疑古时代”。这个提法给我带来很大麻烦,一些学者对我产生了许多误解。按照顾颉刚先生的说法,“古史辨”实际上就是古书辨。很长时间以来,我们都是通过古书来了解古史。如果说很多古书都不可信或不属于那个时代,古史的可信度则要大打折扣。当时,通过考古出土了许多竹简、帛书等古代文献资料,新的考古发现使一些受到质疑的古典文献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本来面貌,人们逐渐认识到古代并非不可认识,古代文献和传说中具有很多可信的因素。这样便自然地超出了过去的“疑古时代”。
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材料都要经过研究者的审核、分析与判断,要疑古,你得把发掘出来的材料研究清楚后再说话,不疑古,你也得把发掘出来的材料研究清楚了再说话。总之,对中国古史和历史传说、对“三皇五帝”疑与不疑、信与不信其实都没有关系,关键是拿出证据来。1920年代,顾颉刚疑古,李济、徐旭生等先生就去找地下的材料。疑古没错,疑得对不对,需要同出土材料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之后才能作出判断。当年,傅斯年先生说,“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顾颉刚先生也说,“我们知道学问应以实物为对象,书本不过是实物的记录”[2]。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意见。尤其是当今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遗存和史前遗存,对于古书、古史信与不信、伪与不伪,最终都要通过分析当前以及今后陆续出土的实物和文献为证。
二
1925年,王国维先生发表《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提出“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并分析了当时四大发现对中国古史研究发展的贡献。第一,1898年甲骨文的发现和随后的研究,改变了人们对古代特别是商代的看法,打破了以前的“东周以上无历史”的观念;第二,西域木简的发现,改变了人们对汉晋历史的根本认识;第三,敦煌文书的发现,扭转了人们对经书和唐史的许多观点;第四,清代内阁大库三千多麻袋档案被罗振玉成功抢救,为人们的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上述四大发现为中国学术史的发展带来重大改观。
20世纪是中国考古大发现的世纪,其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考古发现改变了传统的学术研究方法。由考古发现带来的启示,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3](P33)在此之前,无论是宋学还是汉学,都是以文献来论证文献。但由于文献的可信性难以得到保证,这种方法实际上是有缺陷的。例如,先秦书面文献的撰写和传播过程非常复杂,从远古时代人们的口耳相传,到书写到竹帛之上,其中肯定会有某些走样的地方。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纷援引古史传说,为其政治主张寻找理论依据,为此,人为地改造古史的状况在所难免。而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古籍遭到巨大的人为破坏,到汉魏以降,还有所谓“五厄”、“十厄”之说。因此,研究先秦历史文化,仅仅采用书面文献,显然不足。
而那些埋藏于地下历史材料,均为当时历史文化的如实记录,并因长年沉眠地下而未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与改变。如有幸出土面世则能保存原有的风貌。因此,以地下出土材料印证地上书面文献,一来可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二来可以“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三来可以证明那些即使被司马迁斥为“不雅驯”的如《山海经》等古籍,“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在“二重证据法”之后,有学者还又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即地下出土材料细分为有字与无字的两类。甲骨文、金文、简牍、帛书等有字的一类,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将其与书面文献互相对照和印证,便可以解决许多学术问题。王国维先生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便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而遗址、墓葬、建筑、服饰等无字的出土材料,也可以用来印证古书。
“二重证据法”一经提出,便对学术研究产生了广泛影响,许多学者运用这一研究方法撰写出版了经典性的学术专著。如董作宾的《五等爵在殷商》(1925年)、陈梦家的《商周之天神观念》(1925年)、郭沫若的《卜辞中之古代社会》(1930年)、周传儒的《甲骨文字与殷商制度》(1934年)、吴其昌的《甲骨金文中所见的商代农稼情况》(1937年)等。1970年代以来,随着考古材料的大量出土,二重证据法在中国古代史研究方面更是成就明显,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考古发现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中华文明作为人类世界著名的远古文明之一,具有独立起源、历史悠久、绵延不绝等显著特点。但在此前的中华古代文明研究中,由于资料的缺乏和观念的束缚,一方面研究的视野难以放开,另一方面研究的成果相对匮乏,少有的研究论著或者显得较为狭隘,或者存在许多片面之处。而20世纪考古发掘所取得的一系列新发现,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的传统认识,新发现的出土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许多具有深远意义的研究课题,逐步改变了中国古史研究的基本面貌。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安阳殷墟的发掘及此前的甲骨文发现,不仅使商后期的历史文化建立在坚实的出土材料基础之上,还使人们认识到,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载商代历史大致可信。由此而论,《夏本纪》所载夏代历史亦有可能真实。(2)郑州商城、堰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邢台东先贤遗址、安阳三家庄遗址的相继发现,使文献所载商前期都城地址大致有了着落,可以大致勾画出商前期的历史概貌。(3)豫西偃师二里头遗址与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使人们对夏文化有了一定的认识。(4)豫西登封王城岗遗址、禹县瓦店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夏文化的认识有可能一直追溯到夏初的禹、启时代。(5)龙山时代各种文化的发现,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6)由龙山时代文化上溯,可以探寻中华文明的源头。
而在中原地区之外,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系列的古文化遗址,这些考古发现使人们认识到,过去所谓“中原文明中心论”需要加以彻底改变,中华古文明是多源并起、相互促进的,由此也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中国古史研究的旧有面貌。
第三,考古发现深化了人们对中华文明特点的认识与把握。中国古代宇宙论包含了一系列基本概念,如道、阴阳、四时、五行、八卦、三才(天、地、人)、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等,并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一些现代学者经研究认为,这一理论系统最后定型的时间比较晚,但作为这一理论系统组成部分的若干基本概念,它们出现的时间可能要早得多。在西周或者更早的商代,有些概念便已经存在了,并构成了宇宙论的雏形。1940年代,胡厚宣先生在甲骨文中找到《尧典》中所记载的四方、四风的名称。这一发现证明,《尧典》的记载具有远古的依据。至少在商代晚期,将一年划分为四时,并以四时同四方相结合的宇宙论已经普遍流行。而西水坡龙虎图象、良渚文化中的玉璧、玉琮,凌家滩玉版等告诉我们,中国古代宇宙论萌芽的时间可能更早一些。这些考古发现都有助于加深对中国古文明特点的了解和认识。
三
1970年代以来,大批简帛书籍的陆续出土,为丰富和重写中国古代学术史提供了资料及条件。1992年,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曾谈到“重写学术史”。此后,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中进一步提出:“大量简帛佚籍的出现,证明中国古代学术史必须重写”。2001年我在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论文集书名就叫《重写学术史》。我认为,大量简帛佚籍的出土,促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学术史进行重新思考、重新认识和重新评价。
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两次简帛大发现,一次是西汉的“孔壁中经”,一次是西晋的“汲冢竹书”,两者在中国学术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1940年代以来,中国各地陆续出土了一批又一批简帛佚籍,足以与前二者相媲美。
这些简帛佚籍的出现,对于促进中国学术史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因为这些新发现简帛佚籍大部分都是我们未曾看到过的古书,据此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和认识当时的学术状况。比如,数术和方技是古代十分重要的典籍。在《汉书·艺文志》中,数术、方技各占一类,数量很大。如数术类有190家、2528卷,但目前传世的仅有一部《山海经》。近年来发现的简帛佚籍中有许多部分为数术和方技,今天我们所讲的“科学”,中国古代时归属在方技和数术之中,我们今天开展中国科学史研究,肯定不能忽视这些重要的历史资料。这些新近出土的简帛佚籍,给了我们一个难得的重新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机会,而当前这种有利的研究条件也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可使一些古书的可信性得到基本认可。战国以来的竹简帛书,大多数都是前所未有的佚书,这等于为我们打开了一个丰富的地下图书馆,使我们对古书的形成和传流过程有了一个更为深刻、全面的认识。过去人们不大知道古书是怎样形成和流传的,发现这些简牍帛书以后,方才得知古书的形成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这和纸、印刷术发明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古书的学术传播,主要是通过师传和口述,失传和作伪均不足为怪,但这也为通过出土简帛对古书进行鉴定提供了机会,因为这些当时的原本书籍就是鉴别的依据。比如过去的疑古派,包括日本的学者都认为没有《孙膑兵法》,《孙膑兵法》只是《孙子兵法》的误解,从而将它彻底否定。但在1970年代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中,《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一起被发掘了出来,还原了这部著名兵书应有的学术史地位。
再比如,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发现的竹简本《文子》,也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今本《文子》,前人多指为伪书,以为与《汉书·艺文志》所述不合,系后代赝鼎。我们最初观察竹简,见《文子》多记平王(楚平三)与文子问答,同于《汉志》,似乎更足证今本之伪。后经仔细查对,才知道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有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用新的眼光重新审查古籍,会使我们对古代学术史研究的凭借更为丰富和广泛。
此外,通过出土简帛佚籍,我们不仅可以为某些古书证真,还可以为某些古书证伪。比如,东晋时开始出现的伪古文《尚书》,经过宋、明、清几朝学者的考证证明它是一部伪书。可是一直到近些年,仍有人在为其翻案。现在的清华简中出现了真正的古文《尚书》进一步证明伪古文《尚书》是伪书。“重写学术史”不是要把过去认为是假的都要变成真的,也绝对不会后退到“信古”的阶段上去。
第二,可使一些古籍的属性和成书时代得到大致的确认。比如,过去多数学者认为黄老学派讲的是隐士思想和清静无为等,但马王堆出土的帛书《黄帝书》,一看就是黄老学说,其思想却完全不是隐退的,而是进取的,甚至还有关于战争的论述。这样再去看战国时期有关黄老的文献,就会发现确实如此。
再比如,1956年信阳长台关1号出土的一批竹简,因内有“先王”、“三代”、“周公”等词,儒家气息比较浓厚,所以起初以为是儒家作品。“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山大学的几位学者指出,竹简的内容与《太平御览》所引《墨子》逸文相同。再经查对,传本《墨子》书里也有“三代”、“先王”、“周公”等词。因此,推断长台关这组简是《墨子》佚篇。其中,有申徒狄与周公的对话,周公不是周公旦,而是西周君,因为申徒狄是战国时人。这个《墨子》佚篇的发现的确很重要。长台关这座墓属于战国中期,《墨子》佚篇的内容与传本《墨子》中的《贵义》、《公孟》等篇相似,而《贵义》、《公孟》以前被认为是很晚的作品。现据《墨子》佚篇可知,其写作的时间并不晚,至少在战国中期就出现了。大家知道,墨子的卒年已经到周安王时,即战国中期之初。墨子到过楚国,见过楚惠王,因此这个地方流行墨家作品是很自然的。也就是说,过去我们认为《墨子》书中很晚的一些篇章,实际上并不晚,可能为墨子下一、二代人所撰写。这一点对于我们研究《墨子》具有重要的意义。
还有《墨子》最后面的《城守》各篇,我们拿它与秦简一对照,便知确实是秦人的手笔,所以一定是墨学传到秦国之后,在那个地方作的。特别是篇中有的地方称“王”,有的地方还称“公”。可见后者应该是秦还没有称王,即在秦惠文王称王以前。这如上述佚篇的年代相差不远。因此,我们对《墨子》各篇年代的估计就有重新考虑的必要。类似的例子还很多,如《尚书·洪范》、《易传》、《老子》、《鹗冠子》等书篇的成书年代,均可由新出土简帛的相关内容作出重新思考。
第三,可使许多学术著作的价值得到新的、进一步的认识。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问世,使《易》学史中的许多内容需重新考虑。双古堆竹简《诗经》的出现、关于《诗》的传流也提出了新的问题。上海博物馆竹简中的《诗论》,多有孔子对《诗》的论述,更值得注意。马王堆帛书《黄帝书》、《老子》,使人们对所谓黄老之学有了全新的认识。银雀山简吴、齐二《孙子》与《尉缭子》、《六韬》等等,为兵家研究开辟了新境界。与此有关的,还有张家山简《盖庐》等。简帛中兵、阴阳家的作品很多,均系以往所未见。《汉志》中数术家书众多,但久已无存,简帛书籍中的这一类书填补了这项缺憾。方技类书对探讨中医药史极有价值,已经引起了医学界的普遍重视。这些上文已经说过了。
第四,可对古代时期的学术源流作出新的判断。例如,关于汉初风行一时的黄老道学的渊源问题。过去的学者多以为其源于齐学,有人认为与齐稷下一些学者有关。现在由于马王堆帛书的发现,得知汉初黄老道家的渊源在楚地,齐地的道家非其主源。马王堆帛书中的黄老典籍中,与《老子》并行的有《黄帝书》,其思想内容和风格近于《国语·越语》、《文子》、《鹖冠子》等书。这些都是南方的作品,代表了南方道家一派的传统。《老子》的作者是楚国苦县人,早见于《史记》。但所谓“黄老”的内容是什么,有什么地方特色,前人很难说清。现在通过对这些帛书的研究,可以知其大要。《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流多侧重于北方,对南方楚地的文化史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了这一缺环。
黄老之学在战国中晚期具有相当大的势力。在几个诸侯国握有实权的法家人物多学习黄老,如韩国的申不害和韩非、齐稷下的赵人慎到等,都以其学归于黄老。汉代窦太后好黄老之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仍把黄老列为首位。通过对楚帛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揭示楚文化与黄老思想的联系,这或许会成为打开中国学术发展史中许多疑谜的重要钥匙。
第五,可以重新为战国时期某一诸侯国进行学术史定位。比如楚国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问题。迄今为止,以书籍为主要内容的随葬竹简,已经发现了好几批,最早的如信阳长台关简,后来的慈利石板村简、荆门郭店简、上海博物馆简,加上现在正在整理研究的清华简,其内涵之丰富,远远超出了我们以前的想象。这些简都出于战国楚墓,当然是由于当地埋葬制度和地下条件特殊的原因,但也充分说明了楚国学术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以往的历代学者,常视楚国为蛮夷之地,似乎没有多少文教可言。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偏见。重新考虑中国古代学术的地理分布,有关的材料和研究条件已经逐步趋于成熟,把现有的这几批简综合起来,结合传世文献研究的成果,写一部战国时期楚国的学术史,肯定会别开生面。
出土的简帛佚籍对学术史研究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这些发现本身。比如,简帛《周易》肯定对研究《周易》有意义,简帛《老子》对研究老子很有用,简帛《孙子》对研究孙子具有学术价值。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出土简帛佚籍所显示的当时学术面貌,同我们过去的估计存有较大差异,这便向我们今天的学术史研究提出了大问题。而且,从先秦到汉初是中国文化经典形成的时代,因此,这一时代典籍文献的新发现不仅会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而且直接影响到此后甚至中国整个学术史的研究。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这些简帛佚籍出土,证明我们今天的学术史很有改写的必要。
在中国的历史上,新学问的产生都源于新发现,“重写学术史”正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而提出来的。现在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发现和新发现的时代,面对这些更新、更多、更重要的历史典籍的出土,中国古代学术史定会得到重新书写,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定会出现新的繁荣局面。
来源:《河北学刊》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