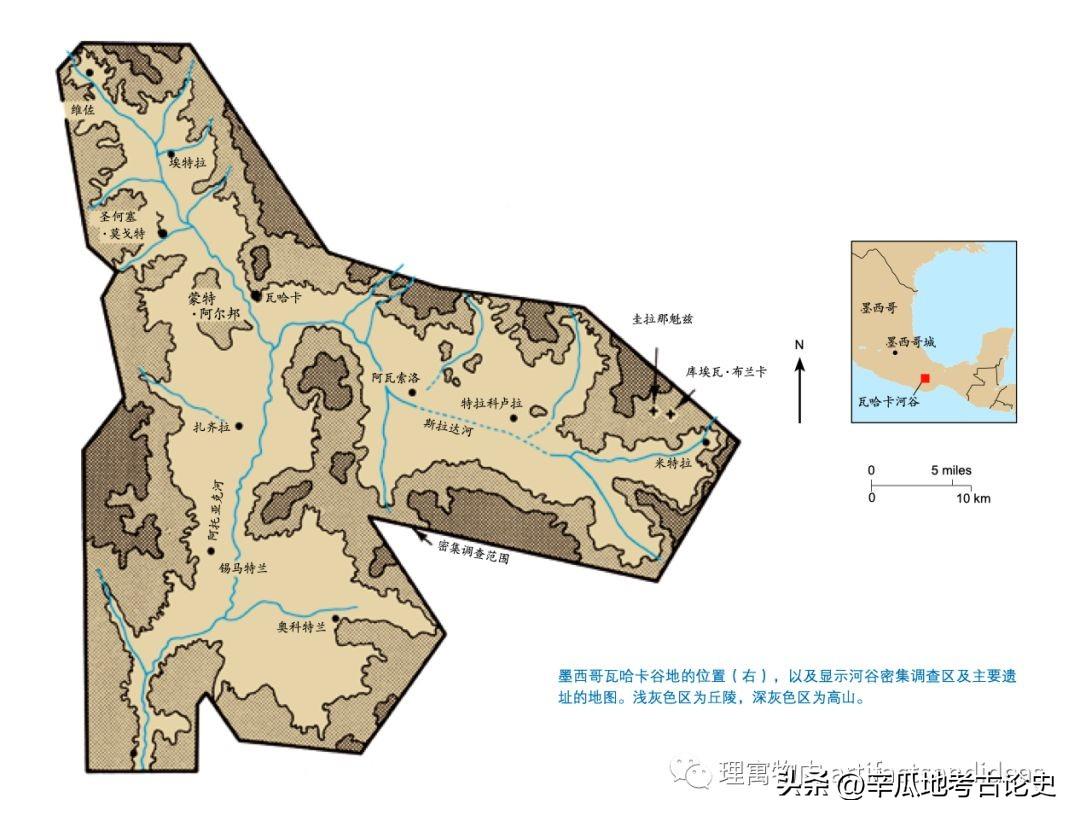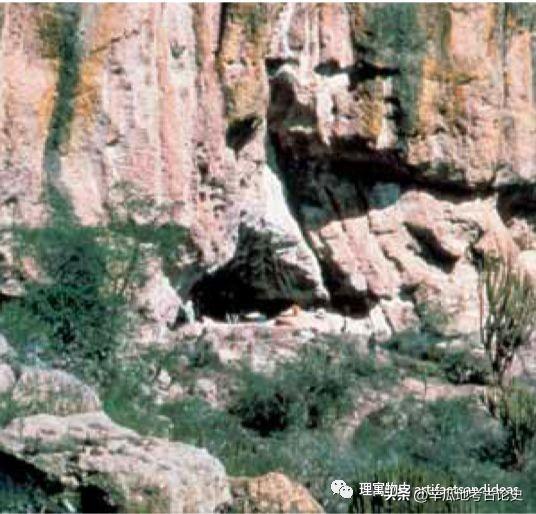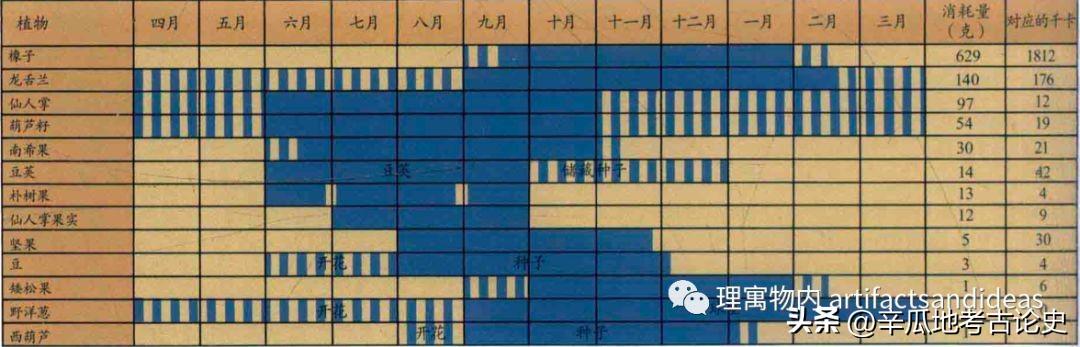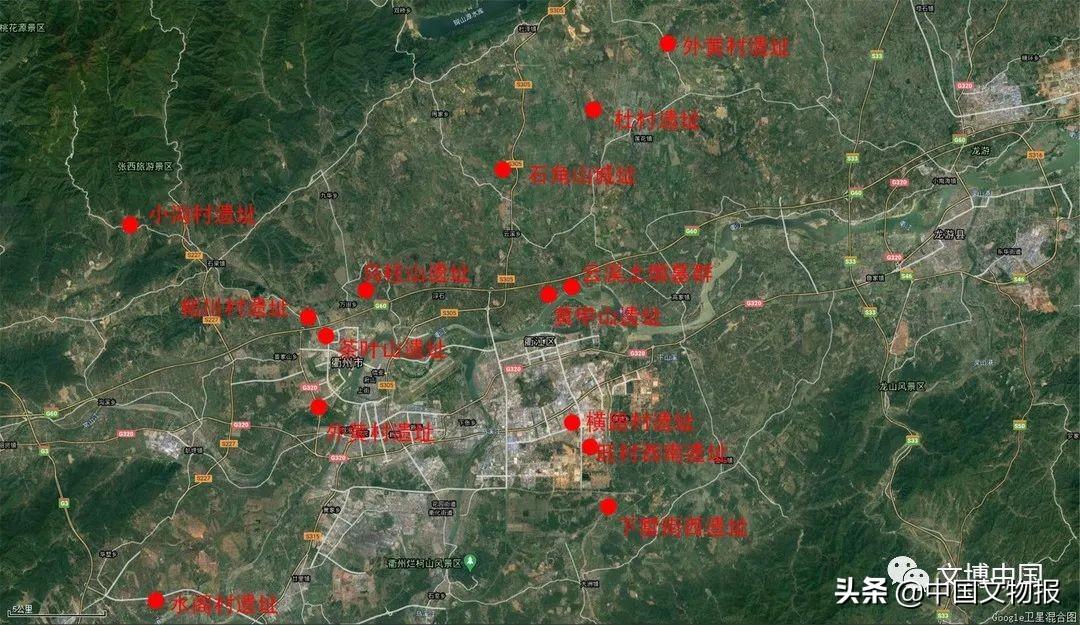赵丛苍;曾丽:关于“考古类型学”的新思考
作为考古学基本理论的考古类型学,所发挥的作用堪称功不可没。但长期以来,考古类型学基本关注的是遗物的本身与表象。笔者认为这个现象背后的情形可能十分复杂,揭示和诠释其丰富的潜在信息,是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诉求,也是当代学者义不容辞的使命。
一、考古类型学的发展
考古类型学是借鉴生物学对生物进行分类的方法而进行的考古类型分期。中国的考古类型学是在古斯塔夫·奥斯卡·蒙特留斯(Gustaf Oscar Montelius)考古类型学的影响下,经苏秉琦等学者的不断研究完善,从而被愈来愈多的学者接受。其为我国考古遗迹、遗物的分期研究,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建立贡献巨大。
1903年,瑞典考古学家蒙特留斯《东方和欧洲的古代文化诸时期》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类型学理论。1935年,中国学者郑师许、胡肇春以及滕因分别翻译了此书,考古类型学理论开始传入中国。
在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的启发下,中国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已开始运用类型学对遗迹、遗物进行研究。梁思永在1930年对山西西阴村史前陶器的纹饰、质地、颜色等进行划分,开始了对类型学的初步探索[1]。李济对安阳殷墟铜器的分类采用序数法,先对其器底的形态进行划分,编为百位上数字;以口径与体高相比的大小及器物的深浅为标准,编为十位上的数字;再根据器物最大径的位置及耳、柄、流等附加部分的有无,编为个位上的数字。这样三位序号便构成了一个序数,从而可从器物的序数中知道器物的形态[2]。苏秉琦通过宝鸡斗鸡台的发掘,于1948年发表《瓦鬲的研究》,根据鬲的制作工艺将其划分为A型、B型、C型、D型,又将介于A、B,B、C之间的过渡型以AB、BC标示。再根据各型中鬲的演变划分出式,以A型为例,其各式以Al、A2、A3表示,最终理清各型式鬲的演变关系[3](P137-147)。苏秉琦对瓦鬲的研究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产生。20世纪50年代,苏秉琦在洛阳中州路东周墓葬的发掘与研究中,对遗物进行型式划分,先划分器类,再在各器类之下划分式,以Ⅰ、Ⅱ、Ⅲ……标示,以表示其年代的早晚关系,是类型学方法的成熟[4](P13-17)。
最初类型学的划分多运用李济的序数法,但是这种方法较为琐碎。至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苏秉琦首先使用的对器物类、型、式的划分,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期别、年代的方法,为大多数人所接受[5](P5)。
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又对仰韶文化进行区系类型划分,将其划分为庙底沟类型和半坡类型,并对各类型的特点、器物的型式演变、年代和分期、分布和分区进行分析[6]。20世纪80年代,苏秉琦正式提出了区系类型学说,指出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则是分支,并将中国史前文化划分为六大区系[7]。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根据共存器物组合的类型来划分考古学文化,是考古类型学理论的一次重大突破。
考古类型学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之一,根据遗迹、遗物的形态异同,将其划分为类、型、式,确定其在时代上的演变规律,对于器物的分期和相对年代的确立,作用不言而喻。同时,在更大范围内运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比较分析,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确立,各文化的地理空间分布、发展演变规律以及文化间的交流诸方面的研究发挥重要作用。
在运用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时,人们往往注重其对分期研究的重大作用,而忽视型式划分之所以存在的内在原因。对于刚刚起步的中国考古学而言,运用考古类型学建立起时空框架一定是必要的。然而,时至今日我国考古类型学研究已历经大半个世纪,各遗址的分期以及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基本确立。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考古学出现了新的范式转变,如后结构主义、后过程考古学、象征考古学等等,主要是反对过程考古学“统一科学(Unified science)”的理念,欲建立一个多样的、认知的阐释模式,因此更加注重文化在塑造人类行为中的作用[8](P27)。而这一目标的实现,仅停留于对遗存进行分期和区系类型研究是远远不够的。考古类型学若沉浸于对物质本身的研究,既不能揭示考古遗存丰富而深层的内涵,又无法满足考古学揭示古代人类社会的需要。考古类型学研究需要突破传统的理念与研究方法,引申思考维度。
二、考古类型学深层内涵之揭示
苏秉琦认为,器物形制的变化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是对器物形态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器物的表面,而应揭示物与人、物与社会的关系[9]。考古类型学的功用,并非仅限于对遗存的分期研究,更重要的是揭示考古类型学型式划分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
考古遗存的形成由众多因素决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而这些因素都是古代人类活动的体现。虽然这些动态的人类活动已经无法看到,但其制作和使用过的工具与用品等还遗留至今,我们可以透过这些物质遗存揭示其所反映的技术、文化、政治、宗教诸类信息。物品之所以做成某种形态,主要是受用途、制作工艺、使用者的生活状况、审美观念等因素影响[5](P7)。而这些因素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且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这种规律的形成,主要因为技术传统乃至文化崇尚、政治和宗教信仰等因素的作用与影响。
(一)技术传统
作为类型学研究主要对象的遗物,在古代生产制造这些器物时所凝结于其中的制作技艺,对其形态的生成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尽管器物的制作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干预,而技术传统具有内在基因的意义。
毋庸讳言,器物形态的形成,取决于制作者的行为意识。这种意识的产生源于制作者的价值标准、审美取向、思维模式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的形成多与技术传统密切相关,进而潜移默化成为内在的基因。一个地区的技术传统是相对稳定的,虽然也会有技术创新,但确是建立在原有传统基础上的创新,并且这种创新一般是循序渐进的,少有突飞猛进的迅速变化。因此,无论是陶器、青铜器、玉器、骨器等的形态演变规律,都是由于技术传统的作用而形成,故而技术传统是揭示物背后人的活动的核心元素。迪兹(James Deetz)提出“概念型板”(mental template)的概念,是指工匠头脑中对一种器物式样的构想,它就像铸模的“范”,只不过它是一种意识的“范”,当器物成型后,意识便随之得到反映[10](P165)。也正是在这种技术传统的影响下,器物形态才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才可进行类、型、式的划分。
1.技术传统的延续技术传统往往是无形的,但其形成模式则是有形的。技术传统的传承形式与模式基本可分为世袭继承和标准化两种,这两种方式相互区别又有所联系。如商周时期主要是有独立式手工业者和依附式手工业者。独立式手工业者多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以世袭的方式继承生产技术;依附式手工业者生活于都城或大型聚落中,政治、经济上依附于王室或贵族,为全职生产者,其生产制造主要服从于王室或贵族的指挥[11],但也存在世袭继承。
以家庭为单位的独立手工业者,其生产规模较小,生产技术多来自继承,因此,产品的形态变化,在一定地域内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而不同地域的产品,往往呈现明显的差异性,可能与当时物质文化交流的不发达有关。
而依附于王室或贵族的全职手工业者,接受王室或贵族的统一领导,其手工业生产虽多以家族为单位进行,但是置于王室的统一管理之下。陕西周原遗址董家村窖藏出土的公臣簋铭文中记载了虢仲委派公臣管理“百工”,并赏赐给公臣马匹、钟和一些铜料[12]。依附式手工业生产规模较大、专业化水平较高,多实行标准化生产。周原云塘制骨作坊生产的产品中,骨笄约占90%以上,其次为骨锥、骨针等。观察同类骨料的制作痕迹,可以发现其制作工艺十分相似[12]。该作坊区南缘出土的甲骨刻辞曰“王以我牧单马冢,卜”,说明云塘制骨作坊的骨料可能来源于单氏领地并受王室的统一管理。
古代社会中,标准化生产是基于政治权力之下的手工业生产的规范化。标准化生产的途径主要是制订标准文件发布并派专业人员分赴各地传授。关于发布标准文件,莫过于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统一文字之事件,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14](P239)经过秦始皇各项统一措施的颁布,秦朝在度量衡、车轨、文字等方面均实现了标准化,成为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必要保证。派专业人员赴各地传授的方式是对手工业者进行培训,以推行统一的手工业生产标准,仍以周原云塘制骨作坊为例。该遗址发现一件骨器上有多个钻孔痕迹,孔的分布毫无规律,缺少实用性的成熟设计支持,当视为初级手工业者制骨练习而留下的痕迹。故而可以推测,在手工业生产技术的传播与推行中存在练习的环节,而这种练习,可能是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的。正因如此,在一个作坊甚至一个区域里,产品方可达到风貌一致的较高水平,从而实现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
类型学研究的基础,是器物形态的相似性原理和一般进化原理,这主要是与一个地区的技术传统息息相关,这种技术传统的延续有家族继承和统一管理两种方式,这两种方式分别体现了生产的延续性和相似性。正是由于手工业生产传承性和标准化的存在,才使得类型学的分期研究成为可能。
2.技术传统基本元素揭示技术传统的延续是类型学得以划分的内在因素,也是考古学文化确立的重要依据。而技术传统所包含的因素,可能涉及制作工艺、手工业作坊的运作模式、审美观念、人群生活方式诸多内容,这些信息的揭示,有助于技术传统的解读。
以往对于技术传统的研究,多集中于器物生产工序的研究。运用微痕分析、实验考古的方法,通过观察器物表面的制作痕迹或者模拟实验,来研究其制作工艺、生产流程。这样的研究无疑难以获取人群的活动、生产管理体系、原料来源、产品流通等更为详细的历史信息。这主要是由于其关注点仅限于遗物本身,而忽视了遗物与遗物、遗物与遗迹、遗迹与遗迹之间关系的考察。当然并非所有的考古遗存都能建立其完善的情境关联。由于古代遗存的形成历经沧桑,遗留下的多为碎片式的信息,而考古发掘也只是冰山一角,致使一些遗存不具备建立情境分析的条件。这也是研究者在实际操作中的困扰。
值得提出的是,手工业作坊应予以充分重视并作为这方面重点研究对象。其基础设施建设所显示的作坊内部结构,手工业者的居址与墓葬所包含的人群活动与族群构成的信息,作坊中工具与产品所呈现的制作工艺,周边宫殿与高等级墓葬所反映的管理体系,各类手工业作坊遗存展现的产业集群规模与结构,等等,足以说明手工业作坊是一个集技术、生产、管理、劳动力、流通等为一体的生产链,体现了技术传统或与之相关联的多种元素,是技术传统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素材。
以周原云塘制骨作坊为例,研究者可将其置于周原遗址大环境之中,以云塘制骨为中心,与周边的建筑基址、青铜器窖藏、墓葬、池渠以及其他手工业作坊等遗存相联系,发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运用情境分析法,通过建立物与物之间的联系,揭示物与人、物与社会、物与环境间的关系。
(二)文化附着
古代人类遗留下的物质遗存,其赖以生产和流传的因素十分复杂,所反映的皆与人的活动有关,内涵丰富。物质遗存承载的文化信息,我们称之为文化附着。揭示附着于物质遗存上的文化内涵,是透物见人的关键。
1.文化的含义 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经过人们长期的创造而形成,是社会历史的积淀物,是一种强大而隐形的对人类活动具有重要指导作用的意识形态。
考古现象反映出,在一定的地域、一定的时间段,物质遗存表现出较强的相似性。戈登·柴尔德(Childe.Vere Gordon)指出,考古学上的“文化”,是指在一定地域考古遗存中所发现的共存关系,即同样型式的器物组合经常在不同遗址出现[15](P5)。在同一文化中,人群往往具有共同的思想、信仰、习惯、技术及行为模式,表现在考古学上为同一型式的器物组合经常出现。
一个区域内的器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相似性,主要是该区域的文化原因使然,在同一文化影响下,器物形态多表现出相似性,同一型式的器物组合反复出现。而在不同文化的影响下,器物则呈现不同的形态,此即考古学文化得以划分与确立的重要原因。以物质遗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考古类型学,应更加注重揭示物质遗存背后所反映的文化信息。
2.物质遗存的历史象征意义物质遗存并非主观意识的产物,其产生附着有技术、思想、习惯、价值等文化符号。这种文化附着是潜在的、无形的,但确是根本性的。要通过物质遗存揭示其所体现的文化内涵并非没有可能,这就需要在实与虚、过去与现在之间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使隐藏在物质遗存中的文化信息可以被阅读。
由于物质遗存并非孤立的存在,各遗存间往往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凯思(Case)提出情景分析,情境(congtexere)是指在一个特定环境中各种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情境中通过分析器物与共存的其他器物之间的联系和作用,便可以获得象征意义。伊恩·霍德(Ian Hodder)认为:“仅仅讨论孤立的器物并不是考古学。考古学关心有地层和其他情境(如房屋、遗址、灰坑和墓葬)的器物,这样,他们的年代和意义才能得到阐释。”[16](P4)这些物质遗存虽有不同形态,但在一定的时空范围内却是相互关联的,要揭示遗存的文化象征意义,需要分析其所处的情境。
麦克吉(McGhee)对加拿大土勒(Thule)文化的史前遗址进行研究,发现象牙、海豹骨骼和鹿角做成的鱼叉头共存,通过考察发现象牙常和捕捉海象的器物共出,另外,象牙制品主要有针线盒、顶针、装饰品及女性人鸟雕像,这些与女性或冬天的活动相关;另一方面,鹿角和陆地哺乳动物相关,特别是驯鹿,是男人和陆地夏季生活的反映[16](P49)。经过相关民族材料的验证得出“象牙、鹿角”分别象征着“海洋、陆地”“冬季、夏季”“女性、男性”。此例可说明,经过对器物存在的情景分析,是可以严谨地推导出物质遗存的象征意义的。
在对遗存进行情景分析时,不可忽视类型学的中心地位。类型学依据器物的相似性和相异性进行型式划分,是深入进行情景分析的依据。象牙象征着女性,观察同一单位中出土的其他器物,以支持女性内容的其他抽象意义。并比较鹿角——男性遗存的共存器物,看其他器物或器物组合是否具有更丰富的文化内涵。考古类型学通过对遗存的类型划分,建立不同类型的情景关联,然后从情景中相似性和相异性的研究,揭示物质遗存丰富的象征意义。
3.文化传播的考古学证明某一地区文化的形成并非孤立的,而是在与其他文化相互交流,吸收有利于自身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张忠培指出:“任何考古学文化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与外界绝缘的孤立系统。”[17](P183-184)因此,文化与文化之间本身便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着眼于文化间的差异性而开展文化分区研究固然是必要的,同时文化间传播与交流的研究亦不能忽视。
由于古代的人群早已不见,对古代文化传播形式和途径的研究,只有依据所遗留的物质遗存去解决。这些物质遗存,附着有技术传统、价值标准、审美取向等文化因子。正是由于这种文化附着的存在,才使物质遗存在一定地域内具有相似性,在不同地域具有差异性。因此,在探讨文化传播时,其有效途径便是透过物质遗存所携带的文化符号来判断文化与文化间的传播。
在研究考古学文化间的传播时,综合的比较分析以及对某些典型器类的关注和研究,至关重要。如丝绸之路的考古研究,便是充分利用物质遗存来研究文化传播,通过丝路沿线出土的反映中外文化交流的遗物,以点带面,透视丝绸之路的文化传播情况。又如,通过对牙璋的研究,为夏商时期文化的传播提供佐证。牙璋最早发现于山东龙山文化,之后传播至河南二里头文化、陕西石峁遗址,再到四川三星堆,至广西、广东,再传至越南任村遗址、越南冯原遗址。通过对牙璋的出土地和形制研究,证明夏商时期已经有一条由北向南的传播路线。
此外,文化因素方面的研究尤其值得关注。俞伟超指出,文化因素分析法运用广泛,在涉及文化谱系的建立、各文化间的相互关系、文化对遗迹遗物的影响等方面作用显著[18](P129)。在研究文化间的传播关系时,可通过对遗物所附着的文化因素来判断其受何种文化的影响。俞伟超在对“楚文化”进行文化因素分析时,提出“楚文化”的主体为“楚文化”因素,从遗存中还提取、识别出周、越、秦等文化因素,是典型的文化因素分析法。这是研究楚文化与周文化、越文化、秦文化间传播关系的重要实例。
文化传播的另一个结果便是使得一个考古学文化包含多个族属。邹衡提出“因为考古学文化与族属并非一个概念,同一考古学文化也可以包括不同的族属”[19](P329)。在三代考古中,要用一种考古学文化只代表一个族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除了通过战争、裒田、分封、联姻、流亡、迁徙等交往而形成文化间的交流、同化、融合和相互影响外,当时的国家是“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的[20]。所以,在对早期秦文化进行研究时,我们只说它是指在秦族活动(或统治)范围内主要是秦族使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而并不排除使用秦文化的还有其他各族,如戎、羌等民族的文化因素。关中西部京当型商文化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总体来说应属于商族,但所包括的族属不会仅限于子姓的商族,还有与商族有一定关系,但并不是出自子姓商王族的其他氏族或部族,还应包括一部分关中西部土著部族和嬴秦氏族[21](P72-76)。这归根到底便与人群的流动、文化的传播密切相关。
如何区分同一考古学文化下的不同族属,一直困惑着考古学家。但是,通过物质文化研究族属,并非没有可能。正如香克斯和蒂利(Shanks and Tilley)所言,虽然某特定物质的式样保持不变,但是其意义在不同背景中会发生变化;它会被不同的方式消费,并根据历史传统和社会背景融入或结合到各种象征结构中去[22](P161)。一定地域内往往有多个族属,不同族属在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信仰等方面是有差距的,但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反映在器物形态上却是一致的。这便需要运用情景分析,考察与某一器物共存的器物组合、遗迹组合间的关系,以划分不同的情景,区别不同族属间入的行为活动。
(三)政治与宗教痕迹
相对于技术传统、文化而言,政治因素对器物形态的影响往往具有强制性。自上而下政策的实施或者在统治者意识的影响下,反映在物质文化上的变化是巨大的。历来的改朝换代,统治者的意志均会影响到手工业者的价值取向、审美意识。因此,随着朝代的更替,其物质形态也会随之改变,而这种变化是根本性的改变。由于物质文化的改变需要一定的适应过程,故而在王朝建立初期往往与前朝后期的物质形态较为相似,而进入到王朝的中期,便会形成该朝代独具特色的物质文化,反映在考古类型学上尤为明显。如周初的青铜器,多因袭商人风格而与商末青铜器在器形与纹饰方面非常相似,往往不易区分。经过成王,到了康王、昭王时,周人自身的风格逐渐显现,与商器区别明显,形成周器的特点。
政治因素对器物的影响还反映在国家政策层面。金朝由于铜的匮乏,官府实行铜禁制度,特别是对铜镜的生产铸造更为严格,为防止民间铸镜和越境流通,官府规定铜镜必须经过相关机构的检查和登记,并在边缘刻以县地官匠验记阴文字铭和押记,才可出售,这就形成了金朝的边款铭铜镜。
史前时期,宗教神权往往与政治相结合。反映在遗迹、遗物上,宗教神权色彩表现相当浓厚。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出土的玉猪龙、斜口筒形器、勾连形佩等,极富神权色彩。良渚文化的玉琮、冠形饰、三叉形器及所饰神徽图案以及玉钺等遗物,即为神权与军权相结合的产物。李伯谦认为,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国家,而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同时又以神权为主的国家[23]。唐代,武则天时期将佛教作为政治统治的工具。武则天为称帝制造合法性,利用佛教僧人附会《大云经》称其为弥勒所生,称其为菩萨现身,教化万民。这也促使当时弥勒信仰的盛行,在物质遗存上表现为弥勒造像所处空间扩大、位置逐渐居中、体型不断增大[24]。宗教信仰往往作为统治阶级巩固统治的工具,是一定政治色彩的体现。
自20世纪20年代我国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学理论在不断发展。从时间上看,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过程考古学于20世纪60年代形成,后过程考古学则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25]。文化历史考古以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为基本理论,侧重于对考古学的分期研究,对史前史时空框架和考古学文化的建立有重要意义。过程考古学以自然科学为导向,希望按照自然科学推演普遍规律,利用考古材料对文化过程予以解释。后过程考古学重在阐释文化行为本身,运用情境分析,更加注重象征、符号、文化、信仰、观念等意识形态的要素在当时社会中的作用。随着考古学学科理念的不断发展,由专注于分期研究到对考古材料的科学解释,再到关注物背后人的活动,为适应学术发展的需要,考古学研究承担着厚重使命的考古类型学急需突破传统的习惯而引申关注维度,以揭示器物类型学型式划分所蕴含的内在原因,以丰富考古学内涵而着重关注物与人、物与社会、物与环境间的关系,使之成为考古学研究中的自觉意识,深化学术层次,促进学科进步。
注释
[1]梁思永.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M]//梁思永.梁思永考古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2]李济.记小屯出土之青铜器[J].考古学报,1948,(3):3-26.
[3]苏秉琦.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
[4]苏秉琦.洛阳中州路(西工段)[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5]俞伟超.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6]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J].考古学报,1965,(1):52-81.
[7]苏秉琦,殷玮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J].文物,1981,(5):11-16.
[8]鲁斯·崔格尔.考古学思想史[M].徐坚,译.长沙:岳麓书社,2008.
[9]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J].文物,1982,(4):1-7.
[10]陈淳.考古学理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11]孙周勇.西周手工业者“百工”身份的考古学观察——以周原遗址齐家制玦作坊墓葬资料为核心[J].华夏考古,2010,(3):118-152.
[12]岐山县文化馆,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岐山县董家村西周铜器窖穴发掘简报[J].文物,1976,(5):26-47.
[13]陕西周原考古队.扶风云塘西周骨器制造作坊遗址试掘简报[J].文物,1980,(4):27-39.
[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戈登·柴尔德.考古学导论[M].安志敏, 安家瑗,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6]伊恩·霍德,司格特·哈特森.阅读过去[M].徐坚,译.长沙:岳麓书社,2015.
[17]文物出版社编辑部.文物与考古论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18]俞伟超.考古学是什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1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
[20]邹衡.关于考古学理论和方法上的几个问题——与梁星彭同志讨论[J].考古与文物,1982,(6):46-52.
[21]张天恩.关中商代文化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
[22]希安·琼.族属的考古[M].陈淳,沈辛成,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23]李伯谦.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红山、良渚、仰韶大墓随葬玉器观察随想[J].文物,2009,(3):47-56.
[24]温玉成.试论武则天与龙门石窟[J].敦煌学辑刊,1989,(1):119-127.
[25]陈胜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范式与范式变迁[J].中国社会科学,2019,(2):182-208.
来源:《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 0000
- 0002
- 0003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