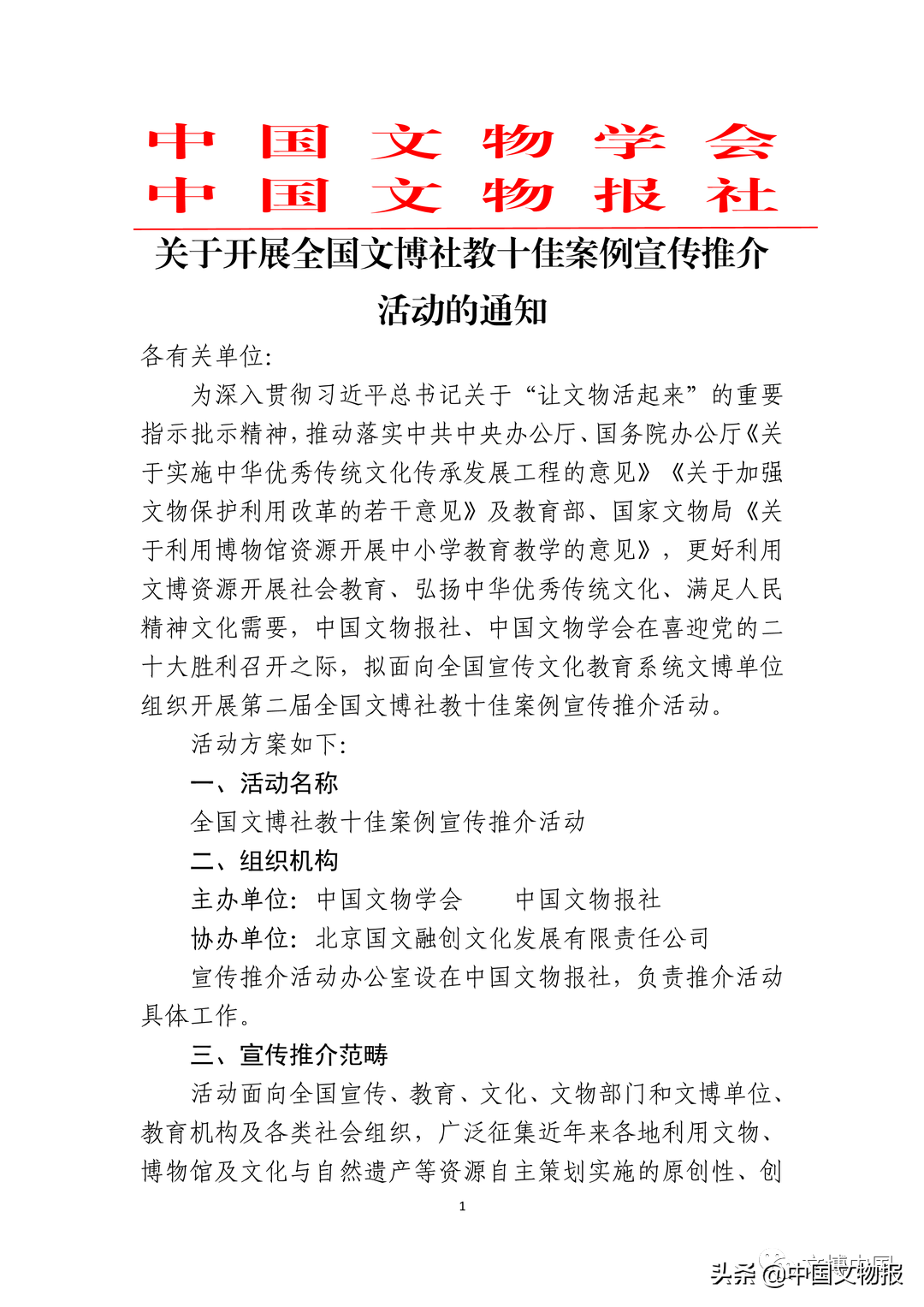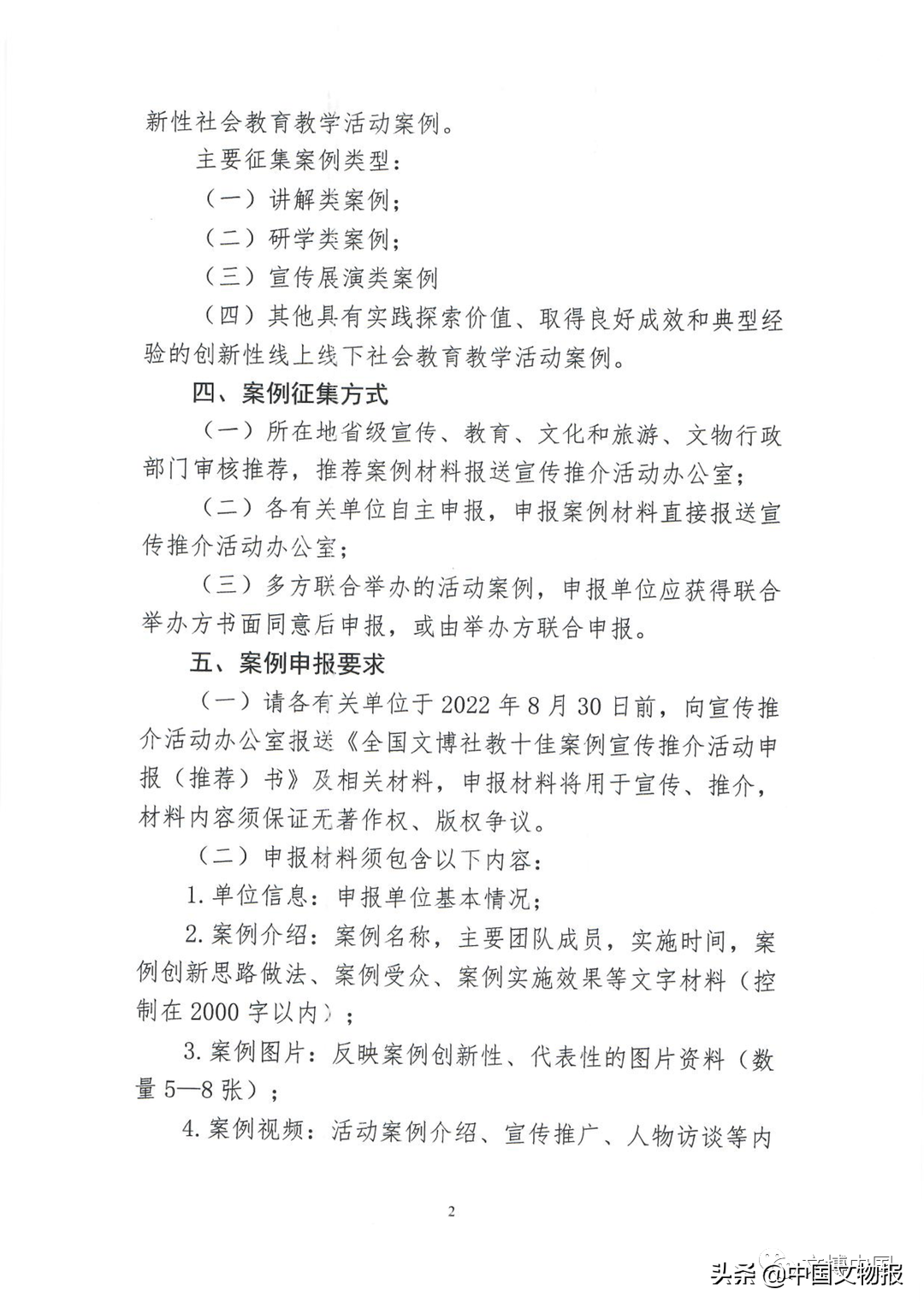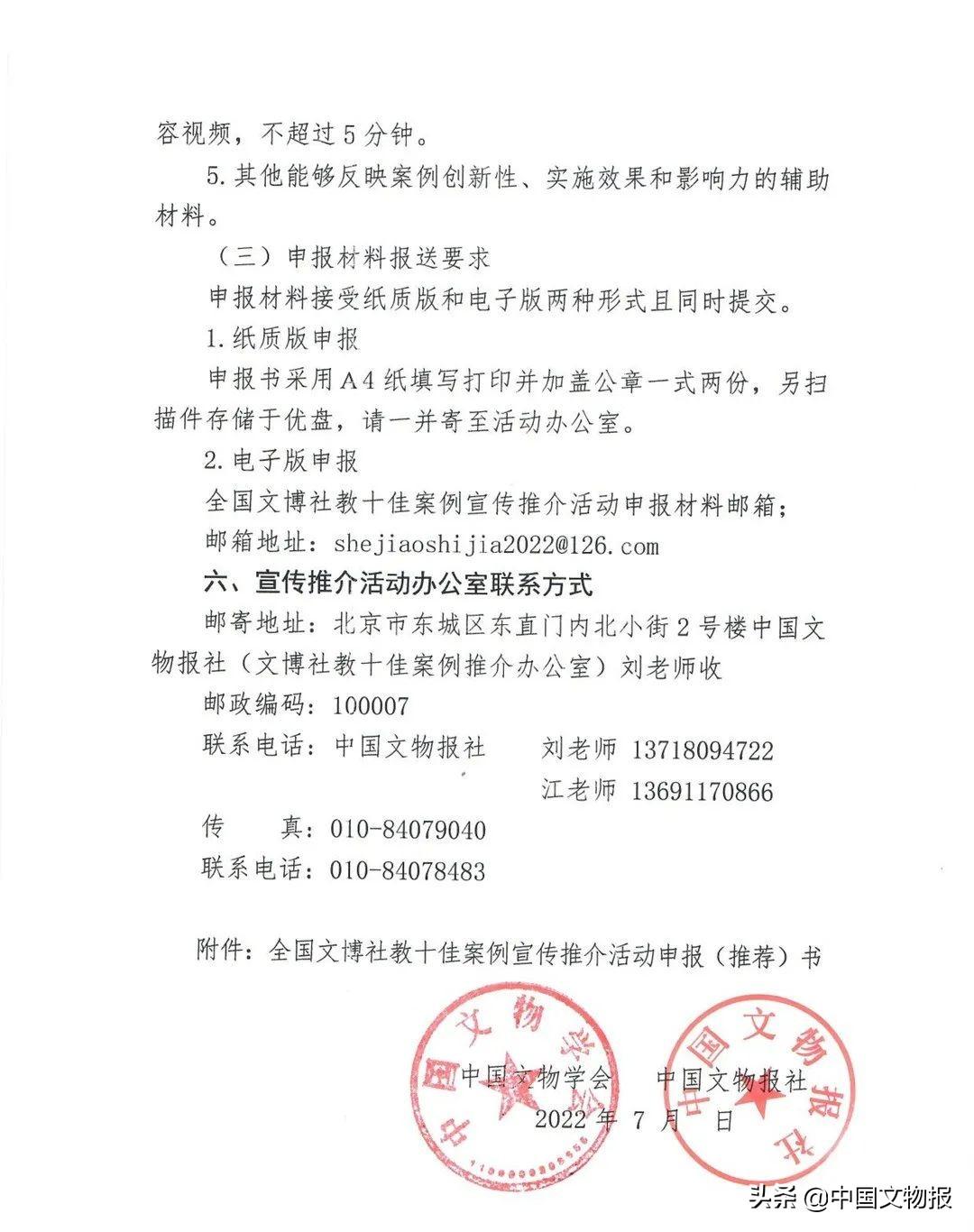唐晓峰:文明进程的足迹
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在断定中国古代文明进程的准确时间,意义非常重大。作为地理从业者,我们称道断代研究的同时,又自然而然地想到另一桩重要的事,即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地理空间问题,有条件的话,我们能否也做一回夏商周“断地”工程,即考察文明进程的足迹。
理论上我们把时空分开,但事情的时空属性必然是交织在一起的。“发生”一词在英文作“take place”,直译是“找一处地方”。这个词用得好,文明发生时,要找一处地方。文明的发生到底在哪里,文明的发展壮大又先后朝着哪些地理方向,文明的地盘又是如何向四面步步壮大,这些都需要做“断地”研究。而这些“地”若与“代”挂起钩来,我们的文明发生问题就更加清晰明白了。
对于中华文明的空间地域问题,历来有各种说法,混乱之状并不亚于“代”的问题。在王朝时代,生长在“文明”地域的冠带士子骄傲得很,以为泱泱华夏在舜爷、禹爷的时代,就南抚交趾,北定山戎,西抵渠羌,东尽鸟夷,“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到了蛮夷的地方)。直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顾颉刚先生带头澄清了这个问题,提醒人们文明不可能一下子就坐出一片大地盘,疆域只能是渐渐大起来的。
但是,后来又有人把早期朝代的地盘尽量地压缩,压到小得可怜。比如说商朝,不过是一个以安阳为中心的“统治家族”,是个极为一般的“城邦小国”。按照城邦小国的思路去想,商朝地域范围怎么也宽广不起来。可是,我们明明读过商朝后人缅怀祖先的诗句“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我们又明明在距离中原近千里以远的湖北黄陂看到典型的商代城址。
那么,我们文明历史上这个光辉的奠基时代,即夏代、商代、周代时期的疆域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是相当重要却又相当难断的问题。在三代以后的朝代,都设立了一套郡(州)县制度,疆域内分布着密密麻麻的郡县名称,它们大多方位记载明确,以它们为定位点,可以做很细致、很实在的古代地理研究。可是在三代时期,没有(或者说没有记载下来)如此密麻准确的地名供我们方便地使用。欲恢复三代地理的本相,需要辅以其他办法,诸如考古学、古文字学等。
在传世及出土的卜辞金文中,有不少三代的地名,如果将它们仔细落实,再结合许多文化遗址,可以大大增进对三代历史地理的了解,明确它们的疆域范围。另外,近二三十年的考古发现已经频频令我们吃惊,不少原以为是“狐狸所居,豺狼所嗥”的地方,忽然挖出精美陶玉,现出庄严鼎彝。对我国早期文明的足迹之密、放形之远,学者们又越来越不敢低估了。对于一些在“想不到的地方”所发现的重要遗址,都引发我们认真地去想一想:它们在古代文明大地谱系中曾占据怎样的坐标、具有怎样的人文地理属性?
由考古新材料所导致的历史地理观念的变化,几乎是“七八年来一次”。过去关于文明的“摇篮”即文明地理重心的理解,还是一元式的,只认黄河中游这一个“摇篮”,尽管其他地方也有另外类型的文化,但不称它们是“摇篮”。现在,只有一个摇篮的理解已经说不通了,因为考古研究显示,在东北、东南、西南都有强大原始文化存在,说明我们的文明最终是由众多摇篮培育起来的。
至于夏商周三代的地理问题,事实与观念也在丰富更新,除了落实新的地名定点、确认地域关系,还有如何认识早期朝代疆域总体形态的问题。我们习惯于将王朝领土想象成连续弥合的,但有专家尖锐地指出,早期国家的领土可以是插花状的。另外,对距都城远近不同的领土,势必存在不同的管理控制方式,比如商代有“内服”“外服”之别,这在早期国家地域机制中意义何在?此外,“四夷”地带的重要性也不能忽略,三代时期是开放型疆域,那是一个大融合时代,在四夷地带照样埋伏着华夏文明的基因火种。
来源:《华夏文明地理新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
- 0000
- 0001
- 0000
- 0000
-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