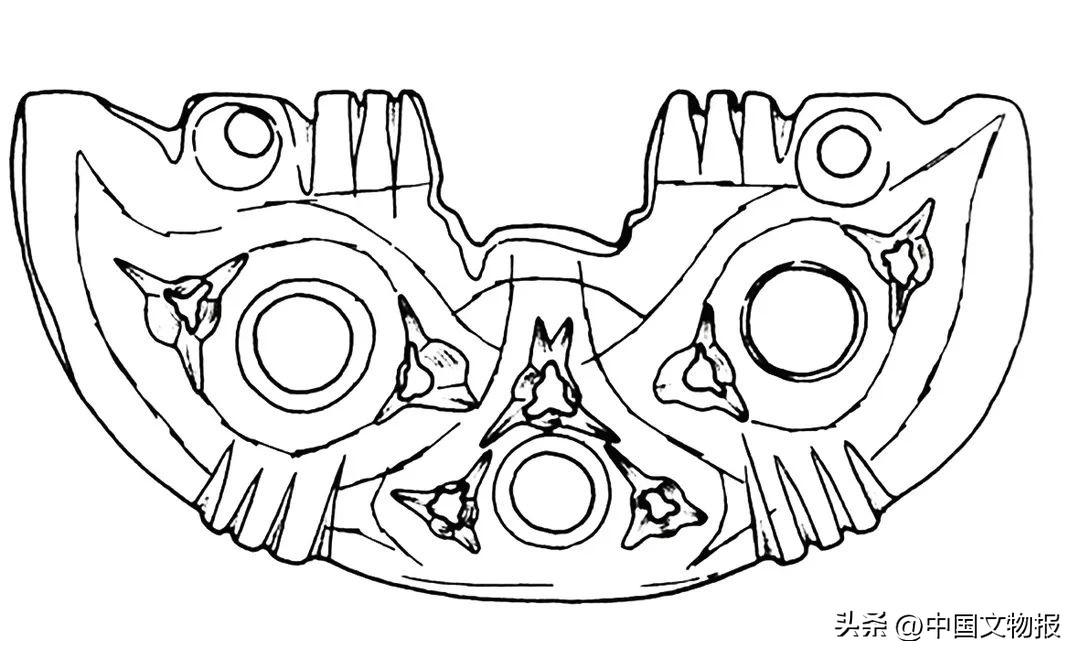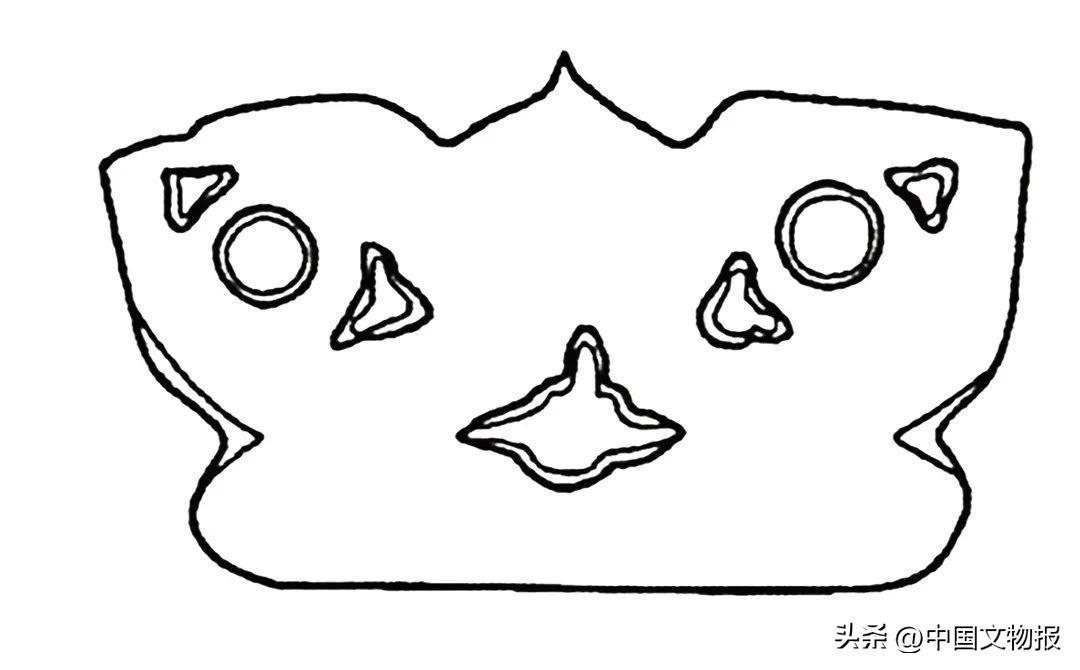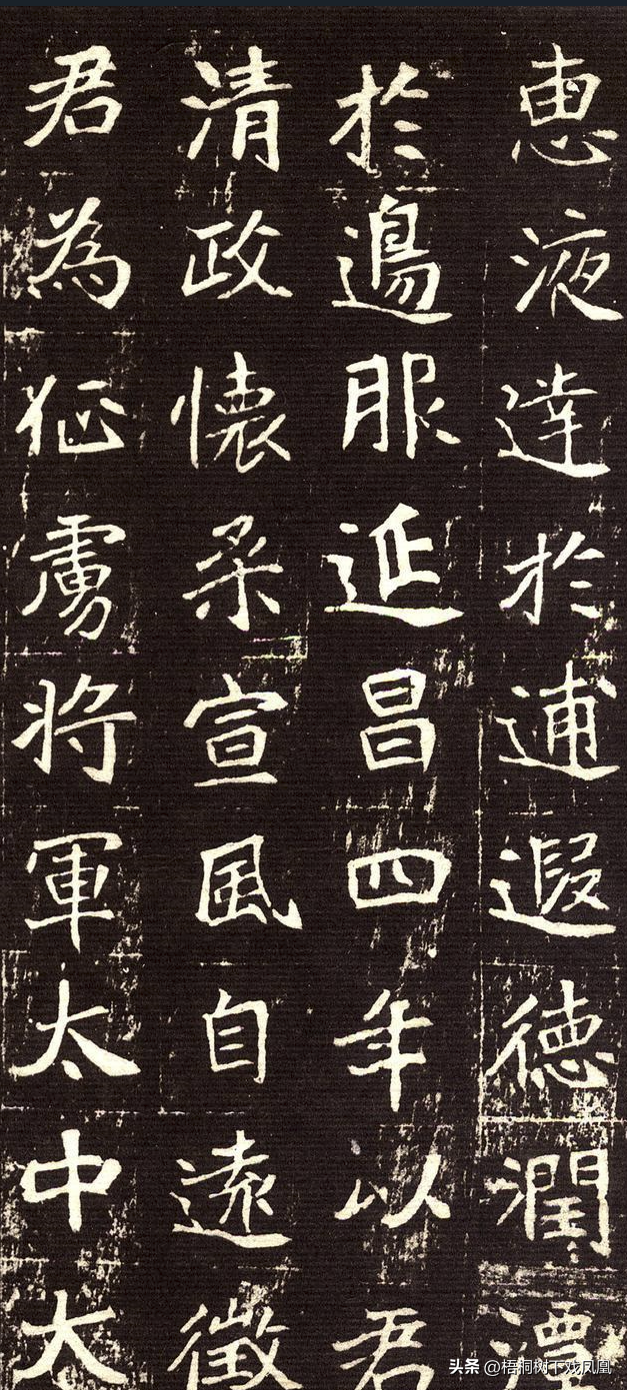严耕望:目录学与校勘学
问 《励耘书屋问学记》各篇多谈到陈援庵先生治史特别重视目录学、校勘学,你的意见如何?
答 这两门学问都是治史的基本学问。目录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础知识之一,校勘学是治史所必备的基本技术之一。
兹先谈目录学。不管你治史走哪条路,对于目录学都要有相当认识,但我又认为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在这上面先下极大功夫。这一点与史学方法论之于史学研究一般,很重要,但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精通此道。若再进一步分析,所谓目录学可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目录学可指一切目录书籍,也可指一切书目知识而言;狭义的目录学是就章实斋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校雠通义》叙)而言,这是学术史的基本功夫,也是一项专门之学,一般史学家不必都能精通。一般史学家所须广博知识者,倒是广义的目录学,因为对于各种书刊内容多所了解,等到研究问题时,就知道当看些什么书。近人着手研究一项问题之前,多先翻查各种目录书,作为研究的准备功夫,也就是想先掌握与此问题有关的目录知识,并无必要达到狭义目录学的境界。但是我认为真正的目录学应就狭义而言,狭义的目录学才能真正算是一门学问。广义的目录学只是些目录知识,不能算是一门有系统的学问。不过史学界所谓目录学,通常都只就广义而言,非就狭义而言。
援庵先生治史特别重视目录学,也精于目录学,这有两个原因:其一,他治学的初步途径是自目录学书籍开始的。他本来只知读四书五经,目标在时文科举。后来偶然的机会,看到了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才知道还有很多好书可看。继而他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做了不少功夫。后来著作也颇多直接关乎目录学的,如《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所以他的史学可说是从目录学入手的,自然也特别重视此项学问。其二,他特别注意史事专题研究,不但很少写通论性文字,而且也不做范围比较广阔的专史研究。他那样只作仄而专,而且比较偏僻的专题研究,就特别需要注意目录学,也就是上文所讲的广义目录学。例如他在抗战期间所写两部有名的佛教史考证文字,《清初僧诤记》征引书目,多到八十种;《明季滇黔佛教考》征引书目更多至一百七十余种,而且都是不常见的书,陈寅恪先生为后者作序,称其“征引之资料所未见者殆十之七八”。若非于广义的目录学先有广博的知识,何能至此!但反过来说,若不作专仄问题的研究,也就不必先有那样深的目录学功夫。即如我常说的前辈四大家中,就广义目录学的功夫言,宾四师与诚之先生、寅恪先生,似都不如援庵先生,不也同样有其高度成就?且如寅恪先生,中年名著唐史两《稿》及《元白诗笺证稿》,皆不藉很深的目录学功夫;而晚年《柳如是别传》,则征引繁博,非深于此道者不为功。此与论题有关,也因时代不同,而运用不同。中古时代的书籍不多,几乎研究中古任何问题,都要把所有相关的古书全看一遍;目录功夫只限于后代,尤其近代学人研究这些问题的成绩了。所以治史需要目录学功夫的深浅,亦因论题性质而异,因时代不同而异,不拘一律。但这门学问仍要有人下功夫去研究。不但狭义的目录学要有人去研究,为学术史建立基础;广义的目录学也要有人下功夫,编辑各种目录书,以便一般人各取所需地去利用。
至于校勘学,古籍传承久远,往往有脱讹处,故阅读时必须随时留意比勘,以免为脱讹所误。清人治学极注意校勘功夫,到援庵先生撰《元典章校补释例》(1959年中华书局重刊本改名《校勘学释例》),校勘学的技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总结经验,认为校勘有四种方法,即“对校”、“本校”、“他校”与“理校”。照他的说明,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此法最简便,最稳当,纯属机械法。其主旨在校异同,不校是非,故其短处在不负责任,虽祖本或别本有讹,亦照式录之;而长处则在不参己见。得此校本,可知祖本或别本之本来面目。故凡校一书,必须先用对校法,然后再用其他校法。”本校法,即“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之前最宜用之”。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可以前人之书校之;有为后人所引用者,可以后人之书校之;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可以同时之书校之。此等校法,范围较广,用力较劳,而有时非此不能证明其讹误”。理校法,即“遇无古本可据,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之时,则须用此法。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鲁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我们研究历史问题,一接触到史料,常会发现古书字句可能有问题,就必须运用校勘方法来解决。否则就可能做不下去;或者为脱讹的史料所诱导而对于史事作出错误的判断。至于校勘方法,大体上不出援庵先生所说四种方法的范围,若能加以综合运用,必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不过需要校勘学功力的深浅,也看自己是向什么方向发展,研究什么问题。有些问题随时要运用校勘技术来帮助解决,有些问题就很少需要。例如我写《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运用校勘法处比较少,而写《唐仆尚丞郎表》,就随时都用到校勘方法。后来写《旧唐书本纪拾误》(《唐史研究丛稿》第十篇),补正《旧纪》一百七八十事,就中很多是传刻夺漏或传刻字讹,都是该《表》写作的副产品,也都是用校勘法所获得的成果。近年写唐代交通问题,发现《元和志》、《寰宇记》及《通典》的《州郡典》,脱讹都很多,我们运用时要随时留意,遇有可疑处,就必须仔细考量,经过审慎比勘,才能引用。我曾有意对于这几部书作一番全盘校勘工作,但时间不允许,只得作罢。大抵讲通论、讲大问题,需用校勘功夫处比较少;讲较小问题,愈下细密功夫,校勘法的功夫就愈大。
1983年3月7日再稿
来源:《治史三书》
- 0000
- 0000
- 0001
- 0000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