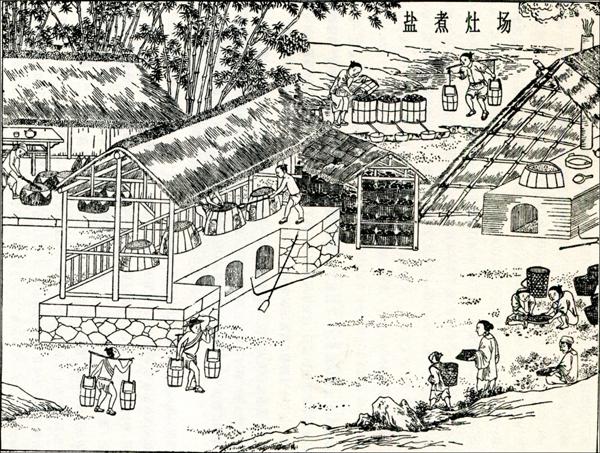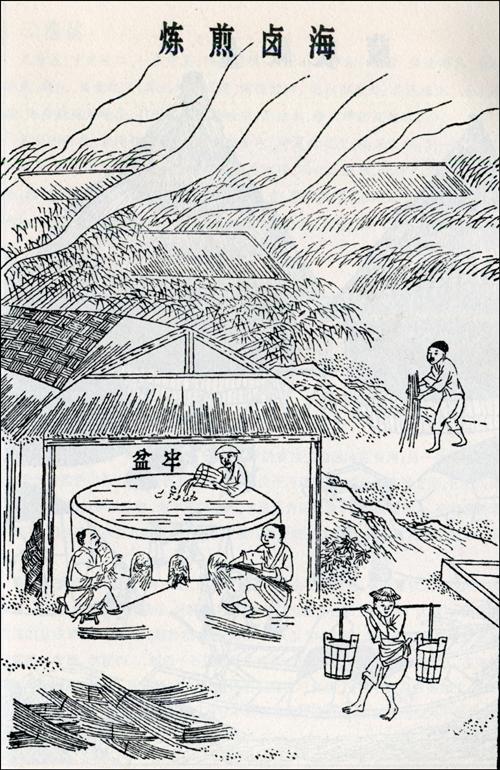严耕望:“无孔不入”、“有缝必弥”
问 你在《经验谈》的《序言》中说,研究问题要“无孔不入”“有缝必弥”。是否可举一两例说明之?
答 所谓“无孔不入”者,当建立自己论点时,要从各方面尽可能的找出有说服力的证据与理由,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论点;当发现史料或他人论点有矛盾或不合常理处,尤其是个好的孔隙,可以钻进去作一番探寻。所谓“有缝必弥”者,已建立了自己的论点,还要看看这个论点与所用证据是否还有漏洞,可能为人所乘,被一举击破;或可能被人误会有漏洞,引起人家怀疑,故必须预先弥缝起来,让别人无怀疑余地。所以前者是积极的,是攻势,是主导方法;后者是消极的,是守势,是辅助方法。
我最近为诸生讲解较早期所写《汉书地志县名首书者即郡国治所辨》一文(《中研院院刊》第一辑。按此文已增订,刊入我的论文选集)。今即先就此文各举一两例。
班氏《地理志》按郡国排列,各郡国下列出所领各县名称,并在适当的地方注明各种史实。就职官言,将本郡国中次要职官都尉的治所与各种业务机关(如盐官、铁官等)的所在地都明白的注明,但却绝不提本郡国的行政首长太守与国王、内史究驻在何处。这种情形,读者应可推想班氏必有义例;否则,班氏未免太糊涂,殊不合理。按《续汉书·郡国志》(即今本《后汉书》中的《郡国志》)在篇首即说明,“凡县名先书者,郡所治也。”《续志》书事,除分州排列外(州在西汉只是监察区,东汉州刺史权重,州实为行政区),一切条例皆仿班《志》,其自言郡国治所条例如此,故自郦道元《水经注》到胡三省《通鉴注》,均认为班《志》体例也是如此,《续志》承之耳。就是说班《志》各郡国下所列第一县就是治所,故不必特别注明。这是个顺理成章的排列次序,也是个极合理的解释。但到清代阎若璩始作翻案文章,说班《志》各郡国所列第一县诚然很多是治所,但不一定是治所。此说见其所著《潜丘札记》卷二。后经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五《郡国属县》之数条)、王先谦(《汉书补注》),迄近代学人如谭其骧(《西汉百三郡国守相治所考》,《禹贡》六卷六期)等,逐一增加史例,似已成定论。但我仍认为元以前旧说是正确的,阎若璩迄今学人的反驳,虽然列证纷纭,但在逻辑理论上都绝对站不住。因为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西汉二百年间,郡国治所常有变动,班《志》乃据西汉末年平帝世一时之版籍写录成篇,自不能与《本纪》、《列传》中随时所见的郡国治所完全相合。阎氏以下诸人,没有时间观念,忽略了这个基本道理,而遍搜《本纪》、《列传》中所见之郡国治所,来与班《志》相比勘,发现某些郡国治所不是班《志》的第一县,就说班《志》第一县不一定是治所,显得班《志》体例紊乱。其实《纪》、《传》所见郡国治所,往往是西汉末年以前某时的治所,自不一定能与班《志》完全相同。
我这篇论文,首先说明班《志》详细注明都尉治所,而绝不提太守治所,如此书事,必有义例。再遍举例证,证明西汉二百年中,郡国时有分合、增加或省废,治所也常有迁徙。然后再就阎氏迄今诸人所提出的证据一一加以检讨,有些处他们没有了解当时史事,尤可怪者,他们都无时间观念,好像西汉二百年间郡国绝无变动,治所更是不可有变动,真太迂执了!其实要使他们的论点能够成立,只要找出一个可信的证据,证明某郡国在西汉末年平帝世(最好元始二年)的治所不是班《志》某郡的第一县。只要有这样一条,就可说班《志》义例不纯,第一县不一定是治所了!只可惜他们提出的证据都是西汉中叶以前乃至秦及汉高祖时代的郡国治所,这样证据,虽征引纷纭,实际上毫无用处!
不过他们证据也有一条很坚强,即梁国八县,首列砀县。阎若璩曰:“梁国不治砀县,而治睢阳,以《梁孝王武传》知之。吴楚七国反,梁王城守睢阳,后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王国以内史治其民,而梁内史韩安国从王于睢阳。非以睢阳为治而何?”这条证据似乎很坚强,所以王鸣盛、王先谦、杨守敬、谭其骧诸学人皆信实其说;全祖望本持旧说者,至此也不能不承认班《志》有此一例外。承认有一个例外,就是承认阎氏新说第一县不一定是治所了!
我认为阎氏举《梁孝王传》为证虽很有力,但若只因梁孝王武与内史韩安国治睢阳,仍不足证明班《志》第一县之砀阳不是治所。因为梁孝王武与韩安国事在景帝世,下距平帝元始年间尚有一百五十年之久,仍不足以推翻班《志》第一县即是郡国治所之旧说。不过,我检查《梁孝王武传》,孝王薨,分为五国,长子买仍王梁,是为恭王。买子梁平王襄仍居睢阳。五传至王立,当成帝世,仍都睢阳。成帝(西元前32—前7)至平帝元始(西元1—5)时代已极接近,只有十几年,甚至只有八九年,就是班《志》所依据的版籍之时代了。所以他们的证据以这一条最为坚强有力;不过他们自己却未仔细分析出来!
我研究这个问题,到此处是一关键,若不能提出有力的证据,作合理的解释,则我的论点就要动摇。但又实在找不到一条积极有力的铁证,必得从各方面寻出孔隙,钻进去深入探讨,作合理的推论,以削弱上引《梁孝王传》这条证据,以维护自己的论点。我搜索思考结果,得到相当满意的合理解释与推论。兹录这段原文如下:
考《获水注》,“获水又东迳砀县故城北,应劭曰,县有砀山,山在东,出文石,秦立砀郡,盖取山之名也。……山有梁孝王墓。其冢斩山作郭,穿石为藏。……山上有梁孝王祠。”
又《续志》惠氏《补注》引《曹瞒别传》云:“引兵入砀,发孝王冢,破棺收金宝万斤。”是砀不但为大县,为秦砀郡所治,且亦为梁国始祖宗庙所在也。又检《孝王传》,梁分为五后,梁国尚有十三县,一传至王襄,有罪削五县,尚有八县,又五传至王立,仍都睢阳,然屡削户数。至成帝元延中(纪元前12—前9),复削立五县,只得三县矣。至平帝元始中(西元1—5)废为庶人。后二年,又立孝王玄孙之曾孙音为梁王,盖还复削五县,故《地志》仍为八县也。据杨氏《汉地志图》,梁国地形,东西两头广大,中间狭仄(中为沛郡之祁乡县所扼),如药葫芦形。西部五县,睢阳其一,东部三县,砀县其一;碍与睢阳之间有下邑、虞、蒙三县,则王立末年仅有三县时,必不能兼有砀及睢阳也。然砀县为梁之始祖墓冢祠堂所在,既与立国,似不宜割隶他郡,盖即其时尽削西部五县,徙都砀县,以就祖墓宗庙欤?且立甚刚戾,其得重罪,始于永始中“对外家(王氏)怨望有恶言”,故元延中削五县,有三县;元始中为王莽所奏废,亦“坐与平帝外家中山卫氏交通”之故。故自始即以不满王氏擅权而得罪,其他罪名皆莫须有也。睢阳为关东有数之大城,军事之重镇,王氏窃权,自不乐为刚戾不驯且素不满王氏者所居,故以东就孝王冢墓祠堂为名,徙都砀县,而收睢阳以益邻郡耳。故据《孝王传》,虽成帝时梁国仍都睢阳,但仍不能以概平帝元始时之版籍也。
我无直接证据,证明自己论点之必是,阎氏诸人论点之必非,但我以梁国祖墓祠庙为基点,参合梁国国土日削,疆域地形与梁王立得罪之背景,从这种种角度上加以推论,则在班《志》所代表的时代,梁国实都砀县非都睢阳已为极明显之事实,这就是“无孔不入”之一例。梁国祖墓祠庙所在、梁国疆域形状与疆土屡削至仅有三县,以及梁王立得罪之背景,这四点都是可以钻进去仔细探讨的孔隙。
再就此文另举一例。汝南郡,《汉·地志》第一县是平舆(今中共图置平舆县)。阎若璩以为汝南郡治上蔡(今县西),证据是《翟方进传》卷首叙事与《汝水注》。我就他这两条证据提出驳论,并从各方面观察,提出理由,推论西汉末年汝南郡治平舆之可能性远较治上蔡为大。兹亦就原文稍加增饰,引录如下:
检《翟方进传》首云:“汝南上蔡人也……父翟公好学,为郡文学。方进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给事太守府为小史。”云云。汉制,郡属诸县之人皆可为郡吏,此段文字何足为郡治上蔡之证?至于《汝水注》,则云“东过汝南上蔡县西。汝南郡,楚之别,汉高帝四年置”。此虽可证高祖始置汝南郡时治上蔡,然高帝时事不足以概哀、平。且高帝四年,天下尚未定,仓猝间所建之郡,其四境及郡治,势难与二百余年后哀平世班《志》之版籍相一致。而班《志》与百余年后之《续郡国志》,县数全同(均三十七城),县名四境变动亦极微。按《续志》汝南郡治平舆,吾人与其相信郡治迁徙在东汉初年,不如相信在西汉末年以前,因为高祖至武帝时代郡国变动最大。而西汉末至《续志》时代变动则甚小。且据《召信臣传》,昭宣之世,上蔡置长,不置令,是为小县,非大县。且于班《志》汝南郡三十七县中地位偏在西北境(参看杨氏《汉地志图》)。按汝南乃中原大郡,班《志》云领三十七县,四十六万余户,平均每县万户以上,必令多而长少;上蔡为长,不及万户,可见在诸县中之地位甚低。以理推之,不宜以地位偏在一隅而人口稀少之上蔡县为郡治。据《汉书·翟方进传》及《后汉书·方术·许杨传》,汝南有鸿郤陂,滨陂地饶民富(参看《淮水注》及杨氏《汉志图》);必多户口众多之大县。平舆为令为长虽不可考,然滨临鸿郤陂东岸,必地饶民富,为大县之可能性极大,加以地处一郡之中心地带(参看杨氏《汉志图》);其为郡治之条件远优于上蔡。则高帝仓猝建郡虽治上蔡,其后迁治一郡中心人口众多之平舆大县,殆可断言,阎氏拘泥高帝四年事以驳班《志》,谬矣。
这也是没有直接硬证,而从多方面寻罅蹈隙,找出合情合理的理由来支持自己论点之一例。
同一文中,也有“有缝必弥”之例。我在原文第六节中,先提出证据,证明郦道元《水经注》已以《汉·地志》首书之县为郡国治所。但是郦《注》中言汉郡治所亦偶有非《汉志》之第一县者,这岂不是我的话有了漏洞?所以下文又设为“或问”预作解释说:
或曰,郦氏既承认《汉·地志》首书之县即郡国治所,何以《注》中言郡治偶有非《地志》首书之县欤?曰,此亦有故。第一,郦《注》常云故某郡治,旧某郡治,或汉某郡治,属辞含混,并不一定指西汉而言。如《水注》,高柳故城,旧代郡治。按《地志》,西部都尉治高柳,必非太守所治;东汉乃郡治也。又如《濡水注》引《地理风俗记》曰,阳乐故燕地,辽西郡治。此明东汉郡治也。此类情形极多,不列举。前人于西汉郡治之无考者,即取此类所谓旧郡治、故郡治作为西汉郡治,遇有非《地志》首书之县,即据此訾班《志》无义例,此非逻辑所允许者。第二,郦《注》本非专言郡县之书,尤非专言汉世郡县之书,惟就河流所经附带追述故事耳。汉代郡国治所前后既常有迁徙,即曾为治所者不止一城。设有甲乙两城,如甲城为西汉末年所治,故《地志》列冠他县,乙城为前期治所,故《地志》序在甲后。前后治所既有甲乙二城,若甲城无河流,乙城有河流,甲城既无河流,郦《注》自遗而不载,乙城既有河流,自可附书为汉代郡治,吾人固不能据此以否认郦氏承认《地志》首书之县为郡治,亦不能据此谓西汉郡治乙城,即不治甲城也。若甲乙两城均有河流经其地,则或两书之:如中山郡,既云治唐县之中山城,又云治卢奴;又如河内郡,既治野王,又云治怀;是其例也。亦有一书一不书者。如犍为郡,西汉四易治所,皆近河流。郦《注》惟于鄨云郡治,于武阳似亦以为郡治,而于南广、僰道两地则失书。然吾人亦不能据此以否认郦氏承认《汉·地志》首县为郡治,亦不能据此谓西汉犍为郡治鄨及武阳,即不治僰道、南广也。此皆关乎逻辑方法问题,前人考证往往忽之!
这是我自己找出自己论点可能被误解为有漏洞,而预为辩解之一例。
以上皆就班《志》郡国治所问题各举一两例。我写论文,有述证处,有辩证处。辩证处,就经常要运用这两方面的方法。兹就其他论文再分别各举两三例。
关于“无孔不入”者,例如我写《括地志序略都督府管州考》(《史学论文选集》第七篇)就是由史料中两种不合理的情形所引发。《括地志》久已散佚,只有徐坚《初学记》之《州郡部》录存其《序略》,列举贞观十三年大簿之府州三百五十八个名称甚备。而孙星衍《辑本》辑此条,排列方式殊为可疑。如胜州都督府(治所在今河套东北角黄河东流折而南流处之南岸)越过好几州而远统蒲州(治所在今山西西南角永济县)、虞州(在今山西南部安邑县),黔州都督府(治所在今四川东南部彭水县)越过潭州(今湖南长沙)、洪州(今江西南昌)而远统睦州、括州(皆今浙江省境)、常州(今江苏南境)、抚州(今江西东境)等。如此之类颇多,绝不可能是事实。又《旧唐书·地理志》述各州沿革,有置都督府者,述其督州,屡次说“今督”某某若干州,而“今督”之后又有高宗、武后、玄宗年号,如永徽、显庆等。《旧志》为五代时期所编辑,此云“今督”显非五代时期之“今”,而为抄录过去志书原文。这两点都是大“孔隙”,可以钻进去深入探讨的,结果写成这篇论文。
又如东晋十六国时代末期,慕容燕与拓跋魏因参合陂一战(西元395年)而决定了燕亡、魏兴之命运,奠定魏统治北方之基础,这是北朝史上一次关键性战役,其重要性不下于东晋、前秦的肥水之战。但其地究在何处?郦道元《水经注》指在平城西北约三百里之遥的仓鹤陉,即后立为参合县处(今岱海西南)。但自汉世代郡有参合县,在今阳原县,是在平城之东百里以上,不在其西北。这又是史料有矛盾处,不过时代不同。我写《北魏参合陂地望辨》(《太原北塞交通图考》附录,《新亚学报》第十三卷),从种种角度研究,也可说从种种孔隙处探讨,乃知北魏初期之参合陂仍在平城东北汉参合县,今阳原县地,不在今岱海西南。但汉县故地之参合陂,到北魏后期已淤废,而苍鹤陉音近“参合”,又当平城西通云中故都之大道,近处亦有陂地,故不免世俗相传,以为即燕魏战地之参合陂,郦氏不察,故有此误耳。
再如《旧唐书·玄宗纪》,开元十七年八月“乙酉,尚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兼吏部尚书宋璟为尚书右丞相。尚书左丞相源乾曜为太子少傅”。按此文显有问题。姑不论宋璟官衔前后两“右丞相”是否有误;而宋璟原衔,开府仪同三司是散阶,右丞相与吏部尚书都是实官,唐籍中书人官衔,决无以散阶夹于两官名之间之事例。此显然是一大孔隙,有问题。经过与他人官历参互比勘,多方取证,乃知第一个“尚书右丞相”下脱去“张说为尚书左丞相”八个字,以致文理不通。说见拙作《旧唐书本纪拾误》(《唐史研究丛稿》第十篇。按《旧唐书·玄宗纪》此条已编入《正史脱讹小记》,刊我的《史学论文选集》)。
我撰论文,如此诸例,不胜枚举。但有些史料所显露的小孔隙,当时懒得细心追求,即酿成大误。例如我写《唐五代时期之成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十二卷),在附记中已自表白,这篇论文的写作态度比研究交通问题松懈得多。但一放松就出毛病。例如第三节讲城郭,我遗漏了《舆地广记》卷二十九成都府双流县一条重要材料,因此白费了许多转弯抹角的考证功夫(虽幸结论不错,但那条材料早已讲明了),这且不说。而照这条材料看,高骈所筑外围罗城之南墙在外江(大江)之北,内江故渎之南。我虽未看到这条材料,但我写作当时,看到《元和志》成都县目云“万里桥架大江水,在县南八里”;《寰宇记》华阳县目云,“万里桥在州南二里”。益州成都府所治成都、华阳两县实在一个城中,两书记万里桥去城墙距离有六里之差,当时本已想到《元和志》撰述在高骈筑罗城之前,自就旧城(即后来之内城)而言,《寰宇记》撰述在高氏筑罗城之后,当就外围罗城而言。若当时循此孔隙追求下去,可能有所发现;但态度放松了,此等细节处懒得再进一步分析。所以本文中未加说明,后面附图,不免随便将外围罗城的南墙也画在内江故渎之北,因此就错误了。这是个好教训。所以真正的以绝对标准研究问题,实在是一点都不能放松的!何况不着实际的放言高论!
至于“有缝必弥”者,例如我近年讲唐代户口问题。一般人总拿正史《地理志》所记户口数作为当时中国的户口实数;其实这是大错。《地志》所记户口只是户籍,政府凭以收税,当时实际上的户口数照例比户籍簿上的户口为多,有时多几倍,乃至十倍。唐朝户籍之户口数以天宝年间为最多,但仍非实际户口数,因为除了隐没户口之外,还有很多种人合法的不入户籍簿;如僧道、商贾、官户、杂户、部曲、奴婢等等都不入户籍簿;中国境内还有少数民族,也多不入户籍簿。所以实际上的户数口数都比地志、政书所记户籍数量为多。因此在唐代其他文献中所见到的各州实际户口数字多半比同时代或相近时代户籍簿中的户口数字为大,而且有些大得多。例如元结《舂陵行序》云:“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全唐诗》四函六册)癸卯为代宗广德元年,上距《新唐志》所记天宝版籍甚相近,而户数几为《新志》道州户数(二二五五一户)之两倍。又如韩愈《潮州请置乡校牒》云,“今此州户万有余。”(《全唐文》五五四)按愈以元和十四年贬潮州,在《元和志》版籍之后只六七年,而民户为《元和志》潮州户籍(一九五五户)之五倍有余,亦为《新唐志》所代表唐代户籍最盛时代潮州户数(四四二〇户)之两倍以上。此两条证据皆无可置疑者。但有些证据却可能被怀疑有问题。如顾况《宛陵公署记》云:“夫宣户五十万,户二丁,不待募于旁郡,而宣户之半已五十万矣。”(《全唐文》五二九)按此《记》以庚辰年作。检《新唐志》,宣州天宝户一二一二〇四。《元和志》二八,宣州元和户五七三五〇。庚辰为贞元十六年,上距《新志》版籍四五十年,下距《元和志》版籍至多十二年,而户数为《元和志》之九倍,亦为《新志》之四倍。不管如何解释,都比户籍簿上的数目多得出奇。惟此文所记数字有一可能的漏洞,即两个“五十”之“十”字可能为衍文。若此“十”字果为衍文,正与时代极相近之《元和志》所记户籍数相当。欲推翻我的论点者就可能这样怀疑,所以这两个“十”字是这条证据可能的漏洞。但考韦焕《新修湖山庙记》,“今宛陵、泾县十八乡,户四万,民奉湖山神。”(《全唐文》七九一)检《元和志》,宣州领乡一百九十五,韦《记》云十八乡四万户民奉此神,则一百九十五乡正当近五十万户,所以“五十”极正确,无衍文。如此一来,顾《记》作证的力量就大为增强,成为一条铁证,证明宣州在贞元元和间实际户数毫无疑问的为户籍簿中户数之八九倍。这是“有缝必弥”之一好例。
又如我写《汉代地方官吏籍贯限制》(《史语所集刊》第二十二本,又《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一章),主要方法是用诸多史例作统计,但发现有极少数例外,我都自己提出来,一一预作解释,或证明该条材料本身有误;不要等到别人发现这些史例来驳我的论点。或者如果材料本身就有局限性,影响到结论的准确性,也要先自加以说明。例如我写《扬雄所记先秦方言地理区》(编为《史学论文选集》第三篇),照史料数据统计,吴越方言,只是亚强区(C级),至多只能归入强固区(B级),不如东齐、南楚之为特强区(A级)。这一点决不是事实,所以也预为说明吴越数据何以偏小之故。我写论文,在这些方面很注意,尽可能的不遗留一个缝隙一个弱点,让人家抓住,也尽可能的不遗留一点可疑处引起人家的误会!这就是所谓“有缝必弥”。不过这只是辅助方法,不是每一篇辩证性论文一定都用得到的!
大抵研究问题,提出自己的论点,一般人通常都能努力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论点;但对于自己论点的漏洞或可能的漏洞,通常都比较疏忽,不太注意。即如上文所提到的《汉书·地志》郡国治所问题,自康熙时代的阎若璩直到现在差不多三百年,好多有名的学人只是尽力的去找出治所不是《汉志》郡国下所列第一县的证据,却不反省一下,班《志》详记都尉治所而绝不提太守治所,其故何在?也不想想,西汉二百年郡国治所有迁移的可能性。这可说是,只知盲目的进攻,不知稳健的防守,自己留下了明显的大漏洞,致命的大弱点。所以我在大学读书时代就看出他们的论证在基本理论上站不住,不过要提出批驳的具体证据,就要十年以后才能做得到!再如有一位很有地位的史学家,研究《蛮书》中所记戎州石门通南诏道,谓道中之“曲州、靖州”即今云南曲靖县,旧南宁县,南北朝以来之宁州、南宁州。按《蛮书》此段记程甚详,云“从戎州南十日程至石门”“石门……西崖……有阁路”“阁外至蒙夔岭七日程”。下文详述自石门第三程、第五程各至何处,“第七程至蒙夔岭”“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凡从鲁望行十二程,方始到柘东”。按戎州即今四川宜宾县,柘东即今云南昆明市,都绝无问题。曲、靖州故地若在今曲靖县,则由曲靖西至昆明平地三百华里,为十二日程,而宜宾南至曲靖一千五百里以上之千古险道乃仅十九日程,这是绝不合理的,所以这个论断必有问题,是一个大漏洞,而作者竟未考虑到,无疑也太疏忽,读者只要细心一点,马上可以看得出来,不过要指明曲靖故地究在何处,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此段辩论,请参看拙作《汉唐川滇东道考》(按此文收入《唐代交通图考》第四卷)。
总之,不论是“无孔不入”或“有缝必弥”,都是要细心的阅读史料,严密的思考问题,否则自己论点很难真能建立起来,所提论点也很容易被人一捣即破,归于失败!
1983年3月2日再稿
1984年8月3日最后增订
来源:《治史三书》
- 0000
- 0003
- 0005
- 0001
- 0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