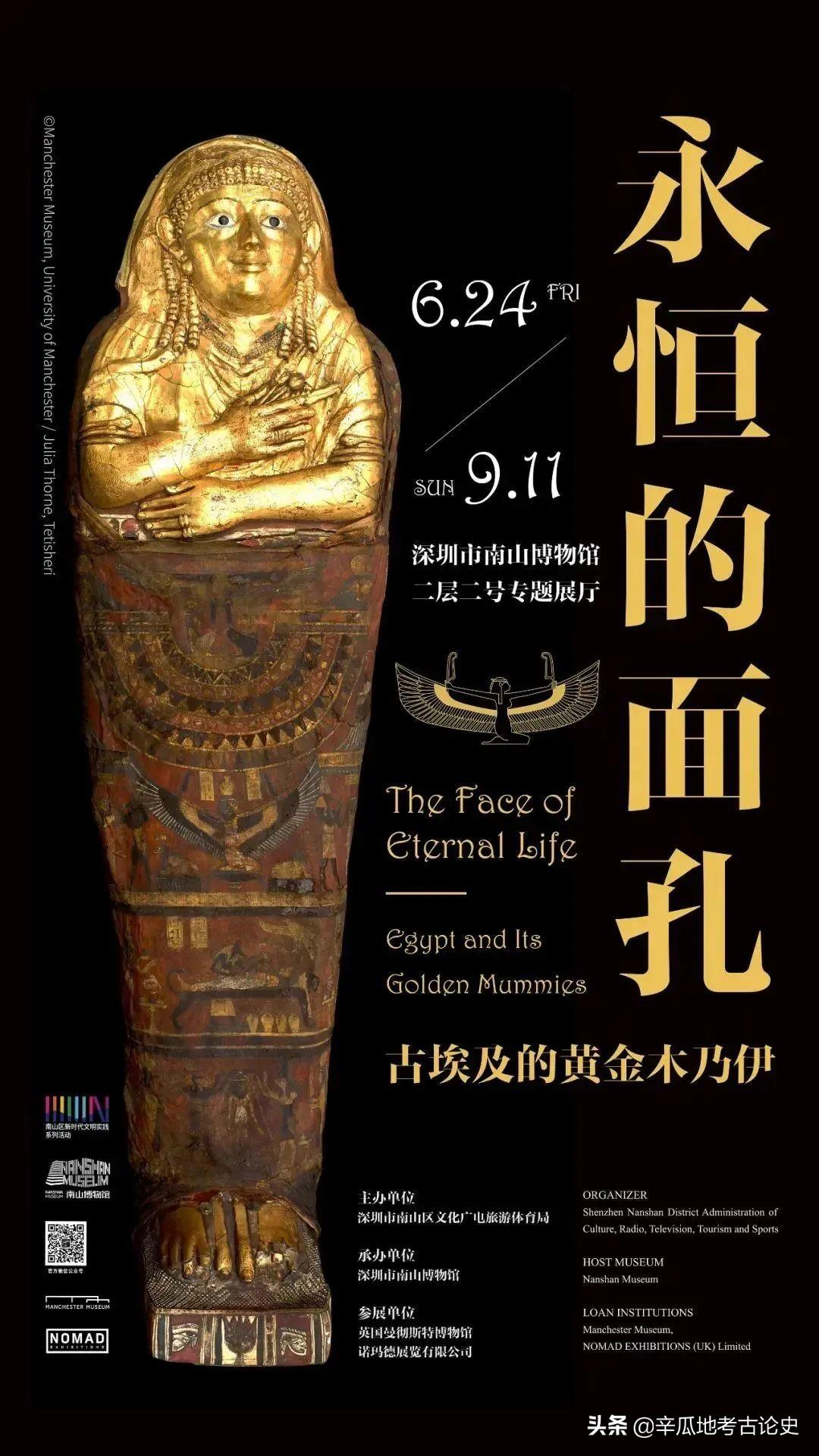追溯三星堆文明的起源
距今三四千年前,在今广汉三星堆遗址一期文化(宝墩文化)的废墟上,高高耸立起坚固而厚实的城墙,城墙外掘有深深的壕沟。
南城墙内的两个祭祀坑内,埋藏着数以千计、举世罕见的大型青铜制品、黄金制品、玉石制品、象牙和海贝。

方圆达3.5平方公里的城圈内,分布着密集的文化遗存,有宫殿区、宗教区、生活区和作坊区,出土大批玉石礼器、陶制容器、陶塑工艺品和雕花漆木器。在一些陶器表面,还赫然醒目地刻画着一些文字符号。
 新津宝墩古城墙遗址的西城墙
新津宝墩古城墙遗址的西城墙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情况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出土器物情况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虎形金箔饰
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虎形金箔饰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
三星堆出土的海贝
 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上的刻画符号
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上的刻画符号
这一切,都确凿无疑地表明,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城市、文字(符号)、青铜器、大型礼仪中心等多个文明要素不仅都已同时、集中地出现,而且还发展进化到相当高的程度,它显然标志着古蜀文明时代已经来临。相应地,城乡分化、阶级分化、社会分层、权力集中,也已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一个植根于社会而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古蜀王国已经形成。这一切都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一个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心,已经诞生在古蜀深厚而广阔的大地上。
三星堆文化是长江上游地区最早的古代文明,它的初创年代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稍晚于中原夏王朝,而它的终结约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相当于中原商王朝的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雄踞西南,连续发展千年之久,对于一个文明古国或古王朝来说,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多见的。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酒器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陶酒器
古蜀之所以能在距今三四千年前就创造出如此辉煌的古代文明,这与它深深地植根于博大而深厚的基础分不开,即它是立足于农业的长足发展、手工业的巨大进步、商业贸易关系的广泛建立、科学知识的积累创新,以及与其他古文化的密切联系和交流。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和陶器,有相当一部分属于酒器,显示出发达昌盛的酒文化。大量酿酒,必然以粮食的大量剩余为前提,可见农业发展之一斑。《山海经·海内经》载:
西南黑水之间,有都广之野,后稷葬焉。其城方三百里,盖天下之中,素女所出也(此十六字原脱入郭注,今据郭注、郝疏并王逸注《楚辞·九叹》所引补)。爰有膏菽、膏稻、膏黍、膏稷,百谷自生,冬夏播琴(毕沅云:“播琴,播种也。”)。
文中,“都广”乃广都之倒文,都广之野即成都平原。可见古蜀农业发达,是文明起源最重要的前提。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制品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黄金制品
三星堆祭祀坑内出土的黄金制品和大型青铜器群,气势宏伟,蔚为大观。其中的青铜雕像群,如青铜大小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神树,以及金杖、金面罩等,都是中国首次发现的稀世之宝,价值极高,而又与中原夏商文化判然有别。大批玉石礼器和陶、漆工艺品,都展现出高超的技术水平,从而体现出细密的分工和生产的专门化。青铜器制作所必需的采矿、运输、冶炼、合金、铸造加工等环节,也无一不是分工协作的有力证据。可见,经济部门的分化,大批脱离食物生产的手工业者的技术专门化,为青铜时代的到来奠定了知识、技术和生产者队伍的雄厚基础。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海贝,背上多有穿孔,学者们多认为是贝币,反映出商业的繁荣。而海贝本身,以及六七十支象牙,也正是远程贸易的实物见证。青铜器所必需的铜料锡料,也是通过贸易进口。这些说明贸易已不是偶然现象,它已从获取生产原料,进一步发展到获取王权所及的一切奢侈品。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
丰富的科学知识、高超的技术和伟大的艺术,共同融进作为创造性产物的各种物质形式之中。从金、玉到陶、石,从青铜器到建筑物,都是它们直接而具体的表现。其中也包含不少通过交流从外部移入的文化因素。如中原商文化中的青铜礼器,近东文化中的青铜雕像、权杖等文化形式。正是由于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才使古蜀文明具有世界文明的色彩,使它成为一种富于开放性特点的灿烂的古代文明。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象牙出土情况
三星堆三号祭祀坑象牙出土情况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三星堆文明又是上古四川盆地及周边各族共同创造的伟大成果。例如,文献记载古蜀文化的初创者三代蜀王,来源于岷江上游地区;而四川盆地以北的陕南汉中盆地,以东的长江三峡以至鄂西宜昌地区,以南的大渡河和青衣江地区,又是三星堆文明辽阔的空间构架中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这就表明,三星堆文明的创造,一方面是古蜀史前文化高度持续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其文化因素的多元性来源分不开。因此,三星堆文明的基本结构框架,同样是多元一体,而不是一元形成的。
- 0000
- 0000
- 0002
- 0000
-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