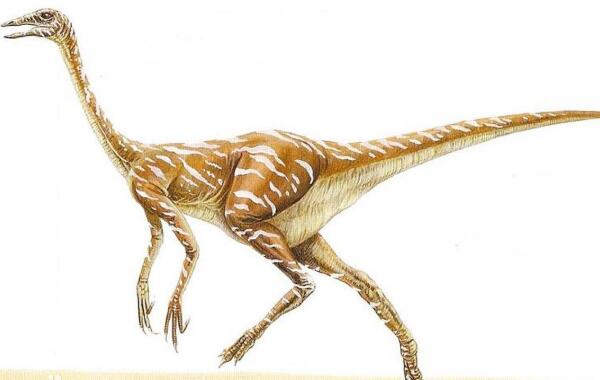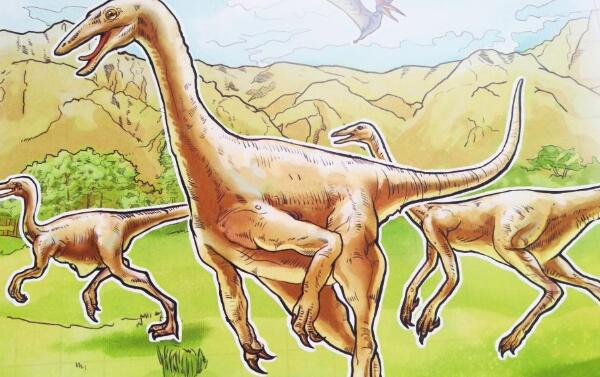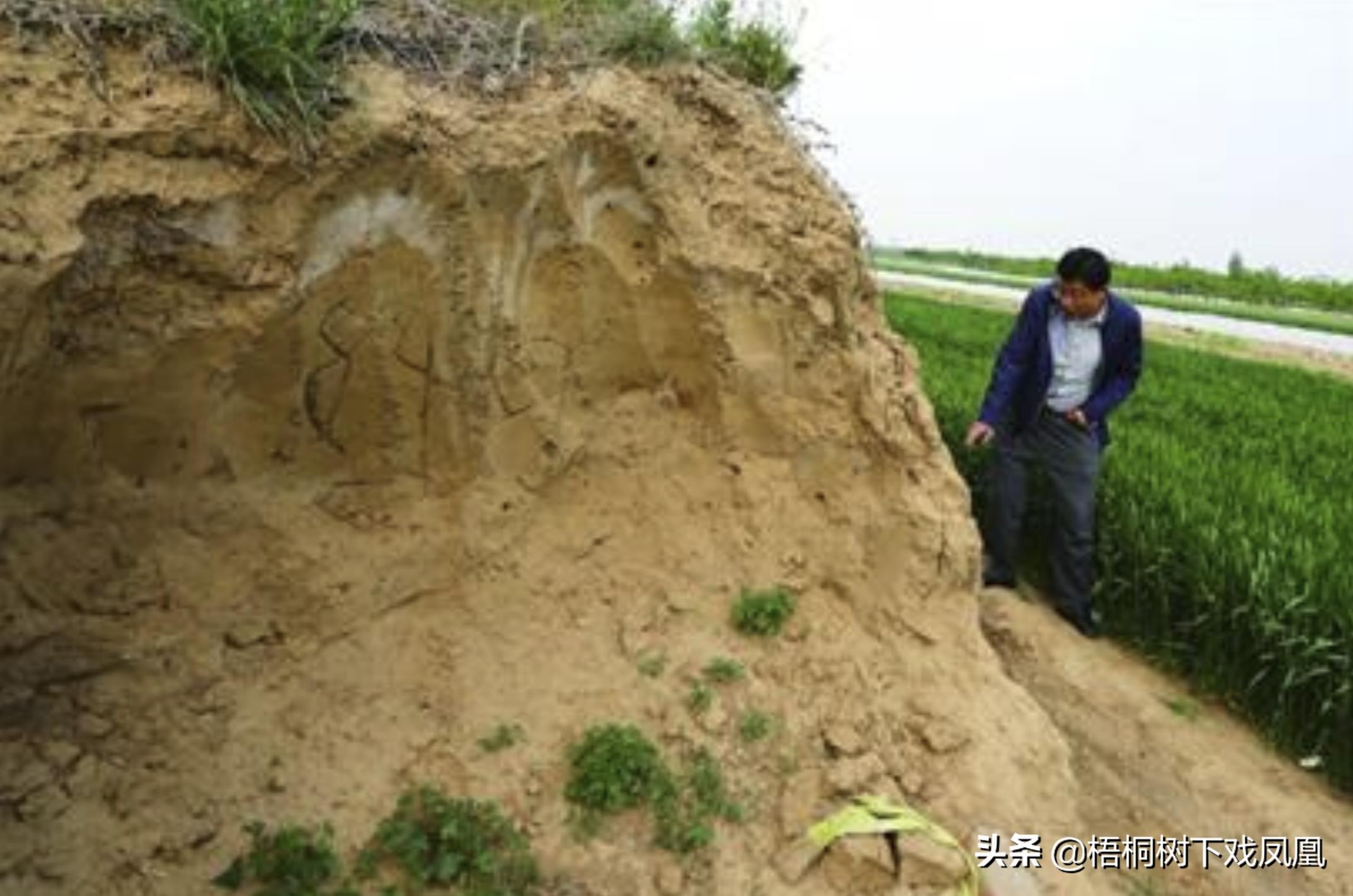陈志华:中国古代园林
中国造园艺术在世界上自成体系。世界上大致有五个造园体系:意大利的、法国的、英国的、伊斯兰国家的和中国的。其中,意大利、法国和伊斯兰国家的园林都是规则的几何形。英国和中国则同是自然风致式,但英国园林以天然牧场风光为基本格调,大面积的缓坡草地,点缀一些疏林老树和池沼,中国园林则以典型地再现荒莽的山水之美为特色。
保留下来的中国古代园林,不是创建于清代的,就是虽然创建较早但在清代经过重大改建的。清代之前的园林大多只能据文献资料去认识,明代的还有一些片段。
从起源到基本风格形成
园林是绿化的生活环境。它区别于蓄兽游猎的苑和囿以及种蔬艺果的园和圃的,是它的游赏性;区别于可供游赏的自然景观的,是它的人工性,并限于一定的范围。
就文字记载看,西周周文王的灵囿可算最早的园林(见《诗·大雅·灵台》)。它有高台、池沼,风物悦人,方七十里,百姓可以去樵采狩猎(见《孟子·梁惠王上》),其景观当然是很自然的。
春秋时期,营建渐侈,如吴王夫差建姑苏台、梧桐园等,开江南造园风气之先。战国各国更是“高宫室,大苑囿,以明得意”(《史记·苏秦列传》)。北方燕、赵等国古都遗址中,官苑都很大,其中遍布建筑物,燕下都宫苑里竟发现有台基三十余座,气魄宏大。屈原《招魂》描述楚国宫廷:“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网户朱缀,刻方连些……川谷径复,流潺谖些……坐堂伏槛,临曲池些;芙蓉始发,杂荷芰些……”建筑物与园林相渗透,风格纤丽。南方园林与北方的差别已约略可见。
秦朝在上林苑内引水筑兰池,池中建蓬莱、瀛洲二岛;汉在建章宫内苑筑太液池,池中建蓬莱、瀛洲、方丈三岛(均见《三辅黄图》),虽有求仙的迷信色彩,却都是造园。相传梁孝王的兔园和茂陵富人袁广汉的私园也都以人工堆垒的石山和水池为主要内容(见《西京杂记》)。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抓住了自然景观中两个最基本的因素,后来的人就以山水代称自然,成了自然风致式园林的基本因素。水与山不仅动静相对比,而且以空灵比质实,以明净比苍莽,以浩渺比峭拔,以柔比刚,有很重要的审美意义。这个时期的假山水的规模都比较大。兔园里“诸宫观相连,延亘数十里”,袁广汉园里“徘徊连屋,重阁修廊,行之移晷不能遍也”。可见园里建筑物的比重很大,后来便成了两千年中国园林的传统特点。
东汉在洛阳营西园和芳林苑。曹魏明帝时在芳林苑里筑景阳山,竟至亲自率领公卿群僚去挖土。景阳山是土山,“树松竹杂木善草于其上”(见《魏略》)。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的园林“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后汉书·梁冀传》)。这“有若自然”,是以后中国造园艺术追求的基本原则。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化发展的转折时期。这时出现了热爱自然的高潮,山水诗和山水画开始流行,进一步推动了造园艺术,“园林”一词也在这时出现。这时期园林的发展主要有三方面:第一,虽然无论南北,宫廷园林规模仍然很大,但私家园林广泛兴建,而且重要性提高;第二,江南园林风格形成,与北方宫廷园林风格对峙;第三,造园艺术由粗放转为细致,景物更典型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斗争和民族斗争异常激烈,士大夫知识分子的生死荣辱变化不定,隐逸之风兴起,知识分子产生了对大自然的亲切感情。老庄的返璞归真,通过自然而达道的思想,与儒家的“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易·乾卦》)的思想,以及佛教的超然世外以求解脱的思想合流,被士大夫知识分子广泛接受。于是他们纷纷寄情山水,兴造园林,过放达洒脱的生活而蔑视礼法名教。这种态度成了对在朝派统治者荒淫腐败生活的抗议和批判,具有一种道德力量。荐举制和以后的科举制都不给予士大夫世袭的、终身的爵禄,他们最后的安身立命之地还是地主经济。所以,这种“田园之乐”一直保留在知识分子心中,成了造园艺术传统稳定的原因之一。
魏晋南北朝的私家园林隐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绝意仕途、雅好自然的文士们的;二类是权势者的。后者如《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争修园宅,互相竞夸。崇门斗室,洞房连户。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台芳榭,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在南方的建康(今南京)则有南齐文惠太子的“元圃”和茹法亮的宅园、梁湘东王的湘东苑等。这类园林虽然有山有水,有树有花,也有吟唱“映月”、“临风”的雅兴,“禊饮”、“琴吹”的闲情,但建筑物不但多,而且华丽壮观,所以园林的野趣反而有限。
晋室南渡之后,江南一带的文士园林则是另一种风格。东晋孙绰在《遂初赋》里说:“余少慕老庄之道,仰其风流久矣。……乃经始东山,建五亩之宅,带长阜、倚茂林,孰与坐华幕、击钟鼓者同年而语其乐哉。”南朝刘宋时戴颐“出居吴下,吴下士人共为筑室,聚石、引水、植林、开涧,少时繁密,有若自然”(《宋书·戴颐传》)。这类园林,多利用天然地形、地物,建筑物少而简朴素淡,景观多野趣,“朝士爱素者,多往游之”(《宋书·刘勖传》)。它们真正与山水诗、山水画一起代表当时新的文化潮流。
使江南园林风格异于北方的,也与当地山水秀丽,开发水平比较高有关系。谢灵运的山水诗和宗炳的山水画都产生在这一带,风光使人应接不暇的山阴道也在这一带。
文士园林与山水诗、山水画同时发展,与诗、画一样,它也有很强的抒情性,所以晋简文帝司马昱才在园林中觉得“鸟兽禽鱼自来亲人”(《世说新语·言语》)。这种抒情性后来也一直是中国园林的重要特色。
文士园林代表着比较高的文化水平,因而对北方园林发生了影响。庾信由梁入北周,也带去了江南园林的情趣。他在《小园赋》里写的“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就是这种情趣。
私家园林比较小,因此在模山范水之际,不免要用些象征手法,借重于想象。当时兴起的山水画提供了经验。宋宗炳说:“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回。”(《画山水序》)于是梁萧统论园林,“穿池状浩汗,筑峰形粜岌”,显然是缩小了山水的尺度。同时,南朝的园林里已经有用单块石头点景,以比拟山峰的了。杨街之记洛阳司农张伦宅园中的景阳山,“其中重岩复岭,嵌峑相属。深蹊洞壑,逦逶连接。高树巨林,足使日月蔽亏;悬葛垂萝。能令风烟出入。崎岖石路,似壅而通;峥嵘涧道,盘纡复直”(《洛阳伽蓝记》),这小尺度的假山仍然具备天然山峦的各种典型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园林的基本因素已经大体产生,风格已经大体形成,以后没有重大的质的突破。
艺术手法的深化和多样化
隋唐和北宋,全国统一,南北造园艺术交流渐多,因而手法逐渐深入和多样化。
皇家园林的建造以隋为盛。隋炀帝在洛阳附近兴建大量宫苑,最著名的是西苑。它大体上还循秦汉上林苑的旧制,在周围200里的范围内,建16院,院间有龙鳞渠曲折盘绕。有山,高百余尺;有海,广十余里。又种杨柳修竹,名花异草。有亭有桥,结构精丽。(见《大业杂记》)炀帝凿通大运河之后,几次到扬州游乐,沿途造离宫别馆,在扬州造上林苑、萤苑等园林。炀帝把北方皇家园林和建筑的一些特点带到了扬州,成了当地建筑和园林风格的一种因素。
唐朝的皇家园林规模不及隋,也不见特色。到北宋初,则有汴梁的玉津园(始于后周)、宜春苑、琼林苑和金明池四个名园。宋徽宗兴建艮岳,是叠山艺术成熟的标志。艮岳在宫城东北,主事者是出自苏州造园世家的朱勔,所用的石料是太湖石,所以颇多江南特色,以再现山岳之壮丽为主,建筑物处于从属地位。徽宗《艮岳记》说:“东南万里,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其绝胜。”这段话第一次道出了将自然山水经过剪裁概括加以典型化的设计意匠。艮岳相当大,高90步,周回十余里,布局注意到分区设景,每景有鲜明特色,东西南北,山上山下,都有不同的山势水态、竹树花草和点景建筑物。这些景色和意境不同的景区以一定的游览路线贯串,造成动态的变化。“复由蹬道盘行萦曲扪石而上,既而山绝路隔,继之以木栈。……跻攀至介亭,此最高于诸山。”景色不但在动态中置换展开,而且是立体的,多方位的,多层次的。“自山蹊石罅搴条下平陆,中立而四顾,则岩峡洞穴,亭阁楼观,乔木茂草,或高或下,或远或近,一出一人,一荣一凋,四向周匝,徘徊而仰顾,若在大壑深谷幽岩之底。”艮岳的设计甚至考虑到“时序之景物,朝昏之变态”。可以说,艮岳是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经过周密构思的最完整统一的造园艺术作品。
艮岳还有全仿农家的“西庄”,显然受到文士园的影响。此后农家常在皇家园林中作为一个景区。
南宋时期,在临安(今杭州)也造了些皇家园林。但毕竟是偏安局面,金瓯半缺,不敢过于奢华;又兼当地文士园传统很强,所以这些皇家园林比较素朴。陆游咏聚景园:“尽除曼衍鱼龙戏,不禁刍荛雉兔来。”曾怀咏玉津园:“江山秋色冠轻烟,别苑风光胜辋川。”一个比周文王的灵囿,一个比王维的辋川别业。
唐代私家园林集中在长安(今西安)和洛阳。在长安,“公卿近郭皆有园池,以至樊杜数十里间,泉石占胜,布满川陆”(张舜民《画墁录》)。至于洛阳,贞观、开元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号千有余邸”,且多有园林,所以“天下之治乱候于洛阳之盛衰而知;洛阳之盛衰候于园圃之废兴而得”(李格非《洛阳名园记》)。北宋汴京(今开封)的园池,据袁裘《枫窗小牍》记载,约有一百余座。南宋的私家园林则多在临安、吴兴、苏州、嘉兴、昆山等地,这些地方从南朝以来,经五代至宋,都是文士园的集中地。临安园林借西湖风光,所以有诗咏“一色楼台三十里,不知何处觅孤山”(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
私家园林,公卿贵戚的与文士的,格调不同。而在造园文化中,文士园的疏淡雅逸至少在理论上成了正宗。王维的辋川别业,白居易的庐山草堂,影响都很大。连南宋大官僚韩侂胄的南园也要有“许闲”之堂、“远尘”之亭、“归耕”之庄(见陆游《南园记》)。
辋川别业虽然不是一所完整的园林,但王维以地貌和植物等给景点命名,如辛夷坞、茱萸沿、斤竹岭、文杏馆等,开创了以后以景为单元经营园林布局的手法。一个景是一幅画面,成景、得景就是园林构图的核心问题。
私家园林通常是起居之所,园林观赏与日常生活相渗透。白居易描写他在洛阳履道里的宅园:“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睡,足以息肩。有堂有序,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肴,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于其间。”司马光的独乐园中有读书堂、弄水轩、钓鱼庵、种竹斋、采药圃、浇花亭、见山台。他在《独乐园记》里说:“平日多处堂中读书……志倦体疲,则投竿取鱼,执椎采药,决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热盥手,临高纵目……不知天壤之间复有何乐可以代此也。”因此,宅园的生活气息很浓,园主人的文化气质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通过给景点命名、给建筑物题匾额,或种竹疗俗,或筑曲水流觞仿兰亭雅集,给园林注入极其丰富的文化内涵。它调动人的多方面知识,引起人的多方面联想,把观赏园林变成高层次的文化活动。以宋代园林名称如“沧浪亭”、“独乐园”与唐代的“平泉庄”、“午桥庄”相比,拿“招隐”、“濠上”这样的景点名称与“欹湖”、“鹿砦”等相比,显见得宋代的造园艺术更深入、精致了,也更综合化了。
画家亲自动手擘画园林,更使造园艺术深入精致。北宋诗人兼画家晁无咎自己设计归去来园。周密《癸辛杂识》记南宋吴兴画家俞征造园,“胸中自有丘壑,又善画,故能出心匠之巧”。园林的综合化又进了一步。
较之庄园里的私家园林,城市里的私家园林一般面积比较小,所以更多发展象征手法调动观赏者的想象力。唐李华《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写道:“庭除有砥砺之材,础褫之璞,立而像之衡巫;堂下有畚锸之坳,圩螟之凹,陂而像之江湖。……一夫蹑轮而三江逼户,十指攒石而群山倚蹊。”努力在小中见大上做功夫,并且接近于写意画。要小中见大,除了像艮岳那样善于剪裁自然山水的典型特征外,掌握尺度是个关键。所以白居易说:“地窄林亭小”、“小水低亭自可亲”。在这种情况下,以单石代山的做法更普遍。士大夫知识分子爱石成癖,有人竟至称石为兄为丈。
突破高墙深院的局限的重要方法是靠楼阁或者假山巅上的亭台眺望外景。如吴兴沈做宾园有对湖台,“尽见太湖诸山”(周密《癸辛杂识》);临安德寿宫内有聚远楼,取苏轼诗:“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
早在汉武帝修上林苑的时候,就重视收集各种观赏花木,至唐李德裕的平泉庄有花木一百种以上。李格非说“洛中园圃花木有至千种者”(《洛阳名园记》),牡丹、芍药就有一百多种,造园因素已经很丰富了。花木的种植不但取观赏性,而且取它们的“品格”。松柏取其岁寒而不凋,梅取其冰清玉洁,菊取其象征隐逸,竹取其虚心劲节。周敦颐《爱莲说》称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喻为君子,所以园林中很喜欢种植它。花木的人格化既增强了园林的抒情性,更丰富了园林的文化内涵。
从极盛到衰败
明末清初是中国造园艺术的极盛时期。
明代的皇家园林主要是北京皇宫的西苑,包括北海、中海和南海。北海在金代是中都北郊的离宫,元代建大都城后成为御苑的一部分。
金代皇帝开发北京的西北郊风景区,在香山和玉泉山建造离宫。明代在这一带建造了大量庙宇,都附有园林。清代初年,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又在这里造了畅春园、静明园、静宜园、圆明园(包括长春园和绮春园)和清漪园五座大型皇家园林。畅春园和圆明园建于平地,利用当地丰沛的泉水。静宜园占香山东麓,静明园就是玉泉山,二者都是山地园。清漪园居于平地园和山地园之间,有万寿山和昆明湖一山一湖。它们各依自然条件布局,特色鲜明。圆明园面积约350公顷,是集锦式的,由几十个小景区集合而成,每个景区大体上是以建筑物为核心的小园,用小山小水把它们分隔开来又连接起来。宫殿虽然居于中心,但在构图上不起统率作用。清漪园面积约290公顷,布局是集中式的,万寿山正中壮丽的大报恩延寿寺和它的高阁统率着整个前山前湖区的构图。后山区和南湖区作为补充,增加全园的深度。乾隆最偏爱清漪园,有诗说:“何处燕山最畅情,无双风月属昆明”。
这五座皇家园林形成一个相互资借的园林群。从畅春园和圆明园西望香山,以玉泉山和万寿山为中间层次,山姿塔势各有不同。在清漪园东望是圆明园和畅春园的湖光树影,向西则隔玉泉山而望香山。在这五座园林的周围还散布着小型的王公大臣们的私园,使北京西北郊成了一个大园林区。1860年,英法联军破坏了全部这五座皇家园林。1889年重建了清漪园,恢复了一部分建筑物,改名为颐和园,正中的建筑物改名为排云殿和佛香阁。
清代初年另一座重要的皇家园林是热河承德的避暑山庄。它包括几座峰峦沟壑比较复杂的山和几片港汊歧出、洲渚纵横的湖。景观很自然而且曲折幽深,外围的山水也很好。全园面积564公顷,是清代最大的御园。
这六座皇家园林是历代皇家园林造园艺术的大总结。它们兴造的时候,特地招聘了苏州一带的著名匠师参加,而且辟出一些地段仿造江南名园,所以它们也是中国整个造园艺术的大总结,是中国造园艺术的重要代表作品。
明代初年,先在南京,后在北京,造了大量功臣将相的私家园林。据王世贞的描写,南京的这些园林,有“最大而雄爽”的,有“清远”的,有“大而奇瑰”的,有“华整”的和“小而靓美”的(《游金陵诸园记》)。可见造园已注意到整体的风格。
明清两代私家园林的最杰出代表则是扬州、苏州和江南各地的文士园。重要作品有无锡的寄畅园,海宁的安澜园,上海的豫园,南翔的古猗园,太仓的弁园,嘉定的秋霞圃,苏州的拙政园、沧浪亭、留园、环秀山庄、网师园和扬州的瘦西湖园林群等。寄畅园建筑物较少而且僻处一隅,以土石山居中,从水池对面望山,则山后接惠山和锡山,境界清旷。拙政园东北部是湖山区,西南部是厅堂廊桥所形成的若干院落区,西北有楼可以眺远,东南有一个小巧的枇杷园,景观的变化对比相当丰富。扬州瘦西湖是利用北城护城河和一段天然河道形成的,“行其途有八九里,虽全是人工,而奇思幻想,点缀天然,即阆苑瑶池,琼楼玉宇,谅不过此。其妙处在十余家之园亭合而为一,联络至山,气势俱贯”(沈复《浮生六记》)。
明末清初,江南一带涌现出一些著名的造园家,其中有计成、张涟和他的子侄、李渔、石涛等,再晚一些有戈裕良。张涟的长子张然应召到北京参加了瀛台、静明园和畅春园的造园工作,他的后人在北京“兴业百余年未替”,称“山子张”(《清史稿》),大约圆明园、清漪园内的谐趣园等处有他们的作品。李渔也在北京创作了“半亩园”的假山。
张涟和计成是这时期的主要代表。张涟“少学画,为倪云林、黄子久笔法……君治园林有巧思,一石一树,一亭一沼,经君指画,即成奇趣,虽在尘嚣中,如人岩谷。诸公贵人皆延为上客,东南名园大抵多翁所构也”(戴名世《南山集·张翁家传》)。计成早岁学画,宗关仝、荆浩笔意,曾在扬州造影园,“于尺幅之间,变化错从,出人意料,疑鬼疑神,如幻如蜃”(茅元仪《影园记》)。
张涟在叠山艺术上有重要革新。自南北朝以来,私家小园为师法自然常常不得不缩小山水的尺度。唐宋的城内小型私园,山水尺度更小。到了明代,这种做法大约已经使假山完全失去了真实感。张涟批评这类假山“何异市人博土以欺儿童哉”!他主张基本不缩小尺度,但不仿造整座山岭,而仅仅仿山的片断,做到“若似乎处于大山之麓”,使人觉得墙外就是大山(吴梅村《张南垣传》)。
计成的最主要贡献是写了中国唯一的一本造园专著《园冶》(1635年刊印),这是文士园造园艺术的大总结。《园冶》包括兴造论、园说和相地、立基、屋宇、装折、门窗、墙垣、铺地、掇山、选石、借景等篇章。相地篇里又有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等,论述在各种地段造园应有各自特殊的风格。他提出的造园的基本原则中最重要的有两条:一是“虽由人作,宛白天开”;一是“巧于因借,精在体宜”。
明清之际的造园论著除《园冶》之外,文震亨的《长物志》、钱泳的《履园丛话》、李渔的《一家言》、沈复的《浮生六记》,都有论述造园艺术的重要内容。小说《红楼梦》对造园艺术的论述也达到很高水平。这些都说明中国造园艺术到了它的成熟期。
但是,就在它的成熟期,中国造园艺术开始出现了衰败的迹象,以后渐趋严重。因为这时候扬州和江南一带的商业经济发达起来,“叠石造园,多属荐绅颐养之用”(李渔《闲情偶寄》)。这些荐绅当中有盐商之类的暴发户,他们以及一些受市井文化熏染的文士们,早已没有陶渊明、林和靖那样恬淡隐退的志趣,也没有谢灵运、王维、白居易那样对大自然的热爱。他们标榜山水之乐、老庄之道,不过是传统的文化惰性。所以他们已经失去了以前历代士大夫对园林的审美理想。他们侷居在拥挤的城市里,自称“市隐”。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说:“吾侪纵不能栖崖谷追绮园之踪,而混迹市廛,要须门庭雅洁,室庐清靓,亭台具旷土之怀,斋阁有幽人之致。又当种佳木怪箨,陈金石图书,令居之者忘忧,寓之者忘归,游之者忘倦。”其实在一些附庸风雅的人家,连金石图书在内,都充满了富贵气。华贵的陈设、精美的雕梁画栋,也压倒了明代兴起的楹联题咏之类带来的书卷气,园林已经退到很次要的地位。连计成也在《园冶》中说:“凡园圃立基,定厅堂为主。”晚清的江南园林里,往往建筑物过于壅塞,在残剩的狭窄空隙里造园,固然锻炼出一些小中见大的精致的手法,但毕竟巧而难工。园林过分曲折,过分堆砌,有些甚至矫揉造作,天趣尽失。有些园林,其实不过是散处在厅堂之间的院落而已。种几棵花木,立几块湖石,在粉墙衬托下仿写意的文入画小品,虽然也有清逸的佳构,但境界局促,谈不上田园之乐和山水情怀了。真正能做到“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文震亨《长物志》)的,百不及一了。
中国的造园艺术,很早就影响了东亚各国,18世纪即传到欧洲,促成了英国式自然风致园的诞生,并进而影响到整个欧洲的造园艺术。
原载《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 0000
- 0003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