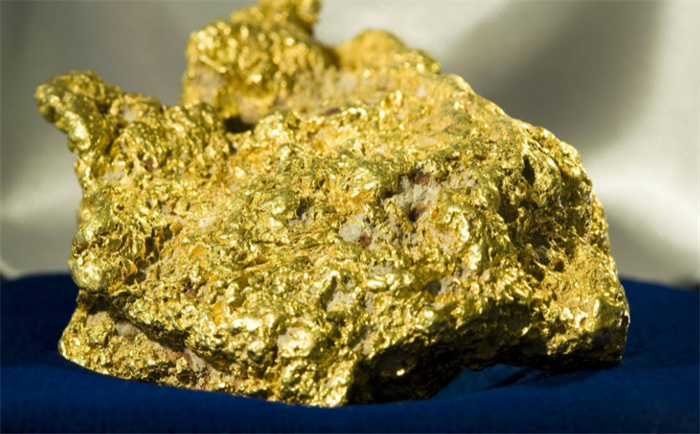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中国人历来认为自己是炎黄裔胄,黄帝是我们的人文始祖。究竟是不是那样,从来都不加以深究。可是进入近代以来,这个观念发生了动摇。当西方列强纷纷侵扰中国时,一些西方学者也忽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生了兴趣。他们无视中国文明的整体特点,摭拾一鳞半爪随意比附,说什么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种是西方起源的,一时间弄得有些中国人也糊里糊涂。不过大多数学者并不相信那些说法,而早先的传说似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把许多学者推上了第一线,其间经历了许多思考和探索。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所指出的那样,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注: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自序,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1944年。)。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起步的。
用考古来探索中国早期文明是从20年代末开始的。前中央研究院史语所考古组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大规模发掘,揭示了一个商代晚期的都城,伴随有一个巨大的帝王陵墓区,大量的出土遗物证实商代晚期已经有了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和成熟的文字体系,已经进入文明时代,但不像是文明的开始。主持安阳发掘的李济就曾说过:“殷商以前仰韶以后黄河流域一定尚有一种青铜文化,等于欧洲青铜文化的早中二期,及中国传统历史的夏及商的前期。这个文化埋藏在什么地方,固然尚待考古家的发现;但对于它的存在,我们根据我们考虑各方面事实的结果,却可以抱十分的信心。”(注:李济《殷墟铜器五种及其相关之问题》,载《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1935年。)李济的预言到50年代就开始逐步验证了。从1952年起对郑州二里岗等处的发掘,不但确定了一个早于殷墟的二里岗文化,而且从1955年开始发现了一座商代前期的宏伟的都城遗址,其中包括有多处宫殿基址和铸铜、制骨、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尽管它是不是成汤所建的亳都还有不同看法,但说它是一个都城级遗址,并且体现了较高的文明水准,则是没有争议的。
商代考古的重大进展以及一系列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特别是龙山文化与商文化内在联系的识别,使许多学者坚信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例如梁思永早在1939年就从十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文化的密切关系, 明确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注: Liang, S.Y.: “The Lungshan Culture: A 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Sixth Pacific ScienceCongress, no.4,PP69—79,1939.中译文载《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英国考古学家丹尼尔在其所著《最初的文明:关于文明的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注:Glyn Daniel, “The First Civilization: TheArchaeology of Their Origins”, Thames and Hudson, 1968. )一书中指出中国是世界最古老的六大文明起源地之一。何柄棣从自然生态环境、农业、养畜业、陶器、青铜器、文字和其他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原黄土地带是中国文明乃至整个东方文明的摇篮(注:Ho, Ping—ti, “TheCradle of the East: An Inquiry into the Indigenous Originsof Techniques and Ideas of Neolithic and Early Historic China,5000—1000 B. C. Chicago & Hong Kong. 1975. )。张光直在其早年的著作中也明确地指出:“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具有特色的本地产物,是中国人民和他们的环境互相影响的结果。”(注:张光直《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继续探索》,”Archaeology”,vol. 30, no. 2 & 3, 1977.引文据《考古学参考资料》第一册20页,1978年。)事实上,从50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中国古代文明是本地起源的,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独自发生的古代文明之一。
但中国古代文明并不是从商代才开始的,因而对于夏代文明的探索一直吸引着许多考古学家。1959年为着寻找夏墟而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是一座规模很大的都城级遗址(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5年第5期。)。那里有大型的宫殿基址和一万平方米以上的铜器作坊遗址,大家都同意它已进入文明时代,而年代比郑州商城早。至于早到什么时候,是夏是商还是前夏后商,长时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83年在二里头遗址附近的尸乡沟,发现一座晚于二里头而与郑州商城基本同时的大型城址(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汉魏故城工作队《偃师商城的初步勘探和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学术界逐渐认识到它的始建可能与商汤灭夏的事件有关,从而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见解便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认同。鉴于二里头已有若干用青铜做的兵器、礼器、乐器、工具、用具和装饰品等,并且有较大的铜器作坊;郑州商城则有更多、更大、制作也更精良的青铜器和规模更大的铜器作坊,至此李济关于夏和商代前期为青铜文化的预测便已得到完全的证实。而夏代不仅有青铜器,还有宫殿、宗庙和一系列典章制度,说它属于文明时代也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不过中国文明的起源似乎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
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在二里头文化之前是中原龙山文化,再以前是仰韶文化,三者在年代上是依次衔接的,中间并没有什么缺环。过去以为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后来在龙山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中都发现了不少小件铜器,甚至在仰韶文化的个别遗址中也发现有小铜器或铜器痕迹,说明那时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而应该属于铜石并用时代(注: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是从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一个时代。这样二里头青铜文化的产生也就不显得那么突然了。同样的道理,以二里头为代表的夏代文明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前面必然有一个酝酿和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从70年代末期以来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使这个问题日益明朗起来了。
在中原地区,从1978年开始发掘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面积达300 万平方米,那里的墓葬非常明显地分为大中小三类(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其比例大约是1∶10∶90。大墓中随葬鼍鼓、大石磬、龙纹盘等大量高档次的物品,说明死者不仅富有,而且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小墓的死者则几乎一无所有。这种级差明显反映其社会已经形成为等级分明的金字塔式的结构。1977年在河南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的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1979~1980年在同省的淮阳平粮台又发现一座龙山文化城址(注: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两处城址虽然都很小, 但前者城内有大片夯土基址和用殉人奠基的情况,后者城内有当时少见的全部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炼铜遗迹和复式地下排水管道等,似乎不是一般的军事城堡,倒有些像是贵族居住的小型统治中心。这些发现都立即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有的认为是夏代遗存,有的认为早于夏代。不管怎样,它们都比二里头文化为早。因而它们的发现表明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努力中,又向前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进入80年代以后,重要的发现一个接着一个。已经发掘了多年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到1983年又有新的突破。在一个大型的仰韶文化晚期聚落中,发现了一座特大型的房屋(注: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甘肃秦安大地湾901号房址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2期。)。有前堂、后室和东西两个厢房,仅前堂的面积就超过130平方米, 前面还有很大的广场。前堂中有直径超过2.5米的特大型火塘和直径达90 厘米的顶梁大柱,地面铺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沙浆,墙壁和房顶都抹灰浆。如此规模宏大、设计严谨、工艺先进的房屋建筑,在以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中从来没有见过,显然不是一般性的公共建筑。有人称之为原始殿堂当不为过。大地湾除这座大型房屋外,还有几座结构和工艺相似的中型房屋和数百座小型房屋,是明显高于一般聚落的一处中心聚落。
在辽宁,从1983年开始发掘的凌原牛河梁则是一处大型的贵族坟山和祭祀中心(注: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8期。), 属于红山文化晚期,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聚落的年代相当。那里有许多巨大的积石冢,每冢有一座主墓,随葬猪龙等精美的玉器,上面还有一些陪葬的小墓。还有一座“女神庙”,出土了许多女性塑像的残块。其中一个人头跟真人的一般大,形象逼真;另有些耳、鼻和手臂等残块竟有真人的三倍大,塑像大小不等表明其地位不同,也许当时在多神中已经产生主神,反映当时的社会已经有等级的差别。郭大顺等认为红山文化晚期社会已进入原始文明阶段(注:孙守道、郭大顺《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文物》1984年第6期。)。苏秉琦则认为当时“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注:苏秉琦《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文物》1986年第8期。)。
稍后不久,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中也露出了文明的曙光。1986 和1987年,在浙江余杭县的良渚遗址群中,先后发掘了反山和瑶山两处遗址。前者是人工筑成的贵族坟山(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后者原来是建造在小山上的祭坛,后来又改做贵族墓地(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在这两处贵族墓地中, 出土了数千件工艺十分精巧的玉器,有的玉器上有近似微雕的王者形象或神徽。1987年底因为扩建公路而在良渚遗址群中间偏西发现一座面积达30万平方米的“台城”,上面有数万平方米的夯土基址,推测应该是宫殿或宗庙一类大型礼制性建筑的地基。所有这些发现使人有理由推测良渚文化时期已经出现某种政治组织形式,论者多认为当时已进入初级文明社会。张忠培则认为当时已经是文明社会,只是在良渚文化分布范围内还没有形成处于一尊统治的局面,而是被众多权贵分割统治的若干具有国家性质的实体(注:张忠培《良渚文化的年代和其所处社会阶段》,《文物》1995年第5期。)。
在长江中游,早在50年代就已发现并且进行过多次发掘的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群,在1990~1991年春进行全面考察时,确定了一个始建于屈家岭文化而一直沿用至石家河文化中期的古城(注:北京大学考古系等《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四川大学博物馆编《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1992年。)。它的面积超过1平方公里, 是已知同时代的许多城址中规模最大的。对于城内外格局和出土遗迹遗物的分析,使调查者提出了“石家河文明”的概念。在此前后在长江中游还发现了若干屈家岭文化的古城,规模都不及石家河古城那么大,看来石家河一带有可能是整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的中心区域或最发达的区域。
这些发现自然会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同时激发考古学家们去寻找更多、更早的城址和高等级的大型聚落遗址。据个人不精确的统计,陆续发现的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史前城址,1991年以前有20多座,1995年即增加到30多座,至1997年更达40多座,现在已知有50多座了,发现速度是十分迅猛的。这些城址分布的地域虽然遍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内蒙古和长江流域的湖北、湖南、四川和浙江等省,但还不能说已经非常普遍。一些很有希望的地方如河北、山西、陕西、安徽等省至今还没有发现。据说江苏已发现良渚文化的城址,也还没有得到确认。这些城址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少数可能略早于前3000年。郑州西山的仰韶文化城址和湖南澧县城头山最早一期属于大溪文化的城址,则已达到或接近于公元前4000年,是现在所知道的年代最早的城址。
过去因为考古工作做得不够充分,许多东西没有被发现出来,自然会低估某些考古学文化的发展水平。例如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理应属于铜石并用时代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石器时代,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在这个时期不但有铜器,还有玉器、漆器、丝绸、象牙雕刻和快轮制作的精美陶器,个别遗址还发现有原始青瓷器(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1期。)。在物质文化迅速发展的同时恰巧出现了一批礼制性建筑和较大的墓葬。从随葬品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墓主往往掌握了军事、宗教等方面的特权和大量财富。事实上这个时期物质文化的最新成就差不多全部为这些新生的权贵所垄断。权贵们不会满足于对本族平民的剥夺,在氏族血缘关系还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这种剥夺自然还会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于是他们把目标转向外部,为着掠夺资源和他人的财富不惜频繁地发动战争。正是在这个时期,专门性武器石钺等的出现与改进,表明战争越来越经常和激烈化了。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战争的人自己也难免受到强敌的掠夺。为了免受战争的惨祸,只好下决心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来构筑防御工事。于是一大批城址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地拔地而起。
在中国大地上出现的第一批土筑或石头砌筑的城址是一种非常醒目的人文景观,它好像是历史长河中一种高耸的里程碑,把野蛮和文明两个阶段清楚地区分开来,中国历史从此开始了新的篇章。但走向文明应该有一个过程,不是一个早上就能够从野蛮跨入文明,更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达到一般意义上的文明的发展水平。但是无论如何,城址的出现应该视为走向文明的一种最显著的标志。
由于考古的发现总是要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会根据考古发现的进展情况而有所调整和深化。在刚刚发现史前城址时,人们虽然会觉得很重要,但在估计其意义时难免有失准确,所以不少学者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当发现越来越多,时间也越提越早的时候,人们就有可能通盘考虑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文明社会的,其中史前城址的出现和演变自然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早年在讨论中国文明起源时,有的学者还提出首先要明白什么是文明,要弄清楚文明的概念,才可以明确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大多数学者不赞成那种从概念出发的思维方式,而主张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分析。至于文明标志,不同的学者多有不同的说法,每个地区也可能有所不同,不能一概而论(注:童恩正《有关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与安志敏先生商榷》,《考古》1989年第1期。)。夏鼐先生在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时采取了一种非常平实的叙述方法,先从小屯殷墟谈起,接着谈郑州商城,然后谈二里头都城遗址(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这既反映了中国考古学探索古代文明的历程,又反映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几个主要发展阶段。夏先生虽然明确提出都市、文字和青铜器可以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但是他的主要立论根据却是上述几个都城。因为都城是国家物化形式的集中表现,是各种文明因素的总汇。
在夏先生发表那篇著名文章的时候,中国还只发现了几座不大的史前城址。所以他认为二里头文化,至少是它的晚期够得上称为文明。“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于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不过在同一篇文章中他又谈到:“有人以为‘文明’这一名称,也可以用低标准来衡量,把文明的起源放在新石器时代中。不管怎样,文明是由‘野蛮’的新石器时代的人创造出来的。”(注: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96页。)这个意见曾经被广泛接受。在1989年《考古》编辑部召开的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学术座谈会上,则把文明要素的起源与文明社会的产生相区别,而究竟是什么时候进入文明社会,在会上就有不同的意见(注:白云翔等《中国文明起源座谈纪要》,《考古》1989年第12期。)。
在中国文明起源研究中,苏秉琦先生独树一帜。他高屋建瓴,在区系类型学说的基础上,先后提出了被归纳为多元论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提出了文明起源的三种形式:裂变、碰撞与融合,以及文明起源的过程:古文化—古城—古国。与此相关还提出了国家发展的三部曲与三模式。他在最后完成的一部总结性著作《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这些观点(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务印书馆,1997年。)。苏先生的研究充满辩证法。他注意到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相通的一面;中国又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有它自己的许多特点。我们要研究这些特点,才能认清中国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人对世界文明史的贡献。他在研究中国文明发展史时,总是不忘记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全局出发, 同时又充分注意地方的特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和民族、文化之复杂,使它的文明起源不可能是单线条的和单个模式的。所以他在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和国家发展三部曲:古国—方国—帝国的时候,认为这一过程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曾经以不同的方式一再重现过。所以中国文明起源与发展应该有不同的模式,有原生型,还有次生型和续生型,最后才形成为现代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他的这一思想在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研究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苏先生关于古文化—古城—古国的理论最先是从辽西地区的工作提出来的,当时还不知道有像郑州西山和澧县城头山那样早的遗址。如果我们根据苏先生的思路,将现在所知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城址和中心级聚落的资料排比一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的庙底沟期、大溪文化的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的早期等,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前3500年左右。除城头山外,据说还有大汶口文化早期的山东阳谷王家庄城(注:张学海《东土古国探索》,《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但还没有见到详细资料。这是城址初现的时期,数量少、规模小,结构上还保留环濠聚落的一些特点。其中城头山城内有较大的制陶作坊和椭圆形祭坛等遗迹,说明那里是一个陶业中心和宗教中心;城内发现的墓葬表明其居民已经有初步的贫富分化和社会地位的分化(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在大汶口文化早期,至少在它的中心大汶口遗址已出现贵族墓和明显的贫富分化与社会地位分化现象(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汶口续集》,科学出版社,1997年。)。仰韶文化庙底沟期则出现了像陕西华阴西关堡和华县泉护村等面积达数十万以至一百多万平方米的中心聚落。西关堡的白衣彩陶豆和泉护村的黑陶鹰鼎,是别的遗址所不见的精美重器。与此年代差不多的还有安徽含山凌家滩的祭坛与贵族坟山,那里出土了玉人、玉龟和刻有方位的玉牌等众多精美玉器。凡此都说明这个时期在一些较发达的文化中心,已经率先迈开了走向文明的坚定步伐。
第二阶段相当于仰韶文化后期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红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大溪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早中期等,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500~前2600年左右,各地的年代容有一些差别。这是史前城址迅猛发展的时期,公元前3000年以后发展更为迅速。城址的数量大增,有的似有成组和分等级的现象,有的规模也十分可观。这个时期社会分化的现象在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和红山文化晚期看得最为清楚,这几个文化的资料往往作为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证据,对于它们的个案研究也进行得比较深入。这时社会的分层已十分明显,甚至达到了比较尖锐的程度。尽管文化之间的联系、接触与碰撞大为增加,而各自仍然保持着相当独特的风格,走着不同的发展道路。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它们都应该属于原生型的模式。目前对这个阶段的社会性质还有各种不同的认识,有的认为已经进入文明社会,有的则认为还是史前社会。不管怎样,这个时期已经比第一阶段进了一大步,文明化程度更高了,文明社会的色彩更浓了,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第三阶段即通常所说的龙山时代,年代约为公元前2600~前2000年。这时长江流域和燕辽地区似乎出现了文化发展的低谷,而黄河流域则更加迅速地发展起来。这一带全局性的转变对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以至吸引不少学者去探索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只是至今还没有得出比较满意的结论。这个时期的城址和特大型聚落遗址也大多见于黄河流域,诸如山西的陶寺,河南的王城岗、平粮台和禹县瓦店等处,都曾被指认为某某都城,虽然不一定准确,也不失为一种探索的途径。这个时期的铜器已经比较普遍,制陶业已经从手制为主转变为轮制为主,建筑上大量使用白灰,有些建筑用人和牲畜奠基,人祭现象也时有发现,墓葬反映的阶级和等级分化更为尖锐。所有证据表明这个时期文明化的程度又提高了一步,也许确实可以看成是文明社会了。由于龙山时代已逼近二里头文化,而二里头文化又已被公认为夏文化(注:关于二里头文化应属于夏文化,邹衡先生曾经进行过详细的论证,见所著《试论夏文化》(载《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文物出版社,1980年)及其后发表的许多文章。过去一些学者以为二里头是成汤所居之亳而反对此说。自从1983年于二里头遗址附近发现尸乡沟商城以来,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以后,大家已一致同意尸乡沟商城小城的始建应作为成汤灭夏的一个标志,从而同意二里头一至四期都是夏文化。),所以龙山时代黄河流域的突出发展,就直接为夏商周文明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碳十四所测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左右,总积年仅300年, 比古本《竹书纪年》所说“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太平御览》卷八二皇王部引)差了许多,起始年代也比一般估计的晚了许多。而中原龙山文化已有许多测年的数据,似不可能比公元前2000年更晚。也许二里头一期的数据太少,又略有误差;也许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之间还有一个小小的缺环,这是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着重解决的问题。不论怎样,龙山时代应该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唐尧虞舜时代。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尧舜时代已经是初具规模的朝廷而不是什么部落联盟。如果说有一定的联盟性质,也应该是古国的联盟,是有政府有元首的联盟。《墨子》就经常把虞夏商周连称,孔子也说“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孟子·万章》引述)。所以说龙山时代是文明初期的古国时代也是与古文献相合的。
在古国时代,各国的关系可能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其中尧舜的国家可能是势力较强而为禹及其后人所继承的。在夏商周时期同样还有许多中小国家,也是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的。商周都经历过从部落到国家的的过程,建立国家以后又分别为夏商所兼并。虽然如此,它们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等到逐渐强大起来以后,又反过来灭掉夏、商。这种所谓灭也有点像改朝换代,是地方政权取代中央政权,所以文化上多有继承,只不过有所损益而已。这是在中原及其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事情。至于其他地方,也曾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也建立了许多中小国家,也有自己的文明。近年发现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包括大洋洲大墓在内的吴城文化,以及湖南宁乡黄材青铜器群所透露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些国家也发生过联合、对抗、征服和兼并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夏商周势力发展得那么大。其中有些势力也曾与夏商周发生过关系,从而为以后建立秦汉那样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讲文明起源不能只讲到夏代以前,至少要包括夏商周,甚至还要包括周秦以后,因为在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在走着从部落到国家的道路,其中有些甚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以至最后融入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中。由于年代较近,相关的文献记载较多,对它们文明化的过程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对于以前发生的文明化过程还可以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所以不可忽视。当然研究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夏代以前或周秦以前。
回顾过去,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虽然有70多年的历史,而进展最快、成绩最大,从而引发观念的转变,真正切入到问题的实质,则不过是最近20多年的事。现在我们认识到:
一、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在整个世界的东方,即从印度的马尔瓦高原向北经过帕米尔高原直到乌拉尔山脉一线以东的广大地区,中国文明是最先起源,发展水平最高,并且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她强大的生命力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二、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最先发生社会分层和分化,从而迈开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当不晚于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3500~前2600年是普遍文明化的过程;公元前2600~前2000年当已初步进入文明社会;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达的时代。秦汉帝国建立以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而在边疆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经历着逐步文明化的过程。
三、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在一个狭小的地方,也不是在边远地区,而是首先发生在地理位置适中,环境条件也最优越的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各地情况不同,文明化的过程也有所不同。它们相互作用,此消彼长,逐渐从多元一体走向以中原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体的多元一统格局,再把周围地区也带动起来。这一格局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特点,也是她之所以具有无穷活力和强大凝聚力,以至成为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而得到连续发展的伟大文明的重要原因。
中国古代文明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现在考古学揭示的主要是一个框架结构,具体内容的研究还很不够。例如对古城的研究看起来很热闹,实际内容不多。现在大多数古城仅仅找到一个城圈,城内有什么建筑设施,功能如何?城内和城外的关系如何?是否城都有城墙围护?如果不一定是,又如何确定城的性质?凡此都要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仅此一例就可以知道要切实弄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短时期可以奏效的,需要有战略的眼光进行长期规划,把重点发掘和普遍勘察结合起来,把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结合起来,庶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我最近在一篇短文(注: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一期,1999年5月。)中指出, 研究古代文明及其起源,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既是课题本身的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考古学研究需要与人类学、民族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合作已经谈论得很多了,这里不谈,不等于说不重要。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的重要。因为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往往涉及到十分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诸如城郭制度、宫庙制度、陵寝制度、棺椁制度、车马制度、礼器制度乃至各种器物的命名和用途等,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讲文明起源不能不讲这些制度的起源,如果不结合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这些情况就难以彻底弄清楚。再如某些考古学文化族属的考订,某些上古地名特别是一些重要都城的认定等等,无不需要结合古文献和古文字的研究。有人认为强调与文献相结合会丧失考古学的特点,不足为法,我却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和优点,必须发扬。如果把握得好,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来源:《文物》1999年10期
- 0000
- 0000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