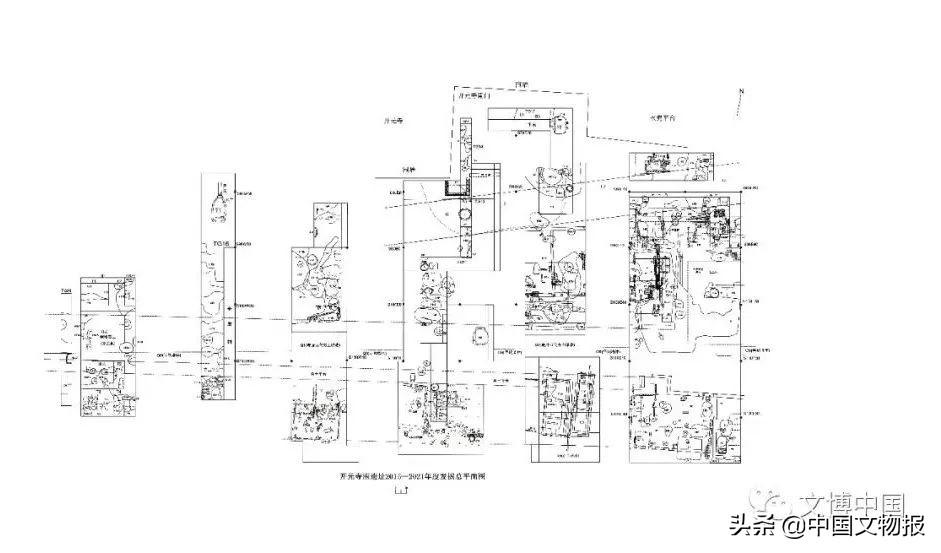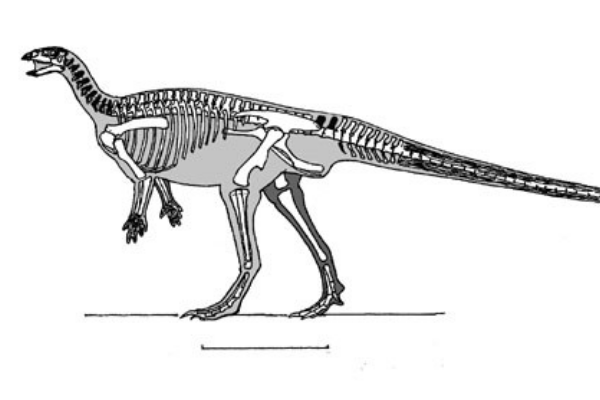潘晟:礼仪、习俗与气候变迁和环境演变关系的思考
一、目前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存在的区域局限
自从竺可桢开创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研究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科学方法以来,无论是气候的冷暖序列重建,还是干湿序列重建,都得到了十分深入的讨论,在文献的认识与处理方面、计量方法的发展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1]该方法也对后来兴起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意义,成为环境演变研究本土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基础。但是我们也感觉到,目前利用历史文献资料系统重建历史时期气候变迁和环境演变的研究成果,[2]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区域局限,即空间上主要着力于历史时期中央王朝核心区的讨论,对于历代王朝边疆地区的研究,在纯自然科学的方法,如孢粉、沉积、冰川、树木年轮以外,主要利用文献资料的成果还很少。[3]
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有两点比较明确,一是受制于资料自身的局限,二是认识方法的局限,而这两者之间又有着一定的相互关联。
关于历史文献的局限性已有比较多的讨论,就一般的层面而言,大体可以概括为两个大的方面,即文献及其记载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与时间分布不平衡。(1)文献及其记载的区域不平衡,这主要是由历代王朝疆域范围的不同,以及王朝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的区域差异所致。因此随着王朝疆域的变迁,尤其是政治核心区域的迁移,以及区域经济中心与文化中心的兴替,相关记载的区域不平衡也随之相应而生,相应而迁。(2)文献及其记载的时间分布不平衡。由于王朝兴替及其内部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区域发展,带有显著的时间性,乃至很大程度上受到王朝周期的影响,这也直接影响了文献数量与质量的时间分布不平衡。影响文献分布时间不平衡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文献生产与传播方式的发展,包括载体、书写方式、保存方式等等。书写作为文明的核心,它的载体、传播方式等都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因此它在总体上是时代离我们愈近,数量越丰富、质量越高,时代离我们愈远,数量越少、质量越低。
文献及其记载的区域分布不平衡与时间分布不平衡,使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建立的气候与环境数据序列呈现出同样的特征,这样拥有能够达到符合计量分析要求的数据序列的区域和时段自然出现显著的集聚现象,相关研究也就集中于这些文献数量和质量丰富的历史区域和时段。而其他区域与时段遂成为“历史空白”。
这种“历史空白”的形成,我们除了要看到资料的客观局限以外,还应该看到其中也存在着很大的认识局限。这种认识的局限首先来自研究过程中预先设置的假设前提,即一定要找到合适的、符合统计要求的长时段数据序列的定量研究思维。精确的定量研究自然是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研究的目标,也是学科发展的一个内在驱动力。但是一旦成为固定的思维模式,或者说成为一般研究的范式它一方面很可能使研究行为自觉或不自觉地屏蔽了那些定性资料,尤其是零星的定性资料,一方面还可能使研究者执着于定量工作而放弃定性工作,尤其是放弃资料本身只能支持定性研究的项目。
在实际的研究工作中,它的另一个表现则是尽量完善自然科学方法,尤其是测年技术,以提高大分辨率即小时间尺度的研究。但是即使如此,大多数的研究其时间尺度往往仍然以千百年计,而空间尺度则以大地理单元或较大的区域为对象,其讨论也以自然规律的基本趋势为探索的核心,小时空尺度的讨论仍然难以深入;对与之相关的社会问题虽亦有论述,但也主要限于轮廓的勾勒,而实际上也难以进行深入的解释。客观地讲,无论是文献资料还是自然的物理数据,都不可能很好地覆盖所有的时空,总会留下空白。因为至少目前的测年技术都还存在着相当的误差,这种误差值在大时空尺度上是系统研究所允许的,但是对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时期而言则显然存在着不足。
在刻意追求定量研究的模式下,一个显著的表现就是不仅仅气候变迁属于不见人影的过程,即使强调人地关系研究的环境演变研究,乃至环境史研究也有着很浓的“不见人影”的历史研究的意味。
认识局限的另一个因素虽然没有定量模式的预置那么明显,但是在气候变迁和环境演变的研究中也值得我们反思,即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其中尤其是气候变迁研究强调其演化的全球性背景。因为自然界的演变是全球性的过程,因此特定地区详细数据序列的研究成果,能够用来在比较的基础上反演其他地区的气候变迁乃至环境演变过程。我们并不否认这一思路,但是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当我们在强调它的全球性演化过程的时候,也还需要考虑到这种全球演化过程中的区域性差异,有时候这种区域差异还非常的重要,尤其是环境演变过程的区域差异十分显著,不仅存在大地理区域之间的差异,还存在中等尺度、甚至小尺度地理区域之间的演变差异。比如喜马拉雅隆起对于由此而形成的不同地理单元,其各自的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显然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演变过程,则有时候并不太大的地理阻隔都足以产生明显的区域差异,形成不同的族群与不同的社会或文明形态。如峨眉岭-绛山一线从新石器时代至商代晚期在晋南、晋西南所表现的文化地理界线作用,以及对此后文化地理分区的影响,[4]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而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会与文明形态不仅存在着生产方式与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还往往有着不同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行为,由此引起的人地关系发展模式也就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区域性环境演化的差异。
因此,我们有必要在不遗余力地推进定量研究方法的同时,仍然需要进行大量必要的定性研究,以拓展我们的思维方式,扩大资料的搜集范围与利用方法,展开深入的定性研究工作,尤其是以往“历史空白”区域与时段的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定性研究工作,使之与各种自然科学方法及相应的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纳入到“集成研究”[5]或类似的方法中以获得更深入或更多的认识。
二、礼仪、习俗与气候变迁、环境演变关系的初步思考
讨论以往“历史空白”区域气候变迁以及环境演变问题,我们在跳出利用完整的成序列的文献资料,进行严格的定量研究的思维束缚之后,目光自然会转向以往较少关注的资料,或者说可以作为资料的对象,并借鉴其他学科的分析方法与观察视角。礼仪与习俗就是这样一种值得我们在气候变迁,以及环境演变研究中加以利用的对象。
礼仪、习俗的形成往往与气候、环境有相当的关联,尤其是习俗或在习俗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礼仪表现更为显著。在我们耳熟能详的节庆习俗中,如春节、端午、中秋、重阳其实都与季节、气候的变化有密切的关联性,因为一方面这些习俗与季节有关,一方面它们的形成过程与农事有关。比如端午,我们熟悉的是吃粽子、赛龙舟、喝雄黄酒、烧菖蒲或艾叶、系五色线,但是若稍稍深入,就会发现这一系列的活动都与这一时期的季节变换和农事劳作有关。农历五月初五前后,一般是长江流域地区正式进入农忙,是水稻移载的重要时节,同时也是天气开始转入蚊虫繁衍的湿热夏天的时节。节俗在热闹的背后都与这一气候的变化有关,如赛龙舟除了有祈求风调雨顺的内涵外,用今天的话来说还带有农忙前动员的意味(实际上不少比较古老的习俗都有这个内涵);吃粽子则与农忙有着十分重要的关联,这是因为粽子一方面耐储、一方面耐饥,是适合重体力劳动的食物,在稻麦两熟轮作制传到这一地区之后该作用就更为显著;喝雄黄酒则与古人认为它具有祛湿避蛇虫的功效有关;烧艾叶或菖蒲的实际功效则在于灭蚊虫,因为此时蚊虫刚刚开始繁殖,用艾叶或菖蒲的烟熏燎很容易杀灭,由于此时杀灭的都是过冬的老蚊子,是繁殖新蚊子的母体,因此其效果十分显著。
虽然端午的日期在农历上每年是固定的,都是五月初五,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作为我们考察礼俗与气候及环境变化的关系。端午属于较重要的节日,各地对于该节日期间的日常生活记载比较丰富,可以从中了解到不少当时的农事活动安排,以及天气湿热等方面的描述;而当我们把农历五月初五换算成公元纪年之后,各种相关记载的时间差异与地域差异也就能够得到比较清晰的展现。由于农事的安排本身就是根据气候变化做出的,故据此整理的记载也就反应了气候变化的某些特征,对于我们认识某一地区不同历史时期的气候变化以及环境演化可以具有较好的指示作用。[6]
为了更好地说明礼仪、习俗与边疆地区气候变迁、环境演变,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下文以讨论较多的辽代瑟瑟仪与射柳习俗为例略作说明。[7]
关于辽代瑟瑟仪,据史料记载,包括择日、祭先帝、射柳、植柳、巫祝、祭东方、再射柳、贞验、厌胜等,是长达数天的仪式过程[8]。它并不是定期举行的周期性活动,只有当统治区域内发生干旱时才举行。仪式内容多样,其核心部分为射柳和祭祀。其中射柳活动并不十分严肃,而是充满了活泼与欢庆的游戏色彩,是仪式中不同身份的参与者狂欢的活动。祭祀,才是庄重而带有祈雨功能的核心仪式。它是在北方民族起源较早的射柳习俗的基础上产生的国家仪式。
《辽史》认为瑟瑟仪最早由遥辇苏可汉制定。[9]而《辽史》中苏可汗的世次不可考,关于其时代有不同认识,[10]我们依据《辽史》和《旧唐书》的相关记载,[11]认为其时代大致在天宝四年(745)迪辇俎里降唐,至天复元年(901)痕德堇可汗立,以太祖为本部夷离堇,此150余年间;颇疑《辽史》所载苏可汗,即为《旧唐书》贞元十一年(795)率25人入朝的大首领热苏。辽太祖七年(913)十一月定吉凶仪,瑟瑟仪成为仅次于祭山仪的辽代吉仪。[12]这实际上是耶律阿保机在建立辽政权的过程中,把已经存在的习俗或仪式规范化、体系化,将之正式确立为王朝政治体系的一个有机部分。
由于瑟瑟仪并非定期举行,只在发生干旱的情况下才择日而行,因此它的产生、确立是中唐以来契丹族活动范围内气候逐渐趋向干旱的结果。这与郑景云等人在讨论2000年以来中国东部地区气候干湿分异过程时指出的,在8世纪中叶至9世纪末气候相对寒冷,华北地区偏干的结论大致相近。[13]
考虑到契丹人活动的地域特点,并结合皇家礼仪的特征,它可能主要在以辽上京临潢府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区内进行。不仅因为该区域原本就是契丹人活动的核心地域,他们对当地的干湿变化有最直接的感受,还在于该区域在土地利用方式上随着契丹的发展,成为半农半牧型地带,[14]它很大程度上也是辽的基本经济区,而其农牧交错的生产方式,对于气候的干湿变化十分敏感。因此推测契丹人建立辽朝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瑟瑟仪,所反映的主要是辽代半农半牧型地带———即以西拉木伦河、老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辽上京道南部、中京道全部、东京道西部,[15]也即自然地理上的燕北地区[16]———的气候干湿变化过程。因此可以作如下假设:当913年太祖耶律阿保机将之确立为正式的国家仪式之后,在辽的核心活动区域没有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它的举行成为该地区气候干湿变化的标志事件;若频繁举行则标志着区域内气候偏干,若较长时间不举行则表明干湿情况有所改善,这样的气候过程又可能影响仪式习俗在日常生活中的演化。
在利用瑟瑟仪考察该时期北方气候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虽然直接记载并不多,且时间分布很不均匀,但却贯穿始终。由此说明它作为正式的国家仪式,得到了较为稳定地推行。至于文献所载射柳活动,并不是祈雨的充分条件,只有当祭祀或祈祷与射柳齐备的时候才构成完整的瑟瑟仪。因此,单纯的射柳记载代表的是帝王游幸及民众的田猎习俗,表明气候的干湿情况相对平稳。[17]
金灭辽以后,袭用的射柳仪式不是祈雨活动。据《金史》卷35《礼志八》云,金承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笔者按:《辽史·礼志》未见此等记载),在重五日拜天礼之后,即举行射柳活动。[18]《金史》所载射柳活动其形式与辽已有相当不同,其仪式的起源也由祈雨变成了拜天,日期也固定为重五日,即端午,显然其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人认为主要是女真人生活的环境较少受到干旱威胁所致。[19]这并不全面,因为《辽史·礼志》并无“金志”所说的仪制;另据《金史》卷2《太祖纪》收国元年(1115)五月甲戌,“故事,五月五日、七月十五日、九月九日拜天射柳,岁以为常。”[20]而此时辽尚未亡,距《辽史》最后一次记载射柳祈雨活动的乾统八年(1108)不过相差数年,辽之礼俗不至变化如此之快,金之先祖对辽代礼仪也不至如此隔阂。故而金人拜天射柳很可能是金人在自身原有习俗基础上借鉴辽代仪制所做的规范化、仪式化的结果,是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立国过程中礼制建设的重要一步。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依据对《辽史》瑟瑟仪及射柳等问题的分析与计量,得到的可能性结论是,辽代燕北地区在公元1000年前较为干旱温暖,尤其是960′s-1000之间。1000年以后旱涝间发,且趋向寒冷,至1080′s达到高潮,且雨涝事件显著增多。而燕山以南地区在1000年以前却相对湿润,之后则干旱事件逐渐增多,旱涝间发,旱多于涝。[21]这与时贤的相关结论略有不同,[22]或可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
通过上述对辽代瑟瑟仪的简单梳理,我们感到在利用礼仪、习俗等资料考察边疆地区或以往的“历史空白”区域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时,至少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其一,要理清礼仪、习俗起源、形成、演化与气候、环境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包括礼仪、习俗中体现气候或环境变迁的指示性内容,即礼仪、习俗中哪些活动确实与气候、环境有关,关联的强弱程度等;它所代表的区域范围,以及区域范围的变化;它的阶段性特征等。
其二,要谨慎理解礼仪、习俗与其所处权力结构的关系。如涉及王朝层面时,它作为权力表现的一个方面,虽然有些礼仪的起源、形成与该地区的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有关;而在礼仪的更迭与演变方面,则很大程度上与王朝鼎革或该地区权力结构的演变有关,气候变迁或自然环境的因素退居次要,因为礼制作为权力的一个重要象征,对它的修订同样表达了、也必然要表达权力的变更。相对而言礼制下面的习俗则往往有更强的延续性。
其三,要充分考虑奉行该礼仪、习俗的族群特征,这一点在环境演变方面的表现更为直接而突出,因为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社会与文明形态不仅存在着生产方式与土地利用方式的不同,还往往有着不同的环境感知和环境行为,由此引起的人地关系发展模式也就存在差异,进而导致区域性环境演化的差异。
其四,虽然礼仪、习俗的记载往往只能做定性的讨论,资料自身的不足导致只能得到较为粗线条的阶段性的认识,但我们应该借助定量分析的方法来完善资料的整理与分析,以增强定性讨论的基础。
注释:
[1] 最新的综述参见杨煜达等《近三十年来中国历史气候研究方法的进展———以文献资料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2] 参见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陈新立《中国环境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史学理论研究》2008年第2期。
[3] 主要有于希贤《苍山雪与历史气候冷期变迁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166页;杨煜达《清代昆明地区(1721-1900年)冬季平均气温序列的重建与初步分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7年第1期等。
[4] 马保春:《晋国历史地理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版,第51-55页。
[5] 葛全胜等:《中国历史地理学与集成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6] 侯甬坚老师向笔者指出,辽代四时捺钵与气候变迁关系密切,诚是,对本文写作启发良多,谨致谢忱。
[7] 相关研究有徐秉锟《横簇箭与射柳仪》,《社会科学辑刊》1980年第4期;王承礼《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郭康松《射柳源流考》,《湖北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张碧波《北方民族的树神崇拜———从契丹、女真族的“拜天射柳”说开去》,《辽金史论集》第7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等。
[8] 《辽史》卷49《礼志一》。
[9] 《辽史》卷116《国语解》。
[10] [日]岛田正郎著、何天明译《大契丹国———辽代社会史研究》,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74页;王承礼:《契丹的瑟瑟仪和射柳》,《民族研究》1988年第3期。
[11] 《辽史》卷63《世系表》、《太祖纪上》;《旧唐书》卷199下《契丹传》。
[12] 《辽史》卷49《礼志一》。
[13] 郑景云等:《过去2000 a中国东部干湿分异的百年际变化》,《自然科学进展》2001年第1期。
[14]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139页。
[15] 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140、139页。
[16] 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55-166页。
[17] 因此在讨论辽代干湿变化的时候,将射柳都看作旱灾,或者全部排除在外都有失偏颇。
[18] 《金史》卷35《礼志八·拜天》。
[19] 常晓宇、李秀莲:《阿骨打拜天射柳》,《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13期。
[20] 《金史》卷2《太祖纪》。
[21] 详细的论证以《辽代瑟瑟仪与北方农牧交错带东段中古时期的气候变迁》为题在“广西历史地理与华南边疆开发”(2010年中国历史地理年会,桂林)会议上小组讨论过,尚未正式发表。
[22] 张丕远等:《中国近2000年来气候演变的阶段性》,《中国科学(B编)》1994年第9期;葛全胜等:《过去2000年中国东部冬半年温度变化》,《第四纪研究》2002年第2期等。
来源:《江汉论坛》2011年8期
- 0000
- 0004
- 0001
- 0000
- 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