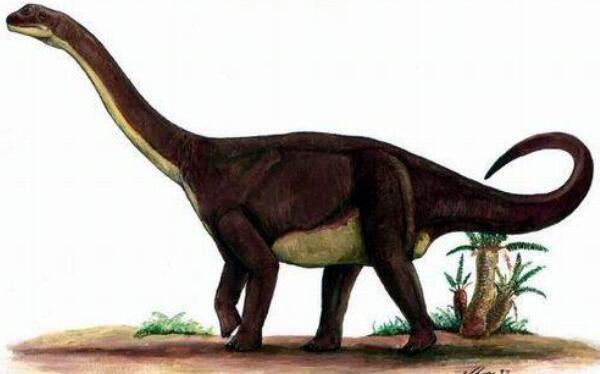陈淳:探究早期文明社会的世界观
一、前言
2012年5月在张家港市召开的《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了要重视文明探源中精神文明形成的问题。这是一个长期被冷落但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而且它在文明探源中与生态环境、技术经济和政治制度等课题同样重要。如果能够能在这个课题上取得成果,那么对于我们加深对早期文明起源、动力、性质和运转的了解有重要的帮助和启发。但是,古代人类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并不保留在考古遗存中,因此难以企及。在文化历史考古学发展的鼎盛时期,美国考古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克斯声称,考古研究所能企及的大体限于人类与其他动物共有的那些方面,而对人类最独特的那些方面则无能为力或很难加以研究。他提出了著名的研究难度级别的霍克斯梯度,即从物质遗存来研究生存方式和经济形态比较容易,重建社会结构比较困难,而最困难的是重建意识形态。这一时期,虽然器物研究中无法避免古代器物所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但是由于缺乏适当的方法论,只能停留在推测的层次如将它们定为礼器或仪式用品,很少探究其与文化变迁的关系和社会功能。而像柴尔德那样认识到宗教在古代文明中重要性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他说,古人创造的迷信和虚幻世界对于他们安于现状和承受生活是必需的,这是支撑社会结构得以矗立的不可或缺的脚手架。城市革命最终被巫术和宗教所利用,登上宝座和拥有大权的是巫术而非科学。于是革命所开拓的新科学,常常被奉承迷信所羁绊。
到了过程考古学阶段,对人类物质遗存中所表现的意识形态有了很大的重视。比如,路易斯·宾福德就指出,器物是人类社会系统各组成部分的反映,它的技术方面反映了人们如何应付生态环境,其社会方面反映了人们如何用它来协调社会关系,而其思想方面则反映人们的意识形态。宾福德以刀为例,表明其切割功能可满足生活需要,它的金质刀柄显示主人的高贵地位,而其刻在刀上的符号可能是祈求神灵的护佑。虽然过程考古学重视意识形态,但是却认为意识形态是人类对环境适应的一种副现象,在重视程度上不如生存方式、聚落形态和环境适应研究。宾福德对考古学研究古代意识形态的能力也心存疑虑,认为考古学家所受的训练不足以从事古心理学研究。
后过程考古学开始将意识形态研究放到了这门学科的显著地位,并体现在这个趋势中的认知领域和象征课题上。后过程考古学家给予古代的思想、价值观、宗教信仰研究以空前的关注,有人指出,了解物质文化在祭祀和显示威望中的作用,是重建社会变迁不可或缺的第一步。由于“意识形态”是如此不可捉摸,而且无法从考古学记录来论证,以至于难以对它进行科学研究,使认知考古学的发展表现为一种无序、不系统和定义不清的特点。肯特·弗兰纳利和乔伊斯·马库斯认为,认知考古学是更加全面了解古代社会的一种途径。对古代思想的研究,不能凭空猜想,而应该像过程考古学实的证方法一样做细致、艰巨和严谨的工作。而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这就是需要有可靠的民族志、历史学、民族史和考古证据的支持和佐证,否则这种研究与科幻小说无异。
在考古学中,我们所见的大部分重要文明遗迹几乎都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和信仰的产物。从古埃及和玛雅文明的金字塔到英国的巨石阵,从殷墟的青铜器和甲骨到良渚文化的玉器,应该都是当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的产物。有学者指出,在世界早期文明社会中,大部分政治思想从本质上都是宗教思想。这是因为早期文明的统治者都试图将他们与一种永恒的神授秩序联系起来,以便使天赋的神力和神秘性能够支持和增强他们在世间的权威。上层阶级就是用基于宗教的意识形态来证明并确立其行为的合法性。
本文试图探讨早期文明社会里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与特点。虽然这种探索可能无法企及说明诸如良渚文化的玉器在祭祀中发挥的具体功能或三星堆文化信仰何种神灵的问题,但是这种史前世界观的探索基于两点人类学理由:(1)所有人类具有基本相似的心理过程和能力,人类社会不会产生无穷变异,而会显示随时间变化的跨文化规律;(2)人类文化具有可识别的形态,即非物质的世界观会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在诸如聚落形态、艺术、建筑和丧葬实践方面。这一尝试希望在宗教人类学理论、跨文化比较的成果和早期文字解读的帮助下,从更深的层次了解宗教信仰与文明进程的关系。
二、信仰的起源
宗教信仰是人类特有的文化现象。宗教使人类行为超越自然与物理世界和生物界的界限,超越为获取食物与繁殖的需求而有了文化的意义。但是,宗教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特征,它是现代人类的特点,其起源与人类体质与智力的进化相关。美国考古学家史蒂文·米申指出,早期人类如能人、直立人和尼人的智慧由四个互不相通的板块组成。一是技术智慧,表现在石器制作的对称和式样的复杂性上。二是自然智慧,是有关动植物、水源和洞穴等景观地理的知识。三是社会智慧,一般反映在群体大小和营地的规模上。四是社会语言,一般从脑容量、神经结构和声道来了解。米申认为,早期人类的大脑好比瑞士军刀,拥有应对特定行为方面的多种智慧,但彼此间缺乏互动。因此,虽然古人类在许多方面和我们相似,但是他们缺少现代人智慧的关键要素:认知的流动性。古人类四种孤立的智慧到现代智人阶段合为一体,形成了所谓的整体智慧,于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人类文化所特有的艺术和宗教现象。然而,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艺术如西欧的洞穴壁画,与今天非实用性物品和创作的艺术概念应有根本的区别。当时的狩猎采集者不会有现代人的闲暇和雅致来创作与生计无关的艺术。考古证据表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并非是在舒适的条件下,而是人们面临极为严酷的生存压力下创作的。艺术体现了古人类三种认知过程的结合,即脑子里的图像概念、交流意图和赋予的含意,标志现代智人整体智慧的形成,而这种视觉象征性的出现为宗教意识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壁画通常被解释为狩猎巫术,在这些地点举行某种仪式是保证狩猎成功和食物供应所必须,其威力可能比拥有一支锋利的长矛更强大。
美国考古学家迪克逊指出,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物质形态表明原始宗教实践的存在:(1)物质现象反映宗教活动,如丧葬实践、壁画和可携艺术品;(2)中晚段更多墓葬的出现,包括妇女和儿童。随葬品的增加和葬俗的多样化;(3)在整个旧石器时代晚期,欧洲的壁画和可携艺术品风格有较大的一致性;(4)欧洲西南部,人类的居址与壁画所在地存在明显的空间两分,从洞穴壁画所在地缺乏生活垃圾表明,这些并非人类的日常居所;(5)壁画艺术各异,其质量和精致程度也有差异;(6)许多壁画位于不易到达的洞穴内部,可能易于创造某种类似梦境的幻觉。由于宗教活动是有组织的活动,与社会文化系统密切相关。因此,墓葬和仪式形式的复杂化反映了日增的社会复杂化。
美国人类学家威廉·特拉梅尔指出,宗教的产生是人类为了应对可怕且不可控制的状况。人类与其他生命都难免一死,加上期望与实际的差距、有限的寿命、疾病、恐惧、沮丧和残忍等不可操控和无法改变的事实令人感到畏惧。在这种意义上,宗教是人类与这些状况最终结局进行斗争的感情和智力手段。这种斗争通过对神灵的膜拜结合起来。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帕斯卡尔·布瓦耶指出,宗教最普遍的特征就是相信无形的生命。他列举了宗教意识形态的三项常见特征:(1)认为一个人生命的无形部分(如灵魂)在死后仍然存在;(2)认为社会中的某些人拥有与神灵沟通的特殊能力;(3)认为用恰当的方式举行某种仪式能够改变自然界。布瓦耶还指出,宗教意识形态的无形生命违反通常的生物学直觉知识,如尽管认为无形生命可能有某种样子,但是它们并不经历生死、繁衍和兴衰的轮回。同样,它还违反物理学的直觉知识,如无形生命(精灵)能够穿越时空和坚硬物体,来去无影。但是,它也有符合直觉知识的方面,如它们会有像人一样的信念和欲望。布瓦耶认为,正是这种违反和符合直觉知识的混合成为宗教意识形态中超自然生命的特点。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詹姆斯·弗雷泽认为人类的意识形态经历了巫术、宗教和科学三个发展阶段,认为科学是文明的最高形式。然而在史前社会,巫术、宗教和科学并不分家。比如,古埃及建造金字塔和太阳历的科学知识就是在宗教迷信的实践中创造的。因此,我们现在称之为巫术和宗教其实是古代人类看待自身和世界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布瓦耶指出,宗教源于人类的头脑需要说明、人类内心需要慰藉、人类社会需要秩序、人类智力易于幻想。对于原始人类而言,整个世界就是一个大谜团。人们被各种令人费解的日常现象所包围,如日月的起落,雷电、降雨、洪水的发生。对于这些现象,神灵能够提供满意的解释。在许多神话中,天上的星宿就是各路神仙。世界各种文化都有太阳神、雷神、土地神、火神、战神、死神等各种掌控自然和人世现象的神祇。宗教也为令人费解的大脑活动提供解释,如梦境和灵魂。死去的亲人和祖先仍以某种方式存在,与人们在梦境中沟通。幽灵则很好地解释了这种现象,可以说明我们在梦境和幻觉中见到的故人或神灵。宗教可以解释世间生物的起源。人们目睹生物的兴替,但是无法说明其来历和原因,而上帝能够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宗教除了为人们提供解释外,还为发展中的人类社会提供管理机制。宗教可以将各怀私利的个人聚集起来像一个整体那样行动。宗教可以建立起稳固的社会秩序,支持和规范社会的伦理道德,以阻止犯罪、偷盗和背信弃义。相信和畏惧上帝对每个人操行的监控,可以规范人们的行为,确保社会的正常秩序。
原始社会的迷信、神话和巫术被现代社会所轻视,但却为当时社会的必然。正如爱德华·泰勒所言,这种信仰为蒙昧人群所固有。巫术是建立在联想之上以人类智慧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但也是以人类愚钝为基础的一种能力。人类较低智力状态会将彼此有实际联系的那些事物联系起来,但是却曲解了这些联系,并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人们还用这种方法来发现、预言和引发事变,变成了纯粹幻想的性质。但在原始社会里,巫术还是具有某种积极的力量。柴尔德说,巫术是由科学实验一样的推理所激发。新石器时代革命并不曾废除巫术,实际上正好相反。面对难以预测的自然灾难,人们仍然用祭祀、符咒和魔力来趋利避害。任何以自己魔力成功控制这些未知因素的人,就会理所当然地赢得巨大的威望和权力。太阳历的发现就是古埃及国家王权的来源之一。柴尔德还对巫术和宗教进行了区分,他认为前者是由非人格化的力量所直接控制,而后者的力量是人格化的,因此可以像人一样用恭维和祈求来施加影响。由此可见,早期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可以说与人类世界观的发展息息相关。
三、宗教与社会复杂化
社会人类学家以不同的模式说明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比如,罗思曼将社会复杂化定义为功能上的“分异”和“集中”。分异是指职业分工和专门化程度,而集中是指社会各部分和最高控制中心之间的关联程度。麦奎尔将社会复杂化分解为“异质性”和“不平等”两个概念,前者是指社会群体之间人口构成或职业的分化,后者是指一个社会内部获取财富和地位的差异。多尔认为社会复杂化表现为三个过程:一是结构的分化,二是功能的特化,三是结构与功能整合到新的机构层次。迪克逊认为,多尔的模式比较契合宗教体制的发展。社会越复杂,宗教信仰和实践也会表现出更加多样化、异化和特化的特点。他以社会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定义的四类宗教机构来描述宗教信仰的发展。这四个宗教类型包括:(1)个人宗教,是最简单和最基本的宗教形式。其特点表现为仪式无需由萨满或巫师等专职人员操纵。大部分游群的宗教实践属于这个类型。(2)萨满教,其特点是由兼职的萨满操纵。这些萨满或与生俱来,或通过训练获得了一种与超自然力量、神灵和祖先沟通的能力。(3)群体宗教,是比萨满更复杂的一种宗教实践,见于有相当人口规模、政治和经济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社会,存在专职的宗教人士。(4)教会宗教,是最复杂的宗教形态,仅见于现代高度发达的社会文化系统。其特点是存在全职的神职人员,并以一种等级制组织起来。宗教形态的复杂化表现为在复杂宗教类型出现后,简单和原始的类型仍然会继续存在。
美国人类学家金斯利·戴维斯在谈到过去几千年来宗教理论与实践的一般性发展变迁的特点时指出,当人类从小型、孤立的社会向大型、复杂的都市社会发展时,宗教信仰会发生5种变化:(1)神祇会逐渐退出本地的舞台;(2)拟人化会减弱;(3)宗教日益与日常事务分开;(4)宗教的同质性减少;(5)宗教系统开始分裂,并发生冲突。所有这些发展特点可以归为世俗化的趋势。由于教会宗教是现代社会的宗教形态,因此在史前或早期文明阶段,宗教形态至多发展到群体宗教的层次,仍应表现为强烈的萨满教特点,只是主持仪式的祭司可能已由贵族或专职人士承担,而且规模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一般萨满和巫术关注通灵、治病和驱魔等实践范围。
在研究史前或早期文明社会中的宗教时,最大的问题是将原始宗教和意识形态与后来或晚近超凡脱俗的宗教,如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相提并论。古埃及有“神”“祭司”和“崇拜”这些词汇,却无“宗教”这个词,因为宗教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早期文明社会像游群和部落一样,并不像我们那样在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之间进行区分。在这些原始人看来,他们所处的自然界,超自然力量无处不在,并因它们而生意盎然。因此,自然和超自然并无区别,所有东西都是活的、有意识、并且相互关联的。自然界由拟人的力量所操控,只不过更加强大,因此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这些力量就是我们所谓的上帝、神祇和精灵。大约从公元前第一千纪开始,古希腊哲学家、希伯来的犹太教、波斯的祆教、印度的佛教和中国的孔子和老子开始挣脱原始宗教的绝对束缚,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神灵的超自然世界区分开来。在希腊,少数唯物主义哲学家否认超自然的存在,只有社会和自然界才是与人类相关的领域。晚期的欧亚前工业社会一项最伟大和意义最为深远的发现,是注意到自然界根本不同于人类社会。于是,人类的思想开始从宗教和神话中解脱出来,开始以理性的思维看待社会和自然界。每个思想家的传道解惑成为一种认知的基础,起先它只是吸引个别的追随者,后来则是整个民族。这些思想体系成为世界主要社会体系的基础。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恰当地将人类世界观发生巨变的这个时期称为“轴心时代”,标志着现代社会的开始。
虽然古代社会的人们将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不分,但是他们像我们一样明白事物的因果关系。比如,特定的石头可以用某种方法打制,黏土烘烤后能够变硬等。古人与现代人世界观的差异主要在于看待天地万物的性质。古人会以他们的理解来看待世界,将其视为与人类社会相同。宇宙是由像人一样的强大力量所主宰。于是,当人类需要超自然力量来帮助他们克服自然和社会危机时,就能求助于它们。古人可能深信,凡是可以说出、写出、画出的事物,在一定宗教仪式的魔力作用下,可以变成现实或另一个世界中的真实存在。这是古代信仰能够成立的根本原因。
由于早期文明社会将超自然世界与人类社会视为一体,因此当时社会可能将取悦神灵看作是像吃饭睡觉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重要的生计。美国考古学家蒂莫西·厄尔指出,在意识形态上,酋邦普遍表现为“神权”性质,普遍建造巨大的纪念性建筑来创造神圣景观的仪式地点,以便使将尘世与宇宙相连。在仪式中,酋长扮演“神”的角色。在早期国家里,国王是上帝在人世间的代理人。布鲁斯·特里格指出,早期文明的国王位于社会的顶点,成为联系世间万物和社会福祉所系的超自然力量与人类之间最重要的纽带。这种关系由仅限于国王及其代表所掌控的祭祀仪式来协调。这种沟通人神的特点,使得早期文明的宗教和祭祀活动带有强烈的萨满教或巫的特点。张光直就指出,中国早期的巫与萨满具有极为相近的功能。
萨满源于东西伯利亚的通古斯语,专指能与神灵沟通的巫觋。后来它被视为古代宗教的普遍形式,常与现代其他正式宗教如佛教共存。萨满活动的主要焦点就是出神的降神会,萨满或巫师用这种仪式来治病、驱魔、调解和占卜。仪式以击鼓、唱歌、跳舞、穿戴精心制作的盛装来表演。虽然酋邦和早期国家的宗教属于“群体宗教”,但是其与神灵沟通的仪式与萨满没有太大的区别,只是规模扩大,主持仪式由酋长或专职人士掌控,酋长用这种降神的力量来强化他的地位和权力。
弗兰纳利和马库斯用乔纳森·弗里德曼研究缅甸克钦人的民族志资料,介绍了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转变。在平等群体中,社会是由一系列平等声望的世系所构成。有一个村寨神被视为所有当地世系的遥远祖先。在更高、更遥远的地方有一批“天神”,在此平等阶段,任何一个世系都能通过自己祖先的媒介与这些“天神”沟通。在向等级社会的转变中,“一个最重要的转变”就是村寨神被某特定的当地世系所垄断。于是,该世系就转变为首领世系。这个首领世系现在与主要天神直接相连,并与他有姻亲关系。该贵族世系的首领成了在超自然和社群之间进行沟通的调停者,旧的平等意识形态现被世袭不平等的意识形态所取代。当部落社会向酋邦制转型时,形成中的贵族世系——本来只是在轮流做东的情况下才由他来代表其社群——逐渐开始永久接管宴庆主办者的工作。依此类推,早期国家的国王只不过是垄断了整个社会与神灵沟通的权力而已。
张光直指出,巫觋在古代中国的政治中占有核心地位。当时,只有掌握着人神沟通手段的人才握有统治的知识和权力。于是巫便成立每个宫廷必不可少的成员。三代王朝创立者的功德都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甲骨文中,有商王占卜问风雨、祭祀、征伐或田狩的记载,也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它表明,商王就是巫师。吉德炜认为,商人将自然现象看作是神灵所为,因为在他们生活的世界里,并没有像我们那样将神圣和世俗区分的观念。于是,像刮风和下雨这样的现象天生就有神圣的意义。甲骨文显示,商人认为,这些自然现象由风神或雨神所造成,但是这些神祇是听从帝或土这样的最高神祇的驱策。
这种萨满教传统在西周仍然延续,郝铁川认为周公也是一个巫师。理由是:(1)据《史记》记载,周公曾先后两次为武王、成王跳神治病;(2)西周的巫祝卜史官职通常为家族世袭,周公后裔邢也为太祝;(3)西周的重要占卜活动都是由周公亲自进行;(4)巫祝的一个职能就是看风水,周公曾为兴建东都洛邑占卜;(5)周公在摄政时,用商代巫祝卜官辅佐商王的先例以证明自己辅佐成王的合法性。然而,周人制度大异于商者,应该是周公“制礼作乐”的贡献,他为治国方略建立起世俗的道德法规,为将依赖巫术执政转变为礼制执法做出了贡献。这似乎是东周开始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轴心时代”来临的先声。
四、意识形态的物化与研究
如果将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看作虚幻的思想活动,那么考古学可能对此束手无策。但是,在社会复杂化的过程中,当思想和信仰的交流和一体化超出个人和社群的范围,变成酋邦和早期国家全体民众的身份认同时,统治者必须采用文化手段和政治策略来做到这一点。这就是将意识形态加以物化,使之成为具体而有形表现,可以用来反复教育和团结其臣民。于是,考古学家便能从各种物化手段来解读古代的意识形态。德马里斯等人介绍了意识形态物化的四种表现。
第一种就是祭祀仪式。通过举行和参加仪式、舞蹈、宴饮和布道,主持者在参与者中培养一种共享的经验,并用作协调社会各阶层权力关系最有力的手段,包括争权夺利的部落首领到新征服的社群。在许多社会中,仪式会在固定时间,按农历或节庆周期重复举行。许多仪式需要消耗大量食物和用品,展示各种塑像和象征性物品。在酋邦社会中,酋长定期举行仪式和宴饮以展示他调动资源无人可及的能力,以培养臣民对他的依赖和忠诚。早期国家的仪式除了炫耀巨大的财富与国力外,还明确展示权力的不对称。有些仪式会用人牲来展现政治高压。仪式用品会仔细设计制作,以符合表演和演员的不同标准。
第二种是肖像和象征物品。它们包括个人的仪式用品和服饰、绘画、各种雕像和图徽。可携的象征物品有利于在个人、社会团体以及政体之间流通,以确立依附、联合或对应关系。由于象征物品能够拥有、继承和转让,于是它是个人社会地位和权力最好的标志。在墓葬里,随葬品在墓主人死后仍然发挥着这种功能。象征物品一般限制流通,因此极为珍贵。
第三种是纪念性建筑和景观。一些公共建筑如人工土墩和金字塔、大型建筑物、政治活动中心和防卫建筑,能够令臣民叹为观止,对统治者的力量和权威产生敬畏之心。有些大型建筑物如金字塔能被广阔地域内的民众目睹,是进行教化、控制和宣传的理想工具。纪念性建筑也会用作仪式场所,贵族和统治者会对这些建筑加以使用来显示他们的地位,如埃及、玛雅国王和贵族的墓葬往往被安置在金字塔建筑之下。红山文化的积石冢和良渚文化的祭坛可能具有同样的功能。
第四种是文字系统。书写的文件如甲骨、石碑和纪念物上的铭文、法律文书、契约和故事是信仰系统的具体表现。文件能使统治者建立的规则和关系正式化。成文的宗教解释经文、祷文和祭祀传统,将这些讯息规范化,以便在广阔范围内传播和执行。书写的文件也能传递政治信息和进行宣传。虽然整体识字人口不多,但是文字可以作为一种秘传知识,以显示贵族和宗教人士的能力和权威不可或缺。虽然在各早期文明中,文字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国殷商、古埃及和古典玛雅的文字确实与意识形态相关,有了这些文字,我们能够较为清晰地窥视到当时社会的世界观和宗教信仰。
在考古研究中,我们习惯于将那些无法说明其用途的物品看作是仪式用品,或将某种葬俗和艺术表现与宗教信仰联系起来。比如,将墓葬的头向解释成灵魂归宿的方向,将在人骨上撒赤铁矿粉和涂朱看作是希冀死者的重生,将瓮罐葬瓮底的小孔说成是便于灵魂出入,将仰韶彩陶上的鱼纹人面图解释成巫师,等等。对于史前社会这类现象的主位(emic,即从器物主人的角度)解读,如果缺乏文字证据可能永远不得其解。尽管我们无法对史前仪式用品的具体功能做出可信的解释,但是根据人类学的规律探索和意识形态物化的特点,我们还是能够对社会复杂化过程中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以及反映的政治权力做出恰当的推断。
在新石器时代早、中期,我们所见的大部分所谓的仪式用品和丧葬实践可能都反映了个人宗教和萨满教的层次,这类意识形态器物大多表现为异质性特点,虽然某种区域文化中日用的陶器类型比较一致,但是宗教器物可能多为个人物品,较少雷同。表明当时部落和聚落单位仍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仪式由独立的巫师或萨满操纵。柴尔德曾经指出,有明显使用价值的工具、武器,及其他技术用品会被贸易和仿造而迅速传播,而装饰品和葬俗反映了局部品味,相对不易传播。个人宗教和萨满教的信仰应该表现了局部人群的品位,如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龟甲、骨器和石器上的契刻符号和七孔骨笛,应该就是萨满仪式的用品。濮阳西水坡的仰韶文化墓葬中出土了令人注目的蚌壳摆塑龙虎图案,将其看作巫师的墓葬并不离谱。
从萨满教向群体宗教的发展似乎与酋邦的复杂化同步,这在海岱地区的考古发现中比较明显。比如,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大伊山遗址的石棺墓中出土了少量璜、玦和穿孔玉珠,似为个人饰件。而相同时期江苏沭阳万北遗址有红陶钵覆面的葬俗,仪式器物不很明显。但是到了大汶口文化时期,仪式用品也开始日益复杂,并呈现一定的分布范围。其中以莒县陵阳河遗址比较典型,除了墓葬表现出地位和贫富差异外,富墓出土了钺、玉璧、骨牙雕筒和大量的白陶鬶和黑陶高柄杯,刻有图像文字的厚胎大口尊,并在陵阳河、大朱村、尉迟寺尧王城等遗址发现八种二十余字。大汶口文化中比较流行的还有用猪的下颌骨陪葬,墓主手执獐牙钩形器。这些显然是举行仪式和宴饮的物品,出现的图像文字可能作为最早的象征符号显示或传递贵族或祭司拥有某种权力的信息。中晚期的花厅遗址大墓出土了几十件玉器,用人殉、整猪和整狗陪葬。其中M20的规模惊人,墓坑掘入基岩内一米以上,用两名少年殉葬,男性墓主颈挂两串玉珠、左右手套有玉瑗和玉环,头和腰部各置一件精美石钺。墓主显然是一位集酋长与祭司为一体的人物。花厅出土的玉器与良渚玉器非常相似,曾被认为是良渚远征军的墓地。如果考虑到早期文明的强势辐射能力,这类玉器的广泛分布并不令人意外,一如西周青铜器在其势力范围以外地区的发现。到了龙山文化时期,骨牙雕筒趋于消失而玉器出现,并普遍出现卜骨,邹平丁公遗址的陶器上发现11个文字,蛋壳陶高柄杯和陶鬶则成为普遍的仪式和宴饮器物。栾丰实正确认识到这些都是当时的宗教法器,但是对这些器物变化的内涵颇感困惑,觉得这是神权地位逐渐下降和王权出现的表现。其实,早期文明的权力是由经济、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四种权力组成,国王和酋长就是以独特的方式联合操纵这四种权力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我觉得,骨牙雕筒被玉器和卜骨所取代,很可能与酋邦规模的升格与仪式的变化有关。大汶口时期的獐牙钩形器和骨牙雕筒也许因制作成本较低和材质较普通神秘性显然不及玉器,可能是级别较低的仪式工具。玉器从材料和劳力投入来看是更加显赫的物品,而甲骨占卜在沟通人神的仪式上更具神秘性。因此,前者的消失可能与龙山时期的酋邦日趋复杂,酋长或祭司权力和地位日增,需要改用更具超自然力的仪式用品有关。
意识形态的物化以良渚玉器最具代表性。牟永抗根据反山、瑶山大墓中玉器的出土位置复原了良渚最高酋长的打扮:“头戴缀着三叉形式的冠冕,众多的锥形饰立插在冠上的羽毛之间。头的上端束三副缀有四枚半圆形额饰的额带……颈项及胸前缀满珠串,有的还佩以圆牌或璜。两臂除环镯之外,还有串珠组成的腕饰,左手时常握有柄段嵌玉的钺,右手则握以其他形式的权杖或神物。”这完全是一个大巫或祭司的打扮,如果他站在祭坛上,点起熊熊的圣火,供起琮璧,便可与天地沟通,令万民膜拜。玉琮和玉璧一直沿用到历史时期,《周礼》上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的说法。而东汉郑玄注“璧圆象天,琮八方象地”,璧和琮为祭祀天地的礼器是比较可信的。良渚文化分布在太湖流域从苏南到钱塘江以北大约3660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在约1300年的兴衰过程中,这一区域的不同社群用相同的意识形态建立起文化认同,用不同类型和数量的玉器,从纵向厘定整个社会的等级地位,从横向确定各地次级酋邦和社群之间的依附和从属关系,并用反复举行的仪式将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玉器类型的变化也折射除太湖流域的社会复杂化进程,在马家浜文化时期主要是以玛瑙、玉髓为材质的玉玦,为个人饰件。如有信仰崇拜也仅限于个人宗教和萨满教的层次。崧泽文化时期开始使用真玉,类型有璜、环、玦和坠饰等,信仰层次社会结构与马家浜时期相仿。到了良渚文化时期,璧、琮、钺、三叉形器等的大型仪式用品的出现,成为宗教祭祀的法器。从玉器使用的变化,我们明显可以看出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还是平等部落社会,而良渚的群体宗教明显进入了酋邦社会。
复杂酋邦和早期国家的体制转变可能无法从世界观和宗教仪式上加以区分,但是用于仪式显赫用品上的投入也许可以作为某种衡量尺度,如二里头的青铜爵和青铜铃和商代种类繁多和体量巨大的青铜礼器和兵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对于中国早期国家,社会的稳定需用武力来维持外,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必须靠祭祀来强调,巨大的社会资源和能量都被投入到兵器和礼器这两项没有任何回报的生产中去。
此外,商、周的文字给了我们以直接了解早期国家世界观的机会。殷商的甲骨文表明,殷人没有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者的区分,人、祖、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超自然力量包括上帝、祖先和各方神祇(主管天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殷人通过占卜与这些超自然力量进行交流沟通,而且这种关系并不涉及道德或感情因素。殷人通过仪式向神灵祖先进行献祭,祈求它们的庇佑和赐福。目前所见的占卜资料仅限于王室的活动,并不清楚民间是否也能进行同样的宗教活动。但是,从上面缅甸克钦人的民族志资料来看,形成中贵族是通过垄断整个社会与神灵沟通的仪式来获取地位和权力的。因此,举行祭祀仪式与超自然力量进行沟通应该是商王的专利,并借此掌控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西周的意识形态大体与商代相近,但金文和其他文献显示出一种不同的面貌。殷人的上帝不过为诸神中的一员,但是周人赋予上帝以道德判断意志和世间最高仲裁者的地位,宗教仪式开始具有道德天命和礼制规范的意义。这就是上面提及的周公将国家权力从巫术执政转变为礼制执法的意义。
五、小结
在早期文明起源和社会复杂化过程中,世界观和意识形态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虽然考古学对史前仪式用品和现象无法做出主位的解释,大体限于主观的推测。但是从本文的讨论来看,有了宗教人类学、民族志的比较和历史资料的帮助,我们还是能将史前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探究置于较为坚实的理论和实证基础之上。酋邦和早期国家处于群体宗教阶段,具有强烈的萨满和神权特征。当形成中的统治者逐渐加大将意识形态用作权力基础时,他们会在仪式用品和纪念性建筑上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和劳力。这种物品和建筑都会体现显赫技术的特点,这就是不计成本和没有回报的巨大投入。于是考古学可以从仪式用品和纪念性建筑上投入的能量来观察和衡量当时的政治等级、经济实力、劳力调遣规模以及社会凝聚范围。
以“轴心时代”为分野,我们应该慎将早期文明的世界观与历史时期的“礼制”和当代意义的“宗教”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世俗社会的两元划分。在早期文明中,自然、超自然和社会三位一体。古人将神灵和祖先看作和自己生活在一起的成员,随时可以通过仪式沟通。他们对神灵和祖先的崇拜和献祭犹如空气和食物一样不可或缺,甚至更为重要。由于神灵的无所不能和人类的弱小无助,古人便会时时祈求神灵以应对叵测的命运和各种灾难。对于复杂社会中的首领,他们自然会借助神灵以确立自己地位和权力的合法性,宗教仪式便成为支撑政体和社会系统运转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因此,早期文明中的政治和信仰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中国,大约要到春秋战国,古人才将天地和人看作是不同的范畴,需要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于是才有政教的分离。如果以这样的视角来看待古人的世界观,我们也许能够对早期文明起源及社会复杂化进程获得更加深入的认识。
来源:《文化遗产研究集刊》第6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 0001
- 0003
- 0000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