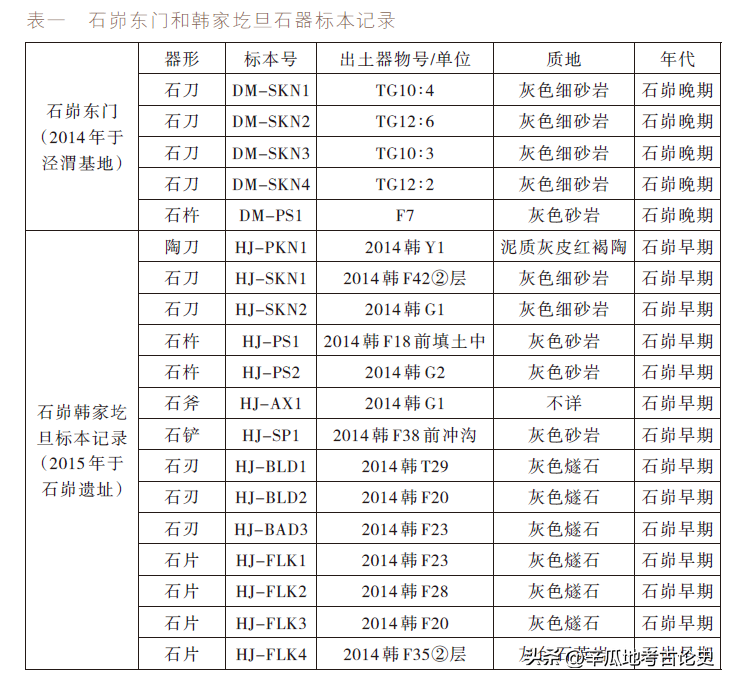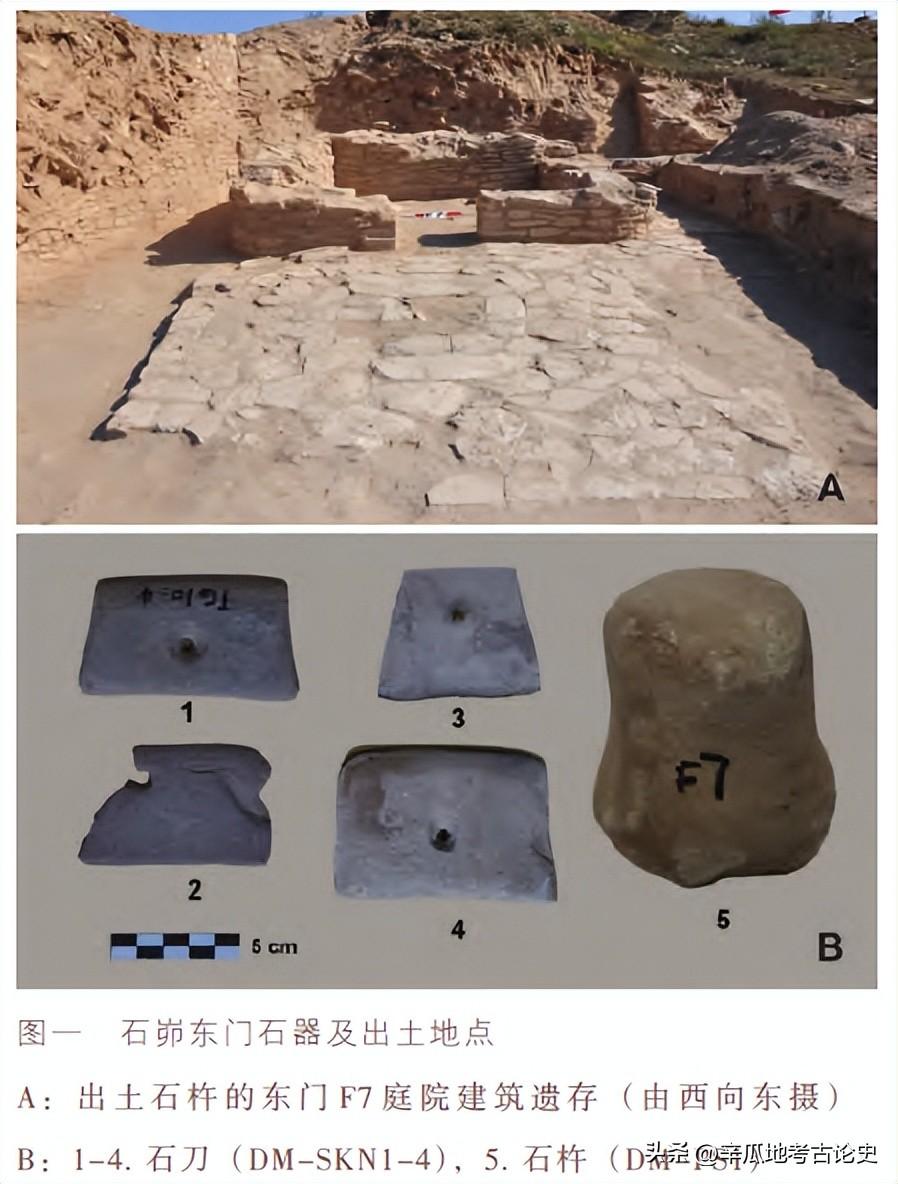陈淳:酋邦与中国早期国家探源
自张光直在他的《中国青铜时代》(1983年中文版)中介绍了“酋邦”,并将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龙山文化列为酋邦之后,这一术语渐为国内学者所知。然而,由于对这一概念的人类学理论背景缺乏全面的了解,国内一些涉及酋邦的讨论便出现了大相径庭的看法。有人认为它意义重大,有人则认为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国。本文试图对酋邦这一概念在中国文明和国家探源中的意义做一探讨,以期能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更大关注。
一、问题与思考
近来,“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结项和一些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心的相继成立,使中国文明与国家起源研究成为一个耀眼的学术亮点。在这一研究课题中有一个值得我们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困扰着我们的问题,即如何将舶来的社会法则研究和中国史实相结合的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将对社会发展一般性规律的探索与中国史学和考古学个案研究相联系的问题。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酋邦这个社会人类学的理论概念在中国史学和考古学研究中是全新的。而且,这个概念在当代文明与国家探源中被视为至关重要并处于不断更新的状态之中,但是在中国它的意义尚未被充分的认识与探讨。
张光直说,在中国古代史这种历史悠久的学科里常常会有很陈旧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包袱。所以有时候,我们要把过去所有的成见暂时地、完全地抛除,进行重新的思考。这种思想包袱不但体现在学术定位和方法论上,而且表现在对理论指导作用的重视程度上。
从一开始,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就被定位于史学范畴之内,受制于传统的史学框架,文献资料不但左右着研究的重心和探索的方向,而且决定了学术成就的价值取向。20世纪初西方科学考古学引入中国的初衷,就是被用来解决国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中国学术界当初对考古学寄予的最大期望,也是有望能够帮助解决三代史实的问题。
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文明与国家探源相比,中国拥有丰富的典籍和发达的史学传统,这是研究的一大优势,但是从科学探索的角度来说,则难免成为一种束缚观念的成见。中国传统史学的一个主导特征是个案的记载,而非抽象的概括。这使得当李济的殷墟发掘在中国建立起新的考古学传统的时候,仍然无法超脱传统史学的窠臼,结果殷墟发掘的主要成就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之上。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方法论承袭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精髓,于是在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中,所有现代化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学在内,全部围绕着史籍的内容而展开,并使理论在科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指导地位和阐释作用被史籍所掩盖和取代。其实,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基础研究的对象而无主次之分,无论是文献研究还是考古观察,都需要用现代科学理论来予以指导和审视。将文献置于研究的核心地位,会使探源工作成为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
所有现代科学都十分重视通则的探究,以求建立具有预测性价值的普遍规律,国际科学界对这种永恒真理的追求看得远比重建偶然事件的真相来得重要,而这一高层次目标则是和理论密不可分的。然而,在当代的中国考古活动中是根本没有理论这个范畴的,这既和中国传统史学本身就缺乏抽象理论思维直接相关,也和科学考古学在被引入的过程中只吸收了获取材料的操作技能而忽略了解决问题的探索思维有关。史学导向的考古学被看作是为证据不足的历史问题提供新依据,它并不需要考古学家发挥独立的思考能力。加之,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利用史实的选择和描述来表明历史学家对价值系统的主观判断,于是在这种历史观里培养出来的考古学家也就特别重视材料的获取和考证,而不信任主观的理论,常以为理论不过是一种空谈。美国考古学家宾福德(L.R.Binford)甚至刻薄地形容,中国考古学家把理论看作是天国里的泼阿斯所为,是某种空洞的胡诌。因此,中国的考古报告是因循守旧的典范,是世界上最令人厌烦的东西。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理论被普遍用来解释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形态,但是由于一方面缺乏从物质现象中提炼人类行为的考古学中程理论研究,另一方面用僵化和教条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有关原始社会发展的理论,使有的学者丧失了探索的主动性和敏感性,把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变成了现成的答案和教条,于是本来就先天不足的理论探讨变成了只是将摩尔根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与考古材料对号入座,陷入了把马克思提出的社会发展规律看成是历史本身的一大怪圈。自考古学引入中国以来,中国学者满足于运用李济及其同时代的西方学者的方法来处理考古资料,错失了许多良机,未能利用中国丰富的或者也许是独特的材料,为构建更完善的社会科学理论做出积极的贡献。
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与历史学、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有着紧密的联系,历史学提供文献线索,考古学发掘地下证据,而社会人类学提供阐释的理论依据。在这点上人类学和历史学及考古学是有区别的,即社会人类学因其探求“规律”的性质而属于“正题法则科学”,而历史学并不从事规律总结的抽象思维,而是以补充的形式重建事件的复杂性。因此有学者认为,缺乏规律性探索和理论支持的历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
社会人类学自从在西方诞生以来,主要是以没有文字和历史记载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因此它所发展出来的理论和方法,都是立足于研究对象缺乏信史这一前提。过去几十年来,社会人类学者努力将当代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来,却还没有成功地解决如何将这些理论方法与一个有悠久文字记载的历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虽然有丰富的史籍记载和悠久的史学传统,但是这段历史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所占的比例也十分有限。而且,史籍提供的信息也有其局限性,难以涉及社会历史各个层面。现代史学也需要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方法,突破传统史料学的窠臼,用严谨的科学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由于中国考古学发生和发展的特殊社会背景,使它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证经补史的作用上面,一旦面对处于史籍以外的考古材料,就只能用常识和经验来进行处理和解释。再加上缺乏社会人类学理论的训练,考古学家自然不会有探索的科学意识去研究材料和现象的原因或社会发展的因果率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中国早期国家的探源工作仍然局限在三代编年学定位上的原因。虽然早在1929年,郭沫若就呼吁我们应当抛弃国情不同的成见,用人的观点来观察中国的社会。20世纪30年代吕振羽也提出,如果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法则不能得到确立,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就不能前进一步,但由于背着沉重的传统包袱,我们在学习和接受现代科学思维时才显得那么的艰难和如此的勉强。
社会科学理论的兴起可以追溯到启蒙时代,经过西方大批哲学家和学者几个世纪的持续努力,创立起社会科学理论建设的优良传统,有关文明和国家起源的理论不断发展,日臻成熟。这一进程完全是和以牛顿、伽利略、达尔文、爱因斯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同步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是和以哲学及逻辑抽象思维为特点的理论发展密不可分的。正是由于西方学术界对理论的重视,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对规律和通则的探索均成为学术问题的核心,并成为无数探究的起点和向导。
中国的国学以“经”“史”为两大支柱,方法是记述和考证。因此,中国的学术传统擅长主观的价值判断,缺乏逻辑推理的抽象思维训练。科学考古学在引入中国之后,就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并没有重视近代科学的演绎法,并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发扬光大,却将其纳入了与传统历史学相一致的描述与编年的窠臼。这种历史学导向的思维也成为我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的主要特点。
在当今国际学术界,文明和国家探源是社会文化演变研究的重要课题。加拿大考古学家特里格(B.G.Trigger)指出,社会文化演变研究可以被视为一种观察人类历史的方法,它可以对历史整体的形态和发展方向做出一种合理的解释,并赋予人类行为以特殊的含义。因此,社会演变和史学研究实质上是通则和个案的区别,两者互补并缺一不可。没有个案的实例和归纳就不可能提出通则所要解决与认识的问题,没有通则的探索也无法科学地阐述历史事件发生的真相。
有学者可能认为,中国经历了和世界其他文明古国轨迹不同的发展历程。文明是某个地区本身历史过程的产物,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塑造了迥异的民族文化,因此,这种“国情不同”的史学研究没有多少规律性可言。过去,西方也有学者将社会文化演变等同于历史发展过程,认为史学研究和社会文化演变的课题是相同的。但更多的学者认为,社会演变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学,而是对社会演变动力的研究。为此,旨在揭示中国国家起源真谛的历史学和考古学研究若不同其他社会科学密切结合,便将无所作为。所以我们应当认识到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研究放到社会科学总体框架中去讨论的必要性。
已经结项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在国内好评如潮,但是国外同行却并不认同,而且引发了一场网上的大讨论。一些外国学者对工程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工程的学者们受政治驱动,试图跨越缓慢而又无序的科学研究去证明中国文化的原初性和独特性。有些美国学者直言不讳地指出,今日中国大陆的考古学田野方法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方法相仿,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他们指出,某些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作为夏的做法是难以接受甚至是误导的。中外学者对工程性质的看法如此大相径庭,使得我们有必要对一些最根本的问题进行反思,这不是单单用意识形态、价值观或文化优越感对一些批评反唇相讥就能解决的,因为中国与当代国际上的文明与国家探源研究,无论在理论还是方法上都存在巨大的鸿沟。
表面上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轰轰烈烈、热闹非凡,实际上它已面临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诚如有些考古学家所言,依靠文字材料搞三代纪年,能做的也基本都做了,即便采用先进的测年技术也不见得能得出真实的结果。另一方面,夏代纪年范围内的遗址也已发现不少,但是学者对什么是夏仍然众说纷纭。问题症结何在?关键在于缺乏能够帮助我们从文献和考古遗存来判别国家形态的科学标准。没有一套用坚实科学理论构建起来的独立分析体系,即便将夏文化的所有遗址发掘殆尽,我们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达成对夏的共识。换言之,面对坛坛罐罐,我们如何来判断它是早期国家?没有对酋邦社会形态的探究,我们又如何能确认国家的诞生?
当前,编史学定位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国家探源研究进一步深入的主要原因。其实,文献和考古材料只是不同的信息库,它们都属于最基本的研究材料而处于基础研究的同一层面并无主次之分。然而,目前我国的国家探源工作仍将史籍记载置于研究的中心地位,所有现代化的科技手段和研究方法包括考古学在内全部围绕着典籍的内容而展开,所有学者的工作也都围绕着同一个目标,这就是要证实三代的史实及其年代学的可信度。显然,这项工作将早期国家探源研究变成了变相的考证而非科学的探索。我认为,这项研究应当尽快从狭隘的编史学中解放出来,引入国际上流行的方法论,并充分重视理论的作用。历史学和考古学是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相关的信息应当通过持续的反馈结合起来,防止将考古研究简单地按编史学的框架来进行设计。中国的国家起源研究必须超越传统文献的线索,努力为新的历史问题提供新的认识与启示,从而创造一种古史研究的新境界。
为此,应当意识到理论探究在国家探源中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它绝不是缺乏事实根据的胡诌,而是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认识早期国家形态和了解远古文明发展历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而酋邦正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切入点,换言之,只有从科学理论上确定了酋邦的社会形态以及什么是早期国家的标准,才能够从物质形态上来探讨它们的存在和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同样,只有借助当代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指导,史学研究才能和考古资料进行科学的整合,进而深入了解中华大地上文明和国家起源和发展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并为完善有关国家起源的社会通则做出独特的贡献。
二、酋邦——前国家的复杂社会
一直到20世纪中叶,西方学术界对酋邦社会仍然知之甚少,尽管这种复杂社会遍布全世界,但是人类学界并没有将它看作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1955年,美国人类学家奥博格(K.Oberg)根据中美洲低地的人类学研究,将当地的部落社会称为“酋邦”,并将社会演进的形态用同姓部落、氏族部落、酋邦、国家、城市国家和帝国等类型来表述,从而开创了酋邦探索之先河。之后,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图尔特(J.Steward)将酋邦定义为由多部落聚合而成的较大政治单位,并将酋邦分为两类:神权型与军事型。然而,如何在酋邦与早期国家之间进行划分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1962年,塞维斯(E.R.Service)在他的《原始社会结构》一书中将酋邦定义为:“具有一种永久性协调机制的再分配社会。”他认为,酋邦的产生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需要将分散的劳力组织起来从事大规模的生产,二是定居社会生态环境的多样化导致经济的特化。在塞维斯看来,酋邦等级制的诞生是源于协调区域性特化经济再分配的需要,而这种分配等级制度基本上是在资助贵族阶层及其政治活动的特殊背景内运转的。
1972年,弗兰纳利(K.V.Flannery)利用丰富的民族学和考古学资料,论证了酋邦与国家的特点和区别。他认为酋邦标志着世袭不平等的出现,在酋邦社会中人的血统是有等级的,高贵和贫贱与生俱来。酋长不仅意味着高贵的出身,而且往往是神的化身。他们与神祇的特殊关系使其权力合法化。酋邦常常以繁缛的祭祀活动来获得民众的支持和接受贡品。至于国家,弗兰纳利认为它是一类非常强大的政体,拥有高度集中的政府和专门的统治阶层,总的来说已基本脱离了标志简单社会的那种血缘关系。它是高度等级制的,居住方式常常基于职业上的专门化而非血缘和姻亲关系。国家可以发动战争、征募士兵、征收税赋和强索贡品。国家拥有强大的经济结构,常常以市场的存在为特点。经济大部分为一批上层人物所控制,他们是产生高官的阶层。
1975年,塞维斯(E.R.Service)在他的《国家与文明起源》一书中正式将酋邦列为社会发展的独特形态和重要发展阶段,提出了原始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一社会演变的新进化论模式,从而取代了摩尔根的蒙昧、野蛮和文明的三阶段文化演变理论。塞维斯认为,酋邦介于平均主义社会和强制性国家之间,社会地位的世袭使它具有一种贵族社会的性质,但是它没有武力压迫的政府机构和法律机制,缺乏由国家行使的那种与权力垄断相关的强制制裁能力。这种社会大部分是用宗教来实施管理,因此酋长的权力基本上是一种调定权而非统治权。酋邦的结构普遍是神权型的,酋长或祭司一般通过宗教仪式来行使自己的权力和使民众臣服。
1981年,卡内罗(R.L.Carneiro)详尽讨论了酋邦的概念,他给酋邦所下的定义是:“由一个最高酋长永久控制下的多聚落和多社会群体组成的自治政治单位。”这种超聚落的社会结构是向国家演进的基础,其下限标志着聚落自治的结束,而其上限标志着向国家演进的起点。卡内罗认为,酋长虽然拥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的权力是有限的,酋邦不存在真正的政府来实施具有法定约束力的决定。卡内罗指出,酋邦一般只有两层等级制,而国家至少拥有三级等级制,包括国王、地方行政长官和聚落首领。卡内罗还列举了从考古学上分辨酋邦的4项判断标准:(1)存在大型建筑物,其规模和所需劳力超出了单一聚落人口所能胜任的程度;(2)存在数量上少于聚落的祭祀中心,表明存在超越聚落自制的社会结构;(3)存在标志特殊地位人物如酋长的富墓;(4)平等部落社会的居址形态和大小布局基本上非常接近,但是酋邦存在一个结构上大于一般村落的聚居中心。卡内罗认为,一般作为国家标志的强制性垄断权甚至在早期国家中也并不明显存在。
随着探讨广泛展开,学术界对酋邦的认识也日趋深入,主要表现在:(1)酋邦不是一种划一的和铁板一块的社会形态,它是一种差异极大、形态各异的复杂社会。简单酋邦和部落相差无几,而高级酋邦已非常像早期国家。(2)酋邦本身的发展体现为一种“轮回”的兴衰过程,并不是所有的酋邦都能向国家演进。探讨的领域也从社会形态的划分转向了解产生酋邦形态多样性的原因。(3)酋邦发展和国家起源的动力不仅是塞维斯提出的劳力集中和经济多样化导致的再分配机制的复杂化,还要将卡内罗提出的冲突和战争动力考虑在内。
20世纪70年代,厄尔(T.K.Earle)根据他对夏威夷土著社会的民族学研究提出了一种复杂酋邦的概念,表现为:(1)酋长与平民之间在等级上完全隔离;(2)领导权特殊化;(3)地区等级分化日益明显。并认为夏威夷是仅次于国家层次的复杂酋邦的最好例证。在1987年的一篇重要的综述中,厄尔认为酋邦是一种进化的社会类型,是原始平等社会和官僚国家之间的一个桥梁。酋邦是形态差异很大的社会,对不同的分类加以归纳:有神权型、军事型和热带森林型的划分;有集团型和个体型的划分;有层级(stratified)型和等级(ranked)型的划分;有最高(paramount)、层级(stratified)和非层级(non stratified)酋邦的划分;还有简单和复杂酋邦的划分。
厄尔认为,酋邦最好被定义为一种根据地域性组织起来的社会,拥有一种集中的决策等级制以协调一大批聚落之间的活动,规模从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酋邦也是一种经济上集中和再分配的社会,贵族阶层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财富的交换来控制经济和劳力。象征、认知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标志酋邦进入了最早的文明阶段;酋邦普遍具有神权的性质,使酋长的统治成为自然规律的一部分,许多酋邦的祭祀建筑将社会的宗教活动延伸到宇宙的秩序上。厄尔总结酋邦三种意识形态的物质表现:(1)纪念性建筑的营造,如英国的巨石棚、密西西比的土墩群和夏威夷的神庙。这些建筑是世俗与神祇的维系点,使酋长能够扮演与宇宙力量沟通的神圣角色。这些建筑也是酋长拥有劳力和资源操纵能力的最好明证。(2)酋长普遍强调他们的外来起源,从而使自己的统治赋予神圣的地位并使自己的地位合法化,这些贵族墓葬里发现的大量珍贵随葬品往往都是舶来品,可以体现他们对神秘知识和权力的拥有。(3)武力的象征,在酋长的墓葬中常常有代表尊严的武器,用以表现由武力主导的宇宙秩序的延伸。
1991年,克利斯蒂安森(K.Kristiansen)进一步阐述了酋邦的多样性,认为它是一种介于部落到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大的社会形态。为了研究酋邦与国家的关系,克利斯蒂安森在酋邦纵向的发展层次上又划分出一个“阶层社会”(stratified society)的形态作为国家结构的雏形,这种复杂酋邦已具有早期国家的一些特征,如强大的社会经济分工和领土意识,但仍缺乏完善的官僚体制。而在横向的变异层次上,克利斯蒂安森定义了两类酋邦:一类立足于控制生存资料生产的常规经济(staple finance),另一类立足于奢侈品生产的财富经济(wealth finance)。但是,克利斯蒂安森认为这两种类型并非相互排斥,非此即彼,而是可以以各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在讨论社会演变轨迹时,他认为酋邦常常处于一个进化和倒退的较大历史旋涡之中,在许多情况下酋邦是次生的发展,但有时却是一种倒退的社会。
1984年,赖特(H.Wright)提出了酋邦发展的一种“轮回”(cycling)概念,指复杂酋邦在区域性简单酋邦群中兴起、扩张和分裂的周期性波动。经过一段时间的扩张,大部分的复杂酋邦会分解成为简单酋邦,或从整体上崩溃。这种波动可能是由于与周边社会的竞争、传染病、人口失衡、农业歉收、领导不力以及继承等各种因素所引起。“轮回”的发展概念被许多学者公认为酋邦社会的主要特点,并成为无数失落文明遗留的悬念。
在1999年发表的题为《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与动力》一文中,弗兰纳利说:“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及公元前200年的墨西哥和秘鲁,人类创造了我们称之为‘早期国家’的大型、政治集中和分层的社会。考古学家面临的一个挑战是要回答为什么。”弗兰纳利进而将起源问题用“过程”和“动力”两个概念来概括,“过程”是指要了解早期国家从哪类社会演化而来,而“动力”问题是要了解促成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因。弗兰纳利指出,虽然酋邦具有早期国家赖以形成的世袭不平等和等级结构,但只有极少数的酋邦才能演进到国家。他深信,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就形成于酋邦“轮回”的动力环境之中,孤立的酋邦不可能转变成国家。
最近弗兰纳利和马库斯(J.Marcus)撰文指出,全世界的酋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如营造大型的土墩和祭祀建筑。卡霍基亚(Cahokia)酋邦建造的“僧侣土墩”(Monks Mound)高达30m,占地300m×212m,是新大陆最大的土墩。墨西哥奥尔梅克酋邦在拉文塔(La Venta)矗立起巨大的石雕人头像、复活节岛的酋邦雕刻了900到1000具巨大的石像。奥尔梅克和新西兰的毛利酋邦都雕刻玉器,并成为贵族的传家宝。许多酋邦还有精美的木雕,贵族房屋的梁和柱都以雕刻加以装饰,有的雕刻着武士,有的雕刻着传说中的祖先。他们还指出,即便是最高酋邦(paramount chiefdom)或阶层型复杂酋邦也不能幸免于轮回与瓦解的进程,也不一定能演进到国家。由于酋邦社会的凝聚机制一般无法控制距离较远的民众,所以酋长总是尽可能将人口集中在自己的居住区周围。只有极少数最高酋邦才能制服和吞并周边的大型酋邦,形成一个不能再作为酋邦统治的政体。因此弗兰纳利和马库斯认为,在这一进程中武力征服的作用不可忽视。早在1970年卡内罗就提出过国家起源的战争理论模式。1992年他又将冲突和战争的理论模式用于解释酋邦的发展。
综上所述,酋邦和国家的关键区别有三点:(1)是否存在官僚政府机构;(2)是否拥有合法的武力;(3)社会凝聚机制的血缘关系是否被地缘关系所取代。美国政治人类学家弗里德(M.Fried)将国家定义为:“超越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社会人类学所确立的国家标准应当可以被看作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科学依据,但是我们在应用这些标准的时候也需要用中国的案例加以检验。张光直指出,在将西方的法则用到中国的史实上来的时候,需要做一些重要的工作,看看有多少是适用的,有多少是不适用的。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的阶段,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缘关系所取代,反而更为强化,因此三代和西周前期应当分入酋邦还是分入国家,成为中国国家探源值得深究的问题。
20世纪末在一篇回顾酋邦与早期国家研究的论文中,美国考古学家斯坦因(G.J.Stein)总结了这一领域研究发展的新趋势。首先,当代学术进展已经偏离构建并检验有关早期国家起源一般性理论模式的导向,开始转向更加关注特定文化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分析。这一新的趋势努力将理论与实证研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以一种复杂社会和政治经济的多样性的框架来解释都市化结构、手工业特殊化和交换的多样性。这一研究的新趋势也反映了国际学术界对新进化论和文化系统论的批判性反思,意识到这些理论模式过分强调文化进化和文化适应、过分强调演绎法所造成的忽视历史个案研究,以及囿于线性观、功能观的和环境决定论所造成的偏颇。
其次,新的研究趋势使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日益紧密,将复杂社会看作是一批多样化的功能实体,在其中意识形态、权力关系与社会经济群体文化传统上的特殊形态相结合,在塑造特定政治实体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有关酋邦研究方面,斯坦因列举了当今国际学术界的三项趋势:(1)酋邦是一个过于广泛的概念,因此有必要在简单酋邦和复杂酋邦之间做出区分。(2)酋邦越来越被从贵族阶层利用扩张的策略来导致并维持经济不平等的角度来予以定义。因此,社会复杂化成型的关键因素是控制剩余产品的流通和聚敛,从而造成经济不平等并使之永久化的能力。(3)意识形态和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被操纵来作为控制剩余产品和竞争权位的主要手段。学者们强调,控制奢侈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是酋邦政体最为关键的要素。
在国家探源的研究方面,斯坦因也列举了四项趋势:(1)现在已不再将国家看作是一种高度集中和权力无限的政体,而倾向于以一种多样化的眼光来看待国家和城邦结构的多样性并探讨国家权力的范围。(2)与酋邦研究相同,国家的研究也关注国家政体的经济结构,特别是中央统治机构与其他社会经济部门之间关系的状况。(3)更加关注农村聚落的社会结构以及中心城市与边缘地区间的相互关系。(4)国家分析开始探究复杂层次上不同的政体之间区域性互动的政治经济学。
斯坦因还指出,由于史籍中几乎没有关于大部分社会阶层如都市平民、个体工匠、农民以及游牧民的相关资料,因此有关这些被史籍所忽视的社会群体的状况就必须要靠考古学的研究来了解。
三、中国学者的误区
酋邦概念在引入中国之后,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并开始尝试用这一概念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和考古材料。由于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背景和沿革缺乏全面的了解,于是在讨论中出现了许多不得要领的情况。
在“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一文中,谢维扬将摩尔根的部落联盟与酋邦放到一起讨论,认为中国的早期国家不是由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演化而来,而是从非部落联盟类型的酋邦发展而来,并用个人观点概括了所谓西方学者对酋邦的定义:(1)酋邦比部落大;(2)社会分层;(3)经济上由互惠转变为再分配;(4)出现了宝塔形权力结构和专职的官员;(5)血缘关系解体。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将部落联盟和酋邦看作不同的前国家形态是一种概念错误。其次,上述的五项特征中除了前三点言之有据之外,其他均属主观臆测。
该文有两个需要澄清的问题。第一,摩尔根时代还没有新进化论的社会发展模式,当时流行的是蒙昧、野蛮和文明的三阶段文化发展模式。摩尔根提到的部落联盟仅是19世纪民族学案例的研究,而酋邦是20世纪提出的社会人类学理论概念,故将酋邦与部落联盟相提并论并扬此抑彼显然将两个时代的不同概念混为一谈。第二,根据新进化论的观点,易洛魁、雅典、罗马以及中国的前国家形态均属于酋邦的范畴,它们之间的社会形态差异反映了酋邦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说易洛魁、雅典、罗马的前国家形态是部落联盟,而中国的前国家形态是酋邦,说明作者对酋邦的理解还是局限在个案而非通则的认识上。于是,从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来评价西方学者有关酋邦论述的武断和片面显然有失偏颇。
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谢维扬除了继续将部落联盟看作是前国家社会的一种不同形态之外,还对酋邦的误解有进一步的发挥,他指出酋邦的主要特点是:在进入国家社会之前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金字塔形的中央集权。该书还罗列了四项酋邦的特点:(1)酋长拥有特权,而且包括了征兵权和对臣民的生杀之权;(2)酋邦有各种官员,组成了一个较为正式的政治机构和权力网;(3)酋长和他的官员拥有特权;(4)酋长的地位成为永久性的。与社会人类学公认的酋邦概念相比,我们可以发现上述这些所谓的酋邦定义存在非常大的问题。诸如中央集权、征兵权和生杀之权、官员和正式的政治机构以及权力网等属于国家的特征,都被用来描述酋邦,误导了酋邦的基本概念。
无论是批评摩尔根的部落联盟不具备普遍意义,还是推测塞维斯不提部落联盟并非疏忽,都是作者概念不清所产生的误解。因为,摩尔根时代还没有将部落联盟作为向国家过渡的普遍形态来加以讨论的背景,因此指责摩尔根的失误显然没有道理。而塞维斯不提部落联盟也并非是因其不具代表性,而是酋邦概念已涵盖了所有多部落的复杂社会。
在谈及国家时,谢维扬令人惊讶地引用了克烈逊(H.J.M.Claessen)和斯卡尔尼克(P.Skalnik)的一句话作为开宗明义的说明:“根本不存在为整个学术界所公认的国家定义。”但是,这句话的本意看来不是指学术界没有公认的定义,而是指没有完美的定义。结果,作者不去讨论诸如血缘和地缘关系、政治经济和合法武力等20世纪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在19世纪恩格斯和列宁有关国家是阶级冲突产物的论述上大费笔墨。
谢维扬有关酋邦的论述存在两个很大的误区。第一,将部落联盟作为一种前国家形态和酋邦搅到一起,以为部落联盟和酋邦是两种不同的前国家社会形态,将西方的前国家社会归入摩尔根的部落联盟,而将中国的前国家社会说成是酋邦。第二,完全以“准国家”的标准来看待酋邦。其实酋邦是一种形态多样、发展层次各异的复杂社会,并以“轮回”兴衰过程为发展特点。于是为了要将酋邦描述成国家的“候选人”,便刻意提升酋邦的地位,将许多进步特点堆砌到酋邦的头上。在这种“准国家”形态的渲染之下,我们看不出酋邦是原始平等社会向国家过渡的桥梁,也不知道什么是促成向国家演进的动力。于是,在将酋邦概念和中国的史实相结合时,也难免流于生搬硬套。
我国资深人类学家容观夐对此提出过批评。他说,我国一些学者(主要是历史学者)不善于运用考古实物资料和文化人类学理论做必要的参证,孤立地进行实证研究。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近年来对我国前国家形态的研究问题上。他们借用当代文化人类学家塞维斯所创建的酋邦概念,认为我国早期国家不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而是古代酋邦在政治上演变的产物。1987年起有不少关于酋邦的专论,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就是在解剖诸如良渚文化或红山文化时,并没有像国外文化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那样,在确定其为酋邦时尽可能地取得实例,然后开展类比分析和验证,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而是由作者仅仅用考古遗物、遗迹和少量的文献记载便构筑起代表整个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的“酋邦社会”的全貌。
对于酋邦,另有学者则持完全相反的看法。比如,王震中认为,酋邦除了启示我们在部落到国家之间还应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之外并无普遍意义,因为它无法和考古遗存对号入座。他认为,从平等聚落、通过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然后向都邑发展这三大阶段才体现了文明和国家起源的轨迹。其实,酋邦是人类学对社会发展阶段普遍性的一种理论概括,是社会规律的总结。无论是史料还是具体的考古发现,这些具体的经验事实和人类学理论概念并不处在同一阐释层次上。科学理论是一种高层次的规律性认识,它们都以全称命题的形式表述,因此酋邦具有理论概念的抽象性和普遍性。而史料和考古材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部分,仅处于低层次的“经验观察”范畴。所以,用考古证据的不同来否定酋邦概念就好比根据性别和人种差异来否认存在抽象的“人”的概念一样。
由于我国历史和考古学者在文化人类学领域并不内行,于是在面对基于人类学理论来探讨历史和考古现象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困扰。有的学者似乎不理解“对社会规律的认识”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之间到底有何不同,时常下意识地偏信直观的事实而怀疑抽象的规律。社会人类学认为,处于相同发展层次上的社会,可以拥有完全不同的物质文化。比如,拥有精美青铜器的殷商完全不同于拥有雄伟金字塔的古埃及,但是两者都符合早期国家的概念。同样的道理,世界各地的前国家形态可以千差万别,但是都符合酋邦的概念。可见,王震中否定酋邦实质上是混淆了两个不同学术层次上的认识,根据自己对现象(考古证据)的认识来否定科学规律性(理论)的认识。对理论概念认识的不足同样表现在将部落联盟和酋邦的相提并论上,谢维扬将两者混为一谈,根本上说也是混淆了对“社会规律”和“社会现实”的认识。
此外,王震中提出用聚落形态判断社会演进阶段的标准,也没有了解目前国际上流行的聚落考古学的精髓,是从人类居址逐级向心聚合的过程和布局及规模的变迁来分析社会结构的复杂化和等级化。当代考古学已发展出一套从聚落和居址形态来判断社会和政体的发展层次、观察史前社会从部落向酋邦和国家发展的理论和方法。比如,弗兰纳利指出,简单酋邦一般具有两个层次的居址等级,表现为一批小村围绕着酋长的大村。复杂酋邦有三个层次的居址等级,小村围绕着大村,而一批次级酋长的大村又围绕着最高酋长的聚落。酋邦通过吞并邻居来壮大自己,或取而代之或迫使他们对其臣服。
虽然对酋邦概念的重视反映了中国的国家探源工作开始将社会人文科学与中国的史实及考古资料结合起来的一种可喜努力,但是由于没有吃透理论概念和掌握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我国一些学者的讨论难免传递了误导的信息和混乱的概念。
在传统的领域,我国学者将典籍中记载的朝代国家不加批判地公认为现代科学意义上的国家,因此夏商周三代自然成为国家探源的焦点。但是由于夏代还没有发现确凿的文字记载,又缺乏判断早期国家的科学标准,使得从考古遗存来分辨夏成为争议极大的问题。现在学术界对夏存在五种不同的看法,几乎涵盖了所有的可能性,所以也就等于没有结论。对于前国家形态的社会也倾向于从典籍的记载来加以辨认,比如,将这些社会称为“方国”或“古国”,或统称为“五帝时代”。由于这些社会都缺乏文字的记载,所以对它们的研究也必须要有理论的眼光,否则这种研究也只能停留在想当然的猜测之上。
目前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的早期文明犹如漫天星斗。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三星堆文化、齐家文化等都是形态各异、复杂程度有别的酋邦社会。我国传统的考古学研究完全根据物质遗存来进行分析与比较,将各种考古遗址命名为不同的考古学文化。用酋邦来分析这些史前的复杂社会,可以为考古学分析引入“社会”的概念。换言之,中华大地上的史前文明可能经历过不同的发展轨迹,有不同的物质文化,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但是这些复杂社会演进的层次和的社会动力可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酋邦作为一种分析概念,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文化特征的比较来了解前国家的社会形态,并探究这类社会如何向国家演进或者崩溃瓦解的原因。
在酋邦概念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检验和完善有关早期国家的理论概念,这是我们从文献和考古发现中认识早期国家形态和了解远古文明发展历程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只有从科学理论上确定了酋邦的社会形态以及什么是早期国家标准,我们才能够从物质形态上来探讨它们的存在和分辨它们之间的差异。
四、小结
将当代社会人文科学理论和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工作相结合有两方面的意义。第一,将中国传统史学和考古学研究用现代科学理论武装起来,使我们传统学科变得更严谨更科学,并能够增强我们对古代社会发展本质的了解。第二,用中国的史实和考古材料来检验社会科学的一般性理论,使中国的文明与国家探源跻身世界学术之林。
对于社会科学理论与国家探源的关系,弗兰纳利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说,哺乳动物原来是由动物学家所定义,于是古生物学家可依此来分辨它们的骨骼。国家最初是由社会人类学家和政治学家所定义,于是考古学家才能据此来分辨其结构的形态。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理论的规律性认识,是考古学家具体研究设计的向导,以及从物质遗存来判断社会发展层次的科学依据。我国史籍中虽然有朝代和国家的称谓,但是它们毕竟和现代科学意义的早期国家并不相同。缺乏理论提供的依据就像是缺乏“按图索骥”的标准,结果,我国的史学和考古学界在对二里头遗址是否是夏墟的探讨就难免变成一场缺乏共识的毫无结果的纷争。因此中国学者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在坚实社会科学理论基础上的国家定义而不是典籍中的线索,才是指导我们从史料和考古资料来判断中国早期国家的标准。
再有,国际学术界从文明与国家探源中归纳出来的社会科学一般法则,只有经过中国史实的考验才可能具备世界意义。然而,中国学者自古以来便作茧自缚,以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外国有的,中国都有,只要研究中国就行了。于是,在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舞台上,中国学者自己选择了边缘化的位置,自甘被弃于主流之外。为了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张光直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的三部曲:(1)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学科主流的核心问题;(2)研究中国的案例能否对全人类的问题做出新贡献;(3)一定要用世界性学者能看懂的语言把自己的贡献写出来。
张光直还指出,将中国国家文明探源置于世界背景中去审视,可以得出两项重要结论。第一,中国的早期国家和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具有相似的起源动力。第二,中国早期国家的特点与西方社会科学所确立的某些通则不合,西方社会科学描述的古代国家表现为亲族制度式微、政教分离、文字的产生是为了记录商品的流通。但是中国的早期国家与此迥异,亲族制度与国家制度紧密相连,政教没有分离,文字最初的使用也和商品流通没有很大的关系。为此,张光直认为拥有丰富史料和考古材料的中国对世界社会科学做贡献的潜力是无可限量的。然而,中国学者若要对社会科学做重大贡献的话,头一件事就是要把当代的社会科学学好。中国史料中与社会科学有关的种种真理,不是不言自明的,也不是闭关自守的学究所能发掘出来的。如果能够做到这点,那么21世纪的社会科学可能是中国的世纪。
要做到这点委实是任重而道远,这首先需要我们跳出圈子、克服成见、放下架子,老老实实从头学起。文明与国家探源是中国能够为世界社会科学做出贡献最有潜力的一个领域,但是像奥运会零的突破一样,我们的成绩若要得到世界公认,就必须遵循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这种贡献既不是用现代科技来考证典籍中的史实,也不是我们对社会科学理论生搬硬套或一知半解的发挥,而应当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成就上的全新创造和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
来源:《中国学术》2003年第2期。
- 0000
- 0004
- 0000
- 0000
- 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