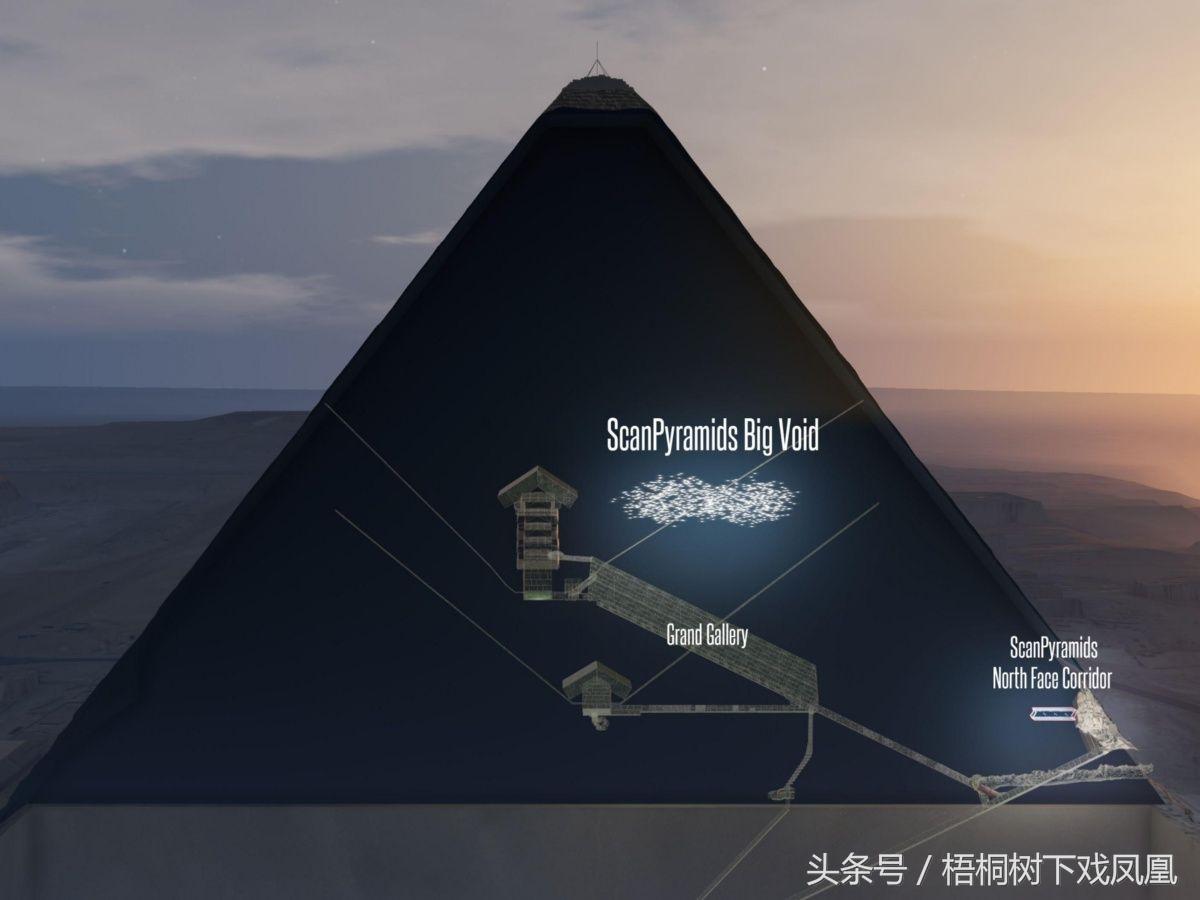霍巍: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的回顾与展望
从现代学术视野而论,由于西藏在自然景观与文化面貌上的独特性,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人们对不同地区人类文明进程、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等诸多方面的人文关怀不断提升,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成为全世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而言,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实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除了前述有关学术史上的重大转折之外,在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组织管理层面,也同样体现出这样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各个方面:第一,在国家严格的管理机制下,田野考古工作从过去的地面调查开始转为深入而有计划的地下田野发掘;第二,通过有计划地组织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初步形成了对从史前时期到西藏各个历史时期文化遗存基本框架和分布格局的学术认识;第三,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的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以及相应的政策法规体系;第四,开始建立形成一支专业化的文物考古管理机构与学术队伍。这些成绩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认同。
当我们回顾这些成绩的时候,不能不提及对于实现这个历史性转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西藏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具有奠基之举的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这项工作已经先后三次在西藏全区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部署,西藏自治区政府和相关文物部门对此高度重视并做了相关的动员、组织,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考古重大工程。从学术史的视野对其进行回顾与展望,具有特别的意义。我曾有幸参加了第二次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1990—1992年),作为一名曾经在西藏的山山水水之间度过难忘考古岁月的考古工作者,更是深有感慨,将这三次文物普查视为西藏文物考古史上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壮举,可以说毫无疑义。
(一)西藏文物普查工作既往史
对于西藏自治区境内的文物古迹进行综合性的调查,早在西藏和平解放之初便已经列入党和国家的宏观文化规划之中。1959年6—11月,中央文化部组织西藏文物调查小组,赴西藏拉萨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等地进行有系统的文物调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次调查工作也具有对西藏局部地区进行普查,从而获取典型经验的含义在内,期望此次工作所总结出的经验能对以后西藏全区的文物调查工作产生指导性意义。这一点,从参加这个调查小组的成员的身份和专业背景上便可以看出。他们当中,既有著名的考古学家,也有精通藏文及藏族历史的藏学家和历史学家,这种组合为后来西藏开展的第一次全区文物普查也提供了借鉴。在当时复杂而特殊的历史环境下,由于国家及时组织力量赴藏开展了科学的调查记录工作,才使得西藏许多重要文物古迹的原貌得以流传后世。
这次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西藏区域性文物普查工作获得了一批丰富资料,也形成了一批学术成果。例如,调查组的其中一位成员——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宿白教授根据他此次赴藏实地调查所获的第一手资料,先后撰成了《西藏拉萨地区佛寺调查记》《西藏山南地区佛寺调查记》《西藏日喀则地区寺庙调查记》等系列研究论文,并最终汇集成《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这部学术专著,由此开创了中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的先河,在国内外学术界均产生了重大的学术影响。调查组的另一位成员王毅则将其调查情况撰成简报《西藏文物见闻记》,在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主办的学术期刊《文物》月刊上连载,使国内外学术界对西藏文物的认识无论是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都提高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新层面,意义也十分重大。可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西藏文物考古事业,正是由这些前辈学者们奠下了最初的基石。
这次调查工作从学术层面来看也有值得总结的经验。据后来当事者的回忆,由于没有进行严格细密的学术分工,所以照片与文字材料并没有统一进行编目收存与建档,除了宿白教授在出版的《藏传佛教寺院考古》这部著作中使用过部分西藏寺院壁画与雕塑的照片之外,大量照片资料尚未公开发表。后来宿白教授曾经问及这批西藏调查资料当中照片的去向,曾长期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过的侯石柱(现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工作)回忆,似乎在整理该所图书资料时看到过一批西藏的文物资料照片,宿白教授当即判断这批照片很有可能便是当年由王毅拍摄保存下来的那批照片,并且建议应当尽快加以整理出版。
在这次调查之后,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藏较大规模的文物普查工作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重新拉开序幕。1984—1985年间,根据国家文物局的统一部署,在西藏自治区境内开展了第一次文物普查工作。这次文物普查工作主要由陕西省文物部门派员进藏,与当地藏族文物考古干部联合组成文物普查队,队伍往往分成若干个小组,每个小组内由一名藏族干部、一名调查所在地的当地藏族干部和二至三名汉族考古工作者加以组合,这种组织结构的有利之处在于既可以充分发挥藏族干部没有语言障碍、熟悉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便于与当地群众沟通交流以获得文物点线索的优势,又可以让专业知识与技能较好的汉族考古工作者对藏族业务干部起到传、帮、带的作用,事实证明这种组队方式是行之有效的,也被后来的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所沿袭。
第一次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实际上也并未在全区展开,而是选择了一些重点地区开展工作,某种意义上仍具有试点的性质。这次文物普查主要调查的区域有拉萨市,山南地区的乃东县、琼结县、扎囊县以及阿里地区的札达县、普兰县等,在工作的深度与广度上均在过去的基础上有重大的突破,有关情况从这次文物普查形成的一批重要文献资料中可见一斑。其中,最主要的成果有由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印的内部资料《拉萨文物志》《扎囊县文物志》《乃东县文物志》《琼结县文物志》。在这批地方文物志当中,按照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与摩崖造像、文物藏品、革命文物、风景名胜地等编排体例对文物普查中所调查发现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公布,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研究意见。此外,在《文物》1985年第9期上,刊载了一组共十五篇论文与考古调查简报,其中所涉及的考古材料大多为此次文物普查中的新发现资料,时代从新石器时代、吐蕃时代直到元、明、清各个历史时期,内容广泛涉及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院、碑刻、印章、古刻本、灵塔建筑、宗教文物等各个方面,可视为将此次文物普查中的精华部分对外展示公布。1985年对阿里地区的文物普查主要集中在以古格王国时期的都城札不让为中心的古格时期建筑遗址的考古调查上,其调查成果反映在1991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古格故城》一书(分为上、下册)中,这是我国学术界对古格王国遗址最为全面、系统、科学的一次调查后形成的学术成果,也是这次文物普查形成的最为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
在第一次文物普查结束之后,时隔五年,西藏全区第二次文物普查再次揭开了帷幕,于1990—1992年三年间实施进行。这次文物普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第一次文物普查的继续,在组队方式上,也采取了与第一次文物普查相同的办法,即将我国其他省份文物考古研究机构和大学的专业人员、西藏自治区当地的文物部门业务骨干以及当地藏族干部组合成调查小组,来自其他省份的汉族考古工作者除陕西省外,还新增加了来自湖南省和四川大学的专业人员与教师。此次文物普查的工作范围几乎涉及西藏各个地、市、县(包括当时尚未通车的察隅县、波密县),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西藏全区文物普查。与过去开展的类似工作相比较,此次工作组织得更为严密规范,通过对西藏全境地上、地下文物进行的全面调查,基本上掌握了西藏自治区各类文物、古迹以及重要考古遗址的分布状况,对当时已查明核实的具有重要科学价值的遗址与墓葬,都做过不同程度的试掘清理,从而获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资料。这些新的考古材料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西藏历史时期,时代跨度几乎包括了西藏史前时期一直到后来的各个历史阶段,内容广泛涉及旧石器时代遗存(包括打制石器地点)、细石器地点、新石器时代遗址、大石文化遗迹、古代岩画、古墓葬、佛教寺院及石窟寺遗址、摩崖造像、古代城址等,无论是在地域分布范围上还是在材料的丰富程度上,都超越了以往在西藏文物考古领域所做的工作。
此次文物普查工作形成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成果,首先可举出的是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西藏地方文物志丛书”,这套丛书现已出版《吉隆县文物志》《阿里地区文物志》《昂仁县文物志》《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亚东、康马、岗巴、定结县文物志》等分县文物志,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县文物普查的成果;其次,由四川大学编辑出版的《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西藏考古专辑》(1991年)和《西藏考古》第1辑(1994年),也是对此次文物普查所获资料及其研究成果的初步总结;再次,由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两部大型资料性画册《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和《西藏岩画艺术》,则是其中专题性的学术资料结集;最后,利用这些调查资料还形成了一些学术研究专著,如霍巍的《西藏古代墓葬制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李永宪的《西藏原始艺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柴焕波的《西藏艺术考古》(中国藏学出版社2000年版),都是建立在这几次文物普查资料基础之上的部分研究成果。
综上所述,通过1959年到1993年间前后三次规模不等的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初步建立起了今天西藏文物考古的基本框架,也逐步形成了今天对于西藏古代文化(尤其是没有文字记载的西藏远古文化)面貌的基本认识。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评价指出:“从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学者开始独立自主地承担起西藏考古工作的重任,陆续开展了一系列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这个阶段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可以说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西藏考古学的初建时期。”西藏文物考古事业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是和由中国汉、藏两个民族共同承担的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所奠定的坚实基础密不可分的。
(二)西藏文物普查工作的学术史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回顾总结西藏的文物普查工作,我认为它对于西藏的文物考古事业具有奠基性的意义,并且成为有史以来西藏文物考古工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这个评价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得以体现。
第一,正是通过文物普查的若干考古发现,才建立起西藏考古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线索,补充了其中的若干重要环节与链条,形成较为完整的时空体系。
从历史上看,由于西藏在政治、宗教、文化上的许多独特性,虽然过去有少数外国人曾经获得特许进入西藏进行有目的的考古工作(如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但绝大多数西方学者要在西藏从事考古发掘工作也是极其困难的。因而,西方学者在西藏开展的工作即便具有开拓性质,但也十分有限,大多仅限于零星的地面调查和对一些寺院宗教文物的考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并不多见。所以直到20世纪的后半叶,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教授仍然评价认为:“如果我们把适当的、有指导的发掘称为考古学的话,那么,西藏的考古是处于零的状态。”与祖国其他省份相比较,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展也相对滞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国大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基本的考古学年代谱系以及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时候,西藏的科学考古工作以藏东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的发掘为标志,才刚开始起步。如果没有西藏全区文物普查获取的宝贵资料,西藏有实物史实可以证明的发展历史将会大大延后并且有若干缺环无法弥补。尤其是其中西藏史前社会的状况及其发展进程,在过去的汉文和藏文历史文献中要么史实缺载,要么充满着虚无缥缈的传说色彩,很难作为信史,但是通过文物普查中对西藏从旧石器时代一直到新石器时代不同考古学文化面貌的了解,早期人类对于西藏的开发与拓殖的历史图卷才开始变得鲜活生动、真实可信起来。以今天的考古材料来重构一部西藏史前史,已经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们正在共同着手进行的一项宏伟工程。
第二,正是通过文物普查工作,研究者在对事物的认识方式上从过去以“地表考古”为主体转化为以“地下考古”为主体,使材料的科学性大大增强,精确度大大提高。
以往在西藏开展的田野调查工作多局限于地表的观察与地面文物的采集,由于没有进行科学的考古试掘工作,缺乏地层学资料的支持,所以许多资料的科学性和精确性都因此大打折扣。在文物普查过程中,考古学工作者有所选择地对各类考古遗存进行了适度的田野考古发掘,对它们的性质、年代、文化内涵等各方面的认识都从此建立在科学的考古学地层学、类型学基础上。这里,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证来加以说明。
例如,山南琼结县境内的吐蕃王陵(俗称藏王墓)的研究,历来为西方学者所关注,对其所做的勘测与考证工作也开始得较早,意大利学者杜齐曾发表过专著《吐蕃赞普陵考》,利用大量文献材料对陵墓的内部构造、陵墓石刻、墓地布局、各墓墓主等问题做过详细的考证。其后德国学者霍夫曼、英国人黎吉生等人也对藏王墓发表有研究意见。可以认为,西方学者对藏王墓所做的调查与考证是他们在西藏所进行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具有代表性的项目。但尽管如此,长期以来关于藏王墓的确切数目及各墓墓主的考订始终还是比较混乱,说法各异,莫衷一是。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我国学者开始对藏王墓进行实地考察,在西方学者的研究基础上虽有新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还是没有突破地表观察与文献比对这种传统的方式。对包括藏王墓在内的吐蕃时期墓葬内部构造的探讨,也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由于缺乏考古材料,大多数学者都只能根据一些藏文史书的记述对藏王墓的内部情况进行推测,如想象“松赞干布墓有九座或五座墓室,设计为方形。中间墓室安放着一口镀金的银棺材,内装尸体。四周摆满了藏王生前使用过的各种物品”,等等,这些情况如果不进行考古发掘,则根本无法加以证实。近年来,中国学者通过对不同形制、不同等级的墓葬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逐步了解到吐蕃时期不同类型墓葬的内部结构、建筑技术、器物随葬制度、动物殉葬习俗、特殊的尸体处理方式、本教与吐蕃丧葬制度的关系等情况,并且对吐蕃墓葬的考古学断代、分期、排年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探索性工作,配合青藏铁路建设在拉萨河谷清理发掘出土的吐蕃时期的大型墓葬,更是进一步推进了对于高级贵族墓葬内部形制构造的认识。这些工作,为最终了解包括藏王墓在内的各类吐蕃墓葬的内部构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以说在杜齐等西方学者工作的基础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尤其是近年来通过实地调查,我国考古学工作者利用GPS、GIS、卫星和航空照片等先进的图像技术手段与地面实地勘测相结合,较为准确地核实了藏王墓陵区内现存陵墓的数量,首次确认了藏王墓由东、西两个陵墓区并列组成的布局特点,并且认识到这个特点与《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西藏王统记》等藏文古籍的记载是基本吻合的,这些成果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一些传统的认识,取得了显著的学术进展。
第三,正是通过文物普查工作,我国考古工作者全面掌握和了解了西藏全区地面与地下文物的总体情况,为进一步开展科学研究和实施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奠定了基础。
在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工作开展之前,在西藏所进行的考古调查和发掘都带有极大的随机性和偶然性,实施科学的保护规划更无从谈起。全区文物普查的成果初步摸清了“家底”,为这些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依据。例如,近年来西藏自治区境内所公布的许多国家级、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来自全区文物普查获取的线索和具体资料;许多重大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也都是基于全区文物普查的前期工作。通过全区文物普查所奠定的工作基础,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和高校与西藏自治区文物部门联合组队,有目的、有重点地开展了一些具有科学研究性质的田野考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这当中如吉隆哈东淌、却得淌旧石器地点的调查与发掘,雅鲁藏布江流域细石器与打制石器地点的发现,曾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的拉萨曲贡史前遗址的发掘,西藏西部阿里高原石丘墓、大石遗迹、岩画的发现与发掘,阿里古格故城以及托林寺的调查清理,阿里皮央·东嘎佛教石窟寺与佛寺遗址的调查与发掘,吉隆《大唐天竺使出铭》的考古发现等一系列近年来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考古工作,都是在全区文物普查之后才有计划地开展起来的,有关的工作情况我曾经有过评述,在此不一一列举。
曾经有学者指出:“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19世纪中期以来的近代化进程到20世纪开始加速,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历史性转换。学术研究是一个时代社会文化的构成部分,同样经历、体现着这种历史的变化。”如上所述,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回顾和总结,我们可以看到,西藏文物考古工作从20世纪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转折,如果说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将它划在20世纪以来西藏全区文物普查前后,这实际上也是西藏社会历史随同祖国现代化步伐发生伟大变化的一个必然进程。
(三)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如前所述,既往的西藏文物普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了它在学术史上的重要意义之外,从行政组织与工作实施的角度而论,也有许多成功的经验,这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总结。这里,我仅仅以个人的亲身感受,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1.严密的组织构架是文物普查获得成功的首要前提
第二次西藏文物普查工作由于得到各级领导部门的高度重视,在行政领导与具体实施的层面是高效有力的。这当中,严密的组织构架是成功的前提。当年由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成立文物普查领导小组,由主管文物的副厅长任领导小组组长,下设有办公室(办公地点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所在地罗布林卡内),领导小组的成员由文化厅主管领导、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文化厅文物处处长以及当年普查所在区域行署副专员等组成,领导小组对全区文物普查实施全面领导与组织协调工作。在领导小组之下,再划分为各个调查小组,由汉族专业人员与藏族业务干部联合组队(详见前述),分片包干负责若干个县、市的文物普查工作。在调查过程中,领导小组穿梭巡视于各个调查小组之间,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各种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与问题,并与当地政府部门沟通协调,保证普查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率领的一个文物普查小组在日喀则昂仁县布马村调查发掘古代墓葬时,不料遇到天降冰雹和大雨,当地群众由于缺乏科学的考古知识,认为这是调查队发掘古墓“惹怒老天”从而造成的后果,群众情绪对立,考古工作一度陷入瘫痪状态。在这个困难时刻,领导小组闻讯后即刻赶赴现场,由藏族干部出面向当地群众讲清道理,传播科学知识,消除他们的误解和对立情绪,使事情很快得以解决,考古工地恢复了正常的发掘,此次调查发掘工作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仅如此,调查队员们还与当地干部群众建立起深厚的友谊。
2.在文物普查过程当中,建立通畅及时的信息交流十分重要
由于当时西藏的通信条件还十分落后,为了确保各调查小组之间保持通畅的信息交流,由领导小组编印了《西藏文物普查工作简报》,及时地将各调查小组取得的重要成果、工作经验等进行总结发布,这一做法不仅起到了互通情报的作用,各组之间取得的考古调查成果也产生了彼此激励、相互启发的效果,促进了工作热情的提高,无形之中形成了各组之间的工作竞赛,大大提高了普查工作的效率和普查队员们的工作责任心与高昂的斗志。这些油印的工作简报成为当时调查队交流普查工作的重要渠道,也成为向各级政府和领导部门进行宣传汇报的有力工具,至今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3.及时总结提炼田野普查所获资料,形成科学的学术成果
第二次全区文物普查在工作程序的安排上也比较合理,充分注意到将田野调查与室内整理紧密结合的科学规程。当时在时间安排上大体上是每年的4—8月在野外开展调查发掘,9—12月返回营地进行资料整理。由于两个阶段前后紧密衔接,在田野调查中所留下的记忆还比较清晰深刻,所以形成的文字资料内容也相对更为丰富、准确,可以弥补文字记录方面的不足。前述已经公开或非公开出版的西藏各县《文物志》当中的条目,基本上都是在田野普查工作结束之后不久便形成的。除此之外,在文物普查从整体上告一段落之后,领导小组还及时组织参加调查工作的专业人员开展相关综合研究,提升对原始资料的认识水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此形成具有一定深度或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研究论著。现在看来,迄今为止在文物普查中所形成的这批学术成果,如果没有当时组织领导者们的远见卓识,及时要求对田野调查所获取的原始材料进行初步的整理与研究工作,恐怕有相当部分会随着人员变动和岁月流逝而有程度不同的散失,造成人力和资源的极大浪费,使许多工作不得不重走回头路或者弯路。
4.形成汉藏团结的队伍,结成永恒的民族情谊
如前所述,由于在文物普查中采取了由区外业务人员与区内业务干部联合组队的方式,队伍中汉、藏两个民族的考古工作者在普查工作中紧密团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结成了深厚的情谊,同时也确保了普查工作能够高质量地完成。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从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培养了第一批藏族文物考古专门人才,在西藏文物普查工作中,这些藏族业务干部勇于吃苦,熟悉当地风俗习惯,语言交流通畅,适应高原环境,给予进藏工作的区外汉族专业人员生活上、工作上的多方面帮助与关怀;区外进藏工作的汉族业务人员专业素质较高,具有较为丰富的田野考古工作经验,也给予藏族同行许多业务上的指导与帮助。在前后两次近十年的文物普查历程当中,他们情同手足,相濡以沫,建立起深厚的感情,至今这些老队员们都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文物普查期间,在他们当中曾经发生过许多令人难忘的事情。例如,1990年,在山南地区某县境内承担文物普查工作任务的一个工作小组由于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全队几乎无一幸免,尤其是队内的藏族驾驶员吐血不止,生命受到严重威胁。在这危急关头,来自湖南省文物局、时任该小组组长的何强临危不乱,不仅做出了恰当的紧急处置,而且在当地一时无法找到驾驶员的情况下,抱病冒着危险驾车连夜将这位危重病员送到距普查地点近100千米以外的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由于处理及时,这位藏族驾驶员终于转危为安。从此之后,他们之间结下来的深厚友谊绵延至今。
总之,西藏文物普查留给我们许多成功的经验,这些经验直到今天来看也仍然具有其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在即将开始新一轮的西藏全区文物普查之际,适时地总结这些经验,我相信将有助于未来的工作。当然,在过去的工作当中也有一些值得汲取的教训,如在后期的资料整理与汇总阶段,由于人事上的变动和相关生活待遇方面出现的一些问题未能得到及时解决,也曾导致部分文物普查资料的回收出现延误与流失的现象,这些教训都应当在今后的工作中通过建立健全更加科学化、人性化的管理制度与手段来加以合理地规避。
我们高兴地看到,进入21世纪,西藏的文物考古工作又将迎来它新的发展高潮。今天西藏自治区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文物考古机构,有了一支由藏汉两个民族的年青一代文物考古工作者组成的专业队伍,西藏自治区各级领导和文物管理部门对于全区文物考古工作的重视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在人力和财力上的投入也达到空前的规模,这些条件都将为新一轮全区文物普查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作为一名曾经参加过西藏文物普查工作的文物考古战线上的老兵,我也衷心祝愿西藏全区文物考古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谱写西藏文物考古事业新的篇章!
来源:霍巍:《青藏高原考古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
- 0000
- 0000
- 00055
- 0000
- 0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