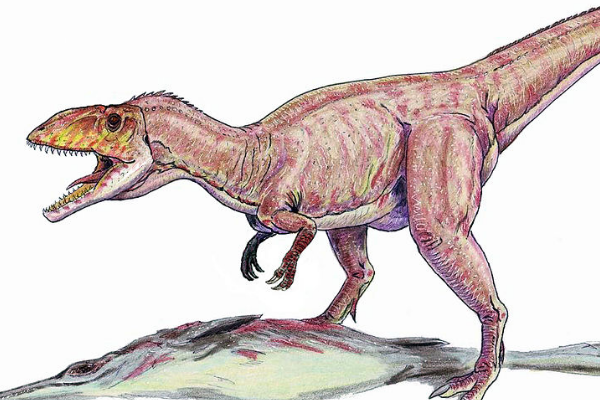竺可桢:科学之方法与精神
近代科学的起源在西洋亦不过三百年前的事。在十六世纪以前,一部《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控制了欧洲人的一切行动与思想。这时候欧洲的人生观,以为宇宙内一切乃上帝所创造,人为万物之灵,地球在宇宙之中,日月五星及恒河沙数的星宿,统统绕地球而行。凡是怀疑这类人生观,以为违背《圣经》和亚里士多德之主张者,就是大逆不道。从公元二世纪以迄十六世纪,“地球为万物中枢说”成了牢不可破的信仰,无人敢置一词。直到十六世纪初波兰人哥白尼始创了“日为中枢”说。当时宗教和神权势力弥漫全欧,哥白尼《天体的运行》这部书,到他去世才敢出版,但哥白尼并没有确实证据,可以打破地球为万物中枢的学说,他断定地球绕太阳而行,是一种推想,一种理论。推翻“地球为万物中枢”的学说,掀起欧洲思想界革命,全靠十六、七世纪几位先知先觉的科学家。其中最重要的四位是开普勒、培根,伽利略和牛顿。
在叙述上面几位科学先驱的工作以前,不得不一讲近世科学的方法。所谓科学方法,就是科学上推论事物的分类。亚里士多德分推论为三类,就是(1)从个别推论到个别。如说这物有重量,就推想到那物也有重量,这称类推法。(2)从个别类推到普遍。如说这物有重量,那物也有重量,就推论到所有对象统有重量,这称归纳法。(3)从普遍推论到个别。假如我们断定万物统有重量,就推论到某一物亦必有重量,这称演绎法。这三种推论中,第一种用不着多少理智,而第二、三种却因为有概括的观念,必须用理智。高等动物如猫、狗之类,和年幼的小孩,统能类推,但不能演绎或归纳,这其间的分别,十九世纪英国哲学家米尔已经指示我们了。科学方法可说只限于归纳法与演绎法。以大概而论,数学上用的多是演绎法。而实验科学如化学、生理等所用的多是归纳法。二加二等于四,二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统是显而易明的原则,从这原则可以推论到个别的事物。亚里士多德和千余年来他的信徒,均应用演绎法以推论一切。这种方法一推论到数目字以外,天然复杂现象,即有困难。如亚里士多德以为天空星球皆为天使,必能运动不息而循正轨,惟运行于圆周上,始能循环不息。从上两项原则,因得结论,所有星辰的轨道必为正圆的圆周。亚里士多德的信徒断定日月五星等各循一正圆圆周以绕地球,就是从这样演绎法推论得来的。最初主张用归纳法的人,要算培根。他并主张观测以外加以有系统的试验,详尽的记录,梓行出版,以公诸世,此即培根之所谓新法。培根虽提倡归纳和实验,但他自身并未实用。首先用归纳法来证明亚里士多德错误的,是开普勒。他的老师第谷,在丹麦和波兰天文台尽毕生之力,测定星辰的位置。第谷死后,开普勒继续他老师的工作。从他们师生三十多年所观测火星的位置,决定火星的轨道,绝非为正圆而为椭圆。太阳并不在轨道中心而在椭圆焦点之一。这才使开普勒怀疑亚里士多德的不足恃,而成为哥白尼日为中枢说的信徒,开普勒的行星运行的三大定律,不久也就成立了。
同时在当时科学的发源地意大利,伽利略正用自造的望远镜以视察天体,发现了木星之外有四座卫星,和金星之有盈亏朔望,与古代传统学说,全不相符。他在比萨塔上的试验,更是轰动一时的。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凡事物自空中落下,重大者速而轻微者缓。伽利略的试验,证明了一磅重的铅球和一百磅重的铅球,从179公尺高的塔顶落下,是同时到达地面的。伽利略的试验不但证明了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而且发现物体下降时之加速度是有一定规律的。这类收获完全是归纳法和应用实验的成效。牛顿更进一步,在1682年将开普勒的行星运行的三条定律和伽利略的动力定律综合起来,成立了万有引力的定律。亚里士多德许多学说之不足信,和地球为万物中枢学说之不能成立,到此已无可疑义了。二千年来传统思想的遗毒,到此应可一扫而空。不过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一样,要收效果必得要相当年代。从哥白尼的《天体的运行》一书问世(1541年)迄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成立,中间经过了141年,欧洲人的宇宙观可说到此才拨云雾而见青天,近世科学的基础亦于此时奠定了。
近世科学又称归纳科学或实验科学,但是科学家从事工作,演绎法与归纳法必得并用。有许多结果,一定要用演绎法才能得出来。譬如讲到日蚀的预告吧,从归纳法我们可以断定一个不透明的物体,走到一无光体与有光体之间,则无光体上必将投有黑影。但是几百年以前天文学家就可以算出1941年9月21日中午左右我国沿海从福建福鼎一直到西北兰州、西宁这一条线上,统可以见到日全蚀,那是要应用演绎法算出来的。又如开普勒何以能知火星轨道非正圆而为椭圆,牛顿何以能从开普勒的三条定律,来发现万有引力定律,这都是从演绎法得来的。相反,数学上有许多简单方程式,如甲加乙等于乙加甲,须得用归纳法来证明的。从此可以晓得近世科学,须是归纳演绎二法并用,才能收得相得益彰之效。至于有计划的实验,是归纳法最有效的工具,而为我们中国所没有的。实验和单纯的观测法不同。单纯的观测是要靠天然的机缘,譬如日全蚀,我国黄河、长江流域从明嘉靖二十年(公元1542年)以来,到如今没有见过,四百年来本年是破天荒儿第一遭。若是全靠天然的机遇的话,天文学家要等四百年之久,不然就得跑遍全球,但至多也不过隔二、三年才见到一次。天文学家往往跋涉数千里以求得几分钟的观测,遇到日全蚀的时候,刚巧阴翳蔽日,颓然而返,这是常有的事。自从前数年李侯发明了日冕仪后,日全蚀可以用人工制造了。人为的实验,不仅可以将时间次数随意增加,而且整个环境亦可以操诸吾人之手。譬如要证明疟疾是蚊子传带来的,我们一定要控制环境,使我们不但能确定所有生疟疾的人统曾经某一种疟蚊咬过,而且要晓得疟蚊所带的细菌,从蚊子身上传到人身血液中的循环,发育的步骤,和对于病人生理上的影响。惟其这样,才能断定病的来源,对症下药。自从十九世纪中叶帕斯德、科克几位细菌学专家把几种重要的传染病祸根弄清以后,接着李斯德发明消毒方法,以及近三、四十年来人造药品的发现,欧美人口的死亡率大为减退。美国人在华盛顿时代平均寿命36岁,1850年为40岁,1900年48岁,到1940年便增到65岁,英、法、德各国近百余年来平均寿命亦有同样的增进。若是我们相信寿长是一种幸福的事,那这就是实验科学对于人类幸福最显著效果之一了。
但是提倡科学,不但要晓得科学的方法,而尤贵在乎认清近代科学的目标。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变,这科学目标,蕲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了解得科学精神是在蕲求真理,吾人也可悬揣科学家应该取的态度了。据吾人的理想,科学家应取的态度应该是:(1)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但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2)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3)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这三种态度,我们又可用几位科学先进的立身行己来证明的。
在十六、七世纪地球之万物中枢学说之被推翻,是经过一番激烈的论战,牺牲了多少志士仁人,才能成功的。公元1600年布鲁诺因为公然承认哥白尼太阳为中枢的学说,而被烧死于十字架上,即其一例。伽利略为了撰写两种宇宙观的论战一书偏袒了哥白尼学说,而被罗马教皇囚禁于福禄林,卒以古稀之年,失明而死。开普勒相信太阳为中枢之说,终身贫乏,死无立锥之地,这是近代科学先驱探求真理的代价。这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精神,和我们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很相类似。认定了革命对象以后,百折不挠,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种求真的精神,明代王阳明先生亦曾剀切言之。他说道:“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他与陆元静的信里,又曾说道:“昔之君子,盖有举世非之而不顾,千百世非之而不顾者,亦求其是而已,岂以一时之毁誉而动其心哉。”此即凡事以理智为依归之精神也。但阳明先生既有此种科学精神,而何以对于近世科学一无贡献呢?这是因为他把致知格物的办法,完全弄错了。换言之,就是他没有懂得科学方法。他曾说:“众人只说格物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说用去。我着实曾用过功夫。初年与钱友同论作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去格看。钱子早夜去穷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力至于三日,便致劳成疾。当初说是他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穷格,早夜不得其理,七日亦以劳致疾。遂相与叹圣贤是做不得的。无他大力量去格物了。”从现在看来不懂实验科学的技巧,专凭空想是格不出物来的。但是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比,则方法易于传授,而精神则不可易得。阳明先生若生于今世,则岂独能格竹子之物而已。科学家的态度,一方面是不畏强御,不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但同时也不武断,不凭主观,一无成见,所以有虚怀若谷的模样。世称为化学鼻祖的波义耳说,他真却能知道的东西,可说是绝无仅有。有人问牛顿,他在科学上的发明哪一件最有价值。他答道在自然界中,他好像是一个小孩,在海滨偶然拾得一块晶莹好看的石片,在他自己固欣赏不释手,在大自然界,不过是沧海的一粟而已。但是有若干科学家的态度,并不是那么虚心。十九世纪末叶英国物理学家的权威凯尔文就是一例。在那时凯尔文与其侪辈以为物理学上重要的理论与事实,统已大体发现了。以后物理学家的工作,不过是做点搜残补缺而已。他自认为生平杰作地球年龄这篇论文里,他以太阳辐射的力量,来估计太阳和地球的年龄,若是太阳里面发热的力量和煤一样强,地球的年龄至多也不得过四千万年。当时地质学家以海水所含的盐分地面上水成岩的厚度来估计,生物学家以动植物进化的缓速作估计,统以为地球年龄非数万万年不为功。凯尔文很武断地把他们的论断加以蔑视。到了1895年伦琴发现了X光线,1898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不久物理学上大放光明,新发明之事实迄今不绝。距近来物理学家的估计,原子的能力,若能利用的化,要比同量的煤大五百万倍。所以地球的年龄可以尽量的延长,而凯尔文的估计,不得不认为错误了。
妄自尊大的心理,在科学未昌明时代,那是为各民族所同具的。我们自称为中华,而把四邻的民族,称为南夷、北狄、东夷、西戎,从虫从犬,统是鄙视的意思。欧西罗马人亦有这类轻视傲慢的态度,到如今欧洲民族中尚存有斯拉夫、赛比亚等名称,这在古代文化先进的民族藐视后知后觉的民族,夜郎自大,并不足怪。但在人类学已经昌明的今日,竟尚有人埋没了科学的事实,创为优等民族的学说,如德国纳粹领导下所提倡的诺提种学说,而若干科学家尚起而附和之,则是大背科学精神了。
科学家的态度,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近代科学工作,尤贵细密,以期精益求精,以我国向来文人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却相反。这于我国古代科学之所以不能发达,很有关系的。如以诗而论,诗人之但求字句之工,不求事实之正确,我国向来司空见惯不以为奇。如杜工部古柏行“孔明庙前有古柏,柯如青铜根如石,双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想来杜甫生平不曾用过量尺。又唐人钱起诗“二月黄莺飞上林”。唐代首都在长安,黄莺是一种候鸟,至少要阴历四月底才到长安,这句诗里的景色,无疑是杜撰的。唐诗如此,现代的诗何尝不如此。诗固然要工,但伟大的作品,无论是诗文、音乐,或是雕刻,必须真善美三者并具。法国科学家邦开莱说道,“唯有真才是美”。照这样的标准看来,明、清两代的八股文没有一篇可称美的。我国八股遗毒害人不浅,到如今地方政府做户口农产的调查,各机关的地图测量,往往是向壁虚造敷衍法令,尤是明清做八股的态度。这种态度不消灭,近代科学在中国绝无生存之理。试看西洋科学家态度何等谨严,卡普勒的怀疑亚里士多德,只在火星轨道不为正圆而为椭圆,在中国素来就没有这种分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1665年已胸有成竹了。可是因为那时地球经纬度测量的错误,以为每度只有60英里。因此他估计地球直径只有3436英里,而地球吸引月亮之力只有每分钟13.9英尺,而非理想上每分钟应有的16英尺,所以他就不敢发表。直等到1682年法国人皮卡德测定地球上一度的距离为69.1英里,使牛顿所估计地球吸月亮之力正与其理想相吻合,他才敢把万有引力的定律公诸于世。所幸近年来教育注重理工,受了科学训练洗礼的人们,已经慢慢地转移风尚。各大学研究院科学作品固希望其多,而尤希望其能精。因唯有这样,才能消灭我们固有的八股习气,亦唯有这样,才能树立真正的科学精神。
- 0000
- 0000
- 0002
- 0000
- 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