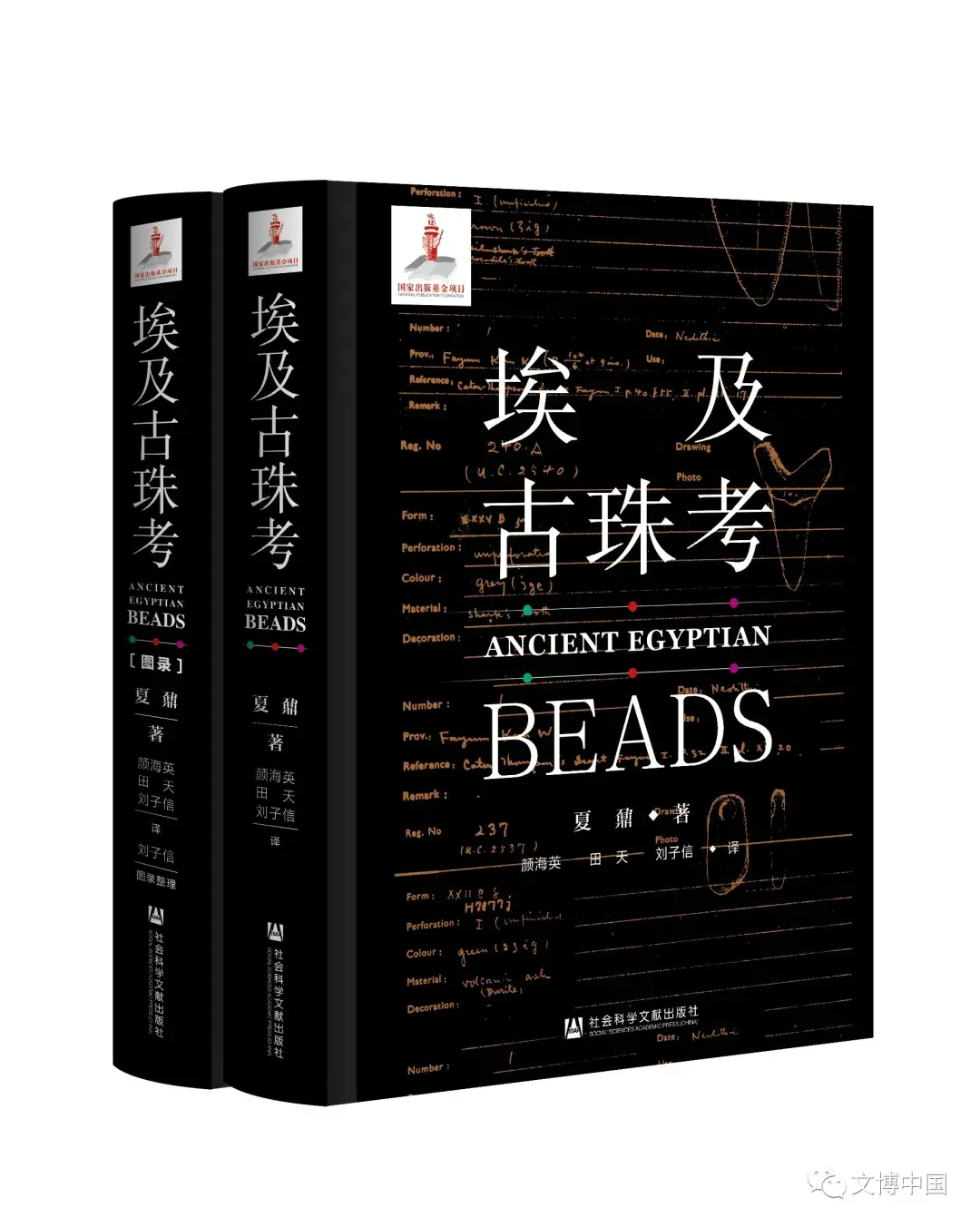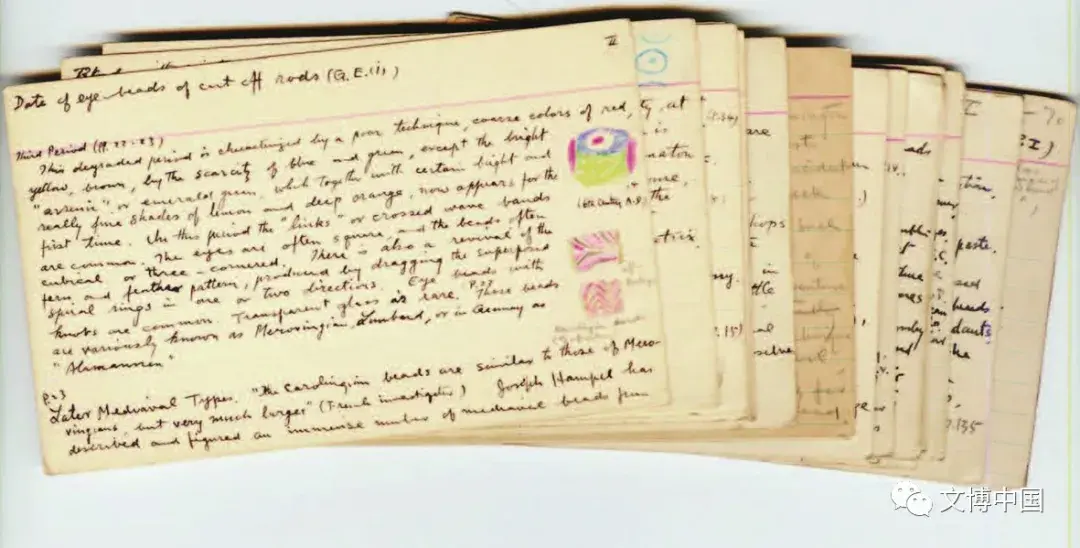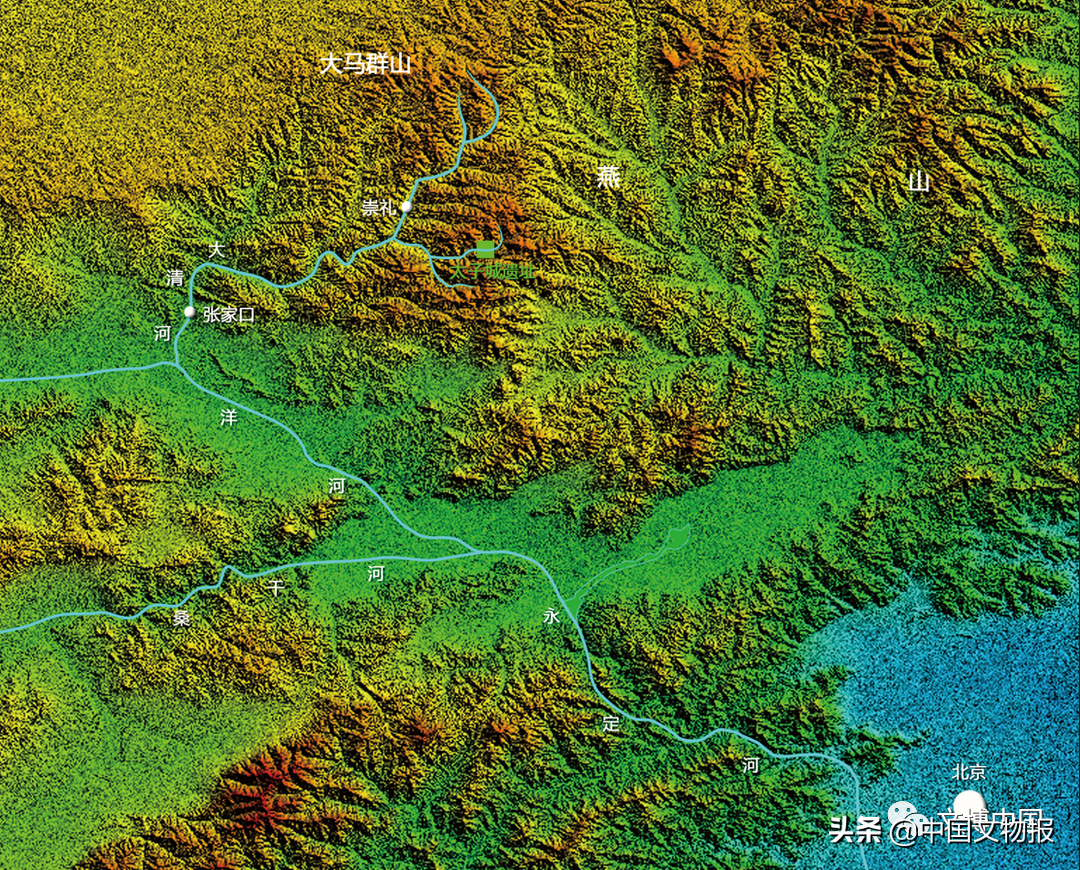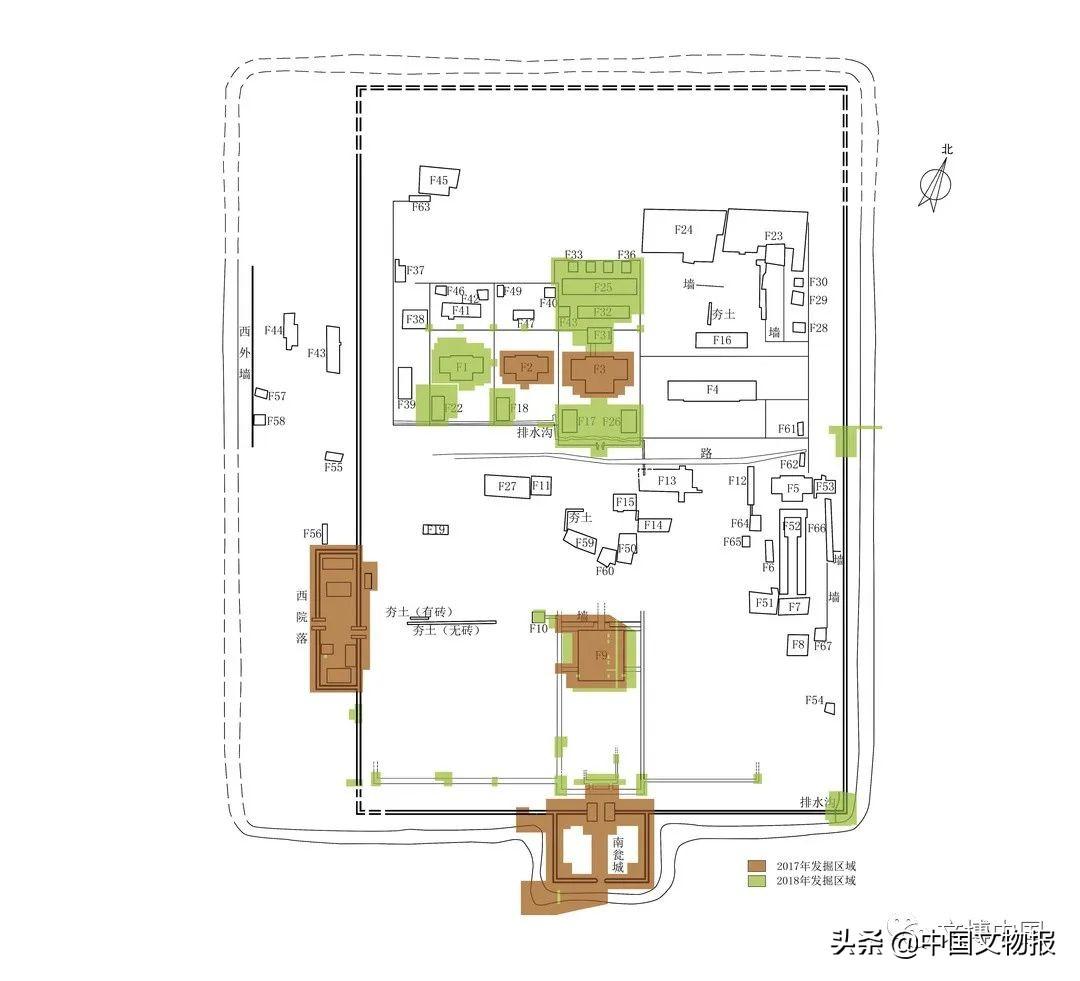王兰仲:王玉哲先生的为人与治学
父亲王玉哲是一位教师,自1943年赴华中大学任教,至上世纪末从南开大学退休,他教了一辈子书。他就像一部活的大百科全书,你仿佛总能从他那里得到你希望得到的信息,他会告诉你,这个问题顾炎武曾经谈过,并随手从书架上取出《日知录》,翻开相应的条目;或者,那个问题童书业先生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还不错。你可以找来读一下。然而今天回想起来,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从来没有一点家长作风,总是可以与他平等地讨论问题。父亲从来不要求学生遵从他的观点或学说。与之相反,他总是鼓励弟子创新,要有自己独到之处,认为任何一种新学术观点的出现,总会与传统说法不一致,甚至互相抵触。这是科学研究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或者说也是应该出现的现象。
记得1996年我去日本,顺道回国探亲时,遇到家父最年轻的弟子朱彦民先生。彦民告诉我,他在从父亲读博士时,在先商族起源地探索中提出一个新说,这与父亲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不尽相同。然而父亲不但不以此为忤,反而加以鼓励。更让彦民吃惊的是,父亲还从自己搜集的史料卡片中,挑出两条史料交给彦民说:这两条史料也许对你的观点有所帮助。父亲一向鼓励学生超越自己,坚信一代更比一代强符合自然规律。上个世纪80年代,在南开大学校学术委员会会议上,父亲告诉时任校长的母国光先生:“朱凤翰在甲骨文一些方面比我还要强。”他曾经称赞赵伯雄先生深厚的功力,说他:“《左传》烂熟!”在与杨志玖(佩之)先生谈及伯雄的训诂能力时,由衷地感叹:“我最多也就理解到这个程度。”家母曾经说过:“有状元学生,没有状元老师。”
父亲宽容的学术精神和谦和的态度,也许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父亲当年在河北省立第十中学上初中时,每一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父亲讲那时真是井底之蛙,骄傲得很。直到当他考进北平男四中高中,始知天外有天。四中的同学们都很聪明且用功,他再刻苦,也就是在班里中等水平。到了考大学的时候,父亲同宿舍六人,四个考取清华,两人考入北大,可见男四中学生平均水平之高。进了北大,他的老师、学长们皆为天才大能之辈。生活在这些聪明人中间,你想不谦虚都不行。父亲刚上大学不久,正值北大为孟森(心史)先生七十大寿庆生。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先生主持大会,诸位学术巨擘皆来庆贺。父亲说外面忽然走进一位戴眼镜、身穿长袍的长者,一进来就与孟先生互相作揖问候。父亲问一位青年助教:“这位先生是谁呀?”青年助教敬畏地告诉父亲:“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寅恪先生。”以后陈先生成了父亲同屋王永兴、汪篯先生的导师。陈先生学贯中西,人们都说他会多种语言,父亲讲这是真的。当年陈先生到图书室来,书架上放着多种语言报纸杂志,陈先生抬起眼镜从容地读读这个,又拿起另一本读读那个,父亲当时就在旁边。
父亲喜欢和我们谈他的师友。他讲头一次去上刘文典先生的课,刘先生突然指着父亲的身后,嘴里支支吾吾地说(刘先生从来都是烟不离嘴的):“你、你,你来干什么啊?我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呀。”父亲回头一看,一位年纪不算太大的学者,正冲着刘先生摆手微笑。这位先生就是沈友鼎先生。父亲讲这个人极聪明,谁的课都听,而且学什么像什么。父亲当年上罗常培先生的音韵学课,沈先生也去听。父亲讲他和其他同学还在五里云雾之中时,沈先生在课间已经与罗先生探讨很深的音韵学问题了。沈先生不拘小节,父亲读研究生时,沈先生经常到图书室借书,然后总忘了归还。最后,冯友兰先生规定他不把所有借的书还回来,不许他再借书。沈先生嗜书如命,不让他借书那可不行!于是沈先生先在图书室窗户外提前看好他想要的书的位置,趁人不备,冲进图书室,拿了那两本书就跑。父亲的师弟王达津先生(两人同为唐兰先生研究生)当时是图书室管理员,在后面就追。沈先生跑回自己的屋子,咔嚓一声把门锁了。王先生没有办法,只好到后院找来冯友兰先生。冯先生声色俱厉地说:“你马上把门开开出来,要不然,我下月扣你的工资!”沈先生吓坏了,赶紧出来,乖乖地把“拿”的两本书交还给王先生。
父亲对他的同年学长们也是推崇备至。他告诉我:李埏(幼舟)、王永兴的英语非常好,比他的英语好得多。当年父亲读西方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读不懂时,常向同屋的王永兴请教。其实父亲的英语不好也是相对而言的。当年读研究生时,李埏介绍父亲在云大附中代课(挣点外快),父亲教的就是英语。我曾经问他,为什么不教中文。父亲摇摇头说:“教中文每两周就得改一大摞作文,太费时间,相比较,改英文作文用的时间要少得多。”我想,他的英语比李先生、王先生可能差些,但也不会太差,否则那不成了误人子弟了吗?后来父亲到华中大学任教,因为一些同事就是外国人,教授会议的官方语言就是英语。开会你不能总是一言不发吧?
我曾经问父亲:“怎么听你说起来,好像每一个你的同学都比你强似的?”父亲想了想回答:“这大概是事实。他们每个人在一个或几个方面都比我强。我只是把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知识和技能,把人类学,音韵学,甲骨文等知识运用于一个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上。仅就这个具体问题研究而言,我并不比世界上任何人差。”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种在父亲身上很少看到的霸气。据说父亲在研究生答辩时,核心见解是反驳王国维先生关于鬼方、昆夷、猃狁等上古部族的考证,从而自立一新说,其论点的新颖,史料之翔实,特别是答辩时的从容与自信,给西南联大教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年暑假华中大学校长来联大招聘,好几位先生,包括清华的先生,都纷纷向他推荐家父。以至父亲毕业后一天助教也没干过,直接就被华中大学聘为副教授了。
父亲从他学术巨擘的老师们,从他的天才同学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容易使人头脑清醒。父亲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天才,不可忘乎所以。同时,他也清楚,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照走别人的路。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在别人忽略的蛛丝马迹中发现别人尚未发现的问题,有自己独到之处。这样的治学方法和态度使家父受益,所以他在多年的教书生涯中,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想把他的治学心得传授给学生。
今天我已然远离文史,但我觉得这种在别人思维中止的地方再进一步的思考问题的方法,让我受益至今。虽然史学与计算工程隔行如隔山,但从科学方法论的角度看,两者是否有些相通之处?我感觉我搞工程有自己的一些独特性,于计算机工程领域亦有几项专利发明,有些地方受益于从家父及南开的师长们学到的做学问的方法及思维方式。
先严乘鹤西去,迄今已逾八载。作为一位随时可以指导我的老师,他已经永远地离我而去。我至今后悔当年没有和父亲合作搞过一个课题的研究,合写过一篇论文。现在只能是永久地遗憾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很多东西都是这样:当捧之于手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只有当永远离你而去之后,方意识到珍贵。其实我应该感到知足,我曾经拥有过。在我的生活中,我曾经有过这样一位父亲,有过这样一个老师,最重要的,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朋友!我想,我是幸运的……
按:原文标题为《父亲是一位教师》,原载《南开大学报》2013-09-23。
- 0001
- 0001
- 0000
- 0003
- 0000